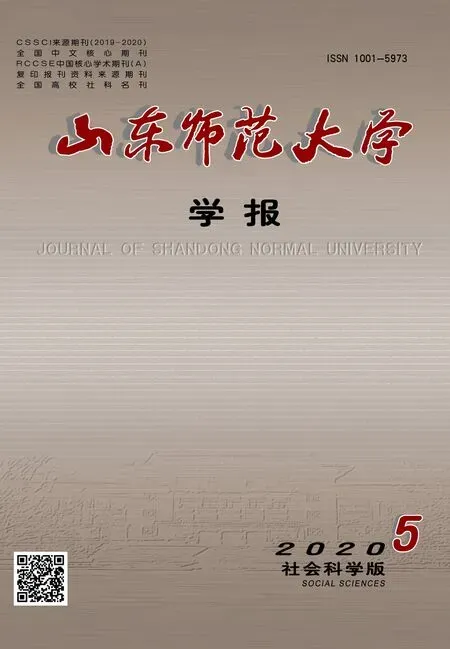中国现代文体学视野中的“型类的混杂”*①
周海波
(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266071 )
“型类的混杂”是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批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时提出的:“‘型类的混杂’亦是浪漫主义者的一大特点,例如散文写诗,小说抒情,这是文学内部型类的混杂。诗与图画同为表现情感,音乐里奏出颜色,图画里绘出声音,这是全部艺术型类的混杂。”(1)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 文学的纪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6页。梁实秋将矛头直指新文学存在的问题,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文体类型及其形态给予根本否定。梁实秋对新文学的批评自有其不可避免的偏颇与偏激之处,但同时也给予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形态的可能性。
“五四”以来新文学“型类的混杂”既是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新文学初期作家、批评家对文体认识的模糊性,是现代作家、理论家徘徊于中国古典文体与外国文体之间的矛盾,也是现代文体发展过程中的类型杂糅及其文学现代性的创作现象,是重新认识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今天来看,梁实秋对新文学的批评似有“杞人忧天”之嫌,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观念和文学创作类型早就突破了梁实秋提出的美学价值规范。尽管如此,重新提出并思考“型类的混杂”的问题,并沿着这一思路重新梳理中国现代文体形态及其特点,思考现代文学的美学走向及其文学史研究,仍然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型类的混杂”与现代文体的新秩序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写于梁实秋留学美国期间,带上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文学思想的鲜明印记。在这篇文章中,梁实秋从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矛盾关系中回望“现代中国文学”,认识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浪漫主义过了头”的特征之一就是“型类的混杂”。从梁实秋批评的“型类的混杂”的现象来看,他实际指的是小说、诗、散文等各种文体杂糅的现象,也就是现代文体类型的混杂现象,他认为新文学文体类型及其混杂是对中国文体秩序的冲击与破坏。所谓“浪漫主义过了头”就包含着不遵从文学秩序而任意作为的意思,是文学创作中的毫无节制,就是“浪漫主义者说:‘我感觉,所以我是’”。在他看来,文学应遵从常态,体现常识,“换句话说,按照古典主义者的理想,理性是应该占最高的位置”(2)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 文学的纪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4页。,但是浪漫主义者最反对常态,最不遵从常识,因而就会造成没有秩序的文体世界。这也就是梁实秋所批评的不遵守“文学的纪律”的文学现象。
“文学的纪律”是梁实秋拿来阐释“型类的混杂”的理论基础,文体类型的混杂是不守纪律的文学现象,而文学不守纪律也就是浪漫主义的表现方式,其表现形态之一就是导致“型类的混杂”。他以现代小说和诗为例,指出了新文学创作中,小说和诗是最不守纪律的两种文体。梁实秋认为,小说的文体功能本是叙事,为读者讲述故事,但新文学的小说却成为抒情的工具。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一位小说作家,但向来在小说中抒写自我、过度抒发情感的郁达夫,显然在批评之列。梁实秋批评说,“近年小说中常有把妓娼理想化”(如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沉沦》《秋柳》等),矛头直指郁达夫。此外,鲁迅、冰心、王统照、张资平等作家,也在梁实秋批评之列。在他看来,鲁迅等作家的小说显然存在着“型类的混杂”的问题。
梁实秋批评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他从遵守文学的纪律出发,试图回到文学本体,以不同文体的特质阐释现代文体的创造。但是,他在具体阐述的过程中,却并没有很好地说明小说是如何发生“型类的混杂”的,也没有指出小说抒情何以不好;同样也没有说明散文写诗,诗可以叙事有何不美,问题何在。小说的文体功能在于叙事,而不在于抒情,但小说并不是不能抒情,作家完全可以用抒情的手法进行叙事,也可以使用叙事的方式抒情。问题在于,小说如何才能真正回到小说本体,更好地实现小说文体的叙事功能。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梁秋实显然没有真正把握现代小说尤其是郁达夫为现代小说文体发展所作的贡献。就郁达夫而言,他的小说既没有过度抒情化,也没有诗化或散文化,而是努力回到小说叙事的本体,通过“一宗事件”叙述自我的生活,创造着现代小说独具形态的文体。如果就此批评郁达夫或现代小说,显然是梁实秋对现代小说文体的误读。
梁实秋所批评的“型类的混杂”现象,主要指向发展初期的新文学。新文学初期,文体概念、文体分类及其文体意识的模糊不清,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创作与批评的发展。中国文化向来讲究“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新文学“型类的混杂”是典型的名不正现象。现代文学在“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3)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的过程中,首先致力于解决文学语言的问题,在文体类型方面则在传统与西方文学的融会贯通中重建新秩序,新的文体概念、新的文体形态在新的文体秩序中越来越呈现出新的文体美学特征。与此同时,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当作家、评论家的文类意识处于混沌状态时,就会明显出现中西杂糅、古今杂糅的现象。例如,胡适的文论就存在小说概念模糊不清的问题。1918年3月15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作《论短篇小说》的讲演,第一次为新文学厘定了“短篇小说”的概念,但随后他在进一步阐述这个概念时,不仅将先秦寓言、神话传说、笔记杂记一类都视为短篇小说,而且将韵文、散文中的一些作品也视为短篇小说,打破了小说与诗、文的界限,打破了小说与散文、韵文的界限,诸如《桃花源记》《木兰辞》《上山采蘼芜》《石壕吏》等都成为胡适心目中的“短篇小说”,于是又出现了“韵文短篇小说”“散文短篇小说”“杂记短篇小说”“白话短篇小说”等杂糅的概念。1921年,张舍我就曾对胡适定义的“短篇小说”概念表示过忧虑,指出他对“短篇小说”的定义“非失之太严,即失之过宽,皆非也”。在张舍我看来,“短篇小说”在欧美文学史上也是“比较的近代之产物”,“正在生长与发达期中”,“故即欲为之立界说,亦必视为试验的物界说,而不能以之为永久不变者也”。因此,当新文学匆匆忙忙为“短篇小说”进行定义时,就出现了概念上的不清晰、文体上的混乱现象:“吾人试读今日报章杂志中之短篇小说而以严格之眼光批评之,大都不能副一短篇小说之名词也,其病在于受笔记体与杂志体、传记体等文章之毒,而与短篇小说,混为一谈。”(4)张舍我:《短篇小说泛论》,计红芳编:《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经典》,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9-60页。以此文体代替彼文体,以其他文体的特征取代短篇小说的叙事,就会出现被人们批评的短篇小说文体混杂的现象。胡适在“短篇小说”命名过程中的“型类的混杂”,恰恰就是对短篇小说文体特征认识不清而导致其对中国小说、西方小说文体概念混淆模糊偏狭的问题。
1936年,在《大公报》复刊十周年之际,《大公报·文艺副刊》组织举办了“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和编选出版《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两项重要活动。林徽因选辑的《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选录了《大公报·文艺副刊》出刊后一年多的“属于创造的短篇小说”,包括杨振声、沈从文、萧乾、李健吾、凌叔华、老舍、蹇先艾等25位作家的29篇作品。因受到副刊及其出版周期的限制,“小说选”所收录的小说“篇数并不多,人数也不多”,但是,这本规模不大的小说选,“聚在一个小小的选集里也还结实饱满,拿到手里可以使人充满喜悦的希望”(5)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天津:大公报馆,1936年,第1页。。《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于1933年9月23日,沈从文与杨振声应《大公报》之邀出任编辑。沈从文作为重要投稿人和主要编辑,为这一报纸副刊的创办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不仅负责大部分编辑事务,还在副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他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期就发表了写于青岛的《〈记丁玲女士〉跋》,随后也发表过一些散文随笔小说一类的作品。林徽因在选编《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时,除选编《过岭者》之外,又收录了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箱子岩(湘行散记之一)》《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湘行散记之一)》《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湘行散记之二)》等三篇作品。《湘行散记》是沈从文的一部游记类的散文作品集,凌宇认为,《湘行散记》“是写实纪闻,以介绍特定地域的自然与人生风貌为目的的作品”,“在文体上不拘一格,具有抒情散文、游记、小说、通讯等各种文体因素”,“是散文中的‘四不像’。……表现出沈从文在散文文体上的大胆创造”(6)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373、386页。。“散记”作为散文文体形态之一,属于写事记人的体裁,沈从文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几篇作品,也都分别以“湘行散记”为副题。林徽因之所以认同《湘行散记》的“散记”形态,并将其作品选入“小说选”中,主要从作品的艺术性考虑,看到了这些作品有故事、有人物、有描写、有叙事。正如胡适把《桃花源记》《石壕吏》等作为小说看待,是将作品中的小说因素等同于小说文体了。
实际上,林徽因及京派作家大多是文体意识尤其是文体类型意识并不很强的作家。这部“小说选”不仅表现出了林徽因对沈从文作品的偏爱与关注,还说明了她对编选作品的文体判断及其美学取向。从《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可以看到,林徽因对这部“小说选”的文体类型并不是特别关心。她在这篇“题记”中,除题目和开始部分使用了“小说”“短篇小说”的概念外,其他地方几乎没再使用过“小说”一词,而是使用了“这部选集”或者“短篇”。这两个概念在这里都有具体所指,即“小说选”与“小说”文体。结合林徽因在其他著述中所使用的文体概念,则可以看到她的文体类型的意识比较复杂,甚至带有混沌的特点。1933年,林徽因在致沈从文的信中,使用过“文章”“韵文”“短篇”等概念,这几个概念中的“韵文”指的是诗,而“文章”和“短篇”则泛指文学作品或其他文体。“萧先生文章甚有味”是指萧乾的短篇小说《蚕》,“关于云冈现状是我正在写的一短篇”(7)林徽因:《致沈从文》,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30页。,应该是指她与梁思成等完成的一篇题为《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的调研报告。从这些有限的材料可以看出,林徽因的文体观念主要限于诗与文学,而缺少具体明晰的类型特征。正因如此,在编选《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时,林徽因虽然考虑到了选集的“小说性”,却没有严格按照小说文体的要求选择作品。林徽因将沈从文的这几篇“散记”收录于“小说选”中,没有进行必要的说明,但从她在《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一文所表达的文学思想中,可以侧面地看到其编选理由。林徽因在表达她选编这部小说集的想法时说,除了“对题材的偏向以外”,主要考虑作品的艺术创造,“在描写上,我们感到大多数所取的方式是写一段故事,或以一两人物为中心,或以某地方一桩事发生的始末为主干,单纯的发展与结束”。林徽因也指出了“小说选”中不少作品在艺术创造方面的薄弱,既是“误会了短篇的限制”,也是作家对“生活大胆的断面”,“少有人尝试,剖示贴己生活的矛盾也无多少人认真的来做”(8)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天津:大公报馆,1936年,第2-3页。。如果说林徽因编选“小说集”并不特别看重小说文体特征的话,那么,她更在意的是作品艺术描写上的“一段故事”“一两人物”“某一地方一桩事发生的始末”,看重具有小说叙事的基本要素,或者一定的故事性。实际上,林徽因已经意识到作为报纸副刊在承载作品文体上的局限性,意识到副刊小说文体在描写上的特点,只不过由于京派作家在文类上的随意性而并不特别讲究而已。
这里并不是说林徽因不讲究文体,不注重文体分类,而是指林徽因及京派作家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对文体及其文体类型的独特理解。林徽因以西方诗学体系为中心,在文体观念中,除了诗之外,将散文、小说等文体混合一起,不分彼此。这种现象也反映了相当长一个时期人们对现代文体认识的矛盾心理。随着现代文体类型分类方法的变化,人们既想否认这种“型类的混杂”现象,又试图以更加清晰的文体命名解决这些跨界文体的问题,于是,“小说化散文”“散文化小说”“诗化小说”“诗剧”等概念应运而生。1936年《学风》杂志第6卷第6期发表书评,对《湘行散记》的评价就在散文与小说之间游移不定,《湘行散记》“形式上好像是一部纪游的作品,实际上却是包含十一个短篇小说!不过也可以当作游记来看,因为他所写作的范围就是他回湘时所经历的一切。这十一篇东西可以连贯着读,也可以分开来读,而且其中有几篇已在别的刊物上发表过了。”这种认为沈从文“是以小说体裁写游记,以游记体裁写小说的”,“所以当游记读可,当小说读也可”(9)芸非:《书报评介·湘行散记》,《学风》1936年第6卷第6期。的观念反映出作者对《湘行散记》文体类型认识的矛盾。从文体类型来说,《湘行散记》已经超越了游记的文体范畴,作品的记“游”的因素让位于所记“湘行”的人情风物,或者说,作家不是以“游”的方式叙述湘西,而是在湘西特定的地域内叙述风景、风物与人物,有个人的回忆,有故事的叙述,也有人物的描写。所以,作家以“散记”名之,从文体概念和文体类型等方面说,是再恰当不过的。
现代文学“型类的混杂”也突出地表现在新诗文体方面。例如,郭沫若的《女神》是以“剧曲诗歌集”的文体形式出版的,这种清晰而具体的文体已经表明它不是一部纯粹的诗集,而是包含着两种文体在内的“剧曲”和“诗歌”集。但包括郭沫若本人在内,对这部作品的文体认识却相当笼统与模糊。郭沫若在《民铎》杂志发表《女神之再生》时,曾有“附白”,表明“此剧取材于”《列子·汤问篇》《说文》《山海经·西次三经》等,同时又在“书后”中说,“此剧已成于正月初旬,初为散文;继蒙郑伯奇、成仿吾、郁达夫三君赐以种种助言,余竟大加改创,始成为诗剧之形。就中郁达夫君读余散文旧稿时,赠余一诗,余尤得其暗示不少”(10)郭沫若:《女神之再生·书后》,《民铎》1921年第2卷第5号。。1921年8月《女神》出版,郭沫若在《女神之再生》标题下用括号注明“诗剧”。同一作品,郭沫若使用了“剧”“诗剧”“散文”三种文体命名,可见作者本人的文体类型认识比较模糊。如果说《女神之再生》因其文体形态可以视为“诗剧”的话,那么,“女神三部曲”中的《湘累》《棠棣之花》则与《女神之再生》不同,无论作品的表现形式还是命名,就只能属于“剧曲”,但在一些文学史以及《女神》研究中仍然被认为都属于“诗剧”文体。如楼栖就认为《女神》“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女神三部曲”就是“表现神话或历史主题的诗剧”(11)楼栖:《论郭沫若的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9页。,桑逢康也认为“《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歌集”(12)桑逢康:《〈女神〉汇校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其他如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都采用了《女神》为“诗集”或“新诗集”的文体概念。这些观点并无明显的问题,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女神》的文体学意义。一般来说,“剧曲”是戏剧与杂曲的合称,徐慕云认为,“中国现有之歌舞艺术,除欧化之新剧,有声电影,以及黎锦晖氏所独创之半欧化歌舞而外,约分戏剧与杂曲两大部门”(13)徐慕云:《改良剧曲刍议》,《文化建设月刊》1936年第2卷第5期。。也有以“戏曲”等同于“剧曲”者,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将戏剧、戏曲统用,戏剧的意义在于“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因此,“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14)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3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7页。。也就是说,剧曲既突出了“剧”的言语对话性,也呈现了歌唱的音乐律动性。剧突出了文体的叙事性,曲则强调了文体的抒情性,前者与小说相关,后者与诗相连。“女神三部曲”在文体上并不一致,《女神之再生》受歌德《浮士德》的影响而呈现诗剧的特点,《湘累》《棠棣之花》整合西洋话剧和传统杂曲的艺术手法,创造出既有现代特质而又合乎民族审美要求的体式。但郭沫若将不同文体的剧曲与诗歌合为一集,又表现出“郭沫若对于自己创作的‘剧曲’,在文体归属上也存在认知的混沌性”,是新文学初创时期跨文体的表现。实际上,《女神》研究中“忽略了这本作品集中有至少三篇剧作的事实,更忽略了‘剧曲’与‘诗歌’搀杂的别样意味”(15)周维东:《论“剧曲”之于〈女神〉的意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二、“型类的混杂”与现代文体功能探寻
梁实秋在批评“型类的混杂”时,还特别指出了文体创造过程中的内部混杂:“小说本来的任务是叙述一个故事,但自浪漫主义得势以来,韵文和散文实际上等于结了婚,诗和小说很难分开,文学的型类完全混乱,很少有人维持小说的本务。现今中国小说,什九就没有故事可说,里面没有布局,也没有人物描写,只是一些零碎的感想和印象。散文往往是很美丽的,但你很难说他是小说。”(16)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 文学的纪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9-20页。梁实秋的批评主要针对现代小说,但不仅仅限于小说,也包括了诗歌、散文甚至戏剧等文体。
梁实秋的用意主要在于从文学本体出发寻找“顶好的”文学。所谓“顶好的”文学,就是他心目中的古典文学。在梁实秋的观念中,所谓古典文学并不一定是古代的文学,而是具有古典美学形态的文学。对此,他引述哈克敦的论述说:“一切文学的作品,无论是描写人物或是建筑格局,各型类均各有其确定不移的形式完美的规律。守此规律的即为适当;否则失败。”(17)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浪漫的与古典的 文学的纪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11页。也就是说,古典文学拥有一定的艺术手段,诸如描写人物或讲究建筑格局等,同时具有一种规定性,呈现着“最好的”文学的美学特征。但是,当文体功能出现混乱状态时,文学的文体美学特征就会受到影响。而当新文学整体上出现文体的混杂时,作家的文体类型意识薄弱,概念混杂,从而会导致现代文学在文体类型方面的模糊不清,在文体功能上出现位移的非正常现象。
梁实秋对郁达夫等作家小说创作的批评,就是着眼于小说文体功能,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何看待郁达夫的小说,郁达夫为现代小说提供了什么艺术经验,抒情小说、散文化小说等概念是否可以概括现代小说的某些文体类型,都是郁达夫研究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未解之谜。梁实秋站在古典主义的文学立场上批评郁达夫,自有其一定的道理,却不能很好地理解郁达夫。简单地从古典主义的立场出发把郁达夫归为浪漫主义作家,或如茅盾、陈西滢、苏雪林等作家批评的那样,认为郁达夫的小说在结构上存在缺陷,不讲究小说结构,或如文学史家那样概括为“抒情小说”“散文化小说”,都没有真正接近郁达夫小说的文体形态,而片面地理解了郁达夫小说的抒情性特征。实际上,梁实秋批评小说抒情,是从小说的文体形态与文体功能的角度阐释文学的纪律。小说就是小说,应当具有小说文体的基本特征,“有纪律的形式,正是守纪律的精神之最具体的表现”,所以,在梁实秋看来,“形式的意义,不在于一首诗要写做多少行,每行若干字,平仄韵律等等,这全是末节,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其真正之意义乃在于使文学的思想,挟着强烈的情感丰富的想象,使其注入一个严谨的模型,使其成为一有生机的整体”(18)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浪漫的与古典的 文学的纪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24页。。诗是抒情的,小说是叙事的,这是文体的基本属性,如果打破了这种“纪律的形式”,文学也就随之失去了“文学的精神”,这是型类的混杂,是现代文学文体功能的紊乱。郁达夫是坚持小说重在“具体的描写”观点的作家,在他看来,“小说的生命,是在小说中事实的逼真”,而小说的结构则与小说所叙述的“一宗事件有关系”(19)郁达夫:《小说论》,《郁达夫文集》(第5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17、21页。。他反对那种“说带哲理的空话”(20)郁达夫:《读〈兰生弟的日记〉》,《郁达夫文集》(第5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245页。,认为只有在真实的事实描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创造出合乎小说文体的艺术结构。从这个角度来看,郁达夫并不是主张小说的文体功能是抒情,而是强调小说要讲述自我个人的生活事实或描写社会的“一宗事件”。他早期的《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以及后期的《迷羊》《迟桂花》等,多以作家本人所经历过的“一宗事件”为叙事主体。正如锦明所说,郁达夫的小说在《沉沦》时期,“拿他的生活作依据,创造一种普遍的意义相冲突——灵肉的冲突”,在“自我表显的时期中”,“大半是个人生活的记录”,在“蜕变时期”,“他开始了那纯想象的创造”,以《过去》为代表的小说,“篇中的内容已充实了,艺术已精炼了”(21)锦明:《达夫的三时期》,《一般》1927年第3卷第1期。。也可以说,郁达夫的小说是一种客观的叙事,多以事实的叙述为主,尽管这些事件具有“自叙传”特征,是个人私生活的书写,但仍然是“事实的”描写。也就是说,郁达夫以独具特色的叙事方式,成就了现代小说文体艺术,为现代小说创造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代诗歌文体功能的混杂可能是最为典型、最为突出的。这里不仅具有“诗”与“诗歌”概念的混杂,也存在着诗歌本身的文体功能问题。“白话诗”“口语诗”“新诗”“诗”与“诗歌”概念的混杂,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相关文体的认识,改变了诗与诗歌的文体美学特征。
1923年,诗人徐志摩在《努力周报》第51期发表《杂记(坏诗,假诗,形似诗)》,提出“到底什么是诗”的问题,认为“诗也有真诗、坏诗、假诗、形似诗”。徐志摩在文章中还谈到胡适说过的“笑话”:“我的‘尝试’诗体也是作孽不浅,不过我这一派,诗坏是无可讳言的,但总还不至于作伪;他们解决了自己情绪的冲突,一行一行直直白白的写了出来,老老实实的送到报上去登了出来,自己觉得很舒服很满意了,但他们却没有顾念到读他们诗的人舒服不舒服,满意不满意。但总还好,他们至少是诚实的。”(22)徐志摩:《杂记·坏诗,假诗,形似诗》,《努力周报》1923年第51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徐志摩对“好诗,坏诗,形似诗”的区别。这是徐志摩站在他的新诗立场上的审美判断,符合其诗的美学主张和原则的当然就是好诗,而其他的则被视为“坏诗,假诗,形似诗”。实际上,当我们从“型类的混杂”的角度看待“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诗与诗歌的话,对此可能会有另外的认识。这一点从新月诗派诗人、批评家如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对待郭沫若《女神》的评价和态度就可看得出来。向来看不起“五四”以来白话新诗的“新月派”同人,却对郭沫若的《女神》一致好评,称赞《女神》的神思幻想。而对于胡适提倡的白话新诗以及“小诗”等文体类型,则大多持否定态度。在“新月诗派”看来,《女神》是“诗”,胡适的《尝试集》是“尝试体”的白话诗,而早期诗人如朱自清、冰心等人的作品则只能是“新诗”。这些都冠之以“诗”的名义出现的文体,却不一定都是诗,而有可能只是“形似诗”,甚至是“坏诗”。
对于现代文学而言,诗是最能体现“型类的混杂”文体特点的。一方面,现代文学中的诗歌与诗的概念往往混杂使用,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文体概念。另一方面,诗与诗歌在概念内涵与外延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的文体概念交叉混用,从而遮蔽了诗在现代文体发展中的意义。胡适在提倡“文学革命”时一般提及古典诗词,多以“诗”“词”或者“旧诗”等概念为主,而论述新文学时则主要以“白话诗”“新诗”等概念为主。早期胡适为了证明白话能够作诗,提倡“诗体的大解放”,以“尝试”体式写出了《尝试集》中的作品。对此,胡适本人大多以“白话诗”或者“新诗”概括。1917年他在《新青年》发表其作品时,也以《白话诗八首》为题。郭沫若在《凫进文艺的新潮》中说,他“偶然地写过一些口语形态的诗。象《死的诱惑》一诗便是在一九一八年的春间做的”,“副刊里面时时登载一些白话诗”,“我便把我以前做过的一些口语形态的诗……抄寄去投稿”。胡适有意识地将“白话诗”“新诗”区别于“诗”,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文体概念。郭沫若使用“口语形态的诗”时,明确将其与诗进行区别,“新诗”则是介于“口语诗”与诗之间的一种文体。及至“诗歌”概念的出现并被人们广泛使用时,由诗向诗歌的文体转化已经完成。从“诗”到“诗歌”,不仅仅是概念的变化,本质上则是诗的文体形态与性质的转化。1922年,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发起了猛烈攻击,首先批评的就是《尝试集》,认为《尝试集》“形式精神,皆无可取”(23)胡先骕:《评〈尝试集〉》,《学衡》1922年第1期。,更不承认它是诗。实际上,“学衡派”“新月诗派”等使用的“诗”和胡适等人使用的“白话诗”“新诗”概念具有不同的文体特征,甚至不是指同一类型的诗体。学衡派或新月派提倡的“诗”更多接近于西洋诗,是一种贵族化的诗体,而“白话诗”“新诗”等现代诗歌则是在中国文化与文学大众化、平民化的过程中发生的变体,是趋向于平民化大众化的文体。
三、“型类的混杂”与现代文体新变
深受欧美文化影响的梁实秋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型类的混杂”是现代文体变异的重大突破,不能理解现代文体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守常与变异的这一既旧又新的问题。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24)刘勰:《文心雕龙》,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5页。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文学体式遵从古代承传的制式,符合礼制的规范,才有可能求得新的变化。在刘勰那里,他所遵循的规范就是“必征于圣”,只有明晓了圣人的旨意和做法,才能辨明事物并获得雅正的言辞。也就是说,无论文体如何变化,都不可能脱离圣人的经典著述,无论文章如何写作,都是在传统文体体制制约下形成的。“据事制范”是文体范式的制订,也是对后世文体的规范,而后世所立之体,又是在传统所制规范中完成的。在刘勰这里,体与经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由《礼》而立,制订了各种规范,后来的文体无论怎样变化,都不可能真正离开“宗经”这一宗旨。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就是要“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25)刘勰:《文心雕龙》,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76页。,对于经典著作的文体,首先要追溯它们的本源,才能够考察其流变,对不同的文体概念,先解释清楚它们的名称来历,才能够说清楚文体的内涵及其特征。这里所指就是文体的常与变,考释本原,梳理流变,这是文体学的要旨,也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对此,王国维作过更具现代性的阐释:“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也。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26)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1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7页。王国维没有说明帝王派与非帝王派的关系,但他对这两大派别的梳理中,隐含了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两大派别在不能调和中互为存在。王国维是一位追求文学现代性的学者、诗人,他的追求是建立在对传统皈依的基础上。一部《人间词话》是对中国词学的总结性批评,以“词话”这一古典的批评体式,陈述“境界”这一古典文学的重要命题,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批评方法,以古典阐释现代,以现代证实古典。在文体类型方面,王国维并没有特别坚持古典形态的文学,对于小说、诗歌、戏曲等文体,他都有比较中肯的评价。他的《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等批评著述,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理想中的文学,《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则从理论角度论述了“古雅”与中国文学文体形态的内在关系,特别强调了形式在艺术表现中的重要地位。在这方面,英国批评家贝尔在《艺术》一书中提出过“有意味的形式”,认为艺术表达的东西是他的感情,而感情的表达则是在一定的形式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当作家艺术家通过形式表达感情时,形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家艺术家必须遵循一定的艺术形式。而形式的存在,“对于创作它的艺术家而言,则意味着对某个概念的完全认识和对某个问题完美的解答”(27)[英]克莱夫·贝尔:《艺术》,马钟元、周金环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第38-39页。。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形式,需要在正确的形式中进行创造。在这方面,贝尔的理论恰恰印证了王国维美学思想,“有意味的形式”与“古雅”具有同样的美学意义,一定的文体形态展示了审美境界,是文体形态的理想,是文体美学上的最高境界。
从文学发展史来看,文体在不断的变异中求发展,没有变异,就没有发展,文体发展既是文体的不断成熟与丰满,也是文体的变化与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说,文体的创新就是变异,就是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创新再造。艾略特曾对传统与创新有过论述:“当一件新的艺术品被创作出来时,一切早于它的艺术品都同时受到了某种影响。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艺术品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这个完美体系就会发生一些修改。”(28)[英]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页。由此来看,“五四”新文学形成之后,原来完整的中国文学体系受到巨大冲击,传统的文体也受到新的媒体、新的作品的挑战。这时,文学艺术以不断的创新,传承人类文化的传统,将传统的美学形态与精神通过创新的文体形态呈现出来。人类早期以及新的文学形态出现时,文体类型往往是混沌的,是多种文体杂糅的。因此,过于强调文体分类,突出“型类的混杂”对文学的制约,并不利于文学的发展。梁启超提倡“新小说”“新文体”“新诗”是在对中国文化传统深刻研究的基础上向现代的突破。梁启超通过“新小说”文体,借小说家的言论,“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实现其“新民”的社会理想。但是,什么是“新小说”,或者什么是梁启超心目中的理想小说,他本人并没有明确的阐述。通过梁启超及其同人的相关论述,可以大体看到,梁启超心目中的理想文体应是具有词章之学的古典文章风范的文体。平子就认为,“小说与经传有互相补救之功用。故凡东西之圣人,东西之才子,怀悲悯,抱冤愤,于是著为经传,发为诗骚,或托之寓言,或寄之词曲,其用心不同,其能移易人心,改良社会”(29)平子:《小说丛话》,《新小说》1903年第8号。文中标点为作者所加。。可见,平子所认为的理想小说也应与经传、诗骚等文体具有相通之处,能够移人心、改良社会。与此同时,林纾翻译外国小说,也以词章之学作为翻译小说的审美理想。他一方面反对言必称古,“嗜古如命”,一方面又惊叹“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30)林纾:《〈斐洲烟水愁城录〉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8页。。钱玄同曾指出梁启超的政论等文章“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31)钱玄同:《通信·寄陈独秀》,《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1号。的问题。从梁启超的“新小说”,到林纾的“林译小说”,形成了中国现代小说两类不同的文体,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等类型化小说作家,以欧美小说为模仿,结合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特征,形成了“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的文体,这种文体融合了“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32)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1902年第1号。文中标点为作者所加。文体要素,形成了跨文体的写作。而林纾的翻译小说,则以欧美小说创作为译本,同时又结合了中国古典文体的要素,如他在翻译《黑奴吁天录》时,就看到了此作品“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与其说他“就其原文,易以华语”(33)林纾:《〈黑奴吁天录〉例言》,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3页。,不如说林纾以古典的词章之法和语言方式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以古典文体成就了外国文学的翻译。无论梁启超还是林纾,在其小说创作或翻译中,都误解了小说文体,当然这是一种美好的误解。当梁启超将小说作为宣传工具,将大量的议论、演说、论述嵌入小说之中时,林纾却努力将西洋小说中国化,以文章之义法赋予小说以古典的涵义。梁林二人以不同的方式,走向了现代文体的不同道路,为中国现代文学“型类的混杂”各自开启了不同的大门。
在新的文化环境和社会诉求以及新的美学原则下,中国传统文体如何在“宗经”中变异,现代文体如何更好地适应读者的需要,满足新的阅读群体的审美需求,这里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而且也包括诗与文章的文体形态,新的形态与新的表现方式是否能够适应新的媒体、新的文化,都需要新文学家给予必要的回答。钱玄同说过,《尝试集》“用现代的白话达适之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用古语,不抄袭前人诗里说过的话”,“的确当得起‘新文学’这个名词”(34)钱玄同:《〈尝试集〉序》,欧阳哲主编:《胡适文集》(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7页。。而谦逊的胡适却认为,他的“尝试”“因为没有积极的帮助,故这一年的诗,无论怎样大胆,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35)胡适:《〈尝试集〉自序》,欧阳哲主编:《胡适文集》(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0页。。不仅如此,同时期的沈尹默、刘大白、康白情等人的白话新诗,大多在“新”与“旧”两者之间摇摆,没有形成新诗形态的稳定状态。
散文是文体概念最为复杂并且最晚获得相应文体命名的一种现代文体。一般来说,现代散文与古代文章具有密切的关系,但如果说古代文章演变成为现代散文,在文体发展脉络上是不成立的。即如被周作人等特别强调过的晚明小品,在文体特征上与五四以后的小品文、随笔、杂感等也相去甚远。从文体创造的角度来看,现代散文与现代兴起的报纸杂志的文体存在一定的联系,也与外国小品随笔具有一定的关系。从文体类型方面看,美文、小品文、随笔、随感、杂感、散记、笔记、札记、游记,等等,都被纳入到散文文体中,甚至报告文学、速写一类的文体也被归于散文之中。现代散文在“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之间摇摆,无法真正形成稳定的文体特征。而在文体内部,散文文体的功能比较模糊不清,它兼具叙事、抒情的功能,但叙事与抒情都不是散文真正的文体功能,散文的叙事与小说不同,散文家叙述的故事很难进入小说家的视野,而散文的抒情更无法与诗歌相提并论。不过,现代散文的魅力也正在于文体边界的模糊,有一定的故事和人物,有抒情和议论,理性与情感融合,在报纸期刊等现代传媒载体的语境中,散文文体的跨界与破界成就了散文不同文类的审美特征。鲁迅称自己的杂感类作品为随笔、短评等,周作人称他的散文写作是在“自己的园地”里的劳作,沈从文称他的散文是“情绪的体操”,属于精神与情感方面的文体,呈现出了现代散文文体的美学变化。
文体边界的混沌状态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同文体相互融合的现象之一。与中国古代文学相比,在报纸期刊等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不仅具有传播的开放性,而且文体边界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特征。这种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体边界的开放性。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中就说过:“我们主张新文学,自然也得借径于西洋的新文学。……只可惜我们历史上的白话产品,太少又太坏,不够我们做白话文的凭藉物。”所以,新文学的建设需要借鉴并引进外国文学的文体经验,“直用西洋的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36)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1919年第1卷第2号。等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周作人提倡的“美文”、王统照提倡的“纯散文”、胡梦华建议的“絮语散文”等,就是借鉴了外国文学的文体概念,“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37)周作人:《美文》,止庵校订:《谈虎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页。。在新诗创作方面,梁实秋认为“外国影响足使中国文学改换一个新工具”,因此,“五四”以来的“新诗就是外国式的诗”,“是‘十四行体’,‘排句体’,‘颂赞体’,‘巢塞体’,‘斯宾塞体’,‘三行连锁体’,大多数采用的‘自由诗体’”,“在新诗的体裁方面很明显的露出外国的影响”(38)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8-9页。。二是文体内部边界的开放性。梁实秋在批评“五四”以来新文学“型类的混杂”时,特别指出了“散文写诗,小说抒情”的文体内部的混杂现象,这是文体边界开放的现象。现代文学所处的文化环境,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社会,报刊媒体的崛起为社会提供了开放式的平台,而文化沙龙一类的公共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开放式的场所。在这样的空间里,诗歌、散文、小说各种文体共处,都有可能在一个杂志、一个栏目中出现,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借鉴,促成不同文体试图寻找另类的表达方式。1921年1月《小说月报》改刊出版时,主要栏目分为“创作”“译丛”和“海外文坛消息”,文学批评或论文以单独的题目与上述三个栏目并列,“创作”和“译丛”栏目包括各种文体如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所有作品没有文体之分。自1922年第13卷第1号开始,栏目分类发生变化,“短篇及长篇小说”“诗歌及戏剧”“文学家研究”“海外文坛消息”“读者文坛”等,第13卷第7号开始将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分开栏目发表。1923年1月,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后,多以混杂编排为主,不再明确分栏发表作品。这种分类或混合编排出刊的方式,虽然不能完全说明编辑者的文体意识,但从一个方面表现出现代报刊与文体混杂的关系,也反映了不同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现象。
文体的守正与出奇是坚持文学的古典形态与美学原则,还是寻求新的文学形态与美学原则,这是文体美学原则的重要分野。古典形态的文学文体往往坚守了文学一贯的美学原则,是贵族的、古典的,新的文体形态则是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的美学突破,是写实的、社会的、平民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西文化大碰撞、大融合背景下的一次现代转型,同时也是在报纸期刊为主体的现代传媒出现并成为现代社会重要传播方式之后的美学变形。“型类的混杂”并不完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天性缺陷,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形成时期中国传统文体形态与西方文体观念冲突融合在创作中的表现,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文体新变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