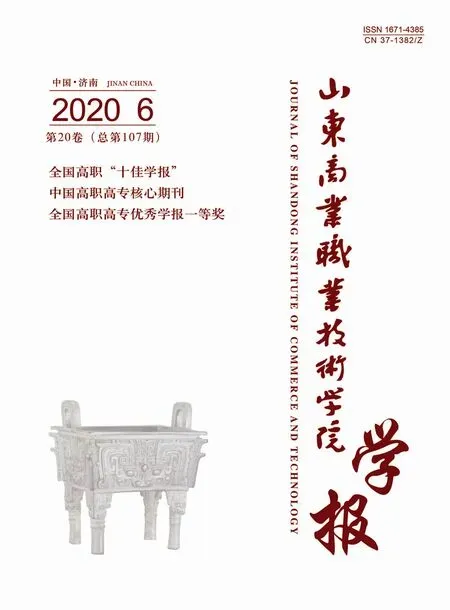现实的绝望和精神的觉醒
——汉乐府苦难家庭诗歌中的人生困境与意识突破
孙峻旭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汉乐府是继《诗经》《楚辞》之后,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灿烂篇章,“乐府之丰富了汉代诗歌,简直是使荒漠变成了花园”[1],它也以其饱满的现实主义精神为两汉文学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一、汉乐府苦难家庭诗歌
汉乐府具有很强的写实性,《汉书·艺文志》提出汉乐府“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即是说汉乐府都是创作者感于现实中的悲与欢,于生活中的具体事件而创作出来的。在汉乐府中,有一类以苦难之家为描写对象的诗歌,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和《十五从军征》等,就充分体现了汉乐府的现实色彩。《东门行》写的是一个男子为贫穷所迫,不听其妻劝阻,愤而“拔剑”反抗的悲慨故事;《妇病行》写的是一个穷苦家庭妻子病故,舍下丈夫幼儿的凄惨景象;《孤儿行》写的是一个孤儿在父母亡故之后受兄嫂虐待的悲苦命运;《十五从军征》写的是一个老兵少小从军、暮年归家却又无家可依的苦难归宿。
对于这一类诗歌,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悲惨主题表现、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手法运用、联系社会背景考察此类诗歌的成因等方面。本文试图以上述四首诗为例,从人生困境和意识突破两个角度对汉乐府苦难家庭诗歌进行深度分析,藉此进一步探讨汉乐府对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意义。
二、汉乐府苦难家庭诗歌中的人生困境
首先是异常窘迫的生活困境。这四首诗都非常关注主人公的衣和食。《东门行》中男主人公面对的是“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妇病行》中病妇嘱托丈夫“莫我儿饥且寒”,而她的孩子却是“抱时无衣,襦复无里”;《孤儿行》中的孤儿不但“足下无菲”,而且“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十五从军征》中的老兵从军多年却无饷银积蓄,回家之后做饭用的是院子里生的野谷,煮汤用的是井台边长的野葵。衣食充足是人生存下去的基本保障,缺衣少食的饥寒生活大概是人最绵长的痛苦。四首诗的主人公们几乎都处在缺衣少食甚至无衣无食的异常窘迫的困境状态,免于饥寒就成了他们的奢望,无怪乎有人要造反,有人内心满是绝望。对于这几首诗所表现的生活贫困已有较多论述,本文不再多做分析。
其次是无处安放的生命困境。基本生活资料的极度匮乏影响的不仅仅是生活质量,在这几首诗歌的情境里,它已严重威胁到了个人的生命,这在前三首诗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孤儿行》中,孤儿原本的家庭是比较富裕的,但其父母亡故之后,因为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制度,一家之主的地位和家庭财产全由其兄长继承,再加上兄嫂的专横和凌虐,孤儿失去了原有的庇护和幸福,成了一名有家的“孤儿”,过着如奴婢一般的生活。他不但要常年走南闯北为兄嫂做买卖,年底回到家还要做饭、喂马,劳累不堪。寒冬腊月还要远出汲水,他没有鞋子,只好光着脚走在满是蒺藜的霜地之上。在兄嫂眼里他毫无地位,有苦却不敢言,时常泪如雨下,无法忍受的血泪生活把他推向了生不如死的境地。《东门行》中,男主人公因无米无衣的生活断然拔剑出门之时,面对妻子的苦苦劝说,他告诉妻子:我的头发都白了,而且常常掉落,活不久啦!于是决然而去!我们无法猜测男主人公要做的究竟是什么事情,结局又是如何,但我们知道生存已将他逼迫得不惜以命相搏。《妇病行》则让我们直接看到了生命的死亡。诗中对病妇的刻画极其生动。已被病痛折磨多年的她偃卧病榻之上,她自己知道将不久于人世,于是要给丈夫留下遗言,要说还未说,眼泪却先“翩翩”落下,她交待丈夫不要让孩子饥寒、不要打骂孩子,充满了对孩子的爱怜和不舍,但无情的病魔还是夺走了她的生命。面对妻子的亡故,丈夫守在床前却无能为力,这该是怎样的一种撕心裂肺的苦痛!在这三首诗的描述中,劳累、凌虐、饥寒、疾病是贫苦之人无法摆脱的,都是逼迫他们走向死亡境地或已致人死亡的原因,主人公们深切感受到了生命无处安放的悲哀。然而更深一层的思考在于,个人不得保全,家庭又该如何存续?支离破碎乃至于完全消逝是苦难家庭的必然结局。
最后是孤苦绝望的心灵困境。比肉体生命层次更高的当是人的心灵,在肉体时时面临死亡之时,心灵所承受、体味的凄苦悲凉是最深和最重的。《妇病行》大概描摹出了最令人泪目的情节:丈夫在妻子死后,“闭门塞牖”,要到集市上给留在家里的孩子买食物。而当他在路上碰到亲交,便悲痛地“泣坐不能起”,他央求亲交帮他买食物,自己则返家照看孩子。当他推开门,当孩子们看到父亲回来,人世间最富哀情的场景出现了——年幼的孩子们尚不明白他们的母亲已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仍在向着父亲“啼索其母抱”!他不知该如何作答,只好“徘徊空舍中”!也许他会捶胸顿足,也许他会嚎啕大哭,也许他会不断地喊着:“天哪!天哪!”面对需要独自抚养的孩子,面对孩子即将如他们的母亲一般死去,这位丈夫所感受到的是来自心灵的绝望,这种绝望是痛失妻子、独立难支、不知如何生活的孤苦无依。《孤儿行》同样描写了一个血泪情节:孤儿推着收来的一车瓜回家,可不曾想瓜车翻了,帮他捡瓜的人少,趁机吃瓜的人却很多。孤儿只好祈求众人吃完瓜将瓜蒂归还,只因兄嫂太过严厉,怕是计较起来没完没了!而当兄嫂得知瓜车翻覆,果然对孤儿叫骂不止!当此之时,孤儿想到了黄泉之下的父母,他想给他们写一封信,告诉他们“兄嫂难与久居”!孤儿内心凄怆,“居生不乐”“命独当苦”,也许他永远不能理解一母同胞的兄长为何如此刻薄无情地对待他,当他觉得“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时,他的心灵同样是绝望的,这种绝望是没有父母、没有庇佑、有亲实如无亲的孤苦无依。漫长的从军生涯已让《十五从军征》里的老兵凄苦不堪,在无数次的死里逃生之后,他终于回到了家,然而,他的家里“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家人一个都没有了,家也没有了!远征思亲,当他终于能够回家,最渴望的便是兴奋地告诉家里人:“我回来了!”可这句话永远也说不出口了!这种万分悲痛的失落我们都能感同身受。他接受不了所有亲人的亡去,接受不了无家可归的事实,他想象着家还在、家人也还在,于是他忙碌起来:“舂谷持作飰,采葵持作羹。”可是等到饭熟了,汤好了,要送给谁呢?也许此刻,他才悲从中来,放声痛哭——还不如战死沙场,又何必回来!面对余生,老兵的心灵更是绝望的,这种绝望是永无亲人、无家可赖、生无所恋的孤苦无依。这三首诗所表现的主人公心灵上的绝望都是惊心的,所有的人都是有家却无家可归,他们没有了生活下去的信心,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他们不知道活着的意义,心灵也没有了归宿。
汉乐府苦难家庭诗歌所反映的人生困境大概是当时普通人最常遇到的现实困境,只是这样的现实太过辛酸,太过悲苦,也太让人感到绝望。诗歌中的困境层层叠加,从生活到生命再到心灵,但这样的困境并不总让人绝望,因为它们极富启迪意义,正是这些绝望的困境预示了诗歌史上的一次新的精神觉醒。
三、汉乐府苦难家庭诗歌中的意识突破
文学自觉的前提是人的自觉,即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它包含着自我对生命有限性的认知、对人生态度的建构、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等,只有这样的独立意识的觉醒才会使文学减弱 “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2]。本文所说的“意识突破”正在此处。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汉乐府苦难家庭诗歌的思想内涵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现实的人生困境几乎把每一个主人公都推向了生命的边缘和心灵的绝境,在最无望的处境里,他们无不深刻地咀嚼着自己生命的况味和人生的意义。
《东门行》中,男主人公一入家门便惆怅悲苦,饥寒中的挣扎终于让他愤而拔剑。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妻子劝阻他的言语:“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这四个理由每一个都分量千钧,但哪怕妻子不慕富贵、甘苦不弃,哪怕孩子尚在幼年,哪怕青天朗朗当头,都没能化解丈夫对苦难人生和悲剧命运的懊恼,反倒激起了他对生与死的另一番解读:“你不要管!走啦!我已去得太晚了!我的白头发已常常落下,我不知道还能活几天!”面对活不下去的现实,与其等死,不如舍命一搏!与其说这表现了主人公强烈的求生欲望,倒不如说这是面对即将来临的生命终结,他的内心被紧迫的生命感强烈地搅动。正是这种深度的对于自我生命的感知才使得故事的结局震撼了我们的心灵。在这一点上,《孤儿行》与《东门行》非常相似。孤儿面对被兄嫂虐待、有家实如无家的生活,多次想到了死,想到曾经父母温暖的怀抱。他的绝境在心灵,或许他在不停追问:我的生命难道就是这样?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妇病行》和《十五从军征》则共同表达了对人生不确定性的忧思和迷茫。《妇病行》中的男主人公面对妻子的亡故,面对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随母亲而去的孩子,他心力交瘁,只好在空空如也的房子里不停地徘徊,他突然迷茫了起来,不知道自己的家庭和人生还有没有希望,更不知道自己的余生该如何度过。就连演唱此曲的乐工唱到最后都悲痛不已,不愿再继续唱下去,也许连他都不愿意再去编织这样的看不到光明的未来。《十五从军征》中,当老兵端着做好的饭和汤却不知道送给谁的时候,他的眼里除了眼泪剩下的也只是迷茫,这迷茫源自于他渴望团聚但亲人无存的巨大遗憾,源自于他充满欣喜却只能空留余恨的巨大落差,他内心的希望跃出之时也正是他的人生信念崩塌之时,他迷茫地站在已是一片坟墓的“家”里,他的风烛残年又该如何捱过,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难题。
当这些诗的作者在深入细致又无比动情地描摹故事主人公的命运和人生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正在思考和回味着属于自己的生命和人生,这样对人的独立意识的表现更像是“自觉”的文学的表现,所以感染力极强。“在中国诗歌史上,以文学的形式反映这样的生活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但它所产生的艺术震撼力却是巨大的。”[3]
此前的诗歌中有没有这样强烈的独立意识呢?当然有,但是与汉乐府苦难家庭诗歌所反映的独立意识是不一样的。
先看《诗经》。《诗经》的时代,个人的“存在价值就是整个宗法集团的存在价值,人的意义是作为宗族的意义、国家的意义来被感知的”[4],所以《诗经》中的大部分诗篇表现的是人的集体意识,而能够表现人的独立意识的大都是民歌中以爱情和婚姻为主题的篇目,如《邶风·柏舟》和《王风·大车》里女子追求男子的强烈意识,《郑风·溱洧》中男女之间的互诉心曲,《郑风·女曰鸡鸣》中夫妻二人真挚的爱情对白,《卫风·氓》和《邶风·谷风》中弃妇的哀怨等。以《王风·大车》为例,这首诗中的女子大胆地向一位男子表白,或许是男子的态度暧昧不明,女子就真心鼓励男子私奔,而且向天发誓:“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这样的直率充满了野性的生命力,个性愿望的表达也极富张力。这些作品虽然表现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但都是爱恋的表达,弃妇诗虽有对生活乃至人生的思考,但远没有汉乐府苦难家庭诗歌反映个人独立意识的深度和力度。汉乐府继承了《诗经》的婚恋主题,如《上邪》写女子的爱情誓词,《饮马长城窟行》写夫妇情爱,《白头吟》指责男有二心,《塘上行》写弃妇的怨苦等。其中,《上邪》写道:“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诗中女子的誓言比《王风·大车》还要决绝,个人意识更加强烈,表达上也更加生动。
再看屈原的诗歌。屈原是一个有着强烈个人意识的天才诗人,他以《离骚》为代表的诗歌也表现了他强烈的个性色彩。但屈原的诗歌具有双重性,在表现其个人意识的同时,还表现了屈原本人难以冲破的宗法情感,楚怀王和楚国就是屈原生命的全部,当怀王客死,楚国败落,屈原的人生也就失去了他的依附和价值。屈原无法摆脱时代的烙印,他身上具有独立与依附的双重人格,他的诗歌在相当程度上也具有“服务于政治教化”的意味。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认为汉乐府苦难家庭诗歌所表现的个人的独立意识即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是一种意识突破。这样的意识突破当然不止表现在苦难家庭诗歌中,其他篇章同样有精彩的表达:“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露》),“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蒿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西门行》)等等。这些表述能让我们清晰地感觉到当时的人们对于生命和人生的强烈关注和感慨,这种感喟当然是属于自我的。
四、汉乐府对文学自觉的意义
汉乐府尚未完全实现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这一觉醒要到魏晋时代才更加清晰,但汉乐府至少是文学精神觉醒的一个导向。
一般来讲,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末文人五言诗对魏晋时代的文学自觉具有更加直接的影响,但《古诗十九首》是当时的文人“学习汉乐府民歌的结晶”[5],如《生年不满百》篇便是直接从汉乐府《西门行》演化而来的。“《古诗十九首》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茫无边际的个人迷失情绪”,如“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这种迷失情绪与汉乐府苦难家庭诗歌中的迷茫情绪一致。
作为魏晋文学开端的建安文学对汉乐府同样有着很好的继承。建安文学对于生命和人生都表现出强烈的忧患和紧迫感,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短歌行》),“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曹植《箜篌引》),“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自知百年后,堂上生旅葵”(阮瑀《无题》),这样的感受也能从汉乐府苦难家庭诗歌中找到影子。
不难看出,汉乐府不仅与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末文人五言诗的精神意蕴有直接关系,也对建安文学的思想内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讲,汉乐府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