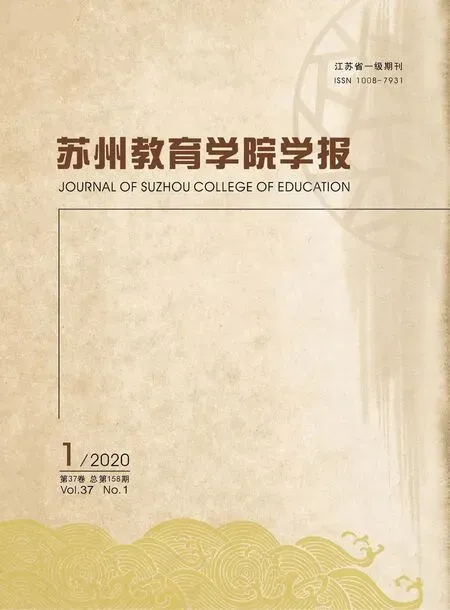“人”与“国”:新文化诸将与国民党右翼的对话
徐从辉,杨 潇
(浙江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随着新文化运动高潮的退却,“革命”的逻辑渐渐取代“启蒙”与“复兴”,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在与“革命”对话的过程中,新文化诸将中的大部分秉持着新文化时期所开创的自由主义立场,选择了韧性的抗争。本文重在考察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诸将在与国民党右翼的对话过程中所呈现的“立人”与“立国”的思考。
一、“故鬼重来”
周作人与左翼文学界间的紧张关系学界探讨较多,对于周作人与北洋政府之间的关系,研究也较多[1]。周作人在遭遇北洋政府的暴力、屠杀、专制时展现了其作为“叛徒”的一面,但周作人与国民党右翼文学界之间的关系学界则较少探讨。后“五四”时期,北京经历了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的政权更迭,周作人与北京当局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转变?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中心远在南方的广州和上海,那么,对于眼下的当局及其文化文学场域,周作人作何反应呢?
周作人生活在军阀政权不停交替更换的北京,这是一个交织着生与死的时代。他把希望寄托在南方的革命政权上,把它看作“民主思想”的化身,“南北之战,应当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2]。然而,国民党在1927年发动的“清党”运动打破了周作人的希望,这场残酷的大屠杀使周作人认识到民族的虐杀性。对于国民的劣根性,周作人有着深刻的反省——嗜杀在中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遗传病,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无不传染得很深很重。周作人的一些学生也被以“左派”的名义而杀害,他悲愤地写道:“至于那南方的杀人者是何心理状态,我们不得而知,只觉得惊异:倘若这是军阀的常态,那么惊异也将消失,大家唯有复归于沉默,于是而沉默遂统一中国南北。”[3]这种由党争带来的排他性、嗜杀性使周作人深感失望,“沉默遂统一中国南北”,正如鲁迅笔下的“无声的中国”,这是周作人对国民党赤裸裸的批判。
问题更在于杀伐的队伍中竟有昔日的友人——蔡元培和吴稚晖,他们或是“帮凶”,或是沉默。蔡元培和周作人是同乡,周作人1917年之所以能到北大,离不开他的帮助。周作人与蔡元培的分裂可能从1923年的“非宗教大同盟”运动就开始了,但这并不影响周作人对蔡元培的总体评价。1926年,蔡元培从欧洲回国后逗留沪杭无意北上,周作人于4月25日写信给蔡元培,恳切要求其北返,对其教育事业也是持支持态度的。但“清党”运动发生后,周作人对蔡元培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他先后在《猫脚抓》《怎么说才好》《功臣》等文中批评蔡元培对“清党”造成的冤死青年“不能辞责”,以及其对屠杀行为的“视若无睹”①蔡元培不认同共产党及其阶级斗争主张,主张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党籍,并把“清党”运动定名为光复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护党救国运动”。他从一个开明学者转变为一个“清党”运动的支持者,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据目前的史料来看,蔡元培实为蒋介石所利用,后来他看出“清党”实为摧残法治,蹂躏民权,渐与蒋介石分离,之后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走向了蒋介石的对立面。参见张晓唯:《所谓蔡元培“晚节不保”问题》,《书屋》2006年第11期,第34——38页;丁晓平:《蔡元培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党史文苑》2015年第9期,第40——45页。,即使在私信中也不忘对蔡元培的批评。1928年8月,国民党实行大学区制,划河北、热河、北平、天津为“北平大学区”,并改“中华大学”为“北平大学”,任命原代蔡元培主持校务的李润章为北平大学校长,遭到国民党平津党部和原北京大学师生的反对。前者反对实行大学区制,后者反对取消北京大学和任命李润章为北平大学校长。周作人在给江绍原的信中写道:“唯反李(李润章)而不反蔡乃一奇,或者蔡公更善于作官可用为说明,至于瞎用武力似无甚关系,敝人在平所见闻未闻有若何武力也。”[4]130周作人对蔡元培参与“清党”一事一直念念不忘,“北大师生至今尚迷信蔡公,甚奇。至于不佞则反蔡而不拥李。近来狠想不做教员,只苦于无官可做,不然的确想改行也”[4]179-180。周作人对蔡元培的讥讽由此可见。
吴稚晖个性极为鲜明,在“科玄论战”中为科学派的中坚人物,也是国语统一运动和注音字母的开创者之一,他主张“科学万能”,对国故、国粹颇不以为然,“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省,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乱世的产物。非再把它丢在厕所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5]。但吴稚晖在“清党”运动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②1927年蒋介石预谋发动政变,3月27日蒋介石由南京抵上海后,招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密谈。吴稚晖对蒋说:“你今天身负军事和党国责任,此刻之心情,正如经书所说:‘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只有出之以戒惧恐惧,采坚持正确的毅力与决心,乃能无畏于横逆,而终底于胜利成功。”参见杨恺龄编:《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第68页。吴稚晖建议蒋介石下决心对共产党下手,当事人之一蒋梦麟回忆:“当时先生(吴稚晖)约蔡孑民先生、邵元冲先生及余四人与总司令邻室住宿。吴蔡两先生与蒋总司令朝夕讨论清党大计,吴先生并相约清党明令未宣布以前我们四人不得离此外去,以免外人探知吴蔡两公行踪,多所推测。而这一‘无盔甲的袁世凯’(吴稚晖)尤为共产党人所注目。”参见朱传誉:《吴稚晖传记资料(第1册)》,台湾天一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4页。在周作人的记忆中,“《青天白日报》记者二名与逃兵一同斩决,清党委员到甬斩决共党二名,上海枪决五名姓名不宣布,又枪决十名内有共党六名,广州捕共党一百十二人其中十三名即枪决……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6]面对昔日同人胡适、吴稚晖的沉默,周作人诘问道:“胡先生出去只见不文明的人力车而不见也似乎不很文明的斩首……这回,吴先生却沉默了。”[6]“白色恐怖绝不会比赤色的更好。”[7]周作人听闻吴稚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封致汪精卫的信,其中挖苦在江浙被“清”的人,说他们无杀身成仁模样。周作人对此大加抨击,认为好生恶死乃人之常情,不能成为嘲弄人的谈资,何况事实并不尽然。“吴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杀人,还要摇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种残忍行为盖与漆髑髅为饮器无甚差异……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永乐乾隆的鬼来,于此足见遗传之可怕,而中国与文明之距离也还不知有若干万里。”[8]吴稚晖“又忽发杀人之豪兴,发起清党之盛举,由青红帮司执行之责,于是残杀遂开始,共党之死者固不少,而无辜被害的尤多,凡略有桀骜不羁之青年非被屠戮亦在逃亡,而土豪劣绅乃相率入党,荼毒乡里,莫知纪极,至今江浙一带稍知自爱者至以入党为耻,这都是吴委员的功劳”[9]。周作人对吴稚晖的“八股文”之说常有引用,但是对吴稚晖参与“清党”一事鞭挞不遗余力,从中也可以看出周作人的人道主义立场以及对自由主义的坚持。周作人的自由主义精神可以追溯到其早年对民族危机的关注,“不愿以血灌自由之苗,而甘以尸饱江鱼之腹,乌乎可哉?如生而痛苦,则何尚天年?死而无知,则何悲菹醢?吾身虽死,自由不死;吾身虽灭,原质不灭”[10]。周作人道出了以血灌自由之苗、身虽死然自由不死的坚定之志。虽然每个阶段的任务不同,周作人的思想也有所变化,但其立场并未改变,这与其包含个人主义在内的人学思想紧密相关。
陈思和在反思“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时曾说:“只有拒绝了对任何一种政治力量的依赖,坚持用个人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去批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11]在此意义上,后“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也可以说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创作和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等人的文学创作开创了20世纪中国的自由主义文学。
二、“个人主义”
费正清曾有这样的观察:“1921年以后,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学界面临一场痛苦的抉择,学者或是避开政治埋头学术研究,或是以学术为政治的附庸。”[12]文艺被绑上了政治的战车,自主性遭到碾压,思想文化研究的积极性被压抑,这些和个人主义①刘禾考察了“个人主义”话语的由来、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场域中的“游走”和创新及民国初年关于个人主义的论辩。“个人主义”在中国的语境中从没获得过稳定的意义,也并不总是和“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民族救亡”等群体概念构成二元对立,“个人主义并不总是构成国族主义的对立面,启蒙运动也并非是民族救亡的反面。这两种话语中间的张力产生于历史本身的不稳定性,同时也源于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盘结”。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第117页。本文认同个人主义和国族之间的辩证关系,但主要考察的是它们之间的冲突关系,文中的“个人主义”主要是指人道主义下的个人主义。与党派、国族之间的冲突有着莫大的关联。
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新文化运动推崇的个人主义之间存在冲突。国民党对“五四”新文化的看法以孙中山和蒋介石为代表。孙中山曾积极支持“五四”学生运动,注重“五四”新文化思想变革之用,尤其是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的作用。但孙中山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并不完全接受新文化所倡导的思想,如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就具有保守主义色彩。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新文化诸将带有激进的反传统色彩,而孙中山认为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实际是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对于中国固有的道德要采取扬弃的态度,不能一味全盘抹杀。孙中山肯定了中国传统伦理的价值与意义,其文化保守色彩受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胡适等人的批评。胡适批评孙中山“抬高中国的旧政治思想和旧道德……国民党的历史上本来便充满着这保存国粹和夸大传统文化的意味”[13]428-429。尤其是在对待个人自由的问题上,孙中山更是从一个革命家、政治家的立场认识到政治团体中个人自由的不可能。孙中山在《民权主义》演讲中批评“新青年”所提倡的“自由”把什么界限都打破,流于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各人的自由太多。由于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国要革命”[14]。1924年11月3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告别演说中分析了近二三十年来中国革命屡次失败的原因,在于错误理解了欧美的平等、自由,“民国十三年来革命不能成功,就是由于平等、自由的思想,冲破了政治团体……无论什么人在哪一种团体之中,不管团体先有没有平等、自由,总是要自己个人有平等、自由……中国现在的革命,都是争个人的平等、自由,不是争团体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总是失败”[15]。值得肯定的是,孙中山区分了政治团体与普通社会中的自由与平等,但他随后又否定了学校与家庭中的自由与平等,因为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从革命家的战略立场出发,认为个体应该统一到团结的组织中去,个人和集体处于一个对立的位置,而且“个人主义”含有消极意义。他对列宁的建党经验赞赏有加:革命党要有自由,不要革命党员有自由,个人要绝对服从党的命令。孙中山把个人自由近同于个人的自私自利,是与民族国家对立的概念。对此,胡适也有过批评,胡适认为孙中山只把新文化运动当作政治革命的工具,“今日的国民党到处念诵‘革命尚未成功’,却全不想促进‘思想之变化’!……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13]449。胡适展示了难能可贵的批评勇气。
蒋介石执政后,基本上沿袭了孙中山的这一观点,肯定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偶像破坏”精神,“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16]。蒋介石后来甚至把“民主精神”解释为“纪律”,把“科学的意义”解释为“组织”,从自己的立场对新文化进行了选择性的理解和重构。
从上文可以看出,国民党反对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个人主义”。在“个人主义”问题上,与其说是国民党高层反对新文化运动,不如说是对它的一种“误读”。孙中山和蒋介石是从政治革命的立场强调革命的组织性与纪律性,而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个人主义”则是在世界文明的思潮中对“人”的价值的发现,是在人类的历时发展进程中发掘人的生命的尊严与自由,而非指向“战时”的阶段性任务,两者意义实践的背景不同,但这对服膺于西方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而言是一种挑战。
以胡适为例。1930年12月,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提倡“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并劝诫青年朋友——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17]其后,胡适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中再次谈到个人主义,他认为个人主义有两种:“(1)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2)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这后一种就是我们当时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18]可见胡适更重视个人自由,它是构成国家自由的前提,而不是奉自由之名的国家主义。胡适认同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五四新文化的重要遗产,“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和“造成独立的人格”的个人主义是“新社会”与“新国家”的重要推动力[18]。殷海光反省三民主义就是一种“统战工具”,有其局限性。但问题不止于此,个人和集体的冲突也是造成激进主义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由于对集体的高度统一,必然带来一定的排他性:表现在党派上,是一党对另一党的排斥;表现在文化上,要求统一性,容不得异己的存在。胡适认为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并没有延续“五四”精神,“一是苏俄输入的党纪律,一是那几年的极端民族主义”[18],铁纪律含着“不容忍”的态度,排斥异己,与“五四”提倡的自由主义相悖;民族主义的三个方面依次是“排外”“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18],胡适对国民党的批判后来也在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中应验了。革命文学开始时,来自革命阵营中对鲁迅及周作人等人的指责便是其例。
三、“大时代”:喧哗与共通
标举“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五四”新文化本身就含有一种内在的冲突,如激进主义的文化主张和思想自由的冲突,这在后“五四”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王造时评价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的时代:“新文化运动的影子没有了。又是一朝江山,又是一朝君臣,又是一个时代。”①转引自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第20——35页。这个时代显然不是此前的新文化时代,新文化的主体阵营也发生了分化。
五四新文化知识分子中以陈独秀最为激进,在1920年9月发表的《谈政治》中,陈独秀称:“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利器。”[19]陈独秀接受了革命的观点,由早期民主启蒙立场转向政党政治,由世界主义走向了民族主义。
对胡适而言,留美期间受到实验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影响较大。1917年,胡适回国,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于是下定决心,20年不谈政治,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创造革新的条件,他希望思想文艺层面问题的解决能够成为政治革新的基础。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胡适接手《每周评论》,针对当时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希望能避免空谈,“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多研究现实问题,从而对政治改良有所作用。[20]直至《每周评论》被封近三年之后,胡适再次涉足政治。1922年5月14日,胡适联络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孟和、梁漱溟、李大钊等人,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倡“好政府主义”,把政治改革的目标定位为“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21]胡适在《我的歧路》中说道:“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22]从实质上说,胡适从未放弃实验主义哲学,甚至其文艺思想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可以说胡适从未放弃对现实的关怀,因此也不难理解其后来对政治的参与。总体上看,胡适展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
新文化运动之初,《新青年》同人相约“不批评时政”,但这一约定并不表明他们不关心政治,而是企图从思想文化入手,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新潮》主将傅斯年和罗家伦抱着学术救国的思想留学,然而在归国后的1926年,傅斯年便说,希望中国出现一位有能力的“独裁者”,“他将把秩序与文明强加给我们”;1936年,罗家伦选定希特勒的《我之奋斗》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他们两人这些同新文化运动时“自由知识分子”定位大相径庭的言行,表面上殊为难解,却并非特例,而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潮流之一。[23]被罗家伦视为楷模的蔡元培,也有军事化的思想。对晚清民初的知识分子而言,如何摆脱民族被辱被打的命运,重建家国共同体,也许军事化是一种直接有效的介入方式,这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另一面,文学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性被严重削弱了,被要求统一到“主流”中去,甚至遭到排挤和打击。本文无意对历史人物进行价值评判,而是力图呈现“大时代”中文学、思想、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以及人物思想的脉动,试图走近历史,理解历史,反思历史。
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严复、梁启超的引进伊始,在1920年代以后又分为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等。本文无意于这些概念的辨析。但大体而言,周作人对个体意志的强调、对言论自由的坚持、对权威的反抗可以构成自由主义的内容之一。胡适和周作人并不相同,除了对个人主义、宽容的强调外,胡适还注重社会制度的顶层设计,这是周作人所不具备的。而周作人在后“五四”时期也展现出和胡适不同的地方,即其所宣称的“半是儒家半释家”的思想面貌,尤其体现为中国传统中士的自在精神——涵盖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庄子“逍遥游”的自在、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隐逸,这也使周作人的“自由主义”内涵变得极为驳杂。
其实,“自由主义”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不可通约,虽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较为激进的反传统倾向,中国传统文化成为西学的对立面,儒学自然也就成为西方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对象。事实上,两者具有一些共识共通之处,如儒家的中庸之道和自由主义的宽容禀性可以形成良性互动,自由主义对权威的反抗也暗合中国“疾虚妄”“重知”的精神,这在周作人所称的“思想界三贤”——王充、李卓吾、俞理初——的身上就有所体现,周作人企图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寻出现代精神,从而实现文艺复兴之梦。后“五四”时期,胡适的“整理国故”中蕴含着还中国传统文化以本来面目的努力,周作人则倡导礼乐传统,自称是“孔子的朋友”,二者都含有文化复兴之意。观察后“五四”时期的胡适、周作人,他们与各种权力话语的对话实为“个人主义”发声,以免形成在集权专制下“无声的中国”。
综上,在与后“五四”时期各种权力话语对话的过程中,胡适、周作人展示了个人之独立,不依附党派和组织,对言论自由的坚持,对权威话语的反抗,其实与其“五四”时期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精神也构成我们当下与世界对话的重要基石。于今,新文化运动已是百年,然而历史的悲情仍让我们在故纸堆中寻求岁月的温度,感知当年的人和事,在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仍需不时回望那切近切远的丰碑——“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