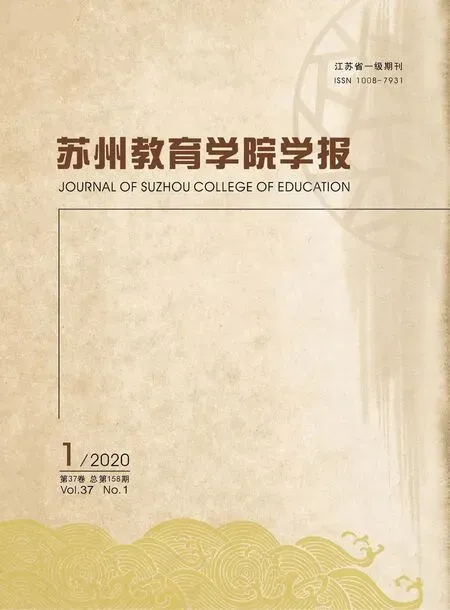悲观主义哲学视域下陶渊明的幸福之路
刘荣霞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陶渊明是我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堡垒,独特的个性使他视官场如尘网,把远离官场、坚守自我当作人生理想。辞官后的思考与创作几乎是他全部的生活,他的作品里有悲、有痛,也有淡然、有幸福,痛苦与幸福交织转换着,陶渊明内心是一个矛盾而丰富的世界。叔本华将人生的痛苦归结为不同形式,认为人从本质上来讲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同时,人生中也会有满足欲求的幸福体验。陶渊明的一生充满了苦痛,但他还是能苦中作乐,坚持不懈地寻求幸福。正因如此,后人才能以他为精神依托,寻求超越现实并获得幸福的方法。
一、“人生即痛苦”的哲学观与陶渊明的痛苦生活
19世纪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是唯意志主义的创始人,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说:“一切欲求皆出于需要,所以也就是出于缺乏,所以也就是出于痛苦。”[1]27“人,彻底是具体的欲求和需要,是千百种需要的凝聚体。”[1]425受生存意志驱动,人产生生存欲望,这种欲望是非理性的,周而复始、永无止境,始终无法被完全满足,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它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1]425。人生就像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苦难、灾祸不断,尽管奋力挣扎,最后只能绝望地发现生命就是一种痛苦,根本无法被救赎。
叔本华的观点,在中国古代道家那里有相近表述。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2]29因为有了躯体,便有了生老病死等忧患,便有了各种苦痛。庄子说:“人之生也,与忧俱生。”[3]332在人来到世界上的那一刻,痛苦就随之而来,忧愁与生命同在,随生而存,随亡而灭。故老子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2]45。保持朴素,减少私欲,如此才能不被困扰。庄子《大宗师》云:“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3]134天地自然赋予人形体使人有所寄托,赋予生命使人辛劳。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生存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4]19-29这五个层次的需要依次推进,一项需要被满足之后另一项需要就随之而来,逐步完成后还可达到超越性需要(即精神性需要或超越自我实现的需要)。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观之,陶渊明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还有自尊需要与自我实现需要都有不同程度的缺失,因此他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马斯洛指出:“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占绝对优势。”[4]20陶渊明少时家境衰落,生计之苦几乎伴随他的一生,改善生活条件是他出仕的主要目的。辞官回家后生活每况愈下,甚至晚年还不得不出门借贷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乞食》)[5]48“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5]107“畤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饮酒》其十九)[5]98陶渊明的生理需要长期不被满足,他的痛苦显而易见。
人处于真正的危机状态中对于安全需要的渴望尤其强烈。马斯洛概括的危机状态包括:“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浪潮、社会解体、神经症、脑损伤、权威的崩溃、长期恶劣的形势等。”[4]25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荡,长期恶劣的形势让他忧心忡忡,深有朝不保夕之感。况且他体弱多病,疾患常在。他在《与子俨等疏》中说:“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5]188他担心自己不久于世,告诫孩子们要团结友爱、安贫乐道。义熙四年(408)六月,陶渊明家中还曾遭受火灾,生活雪上加霜,加之自然灾害使得庄稼连年歉收,生活逐渐捉襟见肘。来自社会、家庭、自然、自我的种种不幸和苦难煎熬着陶渊明,他不得不忍受安全需要缺失的痛苦。
马斯洛认为:“对爱的需要包括感情的付出和接受。如果这不能得到满足,个人会空前强烈地感到缺乏朋友、心爱的人、配偶或孩子……他将希望获得一个位置,胜过希望获得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东西,他甚至可以忘记:当他感到饥饿的时候,他把爱看得不现实、不必需和不重要了。此时,他强烈地感到孤独,感到在遭受抛弃、遭受拒绝,举目无亲,尝到浪迹人间的痛苦。”[4]27陶渊明是一个不被命运眷顾的人,先后有父亲、妻子、母亲、程氏妹、从弟敬远等亲人陆续离他而去。“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在己何怨天,离忧愁凄目前”(《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5]49-50,“情恻恻以摧心,泪愍愍而盈眼”(《祭从弟敬远文》)[5]193。至亲离世、爱人离世,与亲人天人两隔的摧心之痛他经历了无数次。于是,他不由发出“人生若寄,憔悴有时。静言孔念,中心怅而”(《荣木》)[5]15-16的感叹。人生有限而宇宙无限,人也只是暂时寄居人世而已,终归还是要离开的,无一例外。陶渊明也是一个孤独的人,有着漂泊无依的灵魂。他独游、独慨、独饮、独醉、独策还,独自一人立于世间,虽然也有颜延之、庞主簿等为数不多的朋友,但并不能抚慰长时间离群索居的他。“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和胡西曹示顾贼曹》)[5]68,“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戊申岁六月中遇火》)[5]82,为此,陶渊明忍受着归属和爱的需要缺乏的痛苦。
自尊需要即“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4]28。并且“最稳定和最健康的自尊是建立在当之无愧的来自他人的尊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名声、声望以及无根据的奉承之上”[4]29。陶渊明做官是出于改善生活的考量,但也不会为改善生活而折腰。他好酒,虽家贫不能常得,却也不随意去喝任何人的酒,这是出于他的骄傲,也是他的自尊、自重。即便没有食物、没有酒,他也不会打破自己的底线。“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祭从弟敬远文》)[5]194“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尚皆同,愿君汩其泥。”(《饮酒》其九)[5]92世间本难有两全之法,陶渊明的自尊需要还是未能满足。
“自我实现”指“人对于自我发挥和自我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人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4]29。陶渊明也渴望建功立业,一展大济苍生的政治抱负,“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5]117,然而,现实却是“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戚,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5]115-116,因而“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杂诗》其五)[5]117。陶渊明有三次出仕经历,可惜总有各种原因致使他放弃仕途。而生活中的他也没有成为好父亲,“吾年过五十,而穷苦荼毒,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使汝等幼而饥寒”(《与子俨等疏》)[5]187。愧疚苦痛之情溢于言表。自我实现未能完成,自我价值无从体现,陶渊明忍受着壮志难酬、节节败退的痛苦。
马斯洛的五种需要理论依次递进,陶渊明的五项需要却是同时并进的,因为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哪一种需要一直被满足。叔本华提出:“意志愈是激烈,则意志自相矛盾的现象愈是明显触目,而痛苦也愈大。如果有一个世界和现有的这个世界相比,是激烈得无法相比的生命意志之显现,那么这一世界就会相应地产出更多的痛苦,就会是一个人间地狱。”[1]539陶渊明的痛苦并非浅层次的痛苦,而是最高程度的痛苦,因为他是“达道”之人,也是意志强烈的人,更重要的他是一个心中有桃花源世界的人,因而也是最痛苦的人。但是,陶渊明毕竟不同于其他人,强烈的痛苦反而是试金石,最终他会将强烈的痛苦转化成新生的力量,使人生达到新的高度,甚至为后来者开疆拓土,找到自我解救的范式。
二、叔本华的幸福论与陶渊明的幸福之路
“幸福”是什么?《尚书》认为“幸福”指一个人五福齐备,“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6]。所谓五福即长寿、富有、健康安宁、道德高尚、寿终正寝。《礼记》云:“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7]幸福就是完备,完备就是诸事顺遂。然而,道家坚持辩证的幸福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2]151,“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庄子·则阳》)[3]477,痛苦和享福会相互转化,因此,忍痛和求福是同一的,保持痛苦较少的状态,幸福的体验便会增加。
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中认为“人生即苦”,但他也认为:“对于一个人的幸福,甚至对于他的整个生存的方式,最主要的明显的就是这个人自身的内在素质,它直接决定了这个人是否能够得到内心的幸福,因为人的内心快乐抑或内心痛苦首先就是人的感情、意欲和思想的产物。而人自身之外的所有事物,对于人的幸福都只是间接地发挥影响。”[8]4叔本华坚信:“一个精神富有的人首先会寻求没有痛苦、没有烦恼的状态,追求宁静和闲暇,亦即争取过上一种安静、简朴和尽量不受骚扰的生活。”[8]20精神禀赋卓越的人,“过着思想丰富、生机勃勃和意味深长的生活;有价值和有兴趣的事务吸引着他们的兴趣,并占据着他们的头脑。这样,最高贵的快乐的源泉就存在于他们的自身”[8]28。人修炼内在素质、丰富心灵世界、摒除杂念、控制欲望就是获得幸福的关键。获得幸福,需要人们享受孤独、从事某种活动,还有禁欲。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中,意志是痛苦产生的直接根源,因此,摆脱痛苦获得幸福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否定生命意志,禁止欲望。
既然幸福就是释放天性,那么,人心中畅快、无忧无虑,也就不必刻意寻找幸福。冯友兰在《人生哲学》中说:“凡物皆由道,而各得其德,凡物各有自然之性。苟顺其自然之性,则幸福当下即是,不须外求。”[9]陶渊明的内心有诸多无奈与痛苦,但他一直都在努力顺随天性,过着朴素、安静的田园生活,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超越,并由此获得不须外求的幸福。
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是怡然自乐的,也是孤独寂寞的。他的诗中有许多关于孤独的描写,暮春独游、策杖独还、有酒独饮、慨然独悲等,但他定然也是享受孤独的。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中剖析了孤独的益处:“第一,他可以成为自己;第二,他用不着和别人在一起。”[8]136并进而提出:“一个人只能与自己达致最完美的和谐。”[8]133故“青年人首上的一课,就是要学会承受孤独,因为孤独是幸福、安乐的源泉”[8]133。而且,“没有足够的独处生活,我们也就不可能获得平静的心境”[8]136。孤独的岁月让陶渊明成为了真正的自己,从而能享受到身心的自由。孤独的田园生活使他获得平静的心境,也是他幸福、安乐的源泉。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描写自己回归田园是“载欣载奔”“眄庭柯以怡颜”“园日涉以成趣”,[5]161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只想“息交以绝游”[5]161,过不被打扰的幸福生活。
叔本华总结人的快乐源泉的第三类是“施展感觉能力方面的乐趣:这些包括观察、思考、感觉、阅、读、默想、写作、学习、发明、演奏音乐和思考哲学等”[8]26。回归田园的生活,让陶渊明有了充足的时间去观察和思考,他观察一切能让人获得审美愉悦的事物,思考宇宙、社会、人生。他的观察、思考、感觉和默想是联系在一起的,最后形成了他独有的哲学观点。哲学思考让陶渊明充分认识到“天道”,让他意识到简单、朴素地活着是多么重要,也让他更超脱,幸福感更强烈。诗、书、琴、酒是陶渊明生活的主要乐趣,是他获得幸福的手段。“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其一)[5]56,“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其一)[5]133,“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5]175,“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五柳先生传》)[5]175,“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移居二首》其二)[5]57,“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5]74,“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5]96,“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答庞参军》)[5]22,“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5]60,“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5]71,“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归去来兮辞》)[5]161。诗、书、琴、酒是陶渊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他消忧的良方,快乐的源头。
叔本华说:“能够从事某样活动,如果可能的话,制作某样东西,或者至少学习某一样东西,对于我们的幸福是绝对必要的。”[8]154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被钟嵘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10],王国维认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11]朱光潜高度评价陶渊明:“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12]袁行霈对陶诗进行了充分的肯定:“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题材的作品。”[13]作为一个将自我与人生看得十分透彻的人,陶渊明一定感觉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意志即欲望本身,欲望产生痛苦,叔本华认为:“没有痛苦的状态才是真正的、最大的幸福。”[8]114欲望让人心处于不断的运动状态中,就像禅语中说的,人生在世就像生活在荆棘林中,如果心静,人就能把持住自己,不随意妄为,以免受到伤害。如果心不静,各种痛苦都随之而来。而“缺乏痛苦的程度是衡量一个人生活是否幸福的标准。如果能够达到一种没有痛苦,也没有无聊的状态,那就确实得到了尘世间的幸福,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8]113-114。因此,禁止欲望,保持内心的宁静与满足即是开启幸福之门的钥匙,是获得幸福生活最永久的路径。
陶渊明少有壮志,希望能像曾祖陶侃与外祖孟嘉一样,有一番成就。但是,建功立业的路上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本性使他无法忍受,于是在仕与隐之间反复纠结、徘徊。陶渊明心中仕与隐的斗争愈发激烈,痛苦的持续增长让陶渊明无比绝望,因此,他甘愿抛弃曾热烈追求过的政治理想,弃绝仕宦回归田园,以保持心境的平和与超然。就像他在诗中描述的那样,“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5]37,一个人如果能放弃最想达成的一个愿望并且能让波澜起伏的心境沉寂下来,这必然是一件幸福的事,也必然是一件能提升人生境界的事。《老子·十五章》云:“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2]33在浑浊中安静下来渐渐澄清,在安定中活动起来慢慢出现生机是多么难得的事情。但是,陶渊明做到了,他在混乱的官场中保持清明,在痛苦的洗礼中觅得幸福。而后,他安静地保持真意,安静地在他理想的桃花源世界中做一个怡然自足的幸福之人。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论道:“世界上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持久的宁静。因此,我们看到圣者们的内心生活史都充满心灵的斗争。充满从天惠方面来的责难和遗弃;而天惠就是使一切动机失去作用的认识方式,作为总的清净剂而镇住一切欲求,给人最深的安宁敞开那条自由之门的认识方式。”[1]533最深的安宁源于天惠,最大的幸福来自天惠,天惠是可遇不可求的内在特质。天惠甚至让陶渊明越过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而获得求之于内的幸福,达到自我超越的人生境界。由此观之,幸福的确不须外求,陶渊明也的确是当之无愧的幸福之人。
三、陶渊明的幸福之路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陶渊明由痛苦转向幸福的过程,是一个征服生命悲剧、提高自我认知、获得心灵自由与升华的过程。他挣脱身心枷锁回归自我,持守着心中的净土,在自由中体验许多在泥淖中挣扎的人难以享受到的幸福生活。崇尚自然让陶渊明选择回归,回归使陶渊明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获得幸福,因而回归自然的喜悦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十分显著。
陶渊明不仅仅是诗人、文学家,还是哲学家、思想家,甚至他被很多学者评为大思想家。陈寅恪说:“(陶渊明)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14]袁行霈也认为:“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考,这使他卓然于一般诗人之上。”[15]1鲁枢元认为:“陶渊明是中国古代的一位诗哲,也是汉文化圈的诗哲。”[16]的确,陶渊明的诗中有很多关于宇宙、人生问题的哲学思考,在幸福生活的道路上,正是这些思考让陶渊明完成了自我认知的升华。
陶渊明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自然,“自然”是指万物的本来面貌、天性的本真状态,这种状态是生来即是的、没有被世俗异化的样子。这种状态是最美的,也是最好的。陶渊明十分推崇他的外祖父孟嘉,他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写到孟嘉认为最好的音乐形式是“渐进自然”[5]171,外祖父的这句话也成为他的毕生追求。回归自然是陶渊明幸福生活的秘诀,自然状态便是陶渊明的幸福所在。恰如袁行霈先生所言:“陶渊明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恼,以‘自然’作为医治人生各种弊病的良药。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苦于人生之短暂,‘影’苦于修名之难立,‘神’认为他们的苦恼都源于不明‘自然’之义,因而表现为‘惜生’。如能辨明自然之义,就没有这些痛苦了。”[15]6
陶渊明回归自然——回归景色宜人的山水自然、回归人性的本真自然、回归万物运行的自然大道。正是因为陶渊明认识到了亲近大自然的生活的重要性,认识到了回归天性本真的必要性,认识到了人生归于空无的必然性,他才能作出最终回归的选择,才能获得幸福。陶渊明回归到山水之中,这里没有官场的污浊,没有世俗的烦扰,也没有闹市的喧嚣,有的只是简朴的生活方式和秀美的自然风光。他在“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其一)[5]40、“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归去来兮辞》)[5]161的生活环境里“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5]40,“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5]42。他可以“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归去来兮辞》)[5]161,也可以“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5]162,最喜爱的是“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其一)[5]60,“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时运》)[5]14,亲近大自然的生活无处不愉悦,无处不美好。
回归自然,不仅指回归大自然的生活,更是指“回归到人的自然本性,过一种自然而然、无拘无束的率真生活”[15]96。陶渊明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 (《归去来兮辞》)[5]159,自己的天性本就不能被绳墨束缚,因此只能依照本性生活,保有一个不被世俗玷染的、自然的、顺化的真我。其《劝农》诗还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5]24意即自然朴素就是保持真我的最好方式。他称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5]40,思归的情绪贯穿着整个仕宦生涯,“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5]71,官场的生活像是在牢笼里,身心都被形役,幽幽的思归情绪弥漫在心底持续不减,他渴望回归自然、回归真我,只有回归大自然才能保持自然的性情,回归便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5]40。
对于宇宙来说,人的躯体与生命只是短暂的客居,陶渊明已经体悟到这一真谛。“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连雨独饮》)[5]55,由生到死回归自然大道是必然的规律,古今同例,贤愚无免。“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5]42,人的一生好似幻化出的场景,最后都会归于空无。因此,人应当顺应造化了结一生,以天命为乐,也没什么可犹豫彷徨的。
陶渊明关于回归自然的思考与实践,使他的自我认知得到升华,并借此选择了身心的栖息地。他在这方栖息地上思考、创作,为自己创建了轻松自由的桃花源秘境。在这里,他是幸福的。这个“桃花源”不仅是他自己的精神家园,也是后世同道者的精神皈依之地。陶渊明成了他们的精神领袖与归宿,陶渊明其人成了永不过时的话题,其作品也成了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白居易用生命效仿陶渊明,苏轼甚至还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向陶渊明致敬。陶渊明身后的文人士大夫,当他们觉得“迷路”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回归陶渊明,为自己寻找安慰与出路,寻求身心的自由与认知的升华、超越。
叔本华认为:“在这世上有三类贵族:一是基于出身和地位的贵族;二是基于金钱财富的贵族;三是精神思想方面的贵族。最后一类是真正至为高贵的;只要给予他们时间,他们的尊贵就会得到人们的认可。”[8]145陶渊明是在精神方面得到世人认可的贵族,他克服痛苦的过程是他圣化的过程,也是引起人们敬重的过程,因而后世才会有无数尊崇他、效仿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