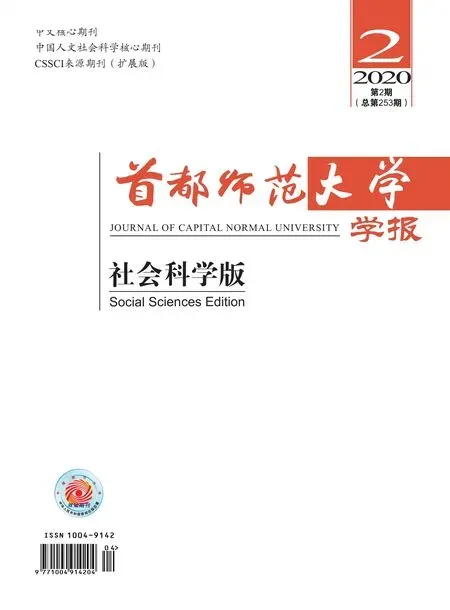从尝试新潮演剧到回归“旧剧的途径”
——对梅兰芳1912—1935年表演剧目转圜的反思
邹元江
一
梅兰芳曾多次言及他18岁(1911年,清宣统三年)之前“所演的都是纯粹的青衣正工”戏,都是向开蒙老师吴凌仙先生和乔蕙兰先生学的,如《二进宫》《战蒲关》《祭江》《祭塔》《三娘教子》《浣纱记》等。①梅兰芳一生表演过的传统京剧剧目据不完全统计有《战蒲关》《落花园》《九更天》《二度梅》《岳家庄》《搜孤救孤》《春秋配》《空谷番》《回龙阁》《摘缨会》《汾河湾》《别宫》《祭江》《南天门》《红鬃烈马》《长坂坡》《彩楼配》《庆顶珠》《盂兰会》《赶三关》《银空山》《大登殿》、二本《虹霓关》《盗宗卷》《四郎探母》《三世姻缘》《献长安》《女起解》、头本《虹霓关》《儿女英雄传》《六五花洞》《八蜡庙》《打渔杀家》《游龙戏凤》(《梅龙镇》)、《穆柯寨》《雁门关》《芦花荡》《天河配》《四五花洞》《双金莲》《五花洞》(《真假金莲》)、《素富贵》《悦来店·能仁寺》《金榜乐》《混元盒》《桑园会》《破洪州》《天门阵》《樊江关》《枪挑穆天王》《金针刺红蟒》《琵琶缘》《审头刺汤》《法门寺》、全本《王宝钏》《回荆州》《浣纱记》《桑园寄子》《美人计》《朱痕迹》《珠帘寨》《甘露寺》《延安关》《六月雪》《缇荣救父》《煤山恨》《朱砂痣》《孝感天》《龙凤呈祥》《宝莲灯》(《二堂舍子》)、《孝义节》《截江夺斗》《梅玉配》《打金枝》《三击掌》《御碑亭》《探寒窑》(《母女会》)、《武家坡》《三娘教子》《祭塔》《二进宫》《玉堂春》等83出(不包括移植改编的《贵妃醉酒》《宇宙锋》《凤还巢》《春灯谜》《牢狱鸳鸯》《生死恨》和《抗金兵》等7出,以及反串戏和合演戏)。“后来感觉到所能演的戏太少了,于是跟路玉珊先生学习刀马旦,如《樊江关》《醉酒》《梅玉配》《虹霓关》《穆柯寨》《雁门关》等戏”①梅兰芳:《四十年戏剧生活》,见《华文每日半月刊》(1941年第9卷第9期)、《华文大阪每日》(1942年第9卷第10、12期)、《影剧》(1943年第8期)、《华文每日》、《时海》(1946年第1卷第2期)、《大国民》(1946年第1、2期)、《艺文画报》(1948年第2卷第8期)等。《四十年戏剧生活》可以被看作是20世纪50年代初梅兰芳口述《舞台生活四十年》的雏形。此文在“坐科习艺时期”这一部分,梅兰芳提及“开蒙老师是吴凌仙先生和乔蕙兰先生。头一出戏教的是《战蒲关》。”刚11岁第一次登台演戏是“在广德楼唱《天河配》……听见听客们喝彩的声音”。此时他搭班学艺的喜连成班常在广和楼和广德楼演唱,《二进宫》《战蒲关》《祭江》《祭塔》《三娘教子》《浣纱记》等都是他常演唱的戏。这些戏显然都是传统的青衣旦角抱着肚子傻唱的,缺少剧舞身段的表演。在“搭班演唱时代”这一部分,梅兰芳提及他在宣统末年出科喜连成班后,初搭鸣盛班,后搭双庆班,与俞振庭、贾洪林、李鑫甫、王凤卿等同台。他说:“在这个时期内我是纯粹唱青衣,后来感觉到所能演的戏太少了,于是跟路玉珊先生学习刀马旦,如《樊江关》、《醉酒》、《梅玉配》、《虹霓关》、《穆柯寨》、《雁门关》等戏在隶天乐园与孟小茹、王蕙芳合演时先后演唱。”民国初年,梅兰芳初次随王凤卿到上海丹桂第一台演唱,他说:“当时的票价初为一元二角,其后一再增加,最高增到三元多,在那个时候,正是破天荒的最高价了。我所演的都是纯粹的青衣正工,偶然贴演《穆柯寨》、《虹霓关》等戏,这已令观众们感觉到新奇了。”。
梅兰芳从19岁(1912年,民国元年)开始到1935年,他的剧目选择出现了几个重要的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梅兰芳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季看了玉成班班主田际云邀约上海王钟声剧团到北京演出的《禽海石》《爱国血》《血手印》等改良新剧(话剧),尤其是民国二年(1913年)冬季第一次到上海演戏期间看了夏月润、夏月珊兄弟的《黑籍冤魂》《新茶花》等京剧时装戏及欧阳予倩的《茶花女》《不如归》等话剧新戏后,欲意改变自己18岁之前“纯粹唱青衣”的传统路数,从民国四年4月到民国五年9月的这18个月中,他在冯幼伟、齐如山等一批文人和乔蕙兰、陈德霖等昆曲艺人的帮助下,几乎同时开始尝试涉猎时装新戏、古装新戏的新剧目编排和对传统昆曲剧目的学演。这些时装新戏包括《宦海潮》《邓霞姑》《一缕麻》《孽海波澜》《童女斩蛇》等5出②参见邹元江:《对梅兰芳民国初年排演“新戏”的历史反思》,《戏剧》2012年第2期。;古装新戏有《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千金一笑》等③梅兰芳前后编演的古装新戏有《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麻姑献寿》《红线盗盒》《洛神》《廉锦枫》《霸王别姬》《木兰从军》《上元夫人》《西施》和《太真外传》等11出,还有《黛玉葬花》《千金一笑》《俊袭人》等三出“红楼”戏。;昆曲如《孽海记·思凡》《牡丹亭·闹学》《西厢记·佳期·拷红》《风筝误·惊丑、前亲、逼婚、后亲》等④梅兰芳学过三十几出昆曲,常演的有《白蛇传》(“金山寺”、“断桥”)、《牡丹亭》(“游园惊梦”“春香闹学”)、《金雀记》(“觅花·庵会”“乔醋·醉圆”)、《孽海记》(“思凡”)、《西厢记》(“佳期·拷红”)、《玉簪记》(“琴桃·偷诗·问病”)、《风筝误》(“惊丑·前亲”“逼婚·后婚”)、《翡翠园》(“盗令·杀舟·游街”)、《铁冠图》(“刺虎”)、《昭君出塞》(“出塞”)、《南柯记》(“瑶台”)、《长生殿》(“鹊桥·密誓”)、《渔家乐》(“打舟·藏舟”)、《狮吼记》(“梳妆·跪池·三怕”)及吹腔戏《奇双会》(“哭监·写状”“三拉·团圆”)等15出。。
第二个节点是梅兰芳两次访问日本。1919年梅兰芳第一次访问日本,共演出《天女散花》(5月1—5日、5月20日、5月25日)、《御碑亭》(5月 6—8日、5月19日)、《黛玉葬花》(5月 9—10日)、头本《虹霓关》(5月11日)、《贵妃醉酒》(5月12日)、《琴挑》(5月20日、5月25日)、《游龙戏凤》《嫦娥奔月》(5月23日)、《春香闹学》《游园惊梦》(5月24日)等9个剧目10出20次。其中古装新戏《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嫦娥奔月》分别演出了7、2、1次;传统京戏除了《御碑亭》演了4次外,头本《虹霓关》《贵妃醉酒》《琴挑》《游龙戏凤》各演了1次;昆曲《春香闹学》《游园惊梦》两折也各演了1次。
1924年梅兰芳第二次访问日本,共演出《麻姑献寿》(10月20日、10月25日)、《廉锦枫》(10月21日、10月31日、11月11日)、《红线传》(10月22日、10月30日、11月7日、11月12日)、《贵妃醉酒》(10月23日、11月8日、10月28日)、《奇双会》(10月26日)、《审头刺汤》(10月27日、11月1日)、头本《虹霓关》(10月29日、11月3日、11月10日)、《御碑亭》(11月2日)、《黛玉葬花》(11月4日)、《洛神》(11月9日)等10个剧目21次。其中古装新戏《红线传》(即《红线盗盒》)《廉锦枫》《麻姑献寿》《黛玉葬花》《洛神》分别演出了4、3、2、1、1次,其他除了《奇双会》是一出吹腔戏外,只有《御碑亭》《审头刺汤》(即《一捧雪》)《虹霓关》和《贵妃醉酒》是传统京剧剧目。①参见邹元江:《梅兰芳表演美学解释的日本视野——以梅兰芳1919、1924年访日演出为个案》(上、下篇),《戏剧艺术》2014年第3、4期。
第三个节点是梅兰芳第四次到上海演出。梅兰芳民国二年(癸丑)秋第一次应邀到上海丹桂第一台演出,民国三年(甲寅)第二次去②《梅兰芳全集》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292页。,民国五年(丙辰)第三次去③《梅兰芳全集》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299页。,民国九年(庚申)阳历四月八日下午两点二十分梅兰芳一行40余人第四次抵达上海,十二日开始演出,到五月二十四日合同期满临离开上海前,天蟾台主许少卿又挽留十日,前后五十余日。梅兰芳第四次到沪上未加演前43天共演出了43个夜场、7个日场,共26个剧目。④刘豁公编:《梅郎集》卷四,中华图书集成公司,民国九年,第16-19页。其中出演《天女散花》(新戏)6次;《上元夫人》(新戏)4次;《游园惊梦》(昆戏)、《贩马记》(吹腔)、《麻姑献寿》(新戏)、《黛玉葬花》(新戏)、《嫦娥奔月》(新戏)均 3次;《汾河湾》(皮黄)、二本《虹霓关》(皮黄)、头二本《木兰从军》(新戏)、三四本《木兰从军》(新戏)均2次;《彩楼配》(皮黄)、《玉堂春》(皮黄)、《千金一笑》(新戏)、《樊江关》(皮黄)、《狮吼记》(昆戏)、全部《红鬃烈马》(皮黄)、全本《珠帘寨》(皮黄)、《贵妃醉酒》(昆戏)、《御碑亭》(皮黄)、全本《四郎探母》(皮黄)、《春香闹学》(昆戏)、《玉簪记》(皮黄)、《佳期考红》(昆戏)、《邓霞姑》(新戏)、《辕门射戟》(皮黄)、二本《春秋配》(新戏)、三四本《春秋配》(新戏)各1次。⑤以上剧目统计据亚庸撰:《梅屑》,刘豁公编:《梅郎集》卷四,中华图书集成公司,民国九年,第16-19页。舍予撰《上次(注:1920年)梅剧录》与亚庸所录有出入:“爰将上次即庚申年二月二十四日起,迄至四月初七为止,所演诸剧,分类录出,俾资参考焉。 《彩楼配》、《玉堂春》、《汾河湾》、《探母》、《武家坡》、《御碑亭》、《虹霓关》头二本、《醉酒》、《珠帘寨》(以上属青衣旦戏),《樊江关》一次,《千金一笑》、《嫦娥奔月》、《散花》、《葬花》、《上元夫人》、《献寿》(以上属古装戏),皮黄《春秋配》头二本一次,小生《射戟》一次,《木兰从军》头二三四本各二次,《游园惊梦》、《狮吼记》、《玉簪记》、《烤红》(以上昆曲戏计四出),时装戏《邓霞姑》一次,吹腔《贩马记》三次。统计二十五出。惟《散花》演有六次之多。《游园惊梦》及《汾河湾》亦各演三次。(却酬)。”《申报》1922年6月1日第8版。不难看出,这26个剧目,新戏与皮黄各有十出,外加昆戏五出,另有吹腔一出。梅兰芳共50个日夜场演出,除了昆戏7场、吹腔3场外,新剧就占了27场,而皮黄仅有13场。⑥如果加上后十天加演的剧目,像《一缕麻》等新戏的比例更高。这也就印证了亚庸在《梅屑》一文中的“揣度”:
沪人观剧之趋向,大率以新颖为归。则此四十日中,余知必有几度之散花、葬花。而其最为擅长之戏剧,若祭塔、孝感天之类,或始终不见其一演。余自信余之揣度盖不谬也。⑦刘豁公编:《梅郎集》卷四,中华图书集成公司,民国九年,第12页。其实梅兰芳的昆曲也还是不错的,《游园惊梦》此次沪上就演过三次,而且还真有知音:“昨日戏游园惊梦之佳,为海上所仅见。而识者谓即在京城中演之,亦不能细腻熨贴至如此田地。”刘豁公编:《梅郎集》卷六,中华图书集成公司,民国九年,第31页。又云:“游园惊梦之妙,传神阿堵。光景离合,而戏词尤脍炙人口。前日纵覆演,在座者仍极拥挤也。”刘豁公编:《梅郎集》卷六,中华图书集成公司,民国九年,第11页。
的确“不谬也”!鹤有云:“兰芳唱工以反二黄见长,祭塔一出尤为绝唱。”⑧梅社编:《梅兰芳》第八章,中华书局,民国八年,第38页。《祭塔》《孝感天》之类梅兰芳最擅长的开蒙童子功正工青衣戏⑨梅兰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岁正式从时小福的弟子吴菱仙启蒙学青衣戏,就学了正工青衣戏《二进宫》《桑园会》《三娘教子》《彩楼配》《三击掌》《探窑》《二度梅》《别宫》《祭江》《孝义节》《祭塔》《孝感天》《宇宙锋》《打金枝》等,共约三十几出。梅兰芳说:“在十八岁以前,我专唱这一类青衣戏,宗的是时小福老先生的一派。”,他之所以在天蟾舞台一次也没演⑩在此次上海期间,梅兰芳的传统拿手戏只在堂会上演过,野马在静安寺路专电云:“梅兰芳、王凤卿因应某公之请,于今昨两日在哈同花园串演生平拿手杰作。”刘豁公编:《梅郎集》卷七,中华图书集成公司,民国九年,第3页。,恰恰说明梅兰芳是非常了解上海票友的关注焦点的。
无名氏曾著文《平心静气:对梅兰芳解剖一下》曰:“若论梅郎所演各剧,当以旧戏为最好,尤以闺门旦、刀马旦为擅长,如穆柯寨、樊江关等戏,设能配角整齐,实属耐人寻味。余平心而论,梅之旧戏,较胜新戏多,即如青衫之轻易不唱之祭塔,唱来嗓音,颇似一缕游丝,当空袅袅,高下抑扬莫不中节,及今思之,尚醰醰有余味。余听梅戏多年,此剧只聆一度,嗣闻尚小云歌此,音较高亢,似欠柔和。惜此剧梅不常演,至民八九以后,梅即以新戏相号召,嫦娥奔月、黛玉葬花、木兰从军等等,此类戏剧,余于平沪两地,聆之熟矣……余以为兰芳之戏,除木兰从军外,余亦无甚特殊,他如奔月、葬花、西施等等,其姿势皆大略相同,场子亦不见紧凑……”①无名氏此文开篇即说:“此次梅郎去京演戏。”又云:“梅于此时,年龄将及五十。”但从《梅兰芳艺术年谱》的记载来看,梅兰芳自1938年春末结束在香港的演出之后,就租住在半山斡道八号(干德路)一所公寓,毅然决定息影舞台,暂居香港,不再返回已沦陷的上海。这一年他45岁。1942年7月27日梅兰芳借道广州回上海后仍闭门谢客,从未再演出过,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在息影八年后于10月10日复出,在上海兰心剧场重新登台义务演出了《刺虎》。这一年他52岁。由此可知,梅兰芳在“年龄将及五十”的这些年,是不可能“去京演戏”的。从现有的确凿材料来看,梅兰芳从上海“去京演戏”的时间是1936年9月2日由沪乘机赴京,参加从9月6日至10月14日第一舞台梨园公会为救济贫苦同业筹款义务戏演出。这是梅兰芳迁居上海四年后第一次回北京演出。这一年他仅43岁。参见谢思进、孙利华编著:《梅兰芳艺术年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236页、第212页。由此看来,无名氏所说的“此次梅郎去京演戏……梅于此时,年龄将及五十”是可存疑的。《祭塔》是梅兰芳最初从吴菱仙先生嘴里一句一句学会的童子功戏,梅兰芳自己也深知这些童子功戏对他演技的奠基意义。他曾回忆说:“那时学戏的基本功首先是讲求唱功,这是做一个演员最重要的一条,人们讲的是听戏,比如《祭塔》这出戏,听戏的坐在台下闭上眼睛,实际上是在闭目欣赏你的唱功。你的演唱艺术如能使观众静坐而不起堂,那是极其不易的。”②梅葆琛:《怀念父亲梅兰芳》,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可见,真正熟知京剧传统的票友,无论是京都的还是海上的,都还是更加欣赏梅兰芳童子功扎实的“旧戏”,而对他的“新戏”则多有微词,只是出于对梅兰芳的偏爱和呵护,而不愿疾言厉色加以指瑕、评说而已。③参见邹元江:《票友族群与梅兰芳表演艺术的“创新”——以〈梅郎集〉为研究个案》(上、下篇),《民族艺术》2015年第2、3期。
第四个节点是梅兰芳1930年赴美演出。1930年梅兰芳访美剧目除了2月14日在华盛顿参加由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为梅剧团访美演出举行的招待会演出了《嫦娥奔月》《青石山》④《青石山》是由梅剧团的朱桂芳(饰狐精)、刘连荣(饰杨戬)、王少亭(饰吕洞宾)表演的。见北京梅兰芳纪念馆藏梅兰芳在旧金山大埠弯月戏院公演戏单。《千金一笑》外,原本按照总导演张彭春的意见2月17日在纽约正式开演时演出最能代表东方艺术真精神的中国旧剧《汾河湾》《青石山》《刺虎》《空城计》和《霸王别姬》五剧。但2月16日在纽约百老汇四十九号街剧院招待试演后,张彭春感觉有些冗长,于是拿掉了《空城计》和《霸王别姬》两剧,在《汾河湾》《青石山》和《刺虎》之间加上了《剑舞》,这就构成了2月17日正式公演的两个小时的剧目。
在纽约百老汇四十九号街剧院演出的剧目是《汾河湾》(2月16—20、25、26、28日;3月1日日夜两场、3日)、《青石山》(2 月 16—20、25、26、28 日;3 月 1 日日夜两场、3 日)、《剑舞》(2 月 17—20、25、26、28日;3月1日日夜两场、3日)、《刺虎》(2月16—20、25、26、28日;3月1日日夜两场、3日)。
在纽约四十一号街帝国剧院演出的剧目是《汾河湾》(3月3、6日)、《青石山》(3月3、6日)、《剑舞》(3月 3、6日)、《刺虎》(3 月3、6日)、《贵妃醉酒》(3月 9、10、13、15、22 日日夜两场)、《羽舞》(3 月9、10、13、15、22 日日夜两场)、《芦花荡》(3 月 9、10、13、15、22 日日夜两场)、《打渔杀家》(3 月 9、10、13、15、22 日日夜两场)。
应当说梅兰芳在美国的演出,纽约两个戏院上演的剧目是最具代表性的,之后从4月7日开始在芝加哥公主戏院的10天演出剧目与纽约是相同的。只是在4月24日至28日在旧金山大埠弯月戏院、5月7日至9日在旧金山喀皮他尔戏院的演出剧目有了一些变化,增加了《虹霓关》(4月24日)、《天女散花》(4月24日)、《廉锦枫》(4月25日)、《霸王别姬》(4月26日)、《麻姑献寿》(4月26日)、《尼姑思凡》(4月27日)、《黛玉葬花》(4月28日)、《嫦娥奔月》(5月7日至9日)。5月13日起在洛杉矶联音戏院的12天演出剧目和从6月底在檀香山美术戏院的12天演出剧目均没有详细的文献记载,但应当大体上与纽约、旧金山的演出剧目相近。①参见谢思进、孙利华编著:《梅兰芳艺术年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168页。
第五个节点是梅兰芳1935年访苏演出。梅兰芳访苏期间从3月23日至28日在莫斯科音乐厅演出了六场,剧目就是3月22日在高尔基音乐大厅试演的《汾河湾》《剑舞》和《刺虎》。4月2日至9日梅兰芳在列宁格勒维保区文化宫戏院又演出了8天,除了《木兰从军》和加了《剑舞》《袖舞》外,全是传统剧目,其中4月2日的剧目是《汾河湾》《剑舞》和《虹霓关》,3日是《打渔杀家》《袖舞》《刺虎》,4日是《宇宙锋》《剑舞》和《虹霓关》,5日是《汾河湾》《梁红玉》和《刺虎》,6日是《打渔杀家》《剑舞》和《虹霓关》,7日是《宇宙锋》《梁红玉》和《虹霓关》,8日是《汾河湾》《木兰从军》和《刺虎》,9日是《打渔杀家》《思凡》和《虹霓关》。4月13日梅兰芳临别纪念演出的剧目是《打渔杀家》和《虹霓关》。梅兰芳在苏联期间,共演出《虹霓关》6次,《打渔杀家》4次,《汾河湾》《刺虎》和《剑舞》各3次,《宇宙锋》《梁红玉》各2次,《思凡》《木兰从军》和《袖舞》各1次。《虹霓关》被关注与爱森斯坦拍了电影有关。
二
梅兰芳1912年至1935年的剧目选择,尤其是梅兰芳出访日、美、苏的剧目选择有三重视野,即既看重话剧的合道理性,也追求票房的可盈利性和西方的可接受性。由此显现出梅兰芳在剧目转圜上基于商演的表象性与表现方式基于观念差异的本质性。
梅兰芳看重话剧的合道理性是从他民国初年接受齐如山120封信的意见就开始的,并且深深地影响了他一生。1943年由梅兰芳口述、许姬传笔记的《缀玉轩回忆录》一文专门提及“新戏感人”的话题。②梅兰芳口述、许姬传笔记:《缀玉轩回忆录》,《大众》1943年第4期。这里所说的感人的“新戏”就是梅兰芳民国初年编排的时装戏《一缕麻》。梅兰芳认为在他演出的5个时装戏中,《一缕麻》要算是演出效果“比较好一点”的③《梅兰芳全集》壹,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276页。,因为陪他唱这出戏的贾洪林、程继仙和路三宝“都能紧紧地掌握住剧中人的身份和性格”,贾洪林“由于他的演技逼真,连我这假扮的林小姐听了也感动得心酸难忍。台下的观众,那就更不用说了,一个个掏出手绢来擦眼泪”,在天津上演时甚至还“对一桩婚姻纠纷起过很大的影响”。④《梅兰芳全集》壹,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275页。
梅兰芳后来也检讨了在民国初年排演时装新戏所存在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内容与形式的矛盾。⑤《梅兰芳全集》壹,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1页。即日常生活形态与戏曲舞蹈化动作之间的矛盾。梅兰芳感到特别棘手的是,时装戏在“身段方面,一切动作完全写实。那些抖袖、整鬓的老玩艺,全都使不上了”⑥《梅兰芳全集》壹,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20世纪50年代初,他对这个问题做了冷静的思考,他说:“时装戏表演的是现代故事。演员在台上的动作,应该尽量接近我们日常生活里的形态,这就不可能像歌舞剧那样处处把它舞蹈化了。在这个条件之下,京戏演员从小练成功的和经常在台上用的那些舞蹈动作,全都学非所用,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势。有些演员,正需要对传统的演技,作更深的钻研锻炼,可以说还没有到达成熟的时期,偶然陪我表演几次《邓霞姑》和《一缕麻》,就要他们演得深刻,事实上的确是相当困难的。我后来不多排时装戏,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⑦《梅兰芳全集》壹,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页。梅兰芳的这个想法或许有所本。齐如山曾在《与陕西易俗社同人书》中说:“欲艺术精美,则须先练旧戏也。因永排新戏,则各脚之神情、身段必皆模糊而不坚实。倘排新戏太多,更必把旧规全失,而国剧亦随之破产矣。因国剧之规定皆系用美术化方式表现,非将各种方式练的确有根柢者则表演时不能美观;率尔操觚,必不值方家一哂也。”《齐如山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但在20世纪40年代初,他对为何不再演《一缕麻》也言及有其他的原因。
梅兰芳在《缀玉轩回忆录》一文中说:“这出戏里面的配角,最重要的是新娘的父亲,由贾洪林君担任。他真有戏剧的天才,劝女儿上轿,十段道白表情,实在不好做,他在家里烟灯旁边,琢磨了两夜,演出以后,异常精彩。看客真有感动得下泪的,戏词是吴震修、齐如山两位先生,商量着编制出来的,思想非常新颖而深刻!可惜自从贾洪林去世以后,别人简直唱不了,都是敷衍了事,才兴味索然,所以后来我也不常演唱此戏。”①梅兰芳口述,许姬传笔记:《缀玉轩回忆录》,《大众》1943年第4期。显然,与20世纪50年代初梅兰芳口述《舞台生活四十年》不同的是,梅兰芳20世纪40
年代初仍是很认同贾洪林更接近于话剧的“演技逼真”“能紧紧地掌握住剧中人的身份和性格”的时装戏的演法,而不仅仅是怕青年戏曲演员常演时装戏对“传统的演技”就难以掌握的问题。“十段道白表情,实在不好做”,贾洪林便“在家里烟灯旁边,琢磨了两夜”。显然,这不是戏曲优伶进入的戏曲表演状态。对戏曲伶人而言,没有什么“道白表情”是“不好做”的问题,戏曲优伶从小练就的极其复杂化的唱念做打的童子功,别说是将十段道白表情幻化为载歌载舞的极富审美表现力的表演根本不算什么难题,就是上百句的唱段也能美轮美奂地自如表现而不在话下。可问题是一个习惯于戏曲程式思维的优伶突然面对生活化、口语化的时装戏表演时,这“十段道白表情”真的就“实在不好做”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极其出色的戏曲优伶居然也会“在家里烟灯旁边,琢磨了两夜”的根本原因。贾洪林的表演之所以“异常精彩”,恐怕也未必就是完全以话剧式的、日常生活化的道白表情来处理这十段台词,很有可能是将日常生活的道白表情加入了一些富有表现力、感染力的戏曲程式化的处理。而正是这种在当时来说还是很新颖的既非纯粹话剧化也非纯粹戏曲化的表演,让并不熟悉话剧表演,也不情愿像贾洪林这样愿意尝试新的表演的一般戏曲优伶在贾洪林去世后“简直唱不了”,不“敷衍了事”又能怎么办呢?所以,自然难以重现梅兰芳所期望的像贾洪林这样“真有戏剧的天才”的这种表演效果。既然后来的优伶表演贾洪林曾扮演的这一个角色令人“兴味索然”,所以,梅兰芳说此后他“也不常演唱此戏”就是自然的了。言下之意,如果贾洪林仍在,梅兰芳是仍会继续演出像《一缕麻》这样的时装戏的。这就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梅兰芳对时装戏的态度的复杂性。
也不仅仅是时装戏,梅兰芳对传统剧目也是从合道理、合情理的角度加以“纠正剧情”或删减检场。如梅兰芳在国外常演的《汾河湾》并不是完全依照国内的剧情:薛仁贵为了救丁山于虎口而误将他射死。梅兰芳认为这不合情理,所以他就按照原本梆子戏的情节来“纠正剧情”:薛仁贵因妒忌丁山的才能才射杀了他②梅兰芳说:“仁贵射丁山,照梆子戏原是仁贵见丁山小小年纪,打雁镖魚,十分了不得,心想若此儿长大成人,他的两辽王的英名岂能长久?由于这种嫉妒心理才射他的。”梅兰芳:《身段表情场面应改善,改革平剧需要导演——为〈星期六画报〉周年纪念而作》,《星期六画报》1947年第53期“纪念特大号”。,可“这样演出国内观众不认可”,所以他一回国就仍按照国内的演法。他很遗憾地把这改回来的剧情视作是“社会上一般习俗成见是很难破除的”,而并没有反思为何国内的观众不认可这种“纠正”。又如免掉本不该免掉的检场。梅兰芳说:“薛仁贵听说射死的是他的儿子,就当场晕过去了,这老戏叫‘气眼’。原本是由检场的把椅子给移到台中间来,我改让仁贵晕倒在旦角的椅子上。”检场人把椅子移到台中间来让演员表演“气眼”绝技,这原本是为了更加凸显薛仁贵的伤心欲绝的情感,这是非常富有戏曲审美特色的情感外化表演程式。减去了检场人,看似简化、纯净了舞台,更尽乎情理,但却是以淡化甚至消解戏曲独特的审美假定性为代价的。
至于梅兰芳追求票房的可盈利性,这原本就是所有戏班班主都首先要考虑的问题。1920年梅兰芳第四次到上海演出之所以在演出间隙还紧锣密鼓地排演新戏,就是为了赢得更多的票房收入。野马发自平望街的专电说:“梅兰芳现集白牡丹、沙香玉诸云仙与姚玉芙在寓,日夜排练。《上元夫人》剧中有五人合舞一场,不能香人羞错毫厘,故教练甚难,恐演期将改迟云。”又曰:“梅兰芳新编之上元夫人。定于下星期三晚(十二)出演。”①刘豁公编:《梅郎集》卷七,中华图书集成公司,民国九年,第7页。春醪曰:“畹华于本月二十三日合同期满,大约续演十日已成议矣。上元夫人出演,总在三五日后也。”②刘豁公编:《梅郎集》卷六,中华图书集成公司,民国九年,第10页。秋声在南京路电话中又曰:“梅兰芳近日添置最流行之女服甚多,专备演时装剧用。承办裁缝名阿小,获利甚丰。”③刘豁公编:《梅郎集》卷七,中华图书集成公司,民国九年,第4页。可知,在最初的合同中并没有加演新剧的内容,春醪说:“畹华此遭赴沪,初不拟演时装戏,特所演者大都已重复,故尾声定一缕麻、邓霞姑等,天蟾主人亦已牌示矣。”④刘豁公编:《梅郎集》卷六,中华图书集成公司,民国九年,第10页。纷纷在二首路电话中曰:“梅兰芳在沪演剧订约一个月,临时延长未可知。登台第四日,即演新剧。”⑤刘豁公编:《梅郎集》卷七,中华图书集成公司,民国九年,第2页。但事实上梅兰芳却一直在做着加演的准备,而且是满足“沪人观剧之趋向,大率以新颖为归”⑥亚庸:《梅屑》,刘豁公编:《梅郎集》卷四,中华图书集成公司,民国九年,第12页。的喜新厌旧的心态,以新剧为号召。甚至有报道说:“梅郎之妻王夫人闻梅郎将演新剧,恐带出之梳头役数人不合郎意,故于前晚(十六日)九时,乘快车抵沪,即寓望平街许宅云。”⑦羊城:《梅花香屑满申江》,刘豁公编:《梅郎集》卷三,中华图书集成公司,民国九年,第7页。不过,虽然随同梅兰芳“以缀玉轩阁员莅沪者有六人之多”⑧刘豁公编:《梅郎集》卷六,中华图书集成公司,民国九年,第29页。,但这种迎合性的急就章新剧总是比较粗糙的,还累个够呛,春醪就非常客观地报道了这一点:“连日排演新剧,剧之名贵固不待言,而演者亦劳顿异常,晚来一点钟后排演,非三时不已也。”⑨刘豁公编:《梅郎集》卷六,中华图书集成公司,民国九年,第4页。当时的《申报》就直白道:“上元夫人剧本当日草草编簒,回京后尤需更改,故尚非定本尔。”⑩刘豁公编:《梅郎集》卷六,中华图书集成公司,民国九年,第31页。《上元夫人》的剧本是齐如山编的,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藏有这个剧本的齐如山手稿,是用的竖排红线方格纸,上有“梅柳居用纸”红字,右首第一行顶格书“上元夫人”,下空八格书为“齐如山编”,第二行上空三格书“第一场”,第三行至第十行是剧文。该馆还藏有《天女散花》的齐如山手稿本,用纸及格式与《上元夫人》同。显然,编演新剧对并不像京都票友一般熟悉旧剧的沪上票友而言是易讨巧的,但真正懂得戏曲奥妙的票友仍是明白这由缀玉轩“草草编簒”的《上元夫人》并不像报道中所说的那样真的就无懈可击了。其实,应节令的《上元夫人》是1920年3月编演的,用凌霄汉阁的说法,该戏曾在新明(戏)院上演了五日,又在某堂会中演过一次。此番在沪上再演“是‘改造’以后之《上元夫人》。盖初演三日,颂扬者虽多,而讥其杂乱者亦不少。梅夫人盛德谦和虚衷受益,暂停数日,从事于改造,而后续演焉。然犹有谓为虽‘改’而仍不‘良’者。亦有谓本已美已善,改造后乃益尽善尽美者”⑪凌霄汉阁:《梅夫人圣德记》,刘豁公编:《梅郎集》卷二,中华图书集成公司,民国九年,第9-10页。。所谓“颂扬者虽多”是有根据的,《大光明》曾从声调、容貌和技艺三个方面评价《上元夫人》“声色艺之佳可称三绝”⑫参见王长发、刘华:《梅兰芳年谱》,《梅兰芳全集》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7页。。春醪在《梅兰芳束身綦严》一文中也称,新排的《上元夫人》“卖座极盛,预计三日可得万五千元”⑬见上海《申报》1920年5月16日。。然而就像剧中李敬山起内监所说的“这戏是博学的人给我们编的”⑭凌霄汉阁:《梅夫人圣德记》,刘豁公编:《梅郎集》卷二,中华图书集成公司,民国九年,第9-10页。,即这种缀玉轩中文人票友族群攒戏,其性质不同于传统优伶幕表戏和台上见的流水词。这些文人票友族群虽有“博学”,但正如梅兰芳所说的这些“外行人”毕竟不太明白“博学”之词与场上表演还是两回事。所以,梅兰芳明知道《上元夫人》“杂乱”并不成熟,也要每晚后半夜坚持排演,其动力就是要迎合沪上票友趋时趋新的心理,而这就是赢得票房的重要保障。梅兰芳这一次到沪上演出很不同于前三次的地方就是他带了一个四十多人的庞大戏班子,而前三次,尤其是前两次只有他和王凤卿只身被遴选到上海,并没有像这一次要负责这么多人的日常开销和工钱。因此,票房收入首先是梅兰芳要考虑的。
关于梅兰芳追求西方的可接受性,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梅兰芳曾回忆南通张季直先生在他的私邸里特地建了一座“梅欧阁”,作为其对梅兰芳和欧阳予倩的纪念。梅兰芳说:“自后欧阳先生即努力于新剧运动,今日风行的话剧,欧阳先生厥功甚伟,而我始终没离开过本来的格调。”①梅兰芳:《缀玉轩杂感》,《幸福世界》1941年第1卷第7期。这或许是梅兰芳的自许,但他不同于一般优伶的到国外的演出经历,尤其是要寻求西方观众对中国戏曲的可接受性,他不能不有所偏离一些京剧的格调。
1914年梅兰芳也有感于昆曲衰微,开始跟乔蕙兰先生学习了许多昆曲戏。乔先生“在清末曾为内廷供奉多年,为当时北方昆曲界惟一的典型人物”。而最让梅兰芳感到“快心的事”就是虽然他个人不能扶昆曲于即倒,但他却将中国戏曲的精粹昆曲带到了国外;最让他得意的是,“在美国表演,最受观众欢迎的也就是昆曲中的《铁冠图》《刺虎》,连唱四十多次,盛况不衰,由这里就可以表现出昆曲的价值了”。其实,梅兰芳在美国的《刺虎》演出并不是“连唱四十多次”,而应该是“连演四十多次”。1930年梅兰芳访美演出回来后许姬传曾问梅剧团的琴师徐兰沅:“《汾河湾》、《刺虎》两戏,在中国演出时要用两个小时,你们是怎样剪裁的?”徐告诉他:“《汾河湾》里薛仁贵在窑外的大段唱工全删,只唱两句散板就进窑了。《刺虎》里,费贞娥的主曲【滚绣球】也删去,其他唱词和身段也有精简,我们事先反复排练。张彭春先生拿着表,掐钟点,《汾河湾》规定二十七分钟……《刺虎》三十一分钟,时间的准确使美国人感到非常惊讶。”徐兰沅还说:“梅剧团在美国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演了一百场戏,没有唱过一句慢板。”②许姬传、许源来:《忆艺术大师梅兰芳》,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由此可见,戏曲的唱词作为抒情性的主要手段被精简甚至被删去也并不影响故事的连贯性,而故事的连贯性和紧凑性恰恰是西方话剧的基本特征和观众的观赏重心。因此,张彭春为了适应、迎合西方观众的欣赏习惯,精简或删去不具有故事叙述主要功能的唱词,尤其让梅兰芳不用最具有戏曲审美特性的慢板声腔演唱就是明智的选择。不仅如此,张彭春为了满足西方观众对故事情节的关注习惯,在已经将原本两个小时的两出戏删减到不足一个小时的情况下,还在演出前增加了“说明剧情”的环节,而且占用了四十多分钟时间。1935年5月初带领梅剧团返回国内的张彭春在向外交部汇报梅剧团在苏联整个演出的盛况时说:“此次赴苏联表演之梅剧团人员,均系经过选择,故极为整齐,表演时颇能尽力合作,亦能遵守时间。在苏联所演之戏剧,均系中国旧剧,如打渔杀家、虹霓关、刺虎、汾河湾,尤以打渔杀家及虹霓关两出最受欢迎。所表演者,亦与在国内表演者稍有不同,每出均系最精彩之部分,仅须时四五十分钟,俾使观众易于了解。”③《梅剧团载誉归来》,《时事新报》1935年5月6日。由此看来,虽然梅兰芳在苏联的演出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没有具体记载张彭春所要求的每场每一出戏的演出时间及演出前演说者的演说时间,但毫无疑问,苏联戏剧家所期待观赏到最纯粹的戏曲艺术的愿望是要大打折扣的。④当年梅兰芳访美演出,也是为了迎合美国观众的观赏习惯,删去了大段的唱,于是,人们就发现,梅兰芳在面对语言隔膜的观众时“就下意识地偏重做工”了。见许姬传、许源来:《忆艺术大师梅兰芳》,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三
梅兰芳访问苏联,鄂森斯坦因(即爱森斯坦)曾说:“还有一件事我愿意声明的,就是现在苏俄戏剧已经确切规定,要遵循着中国旧剧的途径走,所以此时梅兰芳来俄,可以由自然主义或是由习惯主义,走上写实主义的苏俄戏剧界人士,明瞭中国戏是怎么解决这些艺术的写实主义的问题。这个对于我们的将来研究怎样达到社会的写实主义的目的,可以发生重大的影响。”⑤《苏联戏剧家对梅兰芳之感想》,《时事新报》民国廿四年二月廿五日。见北京梅兰芳纪念馆《梅兰芳游俄记》手抄本。可爱森斯坦绝对不会想到,梅兰芳为了追求西方对他的戏曲的可接受性,实际上已经偏离了作为“旧剧的途径”的戏曲“歌舞”之“舞”的本质。
1932年(壬申)3月,梅兰芳为齐如山的著作《国剧身段谱》作“序”,说齐先生研求剧学已三十余年,对梨园中的老一辈艺术家和后生无不熟稔,“识力既高,又能虚心,逢人必问,故一切规矩知之极深,若纹之在掌。昔年与余谈曰,中国剧之精华,全在乎表情、身段及各种动作之姿势。歌舞合一,矩镬森严,此一点实超乎世界任何戏剧组织法之上。余深服其言。二十年间,余所表演之身段姿式,受先生匡正处亦复不少。近又将各种身段之原则,一一写出,实为历来谈剧著述中之创举,我侪同业旧辈咸视为极重要之发明,深信国剧不至失传,将惟此是赖”。
1932年6月,在梅兰芳、余叔岩倡导成立的国剧学会下创设的国剧传习所开办月余之际,梅兰芳在授课时说:“中国戏曲的起源,是由于‘歌舞’,而它的优点,也就在‘歌舞’能具备艺术的条件:真,善,美。这次我到美国的成功,‘舞’的成分就占大半。‘舞’在现时就叫身段,无论什么角色,做出一种身段得像真,得好看。学旦角身段,最初先练脚步,练脚步看着似乎很易,其实最难。初练应当身直,胸微挺出,小腹微收,两眼看平,普通都以旧式舞台之楼沿做标准。两手呈兰花指,拇指拈中指食指之间,食指与无名指翘平,中指落低,小指曲伸高起。左手抚腹右方,右手与左手相接成半圆式,走起路来,应脚跟先着地,脚尖后着地,循循如一字形。”①梅兰芳讲授,郭建英笔记:《梅兰芳先生之一课》,《国剧画报》1932年6月17日第1卷第22期。
在国剧传习所,梅兰芳虽然也向学员亲授京剧歌唱之法②梅兰芳讲授,郭建英笔记:《梅浣华先生讲授之唱法》,《国剧画报》1932年10月21日第1卷第40期、10月28日第1卷第1期连载。,但显然梅兰芳更看重戏曲的剧舞身段的教授,他和朱桂芳向学员不厌其烦地亲授“剧舞”,涉及“行走姿式”“开门之姿式”“掌灯之姿式”“普通出场”“指物或人之姿式”“双手表示失望或无可奈何”“双手表示拒绝或不接受”“三羞”“自刎”“上马下马”“上船下船”“上楼下楼”“上轿下轿”“上车”“花旦之行走”“花旦之出场”“指头”“醉步”“拆书与写信”“进宫殿与进门之不同”“进帘子”“醉酒之指雁”“醉酒之上轿”“醉酒之卧云”“醉酒之鹞子翻身”“跪”“旦角之站立法”“眼神”“追逐”等旦角的基本身段和各剧目中的某一句唱词或某一个动作的身段或一组身段,如《汾河湾》中之“有道是远”、《穆柯寨》之射箭、《虹霓关》丫环之打板子、《战蒲关》之托香盘、《武家坡》之扬土、《梅龙镇》之拾巾、《武家坡》之关窑门、《御碑亭》之滑步、《武昭关》之服饰、《梅龙镇》之出场、《梅龙镇》之卷帘、二本《虹霓关》丫环之出场、二本《虹霓关》丫环之“思春”与“擎茶”等。③梅兰芳、朱桂芳示范,郭建英笔记:《剧舞笔记》,《国剧画报》第二卷1932年11月4日第2期、11月10日第3期、11月17日第4期、11月24日第5期、12月8日第7期、12月22日第9期、12月29日第10期;第二卷1933年4月20日第14期、4月27日第15期、5月18日第18期、5月25日第19期、6月1日第20期。
由于对戏曲“剧舞”的重视,梅兰芳1935年访问苏联后又旧话重提:“由梅剧团赴美游俄两次成功的经验,我们感觉到中国戏剧的‘舞’比‘歌’还要重要。因为欧美人士听不惯中国语言,听不惯中国的音乐;而他们所能领会的,也就仅是表情的姿势和舞蹈的身段。由此我们可证明,中国戏剧在欧美,能博得很大荣誉的原因,不是‘歌’而是纯粹的‘舞’。”④梅兰芳先生教授,郭建英绘图笔记:《〈霸王别姬〉之舞剑》,《戏剧旬刊》1936年第13、14、15、16、18期。可见,梅兰芳给予苏联观众的是一个片面的中国旧剧的传统,即多剧舞而少声腔的戏曲艺术,而这个剧舞也是话剧体验式的合道理的“舞”。爱森斯坦曾非常推崇梅兰芳的表演,尤其是《虹霓关》,他甚至将这个戏的东方氏与王伯党“对花枪”的一节拍成了电影,认为电影也应当这样来演。为什么《虹霓关》如此触动电影艺术家?这从梅兰芳(与朱桂芳一起)向国剧传习所的学员讲解示范二本《虹霓关》丫环之“思春”与“擎茶”的剧舞身段似可显现其中的端倪。
《虹霓关》之丫环,老先生孙怡云讲,本是东方氏之乳娘,昔为老旦应行,近因添出许多情节,故改为闺门旦。东方氏出场念引子,定场诗,话白完后,叫起原板,唱至第三句叫板,由胡琴拉小过门作春困状,两手相揉伸懒腰向左打哈唏,以右手靠椅背垫头,左手搥腰,冲嘴三次应三小锣。睁眼揉手作神想状,慢慢向右伸懒腰,以右手垫椅背枕头再睡,冲嘴三次,揉手擦眼弹垢作回忆状,意似刚才两军阵前,遇见那个美貌王伯党,被我用计擒来,如何才能够成为夫妇呢?将手卷(当为“绢”——引者注)左右两翻,右腿迈过右(当为“左”——引者注)腿,将手卷起,一端用口衔着,一端按于膝上复作情思状,停片时忽然想起:我与他交锋时衔着一彩球,是这样美丽,这样可爱,但是放在哪去呢?急在左右袖口寻看皆无有,立起搓手作焦急状,复搓臂部,两手一拍同时齐往腹部一拍,似焦急万分状,但在拍腹部时,忽然一惊,再嫣然一笑,则彩球在此矣。
此时窃在两旁四顾,右手扶椅背,右腿迈于左腿之上,右手伸入腰作掏彩球状,忽然一惊愕,神思极镇静,似门外有响声,蹑足至门外作探视状,以右手摇向台,似告无有何人……①梅兰芳、朱桂芳示范,郭建英笔记:《剧舞笔记》,《国剧画报》第二卷1933年4月20日第14期、4月27日第15期、5月18日第18期。
梅兰芳这段“思春”与“擎茶”的剧舞身段的解说,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很像话剧导演在给演员说戏,交代演员表演每个动作的心理活动,要做到合情理、合道理。那么,是谁给梅兰芳如此的话剧式的说戏影响呢?当然最初是民国初年游学欧洲的齐如山给梅兰芳120封信的影响,以及之后李释戡、吴震修等留学日本的文人与齐如山在帮助梅兰芳编排新戏时不期然将西方话剧的观念传递影响了他。但真正意义上对梅兰芳的话剧思维有直接影响的,当是梅兰芳1930年访美期间张彭春作为梅兰芳聘请的总导演和总顾问给梅兰芳留下的极其深刻的印象。
1930年2月14日,梅兰芳在华盛顿参加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为梅兰芳剧团访美举行的招待会上演出《嫦娥奔月》《青石山》尤其是《千金一笑》终场之后,当时正在美国某大学讲学的张彭春也应邀观戏,他到后台化妆间向梅兰芳道乏,梅问:“今天的戏,美国人看得懂吗?”张说:“不懂,因为外国没有端阳节,晴雯为什么要撕扇子,他们更弄不清楚。”梅兰芳紧握张彭春的手说:“这次我们的计划以自编的古装歌舞剧如《天女散花》等为主,大都情节简单,照您的说法要另选剧目,请您帮忙代我重新组织安排一下。”张说很愿意,他的讲学可以推迟些日子,但他提出必须征得家兄张伯苓的同意。由此,梅兰芳即刻给冯耿光打电报,请他转达张伯苓。当张彭春与梅兰芳一同到达纽约时,接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同意的电报。由此,梅兰芳正式聘请张彭春担任梅剧团访美演出的总导演和总顾问。这是梅剧团第一次建立导演制。②参见许姬传、许源来:《忆艺术大师梅兰芳》,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2页。
张彭春作为总导演除了要确定上演的剧目、剧场表演的方式等事项外,给梅兰芳留下终身影响的就是现场由张彭春极其严格地说戏排戏,这是过去的戏曲优伶从未经历过的。从现有的文献看,梅兰芳在美国演出期间张彭春起码集中为梅剧团排演过三次戏:第一次是3月3日梅剧团由纽约百老汇49号街剧院(49#Sheet Theater)移至41号街帝国剧院(Imperial Theater)仍在上演《汾河湾》《青石山》《剑舞》和《刺虎》剧目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4日,张彭春就在帝国剧院指导梅剧团排演了《打渔杀家》《贵妃醉酒》《芦花荡》和《羽舞》。第二次是3月6号,梅兰芳随张彭春出席了一个戏剧美术文学界知名人士的演讲会之后,又到帝国剧院由张彭春导演排演了《打渔杀家》,张先生尤其注重演员的身段和表情。就在这天晚上演出结束后,张彭春又再次召集梅剧团全体成员排演《打渔杀家》。正是经过张彭春这几次的反复导演排练,直到3月9日,张彭春才让梅剧团在帝国剧院为戏剧界、作家、赞助者和记者试演了《贵妃醉酒》《羽舞》《芦花荡》和《打渔杀家》。取得了成功以后,张彭春才决定3月10日梅剧团正式开始将原来上演的剧目《汾河湾》《青石山》《剑舞》《刺虎》换成《贵妃醉酒》《羽舞》《芦花荡》《打渔杀家》,结果取得了盛况空前的效果。①许姬传说:“美国的风气,只要在纽约打响了第一炮,其它城市就一帆风顺,左右逢源。所以在纽约上演后能否叫座是关键所在,那时正逢美国经济危机,事先大家心里都很嘀咕,选定了49号街剧院是因为这是上演歌剧的高级剧院,座位只有一千个,演了十四天,由于上座率好,后来就移到帝国剧院(Imperial Theater)演出,那里有两千多个位子,又演了二十一天,观众达七万多人次,在市面不景气的时候,可称奇迹。”见许姬传、许源来:《忆艺术大师梅兰芳》,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第三次是3月17日,梅兰芳在参观纽约花会并拍摄电影以作纪念后,仍前往帝国剧院排演《春香闹学》。②参见谢思进、孙利华编著:《梅兰芳艺术年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163页。关于这几次张彭春亲自导演排戏究竟是如何进行的,现在已很难具体知晓,只是从当年参加过排演的演员的零星的介绍里知道张先生是非常严肃苛刻的,谁都怕张先生,“连梅大爷都得听他的,人家是外国的博士,懂得洋人的脾胃”。姚玉芙曾对许姬传说:“梅剧团赴美演出时,每个节目都经张彭春排练过,于是剧团有一句口头语‘张先生上课啦!’”③许姬传、许源来:《忆艺术大师梅兰芳》,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41-42页。比较详细记载张彭春给梅剧团导演的是梅兰芳《身段表情场面应改善,改革平剧需要导演——为〈星期六画报〉周年纪念而作》一文。梅兰芳曾回忆说:“原来的平剧只有说戏而没有导演的,演员和舞台工作者如场面也不太听说戏先生的话。但我在莫斯科演出时每一戏在上演前,都须经过仔细的商讨和严格的排练。那时我们的导演是当时南开教授张彭春(P.C.Chang)。彩排(Drott Roho.Arsal)时,张彭春、余上沅和齐如山三位先生坐在台下看着,遇有不合适的地方,马上叫‘停下再来’,常有反复排练达五六次的。从演员到场面谁也不敢不听,就是我也很害怕张先生的。”④见《星期六画报》1947年第53期“纪念特大号”。当年担任梅兰芳到苏联访问演出总导演的是张彭春,副导演是余上沅,齐如山并没有去苏联,只负责国内的筹备事宜。见《梅兰芳游俄记》许姬传“序”及“人事问题”,《梅兰芳全集》第七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第23页。
梅兰芳在他的回忆录和文章中也多次提及张先生的导演的意义,甚至认为“将来的新平剧一定要有严格的导演才会有完整的好戏”⑤梅兰芳:《身段表情场面应改善,改革平剧需要导演——为〈星期六画报〉周年纪念而作》,《星期六画报》1947年第53期“纪念特大号”。。其实细想一下,张彭春为梅剧团导演的主要方式就是话剧式的“说戏”,即告诉这些戏曲艺术家,你们的每一个身段、表情为什么要这么做,怎么做才是合道理、合情理的。这就是将表演的潜台词、心理活动加以说明,这样所演的戏,即便是美国观众听不懂台词,但仅仅是通过演员身段动作表达情节、情感的准确性,观众也能够看明白这种载歌载舞表演的主要内涵。当时,张彭春和梅剧团开了一个会,他说:“外国人对中国戏的要求,希望看到传统的东西,因此必须选择他们能够理解的故事。中国戏的表演手段唱、做、念、打,但这些都为剧情服务,外国人虽不懂中国语言,如表情动作做得好,可以使他们了解剧情……”⑥许姬传、许源来:《忆艺术大师梅兰芳》,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也即是说,张彭春原本并无意将话剧的导演方式强加给梅剧团的艺术家,但为了让熟悉话剧、电影的美国观众能够多少明白一点每一处戏曲所要表达的主要内涵,就只能将话剧的说戏方式用来导演戏曲,主要目的自然是为了中西演员与观众的有效理解与沟通。这与他将剧目中大段的唱段删除或压缩、演出前加上故事情节的英语介绍等方式都是同样地面对异国观众的传播策略。
但正是这种话剧式的说戏导排,却不期然给梅兰芳及梅剧团的每一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梅兰芳在离开纽约之前,美国戏剧评论家斯达克·杨曾对梅兰芳作了四个小时的专访,斯达克·杨下面的话让梅兰芳也惊讶他一眼就看出了自己表演的问题:“我对梅君所唱的女声,觉得毫无隔膜,我感到梅君小嗓与女子真嗓相比较还是协调的,戏中的身段和平常人的动作也是美术化了的,听了看了非常舒服,但我觉得梅君的嗓子很好,似乎不敢用力唱,你怕美国观众不能领略中国歌唱的妙处,其实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美国人既然公认中国戏是世界艺术,就应该努力发挥固有长处,因为许多人不是为取乐,而是抱着研究东方艺术而来的。……我想,梅君在中国演戏,一定比在美国好。在这里演出,我看出有迁就美国人眼光心理的迹象,我奉劝不要这样,致损及中国戏的价值。”面对如此坦率又精准的批评,梅兰芳对斯达克·杨当即表达了真诚的谢意:“您认为我对言语不通的陌生观众,能否领略中国戏的唱腔有问号,这就敏锐地说到要害,我将根据您的意见,解决我心理上的矛盾。此后,我还打算到欧洲去旅行演出,今天一席话,对我有启发有收获。”①许姬传、许源来:《忆艺术大师梅兰芳》,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但显然,梅兰芳在此后的表演中虽有所调整,可他在演讲、示范解释戏曲身段、戏情时,仍有意无意间留有话剧式的思维痕迹。梅兰芳从美国回来后,朱季黄曾对许姬传说:“我看他的戏,感觉到唱与做不平衡,唱的技巧未见提高,而手、眼、身、步的目的性,却比以前准确而强烈。过了一个时期,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但不是恢复原状,而是进入了新境界。”所以,许姬传说:“由此可以证明,演员对语言隔膜的观众就下意识地偏重做工,当回到老观众中便很自然地又起了变化。”这就是梅兰芳事后所说的:“演员与观众的关系是密切而微妙的,经过这次交流后,不仅唱、做方面有所演变,对化妆、声学、光学、剧场管理、严格遵守时间,都有新的体会,古人强调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非亲身经历,不知其中甘苦。”②许姬传、许源来:《忆艺术大师梅兰芳》,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梅兰芳《四十年戏剧生活》这篇回忆文章的第三部分是“编导古装新戏时代”,而跳过了民国初年他从上海回到北平后有意学习上海的新戏而编演五出时装新戏的这段经历。梅兰芳在这篇文章中是否有意舍弃这一段重要的经历,我们从他尝试编演古装新戏的基本观念可以做出一些判断。梅兰芳说在第一出古装新戏《嫦娥奔月》借助古代名画取得演出成功之后,就开始继续探索排演古代装饰的《黛玉葬花》。他说:“当时很研究了一阵,有人说,《红楼梦》记述满洲贵族家庭,应该旗装说京白,这个理由是很对,不过这么演法,于话剧相宜,歌舞剧就嫌不庄重,同时贾宝玉如果穿着袍褂,未免显得俗气,更不能表现林黛玉的绝世聪明,而且著书的人,在第一回楔子里面,就声明所记事迹,朝代同地点都不可考,这是著者的一种玄妙的技术,后人种种影射揣测,其实多事。所以多数人主张用古装来表演此剧,一则可以尽量发挥林黛玉的才华,二则可以在葬花时表演种种姿势,所以第一次演出,大家都很满意,认为理想中的林黛玉,应该是这个样子。要知道这出戏何以前人未曾排演,大概就因为服装的关系吧。以后又续编红楼剧,如《晴雯撕扇》、《俊袭人》等,此为古装戏之萌芽时代,以后各地纷纷摹仿排演,成为一种风气。”由此可见,梅兰芳通过时装新戏的编演,已经对话剧与戏曲的差异有了相当清晰的认识,什么表演方式,包括服装、念白、身段(姿势)等是“于话剧相宜”(求真可考),还是更与歌舞形态(求美玄妙)的戏曲相合,通过古装新戏的成功,梅兰芳心里是更有底了。所以,在这篇回忆自己四十年戏剧生活的文章中,梅兰芳显然是有意舍弃曾经尝试的时装新戏的这个时段,而更加关注与古装新戏直接相关的古代歌舞的戏曲化转换问题。他说:“我对于古装有了成绩之后,就进一步研究各种古代歌舞,如《天女散花》之风带舞,《麻姑献寿》之袖舞,《西施》之羽舞,《上元夫人》之拂舞,《太真外传》之霓装舞;而《霸王别姬》之剑舞,最费功夫,因为这种舞剑,是歌舞中之舞,不是武术当中的击剑舞,又要跟音乐调和,所以费的研究时间最多。”③梅兰芳:《四十年戏剧生活》,《华文每日》1943年第9卷第9、11期,第10卷第1期。梅兰芳先生教授,郭建英绘图笔记的《〈霸王别姬〉之舞剑》一文就是佐证。严格说起来这不仅仅是一篇一般的口述记录文字,而是对舞剑的舞台调度的平面绘图(共22幅)和对梅兰芳舞剑的身段影像(共30幅)的注释说明文字。应当说这是过去的优伶传承方式中从未有过的一种极其直观生动的戏曲舞剑身段的立体图谱(乐谱)记录。④梅兰芳先生教授,郭建英绘图笔记:《〈霸王别姬〉之舞剑》,《戏剧旬刊》1936年第13、14、15、16、18期。表面上看,梅兰芳之所以对《霸王别姬》的舞剑如此上心,是有点迎合西方观众的观赏戏曲艺术的重心在舞蹈的心理,即“《霸王别姬》的舞剑,是梅先生欧美表演主要的节目,是欧美艺术家最欢迎的一段,也是全出戏最精彩的一节”⑤梅兰芳先生教授,郭建英绘图笔记:《〈霸王别姬〉之舞剑》,《戏剧旬刊》1936年第13期。,但客观上讲,这种重歌舞的古装新戏是从根本上回归了戏曲艺术,尤其是昆曲艺术原本就载歌载舞的本体审美特征。
梅兰芳访苏演出最令人吊诡的是苏联艺术家认为梅兰芳是真正代表中国戏曲的传统,苏联戏剧界也已经确定,“要遵循着中国旧剧的途径走”。可事实上梅兰芳在苏联的演出正如他在美国的演出一样,并没有真正遵循“中国旧剧的途径”,而是在导演、检场、剧情、身段表情等各个方面都加以了适应西方观众的改革。虽然梅兰芳也说“我归国后便把改良过的地方差不多又都给改回来了”,但有些改革,梅兰芳就是回国后也仍在坚持,比如《打渔杀家》的表演。梅兰芳说:“外国东西,当然也不会全好,在莫斯科时曾参观某剧场水景,系用四人扯着几匹蓝绸子抖着象征水波。配上灯光显得小舟一叶波浪间。及至他们看了我演《打渔杀家》,在渔舟上的身段,他们颇自叹不如,说他们那太笨了。熊先生曾说《打渔杀家》第一场桂英在艄后虽系避开生客,但仍应作种种洗杯煮酒等身段,而不应闲着。我在外国演出时恰是那样的。但回国后人家说那样演会分散观众对前面的注意,所以我取消了。但今年在天蟾舞台(戏剧节)我演《打渔杀家》的时候我仍是做了一些身段的。”①梅兰芳:《身段表情场面应改善,改革平剧需要导演——为〈星期六画报〉周年纪念而作》,《星期六画报》1947年第53期“纪念特大号”。这个“熊先生”,是话剧导演熊佛西,还是梅兰芳1935年访问英国时送他《萧伯纳戏剧全集》的熊式一②熊式一是在1935年4月20日梅兰芳结束了在苏联的演出和参观之后赴波兰、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等地考察戏剧期间,5月17日专程从伦敦到法国邀请梅兰芳一同出席在西班牙举行的万国笔会年会的。5月26日熊式一陪同梅兰芳抵达伦敦。在伦敦期间(梅兰芳在1935年7月乘坐康特凡第号经大西洋入地中海,穿苏伊士运河到红海过印度洋,途中在埃及、印度和新加坡停留,于8月3日下午抵达上海招商局北栈码头,结束了苏联欧洲之行),熊教授接待了梅兰芳,并在赠给梅的《萧伯纳戏剧全集》的扉页上题词曰:“畹华兄虚心不耻下问,对于泰西戏剧孜孜攻之,常百观不厌,在英下榻我处,每晚必同至一剧院参观新剧,固不致有所遗漏,旧剧则难图晤对,今赠此册,暇中故可开卷揣摩也。”见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另见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1页。该书第141页、第156-157页均有梅兰芳与熊式一的合影。教授不得而知,但两人都是研究话剧的教授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向梅兰芳提出逼真意义上的桂英在避客时也不能闲着,应像生活真实一样继续做洗杯煮酒的身段就是必然的。问题在于,梅兰芳在苏联就这么演了,回国后仍这么演,有些偏离了京剧“本来的格调”③梅兰芳1952年底到1953年初第二次顺访苏联的三次演出仍是迎合苏联观众的欣赏习惯,尤其《霸王别姬》仍是演“剑舞”,突出戏曲的“剧舞”性。参见《梅兰芳全集》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159页。1953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梅兰芳到朝鲜慰问志愿军,曾在地下剧场演出《霸王别姬》中的“剑舞”,朝鲜党政领导人金日成、崔庸健、洪命熹等观看了演出。参见梅兰芳:《我在平壤的时候》,《文艺报》1954年第4号。关于梅兰芳《霸王别姬》的“剑舞”问题,还可参见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6页、第178-187页。,也即梅兰芳并不明白这种逼真的表演恰恰是违背戏曲表演美学精神的。
许姬传曾在《梅兰芳表演体系的形成和影响——缀玉轩诸老和梅兰芳》一文中提出:“梅派大发展的关键是把中国古典戏曲介绍到国外,扩大影响,载誉而归,这和缀玉轩诸老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④许姬传、许源来:《忆艺术大师梅兰芳》,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如果真像许先生所言,“梅派”形成发展的主要契机就是“把中国古典戏曲介绍到国外”,那么,我们对“梅派”的实质就有了边界清晰的划分。仅仅从梅兰芳1912—1935年表演剧目的转圜,尤其是梅兰芳从1919年到1935年的四次出访日、美、苏所发生的从剧目、剧情、身段、表情、导演、检场、声腔、服装、音乐、灯光、布景等一系列的不同于国内演出的变化,我们就可以非常明晰地看出,“梅派”的形成发展并非完全是对古典传统戏曲表演审美精髓的凝聚,也没有真正回归到“旧剧的途径”,而恰恰是建立在相当大程度上对传统戏曲审美精神偏离基础之上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四大名旦”程、荀、尚相比,作为旦角的梅兰芳既不能真正代表中国古典戏曲旦行表演的审美本质,也是要与中国古典戏曲的审美精神相区分划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