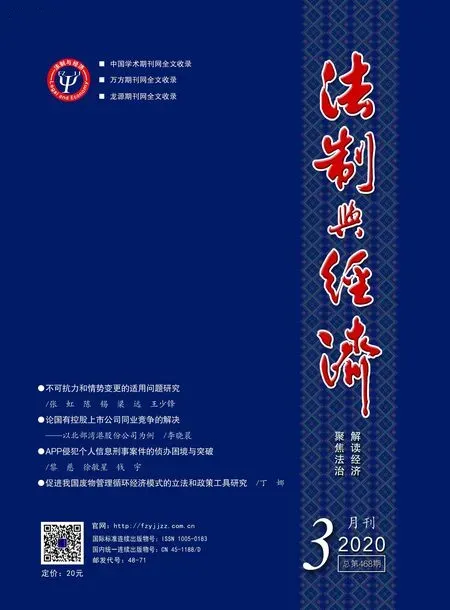对立法增设“非法放贷罪”必要性之探析
邓晨亮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南 长沙410006)
一、非法放贷入刑之必要
(一)非法放贷危害巨大
有学者尤其是经济学方面的学者认为,高利贷具有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帮助中小企业渡过融资难关等作用,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功大于过的,高利贷不应入刑。该类学者的观点破绽之处在于,首先,高利贷之借款人并非只有中小企业,相反借款人在现实中多为个人,而个人借高利贷并非用于投资实业,其行为是否有利于民营经济难于体现,不仅如此,高利贷都能造成个人借款人失学、被迫卖淫、自杀、为偿还欠款而抢劫盗窃等危害后果。其次,高利贷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同时有诱导民营实体经济投向高利贷行业之危险。①高利贷行业是暴利行业,利润空间巨大,而民营实体行业投资周期长、见效慢、利润空间较小,民营实体行业在高利贷超高利润的诱惑之下很容易沦陷转而投资高利贷,从而最终导致国家实体经济的衰败。再次,中小企业借了高利贷之后一旦无力偿还,面对高额的利息,往往只能走向破产,高利贷名为救了实则是害了中小企业。最后,高利贷之放贷者为了不承担任何商业风险往往使用暴力催收、虚假诉讼、侵犯他人隐私、与黑恶势力勾结等违法犯罪手段,这些手段行为严重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了司法秩序。
对此问题,该类学者辩解称,高利贷本身无罪,罪在催收手段之本身,催收手段如涉嫌犯罪的以现有之罪名惩处即可,作为合法部分的高利贷本身还是要保护的。细究发现,该类学者区分高利贷行为与非法催收行为本无可厚非,但其将高利贷行为与非法催收行为完全割裂联系的做法是错误的。②根据事物之间均有其联系的观点,高利贷行为往往甚至是必然导致非法催收行为之发生。试想,一个借款人之所以借款往往在于其经济能力不强,现在一个经济能力不强的借款人面对超高额的本息往往是没有能力按时还款的,借款人一旦逾期还款,放贷人在对借款人加征违约金的同时,为了不容忍本应承受的任何商业风险,通常对借款人采取各种非法手段以催收债务。可见,高利贷行为常常或者说必然伴随着非法催收行为,高利贷并非无害,高利贷之害在于引发非法催收。
(二)前置法调整受控,必须启用最后法调整
对高利贷行为之调控,民法的做法是划定了“两线三区”,对年利率24%以内的给予保护,24%至36%之间的不保护也不反对,超过36%的部分不保护。面对高利贷,民法唯一能做的就是“不保护”,但“不保护”能够遏制放贷人采取暴力催收、虚假诉讼、侵犯他人隐私、与黑恶势力勾结等非法手段吗?不能。放贷人唯一的后果只是不能攫取超高部分的利息而已,与超高利润的利益相比,超低的违法成本已经助长了非法放贷者的野心,民法对高利贷的调整力度不大。
针对高利贷,行政法立法方面目前已经颁布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均有所涉及,但规定的法律后果较轻,惩治力度较弱,根本无法有力打击放贷者攫取超高利润的积极性。可见,面对高利贷,行政法也已经束手无策了。
对某个不良行为的规制,能够通过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解决的就绝对不能动用最后法,只有在前置法调控失效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启用最后法。因此,既然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面对高利贷行为已经束手无策,如此启用刑法调控高利贷行为就顺势而出了。
(三)前置法并非违法性判断之前提
违法性判断具有一元性,即评价某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唯一的判断标尺是刑法,前置法上的评价不能左右刑法的判断(但某些以前置性违法为违法前提的法定犯除外)。③司法实践中,行为人非法放贷涉嫌犯罪,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主张其构成民间借贷而非犯罪,其应承担的是超过法定利息不予保护的法律后果而非刑事责任。但明显辩方的主张是不应该得到支持的,因为刑法进行违法性判断不受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影响,行为是否可以评价为民间借贷对刑法将该行为评价为犯罪不能产生阻碍效果。如在侵占罪案件中,被告人的侵占行为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并不能阻碍刑法将其评价为侵占罪。
(四)高度危险性是惩罚之根据
高利贷等非法放贷行为之害,在于高利贷具有诱发其他犯罪如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犯罪的高度危险性。④该高度危险性也正是刑法对高利贷等非法放贷行为进行规制的根据所在,高度危险性并非实际侵犯了何种法益,为何为刑法所不容?
刑罚的目的是预防,为了预防犯罪,有时候需要对本身并不侵犯法益的行为提前进行处罚。⑤例如,我国刑法之所以严厉惩罚丢失枪支不报告行为,并不是因为丢失枪支不报告行为能侵犯到何种法益,而是为了预防捡拾者利用该枪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又如,我国刑法规定了传授犯罪方法罪,并非传授犯罪方法本身能侵犯到何种法益,而是为了预防被传授者利用习得的犯罪方法去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同理,刑法之所以应对高利贷等非法放贷行为进行规制,在于高利贷具有引发其他犯罪的高度危险性。
从犯罪预防的角度来说,刑法为了预防高利贷等非法放贷行为可能引发的其他犯罪而将其入刑。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来说,刑法对一个行为进行惩罚无非是该行为对法益有所侵犯。实际侵犯了某种法益,刑法要对其加以制裁;未实际侵犯某种法益但对法益保护存在威胁的,刑法也要对其加以制裁。高度危险性便是这样一种对法益保护有高度威胁的存在,因此,刑法要对这种高度危险性之行为加以制裁。
二、以“非法放贷罪”规制之必要
(一)以诈骗罪规制“套路贷”能力不足
2019年两高两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规定,针对“套路贷”,行为人没有采用暴力、威胁手段的定诈骗罪,采取了其他手段的要数罪并罚或者择一重处。该意见的基本观点是,“套路贷”应该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但深入研究不难发现,以诈骗罪规制“套路贷”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套路贷”,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且行为人有采用各种手段形成虚假债权债务之欺骗行为。从形式上看这完全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诈骗罪要求行为人有欺骗行为以及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但司法实践中存在没有欺骗行为或者没有错误认识“套路贷”,以诈骗罪对其进行规制则显得有些棘手。⑥如司法实践中放贷人为规避打击,摒弃了“欺骗”环节,其明确告诉借款人借据上虚高部分为保证金,借款人如未能按期偿还实际借款则按照借据上的数额偿还。放贷人也没有故意制造借款人不能还款的障碍,不能还款的原因系借款人无力偿还。此时放贷人并无欺骗行为,以诈骗罪对该“套路贷”行为进行规制实为不妥。再如,司法实践中放贷者为实施“套路贷”而实施了欺骗行为,借款人对放贷者之“套路”很熟悉,其因资金短缺等原因借了款,后借款人不想还款就以自己受到欺骗为由报警,此时因借款人自始至终未曾产生错误认识如以诈骗罪制裁放贷者未免不妥。因此,以诈骗罪规制“套路贷”之类非法放贷行为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为了打击“套路贷”之类非法放贷行为必须寻找一个“能力更强”的罪名。
(二)以非法经营罪规制高利贷并不恰当
2019年两高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下文称《意见》),该《意见》规定,对高利贷等非法放贷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成立非法经营罪,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违反国家规定”有至少两个层次,一是违反的国家规定只能包括法律以及行政法规,而不包括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等,二是该国家规定将该行为作出“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⑦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虽然明确严禁放高利贷,但该通知属于部门规章,违反它并不属于“违反国家规定”。《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虽然属于行政法规,但该办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将自有资金放高利贷的行为应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违反它也不属于“违反国家规定”。可见,“违反国家规定”前置性违法条件未能满足,非法经营罪就不能成立,《意见》以非法经营罪规制高利贷行为实为不妥。
(三)以高利放贷罪规制非法放贷打击不力
当某一不法经济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其在日常生活中又十分常见,同时该类行为存在独立的罪质,以现有罪名对其进行制裁不能起到较好效果时,此时应将该类行为单独成罪以单独的罪名对其制裁才对,这不仅有利于打击此类新类型犯罪,而且有利于公众对新罪名的理解。因此,对高利贷、“套路贷”等非法放贷行为,以现有之罪名如诈骗罪、非法经营罪等进行规制均不能起到应有之效果,应对非法放贷行为单独成立罪名。
对非法放贷行为单独成立罪名,目前学术界有两大主张,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单独成立“高利放贷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单独成立“非法放贷罪”。但立法设置“高利放贷罪”有不妥之处,高利放贷罪打击的是收取高额利息的非法放贷行为,非法放贷罪打击的是包括收取高额利息在内的一切非法放贷行为。⑧“高利”只是“非法放贷”的表现形式之一,不足以覆盖“非法放贷”的全部社会危害。⑨如放贷的利息没有超过年利率36%,但放贷者经常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催讨债务,致使多名借款人自杀身亡的,该类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如以“高利放贷罪”进行评价则只能是无罪,但将其评价为非法放贷罪则问题迎刃而解。
三、结语
对高利贷等非法放贷行为,现有罪名难于起到打击犯罪之效果,立法增设“高利放贷罪”又有打击范围过窄的不足,在立法上增设“非法放贷罪”最为合适。高利贷、“套路贷”等非法放贷行为已经日益猖獗,形势严峻,立法上增设“非法放贷罪”已经迫在眉睫,立法机关应该尽快考虑。
注释
①②④⑤周铭川.论刑法中高利贷及其刑事可罚性[J].法治研究,2018。
③王双印.论刑法中的违法性认识[D].黑龙江大学,2009。
⑥闵达.“套路贷”案认定分歧的审查判断[J].中国检察官,2017(11)。
⑦王志祥,韩雪.论高利放贷行为的刑法命运[J].法治研究,2015(9)。
⑧周娆.关于民间借贷中高利贷现象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4。
⑨王心馨.厉莉代表:建议刑法分则中增设“非法放贷罪”,稳定社会 秩 序[J/OL].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22362,2018-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