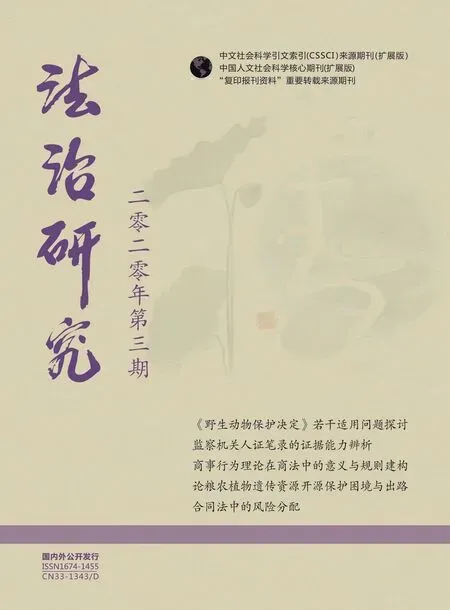《野生动物保护决定》若干适用问题探讨*
叶良芳
2020年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决定》),自即日起施行。从非典疫情到新冠疫情,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让人类接连付出惨痛的代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再一次给人们敲响警钟。疫情当前,既要反思如何从源头补齐野生动物保护存在的短板,又要站在全局高度平衡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的关系。《野生动物保护决定》聚焦野生动物保护的突出问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修改之前,先及时明确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和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等最为紧迫的事项,有利于从源头上防范和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野生动物保护决定》在宏观上以全面禁食野生动物为导向对相关法律的未来修改指明了思路和方向,在微观上确立了加重处罚制度、参照适用制度、全面禁食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鉴于《野生动物保护决定》在相关制度和规则方面较现行法律存在重大变化,因而有必要探讨其内在的设计机理,以便准确地予以适用。
一、关于“加重处罚”的规定
《野生动物保护决定》第1条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禁止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的,必须严格禁止。”“对违反前款规定的行为,在现行法律规定基础上加重处罚”。该条规定恢复了立法实践中陈年搁置的加重处罚的“罚则”,其正当性何在,具体应当如何适用,值得探讨。
(一)“加重处罚”罚则溯源
加重处罚,顾名思义,是指在法定最高限以上处罚。在新中国刑事立法领域,关于加重处罚的规定,始见于1951年《惩治反革命条例》。该条例第4条第2款规定:“其他参与策动、勾引、收买或叛变者,处十年以下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加重处刑。”1952年《惩治贪污条例》也有加重处罚的规定,并与从重处罚并列适用。其第4条第1款规定:“犯贪污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从重或加重处刑:一、对国家和社会事业及人民安全有严重危害者;……。”1979年刑法在制定过程中,其第33稿第64条曾有加重处罚的规定,即“对于个别罪行严重、情节恶劣、怀恶不悛的犯罪分子,如果判处法定刑的最高刑还是过轻的,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在法定刑以上判处刑罚”。但1979年刑法正式颁布时,取消了这一规定。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一些单行刑法,又恢复了加重处罚制度。例如,1981年《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以下简称《劳教决定》)第2条第2款规定:“劳改犯逃跑后又犯罪的,从重或者加重处罚;刑满释放后又犯罪的,从重处罚。刑满后一律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第3条规定:“劳教人员、劳改罪犯对检举人、被害人和有关的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干部、群众行凶报复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罚。”1983年《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治安决定》)第1条规定:“对下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1.流氓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携带凶器进行流氓犯罪活动,情节严重的,或者进行流氓犯罪活动危害特别严重的;……。”1997年刑法在总则中不再规定加重处罚制度,在附则中明确宣告《劳教决定》等单行刑法失效,意味着这些单行刑法涉及的加重处罚规定不再适用。
在行政立法领域,加重处罚制度也经历了一个从有限设定到绝对排除的立法过程。1957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或者加重处罚:一、后果较重的;二、屡经处罚不改的;三、嫁祸于人的;四、拒绝传问或者逃避处罚的。”第22条第3款规定:“连续实行同一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罚。”但是,1986年和1994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均取消了加重处罚的规定。2005年《治安管理处罚法》更是明文禁止加重处罚。该法第94条规定:“公安机关不得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2012年《治安管理处罚法》完全保留了这一规定。1996年《行政处罚法》第32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2009年和2017年《行政处罚法》对该款规定亦完全保留。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行政法律虽然没有规定加重处罚,但却有执行罚的规定。例如,2017年《行政处罚法》第51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又如,2015年《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4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规定期限内不缴或者少缴应纳或者应解缴的税款,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税务机关除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外,可以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当然,执行罚不同于狭义的行政处罚,也不能将其视为加重处罚的一种方式,因为其针对的是行为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内容的事实,是对“新”的违法行为的处罚,而非对“旧”的违法行为的处罚。
(二)“加重处罚”罚则的方法论释疑
对于任何不法行为(行政违法或刑事犯罪),在配置处罚(行政处罚或刑罚)时,都应遵守一个基本原则(比例原则或罪刑相当原则),都应与该行为的危害程度相适应。对于法律既定的“罚则”,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应当给予绝对的尊重——假定“立法规定的罚则都是合理的”,而不能突破罚则的最高限给予处罚,否则便僭越了立法机关专享的立法权。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立法机关能否设立加重处罚的规定,或者在法律中明确授权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在法定最高限以上给予处罚呢?
对此,学界向来存在争议。以1979年刑法草案第33稿第64条的设定为例。赞同者认为,刑法草案分则对各种犯罪设定的法定刑,在通常的情况下是适合的,但考虑到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在各种犯罪中总还会有少数很特殊的情况和问题,如果法律上不解决这些特殊问题,就不利于审判机关在实际工作中对复杂的犯罪区别对待。如果为了解决这些特殊问题而扩大法定刑幅度,就势必在分则条文中过多地增加死刑、无期徒刑,也容易导致在处理一般案件上产生量刑轻重悬殊的现象,不利于国家法制的统一。另外,既然给法院以减轻处罚的机动权力,也应给以加重处罚的机动权力。反对者认为,第一,有了这一条,等于分则每一条的法定刑上面都打开了缺口,这就降低甚至丧失了设立法定刑的意义;第二,从逻辑上说,因加重幅度没有限制,刑法分则每条都可能加重到死刑,与少规定死刑的初衷相悖;第三,设立了这一条,法律本身规定下来的法定刑就不能算数,被告人随时有被加重处罚的可能,不利于巩固和加强法制;第四,把加重处罚和减轻处罚相提并论是站不住脚的;第五,即便将核准权控制在最高人民法院,也难免有司法权超越立法权的嫌疑。①参见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59页。
上述观点之争,从立法权力来看,赞同者的主张是能成立的。鉴于立法权的至上性,无论是以法典或者单行法的形式,设定“从重处罚”这一特殊的罚则,都具有效力上的现实性和权源上的合法性。但从立法技术考察,结论并非那么容易得出。这其实涉及如何提升具体犯罪的刑罚问题,即是采用法定刑升格模式(通过立法给具体犯罪增设一档或数档法定刑)还是加重处罚模式(授权司法者在具体犯罪的法定刑的最高限以上适用刑罚)来提升法定刑的幅度。从法律的明确性要求来看,法定刑升格模式针对具体个罪而设,刑种和刑度明确清晰,显然更为可取。而加重处罚模式,往往针对类罪甚至所有犯罪而设,且可加重的刑种和刑度都极为概括,除非情况特别紧急,否则都不应采用。这可能是立法实践中加重处罚模式通常备而不用的原因。
《野生动物保护决定》第1条规定激活了沉寂已久的加重处罚模式。之所以采用这一模式,参与立法的同志作了如下说明:“全面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需要一个过程,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通过一个专门决定,既十分必要又十分紧迫。”②《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载新华网,http://www.hn.xinhuanet.com/2020-02/25/c_1125621609.htm,2020年2月28日访问。该说明虽然没有直接针对加重处罚制度的规定,但间接回答了这一制度的激活背景。亦即,在当前疫情防控这一紧急状态下,召集全国人大专门讨论《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的修改已经缺乏现实可能性,但“以最严格的法律条文禁止和严厉打击一切非法捕杀、交易、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又迫在眉睫,需要立法先行,不得已恢复加重处罚模式。
加重处罚的规定,要避免为人诟病,关键在于适用对象的明确性。有学者结合立法规定,将加重处罚提炼为两种:一种是罪行的加重,指具体犯罪法定刑幅度的升格;另一种是刑罚的加重,指着眼于刑罚本身的加重。③参见张波:《新中国从重和加重处罚的考察》,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这种划分是有启示意义的,但将二者的区别限定于能否改变刑种(如将最高刑由有期徒刑升格为无期徒刑,或者由无期徒刑升格为死刑)则不甚妥当。笔者认为,罪行的加重,是指因具体犯罪行为又具有其他特别情节要素,使行为的危害性增大,因而加重处罚的情形,如脱逃后实施犯罪、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的。而刑罚的加重,是指具体犯罪行为的情形不存在特殊性,行为的危害性也没有变化,仅因特殊时期为增加刑罚的威慑效应而加重处罚的情形。上述1979年刑法草案第33稿第64条即属于一般性的刑罚的加重,这是要绝对杜绝的。但上述刑事立法和行政立法中出现的个别性加重的规定,由于针对的是特别对象或特殊情形,属于罪行的加重,则具有相对的合理性,质疑的声音也没有那么强烈。现行刑法中虽然也有一些加重犯的规定,但也均是针对具体情形而设,并非抽象性不加区别地普遍加重,如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的规定,刑法第263条关于具有特定八种情节的抢劫罪加重处罚的规定。1996年《行政处罚法》第32条更是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野生动物保护决定》第1条规定针对的是“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的具体行为,对象相对明确,这应属于个别性加重而非一般性加重。但与之前的立法例不同的是,该规定没有对加重处罚附加“情节特别严重”“多次实施”“暴力抗拒执法检查”等情节,有过于宽泛之虞,这是在适用时需要特别警惕的。
(三)“加重处罚”罚则的具体适用
实践中,在适用《野生动物保护决定》的“加重处罚”罚则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加重处罚应当仅限于“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除此之外的行为(无论是上游行为还是下游行为)均不得适用。例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50条是关于“为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发布广告”行为的罚则,虽然这一广告行为也与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的目的行为密切相关,但毕竟不是目的行为本身,因而不得适用加重处罚。
第二,加重处罚应当以现行法律规定的处罚为基础,即不能不考虑具体不法行为的危害程度而一律突破法定最高限予以处罚。例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4条规定:“违反本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以收容救护为名买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违法所得,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将有关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向社会公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假设行为人违反本条的前段规定,构成行政违法,则决定对其处罚时,不能当然地适用十倍以上的罚款,而应首先根据本条的罚则规定,结合其具体行为的危害程度确定一个罚款数额,比如三倍的罚款。再根据《野生动物保护决定》的“加重处罚”规定,决定最后的处罚,比如四倍的罚款。
第三,加重处罚应当有处罚种类的限制,即不能变更不法行为的性质而适用性质完全不同的处罚。例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9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食品,或者为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假设行为人违反了本条的前段规定,构成最严重的行政违法,应当处十倍的罚款,在对其处罚时,也只能在行政违法行为的“罚则”之内加重(如适用十二倍的罚款),而不能将其行政违法行为升格为犯罪行为,进而适用本条的后段规定,予以刑罚制裁。
第四,加重处罚应当有“格”的限制,即不能无限制地加重。正如减轻处罚有“格”的限制一样(原则上在法定处罚幅度的下一个处罚幅度内裁量处罚),加重处罚也应当有类似的限制,即原则上只能在法定处罚幅度的上一个处罚幅度内裁量处罚,特殊情形下在不改变处罚性质(行政处罚或刑罚)时可以变更处罚种类。对此,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汉斌同志曾有如下说明:“至于如何加重判刑,不是可以无限制地加重,而是罪加一等,即在法定最高刑以上一格判处。如法定最高刑为十年有期徒刑的,可以判处十年以上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法定最高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的,可以判处死刑(包括死刑缓期二年执行)。”④王汉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等三个决定(草案)的说明》,载高铭暄、赵秉志主编:《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0页。在具体适用时,行政处罚和刑罚在“加重”的程度方面会有所不同。一般而言,不同的行政处罚之间严厉程度没有刑罚那么明显,因而在“格”的识别上更要仔细辨别。例如,刑罚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这五个主刑之间完全呈现一种阶梯序列,而行政处罚的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彼此之间的级差则相对不够清晰。这是因为,刑罚的主刑除死刑这一生命刑外都是自由刑,而行政处罚则是训诫刑、财产刑、资格刑、自由刑等混合规定在一起。因此,在判断行政处罚的法定最高限时,尤其要结合法条规定的具体处罚种类对比分析。
第五,加重处罚应当有时效的限制,即原则上只能在疫情防控期间适用。行为的危害性,既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主体主观认知和体验。同样的行为,在紧急状态下和非紧急状态下,其社会危害程度是有差别的。《野生动物保护决定》之所以规定加重处罚,正是考虑到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较非疫情防控期间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和风险性。因此,在疫情结束之后,应当尽可能不用或者少用“加重处罚”规定。如果认为现有法律的罚则严厉性不够,则应及时启动立法程序予以修改。
二、关于“参照适用”的规定
《野生动物保护决定》第2条第3款规定:“对违反前两款规定的行为,参照适用现行法律有关规定处罚。”这里的“前两款规定”,即“全面禁食”的规定(下文详述)。对于违反全面禁食的行为,该款设立了“参照适用”这一罚则。
(一)“参照适用”罚则溯源
“参照”,是指参考并仿照;“参照适用”,就是指参照之后照此办理。在法律规范中,“参照适用”则是指参照相关法条办理。类似的表述还有,“应当参照”“可以参照”“参照”“比照”等。我国向来有“比附援引”的法律传统,如《唐律·名例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在新中国刑事立法领域,参照适用的立法例可以追溯至《惩治贪污条例》。其第12条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国家工作人员伙同贪污者,应参照本条例第三、四、五、十、十一各条的规定予以惩治。”1979年刑法既规定了个别性参照适用,也规定了普遍性参照适用(类推制度)。其第138条第1款规定:“……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包括犯人)的,参照所诬陷的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和量刑标准给予刑事处分……”该条没有给诬告陷害罪配置独立的法定刑,仅指出可以参照适用的量刑标准。第79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该条更是直接创设了罪名和刑罚的参照适用,而且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之后,一些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也有参照适用的规定。如1990年《铁路法》第60条第2款规定:“携带炸药、雷管或者非法携带枪支子弹、管制刀具进站上车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指私藏枪支、弹药罪——笔者注)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1993年《红十字会法》第15条规定:“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比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指妨害公务罪——笔者注)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比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但是,1997年刑法对诬告陷害罪配置了独立的法定刑,同时取消了类推制度。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将《计量法》等多部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如“依照刑法第×条的规定”“比照刑法第×条的规定”,统一修改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自此,在刑事立法中,已经不再有参照适用的罚则。
在行政立法领域,参照适用的立法模式则一直存在。例如,1982年《食品安全法(试行)》第6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必须符合下列卫生要求:(一)保持内外环境整洁,采取消除苍蝇、老鼠、蟑螂和其他有害昆虫及其孳生条件的措施,与有毒、有害场所保持规定的距离;……对食品商贩和城乡集市贸易食品经营者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卫生要求,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参照本条另行规定。”1990年《国旗法》第19条规定:“在公众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处罚规定,由公安机关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1991年《国徽法》第13条规定:“在公众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处罚规定,由公安机关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2011年《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7条规定:“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办理。”2019年《建筑法》第83条第1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小型房屋建筑工程的建筑活动,参照本法执行。”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2014年《行政诉讼法》第63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2017年《行政诉讼法》对该款予以完全保留。
以上仅就立法领域而言,但在司法领域,则无论是刑事审判还是行政审判,均存在参照适用的情况。这集中表现在最高司法机关目前推行的案例指导制度方面。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7条率先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2010年和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没有明确各地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是否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只是要求“人民检察院参照指导性案例办理案件,可以引述相关指导性案例作为释法说理根据,但不得代替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作为案件处理决定的直接法律依据”。但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15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办理类似案件,可以引述相关指导性案例进行释法说理,但不得代替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作为案件处理决定的直接依据。”
(二)“参照适用”罚则的方法论释疑
从立法技术来看,“参照”和“依据”“参考”是含义不同的。“依据”,是指依照进行。依据的对象是针对待决事项的法律规范,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可直接援引适用。“参考”,是指参合、考量。参考的对象是学理解释、习惯、政策、参考案例、法院内部的统一裁判尺度要求等,这些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不能作为裁判的法律依据。“参照”,是指参酌考量,再决定是否适用。参照的对象是针对其他事项的法律规范,对其他事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待决事项则为效力待定。因此,参照与依据、参考之间的主要区别在法律效力上,参照介于依据与参考之间,其法律效力小于有直接法律强制力的依据,但大于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参考,其有着弱法律约束力。⑤参见纪长胜:《“参照”的法理与适用》,载李凤章主编:《产权法治研究》2017年第2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页。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参照适用进行不同的划分。(1)根据参照对象的适用强度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加强型参照、一般型参照和选择型参照。加强型参照,是指在“参照”一词之前增加“应”“应当”等词语修饰,以加强语气,强调所参照的法律规范的约束力效果;选择型参照,是指在“参照”一词之前增加“可”“可以”等词语修饰,以减弱语气,表明对所参照的法律规范可以适用也可以不适用;一般型参照,是指在“参照”一词之前不加任何修改语,在法律约束力的效力强度上介于加强型参照和一般型参照之间。(2)根据参照的形式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规范类参照和案例类参照。规范类参照,是指参照的对象是法律法规、政策、办法等;案例类参照,是指参照的对象是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或者其他案例等。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的解释,“参照”一般用于没有直接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但是又属于该范围逻辑内涵自然延伸的事项。这里的“参照”显然仅指规范类参照,即法定授权式的法律扩展适用,而非案例的比照适用。(3)根据参照的程度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完全型参照和部分型参照。完全型参照,是指参照的对象是整个法律规范,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效果;部分型参照,是指参照的对象是法律规范的一部分,即法律效果部分,行为模式则并不参照。1979年刑法规定的类推制度是典型的完全型参照,现行刑法第180条第4款规定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则属于部分型参照(仅指出法定刑需援引适用)。
在刑事立法领域,规范类参照、完全型参照(类推制度)是严格禁止的,可以允许的只有案例类参照和部分型参照。刑事立法之所以取消类推制度,最根本的原因是刑事类推和罪刑法定原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极易导致罪刑擅断,不利于人权保障。“毫无疑问,刑事类推对于成文法的局限性确是一剂良药。但是,刑事类推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标准,本身潜藏着司法擅断的危险性”。⑥陈兴良:《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另外,刑事立法技术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我国刑法自颁布以来,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可以说,相当完备、相当周密。尤其是严重的罪行,已无无法可依之虞。因此再规定类推制度,实无必要,而且这样做只会因小失大、得不偿失”。⑦同注①,第174页。总之,类推制度有利于强化刑法的适应性,但却蕴含着司法擅断的危险;罪刑法定容易导致刑法的僵化,但却有利于人权保障。两相权衡,废除类推制度利大于弊。在行政立法领域,参照适用的立法模式则相当普遍,不仅案例类参照、部分型参照大量存在,规范类参照、完全型参照也不鲜见。《行政诉讼法》确立的“参照规章”规则就是完全型参照的适例。之所以设立这一规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同志作了如下说明:“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和省、市人民政府有权依法制定规章,行政机关有权依据规章行使职权。但是,规章与法律、法规的地位和效力不完全相同,有的规章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草案规定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参照规章的规定,是考虑了上述两种不同的意见,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规章,法院要参照审理,对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原则精神的规章,法院可以有灵活处理的余地。”⑧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1989-03/28/content_1481184.htm,2020年2月29日访问。参照规章,意味着在法律、行政法规、条例等缺位的情形下,完全可以根据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来处理行政事项。如此规定,应是基于行政事项的广泛性和行政行为的效率性的需要。
(三)“参照适用”罚则的具体适用
《野生动物保护决定》规定,对违反全面禁食规定的,“参照适用现行法律有关规定处罚”。但问题是,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并未有相关的关于全面禁食的罚则规定,因而,这里的“参照适用”实际只能是“类推适用”。但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这里的“参照适用”就是完全型参照。事实上,如果考虑到决定对行为模式(全面禁食的违法性)是有明确规定的,而只是未明确规定行为的法律效果(处罚的种类和幅度),而决定本身又属于广义的法律,因而本款规定属于“法律规定了行为模式但仅指出援引处罚”的情形,应该归类于部分型参照。
虽然这一立法“类推”在权源上没有问题,但在具体适用时仍应援引最相类似的条款。目前的法律体系上,最可能被参照适用的应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即“违反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食品,或者为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该条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仅限于“为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情形,《野生动物保护决定》第2条第1、2款规定的全面禁食行为能够刑事入罪的,亦应限定于此。这是因为,刑法是绝对禁止完全型参照的,部分型参照也仅存在有限的适用空间。根据2000年《立法法》第7条第2、3款的规定,“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第8条规定,“犯罪和刑罚”,只能制定法律。《野生动物保护决定》虽然属于广义的法律,但与《立法法》提及的“基本法律”“其他法律”还是不能等同的。因此,笔者认为,它可以创设行政罚则,但不能增设新罪。具体而言,《野生动物保护决定》第2条第1款的禁食行为应当理解为行政违法行为,即便再严重,也不能上升为刑事犯罪;第2款规定的禁食行为,则应区别对待:如果涉及的野生动物系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可以刑事入罪;如果是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则只能予以行政处罚。
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现行刑法规定的罪名主要有:第341条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和非法狩猎罪。前两个罪名的行为类型必须是“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行为,行为对象必须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其制品”;第三个罪名的行为对象可以是“任何野生动物资源”,但行为类型必须是“狩猎”,行为情状必须是“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猎的工具、方法”。由此可见,现行刑法并未将食用行为犯罪化,也没有将所有的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刑罚调整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为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法购买的,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据此,“为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可以以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论处。这一立法解释虽然明确“食用”等目的不影响非法收购的认定,但并未扩张非法收购的对象范围。总之,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野生动物保护决定》禁止的两类行为尚难以犯罪论处。如果要将这两类行为以犯罪论处,则必须要修改刑法。首先,必须扩大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的对象范围,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修改为“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其次,必须取消非法狩猎的情状规定,即禁止在任何区域、任何时间、以任何手段狩猎野生动物。再次,必须增设“食用野生动物罪”,即将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以犯罪论处。显然,这些修改牵涉面极广、力度极大,有无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是将来立法修改时需要充分论证的。
另外,无论是参照适用罪刑规范,还是参照适用行政处罚规范,都应是一般型参照,而非加强型参照。换言之,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决定》第2条规定的禁食行为,执法机构或司法部门在办理案件时,虽然通常情况下应当首先考虑追究行政违法责任或刑事犯罪责任,但在特殊情形下也可以酌情对待决个案不予行政处罚或刑罚处罚。
三、关于“全面禁食”的规定
《野生动物保护决定》第2条第1、2款规定:“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该两款关于全面禁食规定,极大地拓展了现有法律规定的处罚范围,但也是最具争议的条款,值得深入探讨。
(一)没有例外:“全面禁食”规定的涵射范围
全面禁食规定,是一个全新的罚则设定。《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0条:“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禁止为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据此,该法坚持的是有限禁食原则。具体而言,其禁止的是两类行为:一是制售食品行为,且使用的食材必须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二是为食用而非法购买的行为(“购买”而非“食用”行为),且购买的对象必须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此外,《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8条⑨《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8条规定:“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经科学论证,纳入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对列入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可以凭人工繁育许可证,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验的年度生产数量直接取得专用标识,凭专用标识出售和利用,保证可追溯。”“对本法第十条规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进行调整时,根据有关野外种群保护情况,可以对前款规定的有关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野生动物的人工种群,不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实行与野外种群不同的管理措施,但应当依照本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和专用标识”。还引入了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制度,对列入名录的野生动物,可以凭人工繁育许可证,进行出售和交易。因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处罚的是制售、购买行为,而非食用行为,且制售、购买的对象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未列入名录、人工繁育的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没有合法来源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但对列入名录、人工繁育的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有合法来源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则不在禁止之列。⑩据统计,目前有国家一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98种、国家二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308种,还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1591种以及昆虫120属的所有种等都纳入保护范围。但是,蝙蝠、鼠类、鸦类等约1000种陆生脊椎野生动物尚未列入保护范围。总体而言,《野生动物保护法》对“野生动物”和“人工繁育的动物”作了区分,采取的是分级保护原则。⑪参见叶良芳、应家赟:《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属于刑法的规制范围吗?》,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野生动物保护决定》则采取全面禁止原则,将以往对猎捕、贩卖、运输、加工等供应链的单向打击,延伸到对食用需求的消费链的双向打击,编织了一张野生动物全链条保护网。具体而言,《野生动物保护决定》在保留《野生动物保护法》着眼于处罚销售环节的同时,另外增设两项处罚消费环节的规定:一是全面禁食所有的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和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二是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行为,行为对象为所有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简言之,所有的陆生野生动物(水生野生动物除外),无论是国家重点保护的还是非国家重点保护的,是纯野外环境生长繁育的还是人工饲养繁育的,一律禁止食用。值得注意的是,《野生动物保护决定》第3条第1款规定:“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属于家畜家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规定。”根据该款规定,野生动物只要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则视为家畜家禽,可以交易、食用。但这也不能算是为全面禁食开了一个小口子,因为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野生动物”,严格地说,已经不再属于野生动物了。⑫关于“野生动物”和“非野生动物”的区分,《野生动物保护法》采取的是“环境区分法”,即在野外自然环境生长的,为野生动物;在人工控制环境生长的,为非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的动物)。《野生动物保护决定》则改采“目录区分法”,即任何未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包括人工繁育但未列入名录的,均为野生动物;列入名录的,包括人工繁育但列入名录的,均为非野生动物。综上,《野生动物保护决定》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野生动物不能吃,能吃的不是野生动物。就此而言,全面禁食规定可谓是史上“最严禁食令”。
(二)公共卫生:“全面禁食”规定的制定根据
全面禁食规定之所以对野生动物的食用问题作了近乎一刀切的规定,最根本的原因是基于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需要。众所周知,近年来,H7N9禽流感、埃博拉病毒、塞卡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均与野生动物存在直接的关联性。例如,2003年的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就是蝙蝠,蝙蝠感染了果子狸后又传给人类。一些野生动物感染病毒后并无不适,但如果传染给人类,可能产生新毒株,进而致病致死。人类食用这些野生动物或侵害其栖息地,则加大了接触和传播病毒的机会,给疫情爆发提供了可能性。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虽然尚没有明确其自然宿主和中间宿主,但种种迹象表明,它与食用野生动物脱不了干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报告就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于2019年12月初从湖北省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的某种野生动物外溢及其市场环境污染感染人,进而造成人与人之间传播。”⑬《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展和风险评估》,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http://www.chinacdc.cn/yyrdgz/202001/P020200128 523354919292.pdf,2020年3月1日访问。中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考察组的报告也指出:“新冠肺炎病毒是一种动物源性病毒。目前的全基因组基因序列系统进化分析结果显示,蝙蝠似乎是该病毒的宿主,但中间宿主尚未明显。”⑭《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载国家卫健委网站,http://www.nhc.gov.cn/jkj/s3578/202002/87fd92510d094e4b9bad597608f5cc2c.shtml,2020年3月1日访问。因此,如果没有食客对吃野味的口腹之欲的无止境的贪求,就不会有这次新冠疫情的发生;如果能够斩断食客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紧密接触,就能避免将来类似卫生事件的重演。基于这一认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也应作相应的调整,即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价值目标不应仅限于“维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而应同时纳入“保障公共卫生、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内容。⑮2020年1月22日,19位中科院院士、高校教授联名呼吁,由全国人大紧急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公共健康安全的内容纳入到野生动物利用的条款中。参见《19位学者呼吁全国人大紧急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载财新网,http://www.caixin.com/2020-01-24/101508072.html,2020年3月1日访问。
公允地说,立法者的上述认识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研究表明,人类主要疾病,绝大多数可以追踪到脊椎动物的源头,包括灵长类动物、啮齿类动物、兔形目动物、有蹄类动物、鸟类等。不少脊椎动物宿主含有各种病毒,仅蝙蝠身上就宿生有1000多种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将在人类和脊椎动物之间传播的疾病定义为人畜共患传染病,统计数据表明,在175种被认为是“新发”疾病中,75%是人畜共患传染病,如鼠疫、疯牛病、口蹄疫、猴天花、狂犬病等。猕猴(国家二类保护动物)有10%~60%携带B病毒。它如果挠人一下,甚至吐一口水,都可能致人感染,而生吃猴脑者感染B病毒的可能性更大。惨痛的事实一再警示人类,野生动物是一个潜在的危及公共卫生的风险源,对此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从环境资源的角度,也许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动物福利论和反动物福利论还可以唇枪舌剑地大辩一场,但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敬畏大自然、拒食野生动物,却是不容辩驳的安全需要。
不过,认识到野生动物的卫生风险是一回事,如何防范其风险又是另一回事。不少人认为,野生动物在端上餐桌之前都经过烹、煮、炖、烤、炒等高温处理,即使体内潜藏有病毒,也早已经被杀死,不存在传播的可能性。因此,没有必要禁食野生动物。这一观点即使能够成立,也不能否证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正当性。食用野生动物的消费环节也许没有病毒传播的风险,但在前端的制售(猎捕、运输、交易、宰杀)环节却存在极高的传播风险。而“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制售环节和消费环节是一种正相关关系,正是由于数量众多的食客存在,才催生了庞大的野生动物产业链。而以往的治理经验表明,仅靠规制生产、销售等前端环节,预防效果是差强人意的。因为一个完美的野生动物交易市场是不存在的,由于受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再加上病毒演变的复杂性,总会存在一些检疫检验盲区和漏洞。而人一旦被传染病毒,其带来的破坏力是不可估量的。为此,有必要溯源规制,掐断野生动物产业链的源头——旺盛的消费需求。这样,前端堵截和后端死守双管齐下,才是最保险和最有效的预防策略。
(三)关联制度:“全面禁食”规定的实现保障
“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⑯[德]萨维尼:《论立法和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对于一个有着丰富饮食文化的民族而言,“全面禁食”无疑是一个革新除弊的规则创新。要使这一规则真正发挥实效,实现改变民众饮食观念、重塑民众饮食文化的意图,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是根本不行的。立法者显然十分清楚这一点,因而确立了若干配套规定。在此,着重阐述三项配套制度: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制度、养殖户补偿制度和宣传教育制度。
首先,是建立和完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制度。《野生动物保护决定》第3条规定:“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属于家畜家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规定。”“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制定并公布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该条规定坚持了立法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既贯彻了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精神,又从实际出发,将对家畜家禽业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一方面,全面禁食是“零容忍”原则,没有例外,这有利于实践执行;另一方面,列入目录的野生动物不再属于野生动物,可以为人类所用,包括食用、药用,这有利于合理利用资源。对此,参与立法的同志作了如下说明:“比较常见的家畜家禽(如猪、牛、羊、鸡、鸭、鹅等),是主要供食用的动物,依照畜牧法、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管理。还有一些动物(如兔、鸽等)的人工养殖利用时间长、技术成熟,人民群众已广泛接受,所形成的产值、从业人员具有一定规模,有些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按照决定的规定,这些列入畜牧法规定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也属于家畜家禽,对其养殖利用包括食用等,适用畜牧法的规定进行管理,并进行严格检疫。”⑰《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载新华网,http://www.hn.xinhuanet.com/2020-02/25/c_1125621609.htm,2020年2月28日访问。
事实上,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在2005年《畜牧法》中即有规定,该法于2015年修正,关于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相关规定完全保留。但是,该法的立法目的,主要侧重于对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对其“利用”的目的极不明显。这集中体现在该法第12条第1款和第13条第1款的表述上。前者内容为:“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对原产我国的珍贵、稀有、濒危的畜禽遗传资源实行重点保护。”后者内容为:“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分别建立或者确定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承担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任务。”另外,该法也没有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8条规定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制度进行必要的衔接。还有,《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认定标准模糊、更新不定期、公布不规范,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指引作用。2003年8月4日,林业部等12个部门联合发文,公布了《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单》(以下简称《商业名单》),将梅花鹿等54种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其中,可以从事经营利用性驯养繁殖和经营。实操中,这一名单成了判断野生动物能否食用的“白名单”,而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却成了不折不扣的“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单”。这次《野生动物保护决定》赋予畜禽遗传资源目录以确定可供食用的野生动物的“白名单”功能,基本是可行的,但应明确其与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名录和《商业名录》的关系(替代、补充抑或整合),并根据人工繁育和检疫检验技术的发展,不断调整更新具体名单。⑱2020年2月28日,农业农村部出台六项措施贯彻落实《野生动物保护决定》。其中,第2项措施为:“加快制定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规定,将比较常见的家畜家禽(如猪、牛、羊、鸡、鸭、鹅等)等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依照畜牧法的规定进行管理。”总体而言,对于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可以采取分类管理、区别利用的原则:对于猴子、黑猩猩等动物,基于与人类的近亲性,无论是多少子代,都不得纳入名录;对于蝙蝠、果子狸等动物,基于确知的高度卫生风险,也不得纳入名录;对于鹌鹑、梅花鹿等动物,如果养殖技术成熟、检疫标准规范,则可以逐步纳入名录。
其次,是建立养殖户补偿制度。《野生动物保护决定》第7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为本决定的实施提供相应保障。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指导、帮助受影响的农户调整、转变生产经营活动,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补偿。”该款规定明确全面禁食之后,要给养殖户一定的经济补偿。这充分考虑到全面禁食规定对养殖业的冲击和影响,较好地做到了价值权衡。人类对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起始于初民时期,一直延续至今,历经千年,绵延不绝。人类所有的家畜家禽均来源于自然界中的野生物种;为了稳定获取肉类或者毛皮,人类不断驯化新的野生动物。在传统的食用养殖动物以外,人类以食用为主要目的而驯养繁殖的动物种类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催生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食用特种动物养殖产业。据《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17年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数据,2016年我国食用野生动物产业的直接从业者约626.34万人,总产值1250.54亿元。其中两栖爬行类养殖从业人员101.7万人,年产值506.48亿元;爬行动物养殖从业人员501.13万人,年产值643.22亿元;鸟类养殖从业人员14.73万人,年产值76.56亿元;兽类养殖从业人员8.77万人,年产值24.28亿元。禁食野生动物,不得不在商业利益和安全利益之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虽然不是零和博弈,但必须对二者进行价值位序排列。立法机关根据疫情时期的特殊情势,将安全利益置于商业利益之上,是符合紧缺利益优先原则的。
但是,全面禁食规定毕竟对养殖业主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对此,不能完全由其个人承担。《行政许可法》第8条第2款规定:“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这一规定与《野生动物保护决定》第7条第2款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对此,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及各地方政府应当全面地贯彻落实,不能只注重执行禁令,而忽视对“受影响的农户”的指导、帮助、支持以及补偿。(1)获得补偿是养殖户的法定权利,给付补偿是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如果撤回行政许可而拒不给予补偿,则属违法。(2)补偿对象是养殖户,即《野生动物保护决定》所指的“受影响的农户”,一般是人工繁育许可证的被许可人。(3)承担补偿义务的机关是作出并撤回行政许可的机关。根据相关规定,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经营利用的审批权限属于省级政府的林业等主管部门,撤回行政许可的补偿义务,也应当由作出审批决定的机关承担。(4)补偿不是“行政赔偿”,不适用《行政赔偿法》的程序和标准。行政赔偿的前提,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而对相对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撤回行政许可系依据《野生动物保护决定》实施,⑲当然,如果撤回行政许可的决定本身违法,即根据《野生动物保护决定》和相关法律的规定,本不应撤回而强行撤回的,则属于“因行政行为违法而给相对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情形,应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并不违法。(5)补偿标准一般应等于或低于实际损失数额,预期收益不属于补偿范围。行政补偿的标准以实际损失为限,具体标准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确定。经营活动中的预期收益、贷款利息等均不属于补偿范围。
再次,是强化教育宣传制度。《野生动物保护决定》第5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学校、新闻媒体等社会各方面,都应当积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全社会成员要自觉增强生态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意识,移风易俗,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一规定可谓点中了问题的死穴,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牛鼻子。处罚是外部强制性约束,只能治表;只有内心确信滥食野生动物的危害,才能治本。现实生活中滥食野味之所以久盛不衰,与不良的饮食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学者分析了在物质财富丰富、饮食种类繁多、花色品味多样的今天,一些人仍执着于嗜食野生动物的原因。“从收益最大化角度来看,这主要因为嗜食野生动物的‘饮食文化’在现代社会里逐渐被衍生出其他的含义,如炫耀、滋补、猎奇心理,满足了现代人的消费需求,同时这些含义所形成的嗜食‘亚文化’又随着改革开放的火车头广东在全国迅速扩散”。⑳郑风田、孙瑾:《我国部分地区嗜食野生动物的成因探析》,载《消费经济》2005年第5期。
为此,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加大教育宣传的力度,讲清讲透滥食野生动物的危害性,重塑健康的饮食文化:(1)滥食野生动物,将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危及人类有限的生物资源。由于存在大量的食用需求,对野生动物大规模的滥捕乱杀屡禁不止,已经严重危及了种群的生存,许多野生动物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2)滥食野生动物,不仅存在个人健康隐患,而且还存在引发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在全球化的今天,滥食野生动物再也不是纯粹个人的私事,而是必然涉及公共利益。“那些可能带有病毒会危害人类生命的野味,个人的感官享受有时会造成全人类的灾难,原本属于个人无关紧要的行为,有可能导致自己和他人的毁灭”。㉑於贤德:《诱惑与危险——“非典”阴影下的野味饮食文化反思》,载《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3)滥食野生动物,是对野生动物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错误认识的结果,是一种饮食迷信。在传统食药同源的“进补”文化里,山珍野味被视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食用野生动物被认为有助于延年益寿。但实际上,尽管食物的种类繁多,但营养素的种类通常只有蛋白质、脂类、维生素、水等六类。野生动物与家禽家畜相比,在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能量等主要指标上相差无几甚至更低。“吃啥补啥”“以形补形”更多的是食用者的一厢情愿,并无任何科学根据。(4)滥食野生动物,是一种不文明的饮食文化,是虚荣心和猎奇心理的表现。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对野味趋之若鹜,并非真的认为野味有特殊的营养价值或者药用价值,而是一种炫富摆阔的心理作祟,甚至是一种权力腐败的结果。
四、结语
新冠疫情是重大突发事件,《野生动物保护决定》应当归属于紧急状态立法。它明确了当前野生动物保护及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中最需解决的问题,及时弥补了相关法律的短板,为疫情防控攻击战取得最后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这虽不是未雨绸缪,但也绝非亡羊补牢,而是暗室逢灯,非常必要。在紧急状态下,立法偏好风险规避,下猛药治沉疴,大幅度限制公民的行动自由,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均有其历史必要性和合理性。不过,对于病毒的危险性,人类既不应轻描淡写,也不应谈虎色变,而应理性地积极应对。人类的生活史,其实是一部病毒史。地球上的病毒,数量多得不可计数,遍布于各种生物身上。可以说,人类都寄居在病毒星球,野生动物就是这些病毒的蓄水池。㉒参见[美]内森·沃尔夫:《病毒来袭: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的暴发》,沈捷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人类身上也寄宿着大量的病毒,许多病毒对人体并无危害,而是可以和平共处。因此,可怕的不是已知病毒的存在,而是对新型病毒潜在风险的“无知”。相信随着病毒学、检疫学、药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人类必将不断填充对新型病毒认知的盲区,提高对其风险的防控能力。申言之,对于新型病毒,即使不能确定其有无风险,也不能无视其潜存的可能性;相反,“我们恰恰需要保持警惕,这样才能在它们有机会进入我们这个物种之前就采取措施,阻止它们的脚步”。㉓[美]卡尔·齐默:《病毒星球》, 刘旸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3~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