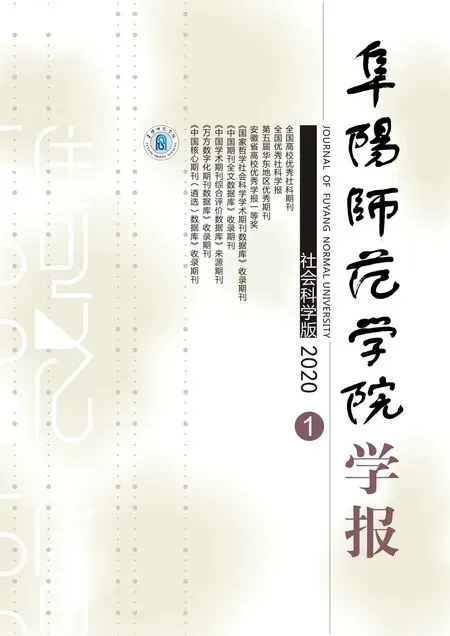从“文学理论”到“理论”:西方文论的历史蜕变及其启示
凌乐祥
□文学研究
从“文学理论”到“理论”:西方文论的历史蜕变及其启示
凌乐祥
(赣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论已出现了五次大转向:人学转向、神学转向、认识论转向、语言论转向和文化论转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文论已从19世纪中叶的“文学理论”演变成为20世纪中叶的“批评理论”,进而在本世纪初蜕变成为“品评天下”的“理论”,出现了高度哲学化和去文学化的倾向。西方文论的历史蜕变是西方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建设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时,应吸取西方文论历史蜕变的经验教训,继承中国古代文论的优秀传统,立足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走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论创新之路。
西方文论;文学理论;批评理论;理论;当代中国文论
西方文论在国内学界通常意指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学理论。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论被大量译介到国内。自上世纪初以来,西方文论在西方学术界盛行,“不断触发学术革命和思想危机”[1]。西方文论,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在国内学界已成为热门话题。近年来,国内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往往驻足于思潮的‘跟踪’、时尚的‘接轨’”[2],甚至出现了运用西方文论对国内外文学文本进行“强制阐释”的现象[3]。本文将在回顾西方文论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西方文论从“文学理论”到“批评理论”以至“理论”的蜕变进行剖析,揭示西方文论高度哲学化和去文学化的倾向,并指出其对当代中国文论建设的启示。
一、西方“文学理论”的历史演变
从古到今,人们一直在探讨文学及其相关问题,这些探讨就构成了文学理论的来源。文学理论为读者提供了一系列的分析和批评的方法,使读者从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角度来阐释文学文本。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发端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批评流派。德国思想家卡尔·罗森克莱茨(Karl Ronsenkranz)于1842年发表了《1826-1836的德国文学科学》[4]。这比初版于1942年由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早了整整一百年。然而,西方的文学理论至少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如按照福柯的“知识型”理论来检视西方文论的发展,迄今为止,西方文论可谓历经了五次大转向。这五次转向的“知识型”依次是人学、神学、认识论、语言论和文化论[5]。
第一次转向是古希腊时期的人学转向。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智者派主张哲学应把社会道德而不是自然规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后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是这一人学转向的代表。第二次转向出现在中世纪。随着基督教在整个欧洲的兴起,西方文论的人学中心逐渐被神学中心所取代,出现了神学转向。中世纪的西方文论把“造物主”上帝作为一切知识的来源。这一时期的文论家代表有普洛丁和奥古斯丁等人。第三次的转向发生在17世纪,是随着笛卡尔哲学的出现而形成的认识论转向。此时的西方文论强调理性,衍生了新古典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以及后来出现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实证主义乃至象征主义等思想流派。第四次转向是语言论转向,肇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索绪尔等人的语言学和哲学理论的影响下,20世纪的西方文论逐渐以语言研究为重心,出现了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文化研究的诸多文学理论流派。第五次转向是出现在20世纪中后期的文化论转向。这一阶段的西方文论虽也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但更加关注文化、政治、性别、通俗文化和网络文化等。
从上面的五次转向可知,西方文论关注的对象由外向内转,即从人学、神学到文本语言,而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文论又开始向外关注与文本相关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因素。依据艾布拉姆斯的文学艺术批评四要素来考量的话,当代西方文论对作品与世界的关系、作品与欣赏者(读者)的关系更为关注[6]。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其批评重心从“作者”转向“作品”,进而转向“读者”。自结构主义以来的绝大多数文学批评的重心都在“读者”。当代文学批评皆“拷问文学作品意义产生的策略以及文学生产所具备的各种要素”[7]179。这有可能使文学批评变得“稀薄且抽象”(rarefied and abstract),但这种批评会“引发我们对诸如社会结构、自我社会定位、世界的组成方式和世界存在的意义等问题的重要讨论”[7]179。正是在此类思想的导向下,西方文论自20世纪后期以来(尤其自本世纪初开始),严重背离传统的文学批评。西方文论从“文学理论”发展成为“批评理论”,进而蜕变成了“品评天下”的“理论”。
二、“文学理论”“批评理论”和“理论”:西方文论的蜕变
在西方,“文学理论”最初是作为文学批评的指导原则出现的。英语中的“批评”(criticism)一词源自古希腊语krites,是“评判”之义。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史专家哈比布(M.A.R. Habib)认为,西方最初的批评类型就出现在古希腊时期诗歌的创作过程中。在他看来,诗人在创作诗歌时,需要做出对主题、技巧、读者和前人创作方面的“评判”。因此,创作活动自身就是一种“不仅涉及灵感,也涉及某些自我评估、反思和判断”的批评活动[8]7。据哈比布的研究,西方的文学批评可追溯至公元前800年的古希腊的“古典”(classical)时期。后经“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period),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于公元前331年成为了西方学术和文学的中心。公元前31年,亚历山大帝国被罗马帝国所吞并。在接下来近一千年的时间里,“诗人、哲学家、修辞学家、文法学者和批评家们拟定了众多基本术语、概念和问题,它们把文学批评的未来塑造成现在的样子”。这些术语、概念和问题包括“模仿”“美”“文学的社会、政治和道德功能”以及各种体裁的发展,如“史诗”“悲剧”“喜剧”“韵文”和“抒情诗”等[8]8。韦勒克等人把文学理论定义为“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似问题的研究”;而把文学批评当作是“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的“静态”的批评方法[9]。在他们看来,文学理论是一种从具体上升到普遍的表述方式,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从普遍理论推演到具体作品的个别性表述方式。文学理论关注的是普遍性,文学批评关注的是个别性。这种情形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西方是普遍存在的。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少当代西方的批评家(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后继者)宣称文学批评独立于文学理论,或者认为文学批评本身就是文学理论。于是,出现了“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的新表述和新的学科分支。Critical 源自Critique(批判),“批判”并不是“对文学作品意义的分析”,而是“关切文学生产或文学创作的文化、政治和心理等诸因素”[7]178。此外,“批判”还关注如下一些问题:“为什么是这些作品而不是其它作品成为我们的批评对象?”“批评本身是如何建构文学作品意义的?”[7]179基于此,“批评理论”主要指“批评者在对文学现象的阅读和评论过程中体现的特定批评方式,以及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价值系统”[10]。批评理论有广狭之分。狭义的批评理论主要是指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学者的社会批判理论。广义的批评理论是指与literary theory(文学理论)意思相近的,对文学文本、图像文本以及文化评论进行批评的当代理论和方法,如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等。广义的批评理论的说法被应用于英语研究、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11]。“批评理论”关注的是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一般性原则[7]180。当下西方的“批评理论”则更加关注“文化和性别差异问题、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差别和多元等他性问题”。它反对“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拒绝接受以“白人至上并倡导异性恋的西方文化价值”作为一切价值尺度的观念[7]183。假如传统文学批评重在考查“文学文本的运行机制”,那么具有跨学科特征的当下的文学批评(批评理论)则极力考查“文本的深层运行机制及其所处的整个文化体制”[7]183。
本世纪以来,“批评理论”在西方还常被简称为“理论(Theory)”,比如美国的诺顿公司出版的西方文论选读《诺顿批评与理论文选》()。在词源学上,Theory(理论)一词源自希腊文theoria,意为“希腊戏剧舞台的一种观点或视角”。因此,有西方学者表示,批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人生观,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为何以某种方式阐释文本”[12]10。如此一来,批评理论“不仅有具体批评方式,而且还有由此出发而对更普遍问题的探索,以及相应的作为支撑的更大的文化价值系统”[10]4。当代西方文论也就出现了泛理论化的现象。美国当代文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就曾认为,近几十年来的西方文学理论早就不是“关于文学的本质和文学的分析方法的系统解释”,而是变成了“一种思考与写作的载体”[13]3。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的文学研究开始关注文学领域之外的论著,因为:“那些著作在语言、思想、历史或文化各方面所做的分析都为文本和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13]3卡勒还认为:“要称得上是一种理论,它必须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它还应该包含一定的错综性。”[13]2如今的西方文学理论已成为一系列毫无界限限制的评说天下一切事物的各种著述(理论),广泛地涉及哲学、语言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电影学、政治学、心理分析和性别研究等学科和领域。美国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针对当代西方的文学理论跨学科化的特点,则提出了“元评论”的概念(一种理论的理论)。詹姆逊认为,传统的“连贯、确定和普遍有效的文学理论”早已显得苍白无力,“最初需要解释的,不是我们如何正确地解释一部作品,而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这么做……每一种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14]可见,当代西方文论已日益哲学化。例如,布莱斯勒在《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中介绍西方某个批评流派时,都会专门讨论该批评流派的理论假设(assumptions)。这些理论假设详细解释了“各批评流派赖以成立的哲学原理”[12]3。有西方学者甚至声称,对理论的掌握将“有助于我们去分析对于任何文本的初始反应和所有的跟进反应,也能使我们通过手边文本去探究自己的信仰、价值观、情感以及最终的整体阐释。”[12]1
从“文学理论”到“批评理论”以至“理论”,西方文论不再只是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评价,它从传统的指导文学批评的原则已蜕变成了“品评天下”的“理论”。如今的西方“文学理论”已变成“某种关于话语的话语(meta-discourse)”,它“并不作为谈论文学的诸种方式之一而出现,而是对其它各种形式的批评分析采取一种批判姿态”[15]。当下的西方理论逼着西方的文学研究者去涉猎他们不熟悉的领域。理论早已成为“一种令人惶恐不安的源头,一种不断推陈出新的资源”[13]15。这也是人们“抵制理论的一个主要原因”[13]17。最近一二十年,西方文论的“理论时期”(“大理论”时期)似乎走到了尽头,出现了“后理论”时代。按照《当代文学理论导论》的看法,西方文论进入了对理论本身的反思期,强调文学理论回归文学和美学政治维度[16]。
三、西方文论蜕变的启示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传统的“诗文评”逐渐为西方的“文学批评”所取代。近年来,随着大量西方文论话语的引进,有学者甚至认为,当代的中国文论患了“失语症”。目前,国内学界基本认识到了建构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的重要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用西方的文论话语来“消解中国传统的文论”,还是“立足在中国的传统之上去消化西方的文论?”[17]这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西方文论的历史蜕变对建构中国当代的文论话语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第一,西方文论的历史蜕变说明,盲目照搬西方文论来建设当代中国文论只能自取灭亡。当代西方文论已远离文学批评实践,走向了泛理论化。我们不妨以英美“新批评”学派的发展为例。自20世纪以来,英语文学在中小学及大学被广泛地讲授。随着英语成为一门学科,人们的关注点从作家的生平转向了作品本身。随即在英美兴起了以文本细读为特征的“新批评”学派。这些批评家并不反对“表达式批评”(expressive criticism)。他们关注作品的价值,而且还把作品当作“审美对象”来“欣赏”。但是,他们并不把作品视为“作家的哲学和社会思想的表达”。为了洞悉作品的“思想品格和审美特性”,“新批评”学派对文学作品会做一些“预想”(assumptions):这类批评虽关注作品本身,但对作品里的重要信息抱有“概念预设”(preconceptions);它们崇尚作品的“复杂性”(complexity),但同时也期待找到“道德观念的一致性”(a coherent moral view),仿佛作者“给生活强加了一套道德规范”或者作品自身发出了“富有正能量的道德宣言”。直到现在,这种文学批评方法在西方并未消亡。此类批评方法在西方虽不能说是错误的,但西方近年来的文学批评方法与之“背道而驰”。当代的西方文论侧重强调作品(文本)中的“矛盾和不确定性”以及批评本身同样拥有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概括地讲,20世纪前半叶的西方文学批评旨在为作品的“整体一致性”(overall coherence)唱赞歌,而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西方文学批评,因受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的影响,更加关注文本的“非连续性(断裂)”(incoherence)[7] 179-180。这种倾向极不利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我们建设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应该走“拿来主义”“实践标准”和“自主创新”之路,立足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创造出“既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文学理论”[18]。
第二,西方文论的发展通常是以一个新学派的观点来批判之前学派的思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文学理论”到“批评理论”,西方文论已经日渐远离对文学文本的考查,转向了与文学文本相关的外部因素。从“批判理论”到“理论”,西方文论更加背离传统的文学批评原则,走向了泛理论化,最后走向了“理论的终结”。解构主义强调去中心化,对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文学理论传统和思维模式进行了解构和颠覆,甚至解构主义自身也遭到了解构,致使西方文论走向了“自我了断”。西方文论的演进告诉我们,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不能割裂自身的文化传统,不能把中国古代文论打入冷宫。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寻求文学艺术创作和接受的内在规律性,寻求民族艺术自身不断完善的途径”[19]。
第三,西方文论的发展困境增强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论的自信心。西方文论重抽象思维,往往采取分析的语言来看待文学作品。再以英美“新批评”为例。“新批评”反对传统意义上的对作家作品的考据,强调对文学作品的价值作分析,尤其是强调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经验。这显然是“客观地分析主观经验”。其实,在忠实地反映“主观的美感经验”方面,“新批评”并不及中国古代文论。高友工指出:“新批评”的主要贡献在于“能以分析的方法来剖解个人的主观经验,而在客观事实(作品)中找到证据”[20]。然而,文学研究毕竟不是自然科学研究,文学研究常常涉及作者和读者的心理状态。今天的批评家可能自认为是“理想的读者”,但古人的“一言片语”也许更能“深刻地透露出他们的风尚、趣味以及理想”。因此,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基调会“赋予作品新的意义”[20]。
当代西方文论“放弃文学本来的对象”,出现了“理论生成理论”“实践服从理论”等“理论中心论”现象[21]。尽管西方文论已进入“后理论”时代或“理论终结”时代,但是理论将一直存在,而且文学也将持续地发展。西方文论的历史蜕变提醒我们,建设文论需要把握住文学理论与文学的关系。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从当代中国的文学和批评实践出发,构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
结语
西方文论思想源自古希腊,历经两千多年,从“文学理论”到“批评理论”再到“理论”,发生了蜕变,现已步入“后理论”时代。西方文论的历史演进过程是西方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论的译介对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要建设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我们必须以西方文论作为参照,而不是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我们应有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自信,以当下的中国文学实践为基础,创造和发展出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论体系,并在世界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发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声音。
[1]赵一凡.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西方文论讲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7:1.
[2]周启超.总序[M]//瓦•叶•哈利泽夫.周启超,等,译.文学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
[3]张江.作者能不能死:当代西方文论考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61-199.
[4]张法.文学理论:已有的和应有的[J].文艺争鸣,2019(9):60-68.
[5]王一川.西方文论的知识型及其转向——兼谈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向[J].当代文坛,2007(6):4-8.
[6]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 郦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
[7]John Peck and Martin Coyle.(3rd ed.)[M].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2002.
[8]M.A.R.哈比布.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M].阎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9]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27.
[10]王一川.文学批评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4.
[11]Julian Wolfreys et al.(2nd ed.)[M].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6:25-26.
[12]查尔斯•E•布莱斯勒.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第5版)[M].赵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3]Jonathan Culler.[M]. Oxford: Oxford UP,1997.
[14]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元评论[M]//快感: 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4.
[15]特里•伊格尔顿,著,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4.
[16]拉曼•塞尔登,等,著.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26-345.
[17]黄霖.序[A]//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5.
[18]高建平.中国文学理论的凝结、坚守与突进[M]//高建平,等.当代中国文论热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0.
[19]李健.中国古代文艺学的现代意义[M]//李健.中国古典文艺学与美学的当代价值.合肥:黄山书社,2012:3.
[20]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8:17.
[21]张江.理论中心论——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说起[J].文学评论,2016(5):5-12.
From “Literary Theory” to “Theory”: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NGLe-x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341000, Jiangxi; The Graduate School of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for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Since ancient Greek period, there have been five big tur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humanistic turn, theological turn, epistemic turn, linguistic turn and cultural turn. With a tendency of high philosophicalization and de-literariness,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the modern sense has transformed from “literary theory”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rough “Critical Theory” in the middle of 20thcentury and further to “Theory” of commenting the world at the beginning of 21stcentury.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s an inevitable product of western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construc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the lesson from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inherit the good tradition of classic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literary theory; critical theory; theory;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2019-12-12
凌乐祥(1978- ),男,江西上犹人,赣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2018级文艺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西方文论、西方美学。
10.14096/j.cnki.cn34-1044/c.2020.01.12
I02
A
1004-4310(2020)01-006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