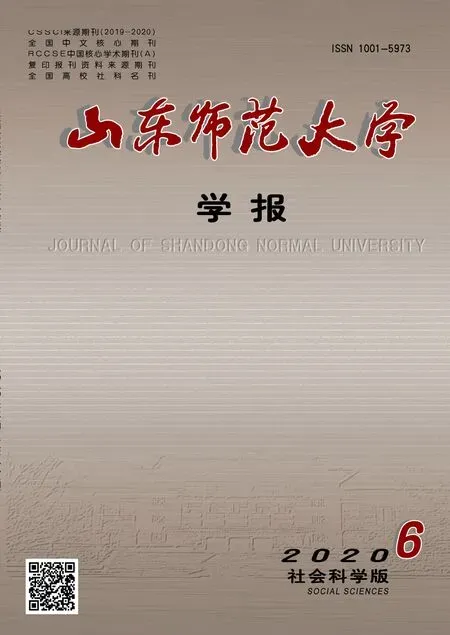近代国学倡导者关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思考与探索*①
曾光光
( 暨南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510632 )
在论及近代中国的国学复兴思潮时,研究者容易将注意力集中于“国”的范畴,认为近代中国学人倡导国学意在爱国保国与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理解与近代学人倡导国学的本意虽无太大偏移,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近代国学思潮更多层面的丰富内涵,容易导致仅从“国内”角度去理解近代国学论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未能充分意识到近代学人对国学的倡导、弘扬涵盖了于内、于外两个方面。前者强调国学在国内的传承及光大,而后者则强调国学的对外传播及弘扬。时人在论及近代国学复兴思潮时曾有如下评价:“内而发挥国学之效用以养成东亚伟大文明之国民,外而欲使国学发扬为世界之学。”(1)叶秉诚:《复宋芸子论国学学校书》,《重光》1938年第2期。中国文化“内”与“外”的发展始终是近代国学倡导者所关注的问题,他们在颂扬、倡导中国文化以增强国人自信的同时,也透露出关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思考。(2)近代中国的国学倡导者在论及文化对外传播时,关于传播对象的用词除“国学”以外,其他用词还有“国粹”(闻一多《论振兴国学》,《清华周刊》1916年第77期)、“中国古代学术”(王光祈《旅欧杂感(续)》,《少年中国》1921年第2卷第8期)、“中国文化”(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9,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9页)、“东方文化”(范皕诲《青年国学的需要》,《青年进步》1923年第63册)等。虑及论述的统一与方便,也为使问题的论述更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与针对性,笔者在写作时除了使用“国学”这一概念外,还采用了“中国文化”“中华文化”的说法。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是当代中国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少有学者对近代国学倡导者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这一问题上的思考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当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供历史借鉴与启发。
一
1902年秋,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致信黄遵宪,其中言及欲筹创《国学报》“以保国粹”“养成国民”。(3)黄遵宪:《致饮冰主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 292页。此议虽未成行,却成为近代中国国学思潮的滥觞。(4)“国学”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最初是指国家一级的贵族学校,后主要泛指“京师官学”。总体来看,古代中国的“国学”主要指教育机构,与近代中国兴起的国学思潮并无多大联系。关于近代中国国学概念的最初提出,应该结合中国近代国学思潮的具体发生来讨论。如果这一概念的提出与近代国学思潮没有直接联系,就不可视为中国近代国学思潮视域下的国学概念的最初提出,而仅仅是一个与中国近代国学思潮没有关联的、巧合的文化现象。不管是黄遵宪于1887年在《日本国志》中提及“国学”,或是屠仁守于1897年5月在《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一文提及“国学”,均应视为一种孤立的文化事件。吴汝纶在1902年考察日本学制期间虽提及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惜其回国后不久即病逝,与随即展开的国学思潮失之交臂。梁启超于1902年秋首倡国学后,陆续撰文就国学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黄节、邓实等人也随后发文附和,倡导国学,国学复兴思潮蔚然兴起。综合考量,学者们一般认为,梁启超于1902年致信黄遵宪谋创《国学报》当为近代中国国学思潮兴起的起点。(参见田正平、李成军:《近代“国学”概念出处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总体来看,近代中国学人倡导国学的目标很明确。一是通过倡导复兴国学以抵御西化浪潮,所谓“有志者亟唱国学,为抵制计”正是此意。(5)显教:《佛学是否国学》,《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1923年第6期。二是倡导复兴国学以图保民族、兴国家。近代中国较早倡言国学的黄节在《〈国粹学报〉叙》中曾论及“学”与“国”“族”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6)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正是从保族兴国的角度,有学者呼吁:“吾人图自保,其可嬉然坐视,不自取旧文化一振刷而光大之乎?”(7)宫廷璋:《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步骤若何》,《民铎杂志》1923年第4卷第3号。在近代国学论者看来,国学屹然挺立,正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数千年的重要文化支撑。
文化自信的提倡是近代中国国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近代国学倡导者试图通过兴起国学以“养成国民”,激发起民众的文化自信,以图实现救亡图存的时代任务。在近代国学论者的笔下,中华文化的历史悠久绵远、中华文化魅力独特、具有种种优长。由此,我们不仅看到近代国学论者对中华文化的无比自信,亦可看到他们倡导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底气与原因所在。文化自信与倡导文化对外传播具有密切联系,由提倡文化自信进而提倡文化对外传播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联动及发展过程。
其一,在近代国学倡导者看来,中国历史绵远悠久,中国文化也长期领先于世界,有裨于世界文明。历史与文化两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凡一国历史绵远悠久者,其文化多璀璨夺目并为他国所关注。顾实就认为:“盖凡一国历史之绵远,尤必有其遗传之学识经验,内则为爱国之士所重视,外则为他邦学者所注意。”(8)顾实:《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国学丛刊》1923年第1卷第4期。作者所言的“遗传之学识经验”当主要指精神文化,中国文化特别是精神层面的文化在古代时期就久为“他邦学者所注意”。这种“注意”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传播,只不过这种文化传播是由他国学者的注意所引发的,并非文化主体的主动行为,是一种非主动的文化传播。某种程度上看,这种由自身文化魅力所引发的文化传播更有力量,有更为持续深远的影响。与顾实仅从精神文化层面展开探讨不同,也有学者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两个层面来论述问题:“夫中国之历史,绵延四千余载,国之精华,焉敢云无。以言形上之学,若周秦之学术,两汉之政治,宋明之理学,皆可超越一世,极历史之伟观,较诸希腊罗马,未或下也。迨及物质文明之发明”,若指南针、经纬度、锦、印刷器、火药、磁器等,“则大裨于全世界之文明”。(9)反:《国粹之处分》,《新世纪》1908年第44期。中华传统文化“大裨于”全世界文明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华文化向外传播与影响的过程。
其二,中华文化具有相当的文化独特性,在世界文化舞台上是“独有之伟观”。曹聚仁曾说:“中华民族之艺术、风俗及政治组织,皆迥然与他民族不同。”(10)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东方杂志》1923年第22卷第4号。闻宥也曾说:“吾华族有文化数千年,向惟从事于自守,除印度哲学接触而外,自余国家关涉殆少。既或有之,亦不过渺小之邻邦,仰我以求余沥,其孳生长茂,蔚然自成为一种独有之伟观,亦正应有之事。”这种“独有之伟观”,正是中华文化向外传播时的独有魅力所在。闻宥还提出合乎“国学”要求的四个条件:“(一)有特殊之色彩者。(二)在历史上有重要之意义者。(三)适合于今日之需要者。(四)足以与他国学术相发明者。”(11)闻宥:《国学概论》,《国学》1926年第1卷第3期。将“有特殊之色彩”列为国学的首要条件,正是对国学“独有之伟观”的强调;将“足与他国学术相发明”作为国学的条件之一特别列出来,充分说明作者对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之间互动、传播、交融的重视与强调。
其三,中西文化各有长短,中华文化之长正可补西方文化之短。关于中西文化的各自短长,梁启超从哲学角度有如下论述:“欧洲哲学上的波澜,就哲学史家的眼光看来,不过是主智主义与反主智主义两派之间互相起伏。主智者主智;反主智者即主情、主意,本来人生方面,也只有智、情、意三者。不过欧人对主智特别注重;而于主情、主意,亦未能十分贴近人生。盖欧人讲学,始终未以人生为出发点。至于中国先哲则不然。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夙皆归纳于人生这一途,而于西方哲人精神萃集处之宇宙原理,物质公例等等,倒都不视为首要。”在他看来,西方的长处即“客观的科学”,我们应该要学习;中国文化的长处即“人生哲学”,正可补西方文化之短,可以“救他们西人物质生活之疲惫”。(12)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9,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4-119页。
从文化互有短长也即文化差异性的角度去考察中西文化,正体现出近代国学论者对文化传播及交融的深刻理解。从世界范围看,正是文化差异引发了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文化间的相互传播又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融。范皕诲就认为:世界文化,分为东西两大系,西方文明以巴比伦、埃及及希腊、罗马为代表,东方文明以华夏与印度文明为代表。“东西两系文明之性质不同,而同为人类精神命脉之所寄,于历史上初无轩轾,各自传衍,经过五千余载,而光华不灭。突焉相遇于今日,自外方之形势观之,阳刚阴柔,西系之动性的文明,与东系之静性的文明,暂时间不无强弱之分。而自内涵之精神观之,则互相灌输,互相调剂,将为孕育世界将来大同新文明之预备。”(13)范皕诲:《我之国粹保存观》,《青年进步》1919年第26册。既然东西方文明之间是“互相灌输,互相调剂”,两者之间的文化传播就是双向互动而非单向流动,这种文化传播的受益者就不仅是某个国家或民族,而是整个世界文明。与范皕诲观点类似的还有宫廷璋“相摩相吸”说。所谓“相摩相吸”,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及相互兼容吸收。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的文化在“相摩相吸”之后会产生一种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而不断传播、“蔓延”。在他看来,中古欧洲文化与条顿文化“相摩相吸”而成西方文化并不断“蔓延”至欧美各洲;秦汉后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相摩相吸”而成东方文化并不断蔓延至东亚各国。进入近代以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接、“相摩相吸”正在发生之中。在这样一种文化发展大趋势之下,作为东方文化主体之一的中国文化应主动整理自我文化以与西方文化调和兼容。不论宫廷璋所言的东西文化调和混合后让“世界文化必将焕然一新”(14)宫廷璋:《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步骤若何》,《民铎杂志》1923年第4卷第3号。,还是范皕诲所言的要让中华文化在“世界将来大同新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都包含着他们对中华文化走出去并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深深期待。
由上所论,可看出近代国学论者倡导文化自信绝非是井底之蛙的自负,更多是基于中外文化对比的宏大视野,正是这种宏大视野使他们在倡导国学之初就开始思考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相关问题。
在论及近代国学论者倡导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原因时,还需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外因对中国的影响。细查欧战后国学倡导者的有关言论,会发现他们当时对国学的倡导与前期有所不同。近代国学思潮兴起之初,其主要目的在通过倡导复兴国学以抵御西化浪潮,所谓“有志者亟唱国学,为抵制计”就是此意。“抵制”一词正体现出当时中学在西强中弱文化格局下的一种守势。守势之下何谈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欧战爆发后,不管是目睹欧战的惨状,还是当时西方部分知识分子对西学的反省及对中学的重估,都极大增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这也正是欧战后国学论者主张文化对外传播呼声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梁启超是欧战爆发后较早踏入欧洲旅行考察的中国学者,《欧游心影录》所载就是他当时在欧洲的所游所感。他在该书中提出,“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后,开始将眼光投向重视“精神生活”的中国文化。他在该书中还表达了对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信心与期待:“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15)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3,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8页。。王皎我对欧战后外国学界对中国国学的关注也有如此描述:“中国的国学不仅引起了世界人们的注意,世界人们的同情,更引起了世界人们的景仰。大半深表同情于中国的外国人,甚可以说凡是深表同情于中国的外国人没有不曾花费一些时间,一些精力向中国的国学里边钻研过的。”(16)王皎我:《中国国学在国际上的新地位及其最近之趋势》,《青年进步》1928年第114期。正是注意到了欧战后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国内一些学者提出要抓住这一机会向西方乃至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范皕诲说:“东方文明之幽光,已为西方人所望见。欧战以后,不但望见,而且非常企慕之、欢迎之。然则以我人所有之瑰宝,贡献于全世界,而增加其幸福,非今日千载一时之机会乎?”(17)范皕诲:《国学研究社缘起与简章》,《青年进步》1924年第69册。王光祈也说:“欧洲自大战后,一般学者颇厌弃西方物质文明,倾慕东方精神文明。……我们亦可藉此机会,将中国古代学术尽量输入欧洲。……使东西两文明有携手机会。”(18)王光祈:《旅欧杂感》(续),《少年中国》1921年第2卷第8期。
近代中国国学思潮的兴起原本是以“救国”为重要目标,欧战的惨状及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关注,让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文化进而萌生输出中国文化以“超拨”欧洲的想法,使国学倡导者在国学“救国”目标之外又多了一层“救世”的期待。(19)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4号。当然,欧战后近代中国学人提倡输出中国文化,虽有“救世”的意味,但从目标上看更多的考虑还是在传播与弘扬中国文化。王皎我则重点关注的是如何保持“中国国学在国际上取得的新地位”;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所言的“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也是将对“祖宗”的责任置于“人类”责任之前。“发扬我们中国的文化,扩张我们中国的国力”(20)许啸天:《王阳明思想的研究》,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88页。,许啸天的这句话虽说得直白,却也将近代国学论者倡导文化对外传播的用意清晰地表达出来。
二
要推进中华文化的传播,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文化的整理研究就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只有通过系统整理,中华文化才能更易于为世界所接受,才能更顺畅地汇入世界文化的洪流中。近代中国学人对此问题的阐述甚多,此处将着重从与文化对外传播相关的角度去梳理近代国学论者对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与探索。
其一,近代国学论者主张中华传统文化的整理,是希望藉此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许啸天在论及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整理时说:“倘然中国的学者,不甘自弃,还希望把中国的学术扶持出来,和世界的学术见面,非但见面,还要和世界的学术合并,使中国老前辈留下丰富而伟大的学术,使世界学术界得到一种伟大的帮助,那非努力于整理六经诸子的工作不可。这整理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要精当而有统系;一,是要适于人生实用。”(21)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新序》,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页。这就将文化整理与文化对外传播联系了起来。其实,若从世界文化来看,学术是没有国界的,整理、传承自我文化就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吴文祺就认为:“中国古代的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因了种种关系,差不多埋没在瓦砾堆里了。我们现在应该用新眼光来研究她,替她补苴罅漏,替她发扬光大。这是谋今后学术进步的必经阶级。学术是没有国界的,一国学术上的发明,各国胥受其赐,所以这种研究,不特有益于中国的学问界,就是外国的学术界,也可以得益不少。”(22)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鉴赏周刊》1925年第1期。对中国固有学术的系统整理既可展现中华文化的面貌,也利于外国学者对中华文化的研究。马叙伦强调中国学人应“自为阐扬”,发掘整理出中华文化“以供欧美学者之研究”,如此也可避免欧美学者对中华文化的“误解”与“轻视”。(23)马叙伦:《国立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画书》,《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第2版。将传统文化整理出来并“公诸世界”,不仅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也是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文化的价值。近代中国国弱民衰,连带中国文化的价值也受到外国质疑。王皎我曾说:“一些外国人以为中国的国学全是纸老虎,及至纸老虎戳穿了,什么也没了!”(24)王皎我:《中国国学在国际上的新地位及其最近之趋势》,《青年进步》1928年第114期。为了改变、打破外国对中华文化的轻视与质疑,系统整理中国文化并对外传播就成为一项紧迫的文化任务,即便是对国学思潮持反对意见的何炳松也主张:“我们中国在国际地位上,常常以毫无供献受人责备;我们正应该急起直追,取学术公开的态度,把自己的学术整理起来,估定他的价值,公诸世界。”(25)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1929年第20卷第1号。
其二,从整理的具体方法上看,他们多主张以西方的现代学科分类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类整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国学论者在思考传统文化整理这一问题时也多取法西方。宫廷璋就说:近代以来,“欧洲科学近益精明,不特自然科学为然,即人文科学之成严密科学,亦方在突飞猛进中。我国古籍本多人文科学材料,欲整理之,莫若取法近代泰西之科学家。首为分科之研究。”(26)宫廷璋:《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步骤若何》,《民铎杂志》1923年第4卷第3号。许啸天也认为,要借用西方的科学分类法,把“一个囫囵的国故学,什么政治学、政治史、社会学、社会史、文学、文学史、哲学、哲学史,以及一切工业农业数理格物,一样一样的整理出来,再一样一样的归并在全世界的学术界里。……这样一做,不但中国的学术界上平添了无限的光荣,而且在全世界的学术上一定可以平添无上的助力。”(27)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新序》,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页。在许啸天看来,采用现代学科分类法对“囫囵的国故学”进行分类,使整理后的中国传统文化能一一“归并”到世界学术文化中。如此,既彰显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也推动了世界学术的发展。以上学者所论虽重在国学的整理方法,但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却有启发意义。以古籍形式存在的中国文化精华,若以原有载体形式传播,其传播效果要大打折扣。若能以西方科学方法予以分类整理,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其三,自我传统文化的整理与对外传播,还涉及文化主动权与主导权的问题,即文化整理与文化对外传播的主导权应掌握在中国学者手里而非欧洲学者的手里。吴文祺就批评过当时国故整理中存在的唯欧洲学者是从的倾向:“他们以为整理国故的目的,只是要减少外人的轻视中国的程度,只是要抬高中国民族的人格,只是要予‘研究东方文明的西方学者’以便利!……他们以整理国故为国际政策,视国故学者为欧洲学者的了头!这种即不是奴隶或至少是政治式的国故论,实在有些不敢闻命!我们应该明白,要不要整理国故是一件事;外国学者研究不研究中国的学问,又是一件事。如果国故有整理的必要,那末虽然外国学者不来研究,我们也是要整理的;如果国故没有整理的必要,那末无论外人怎样的赞美,怎样的颂扬,我们也不该盲从!”(28)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鉴赏周刊》1925年第1期。
以上所论主要涉及提倡整理中国文化的原因、具体方法。要使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落实到具体层面,还需要在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抽取出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内容。综合近代中国国学论者的相关论述来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内容应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中华文化核心的把握问题;二是具体文化的选取问题。
在探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内容时,首先要思考的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把握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王皎我、梁启超、陈启彤等学人的观点较有代表性。
王皎我有两个观点值得注意,一是他将国学从中国文化中抽取出来,视国学为引起世界关注的文化精华:“中国能引起世界注意的,同情的,不是什么景泰蓝、丝绸、茶,亦不是什么海港、矿产,更不是什么风景人物,因为那些只能使世界人们注意,却不能得到它们极充分的同情;惟有中国的国学不仅引起了世界人们的注意,世界人们的同情,更引起了世界人们的景仰。”二是他对国学进一步抽取、凝练,提出“国学的真灵魂”与“国学的真价值”。他在文中对“国学的真灵魂”与“国学的真价值”究竟是什么虽未作具体说明,但他有关如何发现国学真灵魂、真价值的看法对于中华文化核心的抽取、把握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一是国学的真灵魂、真价值终会在中外文化的冲突中渐次“被人们认识出来”;二是对中国文化的系统研究、整理有助于发现、明了“国学的真价值”。他认为,正是因为“以前外国人介绍到他们本国去的中国书,中国留学生等所翻译过去的中国书,大半是一些未曾整理过的,一些未曾研究过的,更是没有什么统系的。这样难怪外国人不能明了中国国学的真价值”。(29)王皎我:《中国国学在国际上的新地位及其最近之趋势》,《青年进步》1928年第114期。
与王皎我仅仅提出问题不同,梁启超直接指出“人生哲学”是中国国学的“最特出之点”:“我们的祖宗遗予我们的文献宝藏,诚然足以傲世界各国而无愧色,但是我们最特出之点,仍不在此。其学为何?即人生哲学是。”而西方则重在“宇宙原理、物理公例”,故其“科学昌明”。也许是觉得仅提“人生哲学”显得抽象,梁启超将“人生哲学”最后定位到儒家上面。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对“人生哲学”的重视在儒家学说上得以集中体现:一是儒家强调“知行一贯”。不像西人“从知识方法求知识”,儒家强调学问“必须自证,必须躬行,这却是西人始终未看得的一点”。二是儒家认为宇宙人生不可分。在不尽的宇宙中,人生虽如蜉蝣朝露一般,但有儒家人生观为指引,人“向前做得一点,是一点,既不望其成功,苦乐遂不系于目的物,完全在我,真所谓‘无人而不自得’。有了这种精神生活,再来研究任何学问,还有什么不成”。与之相对,西方推崇的科学方法“仅能够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机械易懂的。欧洲人却始终未澈悟到这一点”。三是儒家强调“仁”。在“仁”的社会,彼我相通,“故‘仁’的社会,为儒家理想的大同社会”。梁启超对儒家之“仁”评价甚高,以为这份“家业”是“全世界唯一无二的至宝”。(30)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9,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4-118页。
与梁启超的观点类似,陈启彤以为“道”是中国国学的核心。道是什么?在陈启彤看来,道为“诸科之源泉,学术之总汇”,为“学术之指归”。道无所不包,举凡天地鬼神、山川草木、日用人事“莫不毕属”。中国之学的核心为“道”,可谓“博大”,而欧西之学,仅为“局于一隅”的方术而已,可谓“狭”。仅仅言“道”似流于空泛,他进一步将国学之“道”定位为儒家的“礼教”“宗法”。(31)陈启彤:《中国国学博大优美有益于人类说》,《国学杂志》1915年第3期。陈启彤以为,欧西“局局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为其所短,以儒家“礼教”“宗法”为核心的中国之“道”恰好可补西方文化之短。
将中国文化或国学的核心最后归结到儒学上是近代国学论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如范皕诲就认为:“国学的大部分是儒家,儒家的大宗旨,是要人实行道德伦理,做一个躬行的君子。”(32)范皕诲:《谈国学》,《青年友》1924年第4卷第2期。张树璜则将国学精华直接归结为孔学,并认为“孔子之为圣,世界各国罔不推尊,不独中国而已”。为说明问题,他还举出当时欧美各大学对孔子之学的重视:“闻欧美各大学,皆有汉学专科或专系之设备,推尊中国学术,尤崇拜孔子,称为人类唯一之福星。”(33)张树璜:《国学今后之趋势》,《国光杂志》1935年第12期。
将国学落实到孔子之学这一具体文化层面较之于抽象地论“道”或谈“人生哲学”更为实在也更具操作性。其实,国学中的具体文化如文字、诗词等较之玄虚的说教更为生动、直观,在对外传播中更具“染濡”力与“浸化”力。陈启彤就认为,国学的长处不仅体现为“道”的博大精深,较之西学,还具有“优美”的特征。他此处所言的“优美”主要体现在中国文字、诗词等具体文化上。这其中,他尤为推崇中国文字,他以为:“吾国文字,条例不繁,而含义宏深,且又富有感化情志之能力。……其优美而有益于人类也,固信非诬矣。”相较中国文字之优美,“西方之文字,则失之陋是也,彼不自知其陋也,乃自诩其演声之佳妙。”除了中国文字的“优美”,其他如“吾国之书体诗歌,极饶旨趣,故工之者,类多出绝俗,耿介高洁之畴,以往历史,彰彰可征。其流风余韵,岂徒点缀文明而已哉?”作者由此感叹:“我国之文明历数千年而不敝,而异族之与我为缘者,莫不染濡而浸化之,以同归于我。”(34)陈启彤:《中国国学博大优美有益于人类说》,《国学杂志》1915年第3期。
如果说陈启彤对“道”的探析是从文化核心的理论角度探讨问题,那么他关于中国文字、诗歌的看法更多是从文化的具体层面探讨问题。前者关注的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时核心思想的定位问题,后者关注的则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时具体内容的选取问题。虽说中华文化核心思想的定位与具体内容的选取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在选择时若失之偏颇,极易使中华文化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受到曲解。那么,是否有一种相对合理、全面的方式呢?曹聚仁在《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中提出“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由于曹聚仁此文对问题的探讨是置于与“他民族”相比较的宏大文化背景下展开,故他的相关设想有一定借鉴价值。曹聚仁所言“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哲人创导之学说,如老子之“反于自然”,孔孟之“仁义”,墨子之“兼爱”;二是儒家、道家、宋明理学家等各家传授之学说;三是含有民族性、时代性之艺术作品,如《离骚》、骈文、古文、章回小说、词曲、图画等;四是关于记载典章制度及民族生活之文字,如《礼记》《二十四史》等。(35)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4号。曹聚仁以“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来定位、统领中华文化的核心,又将其细分为多个层面,囊括了中华文化各个方面的“结晶”,避免了将中华文化的精华固定于某一方面的局限。仔细推敲,“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的提法与我们今天常讲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颇有类似之处。
论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还涉及对外传播的具体途径与方式的问题。对于通过何种途径、方式向外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近代国学倡导者有一些零星论述,列其要者有:
其一,整理并翻译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要向外传播,整理并翻译本国经典是一条重要途径。邓实早就注意到了书籍在中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夫经欧美之藏书楼,无不广贮汉文之典册;入东瀛之书肆,则研究周秦诸子之书,触目而有。”(36)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9期。邓实此处所论主要指西方、日本对中华文化典籍的收藏,由此却看出中华文化典籍出版并输出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欧战后,随着欧洲学者对中国文化的重视,一些国学倡导者更加意识到了整理并翻译国学经典的紧迫性与重要性。范皕诲曾说:“欧战以后,他们的物质文明破产,所以渴望尤甚,要把我们的国学移译过去,作为他们研究东方文化的资料。若然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却待他们来整理好了,我们想凑现成,不晓得这时候还有我们存在吗?今天我们把自己所有的整理出来,做世界学术上的贡献,表显东方民族的光荣,在世界需要这种文化时,是一个最好的机会。”(37)范皕诲:《青年国学的需要》,《青年进步》1923年第63册。“移译”即为翻译之意。关于有关中华文化书籍的对外出版,除了在国外直接出版或翻译出版中文典籍两种主要方式外,以外文撰写、出版介绍中华传统文化的书籍在海外发行,其效果更加直接,影响更为深远。闻宥曾论及辜鸿铭所著《春秋大义》在西方的影响:“辜汤生著《春秋大义》,扬我国光,被之西土,而大汉文明,昭烂四裔。”(38)闻宥:《〈实学〉发刊词》,《实学》1927年第1期。《春秋大义》为辜鸿铭用英文所著,英文名为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该书主要阐发中华文化的价值,此书出版后,在当时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除了上述书籍的出版工作外,刊物的编辑发行也不失为向国外介绍中华文化的一条有效途径。王皎我在论及民国以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时曾说:民国以后,“到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外国大学多增设了中国语言系,自然慢慢的能有不少的外国大学生可以直接阅读中文的书籍,实即与中国国学行初次的握手礼;在外国各书局所发行的中文书籍(如《中国语自修读本》等)、中文定期刊物或关于中国文化的定期刊物日有所增;这样不就是渐渐的修治钻研中国国学的工具么?”(39)王皎我:《中国国学在国际上的新地位及其最近之趋势》,《青年进步》1928年第114期。作者于此实指出了推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两条重要路径:一是招收外国留学生;二是在国外出版中文书籍及定期刊物,等等。
其二,派遣中国学者特别是“通儒名宿”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早在1905年,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中就叙及国际东方学会议,并认为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能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第一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于1873年在巴黎召开,以后每隔三四年在欧洲各大城市召开一次。这个会议以“讲求东方古今政教、俗尚、语言、文字”为主题,“赴会者多半学界中人,由政府派员代表,各携带著作呈会品评”。邓实对中国政府派员学者参加东方学会议的情况有所记载:“中国政府向不留心此事,从前曾未闻有派人前往之事。惟千九百零二年汉堡之会,由驻德使署派那晋、李德顺、思诂三人赴会。并未携有著作,不过逐队观光,藉资游览而已。今年阿尔日之会,则由驻法孙慕韩星使派同文馆学生唐在复赴会,闻亦未必携有著作。……中国将来派员赴会,当先知该会著重之点,而遣派通儒名宿,则中国虽弱,而往古教化文学之盛,庶不至亦因之而澌灭也。”(40)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9期。
其三,经贸往来也是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当时曾有学者举“锦”为例说明商贸往来对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促进作用:“中国在西汉时,已由中央亚细亚与罗马开贸易之端,中国之锦由是震名于西方。据余意测,今日法人称中国为China,亦本诸拉丁语,其音为震。时人有释为震旦者,非是,当仍锦之原音。西汉之际,华人西渡售锦,人问之曰:‘你卖的是怎么?’答曰:‘我卖的是锦。’西方之人遂因物而指其国为锦国矣,后世遂因之。”(41)反:《国粹之处分》,《新世纪》1908年第44期。在国学倡导者看来,对外经贸输出的不仅是商品,同时输出的还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许啸天对此曾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前年我听印度诗人泰戈尔说:他幼年的时候,住在恒河岸畔,偶然看到一面绣旂,又看到绣旂下面的流苏,随风飘荡着;便想起这流苏是丝做成的,丝是中国的特产品,看到流苏的飘荡,很可以看得出中国人浪漫的特性。因此他未到中国以前,便早已企慕中国人的浪漫生活。”(42)许啸天:《〈国学讨论集〉新序》,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页。
王皎我曾撰文列举了当时中国国学在国际上新地位的种种表现,如当时美国的各大学,均争先恐后增添中国国学讲座;英国、法国于东方文化讲座外特设中国国学讲座;菲律宾的各大学及其他诸国大学的语言系,均增设中国语言系;德国于1927年特别开过一次中国图书展览会;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与北京大学磋商交换教授事宜,并聘该校国学研究院毕业生前往教授中国国学。上述列举正是当时中国国学在国外传播的种种方式,如在国外大学推动中国国学教育、在国外举办中国图书展、中外大学互换教授或学生,等等。这种种方式均可为今天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供借鉴与思路。
结语
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文化对外传播史,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不仅惠及近邻,还对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自鸦片战争以来,面临西方列强的侵凌,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都暂时跌入低谷。在学习西学成为社会思潮主流的时代,文化自信多为文化自卑所代替,文化对外传播更是成为奢谈。在世人多醉心于欧风的时代,近代国学论者倡导古学复兴,力图推进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谋求以国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产生更大的影响。不管是从他们号召国学的初衷来看,还是从他们复兴国学的目标来看,都显示出他们在中华文化发展处于低谷时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坚守,同时也体现出他们对于复兴中华文化的远见卓识。在他们的探索与思考中,我们所看到的既有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坚守,更多的则是他们对于发展、创新、光大中华文化的种种展望与希冀。正如王皎我所言:“设使中国的国学研究者能以永恒的努力,不懈怠的去钻研,中国国学在世界上必有更大昌明的一日。”(43)王皎我:《中国国学在国际上的新地位及其最近之趋势》,《青年进步》1928年第1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