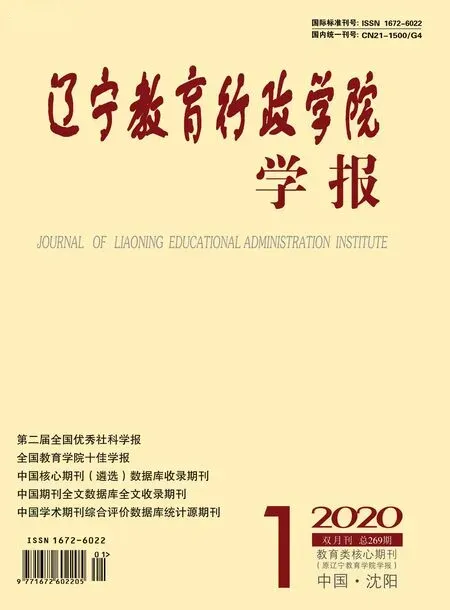儒墨“叩鸣”艺术比较及其当代价值
冯 瑞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650000
《礼记·学记》有言:“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问者反此。”[1](P177)其意思是善于提问者就像砍伐坚硬的木材,首先从容易的地方着手,再去加工难处,这样化繁为简,问题也就得到解决。不善于提问者正好相反。善于回答问题者如同撞钟,轻击则响声小,重击则响声大;待学生从容不迫,再做详解。不善于回答问题者相反。这句话提到了“叩”“鸣”二字,其中叩即问,鸣即答,善待问者如撞钟般,叩小则鸣小,叩大则鸣大,此即儒家所言善待问者。这就是儒家“叩则鸣,不叩不鸣”[1](P177)的教学态度,叩鸣过程也是师与弟子问答对话的过程。儒家经典《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集,其中叩鸣法是孔子采用的最主要的教学方式。孔子非常重视学生的主动发问,从而在对话过程中进行启发诱导。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中包括政治、道德和历史典籍等内容,有孔子主动发问的,也有弟子主动提问的,这些正是儒家叩鸣艺术的集中体现。与儒家并称为显学的墨家虽不反对孔子的“叩则鸣,不叩不鸣”,[2](P426)但墨子在教学中却与孔子反其道而行之,他提倡“强说人”式的“虽不叩,必亦鸣”的教学态度,即强调教师主动而非弟子主动。作为先秦时期两大“显学”,儒墨两派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对“叩鸣”的理解又各有特色,两家的施教态度和方式可以为当下的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儒家“叩鸣”艺术具体表现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官学衰微,私学兴起,“百家争鸣”现象使得教育呈现出师生双向选择的局面,[3](P25)各家学者纷纷讲学,改变教学方法吸引弟子,孔子周游列国,广泛游说,在宣传自己政治思想的同时也与社会各阶层人士深入对话,交流思想;[4](P78-83)同时根据资料显示,孔门弟子大多为成年人,均有思考能力,故孔子方可使用“叩鸣”教学。《论语》一书共20 篇,分492章,根据统计分析,《论语》全书包含师与弟子明确对话86 条,其中弟子主动发问、孔子回答的有67次,师问弟子答的有19 次。[5]由此可见相对于教师提问而言,孔子更注重弟子积极主动提问,即弟子“叩”艺术,孔子在回答过程中的启发诱导则体现了教师“鸣”的艺术。
(一)善问者之“叩”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5](P24),提倡“学思并重”的教育思想,但仅是学思还远不够,孔子还提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5](P279),强调了“问”在“学思”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论语》中弟子问和孔子问共同形成了“叩”艺术,孔子主动提问大多关注弟子从政,在此不做叙述。孔子更注重弟子主动“叩”,弟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主动发问,体现了学生积极的进步思想。《论语》中弟子积极求学,通过各种形式抓住时机热切发问,师与弟子教学相长,其中提问次数较多的有子贡、子路、子张等。
孔子众多弟子中,许多弟子主动提问“孝”“仁”“礼”等方面的内容。但对于孔子的解惑有些弟子唯命是从,如听话的颜渊询问孔子何为“仁”,对于孔子的解惑颜回的态度为“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5](P172)。据记载颜渊对老师的解惑通常都是在竹板上刻记,并不会对孔子的回答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6](P116-120)更值得深究的是其他弟子在与孔子对话过程中,通过进一步的追问来寻求问题的答案。所谓追问,就是对答案连续不断地提问,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地问,直到问询者获取到满意答复。《论语》中有多处是如此描述。如《论语·颜渊》中“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5](P175)在此情境中,子贡询问孔子何为政时所提出的三个连续的问题,环环相扣,连续追问。先是三者去其一,舍谁的问题,待孔子答复“去兵”,子贡抓准时机继续追问,后是二者取其一,舍谁的问题。子贡热切发问求知,一一向孔子提出不解问题,以求最终到底“何先”之答案,此乃追问之精髓。再如“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5](P189)这是《论语》中较为典型的“何加”式追问。冉有在孔子感叹人口众多基础上步步深入追问“何加焉”,以求孔子的“富民”和“教民”之意,追求最终解惑“先富后教”——“教”之重。孔子的课堂氛围时常激荡起伏,常会有像子贡、冉有如此的学生恰如其分地请教老师,与老师进行“心灵对话”,“穷追不舍”地问。
(二)先知者之“鸣”
有问必有答,答即鸣。“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即儒家的“鸣”艺术。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先知”地位,他的“鸣”过程恰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但鸣有鸣的方法和规则,并非随意乱答鸣,也非曲意谬鸣,而是“正中下怀”地鸣。[7](P12-13)《论语》中所记载的师与弟子对话,孔子的答法各有千秋,但均言之有理。最突出的为“叩同鸣不同”,即同一问题对不同之人的回答亦不同。《论语》中对此记录也比较常见。《论语·先进》中“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5](P164)子曰:‘闻斯行诸。’”在此段话中值得关注的是孔子解答不在于同一性定义,而在于根据不同提问者的思想、个性作答。子路冲动故以父兄约束,冉有胆小故需鼓励前进。子游、子夏问“孝”,孔子回答前者“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5](P19);而后者则是“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5](P20)。在此情境中对于同一问题孔子根据其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给予弟子不同的答案。这样的例子还有仲弓、颜渊等问“仁”[5](P172),孔子常常给予不同答案。这也充分表明孔子从学生实际出发,既使学生获得知识,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教育,从不同角度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叩同鸣不同”乃是从学生不同的学习基础和性格特征出发,因材施教,给学生解惑,既达到“传道授业”目的,又对学生提出更高要求,这就是孔子“鸣”艺术的高深之处。
二、墨家“不叩也鸣”具体表现
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为春秋末战国初重要的思想家,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培养具有墨家精神的“兼士”。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墨子深知所有战乱的根源都是因为“不兼爱”,他认为如果不主动教育他人何为“兼爱”,就会“人莫知也”[2](P427),因此墨子大力宣传自己的思想,以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原始材料《墨子》一书全文71篇,现存53 篇,是记录墨子言论和思想的主要著作。其中《墨子·公孟》和《墨子·非儒(下)》两篇主要强调了墨子“不叩也鸣”思想,他认为“叩鸣”有三种形式,即“叩则鸣,一也;不叩则不鸣,二也;虽不叩,亦必鸣,三也”。[8](P47-51)墨子虽也提倡“叩则鸣”,但不同意孔子“不叩不鸣”的做法,墨子更主张“虽不叩,必也鸣”的教学态度,即墨子认为教师应强行施教、主动施教,积极发挥主导作用,问则答,不问则讲,要有积极的施教态度,主动量力,以体现“不叩也鸣”的高深艺术。
(一)强行且主动施教
《墨子》一书记载墨子与人谈话共124 条,其中以“子墨子曰”出现的有84 条,他人提问有40 条,与《论语》中师与弟子的语录形成鲜明对比,这充分体现墨子“强说人”的主动施教态度。首先,表现在墨子“强说人”教学态度上。墨子有言:“遍从人说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2](P42),体现的是墨子更主张努力劝说别人,认为即使弟子没有主动学习、提问,教师也理所应当强行给予知识的教诲,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和积极从教的态度。也即“虽不叩,必也鸣”。在《墨子》一书中,大部分篇幅都以墨子主动向弟子或他人讲授为主,如《墨子·法仪》无学生提问,但全篇墨子都在自行解释“法则”,讲授法则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2](P20)其他篇章譬如《墨子·七患》[2](P26)《墨子·节用》[2](P180)等也均同以上篇章。其次,表现在“行说人”的态度上。墨子认为“行说人者,其功善宜多,何故不行说人也”[2](P427),其意思是出门劝说别人的,得到的功劳和好处比较多,所以为什么不出门去劝说别人呢。在此,墨子所强调的是教师应该主动积极施教,以教人为己任,认为如果过于强调学生的主动提问,就会错过最好的施教时机,以此来体现主动施教的重要性。墨子亲身示范,劳身苦志,可谓是“不叩也鸣”艺术的最佳示范。
(二)因材且量力施教
《墨子》一书虽以“子墨子曰”形式居多,集中体现墨子的“强说人”和“行说人”,但不乏有以他人提问、墨子回答为主要形式的篇章,此中较为有意义的是墨子“因材施教”,这也与孔子不谋而合。如《墨子·耕柱》中有“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2](P395)这句话意思是能进行演说的人就让他演说,能为他人讲解书籍的就去说书,能做事的就做事,体现了墨子根据弟子才能高低不同进行施教,发挥他们各自最大的潜力。《墨子·大取》中也谈到“子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2](P381),意思是墨子教弟子的过程中,弟子深入追究,教师也深入阐述,即弟深师深,弟浅师浅。这也体现着墨子从弟子的理解程度、天赋等方面来对弟子所提问题作答。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这恰恰与孔子的“叩同而鸣不同”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实属妙哉。当然,墨子在因材施教的同时还注重量力而行,如《墨子·公孟》中描述的墨子劝阻几位弟子学射一事,“学必量力之所能至”[2](P443),无不体现着墨子要求学生根据自身能力条件量力选择自己能做之事。
三、儒墨“叩鸣”异同
儒墨两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流派中占据显赫地位,二者并称“显学”。同生活在当时动荡不安的背景下,二者在教育弟子方面有交叉之处,但又因所代表阶层对象不同各有千秋。后世所流传至今的《论语》与《墨子》二书,是后人研究孔墨教育的重要典籍。从二书中可知,二者都注重“叩鸣”艺术,但运用此艺术所持的态度、采用的方法又各有特色。
(一)“叩同鸣异”之同
首先,二者最明显的共同之处是都注重“叩鸣”艺术,儒家和墨家皆表示“叩则鸣”的教育态度,儒墨两家都提倡对弟子的提问给予回答的教学态度。对于“叩鸣”,孔墨都有比较全面的看法和做法。其次,儒墨在师与弟子的“叩鸣”过程中均表现出“因材施教”之式。墨子虽未明确提出“因材施教”,但将其贯穿于墨子教育过程中。孔子有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5](P86)。就是说学习基础处于中等以上者教师可以与学生深入探究高深知识,中等水平以下者要立足于基础,不能传授其深奥知识。表现出孔子对待不同学术造诣之人有不同之教法,如此方可达到较佳效果。墨子虽在“因材施教”处论述不多,但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其也有此意。墨家在教育过程中同样重视教师量力而教,强调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选择学生可接受范围内的知识进行传授,不能统一划齐。孔墨二人在教育弟子过程中,对于弟子的提问,通常是根据弟子实际出发,在弟子的原有特质、理解接受能力的基础上,遵循个体差异性,对弟子的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的回答,使得弟子对问题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获得最佳学习效果。问深答深,问浅答浅,将“叩鸣”教学艺术的独特高深之处淋漓尽致地展现,实属妙哉。
(二)“叩鸣”态度方法之异
儒墨虽处在同一时期,且墨子刚开始“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8]两家于教育上难免存在交叉之处,但由于二者各自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使得二者教育思想上存在差异,“叩鸣”之异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从“叩鸣”过程中教育态度上来看,儒墨两家“叩鸣”的前提不同。儒家提倡“叩则鸣,不叩则不鸣”,孔子所强调的是在弟子主动提问的前提下,教师予以解答和对其教育,教师处于非主导地位。在师与弟子问对中,孔子更提倡学生积极主动提问,抓住各种机会深入学习、思考,与教师进行一场知识的“心灵交流”。师与弟子对话过程中,孔子始终遵循有问必答,无问无答的教育态度。墨子则更注重“虽不叩,亦必鸣”,强调教师要主动施教、强行施教,即“强说人”和“行说人”,墨子认为教师要抓住机会,以教为己任,主动出击传授系统知识,而不能空等学生主动提问,这样有可能会错失教育良机。这也鲜明体现出墨家较儒家更注重教师主动行教,并具有积极施教之心。其次,“鸣”过程中的方法不同。从《论语》记载的孔子与弟子对话可以看出,孔子在回答学生问题过程中注重启发学生深入思考,掌握时机举一反三,鼓励学生“温故而知新”[5](P23),提倡学生积极思考提出更具高度意义的问题,达到学习的更高层次,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而墨子以强学强教为主,采取一贯式讲授,将自己的观点、想法传授给弟子,忽略了弟子主动思考的重要性,有些死记硬背的意味。
四、儒墨“叩鸣”艺术的当代价值
儒墨“叩鸣”艺术是儒墨教育思想中极具特色的教学艺术,对当前教育界有着重大且深远的意义。现如今,我们既需要紧跟教育前沿发展,也需要研究古籍中可借鉴之处,吸收儒墨“叩鸣”教学艺术的精华,将儒墨两家思想有机结合并合理运用于课堂之上,取其教育态度和方法可运用的得当之处,结合当代教育实际,深入挖掘“叩鸣”艺术的当代价值,使其更好地为教育服务。
(一)当代教师施教态度的自我反思
现如今的教学课堂中,由于受到学生人数多、班级授课制及社会升学率的影响,教师单方面主动讲授知识成为课堂教学最主要的手段,这种现象尤其在中小学盛行。大部分教师为了达到所谓的升学率,一味强教,不注重教学中对学生的启发诱导。这种墨家所倡导的“强说强教”的主动教学态度虽值得肯定,但同时也摧残了学生的创造力和耐性,使得学生对学习产生厌恶情绪;但如若教师单纯持有孔子“生叩则师鸣”的启发诱导的施教态度,虽说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激发学生的创造性,但又不利于系统知识的传授,从而导致学生被优质学校淘汰。因此,在当代教学中,针对不同学段的学生,教师到底应该采用墨家强行主动的施教态度,还是儒家启发诱导、注重学生自主的施教态度;或者是将儒墨两家结合的施教态度;教师所持有的教学态度是否应该分段考虑,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
首先,儒墨施教态度的有益结合。中小学学生认知发展仍处于逐步上升阶段,思维能力还未成熟,对事物的认识还不足以达到成人水平,思考存在一定缺陷,因此不能任由其自由发展,完全运用儒家独立自主学习的态度显然行不通。但同时需要考虑的是当代中小学生由于长期生活在电子网络发达环境之下,接收信息的渠道多元。倘若教师一味持有一种单纯讲授书本知识的态度,不仅会扼杀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会使学生产生烦躁、厌学等情绪。可以看出,两种态度任选其一都不足以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应该汲取儒墨两家施教态度之精华,将二者有机结合,以提升教学质量。对待中小学生,首先最重要的任务是传授系统知识,充分运用墨家“强说人”和“行说人”的主动态度,主动并强行施教,教予学生这一阶段内必须学习的基础性知识,并积极关注学生的学习水平,在知识的学习上努力达到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境界。这一阶段的教师要秉承主动出击的态度和思想,抓住机会传达心中所想。但是,同时教师也要结合儒家启发性的态度,在施以学生基础知识的同时增加学习趣味性,引导学生对所学知识做简单思考,提倡学生主动提问,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教学过程中教师采用启发诱导的方法,才能发挥和保持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其次,秉承和发扬儒家启发性的施教态度。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大部分成年人,知识的获得相对占比已经降低,这一阶段的学生尤其处于研究生以上阶段,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科研水平。这一阶段学生的思考能力接近成熟,对于文字的理解也达到一定水平,不需要和基础教育阶段一样,过于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而是需要就某一专业领域深入挖掘,找寻自己感兴趣的可研究点。因此,在这一阶段,教师应该主要采用儒家启发诱导的施教态度,给予学生灵感和问题,引导他们在学习中独立思考,并积极和他们谈论交流专业领域热点问题,激发学生兴趣,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提倡学生主动询问难点,主动提出研究方向,并如孔门弟子般对疑惑性知识一问到底。
(二)当代师生“叩鸣”艺术的合理运用
在当代课堂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相互“叩鸣”(即提问和回答)是课堂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缺一不可。对“叩鸣”艺术价值的充分发挥,《论语》和《墨子》已经有了比较周全的叙述。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时刻处于主导地位,掌握“师叩”的艺术,充分发挥提问的优势,改善课堂气氛,增加学生学习热情;同时对学生提问给予恰当的“鸣”。但更需要注意的是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要鼓励学生在学习中敢于提出质疑,在“学思结合”中勇敢“叩”,让学生自己深入感受孔子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中“问”的重要性。
站在教师一方考虑,到底如何才能如同孔子、墨子将“叩鸣”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呢?首先,教师应懂得“学第一,教第二”。“传道授业解惑”乃是古今教师的主要任务。“传”什么“道”、“授”什么“业”、“解”什么“惑”是教师之学的核心问题。[9](P7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1996 年世界教育报告——教师和变革世界中的教学工作》指出:“教学同其他专业一样,是一种学习的专业,从业者在职业生涯中自始至终都有机会定期更新和补充他们的知识和技能。”[10](P388)在终身学习的时代,教师要深刻明白对优质教学而言,“学”在其中的重要地位。无论是哪一阶段的教师,首先,都要学习理论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转化成自己的主观性知识,如此才能在教学中灵活运用。作为教师孔子清楚该“传”什么“道”和“授”什么“业”,难以猜测的是他的众多弟子在课堂中就某一知识会提出何种程度的问题。正是因为孔子的博学,他才能轻松掌控教学全过程,启发诱导学生积极提问,为学生“解”各种“惑”,并将自己所知所感告诉学生。正如周勇老师在《跟孔子学当老师》一书中谈到“教书不等于教学,除非教的是自己撰写出来的书,而不只是教别人的书”。[9](P64)孔子所教就是自己撰写、体味到的书。其次,教师要鼓励学生“每事问”,如孔子般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努力做到“因材施教”。孔子的“因材施教”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髓,理应取其精华。当然,在我们现实的课堂中,由于班容量大、统一教育目的等一系列外在因素,要做到因材施教很难。但必须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努力去看到每个学生的闪光点,根据学生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教育,就像孔子对待“樊须三次问‘仁’”,三次回答截然不同,长期如此定会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的问题自然滔滔不绝。再次,教师应运用丰富的提问方式,改变以往课堂一贯严肃的提问方式。当前我国教学课堂主要采用班级授课制和讲授法,师生提问气氛单调、沉闷,教师也比较喜欢提问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久而久之,师生疏离。面对这种情况,教师理应深入思考自身教学。当代教师更应该学习孔子,创设轻松的教学环境,让学生可以畅所欲言,相互讨论,而不是单单师问生答。同时教师也可在提问过程中层层追问有效信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但这样一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教师反复做,鼓励学生丰富知识,参与实践,激励学生自己感受、思考,如此学生才能够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最后,教师要学会如何“鸣”。在回答学生问题时,教师不仅要学孔子“不同鸣”,根据学生天赋、学习情况,以最恰当的回答为学生解疑,当深则深,该浅就浅,努力做到使内容深入浅出,同时也要学习墨子的“强行鸣”。即教师要主动了解学生实际,根据以往带班经验找出共同不解之处,适时主动出击,积极为学生解惑。[11](P75-77)将儒墨不同“鸣”有效结合,教师方可发挥其最大作用。
对学生而言,主要是要摒弃传统课堂“师为大”的观念,大胆质疑和提问。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发明千千万,起于一点问”。这“一点问”就是学生思维的火花。首先,作为一名学生应该学会提问,并不耻下问。[12](P56-59)要积极向老师提出问题,不要顾及颜面或他人看法,要知道学习的谜底就是获得知识,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当代学生更应该学习樊须不耻下问的精神,即使碰钉子,也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对于一直理解不了的“仁”,可以三番五次提问孔子以寻求最佳答案。其次,当代学生也应该学习孔门弟子追问的态度。《论语》中记录了很多弟子追问孔子的情境,如子贡询问孔子何为政所提出的三个连续的问题,环环相扣,抓准时机连续追问,这正是当代学生所缺乏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当代学生要在学会提问的基础上,对于教师的回答慎思其中关键以及自己不懂之处,抓住提问的时机,深入追问,一个问题问到底,及时得到教师解惑。[13]综上,学生应该大胆提问,抓住时机,并且要大量阅读获取知识,如此才能更好地应对教师的解疑,并积极参与提问与追问。
可以说,真正的“叩鸣”艺术是儒家“叩则鸣,不叩则不鸣”与墨家“虽不叩,必亦鸣”的巧妙结合。“叩鸣”已经并非是简单的师生问答交流,它所体现的是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矛盾。教师处于主导地位,要“叩”更要“鸣”,前提是知识的传授及终身学习;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更要学会学中“叩”。其实,在师生“叩鸣”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双方的“心意”,“叩鸣”更需要的是双方心灵上产生共鸣。教师首先应遵循墨家“强教”,才能使学生获取知识,然后灵活运用儒家启发诱导,促使学生努力钻研直到探寻出具体问题;而教师也要不断汲取知识,体验学生的种种经历及心理状态,如此一来,师生才能达到前所未有的“心灵交融”,“叩鸣”教学才可称之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