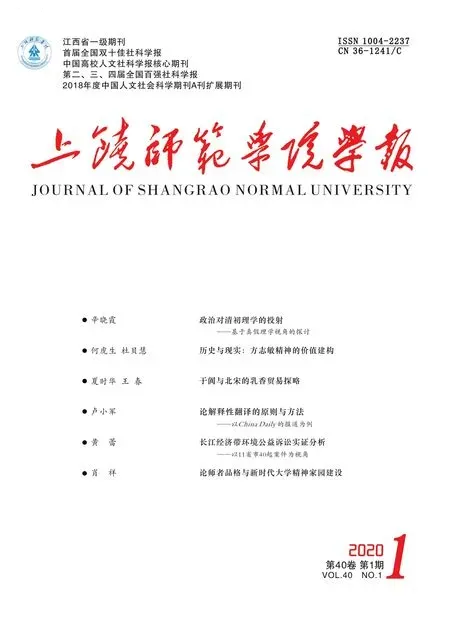曾国藩君子人格养成思想述论
(上饶师范学院 江西省2011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江西 上饶 334001)
曾国藩是晚清“第一名臣”,被后人推崇为“千古完人”和“官场楷模”。其事功业绩、政治家风度及个人品格修养很少有人能匹敌,可以称得上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梁启超曾高度评价曾国藩:“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1]毛泽东亦高度评价:“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2]笔者认为,无论是梁启超,毛泽东还是其他大人物,他们之所以高度推崇曾国藩,除了所谓的事功之外,更多的应该是曾氏毕生追求圣贤君子的人格修为。曾氏一生著述等身,光家书就有一千余封,其著作内容极为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尤其于君子人格的养成上颇多建树。曾氏将程朱性理之学与湖湘学经世致用思想特质融会贯通于君子人格养成思想之中,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他特别讲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致力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如慎独自省,日新又新,磨砺意志,勤俭刻苦,力戒虚骄,读书进德,以恒为本等等。
一、君子慎其独
慎独是传统儒家修身工夫之一,出自《礼记·大学》:“此谓诚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3]所谓慎独,是指人在独处之时,与在人前一样做到诚实无欺,内省无愧。在儒家看来,只要人们在独处时注意自我反省,迁善改过,慢慢地就会心境清明,智慧越来越高。
曾国藩作为晚清理学名臣,素以儒家道统尤其是程朱理学道统之继承者自居,对于传统儒家的这种慎独内省的工夫,自然是感同身受。他在给弟弟或者儿子的家书中,“慎独”提得非常之频繁,他也曾写过一篇《君子慎独论》,专门探讨慎独问题:
慎独则心泰,……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问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4]138
在他看来,古人的修德工夫有很多,其中首先要做的而且成效特别明显的是慎独,唯其慎独,才能心胸安泰。慎独就是要时时刻刻遏制私欲,循礼而行,注重于细节微小处下功夫,惟其如此,才会安泰坦然。如若心里明知有善有恶,却不能在行动上为善去恶,这就是知而不行,自欺欺人的小人行径。他曾写过一篇《记过箴》,详细阐述了慎独基础上改过迁善的工夫路径: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忿,阴恶曰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曰暴,柔恶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语,曰节饮食。凡此数端,其药维何?礼以居敬,乐以导和。阳刚之恶,和以宜之;阴柔之恶,敬以持之;饮食之过,敬以检之;言语之过,和以敛之。敬极肃肃,和极雍雍,穆穆绵绵,斯为德容。容在于外,实根于内。动静交养,睟面盎背。[4]177
心里是否自欺,自心独知,因为修身养性、成德成圣毕竟是自己的事情,外人强求不得。不做让自己内心感到惭愧自疚之事,内心就会心安平和,泰然自若,此乃守身之首务。
慎独不仅要求做到为善去恶,不自欺,不自疚,还要在“诚”的基础上切切实实地做格物致知工夫。要秉承《大学》和朱子格物致知之意旨,在日常生活中用心察识前言往行,检点行为细节,做到“心之际于事者,已能剖晰乎公私;心之丽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4]177,这样才能做到“实有所见”,然后可以确定何者可以做,何者不可以做。如果将慎独仅仅视为只存在于心中的“内照”工夫,而“昧乎即事,即理”[4]177,不在日常生活细节中去格物致知,不在实际事业中去磨练心志,则可能导致慎独“失当”。他以陆王心学为例子指出,陆王过分强调“心”的功用,发明本心、先立其大者、致良知的主张以及知善知恶四句教等,皆过分夸大“心”内照在慎独中的功用,遗弃外在“物”对修养工夫的辅助作用,忽视格物致知工夫的实际功用,从而导致“慎独之旨晦”,因此在格物致知基础上的慎独才是真正的“入德之方”[4]139。
曾国藩一生志不在封侯拜相,而在做人,做孔孟儒家所谓的“圣贤君子”。故在慎独、克己、格物致知等方面,其切实践行,笃定不渝,可谓艰苦卓绝。曾氏每天黎明即起,其日常用力,不是用在处理事务,便是读书作文和反省自己,数十年如一日。曾氏有恒于记日记,细致精到处,必将一日之内的每件事、每个念头都记下来,一有不合圣贤君子规范的行为或念头,都严格地自我检讨,力图把“恶”消灭在萌芽状态。翻开曾氏日记,从他立志成为“圣人”开始,直至暮年,几乎每日都可以看到他对自己之深切痛责。据记载,一日,曾氏到朋友家做客,见到主妇时,色心顿起,注视良久,和人交谈时,语出不庄,如此种种,都被他以“大无礼”“太不检”而记录下来。甚至在做梦时梦见了自己发财,醒来后也要自责贪财之心不死,深自痛责一番。壮年之时,为了克制自己的好色之念,他整日勤奋读书,苦思学问,以求精力耗尽,转移淫欲之思。曾氏30岁以前,最喜欢吸烟,烟瘾甚大,片刻不离,但是到道光二十二年时,他痛下决心戒烟,此后终其一生,再无烟癖。每日无论多忙,均要静坐数刻,静思反省,不断和私欲斗争。如此种种,皆是克己慎独的功劳。功夫不负,曾氏通过自己慎独工夫的艰苦努力,终于实现了精神与人格的提升,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自私、虚伪、阴暗、猜忌等恶劣品质,而是一个集刚健有为、光明磊落、忠恕待人、至诚慎独等诸多优良品质于一身的儒家君子人格典范。曾氏通过慎独和克己修身,达到了儒家成德的化境,养成了中和纯粹、高尚澄明的圣贤君子人格。
二、君子读书明理
在曾国藩看来,要修成君子人格,除了切己慎独做格物致知工夫之外,还要读书。那么,为什么要读书?读书目的何在?曾氏认为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旨在“明理”。此“理”,就大处而言,就是程朱理学所谓的“天理”,是世界万物之本源,代表了天地万物之本性以及人之本性,明了此理,即是圣贤君子;往小了说,即是儒家纲常伦理,道德伦常,也就是儒家所强调的“礼义”。“礼”贯穿于君子修齐治平的整个过程,他说:
古之君子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4]410
明理要求人们在生活日用中克己复礼,践行儒家礼义廉耻、伦理纲常。而君子要做到明理,必先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遵照儒家经典的教导来指导自身的实践,在切身实践中渐渐达到成德成圣的境界。在曾氏看来,成为圣贤君子不是不可企及,唯有立定志向,才能够成就圣贤,“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5]128不过,志向只是成圣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立志而不努力读书,亦难以达到圣贤境界。读书明理,志在圣贤,这是曾氏为学做事的根本目的所在,也是曾氏为学之道的核心内容。在志做圣贤目标指引下的读书明理本质上就是一种圣贤君子人格的修炼工夫,换言之,曾氏读书实乃知行合一的道德践履,读书的终极目标乃在成为圣贤君子,而非世俗趋之若鹜的科举考试。曾国藩的侄子考中秀才,曾氏喜悦之余,颇多担忧,乃在家书中诫勉其侄:
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教之旗帜也。……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6]357
曾氏还劝诫子侄向其好友刘蓉看齐。刘蓉终生不热衷科举功名,不过是一名普通儒生,连秀才都不是,却胸怀大志,博学多才,“尤务通知古今因革损益得失利病与其风俗及人才所以盛衰,慨然有志于三代,思一用其学术以兴起教化,维持天下”[7]。曾氏极力称赞其智慧才能,且因其立志读书,日日精进不已,其所造所得,即使进士也无法望其项背。曾氏还曾命其弟向刘蓉学习,以他为师,说:“霞仙近来读朱子书,大有所见”[8]。曾氏确实眼力非凡,刘虽无任何功名文凭,却能够自学成才,写下了百余卷发挥圣贤义理之书,虽一生不离山野,而见识卓绝,非一般士大夫所能企及。不宁唯是,刘蓉除了学问了得,还人格高尚,德才兼备,其学问事功远胜那些考中的士大夫,曾氏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才是大家学习的楷模。有鉴于此,曾氏时常告诫儿子立志做真正的读书人,八股文、科举试贴皆非今日之急务,徒费时日,汩没性灵,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关于科举之害,曾国藩深刻指出:
自吾有知识以来,见乡之老成夙学,笃于文律者,恒困顿无以自拔,或终身不得当于有司之试。而其所教之子若弟,往往分沾余技,飞腾速化以去。……制艺试士既久,陈篇旧句,盗袭相仍。……名目既繁,科条日密。虽过百人之智,穷十年之力,犹不能洞悉。及其彻于心而调于手,而齿已日长,少时英光锐气,稍稍衰减矣。[4]189
不宁唯是,他还认为,孜孜于科举八股,可能会导致学业无成,贻误终身。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说自己早年并未认识到这一点,热衷科举,学问差一点误入歧途。幸好早一点得到了科举功名,对学问并无多大损害,挽救弥补还来得及。如果自己至今没中举,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钻研八股文,皓首穷经,学问必然踽踽不前,一无所获,岂不惭愧终身?!
可见,曾氏强调读书明理,是为了成就圣贤君子,而不是为了做官。他自己虽然有进士身份,却以学识评价人才,而非以学历衡量人,可谓独具卓识。科举出身不乏无成就者,但即便中了进士,如果原地踏步,不思进取,也必将一事无成。相反,如果刻苦读书,修身明理,即便无科举功名,也不妨碍成为圣贤君子,其成就或许会远远超过那些读书只为升官发财的人。
明理除了读书,还要务实、知人,晓事理。曾氏继承了儒家特别是湖湘学的经世致用学风,强调指出:“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9]87。据此,曾氏修正了宋明理学家们沉溺于心性之学、热衷于从考察思想动机中去鉴别君子与小人的观点,他强调指出:
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昏暧,则为小人。[10]14
所谓“晓事”,不是“求小成于事业”,也不是“求有当于语言文字”,这些入了“末流”,真正的“晓事”,主要体现在君子的“器识”上: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于人人者,岂有他哉,亦其器识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试之以富贵贫贱,而漫焉不加喜戚;临之以大忧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谓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识之谓也。……今之君子,秋毫之荣华而以为喜,秋毫之摧挫而以为愠。举一而遗二,见寸而昧尺。[4]190
又说:
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窥几何,而自以为绝伦之学;辽东之豕,所异几何,而自以为盖世之勋。……此皆识浅而易以自足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履;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431
“器识”“度量”的大小,决定了君子的“晓事”与否,甚至成为衡量君子小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说,读书是明理的内在修为,那么,务实、晓事、知人、器识则是明理的外在呈现,是知行合一,主客观密切结合的道德践履活动。这些活动既坚持了“理”这一客观标准指导,又做到了眼睛向下,虚心考察实际情况,从实践阅历中强化了对“理”的信念。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明理,“不晓事”。他强调指出:“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10]14毫无疑问,曾氏将晓事、知人作为君子小人的区分标准,这对宋明理学笼罩下的晚清社会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超越,为圣贤君子人格之养成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三、君子进德修业
在曾国藩那里,君子士大夫读书除了明理、务实、晓事、知人,还有进德、修业。“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自卫其身。”[5]31进德是指修身立德,仁民爱物,遵循《大学》诚、正、修、齐之顺序来强化自身修养;修业就是通过读书做文章来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他说:“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5]82曾氏认为进德修业需要在主体理性自觉的范导下一点一点地积累学识、才干,“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5]82。而功名利禄并不能自己做主,他说,“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5]82。换言之,功名富贵,皆由命定,强求无益,徒劳而已。反之,若淡泊名利,发愤读书,往往能不求自得。这就是所谓的“尽人事而听天命”[5]82。尽人事要求人们通过读书、立志等种种途径来变化自身的气质: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6]19
变化气质,就是通过读书明理、道德践履将小人的气质转换为君子的气质,乃至于形成圣贤气象。“尽人事”旨在将圣贤书中之“理”付诸生活日用之实践,在日常生活中修身养性,迁善改过,断恶修善。“听天命”就是要在明理修身的过程中不计回报。只要尽力了,天命福德就随之自然转变,就会在断恶修善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改善自身的命运处境。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和小人先天气质“不甚相远”,大体差不多,二者不同之处就在于后天“习”的不同,以及所交朋友的作用不同。他说:
习而之善,既君子矣。其有过,则其友直谏以匡之。又有友焉,巽言以挽之。退有挞,进有旌,其相率而上达也,奚御焉?习而之不善,既小人矣。其有过,则多方文之。为之友者,疏之则心非而面谀,戚之则依阿苟同,惮于以正伤恩,其相率而下达也,奚御焉?兹贤者所以愈贤,而不肖者愈不肖也。[4]136-137
然而,君子变化气质仅仅依靠断恶修善、朋友规劝还不够,必须进德和修业兼顾,而且要终把进德放在首要位置,因为学业的进步并不必然引起道德境界的提升,反之道德的提升往往会促进学业的上进。所以曾氏将“进德”作为自己“为学之道”的核心命题。至于“进德”所要达到的境界,曾氏指出:
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5]34
民胞物与,内圣外王,天地完人云云,都是宋儒倡导的气象宏大的理想境界,也就是宋明理学家所向往的圣贤气象,曾氏以此告诫诸弟不要汲汲于科考失利这类小事,而要胸怀大志,成圣成贤成君子。
曾国藩还时常向兄弟们介绍自己进德修业中所遇到的良师益友,从中可以略窥京师士大夫砥砺修身、进德修业之一斑:
先生(唐鉴)为外吏二十年,萧然无资以自存,即当世所谓迂阔,而其为学也,又惟自治其身心之急,或不沾沾于文艺之短长。……诸君子独相寻于淡泊,究道而考德,夙参而莫造。……何其笃也![4]182
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5]35-36
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5]35-36
曾氏向这些师友学习进德修身的方法,但他很快就发现,日课固然能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毛病,但在改过上并无很大助益。诸如溺情于围棋,好动不好静,对人言不由衷,好名好作诗,读经精力不集中,心有旁骛种种毛病,日日自查日日有,近一个月下来,戒掉的只有抽水烟这一项。他向倭仁请教,得到的答复是,要有耐心,以今日之我战胜昨日之我绝非易事。孔子之“大德不逾闲”,即便是圣人也难以完全做到。孔门高第颜回可以三个月不违仁,这是不易学的。即使“日月之至”的境界,亦非圣贤不能,“我辈但宜断断续续求其时习而说”[11]132。唐鉴则告诉他:“最是‘静’字功夫要紧,……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礼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11]132
日课两月之际,曾氏再作反省:
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所谓三戒、两如及静坐之法,养气之方,都只能知,不能行,写记此册,欲谁欺乎?此后直须彻底涤荡,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求息息极静,使此生意不息,庶可补救万一。慎之,勉之![11]132
倭仁加上的批语是:“力践斯言,方是实学。”[11]132
但说归说,做归做,只过了一夜,他又故态复萌。先是晏起,而后“赴何子贞饮约。……酒后,观人围棋,几欲攘臂代谋,屡惩屡忘,直不是人!……至岱云处,与之谈诗,倾筐倒篋,言无不尽,至子初方归。比时自谓与人甚忠,殊不知已认贼做子矣。日日耽著诗文,不从戒惧谨独上切实用功,已自误矣,更以之误人乎?”[11]132是日,倭仁批语的分量也加重了:“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尽净,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11]132
但是,进德修身殊非容易。曾氏从师友那里学到很多,但他的毛病还是有很多,“自十月朔立志自新以来,两月余渐渐疏散,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仍故我矣”[11]137。于是向好友看齐,再立课程如下:“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11]137
可以看到,曾国藩修身进德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反复,充满心理斗争的过程。这一方面说明曾氏修身道路之艰难,另一方面也向世人表明圣贤君子人格养成殊非易事。人的天性不可克制,即使后天养成的陋习,也绝非朝夕之功所能祛除。因此,进德修身不可急功近利,必须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终身实践,始终不渝,惟其如此,方能成就圣贤君子人格。
四、君子立志有恒
既然养成圣贤君子人格殊非易事,那么应该如何践行呢?曾国藩认为,除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还要立志有恒。众所周知,“志”是人的心灵意志所向,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志”在中国人的智慧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儒家看来,“志”是“士”和“心”的组合,“士之心”,说明了“志”在中国古代士大夫群体中所具有的分量。在儒家士大夫那里,立志和做人是密切相关的。“有志者,事竟成。”志向就是人生的发展目标,如果君子能树立一个比较长远的、正确的、有用的奋斗目标,就会产生前行的动力,鞭策自己努力。目标明确了,行动到位了,慢慢就会有使命感和成就感。因此,志向如何,不但极大地影响士大夫的君子人格,而且也影响其人生成就。对君子而言,什么样的志向才是比较合理的呢?曾氏强调指出:
士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也。就其最善者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4]411
当然,立志只是思想意志上的事情,仅仅立志还不够,还需要为了志向付诸行动。志向远大固然可嘉,但同时意味着朝夕之间难以达到,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在努力的过程中,也势必遇到种种主观或客观的困难,因此必须克服这些困难,才能继续前进。换言之,为了实现志向,必须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荀子在《劝学》中提及研究学问时也苦口婆心地告诫人们,只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就能终成大学问家,做其他事情莫不如此。
曾氏特别注重立志并持之以恒的问题。他认为,判断人才的高下优劣,志趣是首要标准。低劣的人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受世俗的影响与陋规的束缚,因而逐步沦为卑污小人;优等人才仰慕往圣前贤的德业功绩,因此能日益高明,成圣成贤。古人云:“服了金丹,就能脱胎换骨”,在曾国藩看来,立志就是脱胎换骨的金丹。人的气质虽然是天生的,但是确立坚定的志向,就可加以改变。曾氏有一段时间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经过思考,他认为这是志不立所致。因为志未立,则放松潦倒,心中茫然无定向,无方向,则难以保持内心宁静,不宁静则心不安。于是他痛定思痛,立定志向,此后再不动摇。纵观曾氏平生,时常立志,或立志圣贤德业,或立志功成名就,或立志扫平洪秀全,难能可贵的是,他只要一立下志愿,就一定持之以恒,不达目的决不放弃。
曾氏还认为,对君子而言,仅仅立志还远远不够,君子读书为学还应该做到三有:“有志、有识、有恒”[4]42。他说:“有志则断不敢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5]42有志就是树立远大志向,读圣贤书,立圣贤志,而不局限于如前所述的科举功名。有识就是如前所述的明理、晓事、知人。相对于前二者,曾氏尤其重视有恒,在他看来,一个人做好事不难,难就难在一辈子不做坏事只做好事,这就需要以“有恒”的态度来读书做事,迁善改过。读书有恒,每日每时得到圣贤之书和圣人之言的熏陶教诲,得到圣贤德行言语的督促范导,虽然一时半刻难以断灭小恶,却不至积累成大恶,职是之故,进德务必读书,读书务必有恒,有恒则可成明理之圣贤君子。
在曾氏看来,读书进德,不必贪多求全,而应对照书中圣贤言语逐段落实,惟其如此,才是真读书。每日与圣贤书相伴,慎独自照,反躬自省,切磋琢磨,就能变化气质。他说:“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9]239曾氏时常在日记中痛责自己无恒,他说:
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辞,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尚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6]476
有恒还必须树立正确的“功效”观,所谓“功”就是用功的程度和过程,所谓“效”就是事情的结果。在曾国藩看来,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只讲功不讲效固然不行,只讲速效不讲做功更是一种无知的“妄”为。所以对君子而言,必然有一段“积累日久”的做功过程,才能取得成效。他说:
是故为学既久,则道业可成,圣贤可到;为治既久,则教化可行,尧舜可至。若是之类,莫不由积日累久而后至,固非骤而及也。……是故君子之用功也,如鸡伏卵,不舍而生气渐充;如燕营巢,不息而结构渐牢;如滋培之木,不见其长,有时而大;如泉之有本,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但知所谓功,不知所谓效,而效亦徐徐以至也。[6]429-430
可以看到,做到了读书有恒,则能明理进德,树立了正确的功效观,做到了锲而不舍、自强不息,则有识和有志也就能够最终实现。纵观曾氏一生,时常慎独、反躬自省,真正做到了读书有恒,最终成就了具备“三有”品格的真正的道德君子。
事实上,就天资来说,曾国藩并非特别聪明之人,这一点就连他自己也承认。但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晚清功德圆满的“中兴重臣”,靠的是持之以恒的努力。中进士之前,曾氏的全部精力都用在钻研八股文上,日夜苦读只是为了功名利禄,出人头地,对儒学之大理大节,并未深加研究体味。中进士之后,到了人文渊薮的北京,目睹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大儒们的高美仪范,才意识到自身学问修养毫无根基。自惭形秽之余,遂痛下决心,弃暗向明,做真学问。从此以后,在学习上,勤奋刻苦,奋发向上,从未间断。即使是在统领湘军,全权处理攻打太平军、捻军军务,主管江南数省军政,肩负着极其繁重的任务的时候,仍然坚持利用闲暇时间读书写字。1835年参加会试之前,读的是四书五经,习的是八股时文。进士及第以后,开始广泛涉猎诗文。后又借钱买了一套二十三史,每日刻苦钻研。入翰林院后,利用种种条件,广泛涉猎,做下大量读书笔记。就这样,在库阅读以及良师益友的切磋扶持之下,他的学业取得巨大进步。可以说,在京十二年期间,曾国藩广泛阅读了涵盖经、史、子、集各个方面的大部分书籍,学问日益精进。1842年,他又为自己制定了“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读书计划,并坚持遵循不懈。晚年曾国藩身患重病,身体极度衰弱,但依然坚持不辍公务,虔心向学,精进不已。《理学宗传》数本,每天翻阅不释手。1871年二月初三,他在去世的前一天,还阅看了其中的《张子》一卷,并记了日记。这一天的日记,是他自道光十九年(1839)以来所写日记的最后一页。翌日上午,溘然长逝。曾氏一生,其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皆亲手所写或删定,洋洋数千万言,其毕生用力之勤之恒,世所罕见。
可以看到,曾国藩一生读圣贤之书,日日有恒,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持之以恒的效果是显著的。即使在他所不甚看重的舞文弄墨等“雕虫小技”方面,他也取得了不低的成就。他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在道德学问方面自然就更不待言。一部《治学论道之经》是曾氏作为清末著名理学大师的代表作,反映了其学术造诣极深。《疆场竞斗之计》军事思想内涵极丰,有过人之处。另外,在教子、养生、交友、人情世故以及政治、外交方面,他都有自己的卓识。正是因为持之以恒,他才能在伦理道德方面和他所献身的事业中,日新日日新,天天进步。而这一天天的进步,累积起来的就是一个“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