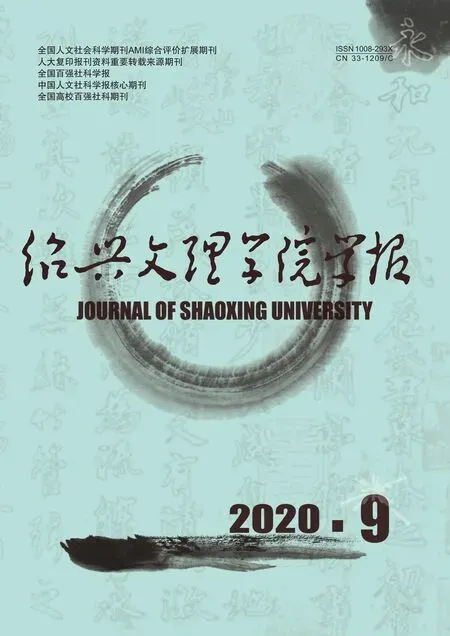神圣时间与社会秩序
——论《春秋公羊传》的时间体例与社会秩序构建
黄艺彬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市 200433)
引言
《春秋》作为儒家传世的“五经”之一,地位之高自不待言,因历代研究者众多而形成了所谓的“春秋学”。《汉书·艺文志》载“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1]1714,其中作传者五家[1]1713,传世者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家。三家在阐释《春秋》经时形成了不同的系统,皮锡瑞对此有概括:“《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谷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氏》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赡,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故三传并行不废。”[2]19要而言之,尽管《春秋》经之文本均由史事构成,但是《公羊传》的目的却在于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以求“通经致用”。换言之,《公羊传》的本质是一套具有实践性质的政治理论体系(1)这也是“公羊学”能够在汉代大兴并对实际政治产生影响的原因。[3]207-306。其中,“例”作为理论体系建构的一种方式,在《公羊传》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4]227-229,而关于“时间”之书例,在各种例之中又显得尤为重要(2)据雷戈先生统计,“《春秋》中有关纯粹时间的文字就有4273字,为全部正文的四分之一”。[5]88。
时间书例之所以重要,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理论体系的构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秩序的构建。在阐释《春秋》首条经文“元年,春,王正月”[6]5时,《公羊传》所提出的“大一统”[6]10思想,正是对秩序之追求的一种极端体现(3)尽管“大一统”在《公羊传》中仅一见,但这种思想在全传之中却是一以贯之。诸如“王者无外”“王者无敌”“先王命也”“不与致天子”“不与再致天子”等均为“大一统”思想之体现,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提出也是由此而来。[7]74-82,而社会秩序的构建和维持所依赖的一个基础,便是时间秩序。那么,《公羊传》以何种时间观念作为其构建社会秩序之基础?具有自然属性的“天文时间”或“物理时间”与人类社会秩序之间如何建立联系?这便是本文所欲探讨的问题。
一、时间的神圣性
早期中国人从日夜更替、四季轮转的自然现象中发现了某种循环时间。《尚书·尧典》记载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8]10-12,尧之后的舜也“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8]43。这便是根据日月天象的循环变化而制定时间、历法,进而以此组织社会活动。这种循环对人而言乃是一种永恒性的循环,而永恒性在相当程度上即等同于“神性”。时间因此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天文时间,而是带有神性的“神圣时间”。
时间之神性并非仅仅体现在永恒循环,还因为这种循环是“象天”的。时间、历法被认为是来自于“天”,如前文所引“钦若昊天”,《论语·尧曰》亦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9]207。“天”对早期中国人来说,并非仅仅是自然之天或者规律之天,在更多的时候,它是具有神性的“神圣之天”。考古发掘出的周代钟鼎器上的铭文亦可反映出这一点,如《大克鼎》:“克佑于皇天”;《宗周钟》:“我隹司配皇天王”[10]79;“《大盂鼎》:‘不显文王受天有(佑)大命’,……已有天佑之大命和畏天威的观念。”[11]581至于孔子所言的“三畏”,首先也是“畏天命”[9]177。这都体现出将天视为具有神性之最高主宰的观念(4)根据殷墟卜辞,尽管殷商时的最高主宰被称为“帝”或“上帝”,但也是通过天象来展示其恩威。[11]580。西周以后,人间的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与天为父子关系[11]581。正因为天具有神圣性,由天而来的时间也便继承了其神圣性。这种神圣的时间在人间则由与“天”具有血统关系的统治者“天子”所掌握。
在以“配天”(5)《召诰》:“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思文》:“克配彼天。”[11]581为政权合法性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历法的制定毫无疑问地被视为一种极其神圣的行为。或者说,掌握了时间,其实反过来也可以证明其政权之合法性。此外,对农业社会而言,时间的重要性自然无需多言。故而可以说掌握了时间,便掌握了控制社会的神圣武器。因此历法之制定与颁布均由官方所垄断,民间不得私习。《礼记》中便有如下记载:“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12]374其中之“时日”虽然不是指历法,而当是指“择吉”之类的行为。然而无法忽视的是,这与时间之神圣性密切相关。也正是因为这样,“时日”才会与“鬼神”“卜筮”之类的行为并列而言。时间的这种神圣性,在《春秋公羊传》之文本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因为《春秋公羊传》既然试图构建一种政治理论体系,必然无法回避政权合法性以及社会秩序之构建问题,进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时间的问题。
二、《春秋公羊传》中的神圣时间与权力时间
作为经名,“春秋”二字已然是一种时间之标记。并且,时间之重要性在《春秋》经之开篇即得到体现:“元年,春,王正月。”[6]5
在这里,“元年”“春”“正月”全部都代表着时间的开端。然而问题在于,这里的“正月”其实乃是夏历的十一月(6)据《史记·历书》:“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13]1503,在气象学上,则显然应属于冬天,而非春天。并非春天而记之以“春”,而且这种书写方式贯穿全书,原因何在?《公羊传》之传文对此作出如下解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何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6]6-10
何休在注解中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6]6
通过这段注解可以发现,这里的书写方式乃是一种象征:它意味着王者是受天命而为王,王者之始也就是天之始,其所颁布的正朔亦是受天命而为;天之始,在于四季则为春(7)“春者,天地开辟之端,养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时本名也。”[13]7,所以王者之正月亦即是作为四季之始的春。王者在这里实际上扮演了“天”或者“创世者”的角色,他所确立的时间体系在其效力上则被等同于神圣时间。这也正是《史记》中所说的“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成厥意”[13]1500。
《公羊传》对“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的最终解释是“大一统”,更为明显地显示出这种书写体例其实是为了体现王者确立了对天下的统治,而这种统治的确立又是以王者确立其时间体系为标志。为了便于称引,不妨将这种时间体系称之为“权力时间”,因为它是由统治者通过其权力所确立的。依据《公羊传》的解释,《春秋》经全篇均依此书例,倘若“首月无事”,则有事的“二月”或者“三月”之前也必然都加上“王”字;哪怕因“昭公出奔,国当绝,定公不得继体奉正,故讳为微辞,故不书正月”[6]544的定公元年(公元前509年),亦在“春”之后存一“王”字,这些无一不是为了强调王者的这种绝对统治权及其合法性。当然,《春秋》经中也存在一些被公羊家称为“变例”的情况,如桓公在位的十八年中有十四年在首书之月未书“王”字。尽管此处未依常例进行书写,但根据公羊家的解释,却是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之所以不书“王”,乃是由于“见桓公无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见始也。十年有王者,数之终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终也,明终始有王,桓公无之尔”[6]76。实际上乃是因为并不认可桓公为王,所谓“若桓公之行,诸侯所当诛,百姓所当叛”[6]78。
正如前文所言,权力时间体系实际上象征着天命,天命的神圣性则赋予了这套时间体系一种合法的强制性。《公羊传》对《春秋》经之文本的解释也刻意模仿具有神圣性的天文时间,反过来强调权力时间之神圣性。这在经文中主要体现在每一年都四时俱备,所谓“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6]54,哪怕终年无事,也要记上类似“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之类毫无实质性内容的文辞。恰如天文时间之必然有春夏秋冬四季,有始有终。通过这种形式,天文时间和权力时间二者交相强调,神圣之天的天文秩序和人间的社会秩序融合为一。
但是,应该看到,《公羊传》所构建的这种书写体例也仅仅止于象征层面的神圣性,而且这个象征体系是经由《公羊传》的阐发而建立起来的,并非《春秋》经本身已经具备。有学者亦注意到这种时间书写的神圣性,但是却直接认为《春秋》经乃是宗教文本,这种“系统而严密的‘天时’构架,正是其通神特质的体现”[14]28。同时,在该篇论文中,作者还认为“时间与历法是宇宙的秘密,掌握了这个秘密,就能实现与神灵的沟通,得到神灵的启示”[14]28,并进而认为古时“春秋”可以代表四时,而四时与祭祀活动有关,则“春秋”亦可以代表祭祀活动,随即认为“《春秋》可能就是关于四时祭祀的文本。《春秋》构建的时间框架,相当于搭建与神灵沟通的神秘通道,人间的信息可以从此通道传递到先祖那里,这种观念同现代穿越小说通过神秘的时空隧道可以到达另一个时空的想象有异曲同工之妙”[14]28。尽管这种权力时间具有相当的神圣性或者说宗教性,但是这种看法未免有过度阐释之嫌,原因有二。
第一,其“春秋”可以代表“祭祀”的结论乃是从两条文本中得出,其一是《诗经·鲁颂·閟》中的“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其二是《孝经》中的“春秋祭祀,以时思之”[14]28。从这两条文本中,仅能得出祭祀活动有一个统一或者说固定的时间,也就是说“春秋”在这里只是代表着某种时间节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春秋”二字和祭祀之类的字眼同时出现便得出“春秋”可以指代四时之祭祀的结论。
第二,关于《春秋》文本通神的说法则更为可疑,因为所谓“通”,便意味着和神灵进行交流,这也是作者在该文中用来和《春秋》经作对比的甲骨文所具有的典型特征。但是从《春秋》经中却只能看出其对天文时间或者说神圣时间的一种模仿,而交流的痕迹则无处可寻。
简而言之,《春秋》文本的本质不可能是该文所言的宗教文本,甚至其本身之宗教性也并不强,只是经过了《公羊传》的阐发而得到了强化。然而即使仅就《公羊传》而言,它也不过是为了构建一种政治理论体系之基础,也就是解决政权合法性以及社会秩序构建的问题。换言之,其表现形式具有宗教性,但自身之目的却并非宗教性的。
司马迁云:“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13]1503这种以神圣时间为名的权力时间一旦确立,诸侯国便要依照此时间秩序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其他诸如个人时间、天文时间在客观上仍然存在,但在社会活动之中只有王者的时间体系才是唯一合法的。除了在一年四时之书法上有其一贯之例,《春秋公羊传》还通过对《春秋》经中所载与时间相关的具体事件进行解释以强调这种“一统”的秩序,这便是文本中出现“时”或“不时”之评论的原因所在。
三、《春秋公羊传》中的时间与社会秩序
《春秋》中记载了许多不合正常秩序的事件,这类事件大致可分为自然与人事两类。其中,自然事件的记录在《公羊传》中称为“记异”。关于《春秋》所载之“异”,何休说:“异者,所以为人戒也。重异不重灾,君子所以贵教化而贱刑罚也。”[6]551言外之意,所载之事件虽然在形式上以自然现象出现,但它的出现乃是人在社会中的活动违背了既定秩序所导致。在这里,社会秩序与天文秩序,权力时间与神圣时间并非平行而不相关,相反,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亦即,通过记天文现象之异常来谴责违背既定社会秩序的行为。在《春秋》中,这种异常现象的记录有多种,“不时为异,非其地为异,太甚为异,不为害之灾亦以异书”[4]232。下面主要考察属于“不时”之“异”的一些事件。
1.《春秋·隐公三年》:“己巳,日有食之。”[6]35《公羊传》云:“何以书?记异也。”[6]35之所以属于“异”,是因为日食本当在朔日发生,而这次日食却发生在其他的日子。何休对此“异”的注解是:“先事而至者,是后卫州吁弑其君完,诸侯初僭,鲁隐系获,公子翚进谄谋。”[6]35
又分别针对日食在朔日、朔日后、朔日前这三种不同情况所对应的人事活动情况进行解释:“此象君行外强内虚,是故日月之行无迟疾,食不失正朔也。”[6]35“此象君行暴急,外见畏,故日行疾月行迟,过朔乃食,失正朔于前也。”[6]36“此象君行懦弱见陵,故日行迟月行疾,未至朔而食,失正朔于后也。”[6]36
2.《春秋·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6]62《公羊传》云:“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不时也。”[6]62此处的三月对应的乃是夏历的正月,正月而有雷电属于不正常现象。何休解曰:“此阳气大失其节,犹隐公久居位不反于桓,失其宜也。……发于九年者,阳数可以极,而不还国于桓之所致。”[6]62
3.《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6]92《公羊传》云:“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不时也。”[6]92此十月为夏历之八月,正当气象学上的夏天,夏天下雪,属异常现象。何休解曰:“此阴气大盛,兵象也。是后有郎师、龙门之战,流血尤深。”[6]92
4.《春秋·桓公十四年》:“春,正月,公会郑伯于曹。无冰。”[6]103《公羊传》云:“何以书?记异也。”[6]103此处的时间为夏历十一月,正当寒冬,寒冬而无冰,属异常现象。此外,尚有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二月、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春记“无冰”。对于桓公十四年(公元前698年)的异常,何休解曰:“无冰者,温也。此夫人淫泆,阴而阳行之所致。”[6]103
5.《春秋·僖公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公至自齐。……陨霜不杀草,李梅实。”[6]273《公羊传》云:“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不时也。”[6]273此时为夏历十月,未至寒冬而降霜,不合季节时令。何休解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记》曰:‘阴假阳威之应也。早霣霜而不杀万物,至当霣霜之时,根生之物复荣不死,斯阳假与阴威,阴威列索,故阳自霣霜而反不能杀也。’此禄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应也。”[6]273
6.《春秋·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6]613《公羊传》云:“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不时也。”[6]613对此,何休解曰:“螽者,与阴杀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当见,故为异。比年再螽者,天不能杀,地不能埋,自是之后,天下大乱,莫能相禁,宋国以亡,齐并于陈氏,晋分为六卿。”[6]613
通过以上记述,可以发现,“不时”之异象或是不合既定秩序之重大人事活动的结果,或是预先对即将出现此类事件进行警告。总之,天文秩序和人间秩序,尤其是王侯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倘若神圣时间秩序出现异常,必是人间秩序错乱之应。这里固然存在借天象规范王侯活动的目的,但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进一步强化了神圣时间与权力时间的关联,是对权力时间合法性的一种反向强化。换言之,之所以通过“异象”的方式警告王侯,正是强调王侯与“天”的对应关系。这一点在对“不时”的人事活动进行谴责时也得到了体现。
自然现象因呈现出异于往常的状态而被视为异常,在人事活动方面,诸如婚、丧、嫁、娶、祭祀等,亦有其规定之“时”,若违背则被视为“不时”之举,并因此受到谴责。试举数例:
1.《春秋·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6]36《公羊传》云:“何以不书葬?天子记崩不记葬,必其时也。诸侯记卒记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时也。”[6]36
在丧葬方面,天子或诸侯举行相关礼仪都有规定的时间,符合这个时间规定才能被称为“时”,并且天子之“时”具有绝对的优先性,诸侯之“时”必须以天子之“时”作为行动的第一准则。当诸侯有丧事时,“倘若有王、后丧事,必越绋奔丧”[15]21,因此不能按时下葬。
2.《春秋·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6]423三卜本合于礼制,按《公羊传》总结的书例可以不书。对此,徐彦在僖公三十一年(公元前629年)下面解释道:“襄七年乃在周之四月,以其不时,是以书也。”[6]266
郊祭是天子才可举行的祭天之礼,按时举行。鲁国郊祭则是天子特许,但需占卜求吉方可进行。依礼,卜吉卜三。鲁国可以于十二月下辛、正月下辛、二月下辛分别卜正月上辛、二月上辛、三月上辛,四月卜则非礼[15]271。由此可见,郊祭之类的祭祀活动均有其比较严格的时间规定,即使占卜求吉的行为符合礼制,也不可以随时举行。
3.《春秋·文公二年》:“丁丑,作僖公主。”[6]277《公羊传》云:“作僖公主,何以书?讥。何讥尔?不时也。其不时奈何?欲久丧而后不能也。”[6]278
文公为去世之僖公作神主的时间太迟,不合礼制,因此受到谴责。而服丧期亦有一定的时间长短,否则便为乱制。
4.《春秋·文公九年》:“辛丑,葬襄王。”[6]292《公羊传》云:“王者不书葬,此何以书?不及时书,过时书,我有往者则书。”[6]292-293
结合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这里乃是强调王者下葬时间有其固定之制。除此二例,尚有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十月记“天王崩”[6]324、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正月记“葬匡王”[6]326、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四月记“乙丑,天王崩。六月,书鞅如京师。葬景王”[6]513均属此例。
通过以上对自然、人事两个方面记录的考察,可以发现,《春秋公羊传》在构建社会秩序时,往往将自然秩序与人间秩序相互关联,而关联二者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时间:自然秩序有其“时”,人间秩序亦有其“时”。通过天文时间的神圣性赋予权力时间神圣性,以权力时间作为神圣时间和世俗社会时间的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统一管控。
四、结语
作为政治学说体系,《春秋公羊传》必然要构建一种统治者可控的统一秩序;作为这种秩序之主导的统治者,首要任务便是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否则便无统一的可能。“时间”这个要素能够同时服务于以上两个目的。首先,一种秩序倘若要实现统一、可控,时间必然是其基础要素,离开了时间,这种秩序便无实现之可能。其次,在合法性论证方面,由于“天”所具有的神圣性,以“配天”作为合法性论证为当时所公认。在如何配天的问题上,时间要素依然重要。因为时间的测量与天文历法的制定全部来自于“天象”,时间也就因此继承了天的神圣性而成为一种“神圣时间”。基于此,掌握时间就掌握了“天命”,统治权的合法性得到了解决,权力时间也因此而具有神圣性。由于空间上的活动也是时间中的活动,因是之故,在拥有了具有绝对强制性的权力时间的基础上,通过将不同群体、不同活动与神圣时间、权力时间相关联而对行为节奏乃至方式进行限制,使其具有明确的边界而形成分野,一种理想的社会结构于是借助时间工具在空间意义上也得以确立。统治政权因此拥有了掌控和支配整个社会生活节奏的工具,社会秩序也在时间之流中具备了完成其构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