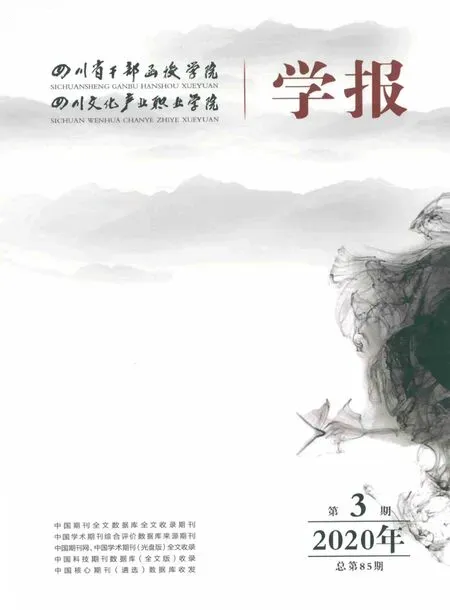中法文学作品中风尘女子形象的选择与建构
——以《卖油郎独占花魁》和《茶花女》为例
◇周怡佳◇
风尘女子,是非常特殊的女性职业群体,“风尘女子又称烟花女子、青楼女子,指的是自愿或被迫走上歌妓或艺妓道路、沦落风尘的女子,一般是命运比较坎坷、值得人同情的妓女,是对妓女的美称。”①张倓:《论“三言”中风尘女子的正面形象》,《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在中法文学的不同历史时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风尘女子这一类具有特殊性、争议性、反叛性的文学形象的选择与建构,其在文学阐释层面中拥有着独特的魅力和巨大的张力。风尘女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各自经历不同的世事,生发不同的故事,但都是男权社会中被极度他者化的角色,因此她们具有了文化视野的可比性。
本文将对中法文化背景中风尘女子社会文化境遇和风尘女子文学形象的社会意义进行比较,并以中国明代冯梦龙《醒世恒言》中“王美娘”莘瑶琴和法国19世纪著名作家小仲马《茶花女》中“茶花女”玛格丽特这两位风尘女子形象为例,论述不同文化背景中作家对风尘女子形象的选择与建构问题。
一、中法风尘女子社会文化境遇比较
(一)中国古代风尘女子:从事贱业的贱民阶层
1.男权社会中女性被逼无奈的职业选择
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男权(主要体现为父权和夫权)社会,“男尊女卑”思想代表着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为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需要,儒家礼教制定了“三从四德”,使之成为女子必须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三从四德”是 “三从”与“四德”的合称。“三从”指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红。在这样的社会语境塑造下,女性的婚姻观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性观念是从一而终、保贞守节。
为适应稳定家庭、免除男性后顾之忧的需要,儒家强调“内外有别”原则,在社会分工上凸显了严重的性别歧视。绝大多数女性被先在地剥夺了社会职业选择的自由,只能完全从属于家庭,具体负责诸如相夫教子、奉养公婆、操持家务等事项。女性作为家庭主妇,没有社会职业,没有经济收入,只能依附男性,使得女性处于卑微服从的地位,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的社会职能被单纯界定为以“夫荣妻贵”为旨归的“相夫教子”。
这就使得中国古代女性的职业化道路异常艰险和曲折,只有极少数女子在迫于无奈时才会选择自己谋生的职业道路。事实上,中国古代女子的社会职业选择范围非常狭窄,且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生产性职业,主要包括以补贴家用为目的织女、绣女等职业。在绣坊从事纺织物和绣品的生产,是典型的产业女工。(2)专业性职业,主要包括“三姑六婆”九类①元代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三最先提出“三姑六婆”这一概念,“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也。”。作为中国古代的专业职业女性群体,她们在各个历史时期遭到不同程度的污名化误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衣若兰《三姑六婆——明代妇女与社会的探索》郑重为其正名,指出她们为在宗教信仰、医疗生育与买卖中介等方面为女性提供的服务,是当时其他男性相关从业者所无法代替的②引自衣若兰,《三姑六婆——明代妇女与社会的探索》,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她们可谓是古代中国最初的专业技术女性。(3)卑贱性职业,主要指娼妓行业,包括色妓、歌舞伎或艺伎等,主要以提供色情服务、歌舞表演和才艺表演为生。这个职业是中国古代四大贱业之首③中国古代四大贱业为倡、优、皂、卒。娼:娼妓;优:从事表演类活动的人;皂:衙门里的衙役;卒:兵丁。,受歧视程度最高。在倡优皂卒四者之中,娼妓地位最为低贱,作为中国古代提供色情服务的特殊职业女性群体,她们还需承受道德家们的唾弃和攻讦。中国古代男性一方面坦然享受风尘女子的色情服务,另一方面又义正言辞批评她们水性杨花,不守妇道。
风尘女子从事娼妓贱业,往往并非自愿,而是被逼无奈或生计所迫。妓女按服务场所可细分为宫妓、营妓(军妓)、官妓、家妓、民妓。其中,宫妓、营妓(军妓)和官妓三类多因父祖或丈夫犯重罪而被牵连而被罚入宫中、教坊司或军中充当女伎,是罪罚强迫。家妓、民妓两类则多因家道中落或家中贫困自愿或被迫卖身为妓,是生计所迫。总之,风尘女子是中国古代男权社会中女性无可奈何之下的一种被动职业选择,如蒲松龄《聊斋志异·鸦头》妓女鸦头所言“妾委风尘,实非所愿”,自述其沦落风尘,实在是迫不得已,有难言苦衷。在当时的三类女性职业中,风尘女子最受轻贱。
2.贱籍制度下风尘女子群体的“落籍从良”追求
中国古代风尘女子的产生由来已久。刘向《战国策》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语·齐语》记载:“齐有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通国用,管仲相桓公时,立此法,以富国。”管仲通过向妓女征税确立了妓女的合法地位,这应是史书记载的最早期的官办妓院。这说明早在战国时期妓女就已经是合法职业。但合法化的身份带来的是歧视性待遇。“古代中国为身份社会,举凡政治权力、生活待遇都与身份相关。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良贱身份作为定罪量刑的要件。在户籍制度上,贱民阶层专门立有贱籍。列入贱籍即被剥夺参政权利,最为典型的是不能参加科举、不能为官。”①李若晖:《贱籍与身份社会》,《光明日报》2016年8月1日。贱籍之人社会地位极低,且世代传承,不得随意变更,倍受社会歧视和压制。贱籍主要包括奴籍(奴婢)、乐籍(娼优)和军籍(皂卒)。娼妓群体和乐户都入乐籍,风尘女子就成了乐籍女子。
中国古代普通女性的人伦关系基于其与家庭中男性的关系,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依附关系确定了女性的身份,她们作为男性的女儿、妻子和母亲而获得正统社会的身份认同。但无夫无子的风尘女子们飘零于家庭之外,也就被排除在人伦秩序之外,成为另类的、边缘的、他者的存在。风尘女子想要重新获取正统社会的认同,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归家庭,通过某个男性来重新确定其身份。因此,身处贱籍的风尘女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摆脱贱籍身份,其理想的出路就是择一“良人”为其赎身②良人,古代女子对丈夫的称谓之一,亦指出身为“良家子”之人,在汉代,良家子指从军不在七科谪内者或非医、巫、商贾、百工之子女。后世泛指非贱籍出身、家世清白的子女。,然后嫁与其为妻妾,从而实现“落籍从良”,消除或脱出“乐籍”,加入良籍,最终实现社会阶层和社会身份的改变。“落籍从良”也因此成为风尘女子皮肉生涯中望梅止渴的精神目标,围绕“落籍从良”而起的种种引诱、试探、考验就成为风尘女子日常生活的最核心内容。但由于现实利益、家族观念等因素影响,这一追求在现实中极少能够成功。唐代名妓鱼玄机《赠邻女》“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之句就反映了她才貌双全却无人可将芳心托付的深切遗憾。
正因如此,“落籍从良”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妓女题材作品的重要议题。在文学虚构中,文人笔下的风尘女子往往能因自己的才情、才能、品性得觅良人、脱籍从良,如《李娃传》中的李娃就成功收获圆满爱情且获封汧国夫人,这多是出于对现实的补偿心理。
(二)19世纪法国风尘女子:淫贱和堕落者
19世纪的法国,尤其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性交易尤为普遍。“在现代化的巴黎都市中,妓女总计约12万之多(根据摄影家马克西姆·杜坎1872年估算的数字),这使巴黎成为 19世纪下半叶当之无愧的娱乐之都和寻求性欢愉的向往之地。在这个时代,对于‘妓女’这一职业,存在很多用来指称的特定俚语,足以显示当时妓女的多样化:‘贱妇’‘贪婪’‘淫荡的维纳斯’‘鱿鱼’‘夜宵’‘柏油沥青’‘游街的人’……每类妓女皆有其胜人之处,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引诱‘顾客’。”③吴晶莹编译:《颓废与欲望——19世纪法国艺术中的妓女形象》,《世界艺术》2016年第1期。这个风尘女子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活跃于上层社会的交际花。“妓女也有等级之分,其中社会地位最高的便是所谓的‘高级妓女’(courtesan)。她们虽然身居社会底层,却借助外表维持着一些来自社会上层的顾客。这其中包括富有的银行家、作曲家以及知识阶层,由此,她们也顺势成为巴黎社会的交际花,对于生活讲求优雅,对于艺术别有激情。”①吴晶莹编译:《颓废与欲望——19世纪法国艺术中的妓女形象》,《世界艺术》2016年第1期。许多交际花通过上流社会的文学沙龙结识各方人士,并往往在与文艺界的接触之后成为文艺创作的原型。“阿波尼娜·萨巴蒂埃拥有一个著名的文学沙龙,她是波德莱尔创作《恶之花》的重要原型之一,法国唯美主义文学家泰奥菲尔·戈蒂耶还曾为她写过一封露骨的情书。同样,亨利·热尔韦的作品则以女同性恋妓女瓦尔黛丝·德拉比涅为创作灵感。当时她是众多艺术家极为热衷的交往对象,也是左拉小说《娜娜》的灵感来源。”②吴晶莹编译:《颓废与欲望——19世纪法国艺术中的妓女形象》,《世界艺术》2016年第1期。
另一类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妓女。劳尔.阿德勒在其社会史著作《巴黎青楼:法国青楼女子的日常生活》中描绘了她们的形象,“她们等待天黑。有的蹲在屋子里,打扮成婴儿模样或者披着透明的薄绸,有的站在红色门牌号码灯照亮的百叶窗后面,或者埋在客厅的沙发里,她们耐心等候,夜晚将是长的,蹬着高帮短靴,露出开口很低的脸褡,涂红了嘴唇,描黑了眼圈,她们来到街上,迈着既淫荡又快乐的步子,走到市中心。她们寻找亮点,热闹的咖啡馆,正在营业的餐馆。她们略微提起裙子,抛掷媚眼。偶尔她们叫住行人,用娇滴滴的声音谈起金钱和爱情。”③〔法〕劳尔·阿德勒:《巴黎青楼》,施康强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1页,第200页。在书的最后,他写道,“妓女就其定义而言就是没有故事的,为什么要尝试让她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呢?我企图做的,无非是为她们的故事的片段做一点贡献。”④〔法〕劳尔·阿德勒:《巴黎青楼》,施康强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1页,第200页。
这两类妓女的现实处境看似天堑之别,却同属社会最底层,同样遭受歧视,“在世界各民族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把娼妓视为淫贱和堕落者的看法几乎是惊人的一致。”⑤聂绀弩:《聂绀弩杂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316页。
二、中法风尘女子文学形象的社会意义
(一)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风尘女子形象
中国古代妓女大致可分为色妓与艺妓两类。前者主要靠出卖色相为生,后者则主要从事艺术表演活动。前者被视为纯粹的性交易商品,几乎不见诸文学作品。后者则因色艺双全、风流雅致而成为古代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
艺妓因为家中男子的宦海沉浮、家道中落或生计艰难等种种原因而被迫走出传统女子的后宅生活,进入到男性公众视野,成为一定意义上的社会公众人物。相比古代社会中其他女性职业如织女、绣女及三姑六婆而言,风尘女子,特别是其中的当红人物,社会化程度相对较高,在上流社会抛头露面的机会较多,往往是某些圈子的公众人物,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她们中的一些人大多本来已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才艺修养,且妓院经营者为提高其身价,也愿意对其在声色才艺方面进行大力培养,反而迫使她们挣脱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庸常束缚,有机会成长为能歌善舞、能诗善画、才华出众、色艺双全的一代名妓。如名列唐代四大女诗人之列的薛涛和鱼玄机、宋代名妓李师师、清代名妓陈圆圆等。她们擅长吹弹歌舞、琴棋书画之类的技艺就是她们的职场竞争力所在。她们本人及相关文人的诗文书画作品均能大大炒高她们的身价,如以一曲《金缕衣》名世的杜秋娘。
这些集美貌和才华于一身的艺妓兼具如花容颜、风流才情与高洁情怀,最得达官贵人和文人名士的欢心,最能满足他们“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的男性情怀,也因此最受古代文人青睐。汉代《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中出现的“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字句;南宋时期徐陵所编诗歌总集《玉台新咏》和北宋郭茂倩所编著的乐府歌辞集也出现对风尘女子只言片语的记载,但尚无对风尘女子形象的描绘和塑造;而在之后的唐传奇、宋词、明清小说中,风尘女子形象进一步丰满鲜活起来。风尘女子与男性的交往和情感纠葛衍生了诸多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前者如柳如是与钱谦益的忘年恋情,后者如梁红玉与韩世忠的抗金故事。前者可参考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后者可见南宋以来以韩梁事迹为诉说对象的众多文学作品。这些故事演绎成的通俗文学作品,因为娱乐性而广受市民欢迎,其中的风尘女子形象也广为人知。
总体而言,各朝代对风尘女子形象的塑造不仅描绘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风尘女子群体生存状态,也反映了各个时代女性解放的演进之路。如在“从良”问题的选择上,唐传奇《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和《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尚会对现实妥协,明代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中的杜十娘却已经有了为捍卫爱情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不屈意志,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二)19世纪法国文学中的风尘女子形象
法国奥赛博物馆曾举行过一场特殊的展览 “盛衰记:1850-1910年间的妓女形象”(Splendor and Misery: Images of Prostitution 1850-1910)。该展览首次向公众展示了1850-1910年间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所呈现的19世纪的“巴黎妓女”社会群像。风尘女子题材的巨大魅力可见一斑。该展览名称取自巴尔扎克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交际花盛衰记》(The Splendors and Miseries of Courtesans,1838-1847)。无独有偶,在19世纪的法国文学作品中,风尘女子的形象也被屡屡呈现。
在此之前,法国文学中少见风尘女子形象。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前后,期间法国文学的主人公一直是男性为主:文学作品浓墨重彩、大肆描绘的对象是英雄、骑士、人文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等法兰西民族精神的代表。而19世纪法国文学的理想均源自对当代社会现实的关注:浪漫主义要求关注当下而非古代,自然主义要求呈现细节的真实,现实主义则强调记录当代社会现实并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风尘女子作为社会底层的另类形象,集中了最多类型和最大程度地压迫,从而吸引了19世纪法国作家较多的关注和书写。
总体而言,19世纪法国文学集中呈现了两类妓女形象:一类是活跃于上层社会的交际花如艾丝苔(巴尔扎克《交际花盛衰记》)、娜娜(左拉《娜娜》)和玛格丽特(小仲马《茶花女》);另一类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妓女,如芳汀(雨果《悲惨世界》)、爱丽莎(龚古尔兄弟《妓女爱丽莎》)和羊脂球(莫泊桑《羊脂球》)。
(三)风尘女子文学形象的社会意义
1.身份与性格反差
概观中外文学,诸多文本中显示的风尘女子形象并不与传统思维里那种低贱、下流、无耻的形象挂钩,“妓女”的社会身份往往与其文学形象形成断裂式反差,割裂了常识,产生了巨大的张力。在中外作家的笔下,风尘女子极具人格魅力。她们美丽娇艳、知书达理、才华横溢、心地善良,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嬉笑怒骂都源自家常,与常人无异,甚至在摸爬滚打中,形成了更为高尚的情操。
作家在对人物形象进行选择建构时企图传达的是讥讽、冷眼、含蓄的控诉,是无声的质问。现实生活都化为虚无,主流价值皆为谬误,反而从鄙俗的东西中寻找安慰。
2.身份与命运冲突
“妓女”的身份,本就是施加在社会群体上的“有色眼镜”,根深蒂固地附带着社会层面取向的是非判断与意义辨定。“在她们身上,肉体损耗了灵魂,感官了烧毁了心,放荡麻木了情感。别人对她们讲的话,她们早已熟知,别人使用的手段,她们全领教过,就是被她们激发出来的爱情,也已经被她们出卖了。”①〔法〕小仲马:《茶花女》,李玉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73页。这是对她们这一群体的惯常评价,人们的成见,是隔开风尘女子与其向往的生活的高墙。“宿命论”于她们而言是可笑又可怕的老生常谈,意味着人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无力摆脱命运的捉弄。
尼布尔《人的本性和命运》中阐释了基督教的人性观,灵和肉的二元,人的存在是在灵肉之间的平衡状态。人最容易陷入两种罪恶:骄傲之罪,即认为自己可以趋向灵的存在;情欲之罪,即人忘却自己,耽于肉体感官的享受。风尘女子就是这样灵与肉间矛盾的存在,作家往往把她们塑造成交际花与纯洁多情处女的结合体,从而她们人物形象演变为西西弗斯式的英雄。
3.环境小说的色彩
小说作品中风尘女子往往是作为“花魁”存在,作为泄欲的工具和赚取钱财的傀儡,处在灯红酒绿的风口浪尖,总与上流社会、王公贵族周旋。她们的命运走向与上层虚伪社会紧密相连,中外作品在对风尘女子的刻画描写,全然就是上流社会的风俗画卷,将纸醉金迷展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这样的文明使人们产生了欲念、恶习与虚荣心,容易上瘾,轻易戒不掉。而正是在这特定环境中引发的内在冲突,决定着风尘女子的全部命运走向。勒内基拉尔《流浪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提出“三角欲望”,现实中的欲望不直接,需要介体转折欲望。风尘女子是肮脏欲望的介体。上层对情欲无休止的渴求、对权力的掌握,风尘女子在其中承担了某种符号意义,作为一种象征,面对不合时宜的迷狂、匮乏的信仰与拜物教、主体的分裂,她们注定要与黑暗社会一起沉沦崩溃。
三、个案分析:莘瑶琴与玛格丽特的形象建构
《茶花女》是法国作家小仲马的代表作。这一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青年人与巴黎上流社会一位交际花曲折凄婉的爱情故事。而同是描绘名妓爱情的明代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却洋溢着喜剧色彩。本文将比较分析《茶花女》和《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名妓玛格丽特与莘瑶琴的形象,以探究不同风尘女子形象的选择与建构。
(一)莘瑶琴与玛格丽特的不同选择:抗争或屈服
同为描绘名妓爱情追求的小说,《茶花女》和《卖油郎独占花魁》的结局却大相径庭。《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是牺牲成全、黯然离开、凄苦离世,《卖油郎独占花魁》莘瑶琴却是精心策划、如愿以偿、终成眷属。选择的不同决定了结局的差异:意料之中的悲剧和脆弱的圆满。下面是依据风尘女子的特殊身份对其结局进行分析推敲。
1.玛格丽特:意料之中的悲剧
玛格丽特的悲剧不是其个人偶然的悲剧,是社会、时代的悲剧,是对社会认可的控诉。等级制及其衍生各种扭曲的价值观,这种东西让人变形。而同时,单纯用社会悲剧来解释不够,是人性的悲剧,基于人性纠缠于自然与自我的悲剧。
首先,这是性格悲剧:玛格丽特善良、柔弱、顺从而富有牺牲精神,这通常预示着她浪漫的幻想与追求多流于妥协;其次,这是社会悲剧:社会习俗与不可撼动的“贞节观”深深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个人,无论是阿尔芒的父亲抑或是玛格丽特本人都认同了风尘女子的卑贱,所以阿尔芒的父亲的恳请能够得到玛格丽特的配合;再次,这是命运悲剧:玛格丽特在天命思想与偶然因素间进行的剧烈思想斗争,最终向社会主流价值判断妥协,选择了黯然分手;最后,这更是生命悲剧:人的正常本能和欲望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悲惨结局。
玛格丽特爱慕的阿尔芒是个纨绔子弟,冲动任性、做事不计后果。他的不孝顺、不理智是将自己爱情推向矛盾高潮的直接原因。勒德戈尔蒂埃说:“同样的无知,同样的朝三暮四,同样的缺乏个人反抗,这使得他们听命于外界环境的暗示,缺乏来自内心的暗示。”总之,让玛格丽特毁灭的不仅仅是欲望,其自身的精神匮乏和社会道德绑架也是重要推手,而阿尔芒的不可靠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将玛格丽特推上绝路。
悲剧最终就会指向失去意义、暗无天日地继续沉沦和死亡这两种结局,无法保障生命的价值,那么人就应该自杀,如同加缪谈到的“哲学自杀”。以上两者结局,死亡显得更为幸运,通过死亡寻求自我救赎,阿尔芒在人去楼空的大宅中,意识到玛格丽特的“死亡已经净化了这个富丽而淫秽的场所的空气”。生活是一种过渡,向死亡的过渡。对人生意义最大的怀疑,只有死亡才能深刻地提出生命的意义问题,也只有死亡,才能使她们得以争取到世俗以外的价值,得以反抗压迫。在这场爱情博弈中,玛格丽特凄苦离世,“她将在祭坛上为资产者的体面献身。”她生前考究的生活越是闹得满城风雨,她死后也就越是无声无息。她就像某些星辰,陨落时和初升时一样暗淡无光。
2.脆弱的圆满
风尘女子的故事少有善终,中国古代文学讲述秦楼楚馆女性的作品层出不穷,其中或多或少也有大团圆的结局,而故事往往带有传奇的色彩,逻辑上禁不得推敲,更有甚者将主人公定为魑魅魍魉,才使其得以成功游离于传统礼制的边缘。
《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秦莘二人终成眷属的圆满结局并不偶然,是莘瑶琴精心选择和谋划的必然结果:莘瑶琴在遭受凌辱之后,放弃追求达官贵人翩翩公子,而选择了来自下层阶级且其貌不扬的卖油郎秦重。这个选择保证了秦重不会鄙夷其身份地位。作为一个卖油郎,是一个小本经营、挑担走街的商贩,他的为人无可挑剔,是个人尽皆知的老实好人。他经济状况窘迫,社会地位较低且才貌欠佳,并非白马王子,看似并非良配,但他对莘瑶琴的追求是一个男子对所恋女子的单纯而热烈的追求,他并不把莘瑶琴看作是性交易商品、玩物和男权附属品,而是当作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来尊重。这正是其貌不扬的他能打动莘瑶琴,使她重新相信爱情的真正原因。而莘瑶琴则维系着传统美德与从良的决心。鸨儿刘四妈评风尘女子从良行为:“有个真从良,有个假从良,有个苦从良,有个乐从良,有个趁好的从良,有个没奈何从良,有个了从良,有个不了的从良,”王美娘(莘瑶琴)即是“真从良”“乐从良”“趁好的从良”“了从良”①冯梦龙:《醒世恒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7页。,她省吃俭用,并不奢侈放纵,早早存够了赎身所需花销,能够不为外在因素而迷乱,反而清醒地认识到秦重那极为难得的人品,“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且知情识趣,隐恶扬善,千百种难遇此一人。”①冯梦龙:《醒世恒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2页。莘瑶琴的精心策划、秦重的全力配合,加之并无王公贵族的死缠烂打、老鸨的坑蒙拐骗等令人唏嘘的情节,故事在机缘巧合下拼凑出了令人艳羡的结局。
3. 小结:性别话语与男权社会中的他者建构
比对玛格丽特和莘瑶琴的不同结局,有两个构成要素非常引人注目。第一,阿尔芒是上流社会的公子哥,而秦重只是普通百姓卖油郎。故事最终还是对阶层做出了妥协,安排女主人公不是向上索求,而只是向下寻觅。第二,区别于阿尔芒的避重就轻,懦弱无能,秦重勤劳能干善良踏实,男性主人公的品行变得至关重要。“通过对玛格丽特风尘妓女哀怨命运的分析,说明在男权社会里,被置于‘第二性’的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而存在。”②苏屹峰:《论《茶花女》悲剧的成因》,《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9期。以上两个因素反映了女性获得善终与否,决定权最后竟然还是在男性手里。喜剧结局的获得在于男性的妥协而非女性的追求。两位作者建构风尘女子这一形象,都不约而同以男性为基点,颂赞其人格的高尚美好并非目的,而只是工具,作者写作活动中选择和建构风尘女子形象并非是为其声援,只是各取所需曲线救国罢了。
(二)读者接受角度下看风尘女子形象的塑造
《卖油郎独占花魁》出自冯梦龙“三言”中的《醒世恒言》。“三言”拥有庞大的读者群。“这并非认为小说的读者只是以生员为主的科举考生,另一方面,如同矶部氏发表的资料所示,地位相当高的人也是其读者;可以肯定当时冯梦龙小说的读者包括以生员为主的科举考生和商贾这两个层面的人。”③大木康:《关于明末白话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吴悦摘译,《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2期。“三言”收录的作品来源之繁、覆盖之广、内容之杂,同时也都经由了冯梦龙的主观过滤,是自然主义的人文理想与传统儒家双重解构与建构的博弈。 “三言”在建构明代风尘女子形象时,对她们的美貌和才艺只是简单提及,重点写她们身上的高贵品质,挖掘她们的独特内涵,在重建风尘女子形象的同时不忘加入道德伦理的诉求。因此《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喜剧色彩更多了些“劝人”意味。劝人向善,劝人忠厚老实,平添了家国情怀。
和《醒世恒言》相比,《茶花女》在创作动机上就有很大不同。“小仲马为自己的‘纯真爱情’辩白,对父亲说‘我希望一举两得,即同时拯救爱情与伦理。既赎了罪,也洗涤自身的污秽,任何权威都不可能指责我选择了一个婊子当小说的女主人公。有朝一日,倘若我申请进法兰西文学院,他们也无法说我颂扬过淫荡。’”④〔法〕波罗·德尔贝什《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沈大力、董纯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第1页。由此可见,小仲马的《茶花女》为他自己私心所写的。当时通俗小说已经逐渐流行,小仲马写作的目的是受到关注。妓女题材更具争议性,悲剧更具冲击力,更能让读者记住他的故事,记住他小仲马这个人。因此,无所谓结局悲喜。而实质上,根据他与玛丽·杜普莱西的真人真事,也注定了《茶花女》的悲剧。小仲马以为自己在以现实主义的身份批判,可是社会批判的基本形式应该是讽刺而不是悲剧。他就像小丑,努力扮出旁人喜欢的样子,甚至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而实际上,这个题材新颖又刺激,《茶花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小仲马以伦理的权威自居,高举社会道德这杆大旗,用忏悔的语气,把这爱情和自己的野心神圣化。
结 语
风尘女子聚合了种种极端矛盾特质: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才艺修养极致高超、妆容衣着极尽精美、工作环境极度奢华,等等。而她们最大的特殊性在于,“不论是官妓、家妓和私妓,其地位存在着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即集卑贱与优裕于一身。”①李剑亮:《唐宋词与唐代歌妓制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她们社会地位低贱尤甚于奴仆,却与达官贵人密切相交;她们姿容秀丽,最能讨男性欢心而又备受男性鄙视;她们才华出众,最得文人追捧却又屡遭文人抨击。这些特质使她们区别于当时的普通女性,同时也使她们饱受非议,成为道德卫士的唾弃目标。这种极端反差的处境对她们的心理、情感和婚恋均产生特殊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同时也是女性失落于社会家庭和泯灭自我的历史。尤其是作为私有制和男权中心的产物——风尘女子,她们在这个维系生存的社会里摸索挣扎,她们的整个生命与奢靡的环境、放纵的男性融为一体,其生存方式、内心情感、爱情婚恋及命运结局有许多特异之处,所以风尘女子题材一直都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母题。”②林梦如:《“三言”“二拍”之风尘女子形象研究》,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31页。这一论断同样适合于19世纪法国的风尘女子文学形象。
风尘女子在泥淖里,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她们的卑微社会地位与独特人格魅力及高尚品行间形成巨大反差。她们在遭遇了最彻底的情感欺骗与剥夺后,还依然怀有对幸福的期许;在遭受了最沉重的社会伦理压迫后,还愿意牺牲、隐忍与成全。正是这种弱者的高贵、卑微的光辉、黑暗中的光明赋予了风尘女子独特品格,她们的形象也因此成为了大量文学作品的书写对象,其在文学阐释层面产生着独特的魅力和巨大的张力。中法文学均选择用这样最黑暗的身份来进行最神圣的话语表达。风尘女子形象的选择与建构背后,预示着肆虐的、残酷的恶旁往往也有孱弱的良善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