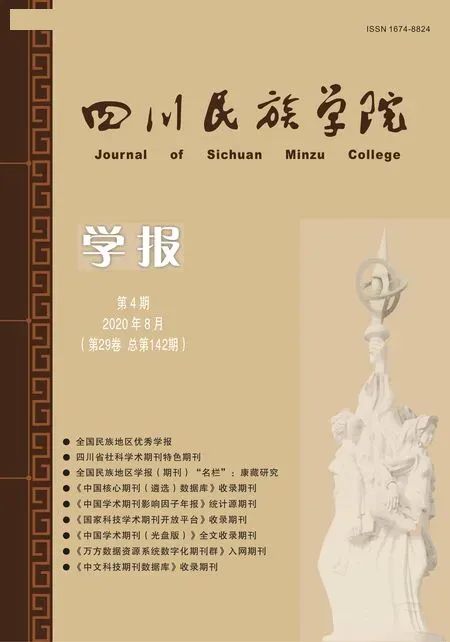大理地区民族手工技艺传承现状及问题初探
隋 鑫
(大理大学,云南 大理 671003)
传统民族手工艺是民族手工业发展的保障性基础,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大理地区有丰富的民族民间传统手工技艺,这些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价值观念、思想智慧以及实践经验,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时代发展,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承链中断、现有企业生产规模单一等问题。因此,振兴开发传统民族手工业,培育弘扬工匠精神,焕发传统民族手工艺活力对传统手工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大理地区民族手工技艺传承方式、存在问题以及创造性继承的思考。
一、大理地区民族手工技艺传承方式
在保护传统技艺时应该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是传承人,没有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随之消失,即所谓‘人亡艺绝’。”[1]文化的传承离不开一定的传承方式和传承场[2],民族手工技艺的传承可分为四种,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型传承;二是师徒型传承;三是培训型传承;四是“以厂办班”的工厂型传承。
(一)家族型传承
家族传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单位为基础,对传统手工技艺进行世代传授。我国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以家族为核心的传承模式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条“传承链”代代相传从未间断,为社会留下了宝贵的文化价值和精神财富。
家族传承中,传承人更愿意将自己的“独门技艺”传授给直系血脉。土陶在中国已有6000年历史,祥云县非遗传承人于菊芬在八岁时就开始跟父亲学习制陶手艺,她表示:“儿子是在七岁时开始学习制陶手艺的,孙女就更早了,在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和我学习了。”(1)调查资料。时间:2019年4月19日,地点:三月街,对象:于菊芬(女,汉族,65岁,省级土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凤羽石砚传至张跃堂已有八代传承历史,可考证到200多年以前的家族手工技艺传承,是很地道的祖传手艺。调查中报告人张跃堂认为石砚不光是技艺传承,更主要是形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他鼓励儿子在大学期间专门修习艺术设计专业, 更好地将石砚技艺创新发展(2)调查资料。时间:2019年5月19日,地点:洱源县凤羽镇,对象:张跃堂(男,汉族,42岁,州级石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手工艺世家的家族式传承,完整保留了“祖传”这一家族财富,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及传承特点。进行家族式代际纵向传播,可以很好保留传统手工技艺的完整性。
(二)师徒型传承
“老艺人的传统保守意识减弱,为了流动加工过程中的互相照应,开始尝试不断招收新徒弟。”[3]由于家族式传承无法满足生产需要,招收徒弟既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又能带来经济效益。
“小锤敲过一千年,还要再敲一千年”彰显了鹤庆县银器锻造技艺的发展趋势。杨标介绍:“我17岁开始到西藏拉萨的布寺跟我师父寸锡魁学习制作银器手艺,三年出师,20岁时在拉萨开店,开始带自己的徒弟,至今为止已有徒弟16个,在招收徒弟的时候主要看重人品。 ”(3)调查资料。时间:2018年12月31日,地点:鹤庆县新华村,对象:杨标(男,汉族,41岁,藏式银器店老板)。
剑川黑陶与祥云土陶的不同之处在于色泽黑亮。在剑川,最为著名的黑陶手工艺传承人是董月畅,作为董老师的第三代弟子李浩告诉笔者:“董老师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和他姑爹学习制陶手艺,后传授给他的儿子董志明和两个徒弟,董志明现已招收3个徒弟,在招收徒弟的时候主要看我们的天分。 ”(4)调查资料。时间:2019年4月20日,地点:三月街,对象:李浩(男,白族,21岁,董志明徒弟)。
师傅在传授徒弟技艺的同时不仅要考虑徒弟的人品,也很看重徒弟学习技艺的天姿和悟性。手工技艺需要长期的学习,师傅的言传身教在很多方面都会对徒弟产生影响,徒弟与师傅在长时间相处后彼此更加信任亲如一家。
(三)培训型传承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脆弱性,它的传承需要特定的时间和空间。”[4]341政府通过组织开展培训,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剑川县政府通过培训机构组织起手工艺培训体验班。刘丽湖表示:“我每年都带培训班,县政府组织的培训机构。一般20天为一期,六十到七十人组成一班,来参加培训班学习布扎技艺的人很多,他们第一期来,第二期也来。 ”(5)调查资料。时间:2019年4月20日,地点:三月街,对象:刘丽湖(女,白族,58岁,省级布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在大理地区,政府部门积极组织开设培训体验班的同时,倡导非遗传承人向学生讲授非遗文化与手工技艺,让更多学生了解非遗走近非遗,对传统民族手工技艺进行有效保护。董志明在传统制陶方式的基础上开设了黑陶传习体验班,他的徒弟李浩介绍:“我们开设黑陶传习体验班主要方便各大高校学生来体验黑陶制作过程,一般采用边体验边讲构图、指导操作、带走作品的方式,让大学生了解黑陶文化。 ”(6)调查资料。时间:2019年4月20日,地点:三月街,对象:李浩(男,白族,21岁,董志明徒弟)。
(四)工厂型传承
“民族文化发展往往是民族经济发展的先导,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是在独特的社会历史发展中积累、传承下来的。”[4]559工厂型传承模式以企业为基础,以就业为导向,有效推动了地区产业发展。
木雕是剑川县的支柱性产业,剑川民族木器厂以“以厂办班”的形式,培育出大批手工艺人。张树林表示:“我接触木雕有30年,当时在民族木器厂,在里面边做边学。现在带的徒弟有二百人左右了,我们成立了自己的一个加工厂,以‘以厂办班’的形式继续培训。”(7)调查资料。时间:2019年4月20日,地点:三月街,对象:张树林(男,白族,49岁,省级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以厂办班”的形式不仅在传承方式上有所创新,也带动了当地就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传承载体的不同,传承方式不同,每种遗产的传承模式都会有很大差别。”[5]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核心在于传承人,无论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传承,还是传统师徒制,或是政府组织的培训班,民间艺人开设工厂,这些传承方式都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二、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传承生产困境
民族传统手工艺以文化产品的形式表现于产业中,若“传承链”出现衔接问题,传统手工技艺就会面临失传、断代危机。如此循环往复,民族传统手工技艺的活力将日渐消逝,民族传统产业将面临生存与发展困境。
(一)传承结构失调
家族式传承技不外传。因传统观念制约,拥有高超技艺的老艺人普遍年龄偏大,守旧观念致使家族式传承中有部分老艺人不愿将自己的“独门绝技”传授给外人。若家族式传承断代,宝贵的非遗文化将被带入黄土。因此,解决好老艺人的技艺传承问题是关键。
师徒制模式缺乏理论指导。传统学徒制表现为“师傅教什么,徒弟学什么”,传授以小范围圈内形式进行,耗时长,徒弟缺少创新能力。加之自然环境条件受限,地区封闭性较强,阻断了与其他地区手工艺人交流的学习,制作产品易形成固化思维。师傅传授方式大多以“口授相传”实践指导为主,徒弟只能获得动手能力,缺乏专业理论知识。
青年一代缺乏传承意识。“由于手工艺学艺时间长、收入不稳定等缺点,年青人望而却步。”[6]他们更侧重于时间短、收益高的工作,不愿意耗费时间学习手工技艺,致使许多老艺人手中的“接力棒”传不下去。将这些文化传承下去,与青年一代紧密衔接是关键。如何让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吸引年轻人,让他们了解并喜欢传统技艺是当前手工技艺传承亟须解决的难题。
(二)生产规模小
生产分布散。小规模生产加工分布散,缺少核心竞争优势,难以形成产业化发展。但扩大生产规模并不意味着盲目追求产销量,在注重产品数量的同时应保留产品的内在神韵。因此,如何在品质与产量之间取得平衡是手工业规模化发展的重点。
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家庭手工艺作坊的弱点在于产量低,制作产品耗时长,价格相对昂贵,难以适应普通消费者对于中端产品的需求。民间艺人手中缺乏资金无法扩大生产,导致出产速度慢,在市场竞争中不具备优势。
三、民族传统手工技艺的创造性继承
大理地区的传统手工技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挖掘才有了如今的规模,如何将前人积累的财富传承下去,促进其产业化发展值得关注。
(一)培养青年的传承意识
传统文化经百年积淀传承至今,凝结着各民族经验智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传统手工技艺展现了民间艺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正是青年一代所需要的精神品质。要培养青年的民族文化自觉,引导青年更多地关注传统文化,鼓励青年学习了解传统手工艺文化的核心理念,增强青年学习继承传统手工技艺的自觉性。
(二)创新传承方式
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主体是传承人,传承人是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者。传统家族式传承中,传承人更愿将自己的祖传绝技传授给家族中的男性,女性甚至无法获得其中核心部分。手工技艺要以活态方式传承,首先传承人应树立正确的传承观,解决传承人思想保守、传承断层等问题。其次“口授相传”的授艺方式因缺少系统理论讲述章法,导致部分技艺遗漏。将传统技艺与高校课程衔接,与非遗传承人达成合作关系,让传统手工技艺走出作坊可更好地传承和创新民族手工技艺。
(三)以销促产扩大规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经济利益是文化产业化追求的目标[7]。 民族手工技艺传承人在肩负传承文化的责任的同时应利用新媒体平台创新产业机制,扩大生产规模,适应产业发展需求。可以通过电商平台增加销量。要以网络平台为桥梁,以文化销售为亮点,让产品走进市场,走近消费者。鹤庆县月辉银器利用当地比较成功的电商平台,通过网络展示产品,促使客户与工厂达成了合作。
(四)以创新促发展
手工艺产品打造不能思维固化。传承、创新、发展,重点应在于突出地域优秀传统文化,突出产品的手工特色,在制作过程中融入新材料、新技法,扭转手工业产品单一的困局。要着力培养手工艺人的创新意识,引导手工技艺产业良性循环发展,促进手工技艺传承。
结 语
“乡村振兴关乎到中国的未来发展如何找到一个文化和经济新的增长点的问题”[8],手工技艺传承发展应融入乡村振兴这一重大战略,形成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产业。大理地区有着种类繁多的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手工技艺是具有文化活力的,它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在于创新,在于发展。如何更好地促进其在守护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是我们应着重思考和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