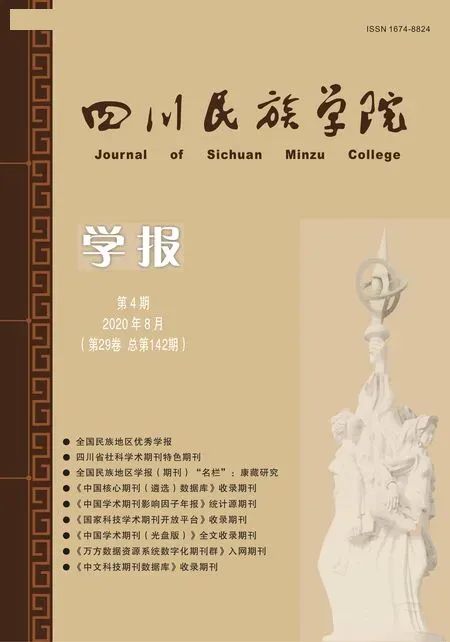藏学翻译风雨路
——访涉藏资深翻译家向红笳教授
谭益兰
(西藏大学, 西藏 拉萨 850000)
向红笳教授是国内著名资深涉藏翻译家。30多年来,一直在藏学翻译领域深耕精进,翻译著作等身。翻译出版的著作有:《闯入世界屋脊的人》《西藏探险》《刺刀指向拉萨》(合译)《西藏考古》《西藏美术史》(合译)《喜马拉雅的人与神》《雍和宫——北京藏传佛教寺院文化探究》《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西藏的睡梦瑜伽》(合译)和《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等多部藏学名著。还翻译了《珍宝——历代中央政府册封达赖班禅史料文物、历世达赖班禅敬献中央政府礼品精粹》《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西藏文化大图集》《历史的见证》《世界屋脊的女人》《西藏面具艺术》《西藏民间艺术珍藏》《十一世班禅确吉杰布》和《中国古代观音菩萨——佛教慈悲女神》等十余种图册和画册。此外,还编纂了《汉英·英汉藏学翻译词典》《藏学专业英语精读教程》《汉英·英汉藏学词汇》等专业词典和教材,为藏学研究、翻译、教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笔者对其进行了学术专访。
一、成长之路
笔者:首先想请您谈谈您的成长和成才经历。
向红笳: 1946年,我出生在湖南湘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土家族,不到一岁跟着父母来到了北京。父母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父亲萧离(笔名)是老北大历史系学生,母亲萧凤(笔名)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毕业。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做过《大公报》副总编辑、北京组长,母亲是《大公报》的资深记者。父母参与了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采访和报道工作,如:开国大典、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取缔妓院、遣返日本战犯等。1957年,父亲因被错划成“右派”,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母亲也从《大公报》调到北京教育局从事教材编审工作。家庭的变故将哥哥姐姐和我置于边缘化的境地,这段异常艰难困苦的岁月教我学会了坚强、坚韧、自强不息,也塑造了我独一无二的性格,风风火火、胆子大、定力强、不受外界影响、桀骜不驯、思想独立、有自己的目标与方向。因此,之后无论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都能秉持理想信念,绝不轻言放弃,这对我后面能进入藏学翻译领域打下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1964年,在“唯成分论”政治背景下,作为“黑五类”之“右派”子女,因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的前身)录取上大学,是我一生不幸中的大幸。尽管我只在大学度过了一年多时光。1968年,响应“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号召,我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北京,前往山西洪洞4658部队进行劳动改造。一年七个月的部队锻炼,再次磨炼了我的意志,也是我一生应对一切艰难困苦取之不竭的精神食粮。劳动锻炼结束后,回到北京顺义一所中学当数学和语文老师,之后又在怀柔一所军工厂担任物理实验分析师工作,专业也因工作不对口荒废了十年。但我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持在工作之余自学英语。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78年恢复高考后,教师尤其是外语教师奇缺,加上师范和英语科班毕业,我顺利应聘到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
回首往事,发现之所以能走上涉藏翻译,因为前期打下了两个扎实基础:第一,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父母营造的良好书香氛围,潜移默化熏陶教育,让我从小学会敬畏知识、尊重知识,喜爱文字,也打下了坚实的中文功底。尤其是父母平反后,在他们已70多岁高龄时,父亲写完并出版了一部散文集,母亲也出版了一部70多万字的小说,这也成为我奋斗求索的精神动力之源;第二,母校北京女师十三中学给我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我们班14人,12人考上大学,所以时至今日我仍然特别感激母校女师十三中的培养。
二、踏上藏学翻译之道
笔者:第二个问题,想请您谈谈是如何走上藏学翻译这条险道的?
向红笳:刚开始在中央民族学院教书,并没有明确的藏学翻译目标。恰巧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后,第一项教学任务就是承担第一届研究生班的英语教学工作。该班有4名古藏文研究生,还有其他学科的研究生,当时我选用了中国佛教学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撰写的《中国佛教》这本中英文对照书,作为英语精读教材。这本书极大地丰富了我贫乏的佛教知识,也让我对佛学文献翻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以说这段教学实践是我与佛学第一次亲密接触。
真正开始藏学翻译时已38岁了,通过分析形势和总结经验,认为自己从事藏学文献资料翻译有四大有利因素:一是丰富的外文历史资料和文献是从事翻译工作的可靠保障;二是国际国内对藏学的重视;三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科优势,特别是藏学、突厥学、满学、蒙古学研究独树一帜;四是语言优势。认定目标后,为了掌握藏文拉丁转写,我开始学习藏文,作为中青年教师,一周16节课,而且是多个课头、多种教材,即便如此,当时还是觉得有点余力能做点别的事情。当时住房条件差,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小平房里,为了集中精力学习,大冬天只能裹着棉被在没有暖气、冷如冰窖的办公室里学习藏文。
从事藏学资料翻译要积累各种藏学专业知识,最直观的方法是亲赴西藏,感受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神秘庄严的宗教氛围和丰富多彩的民俗民风。20世纪80年代,西藏还是一片默默无闻的土地,到西藏旅游者多为外国游客,国内游客寥寥无几。1986年,中央民族学院电教中心派遣一个摄制组赴西藏拍片,当时拉萨还要举办一个国际藏学会议。为了获得这个千载难逢的进藏机会,我主动提出了为摄制组义务服务。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根本没考虑高原反应,一入藏就扛着40多斤的摄影器材去了甘丹寺,现在回想都后怕。第一次入藏后,我陆续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闯入世界屋脊的人》《西藏考古》《刺刀指向拉萨》(合著)等译著。这些作品问世受到了好评,为第二次进藏学习交流提供了机会。1991年第二届国际《格萨尔》研讨会在拉萨召开,我有幸应邀出席。这一次出行也是意外不断,从成都双流机场飞往拉萨,首先是延迟起飞,后面飞行过程中又发生了机械故障;返回北京时,也是一波三折,折腾了三天,最终才在第四天成功登机飞回北京。这两次入藏,虽历经磨难、备受挫折,却令我终生难忘、终身受益。
三、藏学翻译经验谈
笔者: 您是藏学资深翻译家,30多年的翻译实战经验,译著等身,您觉得做好涉藏翻译要注意哪些问题?
向红笳:目前,藏学与汉学、蒙古学、突厥学和敦煌学一样都已成为国际性的显学。藏学涉及西藏历史、宗教、语言、文化、建筑、天文历算、医学、艺术、音乐舞蹈、民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藏学文献翻译也涉及这些方面,难度很大。我的经验是外语专业的人员要做好涉藏翻译,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平时有意识积累藏学知识。利用业余碎片时间,多阅读相关涉藏书籍,不断积累常识和专业知识。有条件的可去西藏实地田野调查,直观学习了解。在具体翻译实践中,翻译动笔之前还要临时恶补与翻译题材密切相关的藏学知识。一名合格的译者永远要保持谦虚谨慎、不耻下问、孜孜不倦的求学态度,不能想当然,除了查阅相关文献,有条件的话最好请教藏学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弥补自身藏学知识不足带来的偏见等问题。
其次,翻译要有十分敏感的政治觉悟和意识。有时,出于某些原因,一些原文会出现政治性错误。如印巴分制线,其实是印巴分“治”线,这个“治”要翻译成governance;又如“金瓶掣签”的“签”要是翻译成单数drawing lot, 而不是复数drawing lots,别有用心者会指出,“如果仅有一签就无须用金瓶掣签”,以此质疑金瓶掣签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此外,我们当代学者、学生外语水平普遍较高,能直接看国外藏学英文文献,但要注意的是:不能随便照搬国外藏学文献的英语表达法,藏学文献汉英译文要与国内权威机构的译文一致。比如,我有一个学生翻译“吐蕃王朝”,直接照搬国外Tubo Empire, 这与我国外交部、统战部、中宣部的英语表达Tubo Kingdom不一致,不能照搬国外译法。因此,我们翻译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敏感性,藏学翻译千万不能迎合西方国家的话语权,涉藏英语译文一定要和外交部、新华社等权威部门口径一致,建立中国涉藏问题的话语权,保持外宣翻译的主动权,不能直接掉进国外涉藏反动宣传报道的陷阱。
此外,要践行“Live and learn”,即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理念。几十年翻译生涯的一个体会是:无论什么时候打开字典,都会有不认识的单词。因此,我们一定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多阅读多积累英语地道表达,汉英翻译才能做得更好。做一名优秀的翻译很难,一字一句都考验翻译的功夫、道行深浅,唯有终身打磨,永不言弃,方能不断精进。
最后,具体翻译实践时,原文理解一定要准确无误,涉及专业知识要多方查证、多方求证。我的做法是:碰到一些原文表达理解上有歧义的地方,翻译一定要与原文作者直接沟通。原文是:“牛怒气冲冲朝上师跑过来,上师一躲,掉进悬崖……”,到底是牛还是上师掉进悬崖了,理解起来有歧义,这就需要和原文作者直接面对面沟通或电话沟通,再次确认原文信息,理解准确。其他基础性藏学知识可以临时恶补,专业性强的问题还必须向藏学相关行业专家请教,确保翻译的第一环节理解上完全正确。具体翻译表达时,注意历史人物、地名、神佛名号等,其表达要与历史上、佛学经典上约定俗成的译法保持一致。遵循名从主人翻译原则,不能随意创新翻译出新的译名,而是要沿用约定俗成的译名。比如“乌金大师白玛迥勒”,意译为“莲花生大师”,其藏文和梵文的名字都是固定的,不要误译成两个人,类似这样的常识性问题是不能出错的。
四、涉藏文本翻译选择标准
笔者: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向教授,您退休后至今还一直活跃在藏学翻译界,仍在译海驰骋、笔耕不辍。最近在2019年第1期《民族翻译》上还看到您新发表的论文《涉藏翻译的难点与方法》,您的新译作《〈四部医典〉藏医唐卡挂图精解》也即将出版。请您谈一下,一般选择翻译涉藏翻译文本的标准是什么?
向红笳:与翻译其他文字的文本一样,在翻译内容的选择上,译者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即便如此,译者对文本的选择还是有一定的主动权,应慎之又慎。当前,涉藏外文书籍种类繁杂,涉猎极广,也良莠不齐。译者首先要在政治方面做出取舍,对有悖于我国涉藏政策、鼓吹“西藏独立”的外文书籍、画册、论文等,无论翻译费有多高,都要拒绝翻译。译者也要拒绝翻译一切抄袭、剽窃或质量低劣的中文藏学著作或外文转译著作。比如我曾经拒绝了陈渠珍《艽野尘梦》英文版电影字幕的翻译,当时要把英文电影版剧本翻译成中文拍成电影,电影名都拟好了叫《西原》,电影拍摄相关批文也拿到了,电影要以陈渠珍与藏族妻子西原的悲情生死恋为主线展开。当时拿到英文剧本,我只看了第一页就断然拒绝了这份翻译工作,因为英语版译者加入了《艽野尘梦》汉语原作没有的一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宗喀巴相当于中国的马丁·路德金”。我们知道马丁·路德金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家,宗喀巴大师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创始人,佛教理论家。把宗喀巴大师与马丁·路德金做类比,我觉得非常不合适。也许这个电影拍出来后会热映,名利双收,但作为翻译者,该有的政治立场一定要坚定,有政治问题的翻译,绝不能做。
此外,翻译选题和版本也很重要。版本选择时需要多加比较,切忌仅依书名进行选择。先浏览原文再做决定,重点看内容是否有新的观点、新的立意,翻译是否有学术价值。很久以前,我拒绝翻译《西藏生死书》,因为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西藏生死书》,当时已有很多版本,个人觉得没有重复翻译的必要性与价值。当然,也可以对比研究几个版本,深入探究其相似性和差异性,再做决定。最近,《〈四部医典〉藏医唐卡挂图精解》译完并即将出版,翻译之初也面临过犹豫不决的选择过程。因为国内也出版过类似的几部藏医著作,但该书前言指明:“画师什雷斯塔忠实地根据当时已公布于世的两套医学唐卡进行绘制。这两套唐卡一套保存在拉萨门孜康(即西藏藏医院前身),另一套保存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由于什雷斯塔从未造访过拉萨,因此,他也未曾见过任何原作或保存在那里的临摹本。”[1]读完后,我认为此书79幅藏医唐卡与前几种出版物在绘制方式和释义上必然有一定的差异,也一定会有独到之处,因此,我认为这就是翻译此书的价值所在。同时该书汉语译本必然会对藏医和藏医唐卡的源流、传播途径、方式以及现状的研究大有裨益。
五、对后辈建议
笔者:向教授,对于那些想要或即将进入涉藏翻译领域的后辈,您有什么好的经验和建议?
向红笳:首先,要确定目标。目标确定后,要学一点藏文,必须熟练掌握藏文拉丁转写,要是时间和精力允许,可以继续精进藏文。要是精力有限,也可只掌握藏文拉丁转写。做翻译最主要是理解,即能看懂涉藏不同题材文本内容。其次是语言转换能力,这是翻译最重要的两大基本素养。尤其是涉藏文献基础知识的积累有一个过程,因此,我认为涉藏翻译是前期投入特别大,收益小,随着经验积累和知识扩展,翻译越做越得心应手,越老越吃香,后期才是涉藏翻译的收获期。
对于刚进入涉藏文献翻译的新手,可选取一些挑战性小一点的题材,比如旅游文本、西藏民间故事、童话、藏族民歌、节假日等民俗这类偏重文化类、简易题材的翻译。随着经验积累增加,翻译水平提高,再尝试翻译涉藏政治、宗教等难度较大题材的文本。也可选取紧扣时代热点话题翻译,如藏区“一带一路”“南亚大通道”等文化外宣题材。无论题材的难易,翻译一定要多查相关词典、字典,不能想当然,要确保原文理解准确、译文表达流畅无误。查阅文献、求证的过程,虽说费时,也是学习藏文化的机会,慢慢地理解Religious Article(法物)、Religious Implements (法器)、the Six Sacred Words(六字真言)、support(藏传佛教中皈依处所,佛经、佛塔、佛像是佛、法、僧的所依)这些藏学基础知识、术语,直至完全掌握。
再次,要把世俗的东西看得轻一点。现在的年轻人不容易,有生存压力,有职称评审压力,但不能把世俗的东西看得太重。即便是评上了教授,作为知识分子,还是要有点精神追求,要做点实事,最好和兴趣结合起来。翻译是一种精神追求,是一项很单纯的工作。为了保证单纯简单的生活,我很少用微信、微博等现代社交媒体,因为不想了解那么多事,只想静下心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藏学翻译、画画等。人到了一定年纪,一定要学着不与自己较劲,不与配偶、家人、社会较劲。有些人,不理解,常问我,怎么退休了还在做翻译,说到底挣多少钱才算完,我也不愿意跟人多解释。我也曾一度完全停下翻译,什么都不做 ,反而整天没什么精神,昏昏欲睡。因此,我还是决定做点翻译,精神更抖擞,既为社会做贡献,还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自己也发自内心地开心。
最后,在具体翻译时,一定记得多查证,可查阅权威文献等网络资源,也可向行业专家请教。翻译不可能什么都懂,我记得有一次翻译一个作品,碰到了马头琴的音乐专业问题,幸好有朋友是德国音乐学院马头琴专家,请教后才能恰如其分地对等翻译处理好涉及音乐专业知识的翻译。此外,还要注意翻译过程管理中的细节,签完合同接下翻译任务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确定翻译原稿必须是最终版本。一般翻译协议达成后,委托方必须给我寄一份原稿终版,防止交稿时因为版本问题出现业务纠纷,甚至带来重译等不必要的麻烦。还有一点要注意,通读原稿若发现原作中有一些与国内涉藏政治、外宣等法规政策精神不符的地方,一定要记得甄别原文本信息真伪,根据实际情况,删减修改不实、有误的信息。
六、典籍翻译保持原作风格的建议
笔者: 向教授,您曾应邀在外交部、西藏网、中国知网、西藏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举办讲座,您这两年也参加民族典籍翻译研讨会,特聘为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翻译资料中心的专家,对少数民族典籍资料的翻译工作进行了具体的指导。想请您谈谈民族典籍翻译。
向红笳:我没有专门进行民族典籍翻译,不便评论。正如我曾受邀参加民族典籍翻译研讨会,在大会发言中曾提出这样的观点:民族典籍翻译要尽量保持原作的风姿,要有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原汁原味。比如在翻译藏族民歌、情歌、格言或史诗时,应尽量保持藏文化风情,切忌译出汉文化印迹极深的藏族文化作品,如将“松石发饰”译成 “凤头钗”,这是不符合原作的风格、风姿。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翻译只有传达出原文独特的文化韵味才有跨文化交际价值和意义。西藏的舞蹈受广阔地域影响,藏族舞蹈活动空间就很大,而日本的舞蹈受生活空间的影响,活动范围就小。如果翻译把西藏的舞蹈译成了日本的舞蹈,我认为那就不是翻译了。
因此,我认为:如果没有民族典籍相关作品的翻译实战经历,仓促做民族典籍翻译评论是片面的、不科学、不恰当的。年轻人若精力充沛,可以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通读原文、译文,做藏族典籍几个不同版本的对比分析更可行。
七、重视民族翻译人才培养
笔者:西藏大学每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报名学藏语,等藏语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这些外语精通、也懂藏文的外国人和西藏本地的藏族学者合作,加入藏学研究、藏学翻译等领域,如2007年8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六青年的故事》,译者是西藏社会科学院白玛加措和旅藏的杰夫·贝利合作完成的作品,如今藏学翻译人才呈现国际多元化趋势,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向红笳:短期看,藏学翻译外宣人才还是很紧缺。藏学专家、学者,不一定具备做翻译的能力,即使做翻译,由于对学科理解深,有时会不自主加入自己的东西;而外语专业出身的译者,又缺乏藏学相关专业知识,不经过系统的培养和翻译实践,很难胜任藏学文献翻译。这也是目前藏学翻译人才短缺的两大根本原因。
文学翻译领域中外译者合作很盛行,理解还是需要本族语读者,翻译表达有外语为母语的译者参与,译文才能表达得地道自然。但是,如果只有英语为母语的译者,翻译过程中有一些观点可能被歪曲,违背了我国外交、外宣政策,所以单靠外国译者承担本民族文化外宣、时政外宣、文学翻译也是不现实、不可取。我曾经帮一个外国译者校译,发现很多错误。这也就是为什么多年前,我曾呼吁相关部门引起重视,建议建立民族资料翻译中心,为国家培养储备民族文学、民俗、民族政策等的外宣人才,向全世界更好讲述中国不同民族的故事,更好地做中国文化外宣翻译。
笔者:向教授,打扰了您这么长时间,今天的采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接受采访,祝您退休生活愉快,全家幸福!扎西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