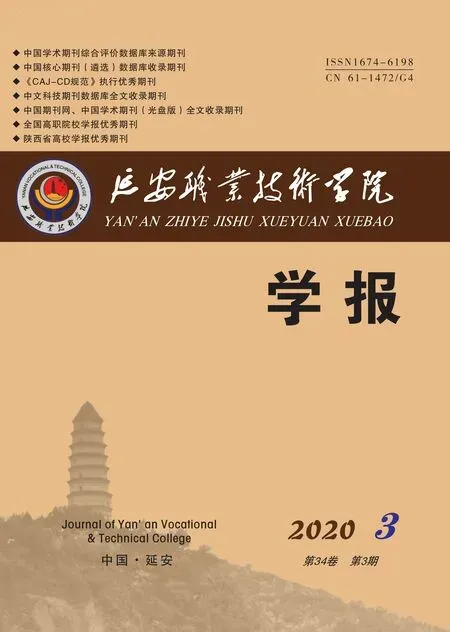刍议视域融合对诗歌翻译的影响
陆少辉
(遵义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0)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缘起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Gadamer)在海德格尔的影响下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现代哲学阐释学。他提出的“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三大原则对现代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诠释了人类如何认知事物及认识事物的过程等。构建起多种语言交流的桥梁——翻译,在伽达默尔看来,就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尤金·奈达将翻译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分析(Analysis),转换(Transfer),重构(Restructuring)。在将源语文本转换为目的语文本的过程中,即具有不同于作者历史背景和人生阅历的译者在分析原文本,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重构输出的过程中,必然有译者与作者/原文本视域的融合。而唯有读者阅读译本,才能实现翻译的目的与意义。读者阅读译本的过程就是朱健平认为的第二次视域融合,也就是目的语语言文化的视域与译者新视域的融合。在译本与原文本越走越远的路上,译者意图与外部因素如出版商、意识形态、读者期待视野及语言力量对比都有影响。最忠实的翻译应该是译本尽可能贴近原文本,使目的语读者接触到原滋原味的异国文化。
西方文化以《圣经》和古希腊罗马神话为源泉,而《诗经》是中国文化的源泉。闻一多先生曾说:“三百篇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传教士理雅各热衷于传播中国文化,追本溯源,早在十九世纪,就把《诗经》英译到西方国家。为传达《诗经》的意美、音美和形美,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的许渊冲先生所翻译的中国经典诗文集中也包含了此本。本文拟取两译本的案例进行对比分析,以探索在社会文化语境中视域融合对诗歌翻译的影响。
二、社会文化语境与视域融合
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亦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语言文化间的差异一方面会造成翻译中一定程度的不可译,另一方面对译者视域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理解的历史性和译者的前见使得译者在翻译实践的第一步分析阶段对文本的理解有所不同。诗歌,作为文学中一大文体,其形式的独特性、结构的跳跃性、表述的凝练性和语言的音乐性这些特征增加了准确获取原文本内涵的难度,用另一种语言表述出功能对等的一首诗歌的难度可想而知,甚至有学者提出诗歌不可译的说法。但国内外的文人学者还是尽力搭建了两种语言文化间的桥梁,用韵体诗或者散体诗来翻译。《诗经》从十九世纪到现在,已经出现同一译者或不同译者的多个译本。这与译者视域的不同有关。在社会文化语境中不同视域的融合,催生了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一般而言,社会文化包括社会阶层、价值观念、亲属关系、政治、法律、教育、哲学、风俗习惯、历史背景、神话传说和思想意识等方面。
(一)历史背景
理雅各的《诗经》译本被西方公认为标准译本。纵览其译本,理雅各在某地方多采用音译的翻译方法,且用的是威妥玛式拼音法;而许渊冲先生却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
1.诗歌的题目。理雅各都是采用威妥玛拼音音译。如《小雅·鹿鸣之什·四牡》译为Sze mow,《小雅·鹿鸣之什·出车》Ch‘uh keu,《国风·卫风·考槃》K‘aou pwan等。《四牡》主要讲的是官员在忙于公务时对父母的思念。许渊冲将其译为Loyalty and Filial Piety,彰显了文章的主题。许渊冲将《出车》这首诗的标题译为General Nan Zhong and His Wife。根据译者的注释,诗前四章的说话人是南仲将军,后两章的说话人是他的妻子。译者选用说话人的角度来创译标题。《考槃》许译为A Happy Hermit,点明全诗主要描写的是一位隐士远离尘嚣的生活。
2.诗歌中一些植物名翻译。“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匪莪伊蔚。”Long and large grows the ngo;--- It is not the ngo but the haou.......It is not the ngo, but the wei.”可见句中“莪”“蒿”“蔚”被理雅各译为ngo,haou和wei,表明这是三种不同的植物。而许渊冲将其意译为sweet grass, wild weed和shorter weed。据此三个短语可知,译者表达的是第一种草受人喜欢,而后两种价值不大,来“兴”作者常年服役,加之经济状况不佳,未能在父母生前尽孝的自责与愧疚,与本诗主题密切相连。
3.诗歌中的一些象声词的翻译。如《小雅·鹿鸣之什·伐木》的首句“伐木丁丁,鸟鸣嘤嘤”,理雅各将其译为On the trees go the blows chǎngchǎng;And the birds cry out ying- ying[5]。chǎng-chǎng和ying-ying分别指的是伐木丁丁的声音及鸟啼叫的嘤嘤声。再如《小雅·彤弓之什·鸿雁》“鸿雁于飞,肃肃其羽”,理译为The wild geese are flying about, Suh-suh goes the rustle of their wings;“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理译为The wild geese are flying about, And melancholy is their cry of gaou-gaou.理雅各将“肃肃”“嗷嗷”分别音译为suh-suh 和gaou-gaou,来模拟鸿雁羽翼扇动的声音和啼鸣的音调以比喻被驱服役者身体的忙碌与内心的悲伤。而细读许译本,会发现译者采用省译法表达了诗句的涵义,却省去了象声词。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越发先进,交通越发便利,这些声音大家容易感知到;另一方面,省译后,采用四步格的表达使得译文更简练,句式更加整齐,保留了原文简朴的风格。
4.称谓语、国名等的翻译。《大雅·文王之什·大明》第六章“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为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Giving the throne to our king Wǎn, In the capital of Chow.The lady-successor was from Sin,....She was bless to give birth to king Woo,...And in accordance with it smote the great Shang.文王、武王的翻译采用的是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式,译为king Wǎn, king Woo;国名周、莘、商及前文出现的挚,采用完全音译法,运用威式拼音,将其译为 Chow、Sin、Shang 和Che。而许译本中,从Ren(任), Wen(文王), Zhou(周)中可以看出,译者音译时运用的是汉语拼音。
许渊冲和理雅各在上述四个板块选用不同的翻译方式。根据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译者对于原作的翻译并非始于研读原著,而是始于自身的前理解/前见。前见的存在影响着从原作到译作品读过程中的视域融合。前见因素中的社会环境、译者动机、语言、记忆、个人阅历及其主观感受包括潜意识、直觉及对事物反应出的情感等都会作用于译者视域与原著视域的融合,从而使得视域融合影响译者用另一种语言将原作内容表达出来的过程。一方面,视域融合影响诗歌翻译过程中译者译码的选择,这就说明了许理选用不同符码的原因。威妥玛式拼音法是由威妥玛创建后翟理斯在其基础上完善,于1867年正式投入使用,在1958年汉语拼音普及前在国际广泛使用。理雅各是在1861 年至1886年翻译了包括《诗经》在内的28卷中国典籍,致力于将其向西方社会推广。秉持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意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理雅各的视域与《诗经》文本的融合,通过使用威式拼音音译尽可能地将原滋原味的《诗经》呈现在读者面前。而许渊冲所处时代,汉语拼音已为世人熟知,更能被广大读者接受。另一方面,视域融合影响着译者进行诗歌翻译时翻译方法的选择。翻译过程中发生两次视域融合。译者要考虑到原作视域的同时,也要考虑读者的公共视域。这就决定了一方面译者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原作,另一方面考虑到读者的接受性和可读性以及目的语文化语言的特点,译作的视域必然不能与原作视域完全重叠。为符合英语诗歌的节奏与格律,受诗歌表意空间的限制与创意效果的推动而形成的反常化特点,译者在视域融合与表达的要求下,必然会对翻译方法的选择及文本中词汇,语句的灵活处理造成影响。
(二)思想意识
理雅各和许渊冲译本的一个共同点是都有类文本。类文本是指与(主)文本相对应的那些环绕在文本四周的要素,包括封面、书名(标题)、前言、后记、附录、评论、插图、注释、目录、版权信息等。许渊冲在《代后记》中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学派文学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理雅各译本则突显在注释之精、之深、之全。他将诗歌中的字词解释与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一并记录于注释之中。通过注释我们也可以管窥到其视域与原文视域融合的过程。视域融合首先存在与过去的相遇。伽达默尔认为,过去对我们“倾诉”在解释学的各种制约中是“最高的制约”。从根本上来说,仅仅过去的“倾诉”不能够使“相遇”成立。为了使相遇成立,必须要倾听倾诉的声音。
理雅各在其注释中阐明该诗以鸿雁“兴”流离失所的平民,并结合前面诗篇《车攻》中“之子于征”的涵义,不认同前者观点,推测其应为国王所派官吏。如此实现了译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相遇”。从旁征博引的注释中,不难发现理雅各在翻译《诗经》的过程中,力求忠实传播中华文化,虽然他作为汉学家对中国文学与文化颇有研究,但碍于中西方当时交流有限,西方对中国所知甚少,所以除翻译出诗句外,理雅各还在注释中尽量详细地介绍与之相关的语言、文化、历史等信息,对于几家有争议的地方,还注入了自己的研究结果,体现出身为一个东西方文化传递者以端正的学者态度与精神翻译和传播《诗经》的思想。但许渊冲认为理译本注释丰富,是学者的译文,却不如原文简朴。这两句的翻译也反映了许渊冲此书翻译思想的一方面。许渊冲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又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之真谛,他翻译的初衷就是使《诗经》以简洁、音美、形美和意美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样的译文读起来朗朗上口,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熟悉,从而较深刻地感知中华文化。许、理两家的翻译行为也践行了他们的翻译意图。可见,思想意识的不同使得不同译者在进行诗歌翻译的过程中,亦即在译者视域与原作视域及公共视域融合的过程中,进行了剧烈的思维活动,形成对诗歌原文的不同理解,彰显了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的彰显并非诗歌翻译之目的,是译者在诗歌翻译时两次视域融合的化身。理解是表达的先决条件,两次视域融合在一起后,译者的整体意识全盘呈现,经自身语言的处理与输出,最终形成译本。视域融合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过程,却是诗歌翻译的必经的重要环节,并且先天性地作用于诗歌翻译成品的问世与反响。
三、结语
通过选取理雅各和许渊冲《诗经》英译本中的案例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意识等社会文化语境中,译者的视域与原文视域形成的共同性有所差别,形成的理解必有所异,故同一文本的不同译本应运而生。译者在两次视域融合过程中,不但要恰当发挥其主体性,还要考虑公共视域,以创作出适应时代的优秀诗歌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