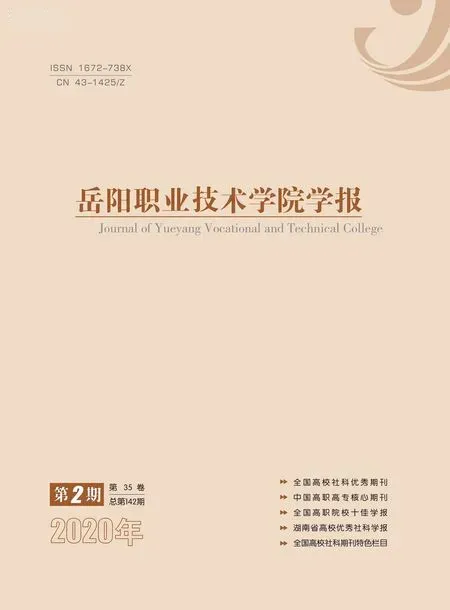卡夫卡《城堡》中的弗丽达女性形象研究
姜周群 雷庆锐
(青海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
弗兰茨·卡夫卡所处的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女性居于附属和屈从的地位。透过卡夫卡日记、书信等发现,时代和家庭等深刻影响到其对于女性地位的思考。然而,宗教是卡夫卡的全部世界,即使作为进步作家,甚至力图从现实社会寻找到女性的解放途径,但其始终无法摆脱早已浸润在自己身体内的犹太女性观。诚然,卡夫卡的女性形象充满矛盾,即便如此,依然不能忽视卡夫卡为我们塑造的女性群像以及女性形象蕴含着的深刻意义。本文试图以卡夫卡作品《城堡》中的女性主义为切入口,深入挖掘《城堡》中弗丽达这一女性形象的复杂内涵。
1 弗丽达形象的内涵
“卡夫卡深深植根于人类生活的悲剧之中,他那无比清晰的作品,足以描摹出人类彻底破碎的形象。”[1]《城堡》中弗丽达形象既彻底破碎又复杂丰富。弗丽达的内涵正如索克尔解读《城堡》时所说:“卡夫卡在《城堡》中描绘了现代人的根本处境。”[2]弗丽达的处境便是通过其“事业”的三个阶段和内心矛盾三种状态展现出来。她以“克拉姆情妇”身份出现,但是荣耀并未填补内心的虚无,事业和自我虚无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峰。为了寻求自我生存问题的答案,弗丽达决定与K 结伴而行。于是,她从另一个世界抽身而出,坚定地倒向了体现出城堡意志的旧世界,心甘情愿地走向了回归传统宿命的道路,宣告了自救之路的彻底失败。城堡是奥匈帝国崩溃前荒诞世界的缩影,弗丽达作为现代人被任意摆布而不能自主,意欲追求自我和存在的自由,但最终未如愿以偿。
1.1 荣——丧失自我的哀愁
主人公K 作为一个外乡人,被贴上了“碍手碍脚、总给人制造麻烦和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的标签。而弗丽达是一个被官员眷顾的女人,可以毫无阻碍地行动着。这与处处受阻的K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弗丽达“克拉姆情妇”的身份能给她带来城堡权力辐射出来的特权。洞眼是为窥探房间里的动静而开,而那正是高高在上的克拉姆的房间,克拉姆允许弗丽达从洞眼里看他,这对于弗丽达、赫伦霍夫旅馆乃至是整个村庄来说都是莫大的殊荣。弗丽达一直以“克拉姆情妇”的身份围绕着以克拉姆为代表的权力奔跑,却无法从无休止的追逐中获得快乐。高贵的身份无法弥补弗丽达内心的空虚与孤独,这让她那双哀愁的眼睛里充满对自我生存的困惑。K 的出现使她眼前一亮,她把自己和K 的爱情捆绑在一起。因此,弗丽达踏上了帮助K 寻求身份、拯救自我的道路。
1.2 枯——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
K 对弗丽达说:“咱们俩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自从咱们互相结识以后,我们各自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咱们依旧感到不安全,因为一切都太新奇了。”[3]弗丽达被城堡控制了意志,自然体现着城堡思维,而K 作为一个外乡人,两人之间不可避免将出现较大的分歧,这不仅体现在对待巴纳巴斯一家人的态度上,亦体现在两人与两个助手的相处之中。诸多不同使得弗丽达的行动和思想总是踏着杂乱的步子,两者的错位让弗丽达充满矛盾与迷茫。
《城堡》围绕着K 追求事业和爱情而展开,K试图通过工作和婚姻巩固自己的信念,顽固地寻觅着任何一个可以证明自己土地测量员身份的机会,希望能名正言顺地在村庄安家落户。K 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弗丽达身上,因此K 的爱情也在潜移默化地被城堡意志所支配。弗丽达本来在男性眼中,有着无穷的生气和毅力,她那平凡的身躯也因此显得特别美丽,显然,弗丽达更适合酒吧的工作。弗丽达内心深知,从在酒吧间的趾高气扬、自信骄傲到被琪莎欺凌,代表理性的权力和代表非理性的爱情与自我在内心的碰撞可想而知。
1.3 荣——回归传统宿命的坚定
弗丽达最终的回归是多重原因的催化。首先,杰里米亚以特殊身份为城堡服务,身上体现着城堡的意志,更何况他是弗丽达幼时的玩伴,是唤起弗丽达在城堡快乐生活的最好媒介。幸福的童年生活加剧了现在的痛苦,弗丽达最终将倒向城堡。其次,弗丽达较长时间处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之中,加之K 与弗丽达之间的意识之别,让两个人的情感无法平稳落在现实生活中,观念的不同意味着一方必须妥协或退让,这种不平等的爱情关系有着破碎的必然性。再次,以艾朗格为代表的官方力量。自有下面追逐权力的人方方面面替克拉姆着想,密切关心克拉姆的安宁。艾朗格要求弗丽达必须回到酒吧工作,不能只顾私人感情,将所有会造成麻烦的可能抹杀。
弗丽达的回归表现在离开学校抛弃K、接纳杰里米亚回到酒吧工作。在这场村民与K 的角逐中,弗丽达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试图拉拢外乡人进入城堡,使K 变成和自己一样的权力的附属品,将K 从被诅咒的一家人中解救出来,亦或试图凭借外乡人逃离城堡,实现精神自由,最后放弃了行动悻悻而归。弗丽达从城堡的边缘重回那个“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就是权力,人的意识是权力的投射,感官知觉由权力发挥效应形成,行动被权力支配,命运被权力主宰。”的城堡[4],这一次弗丽达不再寻求自我,而是更加坚定地接纳它。弗丽达的回归不仅表明了K 追逐爱情的失败,而且揭示出包括K 和弗丽达在内的城堡的仆役们无法逃脱宿命的牢笼,最终向命运低头,心甘情愿地被奴役。
2 弗丽达形象的外延
“卡夫卡的写作非常自由,在思想和情感上充满了跳跃性,修辞和意向非常神秘,表述在意以上有很多悖谬。”[5]而嘉德娜、佩披和阿玛丽亚与弗丽达存在着共性和个性,共性在于某种程度上她们都是弗丽达,“表现形而上的欲望,表现我们时代的精神苦难和困境”[6],共同处于“虚无和世俗之间的中介点”[7],但她们是不同阶段的弗丽达。弗丽达的形象从前至后辐射出未来与过去两个另外的人物形象,即佩披和嘉德娜,一个是渴望接近奋斗者姿态的弗丽达,一个是被抛弃后处于自己幻想世界中病态的弗丽达。而阿玛丽亚和弗丽达面临过同样的处境,均具有是否向权力妥协的选择权,但两人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这三个人物成为弗丽达形象的外延,四位女性共同组成的“弗丽达”成为城堡意志对于女性腐蚀的完整体现。
2.1 佩披——欲与求阶段的弗丽达
佩披最接近K 的气质,“既非进行有目的的真正行动,也非处于停滞状态”[8]。佩披以弗丽达为目标并渴望成为“克拉姆情妇”,举止投足间都散发着欲与求。年轻的佩披因弗丽达职位的空缺偶然得以从房间出来到大厅伺候。佩披有着高扬的生命力,积极地追寻权力、毫不吝啬地付出自己的行动。首先,弗丽达通过装饰外表以提高自己的吸引力。透过K 的视角,佩披在头发、服装、首饰等方面大做文章,将自身的迷人摆在第一位,并为工作充分考虑,心思昭然若揭。其次,佩披一改弗丽达在时的独揽大权,把侍从的管理、账务的管理等统统交给看管酒窖的人。佩披将工作重心放在伺候上房,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偷偷缩在那条勤杂工严禁入内的走廊角落里等待克拉姆的机会。再次,佩披激情的努力还包括对K 的拉拢。弗丽达对克拉姆大声喊道:“我正陪着土地测量员哩!”[3]这顺理成章地成为弗丽达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当K 无处可去之时,佩披成为除巴纳巴斯一家人之外唯一愿意收留他的人,佩披不愿意放弃处于绝望中最后的希望。
佩披为了打败对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眼花缭乱的筹划始终无法改变她注定失败的命运。佩披越是采取过多的行动,体现得过于热情与积极,就与城堡的气质愈为相异。城堡冷若冰霜,冷眼看待着村庄发生的事情,而佩披身上所透露出来的热情似火的生命力不被容纳。由于K 接近城堡失败的必然性,影射了佩拉计划失败的必然性。她错误地高估了K 的地位,K 的行动无疑可以在雪地里留下深深的脚印,但也不会有更多的作为。
2.2 嘉德娜——幻与灭阶段的弗丽达
赫伦霍夫旅馆的老板娘——嘉德娜从克拉姆那里得到了连弗丽达都没有的三件纪念品。这段幸福的回忆和关系停止的疑问充斥着她整个后半生生活。她既不愿意失去平淡的夫妻生活,亦不愿意失去任何一个接近城堡靠近权力的机会。嘉德娜靠着没有克拉姆回应的信仰支撑着她全部的生活,甚至没有克拉姆则无法活下去。她主动放弃了自我意志和独立人格,屈服于以克拉姆为代表的社会基本模式。
面对同样的处境,弗丽达主动寻找自我而离开克拉姆,嘉德娜的灭却与之不同,总是和他丈夫谈论起克拉姆,在虚幻中度日。然而这一点也成为了城堡中的常态:女性以权力男性为中心,在男权为主导统治的社会中缺乏足够的认知,对强大的官僚机构的矢志不渝的信奉。权力腐蚀着嘉德娜的心灵,使她无法回归自己正常的生活,在自己的幻与灭中逐渐病态,把自己撕裂得粉碎。
2.3 阿玛丽亚——罪与罚阶段的弗丽达
阿玛利亚像城堡中的其他女性一样,权利的欲望驱使她精心打扮一番,盛装出席救火车赠送仪式,希望得到官员的青睐。但是,当她如愿以偿地收到索尔提尼的“情书”时,却大胆做出异于常人的选择,将信撕得粉碎,抓着碎片朝着信使的脸上扔去,表现出对权力体系的蔑视与反抗。城堡精神沐浴长大的阿玛丽亚将爱情和对权力的追寻交织在一起,她期待的是圣洁和不容玷污的结果,但她看过信后,对城堡真正失望了。“阿玛利亚的情感和伦理界限是清晰的”[9],她勇敢地选择了一条与弗丽达相反的道路——用拒绝爱来爱。城堡的意志要求无条件尊重、无条件服从。她当然深知自己违抗城堡意志后即将面对什么,义无反顾地成为清醒的受难者。在某种程度上,“阿玛丽亚就是城堡。”[10]
城堡是拥有巨大权利的统治机构,无不透露着对人的约束与惩罚。对巴纳巴斯一家人的惩罚并不需要官方一个明确的文件或指令,无处不在的城堡意志自会惩罚他们。巴纳巴斯一家人遭受神秘莫测的当局的摒弃,亦意味着不再被村庄所容纳。村民成为惩罚的代行者,不仅阿玛丽亚陷入了命运的泥淖,整个家庭都掉进了罪的深渊。不论是朋友还是仇人、熟人还是素不相识的人,谁也不肯再多待上一会儿,平时最亲密的朋友走得最快。父亲失去了鞋店的生意,并且被曾经夸奖自己的上司解除职务,母亲亦因此神智不清。家人们只能用各自的方式恳求城堡的宽恕,祈求或者愤怒地叫喊都无济于事。老父亲不惜花光所有的积蓄贿赂城堡,奥尔珈也不遗余力地讨好城堡里来的侍从,巴纳巴斯更是担任了克拉姆的信使,每个人都希望能减轻罪孽,祈求城堡的宽恕。但他们永远都不会被宽恕,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指控,没有罪名,就无所谓惩罚,更谈不上宽恕。
3 结束语
卡夫卡尊重女性,认为女性显示出来的力量和品质并不逊于男性,甚至优于男性。卡夫卡《城堡》中的女性在价值定位上有被刻意地提升,女性比男性体现出更强的生命力。卡夫卡深知女性生存空间的狭小和有限,却无法凭一己之力去改变女性的生存困境。城堡的意志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能任意赋予或剥夺他人的身份,这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女性只能被迫接受社会强加于她们的角色和弱势的身份和被迫承认社会道德的漏洞和错位。她们是K 追寻路上的同伴,同样未能从毫无希望的死胡同里闯出一条出路来。因此,卡夫卡暗示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女性地位,重构现代文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