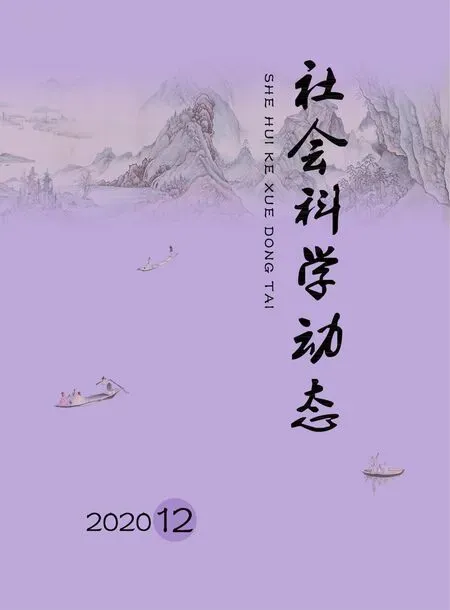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研究的成果、问题与展望
陈 珂
市民社会概念作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基石,近半个世纪以来,逐步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思路遮蔽下脱离出来,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学界围绕马克思市民社会的演进阶段、基本内涵、理论贡献等展开了全面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本文通过梳理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阐明其中的共同之处与分歧所在,在此基础上评析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期为继续辨明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之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定位与称谓”提供一点参考。
一、国内关于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研究述评
近十年,我国学者有感于中国体制转轨下社会基础缺失这一社会现实,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愈来愈重视。然而,关于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本身也有不少争论的声音。学界从纵向上围绕市民社会后期“消失论”,从横向上围绕市民社会概念“等同论”等核心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回应,在此基础上开掘了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生成的意义维度。
(一)纵向:梳理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生成脉络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否是一个前期“经常使用”,后期“弃之不用”的概念?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关涉到市民社会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学者们纷纷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分为两个或三个阶段。
一直以来,在传统的教科书体系中,市民社会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消失的范畴”。随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建立后,市民社会概念就被含义更加明确的经济基础所替代了。受这种观点影响,有些学者聚焦于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将市民社会概念的生成划分为两个阶段。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是从资产阶级社会的意义上理解市民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市民社会的含义转化为作为经济基础存在的交往形式,表现为从“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到“生产关系理论”的转变①。还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外延描述性”概念到物质生产关系的“内涵分析式”概念的转变,做了思想一致性的分析,指出这非但不是“断裂”,而且体现了“逻辑学和认识论”的高度统一②。虽然视角不同,但他们都指出了市民社会从个别到一般,从狭义到广义的思维逻辑,将市民社会概念置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中考察,感触到了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多重含义。但是,这些观点将目光集中在马克思早期市民社会概念含义的演变,遵循的是从具体到抽象的下降思维逻辑,将市民社会概念的多种含义“归结”为经济基础,却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并非仅仅停留在“市民社会一般”这个抽象上,在其后期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使市民社会又重新回到了“思维具体”的形式。由此,两阶段论并没有涉及到马克思后期的思想发展中市民社会概念的地位,其潜在逻辑仍然是将市民社会概念视作马克思早期“不成熟”的后期被抛弃的观点。
为了证明市民社会概念在马克思文本中的“消失”并非是一种“文本事实”而是一种“学术假象”③,三阶段论则在两阶段论的基础上,继续探索马克思中后期、尤其在《资本论》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其演进划分为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的“发端”萌芽期(1843—1844年),深入剖析市民社会内部结构的定型期(1844—1847年)和超越市民社会,实现人类解放的成熟期(1857年—)④。除了以市民社会理论的成熟程度为标准,还有学者以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批判视角的转换为尺度,将其划分为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发掘“拜物教性质”的意识形态批判三个阶段⑤。此外,回归马克思的文本,可以发现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词在前后期文本中使用频次确实有大幅度的下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出现了92次,而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却只出现了10次。如何解释这一转变,也是三阶段论者在论证市民社会之于马克思后期思想重要性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有学者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市民社会概念的“重构”为这一转变提供了一种解释。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在后期马克思减少在“概念形式”上使用市民社会,但市民社会的“概念内涵”不仅没有被丢弃,反而通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得到了“更科学,更系统”的批判性重构,为超越市民社会提供了一条可行性路径⑥。
两阶段论和三阶段论看似只是对于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生成阶段的不同划分,而其核心差异则在于如何认识马克思晚期文本中市民社会概念“消失”的现象,关涉到如何定位市民社会概念的关键问题。三阶段论的观点继续开掘马克思后期对于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以及转变的原因,因而这种观点更能从完整形态上把握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二)横向:考辨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
之所以会产生市民社会概念是否“消失”的争论,其根源就在于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内涵理解上的分歧。由于“市民社会”一词出现在马克思的不同文本,而且在不同文本中马克思的用词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于何谓“市民社会”,学者的回答思路也有重大差异。围绕着如何把握“市民社会一般”与“市民社会具体”的关系,学界大致形成了两种模式、四种观点。
一种模式是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做单向度的理解。第一种观点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归约为单纯的经济关系,等同于“经济基础”。有学者指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市民社会概念“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含义”,和生产力紧密相连,“既受生产力制约,又制约生产力”,其内涵已经相当于生产关系或“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⑦。还有学者在接受这种观点的基础上,从马克思当时所秉持的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的思想背景以及以唯物史观颠倒唯心史观的思想意图出发,分析了马克思之所以要做这种“简化”的原因⑧。
第二种观点是将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由于“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德语中兼有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双重含义,马克思在解剖市民社会时,也往往以资产阶级社会为现实载体,因此部分学者就将二者等同起来。然而,马克思也确实在“交往形式”、 “社会物质关系”的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因此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一般”,以论证市民社会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致性,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要回答的主要问题。从历史上看,根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以往的市民社会“雏形”称作先前的、旧日的市民社会,有学者指出,市民社会的形成是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只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及其雏形——欧洲的市民自治发展起来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市民社会才获得了完整的形态。因而不能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分析型的概念无差别地运用于所有社会关系之中”⑨。从逻辑上看,不同于将市民社会视作现代社会产物的观点,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市民社会,只是“从后思索法”的体现,是资本主义本质的、简单的、萌芽的生产关系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投射,将历史上的物质交往关系视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萌芽与征兆⑩。
然而,也有学者对于上述两种观点持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种“简化”的解释路径,不足以反映市民社会概念原本丰富的内涵。比如有学者指出,将市民社会归结为经济基础只是意味着“马克思从本质上把握了市民社会”⑪,但市民社会中同时也包括了“丰富多彩的其他社会交往活动”⑫,并不能将物质交往关系等同于市民社会的完整内容。而将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则会造成同早期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绘像之间的矛盾,因为当时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还只是“以物质生产关系为基础、以利己主义为原则的私人生活领域,具有历史性、现实性、利己性和敌对性等四重内在规定性”⑬。这部分学者更倾向于从多重含义阐释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由此开启了第二种解释模式。
在第二种解释模式下,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从双重含义上使用了市民社会概念。自从城冢登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划分为代表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与政治法律关系的“具体形象”与“被凝缩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的抽象形象后⑭,这种观点就成了一种普遍的看法。我国也有学者持类似的观点。俞可平认为马克思是在两层含义上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一是作为本质特征是阶级利益的历史性范畴,二是抽象掉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析型范畴,本质上是“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他将市民社会分为逻辑存在和现实存在:逻辑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作为私人领域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而现实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只有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胜利后才独立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马克思从未拒斥市民社会一般⑮。
第四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从三种含义上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第一重含义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作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及舞台”的市民社会。这里的市民社会意味着同上层建筑相对立的经济基础。第二重含义是以私人所有为基础,以商品交换为核心的作为本来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第三重含义则是18世纪产生的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市民社会,此时占主导关系的并不是单纯的商品货币关系,而是雇佣劳动和资本关系⑯。
上述四种不同的观点看似只是给予市民社会不同的“称谓”,其实根源于对其的不同“定位”。第一种模式下的两种观点,都抛弃了马克思的辩证思维方法,或只看到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一般,或只看到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市民社会具体,忽视了“抽象”与“具体”的联系。虽然将市民社会的内涵做了不同的界定,其结果都是将市民社会视作马克思思想史的“过渡性”概念,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下被“经济基础”取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下被“资产阶级社会”取代。而回归马克思的文本就会发现,这类将市民社会等同于经济基础并且后期“消失”的观点无法涵盖马克思使用市民社会概念时的多重意涵,无力解答为何在马克思中后期文本中除了使用“经济基础” (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和“资产阶级社会”这两个具有明确意义的词语(Bourgeois Society),还同时使用具有双重含义的 “市民社会”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而将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也无法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多种用词。据重田澄男考证,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市民社会”一词出现了10次, “资产阶级社会”一词出现了8次, “资本主义社会”一词出现了3次⑰。这说明即使在马克思的成熟时期著作中,他也同样没有取消三者之间的差别,虽然资产阶级社会和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关联之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马克思在用词上的差别,将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三者不做区分地相“等同”。而第二种模式下的两种观点,则较为全面地揭示了马克思使用市民社会概念时的多种层次,说明了考察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不能见木不见林,而应该站在马克思思想发展“整体像”的高度上把握“一般”和“特殊”的思想交织。
(三)关切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生成的意义
学界对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的认识在不断探索中愈益完善。市民社会概念反映了马克思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关切,这也决定了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命力。在梳理和考辨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本身的基础上,学界又对其生成之后的意义展开了积极的探讨。
一方面,学界遵循“从后思索法”探讨了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之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大致形成了两种路向。一是侧重分析市民社会概念形成与发展对于唯物史观建构的价值。有学者强调市民社会概念对于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中轴与基础作用,认为正是通过在经济学领域对于市民社会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才得以提炼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的框架⑱。二是开掘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政治哲学意涵,将近代规范性政治哲学推向纵深。有学者指出市民社会概念内蕴的政治哲学色彩,是近代政治哲学家“据以立论的根本支点”,自由、平等等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都是以市民社会为背景的⑲。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从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中轴——“正义”出发,指出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超越性,认为正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马克思对正义的理解逐渐“从先验抽象的正义”转向“经验、具象的正义”,并从建构正义原则转向推进正义实践, “最终形成了扎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统一的正义思想”⑳。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路向并不是毫无关联的,只是探讨的侧重点不同。有学者以“双重逻辑”概括了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意义,指出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就是使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融聚为一体的桥梁㉑。对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意义的开掘有力地反驳了传统观点中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忽视正义、平等等价值取向的观点。
另一方面,学界围绕我国构建市民社会的可能性开掘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现实意义。这一路向经历了从梳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到认识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现实意义在于“超越市民社会”的研究重点的转变。目前,学界注重阐发批判维度对于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作用。有学者从现代社会的公共性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性出发,指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为当代中国明确了“超越市民社会”的必然性,认为批判并超越市民社会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前提和文明基础”。
二、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研究述评
在马克思之后的时代,其市民社会概念依然受到国外学界的关注。赛格里曼强调马克思之于当代市民社会观念具有开创性作用,一方面古典市民社会观念在马克思那里走向了终结,另一方面也开创了20世纪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实践㉒。和国内学者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发展做出全面的阐发不同,国外学者主要是依据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集中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做出新的阐释,形成了辩护、重释、质疑的三种倾向。
(一)辩护: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恢复
在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辩护中,日本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派的尝试尤为值得关注。随着二战后资本主义在日本的迅速发展,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要正视这一现实,另一方面也要对日本社会中的问题做出回应。这使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重新受到关注。针对传统的教义体系将市民社会概念视为在早期的马克思思想中活灵活现,后期又销声匿迹的“不成熟”观点,望月清司指出,市民社会概念是众多在教义体系中“消失的范畴”里最为重要的一个㉓;平田清明也提出了恢复市民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应有地位的任务。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相应产生。在这样的理论任务的指导下,该学派形成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一,区分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派同样将市民社会视为以私人所有为基础的分工和交换体系,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核心的异化的社会。对二者进行区分的必要性在于,传统的教义体系将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视为可以互换的概念,这是使得市民社会“消失”的主要原因。平田清明在《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从市民的社会关系向资本家的社会关系嬗变的研究思路,在对二者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又点明了其共通性。其二,注重开掘市民社会积极的一面。诚然,近代市民社会作为以私人所有为前提的商品交换领域,必然会出现异化现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形式。但市民社会派同时发现了异化在市民社会中的辩证含义:私人所有和分工的两面性。正如望月清司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研究》中所指出的, “外化=异化使人残缺不全,但是没有外化=异化人却无法成为类的存在”㉔。市民社会带来人的普遍交往,从而为人融入社会奠定了基础。其三,以市民社会理论为核心重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在市民社会派看来,市民社会是一个“历史贯通性”范畴,只有在对眼前的市民社会做出彻底的分析和批判之后,才能进一步追溯史前时期,并展望未来的人类社会㉕。望月清司和平田清明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完整地概括为“原始共同体—市民社会—人类社会”㉖。日本的市民社会派通过严谨的文本考证,确实赋予了以往被忽视的这一重要范畴以应有的理论地位,为市民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野。但该学派对于市民社会概念的研究也存在着矫枉过正的问题,比如人为地抽掉了市民社会中的“阶级因素”,片面地强调分工、交换中所蕴含的生产力因素,有从马克思向斯密倒退的嫌疑。
(二)重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文化维度的开掘
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开展及其成果的运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何以构建“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以抵抗国家权力的膨胀以及市场的“殖民”,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掀起了重释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热潮。葛兰西在市民社会中增添了文化和象征的维度,将视角从经济基础转向上层建筑领域,将传统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法改造为“经济—国家—市民社会”的三分法,指出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国家的基本认识离不开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因为人们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同时将市民社会视为政治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强调市民社会之于国家的堡垒作用。”㉗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就会立即显露㉘。哈贝马斯沿着葛兰西开创的方向继续对市民社会的问题进行探讨,虽然他也将文化领域视为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并没有将市民社会定位为政治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是将其规定为“非政府、非经济联系的自愿联合”㉙的私人交往领域,强调市民社会中商谈和交往的功能。哈贝马斯意图通过在市民社会这一公共领域的相互交流,促进社会中各个阶层的相互接受。柯亨、阿拉托同样也将市民社会视为不同于经济领域的“公共领域”,即“介于经济领域和国家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主要由家庭这样的私人空间、自愿性社团,以及社会运动所组成”㉚,同样强调市民社会促进民主交往以及集体认同的功能㉛。20世纪以来,市民社会概念经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文化维度、商谈维度、社会运动维度的三次重释之后,传统的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架构逐渐发展为国家—市场—市民社会的三重架构,同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已经呈现出两种各异其趣的路径。
(三)质疑: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经济主义”的批评
还有一些西方学者为了调和政治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保持市民社会的独立性,“支持新社会运动,或是支持市民社会反对国家的主张”㉜,并重申了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理解为“经济主义”的经典质疑,形成了三种基本观点。其一,将市民社会理解为纯粹的“经济关系”。爱德华·希尔斯认为马克思“将市民社会分解为经济基础”,并在生产方式的意义上理解市民社会㉝。查尔斯·泰勒同样认为马克思在观察市民社会时将注意力集中于商业或经济方面, “从纯粹的经济层面”界定市民社会㉞。基恩更是指出市民社会“消失在经济基础之中”㉟。这些观点实际上是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简化了原本丰富的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的含义。其二,认为马克思没有区分“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㊱,而是将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其三,从思想史的角度指出,马克思前期从经济维度上界定市民社会是致使市民社会理论在后来被其视为不成熟而放弃,代之以社会、社会关系等更加笼统的词语从而“消失”的主要原因㊲。以上三种观点虽然思路不同,但都意在通过这种经济主义的批判,掩盖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批判维度,以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模式模糊马克思原有的国家—市民社会的架构,削弱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之于现实的生命力。
总的看来,国外学者对于市民社会概念的再思考虽然是出于对“公共领域”独立性的关切和对现实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照,但客观上丰富了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现实意义。首先,通过对当代市民社会中问题的阐发,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矛盾与新变化,这对于推动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次,国外学者对于市民社会概念微观维度的发掘,对我们曾经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维度和商谈交往维度等方面的重视丰富了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对自愿性社团和社会运动的强调,拓展了市民社会概念的外延。但是不论是日本的市民社会派还是西方学者都有意忽视市民社会的阶级因素,将市民社会看作是同国家权力相对立的“独立”领域,没有意识到市民社会矛盾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片面地强调限制国家权力,真实意图则在于为自由市场的发展消除障碍因素。这种视野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所提出的解决市民社会问题的途径不可避免地具有理想主义色彩。
三、关于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研究的评析与展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探讨,在研究视域上经历了从聚焦早期“法哲学”视角到关注“经济学”著作的转向,日益符合马克思本人研究的思维脉络,逐渐发掘了马克思在解剖市民社会中表现出的批判精神;在概念内涵上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化,感知到马克思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多种意涵;同时注重文本考证和文本分析方法的引入,利用国际上最新的文本考证成果,使市民社会的研究更加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原貌。由此,我国对于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研究业已形成了一批较为厚重的研究成果。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个领域不需要继续深入探讨和研究了呢?答案是否定的。现有研究同样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其一,从纵向研究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生成,忽视了对于概念史的专门考察。不论是现有的研究将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生成分为两个阶段或是三个阶段,其考察重点都在理论的演进,而不在概念本身的形成与发展。因此,勾勒概念演变的线较粗,关注的面较广,仅仅对于市民社会多层含义做了表面的说明就浅尝辄止,而对于马克思如何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内涵逐渐丰富以及多侧面展开,市民社会概念不同逻辑之间如何相互交织等还缺乏有深度的、富有解释力的说明。
其二,从横向考辨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容易陷入抽象的、从词句到词句的争辩,存在着方法论的失误。事实上,现有的四种对于市民社会概念的不同理解都不是空穴来风,都可以在马克思的相关文本中找到支撑依据,暂且不论这些解读哪种更符合马克思的本意,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对于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是否应该仅仅停留于抽象的概念考辨。现有研究在理解和阐释这一概念时,虽然大多都发现了其多义性这一特点,但往往没有从历史性的维度认识市民社会概念,而将这个概念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对其作出“抽象化”的理解,从而容易将市民社会理解为“物质关系”在各个时代的具体化。概念本身只是思维抽象的结果,它的形成虽然有利于我们把握对象的“普遍本质”,但它只是手段,而不是终点。市民社会概念在马克思的思想演进中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不同含义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静态的抽象化定义难以反映这种变化之间的相互交织。所以,抽象的概念本身是具有局限性的。这就要求我们考察市民社会概念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个”思维节点,仅仅把马克思市民社会的概念按照“从具体到抽象”的下降逻辑, “归结”为经济基础。这种在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研究中普遍的做法,实际上是对于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的背离。
那么如何使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定位与称谓相符,从而回应“消失论”、 “等同论”的思想史争论呢?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马克思研究市民社会概念的重要方法,其对市民社会的考察经历了“感性直观—思维抽象—思维具体”几个阶段,才逐步把握了市民社会概念的本质与历史性。这就说明仅仅从某个单一视角考察其市民社会概念是不够的,而应当在研究中努力做到静态概念研究与动态概念史研究相结合。一方面,从静态角度注重比较研究的方法,区分市民社会概念、经济基础概念、资产阶级社会概念,避免因三者的交错与混用而造成市民社会概念的消失;另一方面,从动态角度把握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在不同时期何以相互转化,避免孤立地考辨概念而造成马克思思想“断裂”的印象。特别应注重考察马克思如何使市民社会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是理解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历史性的关键节点。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站在马克思思想“整体像”的高度,在考察不同阶段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基础上,得出其市民社会概念的完整定义,客观评价市民社会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切实探讨马克思何以穿过层层意识形态的迷雾,把握市民社会的本来面貌,从而以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观照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时代之问”。
注释:
①蒋红:《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②刘同舫:《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3—85页。
③刘荣军:《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现代社会转型与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8期。
④韩立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4期。
⑤张一兵、周嘉昕:《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认识——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谱系学分析》,《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⑥高广旭:《〈资本论〉对市民社会的 “政治哲学”重构》,《东南学术》2018年第4期。
⑦阎孟伟:《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市民社会概念》,《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5期。
⑧林金忠:《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得与失》,《学术月刊》2011年第3期。
⑨王新生:《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形成》,《南开学报》2000年第3期。
⑩罗雄飞:《“市民社会”及其在〈资本论〉中的逻辑地位(一)——兼与沈越教授商榷马恩著作的翻译问题》,《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3期。
⑪郁建兴:《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
⑫陈晏清、王新生:《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⑬毕秋:《“市民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吗?——〈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再解读》,《湖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⑭[日]城冢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 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肖晶晶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⑮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⑯韩立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4期。
⑰[日]重田澄男:《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卫华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2期。
⑱蒋红:《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和唯物史观的创建》,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⑲李佃来:《政治哲学视域下的马克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7页。
⑳魏传光:《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以市民社会为核心的考察》,《哲学研究》2020年第5期。
㉑李佃来:《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两种逻辑》,《哲学研究》2010年第12期。
㉒Adam Seligman,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New York,Free Press,1992,pp.56-57.
㉓㉔㉕[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114页。
㉖韩立新:《“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及其对当代中国的意义——以望月清司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为中心》,《日本学刊》2019年第2期。
㉗㉘[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194页。
㉙J.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1996,MIT Press,p.366.
㉚徐步华:《20世纪“市民社会”概念的三次重要转变:葛兰西、柯亨和阿拉托、哈贝马斯》,《世界哲学》2019年第3期。
㉛邓正来、 [英]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
㉜㉟Neocleous Mark,From Civil Society to the Social,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95,46(3),p.395,p.401.
㉝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载邓正来、[英]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㉞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载邓正来、[英]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㊱Kumar,Krishan,Civil Society:An Inquiry into the Usefulness of an Historical Term,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93,44(3),p.377.
㊲G.Hunt,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in Marx,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1987,8(2),p.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