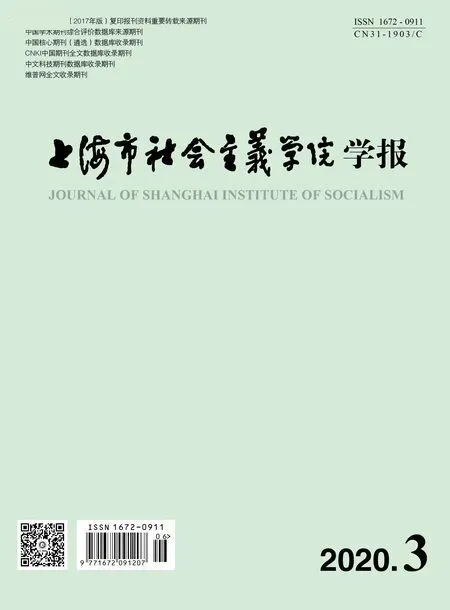习近平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
吉秀华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济南250399)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 也是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 的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多党合作制度的精神内涵, 拓展了多党合作的理论向度, 彰显出新时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制度自信,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价值。
一、 习近平深刻阐明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 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新型政党制度, 从根本上来说,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 在东西方政治文明的交流碰撞中, 历经劫难、 屡次试错之后才找到的一条正确新路。
(一) 多党制试验失败与一党制破产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创建, 拉开了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序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的制定和颁布, 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人民 “言论、 结社、 出版自由”, 掀起了组党热潮,一时间“集会结社, 犹如疯狂, 而政党之名, 如春草怒生”[1], 形成民国初年特有的“政党林立” 时代和纷繁复杂的“政党政治” 现象。 各政党围绕国会选举和组织责任内阁展开了激烈角逐, 试图在中国建立起西方竞争型的政党制度。 从1912 年12 月至1913 年2 月, 经过两个多月的明争暗斗, 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大胜, 似乎给议会多党制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 不幸的是, 国民党选举的胜利并没有奏响资产阶级议会政党政治的凯歌。 1913 年3月, 宋教仁被暗杀, 打破了国民党议会政党政治的幻想。 1913 年10 月6 日, 议会进行了总统选举,袁世凯成为经过选举产生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随后, 袁世凯为了给复辟帝制扫清障碍, 下令解散国民党、 取消国会、 撕毁约法。 至此, 资产阶级议会政党政治的试验宣告失败。 1927 年4 月18 日, 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 开始实行“一个政党、 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 的一党专制。蒋介石将孙中山的“以党治国” 歪曲为排除其他政党参与的国民党一党独揽的 “一党治国”。 坚持一党独裁, 坚持发动内战, 置一党私利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 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反对和背弃。 最终, 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统治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被推翻, 这也意味着一党专制模式在中国的失败和破产。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确立
经过反复比较、 借鉴和探索, 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实现民族复兴、 国家富强的革命征程中, 共产党人不仅确立了自己的领导核心地位, 而且通过执行正确的联盟政策, 形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倡导建立包括各阶级、 阶层、 政党、 政团等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 1940 年,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 革命政权, 将共产党与民主人士在政权中的合作由政治设想变成政治现实, 并把它上升到战略高度。 正如毛泽东所说: “国事是国家的公事, 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与这个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 永远不变的。”[2]
1944 年9 月, 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由各抗日党派、 各抗日军队、 各地方政府、 各民众团体共同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初步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的构想。 但是,这一政治构想屡遭国民党反对, 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 内战爆发, 中国共产党只能依靠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在人民解放战争行将胜利的关键时刻, 中共中央于1948 年4 月30 日发布了著名的“五一口号”, 号召“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 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 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1949 年9 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中国人民对政治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 这一制度选择在长期的革命、建设、 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 并经过实践检验,符合中国实际, 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 是当代中国人民制度自信的历史根源和合法性基础。
二、 习近平深刻阐明了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指出, 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源头和立论基础, 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 使命与资本主义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 从而在斗争策略、 组织原则、 政权建设、 政党执政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上显示出与西方政党制度截然不同的本质特征。 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 执掌政权、 巩固政权这一政党政治的核心命题, 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基本原理、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民主集中制理论, 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 马克思主义政党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的基本原理是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源头。 马克思主义认为, 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政党是由本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 先进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求和典型特征。 与资产阶级政党只代表部分阶级、 阶层的利益要求不同,无产阶级政党所进行的一切活动, 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马克思、 恩格斯指出: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3]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不同的利益, 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4]。 共产党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和前提, 也是区别于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根本特征。 共产党自身的先进性和人民性决定了共产党领导不仅仅是执掌国家最高行政权力, 而是对整个国家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各个方面的全面领导, 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掌舵人,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国家政党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本质, 能够真实、 广泛、 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和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 有效避免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 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
(二)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 彻底打碎一切旧的国家机器, 这对于处于经济文化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讲, 无产阶级政党还承担着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任务。 与西方政党理论“国家来源于社会, 社会决定国家” 的社会中心论不同, 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是一条“以党建国” 的历史道路, 是无产阶级政党缔造了现代国家, 实现了民族独立而后领导并推动整个国家建设。 因此, 无产阶级政党关于政权建设的理论必然要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 这是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区别于西方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展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人民民主专政本质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 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 包括一部分爱国的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联合政权。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 中指出: “团结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 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 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5]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成为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的同盟者和亲密战友, 成为民主与进步力量的代表,为联合政权的建立奠定了政治基础。 多党合作的联合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化创造和具体实践形态。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性质,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政党制度的核心价值、 结构要素和制度特征。
(三) 民主集中制理论
现代政党因民主而生, 政党、 政党制度都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 无产阶级政党在自身建设过程中就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组织原则, 把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作为重要目标。 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也是国家政权建设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指导原则。 1940 年1 月, 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 中明确指出: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政体——民主集中制。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6]。 1945年4 月, 毛泽东在 《论联合政府》 中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 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 选举政府。 它是民主的, 又是集中的, 就是说, 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7]民主集中制渗透到中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政党制度上体现为共产党一元领导的核心性与多党派合作的多元性, 是民主与集中、 集权与分权的制度设计与安排, 这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 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有着根本不同。 民主集中制的核心价值和运行规则决定了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广泛民主与高度集中的统一, 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又能有效避免一党缺乏监督、 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和多党轮流坐庄、 恶性竞争的弊端。
三、 习近平深刻阐明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根脉
新型政党制度是优秀中华文化滋养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 植根于中国优秀文化土壤之中, 有着独特的文化基因和鲜明的民族特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 新型政党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 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 兼容并蓄、 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 “天下为公” 的价值追求、 “大一统” 的政治理念、 “和而不同” 的精神特质共同铸造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根脉。
(一) “天下为公” 的价值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天下为公” 的价值追求。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治国安邦的方略。 重集权、 尚整体的家—国—天下秩序是中国政治建构的起点和政治制度的基因。 在家—国—天下的政治逻辑里, 以权力—责任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政党、 政权必须最大限度地考虑整体利益而非个人、 部分的利益。 因此, 在中国, 国事是众人的事, 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 中国的政党只能为公、 不能为私, 只能代表国家民族利益, 不能只代表少数人、 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 中国各民主党派组建政党, 也不是为了一党之私, 而是出于救国救民的民族大义。 在“天下为公” 的价值理念下, 各民主党派在成立初期尽管秉持着不同的政治理想, 存在政见分歧, 但是在救国救民、 实现民族独立、 国家富强的目标上是一致的, 都没有各个党派自己的私利。 因而, 能够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政治理想的汇流和政治理念的互相融合、 共生。
(二) “大一统” 的政治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 “大一统” 的核心价值理念。 统一不仅是中国五千多年历史的主流和客观现实, 而且已经内化为中华人的政治理想和信念, 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民族性格养成和政治模式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的主要思想流派, 均有着“大一统” 的思想元素, 并最终通过几千年的意识形态发展、 伦理教化和制度实践, 成为历代主流价值和全民共识。 在 “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下, 中国政治制度、 政党制度的选择必然是一个以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为核心、 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 以维护团结统一为目标的命运共同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维护团结统一的大目标下, 既能够维护整体利益, 又能够兼顾各方利益, 有效避免权力分立带来的政治分裂和社会撕裂。
(三) “和而不同” 的精神特质
中华文化具有“和而不同、 兼容并蓄” 的宽广胸襟。 “和合” 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和内核。 “天人合一” “和合而谐” “和而不同” 对中国人的处世规范、 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社会的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早在春秋时期, 《国语·郑语》 就记述了史伯关于和同的论述, “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 晏婴和孔子又进一步把这一思想发展为 “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 的理念首先在于 “和”, 强调一致性。 在政党制度上, 体现为各政党根本利益和政治目标的一致性, 强调的是合作、 协商、 共赢的理念。 “不同” 兼顾的是政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通过协商, 最大限度地把“不同” 凝聚为最大公约数, 实现一致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 通过广泛协商、 广泛听取意见建议、 广泛接受批评监督, 达成最广泛的决策和共识, 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互相倾轧、 固执己见、 排除异己的弊端。
四、 习近平深刻阐释了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新型政党制度契合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需要强有力政党领导、 整合社会、 推动发展、 坚守文化传统的需求, 实现了政治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是对旧式政党制度的超越, 具有自身独特优势。
(一) 与中国历史上政党制度相比, 体现出鲜明的政治现代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政党及政党制度都是现代化的产物, 政党与政党制度伴随着现代化的发生、发展而不断改变自身功能结构、 组织形态、 活动方式, 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 任何政党尤其是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 只有适应现代化发展潮流, 不断增强自身的适应性、 包容性和开放性才能充分发挥自身功能, 更加有效地影响政权和政治运作。 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调整、 适应、 选择的结果。 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裹胁着加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之中, 民族独立、 经济富强、 政治民主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首要目标。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只能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领导中国的现代化。 在各种各样的政党试验中, 之所以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因为这一制度能够更加有效地凝聚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 实现社会的高度整合。 近代以来, 在现代中国建构过程中, 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四万万人如一盘散沙”。 民国初年, 虽然政党多如牛毛, 但各自为政、 各行其是, 给中国带来军阀混战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立足于中国复杂的阶级阶层结构, 在不同时期制定不同的联盟政策, 把不同政党、 不同民族、 不同阶层的人有效凝聚在实现民族独立、 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的旗帜下, 解决了社会分裂和动荡问题, 实现了政治和社会稳定。 同时, 这一政党制度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相比, 充分考虑代表广大中间阶层利益的各民主党派, 重视“多党” 存在的价值, 不搞“党外无党” “一党集权”, 而是创造性地将“一党” 和“多党” 以合作协商的方式结合起来, 形成了“共产党领导、 多党派合作” 的新型政党格局, 有利于形成稳定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秩序。 稳定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秩序恰恰是发展中的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 与中国历史上的政党制度相比, 新型政党制度既确保了权威性核心领导, 又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社会整合, 契合了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需求, 更具政治现代性和民主性。
(二) 与西方历史上的政党制度相比, 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质
政党、 政党制度起源于西方, 是西方议会政治发展的产物。 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大多数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议会和总统选举过程中逐步形成、 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通过竞争性选举取得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和政治资源的分配是其典型特征。 西方学者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出发, 认为在一个由公民、 政党与政府组成的政治市场中, 同样存在竞争。 政党总是代表了“部分” 人的利益, 不同的政党为公民提供不同的政策方案, 而民众总是选择能够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同, 不同政党之间必然展开激烈的竞争。 竞争体制下的政党联盟从本质上讲是基于相似利益要求而结成的权宜组织, 一旦政党间利益发生冲突,政党间的合作就会发生破裂。
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固有的模式, 以合作协商代替倾轧竞争, 以 “执政-参政” 代替 “在朝-在野”; 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 共产党执政、 各民主党派参政,共同担负起建设国家的责任。 这种合作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奋斗目标基础之上, 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政治基础和制度基础。 各民主党派在多党合作制度框架内, 具有参加政治协商、 参政议政、 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渠道, 合作对象固定, 合作关系稳固而持久, 合作内容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执政与参政相结合、 领导与被领导相统一的政权运作方式, 形成了全新的和谐共生的合作性政党关系。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融合了不同政党制度的稳定性、 监督性等优点, 又体现了自身的主导性、 包容性特点, 体现出“中国模式” 独特的制度优势和效能。
总之, 习近平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论述, 立足中国政党制度70 年的政治现实和实践经验, 深刻阐明了中国政党制度深厚的历史基础、 理论根基、文化根脉、 独特优势, 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气派、 中国风格的政党制度理论体系, 打破西方政党理论话语霸权、 提升中国政党制度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新型政党制度所展现出来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与不断表现出意识形态淡化、 选民基础薄弱、 党员数量减少、 基层组织萎缩等衰弱迹象的西方政党形成了鲜明对比。 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集中统一领导与广泛政治参与相统一、 国家稳定与社会进步相统一、 激发活力与富有效率相统一的 “中国之治”, 与多党竞争和多党制下的“西方之乱” 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个“鲜明对比” 充分说明, 新型政党制度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全面超越, 它不仅契合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现实政治需求, 同时也引领中国未来发展、 影响国家前途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