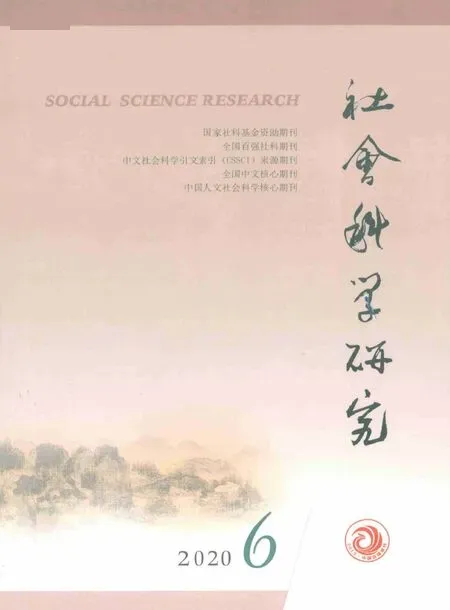资源下乡背景下城乡基层治理的四个命题
贺雪峰 田舒彦
一、引论
当前学界关于城乡基层治理的讨论很多,这些讨论呈现出一些共识,即城乡基层治理效能不高,形式主义现象繁多,痕迹管理过度,缺少对群众的组织,造成村居民自治的丧失。这些讨论十分重要。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当前城乡基层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城乡基层治理问题症结或根本在哪里?如何解决当前城乡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初步讨论。
按黄宗智的说法,城乡基层治理是国家与社会的第三领域。国家治理有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等级体系,行政建制所至均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建制内,中央对地方是上级对下级的关系,下级被纳入国家行政这个体系中,服从上级指挥。国家治理体系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体系内工作人员是公务员,或者至少是事业编人员,拿着国家财政工资,具有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可以在体系内升迁。国家以外的社会具有与国家不同的运转机制。社会有社会运转的规律,是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由市场关系、家庭关系、私人关系、社会组织等等构成,这些都是依照国家法规自行运作的,在此之中人们自己对自己负责,自行得失。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黄宗智所说的广泛的第三领域,城乡基层治理就属于这个第三领域范畴。①城乡基层治理的主体就是村居委员会,对应到城市就是社区,对应到农村就是行政村或村委会。按村居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和居委会干部都是由村民和居民通过选举产生的,没有行政编制,不拿财政工资,更不纳入国家公务员系列。
笔者以为,要理解基层治理应当特别注重讨论与基层治理相关的四个命题:
第一, 基层治理国家化趋势。伴随越来越多国家资源下乡的,是自上而下的规范下乡、程序下乡、督查下乡,基层治理也因此越来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部分,甚至村居干部也越来越行政化甚至半公务员化了。
第二,基层精准治理的悖论。自上而下转移到基层的资源如何使用,能否达到国家投入资源的目的,以及能否得到有效使用,是国家必然要关心的问题,因此,要求基层治理精准有效,不能粗疏低效。在实践中,要求精准就逐渐成为要求标准化和指标化,因为只有标准化,上级才能比较方便地对基层治理是否精准进行考评。问题是,基层治理要精准,治理行为就必须要针对基层实际情况,就必须因地制宜。因为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情况十分复杂,基层事务尤其复杂,难以用统一且内容封闭的标准和指标体系来要求和衡量,所以因地制宜必然会与标准化和指标化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基层精准治理的实践有两种,一种是标准化和指标化,另外一种是因地制宜。而这两种实践很多时候是相互冲突的。实际上第一种只是手段,第二种才是目标,是真正的精准治理,在实践中出现了手段对目标的替代。运用标准化指标化的精准手段是有条件的,若忽视这个条件以偏概全、一概而论,那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基层精准治理。基层有效治理只可能依赖基层好干部与基层群众自组织,当然这又依赖于一个好的基层治理制度设计。不调动基层治理主体的内在积极性与主动性,基层治理主体丧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主体性,基层有效治理就是困难的。将适用范围非常有限的一种手段作为精准治理的全部,却忽视精准治理的条件,是行之不远的。这个命题可以叫做基层精准治理的悖论。
第三,基层治理的根本在于群众自治。基层治理实际上可以分成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为群众服务,第二重境界是在为群众服务的过程中提高服务能力,第三重境界是组织群众自己为自己服务。目前基层治理最大弊端之一是只讲为群众服务,不讲依靠群众,组织群众,结果是基层治理做了很多好事,却未得到群众的好评,甚至使群众形成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使基层治理中边缘群体崛起。
第四,基层干部的角色定位问题。之前一般将基层干部定位为“当家人”与“代理人”,“代理人”就是村居干部都是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协助国家完成需要在基层落实的各种任务,尤其是汲取资源的任务。不过,当前在中国基层治理中,村居干部一般不再向居民汲取资源,其作为国家在基层“代理人”的角色似乎不再显著。从这个意义上讲,再说基层干部是“当家人”和“代理人”,似有不妥。按照当前国家对基层自治的定位,基层干部是为居民服务的“服务员”,村委会和社区都设立了党群服务中心,村居干部为群众提供“坐堂服务”和上门服务。当然,基层干部显然不应当只是服务员,而且应当组织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的美好幸福生活。
二、国家资源下乡与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以取消农业税为界,中国基层治理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取消农业税前,国家要通过基层组织向农民汲取资源,表现在村级治理中,村干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协助县乡完成税费收取和计划生育任务。只要能完成协税和计生任务,村干部在基层治理中采取什么办法是不重要的。或者说,在取消农业税前,村干部最重要的工作是完成国家任务。因为不同地区情况差异很大,很难制定统一的工作方法和要求,所以只要不违法乱纪就可以,村干部对用什么办法来完成国家任务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取消农业税前,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主要依靠“三提五统”、共同生产费和“两工”(积累工和义务工),通过向农民筹资筹劳来保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有些村庄筹资筹劳效果好,村庄就有良好生产生活秩序,村民生活生产就比较便利。一些村庄筹资筹劳效果差,村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难以维系。在这段时期,农民负担持续上涨,干群关系日益紧张,村级债务迅速攀升,“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不仅国家越来越难以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而且村庄也越来越难以筹集到保障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公共品建设资源。
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村干部也无法再通过搭国家税费便车来收取共同生产费,且国家取消了“三提五统”。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唯一筹资渠道是国家规定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通过一事一议按每年每人不超过15元的标准筹集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经费。因为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程序复杂,缺乏强制性,结果就是几乎全国农村都没有真正落实“一事一议”,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品供给出现了严重短缺。
为解决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国家开始实施民办公助,以奖代补。村集体建设公共事业可以向国家申请支持,村民自己花钱建设公共品,国家提供一定补贴。②结果,因为无法向农民筹资,村庄建设公共事业越多,负债越严重,一些经济实力强的村庄却可以轻松获得国家补贴。越是公共品供给完善的村庄越能获得国家补助,越是公共品不完善的村庄越难获得国家补助。这显然无法解决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维系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尝试,现在国家通过项目制和一卡通向农村输入资源,且几乎每年都增加向农村的资源输入。也就是说,在取消农业税前,国家向农村汲取资源,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仅不再向农村汲取资源,而且通过各种方式、途径向农村输入资源。
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自然希望资源有最高的瞄准率,因此倾向通过两种方式向农村输入资源:一是“一卡通”到户;二是通过项目制,由国家部委直接来为农民提供公共品,比如土地整理、乡村公路修建,皆由条条直接安排,通过项目招标由有资质的公司来完成,村干部甚至乡镇干部不得插手,也不必经过乡村干部。
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越来越多,且越是国家输入资源,农民就越是等靠要。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时尽可能不经过乡村干部之手,以防止乡村干部的挪用、贪占。不过,有一些项目不得不通过乡村干部,比如低保指标分配、扶贫资源落地,都建立在识别出低保户和贫困户的基础上,而低保户和贫困户识别其实是有一定困难的,这就给了乡村干部上下其手的可能。由国家直接在村庄实施项目,项目落地时必然要与村民发生关系,也就会有钉子户借机向项目工程队索要超额补偿,村干部也因此要介入进来。
在国家要通过村干部汲取资源时,国家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能否顺利完成资源汲取任务,其次才关心用什么方式办法完成任务。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不仅不再从农村汲取资源,而且向农村输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国家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向农村输入资源的安全和效益,关心这些资源是否真正惠农了。
为了保证资源下乡的安全,国家每项下乡资源都会有相应的使用要求,因此,资源下乡的同时也必然是规范下乡、程序下乡,比如涉及公共资源的分配,几乎所有农村地区都强调“四议两公开”,强调程序与公开性,强调民主决策与监督。更重要的是,随着规范下乡、程序下乡的是督查下乡,各种自上而下的督查下乡,对资源使用、对村干部管理、对各种村级事务都提出了要求,村干部必须要按上级要求的程序、规范来完成工作。甚至村干部为村民提供服务也由上级来考核评估,村干部的待遇当然也与上级对任务完成情况的评价相关。
资源下乡所带来的规范下乡、程序下乡和督查下乡,使得村干部主要工作由之前以回应村民诉求为主的实质治理,变成了应付上级检查的形式治理。村干部必须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且要按上级规定的程序和规范完成,即使这些任务往往与村庄实质治理没有关系,村干部也不得不认真应对。结果就是村级治理中有了越来越多的规范、越来越多的办事留痕、越来越多的形式主义,村干部主要工作不再是回应村民诉求,而是应付上级检查,填表报材料。
因为国家不再需要村干部协助向农民汲取资源,反过来倒是村干部工资待遇都是由国家财政资金支付,且村庄建设资源都是由国家财政提供,国家就有了对村干部更大的管理权限,这种管理权限表现在对村干部具体工作过程的约束上。其中典型表现如全国很多地区农村都出现了上级要求村干部坐班,并要求村居设立党群服务中心,由村居干部坐堂为群众服务,组织部门、纪检部门定时抽查,凡是未按时上下班就纪律处分,扣工资。实际上,农村工作季节性很强,村干部本来就是不脱产的,强制要求村干部坐班,可能完全不适合当地农村实际,造成了不必要的形式主义。
当把村干部是否为村民服务纳入国家对村干部的考评,村干部为群众服务不是因为群众需要而是上级要求,不同地区情况又千差万别的时候,各地村居干部为通过考评而按照上级统一要求向群众提供服务,结合每个村居具体情况来看,就会显得特别不符合当地实际,就显得特别形式主义。这样的形式主义泛滥开来,就成为见惯不怪的现象。当前中国农村基层的这种形式主义已经严重影响了基层治理的效能。
遗憾的是,国家资源下乡背景下,基层治理效能未能得以提高,基层治理形式主义泛滥,这是当前基层治理应当重视的第一个问题。
三、精准治理的悖论
无疑,精准治理非常好,是可以用最少资源达到最大治理成效。如果能做到精准治理,我们就可以说基层治理不只是现代化了,而且也必定是十分完善的了。
问题是,精准治理往往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要达到精准治理其实是很有难度的。对精准治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精准治理包含着两个相互冲突的层面。一个层面是治理内容、方式、目标的标准化和指标化,没有标准化、指标化,就不可能有精准治理。基层治理是否精准,归根结底要由上级来进行考察评估,上级考察评估必须要有治理内容、方式、目标的标准,并且是指标化的标准,这些指标还必须具体,不能含混模糊。另外一个层面则是要求基层治理必须要符合基层实际情况,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两个层面实际上表现出对精准治理的两种理解。一种将精准治理理解为可精确量化的治理,通过将治理任务和考评操作化为各种标准化指标来治理,“精准”表现为治理行为可以由数字或类型表达出来的可测量性、简洁性和可比较性。一种是因地制宜地解决治理问题,“精准”表现为治理目标与治理需求的高匹配度,治理行为对实现治理目标的高有效性,这种精准的实现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前一种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具体的治理方法,后一种精准解决治理问题才是实质意义上的精准治理,在实践中两者不一定能统一。有的治理问题适合于用标准化指标来量化的方法,例如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理解就可以在实践上统一。但是绝大多数不适宜用这种方法,治理现象的可量化程度有限,尤其是广大范围内的统一量化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表现为两种理解在实践上的冲突。而且任何一种标准化指标实际上都是对复杂现实的简化表达,其所能涵盖的情形是有限的,为了尽可能容纳更多情形,会有不断复杂化的倾向,相应地会导致这种方式越来越不经济。
不考虑治理现象可标准化指标化程度的有限性,而无限使用这种方法,就会呈现出精准治理以上两个层面之间的冲突。其冲突性在于,要求基层治理精准,一方面试图对几乎所有地区所有治理事务制定统一标准,设计一套具体指标,以获得直观且方便比较的结果,不然就无法判断基层治理是否精准;另一方面在中国基层情况极其复杂的现实条件下,真正的精准治理一定是符合地方实际的,也一定要因地制宜,有效的治理往往不能被统一标准所容纳,不能被具体指标所衡量。只要因地制宜,基层治理就会表现出复杂性,就要讲条件,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必然造成与基层治理是否精准的标准化、指标化的冲突,即全国不可能用一套清晰、简化和具体的标准与指标体系对基层治理是否精准进行考评,无限可能的实际情况不能被有限封闭的标准化指标所精准描述。
没有办法对全国基层治理是否精准进行标准化指标化的形式化考评,就只能对基层治理进行实质考评。实质考评存在的问题是,基层治理牵涉因素太多,对是否精准进行实质考评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每个治理决策和过程都可以找到理由,每件看起来不够精准的治理都可以找到借口。要对基层治理是否精准进行实质评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要对全国所有基层治理精准程度进行排序就更加不可能了。
达到精准治理目标有两条不同的进路,一条进路是自上而下提要求,并自上而下进行考评。在当前国家资源下乡的背景下,国家为了下乡资源的安全、有效,也一定要有规范下乡、程序下乡和督查下乡。国家自然就会制定出标准化的指标体系来要求基层治理。问题是,自上而下对基层治理制定的标准面临着尴尬的处境,这就是标准过于具体明晰就可能不适合基层实际,若强制要求基层按标准来治理,基层治理不仅不标准,而且必然会做形式主义工作,以应付上级核查,结果是高度不精准。如果标准过于宽泛模糊,基层治理就可能有太多缝隙,基层有太大自由裁量权,上级对基层治理是否精准就很难考评。
另外一条进路则是自下而上实践的进路,即给基层治理以自由裁量权,允许基层治理中的因地制宜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即基层治理中的任何过失几乎都可以找到借口,上级很难对基层治理的有效性进行评估。这显然也无法达到基层治理的精准。
在基层干部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认真负责的精神,没有主体性的情况下,以及当基层干部没有真正干事创业激情且没有对上级任务和群众诉求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进行落实的能力时,基层精准治理是不可能的。基层治理有效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有真正负责任的基层干部,他们不是应付上级与群众,而是积极主动以饱满热情倾尽智慧来完成基层治理任务。
现在的问题是,当基层干部积极主动因地制宜进行治理时,完全有可能因为一个工作环节有瑕疵,上级追责而被处分。尤其是在上级明确要求精准治理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治理方面的瑕疵或任何一个环节对上级标准的偏离都可能造成不规范,都可能成为过失,都可能成为处分的理由。要求基层治理精准,自然而然就不能容忍偏差,出现偏差就要处分。基层干部为了防止被处分,当然就不愿意在开展治理工作时因地制宜,而会从自我保护角度出发,应付上级,做出完美的形式,而不会顾及治理效果。
因为精准治理是很难完全做到的,而上级以精准治理的标准要求基层并对基层干部进行考评,进行督查,所以基层任何工作都不可能经得起这样的考评:严格按上级标准开展工作就可能不符合基层治理实际,因地制宜又可能超出标准要求,真正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上级在督查中找到任何一个过失并进行责罚都让基层干部委屈,他们认为上级求全责备,自己是无心之过,且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是否被上级追责只能看自己运气是否足够好,运气不好被追责了也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基层干部是不可能有干事创业积极性的,最安全的做法是应付上级,不出事,搞形式主义。这样一来,上级要求基层精准治理的结果是基层治理形式主义越来越严重,应付上级的表面工作做了很多,真正服务于基层群众的治理工作却少之又少。大量国家资源投入到基层治理却几乎无效。
试图通过自上而下强有力的督查来保证基层治理精准,结果只可能反过来更加不精准。原因是强有力的上级督查令地方和基层人心惶惶,将应对督查和对上负责放在第一位,而绝对不敢真正因地制宜创造性地结合基层实际进行治理。各种形式上合理却完全不符合地方实际的基层治理反而会因为精准治理的要求而大量发生了。
因此,我们一定要理解,精准治理首先是一种理想状态,是理想目标,实际治理中总会有不够精准的地方。只有允许基层治理有不精准,给基层治理一定容错空间,基层治理才会出现各种创造性转化,才能够结合基层实际进行因地制宜的精准治理。
四、基层治理的根本在于群众自治
如前已述,基层治理可以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就是为群众服务,这也是最基本的。如果基层治理不能为群众提供良好服务,不能增加群众的获得感,不能解决涉及群众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问题,基层治理显然就不可能是好的。
为了增加群众获得感,给基层群众提供更多服务,当前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想了很多办法。可以说,在为群众服务方面,无论城乡都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从资源投入来讲,每年国家投入到农村的资源总额早已超过2万亿元;从服务方式上讲,为基层群众服务可谓是全覆盖且有相当高的强度了。
我们可以具体列举几项:
精准扶贫,不让一个人掉队,所有贫困家庭都必须在2020年脱贫;
城乡低保,应保尽保;
党群服务中心,为城乡居民提供一站化、坐堂式服务;
市长热线,所有涉及民生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市长热线向上反映,市长热线将群众诉求派单到相关部门,大概率会派单到基层社区来办理;
花钱买服务,比如由国家出钱雇请社工为城乡居民提供各种服务,再比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民医保、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设施方面如乡村道路建设、清洁乡村运动、农村厕所改造、清洁用水工程等等。
应当说,取消农业税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国家向城乡基层投入大量资源,为基层群众提供了大量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居民获得感明显增强了。
在当前基层治理中,基层组织为群众做了很多好事,提供了很多服务,其服务能力却似乎没有同步上升。本来应该是,随着大量国家资源投入到农村,国家通过基层组织为群众做了事,基层组织也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了服务能力,钱下去了,基层组织能力上来了。实际情况却远没有这么乐观。
因为强调为群众服务,所以花钱买服务逐渐成为基层治理中比较普遍的行为,比如城市社区花钱买社工服务,社工组织来社区提供几次服务就走了,社区组织能力没有任何提升。与其花钱买社工服务,不如由社区干部来为群众提供服务。社区干部提供服务,与外来社工机构最大的不同在于,社区干部是在地的,他们通过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进一步熟悉居民,只有熟悉才能提高服务和管理能力。
再比如,市长热线是基层群众反映诉求的一个渠道,居民有诉求打市长热线,市长热线将诉求转到社区并进行督办。这当然有助于解决居民诉求,不过却不能提高基层组织的服务能力,反过来倒是让基层社区陷入应付各种琐事中了。其中原因是,打市长热线成本为零,居民通过市长热线反映诉求,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社区越是满足各种不合理要求,就越是会助长群众提出不合理要求的行为。
在由国家为基层群众提供免费服务的过程中,有两个群体特别注意,一个群体是钉子户,试图借国家资源下乡来捞一笔好处,另外一个群体是困难群众,他们尤其需要来自国家的帮助。无论是钉子户还是困难群众,一般来讲都是这个社会相对边缘的群体。国家下乡资源越多,为基层群众提供的服务越多,基层社会中以钉子户和困难群众为代表的边缘群体所得好处就越多,基层组织就越多与边缘群体打交道。
因为资源是国家的,有空间可以争取,所以为了获得更多好处,边缘群体一般倾向力争,甚至通过上访斗狠来谋取好处,结果是好哭的孩子有奶吃,越闹越得好处。之前社区中的边缘人群通过以闹获利,显示出其争夺资源的能力,逐步成为基层社会中的主流人群,在此示范下,之前的社区主流人群也就变成钉子户,越来越多社区群众开始提出不合理诉求,以争取更大好处或应得利益。在与钉子户的死缠烂打中,基层组织主要精力用于应付越来越多不合理诉求。
也就是说,如果片面强调基层群众获得感,在大量国家资源落地时,就会出现为争夺国家资源而来的各种不合理诉求。既然是免费资源,既然是按闹分配,这就鼓动所有基层群众加入提不合理诉求的行列,基层治理也就越来越变成与不合理诉求的死缠烂打、斗智斗勇,变成应付边缘群体,而难以组织主流群体,及无法开展积极主动的工作。
基层治理中的一个关键是借为群众服务来熟悉群众,掌握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防止基层组织被少数边缘群众绑架,提高为群众服务的能力。这是基层治理的第二重境界。
基层治理的第三重境界则是组织群众自治,就是说,基层组织为群众服务,在服务中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都是十分重要的,却又是不够的。基层社会还应当是自治的,因为基层社区是城乡群众生活环境所在,社区状态与他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
一般来讲,国家资源下乡,应当是资源下去了,基层社会组织能力上来了。不能变成国家资源下去了,基层群众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更加严重了。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一个重大弊病就是过于强调为群众服务,较为忽视提高基层组织为群众服务的能力。更重要的则是,无论是为群众服务还是提高为群众服务的能力,都只是在做“一切为了群众”的工作,还未真正达到“一切依靠群众”,只讲为群众服务,却未重视将群众组织起来,让他们自己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
基层治理事务绝大多数都是各种琐碎事务,这些事务边界模糊、性质暧昧、高度敏感、难分对错,无法靠法律解决,市场又不供给,正规体制难以介入,这就需要由社区自身的组织能力来解决。因为社区建设与社区居民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就有责任和义务自己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
城乡基层组织要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将基层群众组织起来,让他们来建设他们自己的美好生活,不应越俎代庖、替代群众、包办本应群众自己去做的事情。同样,国家也不应总是替代基层组织去供给城乡基层公共品,而应当让城乡基层组织通过供给公共品来提高他们的组织能力。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基层治理就应当关注三件事情:第一,要认识到基层社区是共同体,这个社区共同体是不同于国家又不同于个人的,是社会自治的领域;第二,要将社区中的积极分子发掘动员出来成为社区主导力量,应当培养社区积极分子和调动社会积极分子建设美好家园;第三,要充分认识到社区自治的难题,不要以为仅仅自治就可以搞好建设,比如城市小区是陌生人社会,其中业主委员会就很容易被少数黑恶势力控制,这个时候社区基层组织如何指导小区建设就大有文章可做。
简单地说,基层治理的最高境界是群众自治,由群众组织起来建设他们自己的美好生活。当然,群众自治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城乡基层组织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群众组织起来自己管理好自己。国家资源下乡不应当只是为群众服务,而且尤其应当服务于提高城乡群众的自治能力。
五、基层干部的角色
徐勇将村干部角色定位为“当家人”和“代理人”③,在取消农业税之前,这个角色定位是有道理的。村干部当家人的角色是说,村干部是由村民选举的,是村民自治中的组织者。一直到现在,中国城乡基层仍然是自治的,也就是说,村干部仍然是“当家人”。村干部代理人的角色主要指,在取消农业税前,村干部十分重要的工作是协助县乡完成“计划生育和税费收取”等国家任务,尤其是要协助国家收取税费,这是近代以来中国赶超型现代化时代要求的必然。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仅不再从农村汲取资源,反而有越来越多资源下乡,村干部早已没有了协税任务,这个时候再叫村干部为国家代理人似有不妥。当然,即使国家不再向农村汲取资源,也并非就不通过村干部来完成国家任务,比如计划生育仍然没有取消,各种农村信息还要通过村干部上报,国家政策也要通过村干部传达,甚至国家各种惠农资金都要通过村干部分发,所以,说村干部仍然是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也不是不行。
不过,显而易见,当前时期,即使说村干部仍然身兼“当家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角色,这双重角色的内涵也与过去有了极大的不同。正是因此,我们也可以另外赋予村干部两个角色,以更加清晰地定位村干部和城乡基层组织。
我们来考察一下当前村居干部的主要工作。显然,当前村干部不再向村民收取税费了,反过来,村干部主要工作是做好国家资源下乡的服务工作,以及为村民提供各种服务。在取消农业税之后,曾经有一段时期,村干部要通过“一事一议”来向村民筹集公共事业建设经费,目前“一事一议”早就事实上停止了,国家转移到农村的资源超过“一事一议”资金很多倍。
国家资源下乡是要为农民提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以达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村干部主要工作因此不再是协助国家向农民收税,而是协助国家向农村转移资源,服务好农民。从一个方面讲,村干部协助国家向农村转移资源,看起来也是国家的代理人,不过,这个国家代理人是要服务农民,因此,将村干部叫做国家代理人,不如叫做国家在城乡基层安排的服务员更合适。
实际上,当前全国城乡基层都设立了党群服务中心,由村居干部坐班,坐堂为群众提供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看,称村居干部为服务员还是比较合适的。这个服务员既是村民选举出来的,又是国家认可的,待遇往往也是由国家财政支付的,虽然普遍不高。
村居干部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当家人”,不过,这个“当家人”越来越难当家了,因为在国家资源下乡过程中,边缘群众争利导致村居干部陷于他们的死缠烂打中。村居干部与其自己当家,不如组织群众当家,尤其是发动群众形成村居自治中的积极分子,限制群众中的恶意行动者,利用国家资源提高基层社会动员能力和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村居干部是当家人不如说村居干部是“组织者”更为合适。
从当前基层治理的理想状态来看,村居干部应当同时身兼“服务员”与“组织者”的两重身份。不过,在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村居干部更多的只是当了“服务员”,较少去做“组织者”的工作,偏重“一切为了群众”,忽视“一切依靠群众”,这是当前中国城乡基层治理中存在的最大弊病之一。
六、小结
当前中国城乡基层治理中存在着很多仍然有待改进的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的形式主义。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改变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积弊,遗憾的是,即使在当前时期,基层治理的形式主义仍然十分严重。甚至在2020年春节期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城乡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仍然屡禁不绝。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只是表象,根本则是上级的官僚主义,尤其是上级动辄对下级追责,求全责备,按最高标准苛求基层。基层既缺少因地制宜的能动空间,也缺乏因地制宜的主动性,应付上级就成为常态,形式主义就无法清除,治理就尤其难以有效率,为群众提供的服务就要打折扣,上级一味要求基层服务群众,就会使群众形成依赖思想而不愿自己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
本文试图通过提出在资源下乡背景下基层治理四个相互关联的命题,对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做一内在机制的疏理。希望本文的疏理有助于理解当前中国城乡治理的现实,并有助于改进之,以达到基层善治。
① 黄宗智:《重新思考“第三领域”:中国古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开放时代》2019年第3期。
② 田孟:《发挥民主的民生绩效》,《中国农村研究》2019年第7期。
③ 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