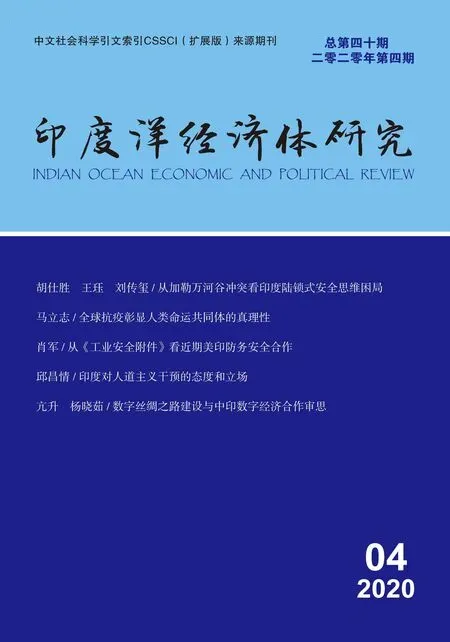从加勒万河谷冲突看印度陆锁式安全思维困局
胡仕胜 王 珏 刘传玺
【内容提要】加勒万河谷冲突错在印度,偶然中有其必然性。这场冲突是印度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实践的最新折射。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实践主要源于印度执迷于追求“绝对安全边界”。这一思维发端自印度精英层内心深处对“安全缺口”的历史记忆,熏陶自印度教传统文化,承继自诸如“前进政策”“缓冲区”“科学边界”甚至“天然屏障”等大英帝国的殖民遗产。然而,“绝对安全”越追求越不可得。即使“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安全合作搞得再好,也难以助力于解决陆上安全问题。唯有在周边地区坚持合作共赢安全观、秩序观,才是新德里摆脱陆锁式安全困局的最佳路径。
2020年6月15日晚,印度边防部队官兵侵入中方控制区搞夜袭,不但破坏了中方边防设施,还率先重伤中方交涉官兵,从而招致中方痛击并导致印方惨重伤亡。由此,原本一场近十年来常见的高原“群架”,因印方的率性鲁莽,演变成了一场严重冲击中印关系的重大事件。夜袭看似偶发,但偶然中存有必然。这场冲突是新德里经年推行“前进政策”的必然结果。
1962年的边界战争、1967年乃堆拉炮击、1975年土伦山口枪击事件、1986-1987年桑多洛河谷大规模军事集结、2017年72天洞朗对峙以及当前的加勒万河谷流血冲突,均与印度政府在边境地区推行“前进政策”密切相关。仅中印关系而言,“前进政策”的破坏力惊人。1962年的边界战争破坏了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2017年的洞朗对峙破坏了1988年以来双边累积互信的诸多努力,此次的加勒万河谷冲突则将两国领导人过去两年间形成的政治共识与外交成果几乎“清零”。两国关系已经到了非重构而难以重启的地步。
新德里对“前进政策”长达70余年的执迷,从本质上而言,反映的是印度陆锁式安全思维及实践惯性。其突出特点是以陆地安全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牵引,沉迷于追求绝对安全的陆上边界,执迷于构建“战略缓冲区”和“天然屏障”,执着于零和式地缘竞夺观,而不相信合作共赢的安全观。
就在加勒万河谷对峙与冲突期间,新德里同时还与巴基斯坦、尼泊尔发生了边境摩擦。印度,作为一个“北背雪山三垂大海”(玄奘语)的大国,在全球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今天,为何仍执迷于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实践,甚至不惜挑起与所有邻国的边境纷争呢?本文主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审视与思考。
一、加勒万河谷冲突中的“安全缺口”迷思
此次印方挑起加勒万河谷冲突的缘起是印方认为,中方在加勒万河谷的边防基建活动,对印度今年计划完成扩建的达尔布克-什约克-斗拉特别奥里地公路(DSDBO)构成严重威胁。这条公路长255公里,沿什约克河修建,北端的斗拉特别奥里地有一新扩建军用机场,去年10月启用,离中国边境实控线10公里左右。因为该公路是印度能联通拉达克地区和喀喇昆仑山口的唯一通道,更是印度确保其对锡亚琴冰川实施有效控制的战略要道,印方高度重视其战略价值。
锡亚琴冰川位于中印巴三国交汇处,既是印控拉达克地区的最高点,也是印巴两军对垒的世界最高战场。在新德里看来,掌控这个制高点就意味着可以“俯视”整个印控拉达克地区,监控中巴喀喇昆仑公路,洞察中巴陆上防务互动。然而,加勒万河与什约克河交汇的大河口恰是这条战略公路客观存在的一个“安全缺口”。出于战略公路的安全考量,新德里必先堵住而后安。
加勒万河与什约克河交汇的大河口原本位于中方自上世纪50年代末即主张的中方控制线之内,但在1960年代初被印方占控。1962年10-11月的中印边界战争中,中国军队将驻守印军赶出河谷。但战后为缓和局势,中方主动撤出加勒万地区哨所(实际上是从1959年11月7日控制线后撤20公里),仅通过巡逻执勤方式予以管控。1970年代中期之后,印军恢复并扩大西线越线活动,逐渐实现对包括大河口在内的什约克河的控制,并逐渐进入加勒万河谷、加南达坂等地巡逻。2011年之前,加勒万河谷地区总体平静。
2011年开始,印度开始修建什约克河西岸战略通道,遂日益重视加勒万河谷的边防巡逻与哨所修建。2012年,印军方要求一线部队每月进入加勒万河谷一次(但2012-2013年间,印军仅维持着一年巡一次的频率,因为中方巡逻频率也低)。此时,尽管中方仍保留对加勒万大河口的“实控主张”,但实际巡逻时中方一般止步于加勒万河大拐弯处(距离两河交汇处约5公里,也是今年6月15日晚爆发流血冲突的地方),并进而将大拐弯处视为“河口”,作为中方巡逻的折返处与实控线边际。双方一线边防部队对此已有默契。印方此前沿加勒万河谷巡逻时一般也止步于大拐弯附近,并将之命名为第14号巡逻点(PP14)。相比之下,因缺乏公路设施,中方无法通过地面巡逻维护对大拐弯处“河口”的有效管控。
莫迪上台之后,印方进一步加大巡逻力度,甚至有意将14号巡逻点建成前哨基地,以便日后控制大拐弯处。特别是,随着DSDBO扩建工程的不断推进,印度日益担心中方若控制大拐弯处,可轻松“偷窥”两河交汇地带,继而可“洞察”印方来往锡亚琴战略高地、斗拉特别奥里地机场的军事调动。而且,这个大拐弯处还有一块面积2700平方米的三角河滩,若中方在此布建永备工事、前沿哨所等,则中国军队可以很容易沿河谷冲下去切断DSDBO战略公路。为此,隶属国防部主要负责边境基建的“边境公路组织”(Border Road Organization)一边扩建DSDBO公路,一边在加勒万河与什约克河交汇的冲积滩上广建兵站、公路、桥梁、哨所、直升机坪、永备工事等,同时边防部队还增加了巡逻频率至一月两次。
由于考虑到今年DSDBO扩建工程必须完工,4月11日“大雪封山”被抢通后,印边境公路组织即快速推进各种“堵漏补缺”的边防基建活动。例如,为便于印边防军沿加勒万河谷巡逻,不断修建通往14号巡逻点的固定工事。印方速度很快,不但在大河口北河滩上新建一片边防设施,增强后勤补给能力,而且沿加勒万河谷先后架设了4座贝雷桥,其中一座便桥还越线修进大拐弯三角河滩,直接对中方主张的控制区构成侵入。
仅从基建本身而言,印方已在不断打破双方默契,率先改变边境现状。为因应这种变化,防止印度在边境侵权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特别是为防止印方今后以14号巡逻点为起点继续向加勒万河谷上游巡逻甚至顺势占控大拐弯处三角河滩的潜在冲动,中方今年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向大拐弯处推进巡逻公路、后勤补给站点等边防基建,并占控三角河滩,修建前沿哨卡,伺机拆除印方抵边越线便桥。于是,双方在大拐弯处形成对峙。两国虽有包括军长级对话等沟通机制,但最终仍未能防止6月15日晚流血冲突的爆发。
纵观整个事态发展,印方对边境争议区“安全缺口”隐患威胁的无限臆测以及近似鲁莽失控的“封堵”冲动,是导致此次流血大冲突的根本原因。本质上,这种不惜制造两军冲突的“封堵”行为,是新德里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实践的微观折射。
二、陆锁式安全思维的历史源起与实践
印度政府之所以不惜冒着与中方发生军事对峙乃至冲突的风险而去封堵加勒万河口,归根结底在于印度决策圈、战略界和军方长期存在追求“绝对安全边界”而绝不容忍任何“安全缺口”失控于人的迷思。这种见“缺口”就封堵的自我强迫症,是陆锁式安全思维的典型体现,有其历史缘由。
(一)开伯尔山口的历史记忆
印度所处的这块大陆自成一体,地理环境独特。北部山脉区,从阿拉伯海直到孟加拉湾,一系列崇山峻岭,包括兴都库什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脉、帕特凯山—若开山脉,组成一个几乎首尾相连的半圆形高墙,从西往东将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明显区隔开来。其余三面是印度洋,将这片次大陆与其他大陆完全隔离开来。因此,这块大陆又常被称为“印度次大陆”。
然而,看以完美的封闭地形却有一个明显瑕疵,西北崇山峻岭之间有一个天然豁口,叫开伯尔山口。山口不大,全长53公里,最窄处不足600米。在英国殖民者确立统治之前,印度历史上竟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尝试去封堵这个跑风漏气的山口。于是,这个神一样存在的山口历史上几乎成为所有外族陆上入侵或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必经通道。可以说,在中世纪之前的冷兵器时代,谁控制了这个山口,谁就控制了从印度河平原到恒河平原的辽阔北印度。
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自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次大陆,并最终确立了印度文明的底色。从此至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印度文明屡遭外来势力经由开伯尔山口的侵扰。历史上,波斯人、马其顿人、希腊人、大月氏人、嚈哒人(也称白匈奴人)、塞种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先后经由开伯尔这个西北豁口入侵次大陆,或劫掠财富,或就地称王。外族频繁入侵往往不是打断或牵制了印度这片大陆的统一步伐,就是进一步撕裂了印度原有的政治版图。小国林立,内斗不已。一次次的被征服也最终导致当今印度成为了世界上的“人种、宗教、文化和语言的博物馆”。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且它的全部历史,如果要算做它的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5页。
由此可见,开伯尔山口曾一直在印度次大陆的历史演进中扮演着塑造者或破坏者的角色。这个山口留给新生印度战略界、决策圈更多的往往是痛苦与屈辱的记忆。这是导致新德里自建国之日起便自陷于陆锁式安全思维的历史缘起。
(二)英国殖民者的边境“封口”实践
英国人自海上殖民次大陆后,由于自身即是海洋强国,并不担心殖民利益受到海上其他势力的威胁。实际上,英国人最终凭借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将印度洋变成了日不落帝国的“内湖”。故而,英印殖民政府更专注于南亚次大陆的北部山区边防安全建设,堵住包括开伯尔山口在内的所有陆上“安全缺口”。其中,重点防范对象就是沙俄。
就在1850年代末英国王室取代东印度公司实现对次大陆的直接殖民统治的同时,沙俄对中亚的扩张已开始对英国人在次大陆的殖民统治构成越来越迫近的威胁。作为次大陆边缘地带的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又属于地缘理论家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的一部分。为拱卫次大陆的殖民统治,以及为在与沙俄的“大博弈”中获得地缘优势,英国殖民者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实施“科学边界计划”(Scientific Frontier Scheme)(2)Stuart Sweeney,Financing India's Imperial Railways (1875-1914), Routledge,2011, p.84,不断将殖民统治边界由兴都库什山—喜马拉雅山山脚向更高的山脊推进,并在次大陆边缘地带寻求建立英俄“缓冲区”。
为此,英印殖民帝国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不但实现了对喜马拉雅山山麓小王国如尼泊尔、不丹与锡金的控制与蚕食,同时还成功地将中国西藏和阿富汗变成了英俄“缓冲区”,从而实现了对次大陆边疆“安全缺口”最大限度的封堵。然而,英国人只顾自身殖民利益的这种封堵实践,最终导致了后患无穷的阿巴“杜兰线”问题、克什米尔问题、中印边界争端以及所谓的“西藏问题”。这些问题与争端,直至现今仍是这片地区合作、发展、稳定与和平的最大威胁源。
(三)印度建国后的“安全缺口”封堵努力
英国殖民者撤离次大陆后,旧有殖民体系崩盘。对于新生的印度而言,随着印巴大分治以及新中国解放西藏,传统意义上的“缓冲区”消失了。原本被“缓冲区”所覆盖的“安全缺口”问题再度突显出来。一方面,尽管印巴大分治使得开伯尔山口不再成为新生印度的“安全缺口”,取而代之的是视印度为“最大生存威胁”的巴基斯坦的存在。特别是克什米尔问题成为了两个新生南亚国家之间的“火药桶”。另一方面,西藏的和平解放使得两个新生的东方大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物理接触,但历史上中印两国间的这条“边界”并没有通过正式签订任何界约予以划定,如何明确两国边防权限的地理范围随之成为双边关系的最大干扰源。
这样的地缘格局大变化使得新生印度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建国伊始即将国家安全重心锁定在陆地上。为此,新德里多管齐下。一方面,保持对巴的强大军事高压,将绝大部分兵力长期部署在对巴边境一带,特别是克什米尔地区。期间,新德里甚至通过第三次印巴战争实现了对巴基斯坦的肢解,将巴基斯坦在次大陆几乎与印度平起平坐的地区大国降格为地区二等国家,最大限度地削弱了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安全威胁能力。另一方面,不断堵住北部“安全缺口”,以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为中印间的“天然屏障”。首先,不断通过强压与封锁,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迫使西藏地方政府承认新德里对大英帝国在藏诸多特权利益的继承;其次,通过缔结一系列“和平友好条约”,逐一掌控对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的安全选择;再次,通过复活英国殖民者的“前进政策”,不断修正英国人留下的“北部边界”,以期掌握边境地带的所有制高点。
建国后,新德里这种对“安全缺口”的封堵冲动,最早体现在对六世达赖喇嘛出生地达旺的抢占上。1951年2月2日,尼赫鲁政府利用中国忙于抗美援朝战争无暇西顾之际,派出由卡辛少校(Major R. Khathing)率领的大批准军事化力量,跨越色拉山口,用武力赶走了我国西藏地方行政管理人员,强行占领了以达旺为首府的门隅地区。
达旺也确实是中印东段边界的一个“豁口”。1962年边界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通过突破达旺这块心形地区,接着又突破色拉山口,然后沿着印度“边境公路组织”新建的邦迪拉公路,如水银泄地般地冲到了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这种记忆恰是促使印度2017年下决心阻挠中方在洞朗修路的一个重要动因。在新德里看来,位于不丹两侧的达旺和洞朗都是印度必须封堵的重大“安全缺口”。
再以洞朗对峙来看,因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原因,中国与不丹对洞朗部分区块的主权归属存在不同理解,这与印度没有直接关联。但新德里却认为,这块地方是中印边界东侧的最大“安全缺口”。一旦中方在洞朗地区修建永备工事,特别是在南端的吉姆马珍雪山上修建观察哨所甚至部署武器装备,将对100公里以外的西里古里走廊构成“致命威胁”。毕竟,夹在尼泊尔和孟加拉国之间的西里古里走廊联通着印度腹地与东北部地区,最窄处仅22公里,又称“鸡脖子”。印度腹地与东北部联通的铁路、公路均处于这拥挤而狭窄的空间里。由于印度东北地区甚至在印度建国之前即活跃有民族分裂武装,至今尚未消停,新德里自建国伊始即担心东北部的裂土而治。加之,中方仍对印非法占有的中国藏南地区(毗邻印度东北部地区,印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保持着主权声索,新德里担心“里应外合”之下,不但会失去对“藏南”的非法“占有”,更可能失去整个东北部地区。由此,印度决策层、战略界与军方一直患有“鸡脖子”综合症。2017年夏,当中方为改善边防生产生活条件而在洞朗推进道路建设时,印方不顾历史约制,悍然越线阻止中方修路,形成长达72天的洞朗对峙事件。(3)胡仕胜:《洞朗对峙危机与中印关系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1期。
一个国家封堵边防“安全缺口”的行为本无可厚非,但安全是相互的,如若一方以牺牲他国安全利益甚至是主权利益为代价而大搞“安全封堵”行动,则只会触发矛盾与冲突,导致更大的安全问题。显然,这是新德里陆锁式安全思维的一种悖论。对“绝对安全”的追求只会导致“绝对的不安全”。
三、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前进政策”
大英帝国在殖民统治次大陆期间所推行的不断强化北方陆地安全的一系列政策及指导理论,均被以“大英帝国殖民遗产的天然继承者”自诩的新德里所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这些“殖民遗产”包括英国人的“前进政策”、“科学边界计划”与缓冲区理论等。这些遗产是新生印度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实践的“催生婆”。其中,“前进政策”对新生印度的统治阶层影响最为深刻,对其继承与发扬也最为执着。
(一)英国人的“前进政策”
英国人的“前进政策”实际上是其在次大陆推建“科学边界计划”的具体落实方案,旨在追求在次大陆建立“更加安全”和“更具防御性”的“安全边界”。其中,寇松出任总督期间(1899-1905),曾通过“前进政策”对中国西藏构成严重侵害,为祸至今。
19世纪中叶,正值英国的多事之时。印度各地频发的起义、与中国在远东的战争以及在近东对土耳其的争夺,使得英国疲于应付,无暇顾及中亚地区。沙俄先后完成了对布哈拉、浩罕、希瓦等中亚三个汗国的征服,并不断逼近阿富汗、土库曼和波斯等地,从而对英属印度形成地缘挤压,并引发英国朝野上下外交战略大辩论。随着主张对俄采取强硬政策的保守派1874年在大选中胜出,英国遂调整对外政策,出台了“前进”外交政策,与沙俄在中亚展开地缘竞夺。
作为保守派势力代表人物的寇松出任英印政府总督后,强烈主张“前进政策”应将边缘地带的西藏一并纳入。寇松的对藏“前进政策”旨在实现一大一小两个目标。小目标是实现英印政府提出的“科学边界计划”的具体设想,即把传统的中印边界线向北推进,将西藏东南部的门隅、珞瑜和察隅大部分地区划入英属印度;大目标是削弱清朝政府对西藏的主权控制,扩大英国在藏特权,阻止沙俄在藏立脚,改变西藏的政治地位,使之成为英俄之间的“缓冲区”。1903-1904年,荣赫鹏的兵侵拉萨则是寇松“前进政策”的具体实践。
由于在寇松出任英印殖民政府总督时,英国内阁尚无完整的对藏政策,故而对寇松的“前进政策”予以默认。然而,1903-1904年英军兵侵拉萨不但引发俄国强烈不满,还导致达赖喇嘛出逃蒙古甚至有意接近沙俄,“前进政策”的效果适得其反。英国政府很快撤换了寇松印督一职,以修补对俄关系,并最终于1907年与俄达成《英俄同盟条约》,把中国在藏主权史无前例地改称“宗主权”,初步实现英俄在西藏的战略缓冲。
尽管寇松对藏“前进政策”实施时间较短,但这一思想理念与实践成果却被新生的尼赫鲁政府所继承。
(二)新德里的“新前进政策”
当意识到新生印度既无法阻挡新中国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步伐,也难以继续将西藏视为“战略缓冲区”之后,尼赫鲁政府退而求其次,通过向北推进军事蚕食与渗透,不断改变中印边界状况,以实现利用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脉为中印间“天然屏障”的目标,从地理上阻隔新中国对印度的“地缘威胁”。
1950年10月,昌都一役大胜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已势不可挡。针对时局新变化,尼赫鲁政府“筹划”的结果,就是将英国人非法炮制的“麦克马洪线”视为印度东段边界,作为实施“新前进政策”的“合法依据”。尼赫鲁在1950年11月印度议会上表示,政府非常关心北部边界安全,不管地图不地图,“麦克马洪线”就是印度的边界,(4)Bhim Sandhu,Unresolved Conflict:China And India(New Delhi:Radiant Publishers,1988), p.94.并鼓励和支持将印度行政管辖延伸到印度主张的全部边界上。(5)B.N.Mullik,My Years With Nehru:The Chinese Betrayal(New Delhi:Allied Publishers,1971), p.85.
从1950至1958年,趁中方忙于抗美援朝和应对台海危机而无暇西顾之机,新德里加紧实施“前进政策”,相继蚕食了东段“麦克马红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中段2000平方公里和西段45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新中国对尼赫鲁政府的单边政策不断进行交涉,希望努力稳住中印关系的大局。
然而,中国政府平定1959年“3.10”拉萨暴乱以及随后边境爆发的两次短暂流血冲突[1959年8月和10月的朗久(东段)和空喀山口(西段)流血冲突],使得边界问题迅速从两国的外交争端发展成为两国间的现实冲突。同时,尼赫鲁也由此加深了对“中国安全威胁”的认知,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必然是一个扩张主义的中国……将构成一种非常危险的形势”。(6)楼耀亮:《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际战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5页。基于对中国敌意的夸大以及本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安全逻辑,尼赫鲁政府终于在1961年11月2日的高层会议上下达了以武力向中国境内全面推行“前进政策”的指令,其主要目的是以事实上的占领来支持其片面的领土主张,追求“绝对安全边界”。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印度陆军迅速行动起来,集中于中印边境西段的不断推进(因为此时东段中国藏南地区已大体上掌控在印方手里),从1961年11月至次年3月,印军利用此前中国边防部队单方面停止巡逻(7)1959年两次边境冲突后,中方出于缓和局势以营造对话解决边界争端的氛围的考量,单方面停止巡逻。中方示好并没有换来尼赫鲁的“回心转意”,反而变本加厉地通过“前进政策”蚕食中方主张的边境地区,直接触发了1962年的边界战争。之机,在边界西段300公里宽的地段上全线向前推进,占领了中国边防部队撤出的哨所。“前进政策”在中印边境西段的不断推进,严重威胁到新中国对藏主权的巩固以及中国西南边疆的战略安全,最终招致新中国的强硬回击,直致爆发战争。
尽管印度输掉了1962年那场边界战争,但此后的新德里历任政府并没有放弃推进“前进政策”。如前所述,自1962年边界战争结束以来,新德里历届政府的“前进政策”在边境地区制造了无数对峙。那么,明知“前进政策”会导致与中国关系走向恶化甚至触发军事冲突,新德里为何在过去70年里一直执迷于此呢?
正如中国学者刘红良所说,“印度最初的‘前进政策’没有遭遇新中国的有效抵制,使之获得了中国政府会默认其边界政策的认知”。(8)刘红良:《边界变移、认知差异与中印边界战争》,《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4期,第35页。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代中国领导人主要忙于国内秩序的重构,如收复西藏主权、肃清各地残匪与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造,甚至准备收复台湾,以及通过“十七条和平协定”在西藏实施“高度自治”政策。与此同时,新中国对外还要处理美国的“封锁”甚至应对战争的近逼(如朝鲜战争)。新中国对印度在边境地区推行的的“前进政策”实际上处于无暇也无力顾及的境地。自然,这种情况使印度倾向于得出“中国政府默认其边界政策”的结论。而且,英国殖民者在“前进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贯做法也给了印度重要启示,即只要对方未提出抗议、未采取针对性举措,这种行动就是合理的,可以继续为之。久而久之,“非法的行为”也就逐渐上升为一种行为惯性。(9)刘红良:《边界变移、认知差异与中印边界战争》,《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4期,第35页。此外,1954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使尼赫鲁自我认定,中国接受至少是默认了印方关于边界的主张。在此协定签订后,尼赫鲁在一个秘密通报中说,“协定是印度与中国和西藏关系的新起点,根据印度的政策以及中印达成的协定,北部边界应被看作是确定的、最后决定了的,并且是不容进行谈判的。(10)D.R.Mankekar,The Guilty Men Of 1962,Penguin Books,2003,p.138.此后,新德里推出新版地图,将所有原先标注“未定国界”的地方全部据此实化为“中印边界”,并发放一线官兵予以实地执行。
总之,在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建国初期对印度“前进政策”事实上的“反应缺失”甚至一味忍让之下,尼赫鲁当局错误地评估了形势,得陇望蜀,得寸进尺,最终将新中国逼入一个不得不采取军事自卫行动的境地。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中方主动撤退,印度却随后跟进。此时,中国又逐渐陷入文革内乱之中,边防巡逻基本废驰。与此同时,印度却时刻都在加强边境巡逻以及抵近工事建设。1976年新德里建立的“中国研究小组”专门修订了印军“前进政策”的具体执行细节,包括巡逻路线、边境地区寻建存在的模式、与中方巡逻队接触时的应对方式等等(11)Shishir Gupta,“Behind Galwan’s Bloody Face-Off, China’s Plan To Interdict Gateway To Karakoram,” The Hindustan Times, June 18, 2020,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pla-s-plans-for-an-observation-post-triggered-clashes/story-HoEL1u5Dxtv1GVH46RnUfI.html。印方边防建设获得稳步推进,并对中方边防形成明显的非对称优势。例如,1980年,中国政府组织中不边界亚东调查组前往洞朗地区的中不边界进行调研。当时,中方调查人员吃惊地发现,印军早已在吉姆马珍山顶上“构筑了约40个暗堡工事,多卡拉山口(2017年洞朗对峙的附近)也有一地堡工事,上面的枪眼都很清楚”。(12)邓和平:《走近中不边界》,选自《西藏岁月》,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1999年,第61-62页。
过去50余年来,经过“前进政策”不断“切香肠”式的蚕食、渗透,目前印军已在中印边界东段、中段基本上控制了所有制高点。
莫迪总理上台以来,随着国内政治生态的迅速右转,印度边防部队聚力于中印边界西段推进“前进政策”,构建所谓的“绝对安全边界”。每年中方针对印度边防力量“非法越线”的指控都在千余起以上,这些习惯性的“越线”行为也是导致莫迪执政以来两国边界对峙频频发生且集中于西段的主要原因。以2019年为例,印度对中方实控线的越线活动多达1581起,其中94%发生在西段边境。一旦中方强势回怼,边界对峙乃至冲突随即发生。边界一出事,基本上两国关系必受波动。这也是2014年以来,两国关系总是高开低走的一大原因,形成了两国关系年度高低曲线与青藏高原雪线升降曲线的密切关联现象:雪线升高(气候转暖),边防对峙增多,两国关系走低;雪线下降(大雪封山),边防巡逻减少,两国关系抬升。
(三)“新前进政策”与边防基建
从尼赫鲁政府到莫迪政府的“新前进政策”实施中,边防基建是其中最为得力的工具。新德里边防基建除了改善边防巡逻及边境生产生活条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以修路搞蚕食、渗透,改变边控现状,寻建安全边界。由于这种修建极具挑衅性且带有浓郁的军方色彩,因此又有人将之称为“边境基建战”(the Border Infrastructure War)。(13)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India Is Still Losing To China In The Border Infrastructure War,” The Diplomat, September 21, 2018https://thediplomat.com/2018/09/india-is-still-losing-to-china-in-the-border-infrastructure-war/印方负责边境基建计划的“边境公路组织”隶属国防部,其历任主任都是军职。当前该组织的总干事哈帕尔·辛格就是一位中将,级别等同于负责中印边境西段国防安全的第14军司令。
两大事件对印度边防基建构成两种不同影响。一是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期间,印在中国藏南地区修建的邦迪拉公路成为中国军队一路打到布拉马普特河平原地带的“帮凶”。这一剧情导致印方长期不愿搞联通内地与边境的大交通网络建设,尽管围绕“封堵缺口”、抢战制高点的一线边防基建一刻也未停止。二是2006 年青藏铁路的开通,瞬间大幅提升了中国远距离军事投送能力,极大地刺激了印度边防的敏感神经。也就在这一年,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通过正式决议,要求印度政府沿着中印实际控制线修建73 条战略道路。此后,印度边防基建迈入快车道。特别是,莫迪总理上台以来,这一速度不断加快。2008 年至2014 年,边境公路建设3610 公里;2014 年至2020 年,边境公路建设4764 公里。(14)Dhasmana, Anil, “India’s Infra Push Behind Chinese Aggression,” Hindustan Times, June 22, 2020.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india-s-infra-push-behind-chinese-aggression/story-hoelKGmwoTdiCkaTGupuPL.html.
近年来,印度边防道路越修越近,并在多处贴近中方主张的控制线,甚至在不少地段或骑墙修建或越线修建,形成对中方实控区的不断蚕食、渗透。本世纪特别是莫迪执政以来双方的重大边境对峙与冲突事件,几乎都与边防基建特别是印方在边境突击修路密切相关。同样,印度边防基建也是引发此次加勒万河谷冲突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加勒万河谷过去几十年都未曾成为两国边境对峙的主战场,相对安宁。但莫迪执政以来,新德里不但要求边防部队每月进入河谷巡逻两次,而且加大边防基建,为巡逻提供后勤支撑。例如,2014年,印度新建了加勒万哨所(驻守约70人)以及另外三个辅助哨所(每个哨所20人左右)。今年4月以来,莫迪政府出于对附近即将扩建完毕并投入使用的DSDBO战略公路的“绝对安全”的考量,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规模推进“前进政策”的实施范围。一些关于边界地区卫星图像的研究显示,冲突之前,印度已在DSDBO公路沿线、加勒万河与什约克交汇区以及加勒万河谷修建了许多军事设施,(15)Ruser, Nathan, “Satellite Images Show Positions Surrounding Deadly China-India Clash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The Strategist, June 18, 2020.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satellite-images-show-positions-surrounding-deadly-china-india-clash/.甚至将便桥修到了中方多年来坚持的“实控线”。印方这种抵近基建行为是为了改变边境争议区的力量对比,以期形成对中方边防基建的优势。事实上,今年5 月之前,中国军队并未出现在加勒万河谷,当时河谷地带也无中方边防基建活动。但当看到印军已在实控线附近大兴边防设施时,中方才最终加快河谷边防基建速度,并最终造成对峙、冲突。(16)Ruser, Nathan, “Satellite Images Show Positions Surrounding Deadly China-India Clash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The Strategist, June 18, 2020.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satellite-images-show-positions-surrounding-deadly-china-india-clash/.
四、陆锁式安全思维与“缓冲区”理念
英国殖民者的“前进政策”实践,催生了“缓冲区”理念。这种“缓冲区”理念不但被印度政府予以继承且更演绎出了“天然屏障”的安全观与政策实践。长期以来,构建“缓冲区”和“天然屏障”是独立建国之后,新德里陆锁式安全实践的核心诉求。
一方面,执念于西藏作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区”。早在英国人尚未撤离次大陆之时,尼赫鲁组建的临时政府即于1946年12月邀请中国西藏代表以与其他亚洲国家代表平等的身份出席由其筹划召开的“泛亚会议”,这是新生印度对英国人“缓冲区”理念的最初尝试。新中国成立之后,尼赫鲁政府以西藏为中印两国间“缓冲区”的动作更频,如1950年反对中国出兵西藏、1956年唆使出访印度的达赖喇嘛搞独立(17)例如,在1956年11月27、28日两次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中尼赫鲁表示,如果中国不按“十七条协议”行事,且西藏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尼赫鲁甚至还称,“你说你想独立,但同时你又说不想流血。不可能!”参见杨公素、张植荣:《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0页;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London: Abacus, 1990), p.161.、放任噶伦堡的“藏独”活动、1959年3月拉萨暴乱期间成为西藏分裂势力的传声筒、容留达赖集团和流亡藏人、助建“流亡政府”、支持藏人残匪武装对藏区搞武装袭扰、1963年正式对外成立“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以作未来“藏独”武装力量之用)等。
尼赫鲁之后,以西藏为缓冲区的迷思一直存在。即便在1988年12月两国关系迈上正常化轨道之后,印度历届政府仍然基于“缓冲区”迷思而奉行“双轨政策”,既不公开支持“藏独”,也不停止为“藏独”势力及其支持者、同情者提供生存空间、活动舞台与政治关照。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对西藏政治地位定性的不同表述最能反映这种“缓冲区”迷思。1959年3月拉萨叛乱前,印度政府曾公开承认过“西藏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此后却一直反复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直至2003年6月,印度政府才在瓦杰帕伊总理访华期间与中国领导人签署的《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里,正式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也是新德里首次在政府间文件中申明这一立场。虽然前后表态只有几个字的差异,但却是一种质的飞跃。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重在从“自治区”这一政治概念来描述西藏与中国的关系,带有英印帝国时代的殖民痕迹,即只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国的一部分”,重在从领域主权的概念来强调西藏的法理地位,即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且接受了中国对“西藏自治区”的地理界定,这与达赖集团的“大西藏”概念大不相同。即便如此,印方在宣言草拟过程中,曾竭力反对中方提议的“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称如中方坚持加上“不可分割的”,印方将拒签此份“宣言”。(18)唐璐:《揭密2003年中印两国西藏问题谈判内幕》,《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6月30日。由此可见,印度对“西藏作为缓冲区”的迷思之顽固。
近几年,随着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不断发展,以西藏作为中印“缓冲区”的念头再度在莫迪执政时期沉渣泛起。莫迪政府“打西藏牌”的力度与频度比1988年以来的印度历届政府都大,如邀请达赖集团行政头目洛桑孙根出席莫迪总理就职典礼、现任总统正式会见达赖喇嘛并一同出席公共活动、推出“2014年藏人安置计划”、允准所谓的“藏人流亡政府”头目洛桑孙根到班公湖印方一侧插上“西藏独立旗”、让内政国务部长(副部级)亲自陪同达赖喇嘛窜访中印争议区印方控制区(即中国藏南)等等。“西藏问题”在沉寂多年后开始频频冲击中印关系的稳定性。不但莫迪政府毫无顾忌地“打西藏牌”,一些政府高官、统治精英甚至还再度提及西藏为印度“缓冲区”的梦呓。2017年7月19日,印度政党领导人、前国防部长穆拉扬·辛格·亚达夫(Mulayam Singh Yadav)在印度国会上称,印度接受西藏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是“错误”的,现在已到了支持西藏作为历史上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了,因为它是两个大国之间的传统缓冲区。(19)“India Should Support Tibet’s Historical Status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Former Defence Minister,” http://tibet.net/2017/07/india-should-support-tibets-historical-status-as-an-independent-country-former-defence-minister/.更有甚者,在达赖喇嘛2017年4月窜访达旺期间,面对中国方面的谴责,伪“阿鲁纳恰尔邦”(中国藏南地区)首席部长佩马坎杜(Pema Khandu)非同寻常地宣称,独立的西藏—而非中国—才是印度在北面真正的邻居,“让我把话说清楚,中国无权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因为它根本不是我们的邻居”。(20)“Arunachal Borders Tibet, Not China: CM Pema On Beijing’s Protest Over Dalai Lama,”Hindustan Times,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arunachal-borders-tibet-not-china-cm-pema-on-beijing-s-noise-over-dalai-lama-visit/story-cDE3x2Nl45uRz14YmMVQwO.html.
另一方面,执念于以喜马拉雅山为中印之间的“天然屏障”。当意识到新中国和平解放西藏的意志与步伐难以阻挡之后,尼赫鲁政府加快扎紧“喜马拉雅山篱笆墙”的步伐。1949年,印利用锡金一地方起义反抗大君之机派军入锡,不但使其成为印度的保护国,而且使其依附程度超过了过去锡金在形式上对英国的依附(1975年更是直接吞并锡金);1949年8月8日,印度与不丹签订《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把英国指导不丹对外关系权利接管过来,并一直阻止其与中国建交至今;1950年,印度协助尼泊尔国王结束拉纳家族的百年统治,并于7月31日与尼泊尔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使尼泊尔在军事与安全问题上受印度操纵。此后,印度又分别在1950年1月4日与阿富汗签订了《友好条约》、1951年7月7日与缅甸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完成法理上的一系列操作之后,新德里开始利用这些条约遏阻任何有可能穿刺“天然屏障”的行为。例如,1989年通过全方位封锁最终迫使尼泊尔前国王比南德拉放弃了从中国进口武器的计划;2013年和2018年利用对大选的强力介入,阻止友华政治势力继续执掌不丹民选政府;2017年制造洞朗对峙,则更是为了防止洞朗变成中国撕开喜马拉雅山“天然屏障”并指向西里古里走廊的匕首。(21)Mandip Singh , “Critical Assessment Of China's Vulnerabilities In Tibet,” IDSA Occasional Paper No. 30, January 2013.在印度人眼中,洞朗地区以及更往北的春丕谷地区 “犹如一把匕首直指印度”。
实际上,加勒万对峙与冲突的发生是莫迪政府“缓冲区”和“天然屏障”迷思的一种微观折射而已。6月6日两国军长级会谈曾达成4点共识。其中,双方同意在大拐弯的“河口”两侧各自搭设观察哨,由现地指挥官会晤落实。然而,印度高层很快反悔,并指示现地指挥官在会晤时向中方表明其对双方在河口设哨不满,并要求中方拆毁。为检查中方是否已拆毁哨卡,15日晚,印军冒险进入中方控制区,焚毁中方搭设帐篷,重伤我留守官兵,从而最终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
印方之所以对中方在大拐弯的三角河滩上设立观察哨反悔,其意图一目了然,就是希望将这个三角河滩作为“缓冲区”,继而将中方边防部队隔离至河谷深处,利用拐弯处大山为“天然屏障”,挡住中方边防部队的巡逻视线。这实际上是印方在无法直接控制三角河滩情况下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此后,印度一直坚持这一要求。6月30日,在第三次军长级会谈中,双方达成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双方一线部队均离开三角河滩各约1.5公里。这一相互脱离接触,客观上至少满足了印方以大拐弯处三角河滩作为一个小小缓冲地带的安全诉求。
五、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印度教化的政治传统
随着越来越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精英不断迈入印度政坛,印度国内政治生态加速右转,日趋“印度教化”,致使印度内外政策更好冒险、更偏强硬,特别体现在对华外交方面。这也是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的政治文化背景。
(一)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印度政治生态的右倾化
2014年和2019年两次大选,脱胎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大家族的印度人民党强势胜出并组建强势政府,一举结束了过去印度政坛长达30年的多党联合执政的弱政府现象。与此同时,印人党的“母体”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母随子贵”,政治发展与影响力突飞猛进,如日中天。这个以印度教民族主义塑造印度社会意识形态的右翼组织,2014年时已拥有近4万个基层分支“沙卡”,但五年后的2019年,其沙卡数目猛增至8.4万(22)根据国民志愿团发布的2019年度报告,印度全境共有84877个基层组织“沙卡”。参见” “How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Is Spreading Its Footprint Across The Nation”, DNA, https://www.dnaindia.com/india/report-how-rashtriya-swayamsevak-sangh-is-spreading-its-footprint-across-the-nation-2728048.,成为统摄印度社会各层的强大存在。国民志愿服务团并不直接参选,但大力支持印人党竞选,助其连选连胜。
从两届政府的决策圈构成来看,“政治挂帅”色彩日益浓厚。莫迪第一任期里,66名部长阁僚中有41位出身国民志愿服务团;第二任期里,53位部长里有38位拥有国民志愿服务团背景(23)Neelam Pandey And Shanker Arnimesh, “Rss In Modi Govt In Numbers-3 Of 4 Ministers Are Rooted In The Sangh,”The Print, 27 January, 2020,https://theprint.in/politics/rss-in-modi-govt-in-numbers-3-of-4-ministers-are-rooted-in-the-sangh/353942/。从执政党党魁到国家总理再到内政部长、防长等重臣均出身“国民志愿服务团”。在议会中,出身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成员也越来越多。以2019年产生的议会为例,在印人党303名人民院(下院)议员中,出身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有146人,占比48%;在印人党82名联邦院议员中,出身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则有34人,占比41%。(24)Neelam Pandey And Shanker Arnimesh, “Rss In Modi Govt In Numbers-3 Of 4 Ministers Are Rooted In The Sangh,”The Print, 27 January, 2020,https://theprint.in/politics/rss-in-modi-govt-in-numbers-3-of-4-ministers-are-rooted-in-the-sangh/353942/
政治生态的右倾化导致印度安全与外交领域的强硬化,并最终体现在新德里在陆地边境问题上的对华示强与冒险行为。例如,当前新德里外交、安全决策团队均为对华强硬派。从国家安全层面看,2017年来莫迪政府推动国安体制改革,国安顾问权限大增,前情报局负责人多瓦尔转任国内顾问。2019年,莫迪强势连任之后,多瓦尔作为国安顾问更是跻身内阁核心,被称为“国安沙皇”。多瓦尔“举贤不避亲”,大量启用情治机构官员,现任3名副国安顾问和1名军事顾问,除1人是前驻俄罗斯大使外,其余3人均来自情报部门。多瓦尔视中国为印度“战略威胁”,不断强化对华防范措施,特别是在边界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他宣称,印度绝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妥协,并曾一手炮制“洞朗事件”,否认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从外交层面看,外长苏杰生对华实用主义色彩浓厚,不回避对华风险投机,在担任外秘期间就主张利用美印合作遏制中国扩张。苏杰生出任外长后,更加频频对华示强,如坚持现状解决边界争端、将印度不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归咎于中方“贸易保护主义”(25)“RCEP: Jaishankar Says India Concerned Over ‘Enormou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The Economic Times, September 9, 2019,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foreign-trade/rcep-jaishankar-says-india-concerned-over-enormous-trade-deficit-with-china/articleshow/71051623.cms?from=mdr.、公开抨击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并坚决主张印度拒绝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等。此外,主张对华开展务实合作、积极促成中印领导人举行非正式峰会的前外秘顾凯杰(26)疫情期间,印前外秘、前驻华大使顾凯杰公开宣称,新冠疫情“不仅是医疗战,更是意识形态之争”。印度作为非西方民主国家,如能胜利“抗疫”,“将是攸关中国意识形态生存的最大威胁”。下阶段,印度或加入美对华舆论战,借中印模式之争撬动美印战略合作,而一旦成功“抗疫”,势必渲染对中国的“模式优势”。、前驻华大使康特、班浩然、齐湛等印度外交部的知华派,在相继退休离职后大幅转变对华立场,纷纷公开表态要对华加强战略防范。而且,外秘一职(27)现任外秘斯林格拉(Harsh Vardhan Shringla)毫无驻华经历,主要涉美涉南亚,对华“竞争”意识较重。不再由外交部内的“中国帮”(China Mafia)把持,这也凸显印度在外交方向上的重要调整。
从政治文化右倾色调到具体外交与安全决策的强硬偏好与冒险特性,进一步加深了新德里陆锁式安全思维定式,加重了新德里陆锁式安全实践冲动,从而导致在对华外交与安全上,新德里往往是一言不合即怒怼。今年上半年,中印关系一路下探即是明证。这实际上也构成了加勒万河谷冲突的大背景。今后,这样的冲突还会有,甚至可能常态化。
(二)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印度教传统政治文化
以国民志愿服务团为首的保守派长期宣扬“印度教价值观”,鼓吹重建“罗摩盛世”。因此,体现印度教传统秩序观、安全观的“曼荼罗”思想、“婆罗门至上”理念,自然也成为莫迪执政团队陆锁式安全思维的丰富滋养。
“曼荼罗”思想(28)有关“曼荼罗”思想的论述可参阅胡仕胜:《洞朗对峙危机与中印关系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1期。强调远交近攻的邻国圈理论,反映了印度自古以来现实主义色彩深厚的安全观与外交观。依据“曼荼罗”外交与安全理念,一个国家在应对外部挑战时有多种模式:和平共处(在国力不济时奉行)、战争(在实力占优时主动攻击)、中立(在自身将强未强之时,使敌人无法伤害自己的明哲保身之道)、紧逼(通过高压政策,不战而屈人之兵)、联盟(寻求他国保护)、双重政策(与一国交好的同时与另一国交战)。可见,“曼荼罗”思想一直深刻影响着新德里的对华政策。从冷战期间的联苏抑华到当前与美及其同盟体系的战略互动,无处不透露出新德里“曼荼罗”思想中的“以邻为壑”、“远交近攻”的外交精髓。
“曼荼罗”外交观、安全观等思想若从深处挖源,又与印度教的“婆罗门至上”世界观密切相关。“婆罗门至上”是一种以“印度天命论”为核心的婆罗门等级世界观,缘于印度独有的种姓制度。“印度天命论”是印度精英认识世界的起点,深刻影响了印度独立以来历届政府的安全及外交思想。在“印度天命论”者看来,“印度理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29)George Tanham, “India’s Strategic Cultur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1992, p.130就像婆罗门位于各种姓之上一样。例如,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曾明确表示,“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是不能引动我的,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30)[印]贾瓦拉哈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页。在尼赫鲁看来,印度的国际地位只能与像美国、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相提并论,而不能与巴基斯坦这样的地区性国家平起平坐。(31)V. M. Hewitt,“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South Asia,”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95.而且,印度在国际上的“一等大国”地位是与生俱来的,而非通过后天争取或者他国恩赐而来的,他国对此只需承认即可。印度精英长期以来抱怨中方未予印度以应有的大国尊重,即是源于这样的传统情结。而且,在印度大国诉求方面,中方在表态时的任何犹豫或模糊都会招致印度战略界与决策圈的公开怨恨与批判。这种“曼荼罗”、“婆罗门至上”思想,自然也反映在此次加勒万河谷对峙的成因上。
一方面,“高风险高收益”。外长苏杰生曾明确表示,印度外交就是要“勇于冒险”(Risk Taker)。(32)Arjun Subramaniam, “The One Speech That Explains India’s New Strategic Thinking: India’s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Has Laid Out Clearly And Cogently A Set Of Guiding Principles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The Diplomat,December 5,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12/the-one-speech-that-explains-indias-new-strategic-thinking/.这是由于国际大环境利好使然。在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不断增加的制华需求催化之下,特别是中美对抗日趋尖锐的情势下,印度的地缘价值陡升,达至建国以来的历史峰值。这使莫迪执政团队在对华示强方面有了更多底气与自信。美国西方集团对印度“婆罗门般”的礼赞让新德里受用非浅,而“曼荼罗”思想所强调的那一套外交观、安全观又完全好使。新德里既可从倚美制华、以华应美的双重政策中不断套取双方的战略实利,也能利用一线边防基建对华构成的明显优势而步步紧逼、主动示强,以榨取中方更多让利空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具体到加勒万河谷冲突的导火索上,如果没有上层对华政策的风险偏好,下层军官也断不敢如此鲁莽冲动“不讲政治”。实际上,没有巴布上校率兵夜袭,就不会出现严重冲击两国关系的流血冲突。
另一方面,以自我为中心。莫迪政府实际上是将印度对绝对安全的诉求凌驾于中国发展加勒万河谷边防建设的正常且正当需求之上。印方坚持要求中方空出大拐弯三角河滩,希望中方尊重并照顾印方关切,边防基建最好远离大拐弯,越远越好。
(三)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印度的“门罗主义”情结
新德里“自我为中心”的南亚外交观以及其他表现形式,如单边主义、印度例外论、印度特殊论等等,实质上就是“曼荼罗”、“婆罗门至上”等传统思想所浇灌出的印度版“门罗主义”。加之,基于印度得天独厚的地理与地缘优势,特别是印度地处南亚“中心”的地理位置,印度精英阶层中普遍存有“独享”南亚乃至印度洋的“门罗主义”情结。
印度建国以来先后出现了两波“南亚门罗主义”强势外交,前一波是在尼赫鲁(1947-1964)和英·甘地(1966-1977、1980-1984)执政时期,重心是将南亚邻国纳入印度的战略轨道,并抵制两个超级大国对南亚的影响。这一过程中,印度实现了使北方小邻国的臣服以及对巴基斯坦的肢解。第二波是莫迪执政以来的这一时期,重在遏阻中国对南亚影响力的拓展。其中,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重点打击的对象。
在“门罗主义”思想深厚的印度精英看来,尼泊尔与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建设备忘录”和边境协议、斯里兰卡积极欢迎中国参加港口与道路修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马尔代夫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中缅共推经济走廊建设等等,都是中国有意多路突围、破坏印度在南亚次大陆长期维系的“印度秩序”的战略图谋。这从印度知名战略家拉贾·莫汉对中方“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即可一定程度上探知印度深层次的战略担忧。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夕,拉贾·莫汉曾撰文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大规模地加强中国在商业、经济、政治及安全上对印度邻国的影响力。(33)C. Raja Mohan, "Network Is The Key: India Must Ramp Up Its Internal Connectivity To Counter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he Indian Express, May 9, 2017,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network-is-the-key-4646728/.为此,莫迪政府近年来频频以“印度安全诉求”压制邻国自主发展对华关系的意愿与需求,甚至不惜干涉内政,制造多国政治乱局。近年来,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政局变动、政权更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凡主张与华友好特别是主张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势力和人物均遭遇新德里的无情打压。
此次边境对峙与冲突期间,莫迪政府频频对华示强,甚至不惜使用战争用语,既为了最大限度地逼迫中方让步,更为了威慑周边邻国,消除邻国在中印之间选边站的任何心思。
然而,“南亚门罗主义”是把双刃剑。在新德里确保其地区绝对主导权、话语权、影响力的过程中必会催生出周边国家对印度“老大做派”的严重不满乃至抗争。这样的事例不在少数。例如,1989年,尼泊尔国王比南德拉曾“擅自”绕开新德里而从中国进口武器;2000年,孟加拉国曾有意与美国探讨租借吉大港事宜,甚至与中国探讨共建索纳比尔深水港计划;2008-2013年不丹产生的第一届民选政府尝试与华建立正常关系、2014-2019年间的马尔代夫政府积极奉行对华友好政策、2009-2014年间斯里兰卡拉贾帕克萨政府更是大张旗鼓深化与华战略合作等等。尽管这些邻国的友华近华政权不断受到新德里打压,但这种打压的失灵只是时间问题。其中,尼泊尔奥利政府今年在边界问题上勇于捍卫自身利益,即是对新德里常年打压的一种最新反抗。
六、陆锁式安全困局的出路
加勒万河谷冲突表明,虽然世界已处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路口,但拥有“三面临海”地缘之利的新德里却生活在大航海来临之前的那个时代,仍然受困于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实践。新德里要想追求尼赫鲁所渴求的“有声有色的大国”地位,必须走出追求“绝对安全边界”的制陆权迷思。越是想通过具有零和色彩的“前进政策”、采取“切香肠”策略来追求“安全边界”,越是容易制造出类似洞朗对峙、加勒万河谷冲突这样的边境事端。而且,每一次边境冲突只会损害两国战略互信,继而导致双方不断增强其应对威胁的军事投入与能力建设。如此,冲突双方不得不陷入螺旋式上升的安全困局之中。这在物理学上叫“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实践证明,只要还不能有效解决与邻国的安全互信问题,新德里无论怎样实施“前进政策”,都难以走出陆锁式安全困境,反会越陷越深。
殖民时期,英国人为掌控次大陆的制陆权,曾推出“科学边界计划”,不断向北推进“前进政策”,确曾取得过不少进展,扩大了北部安全防御纵深,甚至与沙俄达成一系列“缓冲地带”的地缘共处安排。但当时,北部陆块基本是弱邻。即使如此,在撤退次大陆之前,英殖民政府也未能完成“科学边界计划”。
印度建国之后,当初英国人设置的防御纵深体系因殖民统治的崩溃而基本消失。新德里不得不逐一强势重构北部安全秩序,如通过一系列条约、协定将北方诸小邻国和地区纳入自己的战略防御体系。尽管如此,对新德里而言,北方依旧存在两大安全薄弱环节或两大“安全缺口”,阻碍印度“制陆权”的最终确立。一是“南亚火药桶”的克什米尔争端。印巴几度大打出手,热战冷战轮番交替,但克什米尔问题依旧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依旧是印北部陆上安全的最大溃疡。二是中印边境争端。两国也曾为此战争相向,迄今双方仍时而爆发边境对峙甚至冲突,这已成为印度财政资源的巨大“销金窟”。例如,一个加勒万冲突就已经让新德里不得不掏出数十亿美金,四处购置山地战武器。
两大“安全缺口”叠加中巴准盟友关系,已经并将继续迫使新德里不敢降低其对北方陆地安全防御的战略投入。建国以来,印度军费有近三分之一消耗于印北部边境的军事部署、调动与后勤保障。曾几何时,新德里希望利用中印关系正常化以及冷战结束之机,有意发挥其坐拥“三面临海”之地缘优势,彻底走出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实践。继1988年第一次推出《印度海洋战略(1989-2014)》,新德里接连推出多份印度洋经略文件,如1998年的《战略防御评估(海洋维度)—海军愿景》、2004年的《印度海洋学说》、2007年的《自由使用海洋:印度海上军事战略》以及2015年的《确保安全海洋: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等等。
然而,莫迪政府2014年执政以来,随着政治生态迅速右转,执着于寻求建立“绝对安全边界”的迷思再度在精英层与决策圈中回潮,并导致印度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波折不断。特别是随着新德里再度大力加强“前进政策”实施力度,印度边防基建不断向前推进甚至骑线、越线修建,中印边境对峙与冲突频发。由此可见,陆锁式安全思维的生存力之强大。新德里若走不出陆锁式安全思维误区,就难以迈上海洋大国或陆海兼备的大国征程。
最近几年,新德里为摆脱这种自我实现的陆锁式安全困局,有意另劈蹊径,即尝试利用中美对抗加剧、美国对印度战略拉拢之机,迎合美国主导下的“印太战略”,以收“以海制陆”之效。为此,新德里不断推进与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海上联演、海上安全合作与对话、海上态势感应系统与情报分享网络建设等等。然而,印度洋的水解不了雪山的渴,印度洋的水更灭不了雪山的火。印度洋通道是公共产品,且攸关多方核心利益,无论如何新德里也不可能通过施压一条国际通道来助解其远在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所遭遇的陆锁安全困局。实际上,新德里只要还不能摆脱制陆权思维,就不可能有更多财力投入到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继而也就不能在“印太战略”中发挥美国殷切期待的那种“西锚”式战略支点作用。最终结果,新德里也只能让奉行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念的华盛顿日渐失望。
加勒万河谷冲突后,新德里不断将有限资金大量用以采购山地武器装备,已使其海洋战略实施遭遇财政窘境。5月上旬,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Bipin Rawat)曾公开表示反对“修建第三艘航母”。(34)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India’s Defense Chief Opposes Aircraft Carrier Plans,”May 14, 2020,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5/indias-defense-chief-opposes-aircraft-carrier-plans/.对新德里寄予厚望的美国政客与学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认为,新德里在陆地边界安全的过多投入,势必影响其在“印太战略”中支点作用的发挥。(35)Christopher Clary And Vipin Narang, “India's Pangong Pickle: New Delhi's Options After Its Clash With China,” War On The Rocks, July 2, 2020,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0/07/indias-pangong-pickle-new-delhis-options-after-its-clash-with-china/.
21世纪的印度洋已不仅有印度一位主角。除了在印度洋享有独一无二地位的美国之外,中国、日本、东盟、澳大利亚、甚至法国、英国等都在不断增强各自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可以说,印度洋正在成为21世纪大国权力角逐的中心。在这种情势下,印度更难实现“以海制陆”目标。或者,新德里就是有意通过不断营造中印边境战争氛围来进行“风险投资”,以博取国际“以印制华”势力的现时好感与战略回馈。新德里历史上尝过这样的好处。例如,新德里虽然输了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但却赢来了美苏竞相拉拢的高潮。美国要把印度塑造成为“西方民主的橱窗”,苏联则要将印度树立为“社会主义的样板”。在两个超级大国攀比式外援之下,加之英国殖民时期打下的深厚底子,新生印度在1970年代之前一直位列世界七大工业国之列。
如印度所料,此次加勒万河谷冲突也确实为其赢来了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战略青睐。各国除热情表示要提供各种武器装备之外,还纷纷动议与印度开展重大项目合作,与这些国家掀起的“脱钩中国”风潮形成了巨大反差。然而,印度到底能否借由加勒万河谷冲突中的对华示强表现,摆脱其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实践所导致的陆上安全困局,甚至走出一条大国复兴之路呢?其答案显然并不那么乐观。
新德里能否将其利好的战略环境转化为国家发展的持久动能并最终实现对华“变道超车”,前景亦不明朗,因为这主要取决于国内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实质进展。然而,考虑到印度政治生态右倾偏保守,任何结构性改革,特别围绕土地、劳动力的结构性改革都难以顺畅实施。土地流、劳动力流以及物资流不畅,逐利而行的资本流最终也会不畅(36)有关印度劳动力流、土地流、物资流与资本流“四流不畅问题,可参阅胡仕胜:《中印关系中的贸易因素》,2017年11月,http://www.cb.com.cn/pk/2017_1106/1207674_6.html.。如果自身发展问题解决不了,印度政府就会缺乏解决陆地安全困局的足够财政支持,毕竟外来的援助既非不求回报更非能无限“续杯”。
对新德里而言,如其幻想“以海制陆”与“倚美制华”,不如转个思路,以陆上合作共赢安全观取代“绝对安全观”,以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取代“印度门罗主义”的政策实践。实际上,如果禀持合作共赢理念,中印两国边防交通网络建设完全可以成为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共谋大国崛起的发展平台,而非频频触发紧张与冲突的祸源。只有当边境基建突破传统思维窠臼,不再是为了拱卫“缓冲区”和“天然屏障”,而是为“彼此联通、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物质保障,中印及中印所在区域才会赢来真正而持久的和平、发展与稳定。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新德里才有可能摆脱陆锁式安全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