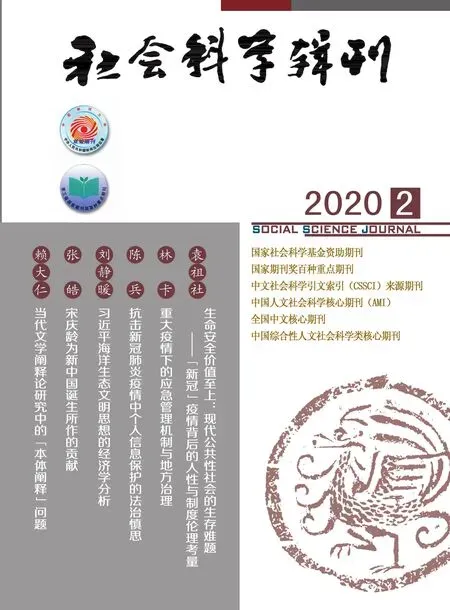日本在中国长江流域的经济倾销(1931—1937)
方 前 移
一、引言
旧海关资料将中国分为东北、华北、华中①注:根据旧海关资料统计的分析,华中是指重庆、万县、宜昌、沙市、汉口、岳州、长沙、九江、芜湖、南京、镇江、上海、苏州、杭州、宁波、温州共16 个口岸。本文中的长江流域是指前15 个口岸及其腹地,不包括温州。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年。(相当于长江流域)、华南四块区域进行研究。 长江流域在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1927—1931年平均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50%,1932 年占42%,1933 占 52%,都位居第一。 〔1〕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在中国国际贸易额中,英日美三国已经稳定成为中国前三位贸易对象国 〔2〕,长江流域是三国竞争的重要市场。 就中日贸易而言,1922—1931年,华中平均占全国输入日货总值的43%,位居第一;平均占全国对日出口贸易总值的23%,位居第二。 但是日本在华中的市场,远不如在东北的势力雄厚。 1922—1931 年,日货平均仅占华中输入洋货总值的20%,而英美分占16%、24%。 〔3〕就长江各埠贸易地位而言,1928—1933 年,仅上海一埠,就平均占全国对外贸易总值的46%。 而在上海对外贸易额国别指数比例中,日本在1928—1931 年占据第二,1932、1933 年则退居第三,分别占7%、12%,不仅落后于美国,而且低于英国。 〔4〕在汉口同样如此,据汉口日本商工会议所调查,在汉口对外贸易额中,1930 年日本占据第一,1931、1932 年则退居第三。 〔5〕
长江流域是近代日本资本最早进入的中国区域。 早在清末,曾任日清汽船会社社长的白岩龙平就曾向日本政府建议,在对清贸易政策上,要充分利用扬子江水域来扩张商业,没有比利用该航行权更有效的办法。 〔6〕日本驻汉口领事山崎上任时也说,日本在长江沿岸扩展通商贸易是头等大事。 〔7〕20 世纪日本开始加大对东北的势力渗透,但并没有忽视华中。 20 世纪30 年代,随着日本侵占东北、策动华北自治,为了与英美争夺长江流域市场,日本政府大肆实行经济倾销行为。
侵略中国是日本政府一以贯之的国家政策,目前中外学界对于近代中日经济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至于日本对长江流域区域经济侵略研究的现状也有专文总结出,相对于其他区域而言,研究成果很少。 至于立足20 世纪30 年代初期的时代背景,从倾销的角度来分析这种经济关系的成果则不多见。①有学者对水泥、煤炭倾销进行过研究,参见卢征良的《近代日本水泥业在华倾销及其原因探析》《20 世纪30 年代日本煤在中国市场倾销原因浅析》等文。此外,对“倾销” 的理解,学界存在着歧义,但是比较严谨和常见的定义是指在国外市场上以低于本国市场的价格销售商品。 〔8〕本文立足此义,试对中日在长江流域的经济关系进行短时段探讨。
二、协定关税规则及贸易统制
1843 年中英 《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 规定,中国对从英国进口货物一般征收值百抽五的进口税,开始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关税条约的历史,中国成为进口关税率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 1896年7 月,中日根据 《马关条约》 签署 《日清通商航海条约》,其第九款规定:凡货物由日本运进中国,其进口税亦比相待最优之国运进相同货物,现时及日后所输进口税,不得加多,或有殊异。 〔9〕实际上该条约承认日本在中国所有事项上都享有最惠国待遇〔10〕,日货输入中国自然开始享受与西方列强同等的低关税政策。
中国历届政府尝试提高进口关税。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与列强各国 (包括日本)进行关税谈判后,从1929 年1 月1 日起实行新进口国定税则,提高税率。 根据其前中日两国关税谈判的约定,1930 年5 月,中日两国签署 《关税协定》,其附件规定:中国政府给予从日本进口的棉货类、鱼介及海产品、麦粉三类物品以3 年期关税优待,并给予杂品进口1 年期关税优待。 〔11〕列入协定的这四类货品细目极多,如棉货类共33 种,子目更在50 种以上,各种棉货类协定税率平均较1929年的国定税率减轻30%—40%;属于鱼介及海产品者共 12 种,税率减轻 27%—46%;麦粉类,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采取免税进口政策,日本为防止中国政策变化,仍要求将免税进口规定纳入协定目录之中,以方便其当时的殖民地朝鲜、台湾地区的粮食输入中国。 杂货类列入协定税率者也有17 种。 这些货物均为日本输入中国的大宗商品。至于日本惠予中国3 年期内的商品清单,只有绣货、夏布及绸缎三类,夏布税率不减,其余两类商品日本征收从价关税从100%减到70%。 但这种互惠完全为偏惠。 据统计,1931 年中国仅从日本进口棉货类、鱼介及麦粉三类商品总值就高达75947883 海关两,而中国出口到日本协定的三类货物总值只有 5974525 海关两。 〔12〕
1933 年5 月中日关税协定期限已满,5 月15日,财政部提出关税修订案,以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动。 因为日本强占东北,中国关税损失严重,对外贸易恶化,国民政府出台1933 年进口税则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提高日本大宗商品进口税率。 棉布、绸缎、鱼介海产品、麦粉、木材、水泥、人造丝、纸、煤等主要日货税率都比1930年高。 例如,棉布、绸缎税率提高80%,人造丝、鱼类和其他水产品税率分别提高自30%到80%不等。 〔13〕同时根据 1933 年进口税则,开始征收粮食进口税,以应对西方殖民地东南亚及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地区向中国东南市场倾销粮食。
1933 年进口税则出台之后,日本各界表示强烈抗议,不肯按照新税率纳税。 5 月29 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日高信六郎会晤中国外交次长徐谟,指责中国提高进口关税,严重影响中日关系。 5 月31 日,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向国民政府抗议,修改关税税则破坏中日贸易基础。 8 月12 日,日高信六郎又向外交部抗议,新税则目的是针对日本货物,采取与他国货物差别待遇。 〔14〕除了外交交涉、施加压力之外,日本在华北、华南发动了大规模的走私活动,中国关税收入锐减。 在日本的压力下,从缓和中日关系及增加关税收入的双重角度考虑,1934 年财政部公布新的进口税则,牺牲了关税保护民族工业的职能 〔15〕,于7 月1 日施行。 该次税则与1930 年中日互惠协定的精神是一致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减低日货进口税率,以满足日本的要求。 对于主要从日本进口的鱼介海产品、纸类、印花及杂类棉布等税率大为减少,如棉货类税率减少10%—50%不等,海产品减少15%—26%。 〔16〕但日本并不满足于中国政府的妥协,仍然大规模走私。 1935 年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修改进口税则,特别是提高人造丝与白糖的进口关税,由于日本反对,最终没有实行。 〔17〕可见,在20 世纪30 年代,在列强诸国中,日货输入中国继续受到低关税率的庇护。
同时,与宣称自由贸易主义的英国相比,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贸易有着国家支持的历史传统。20 世纪30 年代,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为了稳固海外旧市场和开拓新市场,日本更加重视贸易国家统制,尤其重视输出贸易统制。 工厂与小手工业生产相得益彰,是日本工业的显著特征。 同时日本输出同业者之间在海外市场上竞争滥卖,又是日本输出贸易上的通病。 这种滥卖影响着日货在海外市场的占有率和持久力。 〔18〕
为了根本解决这一问题,日本输出统制涵盖了对输出贸易各种事务的统制,包括输出商品品质的统制、输出商品数量的统制、输出商品价格的统制、非组合成员的统制、共同设施统制等各个领域。 〔19〕例如,日本政府更加注重出口同业公会作为贸易事务统制机关的职能发挥。 1926 年9月就施行了 《输出组合法》。 1931 年,日本政府对出口同业公会 (组合)的宗旨又进行修订,规定:凡以同类商品输出者,或以同一市场为目的各业都应设立同业公会,以谋开拓市场,避免恶性竞争,统制同类商品在海外市场价格和质量。 〔20〕同业公会在日本国内和国外都有设立。 如在中国上海,日商同业之间组成纺织同业会、棉纱同业会、棉布同业会、糖商会、纸商组合、工业药品同业公会、药业组合、谷肥同业组合、海产物品组合等。 〔21〕
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市场统制更是执行着明确的规划。 1933 年初,日本外务省通令在华各地日商团体加入“日华贸易株式会社”,作为对华输出贸易统制机关,要求日本各地对华输出贸易商社及在华从事贸易的工商机关联合起来,在通商局长及商务官统制之下,发展对华贸易,总社设在大阪,在天津、青岛、上海、汉口、福州、香港 6处开设分社,管理各该区域内贸易,以谋开拓新市场。 在这种统制政策指导下,其后长江流域各埠日商机构激增,数量最为惊人。 如在上海,实业百货店株式会社与支那物产馆及北福商店鼎足而立,日本最著名的工商中心——名古屋市商会也联合日本各地工商机关在上海设立了大规模的商品介绍所。 此外,日商为逃避中国关税征收,还利用长江各埠租界地域,将各种工业移设于各埠租界。 外务省并在汉口、重庆等上游各地,增设商务官,指导日商贸易。 〔22〕日本政府对输出贸易的统制,无疑是日货在中国市场倾销强劲的重要因素。
三、汇兑倾销及反对中国改革币制
就日本国内生产价值而言,消费资料的生产价值要远远大于生产工具的生产价值,因此必须向国外市场销售过剩的消费资料,以便从国外购入服务于军事的生产工具 〔23〕,加大日本国内商品对外销售就具有国家战略意义,汇兑倾销是辅助日货对外销售的重要手段之一。 1931 年9 月,英国正式宣布放弃金本位,开始了20 世纪30 年代世界货币贬值战争。 同年12 月,日本政府实行金禁出口政策,对外汇兑即开始低降。 继之又颁布 《防止资本逃避法》,与 《汇兑管理法》 之实行,日元价格跌势更剧,汇兑倾销全力实施。 1933 年 5 月,美国上下两院正式放弃金本位,参加货币贬值战争,更使日本积极维持日元之贬值,加入世界商业战争的决心。 〔24〕例如,从 1931—1935 年,英镑贬值 39%,美元贬值 41%,日元贬值 63%。 〔25〕以日元对英美两国货币的平均外汇指数 (以平价为100)而言,1931—1935 年,相继降为 98.6、65.9、55.2、58.8、57.5,日元呈现出更大幅度的贬值。以日元对中国白银价格指数而言,1931—1935 年,相继降为 188.5、110.7、82.9、70.0、50.8。 可见,日元与中国白银货币相比,贬值更为厉害。
各国货币贬值造成各国商品输出价格指数都下降明显,如以1927 年为基准,1932 年英国输出平均价格跌落为55.8,而日本大幅跌落为37.8,因而日货在海外市场有着巨大的价格优势。 棉纺织品为英日两国输出的大宗商品,也是两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最为激烈的商品门类。 以1929—1933 年英日棉布在国外市场价格比较,英国棉布价格跌落35%,而日本棉布则跌落366%。 日元贬值也刺激日本各类商品输出量大幅度增加,1932(1930=100)至 1935 年,日货逐年输出数量指数为118—130—154—172,体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如与1932—1935 年日本输入他国商品数量指数98—102—109—115 相比,则日货输出增加趋势更为明显。 〔26〕
至于对华贸易,由于1931 年之后多重因素影响,中日货币汇率变动与两国贸易之间的关系很难量化分析,但是中日贸易问题专家蔡谦先生从相关系数分析角度,选择对1912—1931 年中日相对和平时期内两者关系进行研究,计算出1912—1931 年日货输华价值与日元对华汇率的相关系数为-0.84 之高。 从中国方面计算,1912—1931 年,输入日货价值与白银折算成美元对日汇率计算二者相关系数高达 0.90。 〔27〕20 世纪 30 年代初,这种高度相关的关系仍然存在,汇率降低,刺激日货向中国各地倾销,又以棉货为数最巨。 〔28〕如1932 年日元对白银汇率剧跌44.7%,致使日本输华的最主要8 种类型布匹,在上海售价一致较贱,未有受到日本国内棉布市场价格上升的影响。 〔29〕铜币是近代中国主要使用的小额货币单位,铸币材料主要从日本进口,1932 年的日元汇率下降,日本各种铜类材料在上海市场价格随之激降。 日本水产品也是输入中国的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因素很多,但是各类水产品在1932、1933 年随汇率升降而涨跌,例外甚少。 〔30〕与英美两国相比,近代日本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其输华商品大多中国均能生产,但是依赖汇兑倾销等手段辅助,日本对华贸易顺差,是遏制中国稚嫩工业发展的一种致命因素。
除了汇兑倾销之外,在20 世纪30 年代集团经济竞争情况下,日本大肆从中国走私白银出口,扰乱中国金融市场,企图压服中国加入日元集团。1934 年6 月,为了顾及国内白银集团的利益和控制中国货币主权,美国出台白银收购法案,国际银价上涨。 白银在世界属于一般商品,在中国却是流通主币,中国也是当时世界上用银最多的国家。 1935年四五月间,国外银价已超过国内银价50%。 〔31〕该年3 月,中国交通银行各分行调查也指出,每出口白银千元可获利 300 至 400 元。 〔32〕国内外市场银价悬殊,导致中国白银移动方向发生逆转,大量白银由上海运往沿海其他各地。 日本政府支持日、鲜浪人走私白银,分为海陆两路运往日本。在华中由崇明、海州两地运出者,每日在20 万元左右;在北方,海路由青岛、烟台等处运出,陆路由北宁铁路运出榆关,同时在大连、天津设立交易所,组织“密输团”,向外输送。 1935 年 5月,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向行政院呈文称,日、鲜浪人大肆偷运,华北每月计有400 余万元之巨流往国外。 〔33〕1935 年 6 月 2 日,铁道部长顾孟余向行政院呈文:“国人走私白银出口,可由海关处理。 如系外籍人,为免引起重大事态,移交各领事馆处置,是否妥当?” 〔34〕可见,日人凭借着治外法权的庇护,大肆运银出境。 日本基本是不产银的国家,从中国走私进口白银,再输往纽约、伦敦金融市场。 1935 年日本白银净出口比1933 年增加29 倍,其中输往英国又增加了29 倍,输往美国更增加了 71 倍。 〔35〕日本通过走私白银,获得暴利,同时削弱了中国经济,以图独霸中国。
大量白银流出,造成中国通货紧缩,经济衰败。 1935 年11 月,国民政府决定实施法币政策,日本各界表示反对。 11 月9 日,日本军部发表对华非正式宣言谓:中国强制施行白银国有,定将引起社会政治纷扰,日本对此不能忽视。 本来中国财政制度的优点在于地方化,而南京此次币制改革的目的则在于集中化,乃是错误举动。 日本外务省也发布意见:中国政府宣布购银价格较时价低减4 成,日本不能允诺。 〔36〕中国币制改革乃是与英国协议后付诸实行,显然蔑视日本立场,日本不能允诺。 10 日,日外相广田弘毅致电日使有吉明向中方提出抗议:中国此次币制改革,日本不能协力,一因日本不能同意中国以低价收取在华日本银行库存白银;二因币制改革使各地现银集中于南京中央政府,如被滥用,会危及中国经济基础,故日方坚决反对。 中国实施法币政策,废除银本位制度,造成日汇处于不利境地,如1933 年国币与日元平均汇率为1.010,1934 年为1.132,1935 年为1.259,1936 年则降为 1.023,1937年为1.020。①笔者根据旧海关资料各册中“海关金单位及关平银折合各国通行钱币数目表”统计得出。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年。显然币制改革之后,国币与日元的汇率不断下降,对日本倾销政策打击重大。 〔37〕币制改革也使得日本企图让中国加入日元集团的期望破灭。
中国币制改革政策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中国政府有无足够的白银储备来无限制地买卖外汇,维持货币稳定。 因而日本政府采取各种针对性的破坏行动。 如鼓励日商收买白银,走私出口;阻止华北当局南运白银,据统计,至抗战前,华北有高达4000 万盎斯白银不能移动;〔38〕指令日行拒绝交出现银,正金银行总行指示在华各分行,拒绝移交白银;在中国境内推广日币,如汉口、上海的日商会均准备用日币买卖交易,阻止中国法币流通。 〔39〕
四、商品倾销
世界经济危机环境下,日货倾销成为世界性问题,英美等国利用集团经济,设置贸易壁垒阻止日货倾销,中国成为日货最主要的倾销市场。
1931 年 2 月,国民政府颁布 《倾销货物税法》;1932 年 12 月,出台 《施行细则》。 1933 年 2月,倾销货物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到1934 年5月,实业部及其管辖的倾销货物审查委员会调查认为,日煤、抚顺煤、日本水泥在中国存在倾销行为。 〔40〕长江流域是日煤主要的销售市场之一,又以上海为尾闾。 日煤等级中最劣的四等煤,品质也比中国煤质量佳。 1932 年7 月,日本四等煤在上海销售市价 (包括运费及保险费价格在内)应为5.85 日元/吨,但实际倾销价格为5 日元/吨,而中国煤价格则达 10 两/吨。 〔41〕日本在东北投资的抚顺煤矿,所产煤炭品质最佳,又因南满铁路给予特别运费优惠、无需缴纳出口关税及矿产税等原因,使得余者中国煤不能与之竞争。 1932 年7 月,上海市场上抚顺煤价应为 7.67 日元/吨,实际倾销价仅为6.80 日元/吨。 因经济危机冲击东北市场,抚顺煤加大对长江流域市场的倾销,成为中国煤最主要竞争对手。 〔42〕实业部调查也认为,每桶日本水泥在日本售价为3.24 两规元,加上由日本至上海的各种费用约2.40 两规元,则在上海出货价应为5.64 两规元,但实际售价仅为3 两规元左右,而每桶国货水泥价计 5.35 两规元。 〔43〕据统计,1933 年中国进口日货水泥,仅上海一地,已达51.3275 万担,较 1932 年增加 18.8983 万担,但价值反减少 152904 金单位。 〔44〕
而对于立案审查的日本电灯泡倾销案、日本纱布在武汉倾销案、日本碳酸钙倾销案、日本人造丝倾销案,该委员会调查认为可能存在倾销嫌疑 〔45〕,而未能作出肯定的结论。 这种模糊的态度一方面与该法的倾销标准难以确立,因而实施上存在着困难有关;〔46〕另一方面经费拮据和人员不足也制约了该委员会职能的发挥。 该委员会在正式成立之前,倾销事务调查由财政部和实业部酌调人员兼办,没有专项经费开支。 〔47〕1933 年 2 月正式成立之后,就经费开支申请而言,主任委员沈叔玉向财政部呈文,申报每月开支1500 元,全年共计1.8 万元。 计算依据中,全部职员6 人 (其中官员 2 人、调查员 4 人)薪俸就占 5880 元,而列入调查费的只有7200 元。 由于经费有限,该委员会在调查倾销事务时,往往需要依靠外交人员代为调查货物在该国的价格等行情,因而沈叔玉在申请中补充说明如下:关于外国商品在国外市场之零售价格、制造成本及有无收受直接间接之奖励金及其他特别利益等项,除请驻外使领馆供给材料外,如遇须派专员赴国外调查时,所需费用还须随时呈报请领。 〔48〕显然,经费、人员的不足,增加了对日货倾销调查取证的难度,倾销调查委员会很难对倾销事实进行判定。 当然,即使认定倾销行为属实,由于中国政府的软弱,也很难采取反倾销措施。
实际上,日货输入中国,除了其企业生产技术与组织进步、毗邻中国的地理优势等外,在中国倾销很多都是不争的事实。 例如,1934 年3 月23 日 《时事新报》 载:近来为独占我们纸业市场,日纸大肆狂跌,如市场销售较多的每令毛边纸,成本至少3 元有余,连通关税2 元及一切水脚等,共需 5.3—5.4 元,而其售价仅为 4 元。 〔49〕为了抵制古巴、爪哇糖在中国竞争,三井财阀控制的台湾制糖公司、三菱财阀控制的明治制糖公司,在政府特许下,削价竞争。 1933 年 4 月,日本糖每担平均生产费13.40 元,在中国贩卖平均价格11.33 元,在日本国内贩卖价格 24.05 元。 〔50〕1933年8 月,倾销审查委员会调查也承认,日本人造丝以我国为主要市场,在上海,日货大量输入,若合运费等项,上海市价较日本为低。 〔51〕
除了上述的采取日元贬值、汇总倾销之外,日本企业还可通过降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的“社会倾销” 方式,降低生产费用,增加资本利润。 〔52〕如据方显廷先生对1930 年中日纺织厂劳动生产率统计,日厂织布工人年产额是华厂工人的 3 倍,平均工资则仅略高华厂。 〔53〕另据数量分析,1931—1935 年,日本国内生产指数(1921=100)相继为 172.6、172.2、190.3、205.5、213.6,物价指数 (1929=100)相继为 69.6、73.3、81.6、80.8、84.4,工资指数 (1926=100)相继为91.3、88.1、85.1、82.9、81.2。 〔54〕在物价、生产指数增高的情况下,工资指数仍然呈现为下降,可见社会倾销对工人的剥削程度。
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各项产业补助金,乃至依托武力,加强日货对华倾销。 如日清汽船株式会社营业于中国长江及沿海。 自1907 年成立以来,为与中英两国竞争长江航运,日清基本上一直有着日本政府的补贴,实行着运费倾销。①笔者根据浅居诚一编纂:《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三十年及其追补》的数据统计,得出此结论,东京:日清汽船,1941 年,第230、258、296、380、387 页。“九·一八” 事变之后,中国掀起抵日运动,日本对华长江航业前途惨淡,航班大多停运。 〔55〕为了复航,日本递信省提高了对日清公司的补贴。1933—1935 年,补助金分别为 78.1 万、117.5 万、105.6 万日元。 就 1934 年而言,日清公司补助金占递信省对华各航线补助金总额的72.1%,可见日本政府对于长江航运的重视。 但是在1928 至1936年间,日清年年亏损 〔56〕,除了中国抵日运动之外,日清低价运输日货,是其亏损的重要原因。如1932 年,日清决定对货客收纳半价,待营业起色时,再行增加,损失由政府补助。 〔57〕1934 年,在沪汉线,从年初开始,日清对于上下货物,私放回佣,降低运输费。 在沙 (市)宜 (昌)线,增加轮船,减收票价,伙食免费,酒资不收。 〔58〕
日本还借助其在长江流域的军事力量,威吓中国抵制日货运动,保护日货倾销。 其使用的方法,或以军舰驻迫在中国通商口岸,强迫中国地方及中央政府命令停止抵日运动;或以军舰护送日货,以陆战队保护奸商贩卖,将各地救国委员会没收的日货劫回;或以武力强制中国人民使用日货。 〔59〕在沿江各埠日领事署,增设移动警察队,支持日货公开起卸。 〔60〕因而在上海停战协定签字后,长江各都会商埠,日人经营之商店,均将货品进齐。 日本政府发放大量补助金,直接津贴各商店,一方面弥补货物滞销损失,一方减低货物成本,采取倾销政策,以与英美货物竞争。 〔61〕并努力开拓内地市场,凡运往长江上游的倾销商品,都直接运往汉口。 〔62〕
除了日本国内货物输入之外,日资企业在华生产的商品,也成为日货主要来源。 1895 年中日签署 《马关条约》,日本在列强当中首先获取了在华投资设厂的权利。 1931 年后,考虑到中国银价跌落、关税提高、劳动力成本低廉等因素,日本加快了对华直接投资的步伐。 纺织业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产业,整体设备能力也只能做到与在华日本纺织业抗衡。 〔63〕据统计,日本 (不包括殖民地台湾地区)在中国直接投资 (包括借款)占其海外投资的绝大部分,1936 年末约占87%。 〔64〕长江流域众多口岸,又以上海、汉口最为重要。 上海为全国商业中心,中外进出口商行荟萃之区,举凡各种商业之经营,中外贸易之往还,莫不以此为枢纽。 〔65〕汉口为长江中游的进出口贸易枢纽。1936 年,在中国 (不包括东北)各埠输出入贸易总值中,上海、汉口位列第一、第二。 〔66〕日本在长江流域投资,自然以上海为根据地,汉口为前哨所。 〔67〕如 1931 年日本对华 (不包括“满洲”)直接投资总数为64700 万元,内以纺织业为主的制造业占36%,金融及银行业占10%,输出入业占38%,其中43000 万元又是在上海投资,日本在华的80%纺织工业设立在上海。 〔68〕同时在30 年代,日本就近在上海投资开设洋行,基本取代欧美洋行,控制上海和日本间进出口贸易。 〔69〕这些洋行日商通晓中国语言,有些更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比较熟悉中国商业习惯,因而日本洋行一般不雇佣中国买办,而是直接雇佣跑街或高级职员。 〔70〕借助这种更经济、易于指挥的方法来加强贸易流通。日本在华企业非常注重横纵向联合,涵盖原料收购、运输、金融、产品推销的各个环节,先是倾销,垄断市场,然后提高价格,获取高利,并设在租界或通商口岸,除了地租和治安费外,不承担税赋 〔71〕,他们在中国直接生产商品,与日本国内日货一起掀起了日货倾销的热潮。 如在上海市场,1931 年日纺织厂跌价倾销开始,纱支愈细,与华纱差价愈大,日厂控制了市场。 〔72〕1933 年倾销委员会调查也认为,日纱、日布在华销售,成本确数无从探求,但售价低于成本可以断言。 〔73〕
1934 年,汉口每日纱交,日货已占 4/5,而国货只占 1/5;棉布销市,日货更占 90%以上。 〔74〕
五、大肆走私出口
除了各种倾销措施之外,日本鼓励日货向中国走私出口,更是倾销的极端表现。 1936 年5 月20日英国 《曼切斯特指导报》 社论批评说,日本在冀东之走私,殆为历来强国所施劫盗行为最可耻的事件 。 5 月24 日美国 《纽约时报》 社论也批评,日本在华走私已成为国家政策之一种工具。 〔75〕日本满铁经济调查会作为情报调查机构,也曾承认说:“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国特别排斥日货,故其采取之关税政策及输入手续,愈趋繁琐,对于此种关税政策,日本究应如何对付? 一言以弊之,即秘密贸易政策 (即走私政策)是也。” 因为“要知在目前的日满华关系下,若欲日满对外贸易发展,只有秘密贸易政策” 〔76〕。
1933 年 5 月 《塘沽协定》 签订后,因有冀东战区作为大本营,日货有组织走私开始在华北登台。 8 月,中日补定 《何梅协定》,华北战区扩大,其后随着冀东伪组织和冀察政委会这两个傀儡政权成立,日本私货更是公然在北戴河、秦皇岛起岸,自由运抵天津,再由天津而遍及全国。 〔77〕中国当局对于华北走私采取各种防止办法,如 《防止路运走私办法》 《惩治偷漏关税条例》 《稽查进口货物章程》 《私缉告密办法》 等等,但日人走私有日本军警为后盾,有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为护符,诚如 《字林西报》 通讯说:“凡诸君所需要之货物皆可随时输入,除非笨重如象者略有困难也” 〔78〕,造成了 1934—1937 年震动世界的华北大
走私。 〔79〕
1935 年 9 月至 1936 年 5 月,中国曾向日方先后抗议5 次。 如5 月15 日,外交部向日本驻华使馆提出严厉抗议:自上年8 月至本年4 月,因华北日、鲜人走私,中国关税损失达2500 万元,而本年4 月起,私货更突飞猛进,仅一个月,关税损失已达 800 万元,实为海关有史以来所未闻 〔80〕,要求日本政府阻止走私。 同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众议院会议上辩解说,华北走私猖獗的原因,一在于中国进口关税税率过高,二在于华北地方当局不愿协助中央取缔。 〔81〕6 月 16 日,新驻华大使川樾茂说,中国政府如果降低关税税率,则日本政府可以在可能范围努力阻止走私。 〔82〕实际上,日本政府鼓励走私不仅要压迫中国降低关税,而且要借走私漏税来动摇中国政府的财政基础,摧毁中国国民经济,压迫中国接受中日经济同盟计划。 〔83〕
华北私货可经津浦、平汉铁路运往长江流域。除了华北走私之外,更早的还有华南地区。 日本有田八郎外相曾在众议院会议上说,走私不限于华北,华南走私亦年达一亿日元。 华南走私以台湾、香港为根据地,以厦门、汕头为活动中心点。台湾地区当局对于华南浪人走私实行统制,在厦门、汕头都有走私总机关,在内地设有分公司、办事处,可向长江流域渗透。 如据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1932 年8 月呈报,近来日货在南京市面充斥,因日商运货均为本埠日本洋行,由下关码头直接运至城内,于晚间用汽车分送各商家,该会以外交关系,无从干涉。 〔84〕“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也更加重视长江流域外事机构的设立和作用。 南京、汉口等领事都是日外务省后起之秀。使领馆的中下级职员,大部分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东京和大阪的外国语学校毕业的中国科毕业生。 〔85〕日本领事馆假借旅行名义,派送大批先锋队分赴苏、皖各省调查走私路径与接洽私货的代销处。 〔86〕1933 年 5 月中日关税协定期满,日政府令日本所出货物尽量倾销中国,实行大规模的倾销政策,华中以上海为中心,雇佣各地熟悉商情的走狗勾结各地商店驻上海的办货员(水客),并更换商标及运输办法,加大走私〔87〕,造成长江流域私货盛行。
如以上海而言,1936 年5 月,因为日货走私缘故,上海与外埠交易,几趋停顿。 〔88〕人造丝业,据上海该同业公会1936 年报告,由于私货倾销,上海人造丝厂由去年21 家,丝织机2 万部,减少到六七家,机数三四千部。 海味业,据上海该同业公会主席葛维庵1936 年调查,现在上海本地海味销路已告绝迹,长江一带市场在下半年也必为私货所侵夺。 此外纺织业、面粉业、卷烟业、火柴业等皆是如此。 〔89〕又如 1936 年 5 月 30 日—6 月 8 日,据长江各埠电讯,5 月 31 日芜湖电,华北私货,由津浦路大宗运往合肥,向皖中倾销。6 月6 日镇江通讯,镇江糖行自华北走私发生以来,私货逐渐南侵,江北各地已有奸商代为倾销,以致私糖充斥,遍处皆有。 6 月5 日常熟通讯,此间沿江各镇私货充斥,尤以白糖为最,该地有奸商若干,集合团体专雇沙船,向旅顺、大连等处贩运而来。 杭州 6 月 8 日电,浙温、台、宁、绍、杭、沿海各地,近多有私货入境,内以人造丝最多。 同日重庆电,渝市私货充斥,沿街叫卖以布头、海味等项为多。 又成都7 日电,泸县有大批廉价由津浦路南下之私货。 〔90〕
除了这些普通货物之外,日本还加大对长江流域的毒品走私。 自晚清中英 《禁毒条约》 签订之后,至中华民国成立之初,鸦片公开贸易已被禁绝,毒品走私开始以吗啡为主,而日人成为吗啡走私主体,延绵不绝,中国政府不断控诉。1934 年驻日内瓦日本总领事曾向国联禁烟顾问委员会提交“1933 年汉口日租界关于鸦片及其他毒品之报告摘要” 书,一方面辩解在汉口日租界并无毒品制造等事;一方面又辩解当日籍侨民经查在中国城市从事非法贩卖时,日本官厅有时感觉难于处罚犯人,因为中国官厅不能供给证据,故也。 〔91〕可见陈述内容自相矛盾,显然日方以治外法权为护符,推脱责任。 日本政府对华走私毒品行为,天下公知。 在1936 年的国际禁烟顾问委员会议上,美国代表福勒就抨击说,日本在华贩卖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已成了显明卓著之事实。英国顾问赖尔也提醒日本,鸦片战争使中英两国邦交失和至百年之久,愿日本勿蹈英国覆辙。 〔92〕1937 年中国政府向国联禁烟顾问委员会报告,1936 年办处的18 件外人在中国境内参与贩毒的案件,主要为日本与朝鲜人所为,并多系在从华北至长江流域的火车上抓到。 上海公共租界的警察帕甫 (Papp)也作证指称,日本人在中国毒品制造与贩运中占控制地位。 〔93〕
在日本官方支持下,各种日货走私规模十分惊人。 棉货、糖类、人造丝等为日本出口中国大宗,也是走私输出大宗。 例如,1932 年日本对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日本棉业中心——大阪纱织业即对于日本派兵赴沪,给予积极支持,以便保持日本在长江之商业地位。 〔94〕英日作为竞争对手,1935 年上海英国商会在发表的英国对华贸易常年报告中也指出,英国纱、布在华销路,日见退缩,总计1934 年前11 个月内,对华输出额仅及1932年同时期的11%,原因之一在于日货走私 〔95〕,排挤英货。 1930 年代台湾殖民地作为日本最大糖业生产地,大举向国内走私糖类。 〔96〕1933 年因中国海关改用旋光测验法作为分类标准,糖税增加,糖价趋向昂贵,日本加大走私力度。 据海关统计,在1934 年中国海关进口总值16637276 金单位的糖货中,就有 1/4 是缉获充公之私货。 〔97〕津浦、陇海线已全为日本私糖霸占,到1936 年,上海本国糖厂几近崩溃。 〔98〕人造丝方面,1933 年中国修订进口税则,提高人造丝进口税率,日丝加大走私逃税。 在1934 年中国海关进口总值32598 金单位的人造丝中,其中 1/3 即属缉获之私货。 〔99〕至于无法缉获的私货,数量一定骇人听闻。
日货通过走私,解决其国内生产过剩恐慌,侵占中国市场,损害中国财政收入,破坏关税主权,摧残中国稚嫩的工商业。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骆耕漠准确指出:日货走私是摧毁中国国民经济最毒辣的手段,主持走私的日本政府是我们应该一致反对的敌人。 〔100〕显然,日货向中国走私,是20 世纪30 年代日本经济快速扩张的显著特征之一。
六、结语
20 世纪30 年代,在世界经济大危机冲击下,日货在世界市场倾销是国际焦点问题。 西方英美等国与其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形成经济集团,采取提高进口关税和设置贸易壁垒等方式应对日货倾销,进行贸易保护。 中国市场对于经济外向型日本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策立华北自治,建立傀儡政权之同时,仅从市场角度考虑,也需要加紧对长江流域这一中国核心区域的扩张。 日本凭借军事、外交、经济方面的实力优势,压迫中国降低进口日货关税,反对中国改革币制,加强对华输出贸易统制,加大对华直接投资规模,来为经济倾销服务。 同时采取各种倾销方式乃至武装走私等手段,对长江流域实施经济倾销,也激起了与英美在中国贸易、投资等领域的争霸战。
如在贸易领域,1935 年美国组成远东经济考察团,曾就美国资本与商品进入中国市场问题与日本政府协商。 〔101〕该视察团在对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中国进行调查后,认为1934 年的中国进口税则和日货走私等原因不利于美国商品输入中国,表示强烈不满。 〔102〕提议应由各国配合中国政府执行统一关税税则,以维持门户开放原则 〔103〕,遏制日本。 在东北、华北为日占据之后,美国非常重视长江流域的市场开拓,美国从中国进口大宗商品也是以长江流域为主〔104〕,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差异,在长江流域输入贸易方面,以英日两国竞争更为激烈,又以纺织品为主。 〔105〕如 1930 年 11 月,以纺织专家汤森爵士领衔的英国远东经济调查团调查认为,日本在中、印棉纱和布匹市场,对于英国纺织业打击重大。 〔106〕为了瓜分世界市场,1932 至1933 年英日两国多次召开民间、官方谈判,均告失败。 由于两国在世界市场各自势力范围内相互排斥对方 〔107〕,加紧对相对独立的中国长江流域市场争夺就具有决定性意义。
又如在直接投资领域,1931 年在上海的投资额占比中,英国占70.3%,日本占20.4%,美国占9.3%。 〔108〕同时上海在各国对华投资中,都占据重要地位。 如据美国远东经济考察团成员雷麦教授估计,1931 年英日美三国在上海直接投资额如下:英国147500 万元,占其在中国 (不包括东北)投资总额的76.6%;日本43000 万元,占其在中国投资总额的 (不包括东北)66.0%;美国 19500 万元,占其在中国投资总额的 (不包括东北)的64.9%。 〔109〕英国仍然位居第一,但是面临着日本日益严峻的挑战。 面对这种危机,1936 年英国财政部首席顾问罗斯在对中国进行为期10 个月的经济、财政全面调查之后,就呼吁英国政府要求国内制造业、商业、银行业密切合作,加强对中国投资。 罗斯总结说,关于供给中国,在日常消费品方面,日本确能战胜英国,但在资本供给上,英国能战胜日本。 〔110〕此外,在三国之中,美国在20 世纪30 年代长江流域对外贸易份额中占据第一,但是在直接投资领域位居最末,为了加强在长江流域市场的投资规模,1935 年美国远东经济调查团也急迫地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措施,以便资助发展美国在华各种新兴投资事业,同样体现出对在华利益的深度关切。
显然,日本选择从事经济倾销及其相关经济行为,即是引发三国对华经济争霸战的原因,也是其表现,因而不仅严重破坏中国稚嫩的民族工业发展,损害中国经济,也进一步激化了中日乃至与英美的矛盾,是日本帝国主义最终发动全面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