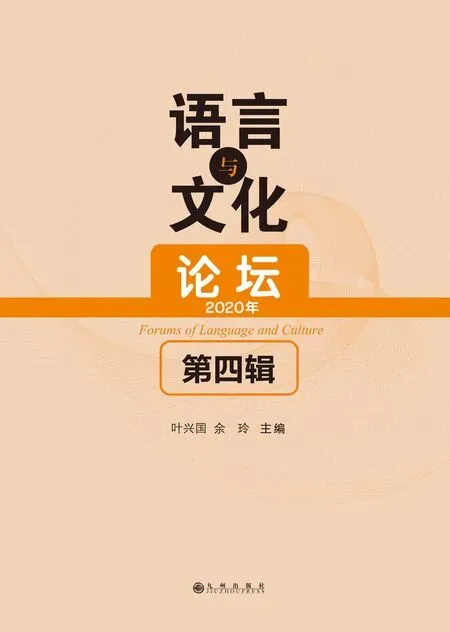关联理论认知语境观及其对隐喻理解的影响研究①
◎王昆芳
1.引 言
隐喻有助于人们有效获得知识以及互相交流,也有助于人们了解语言的本质。在早期的研究中,隐喻只用来修饰话语,渐渐地,对隐喻的研究上升到了句子层面,后来隐喻包含到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中,语言学者们开始对隐喻的认知本质进行研究。隐喻其实是人们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只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更是一种跨越不同领域的认知表达。(束定芳,2000)。关联理论语境观对隐喻的解释和理解至关重要,它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视域。隐喻的本质,在于它用具体的事物来代替比较抽象的概念。当然,这两个概念之间必须有互相的关联,它是客观事物在人们认知世界的相似性联想。由于人类认知能力具有共同性,他们对同一事物一般会有相似的联想。(徐章宏,2007)隐喻是用一种事物的描写来说明另一种相关联事物的思维以及认知模式,交际双方认知区域之间的相似性的语义基础,便是本体和喻体,而这种相似性并不是跟随语言本身的,而是在认知语境背景下创建的。为了正确理解隐喻,需要认真分析认知语境的因素, 以便获取最佳关联,直到顺利完成理解。
隐喻经常以词、词组或者句子的形式大量地存在,有时也会以篇章的形式出现。由于隐喻本身具有的内在关联,越来越多的学者着手以关联理论的框架研究隐喻,并且从“认知语境”这个概念入手,找到了很多相关的最佳关联,最终得以正确解析话语中的隐喻。很多研究者通过关联理论认知语境来分析隐喻的真正含义,进而探讨含义的推理过程以及对理解的影响。本文试着沿“认知语境”这一关联理论下的重要概念,结合此理论的一些特点,探究它在隐喻中的语用理解。
2 关联理论的认知语境观
福多(Fodor) 等的模块理论(Module Theory)、莱考夫(Lakoff ) 等的表征理论(Representation Theory)以及斯佩伯、威尔逊(Sperber , Wilson )的关联理论,构成了认知语境的主要理论基础。而Sperber 和Wilson (1986) 所提出的“关联一交际和认知理论”,是建立在Fodor 理论的基础上的,它加入了认知语境这一概念。认知框架下的语境研究更关注语境的基本单位、结构、功能和规律的研究,最终开创了语境研究的全新之路;反过来,从语言意义研究上来讲,语境研究也为它输入了新的活力。基于关联理论,人们从认知的角度对语境以及语境的特征进行探索,也为话语意思的构建、隐喻的语用研究导入了新的视角。
关联理论其实是一种认知理论,而这种理论的关键就是语境。在关联理论框架下,认知语境以“认知环境”这个概念出现,并且具有最初的解释,“一个人可以感知或者推断出的事实集合,就是他的认知环境,此认知环境是这个人所存在的物质环境和他的认知能力两者的叠加”(Sperber and Wilson,1995),定义中重点提到“感知”和“推断”,体现了认知的特点。关联理论下,交际者用概念表象的形式存留在大脑中,对世界进行假设,从而形成认知语境,来处理新的信息。学者熊学亮(1999)认为,认知环境、话语的关联性和语境效果有着直接的关系,处理话语最佳语境的过程也是寻求话语最佳关联的过程。人类对外部世界的结构化形成了知识的结构,当他们在某个情景或者频繁使用某个语言特征时,或能在其大脑中结构化,最后形成大脑中的各类关系。而当有人说到某个情景,他就会想到在这个情景下应该使用什么语言,当提到某种语言的表达,之前的情景马山又会出现在他的脑海,这就是大脑中的认知语境,它是语用因素的结构化、认知化之后产生的结果。熊学亮(1999)还进一步指出,认知语境其实是一种知识结构的状态,是人类把使用语言的相关知识概念化或者图示化了。关联理论框架下,人们的认知语境是他选取的固定知识的集合,这种选取涉及推理,又通过固定知识形式的命题式,并且受到推理演绎的制约。而命题式则由更微小的成分所组成,这些成分就叫概念,因此固定知识是由概念构成的、结构性的组合。这些概念就像记忆库中的标签或者地址,它的下面有各种各样可以被选取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则形成了关联理论的认知语境。具体来说,关联理论的认知语境具有以下特点:
2.1 动态性
根据关联理论,语用交际中的关联是常项,而语境是变项。从字面可以看到语境的基本特点:动态性。关联理论框架下,人们言语交际的过程中,通过演绎过程的记忆库,把刚得到的信息和已存在大脑中的旧信息互相结合,新的信息通过交际者的认知,激活了原来存在他头脑中的相关语境知识,为了交流的顺畅,产生动态的认知语境以供选择。对话语理解所需要的有关知识和经历是不一样的,所以构成的语境知识也不一样;而每一次交际中所构建的认知语境,之后又会留存在演绎过程的记忆库,构成一个当时的语境,接下来新输入的信息又能在其中得到演化;新旧信息交互作用,产生新的认知语境,它们不断交替和循环,认知语境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更新、补充和扩大,整个过程完全地体现了认知语境的动态性。
例如:
(1)Mark: I’m exhausted.
Alice: I’ll cook the dinner.
可以看出,Alice 的回答肯定是关联话语,但是假如依靠Mark 所给的信息,也无法解释Alice 回答的关联性。也就是说,Alice 想要理解Mark 的话,光用Mark 的信息来做语境是不可行的,还应该包含Mark 这句话所暗示的前提。
a. Mark hopes Alice will cook the dinner.
要找到Mark 话语的语境,刚才Alice 回答的语境意思是:
b. Alice will do the thing Mark hopes her to.
如果Mark 和Alice 的对话是以下的:
(2)Mark:I’m exhausted.
Alice: The soup is ready. I’ll make the main dish.
在此情景下,要找到Alice 说话的关联性理解整句话,那么Mark 使用的语境就需要包括以下隐含的前提:
The dinner is usually composed of a main dish and soup.
我们再把以上前提加到此语境中,就能够推断出Alice 所讲的语境含义应该是:
Alice will cook the dinner.
所以,Sperber 和Wilson(1995)认为,要理解话语中的语境,人们不仅需要理解文中所表达和隐示的信息,也需要了解当时的情景,还包括和此情景有关的旧信息和新信息的所有相关知识。Alice 把Mark 的话“I’m exhausted.”理解成“今晚我想让你做晚餐”。她没有理解成“我们去外面吃晚餐吧”,也没有理解成“今晚我想放松一下,找几个朋友来喝茶吧”等,因为Alice 依赖当时的情景对这种动态的语境进行了选取。依据Mark 的这句话,Alice 在自己的认知语境世界中及时进行判断和选择,把新的有用的信息传递给对方,她迅速把她会做饭的新信息和存在于Mark 头脑中的旧信息结合起来,获得新的判断,他们的语言交际因此而顺利进行。对信息进行处理时,使用者往往有多种选择的假设来构成他们的认知语境,但也不能随意做出这种选择,他们知识记忆的结构、心智活动都约束了这种选择。听话者对每一句话都可以假设出很多种,此时和语境的关系就是选择的重点,如上文所说,关联是不变的、已知的,语境才是变动的、未知的,而关联又是语境选择的核心。
2.2 完形性
传统语境一般处于零散的状态,而动态语境具有明显的完形性;传统语境的研究模式:语境被分为很多因素,这一系列因素构成了语境,然后分别研究它们的功能。但是动态语境的研究模式是不一样的,它视语境为一个整体,其中的各个因素互相关联并且作用于对方。因为存在这种完形性,各种不同信息的输入,在特定的情景下,能够激活一个动态语境的框架,而这个动态语境是人们记忆信息的合成,是一张紧密交织的信息网,这种认知语境观是以整体为特色的,它完全符合哲学科学所包含的认知论的整体主义,它密切联系语言和现实的世界,在理解句子的意思时,往往从多维的语境因素和互相关联中寻找。
关于动态语境的完形性,这不仅是它明显的特征,同时也保证了意思构建和解释,比如:
(3)Mary: Is the book you bought last time very good?
Helen: Wonderful, and the ending is quite impressive.
包括身份验证、数据纠错、数据更新、移动办公等功能。系统通过绑定用户手机号码,建立数据使用分级制,根据用户的级别,以实时验证码的方式定义系统的查询范围、修改权限等,在系统内建立用户自己的数据库。同时,为方便数据的获取与查询,开发了iOS、Android系统的移动客户端,实现数据的实时查询。
Mary: Can I borrow it please?
Helen: Of course , you may get it.
在这样简短的对话中,认知语境的完形性以及动态性一目了然:一开始Mary 的话激活了Helen 曾经买书的经历,“last time”和“the book”激活了Helen 头脑中的信息,使她选取了Mary 与Helen 都知道的某一次买书的经历,使Helen 从无数的买书经历中快速地选择了这一次,而且也确定指的是“那本书”,此时话语的动态语境有了快速的建构。“Wonderful”提示了Helen 已经看过那本书了,Mary 试着假设Helen 已经看过那本书,基于此假设,Helen 的读书经历 (假如她已读过那本书)被激活了,所以她做出了相应的回答“Wonderful”,同时也使Mary 的假设得以证实,为接下来的对话做好铺垫。接着“and the ending is quite impressive”进一步肯定了Mary 的假设,也就是她的确已看完了这本书,并且作了评价。在这段对话中,Mary 和Helen 通过输入“last time”这个信息,“the book”激活了她俩脑海中的信息,还有预设的手段,一起构成了对话理解所需要的动态语境,在结束时,“Helen has read the book”和“very good”作为被推断出的新的定论,被输入到下一轮的对话的动态语境中,而且继续存留在演绎设施的记忆体中,构建了接下去一轮动态语境的基础。而我们已经看到,Mary 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始构建她下一轮话语所需要的动态语境。“Can”是提出请求,Mary 在已经推断出的定识“Helen has read the book”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她的请求,“borrow”激活了关于借书的一系列知识结构,包括“这本书有没有”,“Helen 是否能借”,“可以借多长时间”等等,但基于Mary 与Helen 之间的关系,前面两项一定是被选取的语境信息,而前一轮会话中已经构建的认知语境的信息,为此轮会话所需要的认知语境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从而使Mary 与Helen 顺利地把它延续到新的认知语境,最后成功完成第二轮的对话。
2.3 文化特定性
国家和地域不同,人们对语言、文化和环境的认知,对自然规律的认知,直至认知语境都会大不一样。人类是具有强大的社交性的高级动物,他们在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认知经验和意识习惯,所有这些都有着强烈的文化特定性。在人们的语言交际过程中,这种文化的特性也时时影响着人们对交际意义的正确理解。在不同文化的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同一语境中,对相同的话语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最终会导致各自不一样的语境效果。比如:一对中国姐妹在英国游玩,当地的居民看着姐妹俩很漂亮,赞不绝口:“Oh, you are so pretty!”此时其中的姐妹谦虚地回答:“Oh no, you are kidding, we are not pretty at all”,这会使在场的人感到非常尴尬。这位中国女孩,她就是从中国式的传统认知语境为出发点,用谦虚的方式进行交际,而英国人有着自己的认知语境,他们难以理解女孩的回答,因为他们在得到别人的夸赞时,往往开心接受,愉悦交流。所以,文化背景不一样,人们交流的方式也大相径庭。再如, 莎翁有一首十四行诗,闻名于世,其中的开头:“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e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很多中国人在读这首诗时,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莎士比亚要把夏天和“lovely”“temperate”关联在一起,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和认知里,很多人讨厌夏天,酷暑难忍,蚊蝇乱飞。但是如果稍微了解一下英国的气候就可以理解,英国经常多雨潮湿,夏天对人们来说,绝对是天堂了。
3 认知语境对隐喻理解的影响
3.1 认知语境对隐喻理解的解释力和制约力
认知语境能调节交际双方的言语行为,约束语言的表达与理解。要理解隐喻,必须了解人的思维活动,因为它们是紧密相关、互相作用的。同样一个隐喻,听话人不同,理解会完全不一样。那是因为不同的语言使用者对世界的认知标准不一样,他们有不同的知识经验、不同的年龄;再者,人们拥有的知识体系也不一样,对隐喻的反应当然也不一样。
我们知道,隐喻的基础是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这也是必备条件。词的隐喻义一开始都是立意新颖、栩栩如生的,就像理查兹博士(1936)说过的:“隐喻意思的称呼和描写是被嫁接到另一个和本体不同的称呼和描写之上的。出现在隐喻中的喻体以及隐去的本体,有着相似之处,相同的适应性,这也是语言中通常存在的原则。”
但是,隐喻不是机械地描述人们所看到的相似性,其实它还能预示着新的相似。所有隐喻都包含两个因素:相似性与相异性,二者相互依存。没有相似性,不能称之隐喻,没有相异性,隐喻就变成一般的类比了。正因为隐喻同时拥有相似性和相异性, 它不仅能表达事物间的相似性,也可以暗示甚至引出新的相似性。隐喻中,形成意象的本体不出现,而是和喻体合并在一起。比如, Dryden 在提到莎士比亚时说:“He needed not the spectacles of books to read nature. ”这句话的意思是:莎士比亚不像透过眼镜读书的人那样,他并不借助书籍来看待社会、自然和人情。Dryden 利用隐喻,将很长的明喻表达缩减了。
当然,理解隐喻的关键条件是交际双方共同拥有的认知环境,他们共享的认知环境构成了理解隐喻的基础,也构成了理解话语的基础。此时,说话者和听话者是否成功交际的切入点和他们共处的认知环境质量、双方关系成正比:共处的认知环境越大,相互显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双方就可以更加一致地理解隐喻。
比如:
(4)The sky is crying.
要理解句中的隐喻,听话人需要确定“sky”这个词指的是自然界的天空呢,还是其他有所隐含。“sky”的喻义也可以是西方人的蓝眼睛,湛蓝的就像天空一样。清楚双方的认知语境是隐喻的大前提,认知语境不同,对隐喻的理解会大相径庭。有了共有的认知语境,交际双方才能够快速并且准确地理解隐喻的含义。
3.2 认知语境和隐喻的整合分析模式
在关联理论的认知语境分析框架下,尤其是在特定的语境条件下,可以更有力地解释对隐喻的理解。认知语境对理解隐喻和长久记忆中的概念有关,相邻概念之间的扩展会激活对隐喻的理解,给意思的多样性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基础,也延伸了寻找关联的途径;在对话语和词汇的理解中,关联理论提供了总的关联原则,在此原则下,听话者在解释语言的交际意思时,首先要以语境条件为基础进行意思的选择、建构和调整,确定概念之间的相邻关系,然后通过隐喻来推断特定的概念,从而获取隐喻的认知效果。在整个过程中,关联、语境假设与认知效果有效地相结合,构成了在特定语境下,解读隐喻的一个认知过程。
在此整合分析模式下,前提当然是关联,每一个明示话语都应该对本身的交际行为提供最佳关联性,隐喻的使用也完全一样。关联和语境假设是相互联系的,人们言语交际的过程其实是参与认知语境的过程,其中包含语境假设的选取以及拓展。此时,听话者和说话者如果在语境假设上相同点越多,说话人想传递的具体信息和听话人最终理解的结果之间就会有越大的认知关联性。(冉永平,2004)再则,在解读隐喻的关联过程中,听话者积极地形成和隐喻的本体、喻体有关联的语境假设,以某种方法把两者联系起来,积极构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特殊邻近关系,最后作为推断隐喻的参照, 进而形成特定的概念。我们知道,取得词语的比喻信息仅仅是理解整句话的一部分,获得隐喻词语认知效果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要完整理解隐喻,需要两个方面:第一是隐喻词语的比喻信息,也就是通过形成特定的概念,找到喻体所指代的本体;第二是说话者使用隐喻的意图,也可以说是隐喻所传达的语用含意或者认知效果。(Carston,1996)比如:
(5)Alice:Are you going to the concert this afternoon?
Mark:The saxophone has got ill.
此例句中,Alice 的话语是属于明示交际行为,需要激起Mark 的关联性期待,Alice假设Mark 提供的信息和她的问题“Are you going to the concert this afternoon?”有关。这个Saxophone 是语用信息的开始,它激发了该词条下的逻辑信息和百科知识。依靠常识Alice 判断是人生病而不是乐器生病,关于saxophone 逻辑方面的信息肯定是一种乐器,但是听话者关注的是该词语的内涵,也就是和这个词相关的百科知识。从已有观点看来,内涵不仅仅包含对象的基本属性或者特有属性,也包括此概念所指的对象所有相关的内容。(徐盛桓,2009)由于受到关联原则的制约,Alice 能够假设的语境是:“A saxophonist usually plays saxophone in a concert”,以此建立了“saxophone”和“saxophonist”之间的相邻关系,乐器使用者由乐器来代替,我们可以进行推断,“saxophone”比喻的就是“saxophonist”。对隐喻词的指代确定仅仅构成了完善命题的其中一部分,以关联原则为框架,听话者往往尽量朝省力的方向寻找理解隐喻的认知效果。我们可以继续理解,因为萨克斯吹奏者生病了,Alice 会觉得非常遗憾,今天下午她和Mary 无法欣赏她们期盼中的萨克斯音乐了,也许会她们会改变计划,不去参加音乐会。
在解读以上隐喻词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要理解隐喻,还需要搞清楚概念之间的相邻关系,然后通过推理隐喻来形成特定的概念,从而加强认知效果,此时,认知语境和隐喻的整合分析模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3.3 语境假设与隐喻:最佳关联
隐喻理解过程中,关联理论的“语境假设”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认知语境”的另一种表达。传统的语境包括很多因素, 比如交际时间、地点、说话方式、社会背景、人文地理和语言知识等等,关联理论的认知语境比传统的语境外延更广,它不但指具体的语境因素(比如物质环),也涉及人们多方面的认知因素,比如对事物原有的知识、推测和相关经历,它们本来存在于交际者的头脑中,遇到具体话语时,形成一连串的语境假设,关联理论框架下,语境是动态的,需要不断做出选择,例如:
(6)Chocolate: The “Food of the Gods”(程美丽,2015)
以上标题中, 本体是“chocolate”, 喻体是“Food of the Gods”。读者看到巧克力就会产生以下关联假设: a.巧克力有点贵;b.很多人喜欢吃巧克力;c. 巧克力是从可可树的种子里提炼而成的;d.巧克力来源于国外;e. 巧克力分为黑巧克力和白巧克力……但是这里作者把巧克力喻为“Food of the Gods”,这对读者来说是一新的信息,可能需要新的关联来假设:a.巧克力是上帝给人类的恩赐;b.人们认为巧克力是上等食物;等等。而在之后的文章中,读者发现,一项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巧克力对心脏病的预防起到强大的作用,适当吃巧克力对身体健康是有益的。至此,读者不能使用原来储存于头脑中的语境假设了,而必须根据文章形成新的假设,达到最佳关联,产生强大的语境效果。再比如:
(7)Personality is an iceberg. (胡平,2010)
这句话字面意思是“性格是冰山”,听话人根据已有的认知能力,会产生以下几种语境假设:
a. 冰山的特征是冷,理解为“性格是冷漠的”。
b.冰山通常只露一角,理解为“性格是深不可测的,我们不能看表象”。
c.冰山会把船撞沉,理解为“ 性格很危险,是致命的”。
以上语境假设,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在关联理论中,我们可以灵活地构建各种语境假设,听话人可以根据已有的语境信息做出调整,达到最佳关联,理解说话者真实的目的。这种语境假设的构建过程中,最佳关联是核心,也就是Sperber 和Wilson(2001)所指的关联理论的理解程序:
a.以最方便的途径,最小的努力解释话语 (通过确定指代、去除歧义、对编码内涵进行补充或者调整,对话语进行语境假设、推导隐含的意思等)。
b.如果达到了期待中的关联程度,就可以结束理解的过程。
以下同样是“Personality is an iceberg”的隐喻,看听话人是怎么使用关联理论的理解程序做出正确的推断,进而理解说话人的目的。
(8)A: A person’s personality is an iceberg.
B:Yes, that’s the reason why personality decides a person’s fate.
A: So she can’t blame others. It’s really her own fate.
此对话中,A 说:“A person’s personality is an iceberg.”,我们可能想到了之前的各种语境假设。但是此时B 的回答给了我们更多的语境补充,原有的语境假设就有可能被调整或者修改。我们可以推测,她也许遇到了不幸,但是所有发生的都是她的性格所造成的,为了达到最佳关联,我们可以理解为“她的性格是危险的”,因此可以结束整个理解程序。
隐喻的实质是一种概念代替另一种概念,这两种概念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它是客观事物在人们认知领域里的形象。以上例子看出,人们在理解隐喻时,首先需要找出隐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关联性,然后根据上下文做出推理,努力获得充分的语境效果,在新旧信息之间获得最佳关联性。
3.4 认知语境的文化对隐喻的影响
在关联理论中,同一理论框架下具有它的字面含义和非字面含义,要理解非字面含义,人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我们可以借助认知语境来推导隐含的意思,语言学中,文化和语言相互依赖,构成一个整体。在隐喻理解中,相对于其他因素的影响,认知语境下文化的作用也至关重要。
比如,各民族的文化中,对同一动物的好恶心理截然不同。如“狗”在我们的汉族文化中,很多情况下是讨厌的,大多和“狗”相关的词都是贬义的,例如: 走狗、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狗胆包天、狗嘴吐不出象牙等。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很多和“狗”相关的词语是褒义的,如: “David works like a dog.”“Love me, love my dog”。(马平2011)
说到颜色,在东西方文化中,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英语中,我们通常用“green, blue, black, yellow”等来描述人们的情感。
“green”可以隐喻为妒忌,如:“He’s green-eyed.”等同于“He’s envious”,而在中文中,人们经常用眼红来隐喻妒忌;“blue”经常是伤心、忧愁的隐喻,等同于“sad”,例如词组“in a blue mood, feel blue, have the blues”,而中文的“蓝色”却无此特殊意义;“black”可以隐喻忧郁、愤怒,等同于“very angry”,例如:“She showed me a black look.”;“yellow”可以隐喻为轻蔑,也可以表示非常胆怯,等同于“timid”,如:“The little girl was so yellow-bellied that she retreated quickly.”
由于文化的不同,人们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也受到约束,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势必受到影响。可以说,隐喻极大地显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华,在已有的认知语境下,需要深入了解相关民族的文化知识,才能正确理解隐喻。
4 结 语
本文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分别探讨了认知语境观的特点以及对隐喻理解的影响和解释力。一方面,关联理论中,认知环境有助于获得隐含的意义,而人们对于认知环境具有很大的差异,从而导致不确定的隐含意义。另一方面,因为最佳关联原则约束了听话人对于语境假设的形成,此时隐含意义的取得又是确定的,这可以在实质上解决隐喻中隐含意思的不确定性和确定性。在隐喻的理解过程中,关联理论框架下的动态语境观,用动态的模式研究隐喻的含义,为隐喻性话语的确切含义的推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只有更好地了解认知语境对隐喻性话语多方面的影响, 才能更好地掌握说话者的说话意图,听话人也才能更快速地从认知语境中提炼相关的语境假设,从而正确地推导出说话人的言外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