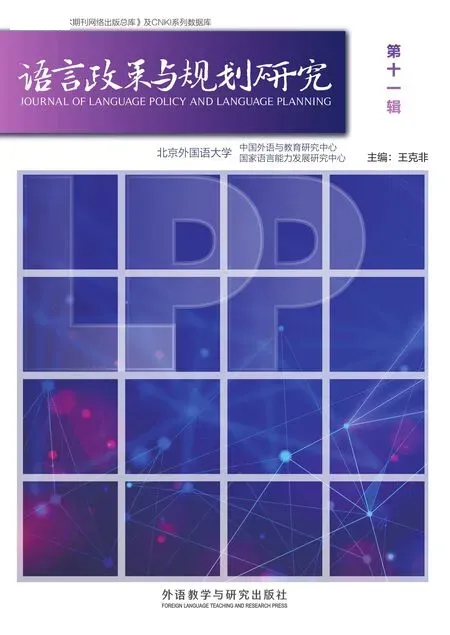土耳其库尔德语言政策述评:从隐形化到逐步开放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刘景珍
提要:库尔德人,作为土耳其境内第二大族群,是一个被“隐形化”却又异常突出的群体。本文以Kymlicka和Patten 提出的语言规划模式为依据,阐释了土耳其自建国以来在不同时期对库尔德人从隐形化到逐步开放的语言政策,探析了相关的语言意识形态及其动因。土耳其从坚定地恪守国家建设型语言规划模式到21世纪初萌生了语言保护型语言规划模式的转向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凯末尔主义、色佛尔症候群、加入欧盟的愿景以及国际形势的变换。
1 引言
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为土耳其语(Türkçe)。土耳其语被认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是土耳其人在总结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的沉痛经验之后提出的,最早见于《1876年宪章》(倪兰 等,2015)。“土耳其国父”奥斯塔法·凯末尔坚信奥斯曼帝国的衰弱和覆灭归咎于当时多文化存在的环境以及帝国对这种多样性存在的纵容,使帝国在面对外部势力操控和少数族群为寻求独立而战时显得格外脆弱(Müller,1996)。因而,语言的统一性一直被认为是国家建设的一把利刃。
目前,土耳其主要的少数族群有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保加利亚人、扎扎人、拉兹人、罗姆人、格鲁吉亚人等(Karimova et al,2001;Öztürk,2012)。然而,土耳其政府依照《洛桑条约》第37—45条的相关规定,只承认希腊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为官方认定的非穆斯林少数民族(Toktas,2006)。此外,在1925年,由于《保加利亚—土耳其友好条约》的签订,土耳其政府把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籍保加利亚基督徒纳入被官方认定的少数族群的行列,享有与其他三个少数族群一样的权益(Toktas et al,2009)。库尔德人虽然是土耳其人数最多的少数族群,但他们并没有官方认可的族群身份。Haig论述了土耳其语言规划中对库尔德语的“隐形化”处理,并将“隐形化”(invisibilisation)定义为“为弱现某一文化的目的而对该文化存在的显性标识进行特意的清除或隐藏”(Haig,2003)123。本文以土耳其库尔德人的“隐形化”处理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土耳其库尔德语言政策的历史嬗变来探究其语言意识形态和影响因素。
2 语言规划模式
在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语言意识形态是Spolsky(2004、2009)语言政策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与语言实践、语言管理共同构成语言政策分析框架的三个部分。语言意识形态就是关于语言的一系列认识、思想、价值观等。也有学者将语言意识形态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语言意识形态可能是官方的,也可能是民间大众的;第二,语言意识形态可能是有利于弱势语言的,也可能是危害弱势语言的;第三,语言意识形态还可能是制度化的(周明朗,2009)47。政治学家 Kymlicka& Patten(2003)指出,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公共辩论中,大部分对语言政策的讨论都默默地遵循了这样的二分法:国家建构型语言规划模式(nation-building model)和语言保护型语言规划模式(language-preservation model)。根据国家建设型语言规划模式,语言政策应该是推进语言同化,这样就可以确保一个国家内部只有一种通用的语言。在19—20世纪国家独立高峰期的时候,这样的理想化语言政策被认为是达成国家统一、社会团结、民主协商或实现机会平等的必要措施;而语言保护型语言规划模式则认为语言政策应致力于阻止语言同化、提倡语言多样性并保护濒危语言。他们不仅认为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对大众有益,就像保护生态多样性一样,而且认为这种语言保护也是濒危语言个体的权利。
3 土耳其库尔德语言政策的发展演变
土耳其的库尔德语言政策历经了建国初期语言改革与单语制实施合力促成的隐形化时期、“民主十年”的缓和时期、军方的再度收紧时期到世纪之交迎来语言政策的转向时期,逐步见证了国家建构型语言规划模式向语言保护型语言规划模式的转向。
3.1 语言改革与单语制推行促成的隐形化
土耳其1928年的语言革命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语言改革。语言改革的第一阶段是文字改革,即用改良的拉丁字母替换阿拉伯字母。这一改革在伊斯兰国家是史无前例的,在一定意义上象征着土耳其共和国与旧传统割裂的决心。第二阶段主要涉及土耳其语言纯洁化的各种举措。1932年,在土耳其政府的支持下,土耳其语言协会成立,主要负责土耳其语的简化与纯洁化,主要成员是政府议员和语言学家。该协会建成之时担负着两项使命:建构新的词汇系统以及探索土耳其语的渊源以便证明土耳其语是所有语言和文明的起源(Bayar,2011)123。该协会把上文提到的19世纪的改革思想逐步实现,其中包括援用土耳其语素替代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外来词以及确立以土耳其语为词根的构词原则等。在该协会的努力下第一本现代土耳其语词典(Türkçe Sözlüğü Örnek Basımı)于1942年面世,其最终版本于1945年确定(Siemieniec-Golas,2015)137。1932年以前,土耳其人使用的土耳其语词汇只占到35%—40%,而现在这个比例已达到75%—80%。这一事实是凯末尔领导的语言革命对土耳其民族卓越贡献的最有力证明。此外,受政府支持的其他各民族和语言机构在进行语言纯洁化和土耳其语现代化进程中也提出了很多学术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是由一众土耳其学者提出的 “语言日心说”(Günes Dil Teorisi/ Sun-Language Theory)。该理论宣称土耳其古老的家园中亚是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所有语言皆起源于土耳其语,还论述了库尔德语的土耳其渊源(Hassanpour,1992)。该理论一直到第一任总统凯末尔去世后才被摒弃(Shaw,2004)。
为保障单语制的有效实施,土耳其政府还对少数族群推行了较为严格的语言政策。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时,土耳其政府就将语言同化界定为民族身份和民族统一的先决条件。少数族群学校的全部课程必须由土耳其公民任教,而其中的土耳其语、历史和地理课程必须用土耳其语讲授,并且不允许新办少数族群学校(Bali ,2001)187。1924年3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政府法案,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均禁止使用库尔德语。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被“土耳其山里人”和“东部”的称谓所代替(Cemiloglu,2009)30。1925年2月,谢赫塞义德叛乱爆发但随即被政府镇压。美国库尔德问题专家罗伯特·奥尔森认为,这是库尔德民族主义的首次大规模叛乱,也是一场披着宗教外衣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李秉忠 等,2014)111,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土耳其政府语言同化的决心和进程。1925年9月,土耳其教育部发布了一条规定:所有的少数族群和外国教育机构必须保证每周5小时的土耳其语、历史和地理课(Yildiz,2001)281。谢赫塞义德叛乱之后,土耳其政府在1926年开展了《东部改革计划》。该计划不仅涉及重新安置库尔德人,而且在东部一些城镇禁止使用除土耳其语以外的其他任何语言(Yildiz,2001)247。此外,土耳其于1934年颁布《姓氏法》(Soyadi Kanunu),禁止使用指示职业、部落、外国籍的姓氏。所有的姓氏都应该选自土耳其语的名字(Yildiz,2001)236。20世纪30年代末期,土耳其政府对语言的实际使用甚至采取军事化监督,在土耳其城市和库尔德地区(当时库尔德人大都生活在农村地区)通过设置警力来对违反语言禁令的人进行罚款(Cemiloglu,2009)31。
3.2 “民主十年”库尔德语言政策的转机
1946年,共和人民党执政的土耳其政府引入多党制。在接下来的1950 年的土耳其大选中,从建国来一直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失利,民主党上台。在民主党执政期间,时任民主党主席阿德南·曼德列斯采取更自由的经济政策并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允许一些有名气的库尔德领导人在议会参政,在库尔德问题上呈现出了良好的转机。自建国27年来,土耳其首次在语言方面解除了对宗教广播、祈祷词的禁令,人们又可以用阿拉伯语而不是必须用土耳其语来进行祝祷(Howard,2001)123。由于民主党内有很多库尔德人力量,在民主党执政的十年(1950—1960年)(又被称之为“民主十年”)中,土耳其族人与库尔德族人关系较为稳定,人们的语言表达相对自由。
3.3 土耳其军方严苛的语言政策
土耳其军方作为凯末尔主义的卫道士,在语言政策监管方面,尤其是土耳其语的推行和库尔德语的隐形化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土耳其民主党政府渐趋专制,并严重波及到了经济的发展,使得民主党政府在50年代后期陷入执政危机,并最终引发了1960年的军事政变。1960年4月27日,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杰马勒·古尔塞勒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了曼德列斯政权并出任临时总统、总理兼国防部长。政变后,军方于1961年起草了的新的宪法,史称《自由宪法》。该宪法宣称赋予了人们更多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宪法第11条虽明确提出“在任何时候都要确保个人的自由”,但《选举法》中第58条又规定:“在广播、电视和其他选举宣传中,除土耳其语以外,禁止使用其他任何语言”(Arslan,2015)38。土耳其语言同化策略在1960年军事政变后实则再度深化。1959年,第7267号法令规定:任何非土耳其语且引起混淆的“村庄名”将在收到省常委会意见之后由内政部在尽可能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变更(Yildiz et al,2004)23。同时,土耳其政府还在城乡地区建设大量的广播电台,用土耳其语全天24小时播放节目,用以推广凯末尔主义思想并抵制来自于周边国家的库尔德语广播节目(Nezan,1993)68-70。1964—1965年间,土耳其政府在库尔德地区建立寄宿制学校,建议甚至强制库尔德儿童忘掉其母语,否认库尔德人的存在并使学生们以库尔德语言、文化和背景为耻(Skutnabb-Kangas,1987)308-313。这些做法不断遭到库尔德民众的抵制,到了60年代末期,各种激进组织出现并引发街头抗议、罢工、政治暗杀等社会动乱。
军方在“备忘录政变”后进一步加紧了对库尔德语的限制。1971年3月12日,土耳其军方以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可信赖的政府”为名向总统和国民议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迫使德米雷尔正义党政府被迫辞职,史称“备忘录政变”。在军方监督下,土耳其组建起一个由保守派组成的政府。1972年,在原有的对库尔德人的语言政策之外,《国民姓氏注册条例》规定,任何人不得用与土耳其文化和传统无关的名字命名;对试图给孩子取库尔德名字的家长,将以有悖道德风尚以及破坏民族文化和传统等罪名将其定罪(Ibrahim et al,2000)23。
1980年的土耳其军方政变对教育、媒体、政治和公共生活领域等主要领域的语言又进行了新一轮更加明确的管制政策。由于在土耳其新一届大选中左右势力势均力敌,议会一直不能任命一位新总统,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科南·埃夫伦等人于1980年9月12日发动武装政变,宣布解散议会和民选政府,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埃夫伦将军本人出任国家元首,建立军政府。1982版新宪法第42条规定,除土耳其语以外的其他任何语言都不得在任何教育机构以母语的形式传授给土耳其公民,并在宪法中用“母语”一词取代了先前宪法里使用的“官方语言”。第28条第2款还明确规定,不得以法律禁止的语言进行任何形式的发表或广播(Zeydanlioglu,2012)110。此外,1983年实施的《政党法》第81条规定,政治党派不能宣称土耳其有少数族群的存在并禁止保护和发展非土耳其文化和语言(Skutnabb-Kangas et al,1995)356。1983年的《语言禁令》规定,在公共场所不得使用除土耳其公民母语以外其他任何语言。在此期间,有2,800多个村庄的库尔德语名称被官方正式改用土耳其语命名(Kolcak,2016)。
总之,随着1960、1971和1980年的三次政变,凯末尔主义所维护的政治及文化统一的思想在军方的支持下不断地得到了捍卫和深化,对语言政策的管制一次比一次更严苛。
3.4 正发党政府对库尔德语言生活的适度开放
自正发党政府执政后,土耳其对库尔德语在内的语言政策进行了规划调整,体现在政治、媒体、法律和教育等语言生活中。
自从土耳其政府在1983年的《政党法》中禁止政治党派使用除土耳其语以外其他任何语言以来,此后土耳其各界政府严格执行该条例。即便是在正发党第一届(2002—2007年)和第二届(2007—2011年)任期内,该条例依旧生效。试图违反该例的政界人士都收到了严厉的刑罚(Kolcak,2016)39。欧洲人权法院谴责土耳其宪法法院的这一做法违反了欧洲人权法院第10条有关个人有表达自由权的相关规定。欧洲人权法院的决议对土耳其政治语言的改革起到了很大敦促作用,土耳其于2011年对选举活动做出修正案。新规明确了选举中可以使用的语言并允许用除土耳其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制作选举宣传标语(Arslan,2015)69。在2014版《民主进程一揽子计划》第16条明确提出将1983年的《政党法》第3条有关选举语言的所有禁令废止(Kolcak,2016)39。在此后的各级选举和政治活动中,土耳其各政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言语自由。
2002年8月第4771号土耳其政府令的实施标志着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允许广播媒体中使用人们的日常语言和方言。为了确保这项法律规定的有效实施,土耳其广播电视最高理事会在2002年底,起草了土耳其公民日常使用的语言和方言进行广播和电视播报的有关规定。这项规定中指出:仅允许公立的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使用除了土耳其语以外的其他安纳托利亚语言进行播报,这些语言包括:库尔德方言、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波斯尼亚语、拉兹语和切尔克斯语(Kolcak,2016)34。该规定同时对各档节目的播放时限和播报领域也进行了细化规定。此外,规定中还要求广播节目必须提供完整连贯的土耳其语翻译,电视节目要有土耳其语字幕。此后的几年中,土耳其人民逐步迎来了对私家电台的语言开放、各种限制的逐渐消除。正发党在第二届任期的2008年通过第5767号土耳其法令,取消了对TRT的各种语言、时限等要求。于是,2008年末至2009年初,TRT创立了一个国有的库尔德电视频道(TRT-6),用多种库尔德方言播报。对此各界争议不断,有人认为是民主发展进程的体现,还有人认为这个频道的建设只是为了抵制丹麦的库尔德民族主义频道(罗伊电视台Roj TV)。罗伊电视台于2004年建成,覆盖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全欧洲(Siddique,2009)。还有人认为库尔德电视频道(TRT-6)设在2009年1月开播,埃尔多安还在开播致辞中用库尔德语祝愿“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第六频道开播有益!”这些举措是为其在同年3月的大选助力(Arslan,2015)72。2011年3月,第6112号新版《土耳其媒体法》出台,正式破除了既往的各种宪法、法律和规定的要求,土耳其广播电视行业的语言限制至此全面放开。
1971年的军事政变之后,有关名字禁用和改名的法律及相关活动影响了各少数群族的利益。到了2003年,有关禁用非土耳其语名字的法律条例被废止,同时还剔除了宪法中第26条中有关“被禁止的语言不得被用来表达和散播思想”的条例。然而,2004年土耳其内政部发出通告来阻止使用那些包含非土耳其语字母的名字,因为《土耳其刑法典》第222条规定,使用非土耳其语字母的人要面临2到6个月监禁的惩罚。直到2014年3月13日,《2013民主进程一揽子计划》正式生效,废除了土耳其刑法中的第222条规定,各少数族群才切实地拥有了给自己及孩子命名的自由权。土耳其的部分地名也经历了类似的曲折命运。土耳其内政部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非土耳其语地名发起了“正名”活动。1949年的省级行政法中明确,非土耳其语的城镇和城市名将由议会的决议进行更改;其他非土耳其语命名的地方,包括村庄、社区和街道由内政部参照省级地方议会的意见进行更改。在此后的30年间(20世纪50至70年代),约28,000个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切尔克斯语、希腊语、库尔德语、拉兹语以及叙利亚语的地方名字,在内政部设立的“更名专家委员会”的指导下陆续改成了土耳其语地名(Kolcak,2016)37。这些更改的地名一直沿用到正发党第三届任期内。2014年,土耳其政府在第6529/2014号土耳其法令的第16条目中废除了1949年有关政府要求少数族群地区更名的条例,并启动了“复名”程序。在2014年5月,第一个库尔德地区的名字得到恢复,11月,内政部又批准了704个亚美尼亚和库尔德地区地名更改的文件,继而拉开了土耳其部分地名回归少数族群语言的热潮。
虽然正发党政府近年来对少数族群的语言使用越发民主、宽容起来,并在政治语言、媒体和法律命名机制的领域内稳进地推行着从开放到自由的语言政策,但在官方语言设定和母语教育方面还是相对保守的。2003年9月,土耳其政府批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根据该条约种族、语言和宗教少数派都被赋予了语言教育的自由,但这一条约的履行却把包括库尔德人在内的穆斯林少数派排除在外。因为根据《洛桑条约》,土耳其共和国只认可非穆斯林少数族群的语言教育权利。虽然穆斯林少数派的语言不能作为教学语言,但土耳其宪法第42条9款规定这些穆斯林少数派的语言可以作为外语出现在教学语言中。第6529/2014号土耳其法令进一步为日后私立学校用除土耳其语以外的安纳托利亚语言和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埋下了铺垫。2014年7月,土耳其教育部颁布了双语教学的有关规定,这为库尔德语等安纳托利亚语言和方言成为教学媒介语开辟了道路。然而该规定只涉及私立学校,土耳其尚未在公立学校采取相应的措施。土耳其语仍然是公立学校最主要的教学媒介语。
综观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语言政策的演变,不难看出,土耳其在国家建设初期固守并坚定地执行国家建设型语言规划政策,到了世纪之交,土耳其社会在谋求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采纳了较宽松的语言政策。民族主义斗争、国家逐步发展的政治理念和世界主流人文思想的影响共同促成了土耳其语言政策的转型,但目前的土耳其语言政策尚处在转型初期,语言保护型语言规划模式的标准还相去甚远。
4 土耳其语言规划模式转向的动因
4.1 凯末尔主义的影响
80多年来,土耳其一直奉行着凯末尔主义的建国方略,试图通过“土耳其化”来打造一个同质的民族国家。凯末尔主义的主要内涵包括:(1)共和主义:以代议民主取代专制君主,奉行人民主权、自由、法制等信条;(2)国家主义:强调国家至上,国家是推动土耳其现代化的工具,其主权不容被挑战与分裂;(3)民族主义:建立一个同质的土耳其民族国家;(4)世俗主义:与政教合一相对,不准宗教介入政治,也不许政治介入宗教;(5)民粹主义:强调人民与君主、贵族、哈里发以及封建领袖等传统统治者的对抗;(6)改良主义:以西方的新制度和新思想来取代固有的旧制度、旧思想(谢国斌,2016)。纵观共和国历史,土耳其军方可谓是凯末尔主义的忠诚卫道士。根据土耳其宪法,军队是一支超党派的力量,军人不得参加选举,不得参加任何政党,在军队内也不准有任何党派活动。军队不受文官政府领导,而且一直被民众视为土耳其民族最高理想的领袖以及世俗共和政权的保卫者。军队在国家正常时期恪守军政分离原则,在必要的危机时刻才干预政治,纠正国家的发展方向。在凯末尔主义的影响下,土耳其历届政府都致力于建设一个在宗教、族群和语言等方面都趋于土耳其化的民族国家。
4.2 色佛尔症候群症状
除了根深蒂固的凯末尔主义,土耳其政府还深受色佛尔症候群(Sevres Syndrome)的影响。1920年8月,战败的奥斯曼帝国被迫签订了《色佛尔条约》。该条约解除了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世界和北非的所有权利,准许亚美尼亚独立,让库尔德斯坦自治并让希腊占有安纳托利亚西岸(Cinar,2011)。色佛尔条约的签订给土耳其人带来了深刻教训,进而发展出色佛尔症候群并演变成色佛尔偏执狂(Sevres Paranoia),即整天担心国家主权与领土有被分裂的危险,其中尤其是提防有独立建国构想的库德尔族人的分裂(谢国斌,2016)。凯末尔主义的同质民族理想连同色佛尔症候群的阴霾严重影响着土耳其政府对少数族群语言政策的决断。从2002年到2016年,正发党领导的土耳其虽然已经开始改善少数族群的语言权利,但是这些措施只是在小心翼翼且不伤根本的推进,因为历届政府都秉承了这一理念——语言统一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必要条件。
4.3 加入欧盟的愿景
欧盟对土耳其少数族群语言权利的良性发展起到了督促作用。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为土耳其制定了“揭开面纱,穿上西装,走向西方”的立国之策,因此成为欧盟的一员是历届土耳其政府力求达到的战略目标之一,然而土耳其的入欧之旅并不顺利,有关土耳其民主与人权问题成为土耳其入欧难的症结所在。语言权利,尤其是母语教育权利是土耳其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尽管已经在使用少数族群语言和方言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但土耳其不顾欧洲委员会再三敦促始终未签署《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Otcu,2013)。欧盟必将对土耳其少数族群包括语言权利在内的文化权利提出进一步整改的建议,尤其是库尔德人的语言权利。只要土耳其入欧的国策和决心还在,土耳其少数族群或将在语言权利方面迎来更多利好的消息。
4.4 现实的国际环境
美国在库尔德问题上的立场影响着库尔德人语言权利的实现。虽然在土耳其入欧问题上,美国表现出积极支持的姿态,但这并不影响欧盟的决策。真正影响美土关系的除了目前在美国国会搁置的亚美尼亚屠杀决议案之外,就是库尔德问题了(陆倩义,1999)。虽然美国协助土耳其抓捕了库尔德斯坦工人党(以下简称库工党)领袖——奥贾兰,美土两国在扫除伊拉克北部的库工党的问题上还是产生了分歧。此外,在抵制“伊斯兰国”的斗争中美国对叙利亚民主联盟党的倚重与土耳其打击库工党过程中对叙利亚民主联盟党的仇视使美土双方分歧深化。美国在土耳其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两个盟友间左右为难(李亚男,2015),美国对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族的立场是美土双边关系的试金石。此外,伊拉克、叙利亚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兴起使土耳其对库尔德问题的处理更加谨慎。虽然库尔德人并未获得伊朗政府的允许建立自己的自治区,但伊朗的库尔德人的文化权益不受限制,因此,伊朗的库尔德问题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严重,因此库尔德人的大规模暴力行动在伊朗很罕见。海湾战争后,美国扶持伊拉克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了库尔德自治区,而后又确立了联邦制,促进了中东库尔德民族国家的建构。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因抵抗“伊斯兰国”而获得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认可和军事援助,成为维护地区稳定的中坚力量。2013年,在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领导下,当地库尔德人正式宣布成立自治政府(张瑞华,2016)。这些库尔德民族主义行动无不刺激着土耳其的神经,并不断促发色佛尔症候群效应,也使库尔德问题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也折射出土耳其政府语言政策瞻前顾后的矛盾性。
5 结语
进入21世纪以来,土耳其国内少数族群对于各自语言的保护意识逐渐增强,政府虽已有了前所未有的政策调整并呈现出积极的趋势,但对多语言共存的开放态度却也是适可而止。土耳其语言政策与语言事实之间的反差折射出其充满矛盾的政治诉求:一方面,土耳其有加入欧盟的迫切需要和成为中东地区的重要角色的愿望,因此在民主进程、宗教自由和少数族群权利方面要做出一些让步;另一方面,土耳其还要坚守自己建设理想大国的理念,全力维护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