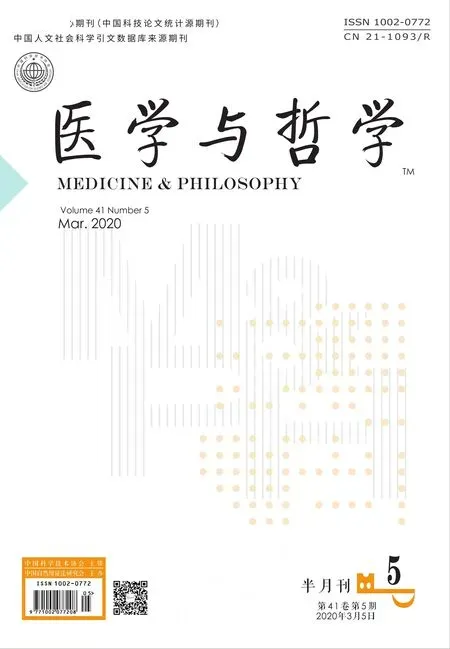论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错误*
——兼论道德无力症与冷漠症对医疗的影响
蔡 昱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医疗中经常出现两种奇怪的现象。其一,是医护人员明知按照医德的要求自己应该如何行为,即他(她)们掌握伦理原则,且其道德反省能力和判断能力是正常的,却不能按照被要求的“你应该……”去做,也就是说,他(她)们的道德实践的动力是缺失或不足的,我们可以称此现象为“道德无力症”。医疗中的道德无力症或表现为盲目遵从医院或科室的不道德的大环境(如看到周围的人都收红包,便害怕自己不收红包会成为“异类”),或表现为不能抵制名利等诱惑(如难以拒绝医药代表所给的各类“好处”)。道德无力症既破坏医患关系,也使医护人员陷入悔恨和自我怀疑。其二,是医护人员认为自己已经按照医学伦理原则处理医患关系了,但因他(她)们所行的是一种冷冰冰的“道德”实践,患者会因此感到羞辱、委屈和愤怒,从而发生冲突与投诉。我们可以称之为冷漠的道德实践,即“道德冷漠症”。道德冷漠症中,医患之间有厚厚的隔膜感,或表现为冷冰冰地遵守医学伦理原则,或表现为将爱与同情作为获取名利的手段而进行的道德表演。道德无力症和道德冷漠症致使西方主流伦理理论指导下的医学伦理教育的作用大打折扣。
显然,道德无力症和道德冷漠症并不局限于医疗,它们是当代社会道德危机的表现形式。究其原因,一方面,道德无力症暴露了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道德主体的道德实践与人类生命的本真驱动力相分离,即道德实践不能表达生命的本真需要;另一方面,道德冷漠症暴露了此种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中无法通达他人而形成真正属人的,即可以呵护人之为人的尊严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道德实践和道德关系不能满足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需要。总之,两者都表明了西方主流伦理理论下的道德主体的道德实践能力的缺失,同时,道德和人的本真需要相分离,即道德没有扎根于人的生命。由此我们发现,只有扎根于人的生命的道德实践和道德关系才能解决道德无力症和道德冷漠症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重塑扎根于生命的道德基础。本文的讨论正是源于上述思考。
本文将首先以人的弱点为切入点探讨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由此回答满足人的本真存在方式需要的属人的社会关系和生命实践应是什么样的;进而回答扎根于生命,即扎根于生命的本真驱动力从而达成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是什么,由此便可重塑扎根于生命的道德基础;之后将探讨扎根于生命的道德实践的道德主体需要具有哪些道德实践能力;由此将发现“原子式个体”不具备道德实践能力,而“超个体的个体”才具备道德实践能力。因此,道德无力症和道德冷漠症的根源在于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错误,即以“原子式个体”充任道德主体。通过抛弃此错误前提,以“超个体的个体”为本位的生命哲学与道德哲学既超越了那些建立在抛弃了人的生命境况的庸俗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的伦理学,也超越了那些建立在无法真正连接生命境况和生存境况的狭隘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伦理学。下文将以人之弱点视角探讨人的本真存在方式。
1 “畏死的恐惧”及人的本真存在方式
人的使命是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能力和潜能,从而成为自己,这是人的内在目的。然而,它常因人的弱点,即“畏死的恐惧”而被扭曲或遮蔽。人的弱点是笔者在之前对人类自身的理解的基础上填补的一块被普遍遗漏的碎片,透过这块碎片,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人类图景”。
1.1 人之弱点——畏死的恐惧
毋庸置疑,人具有急切的自我保存的需要,即生存必须性的需要。正是生存必须性的需要所具有的急迫性,使得生存必须性及其所引发的“畏死的恐惧”,即“对生存性安全感意义上的匮乏的恐惧”,成了对人之自由的一种内在胁迫,即生存必须性的胁迫。生存必须性的胁迫及“畏死的恐惧”是人的弱点。如果被“畏死的恐惧”摄住,便会盲目追求生存性的安全感,从而被他人以虚假的安全为诱饵操控着,将宝贵的生命力虚耗在偏离自我实现的内在目的的外在目的上,进而失落自由而被奴役。
生存必须性的胁迫所引发的“畏死的恐惧”包括两个方面的“对匮乏的恐惧”:首先,是物质性生存必须性胁迫所引发的“对物质性匮乏的恐惧”。具体地说,人是生物性的存在,需要一定的物质以维持生存,否则就会灭亡,由此便产生了“对物质性匮乏的恐惧”。当代,此种恐惧可能来自真实的匮乏,更多的则来自被他人或社会制造的虚假的匮乏。如果某种机制制造了虚假的匮乏从而引发匮乏感,便会迫使人们盲目追求对“匮乏”的满足,从而挟持了人的目的。 其次,是社会性生存必须性胁迫所引发的“对社会性生存安全感意义上的匮乏的恐惧”(简称“社会性匮乏的恐惧”),即“对不被他人或社会认同的恐惧”。具体地说,人是社会性存在,需要与他人在物质、情感和精神上形成关联,不可孤立地生存,由此就引发了对被社会孤立的恐惧。如果某种机制制造了“孤立感”,则会引发社会生存性安全感意义上的匮乏感,它会使人以窒息本真自我和牺牲内在自由为代价与他人关联以追求虚假的安全[1]。
总之,如果没有勇气超越“畏死的恐惧”,就会被“匮乏感”封闭在(盲目追逐生存性安全感意义上的)“仅仅为了活着的目的”和“严格的私人性”(即深深扎根于相互分离的身体及其抽象物——名字,盲目追逐生存性安全感意义上的“仅仅为了活着的目的”下的“对小我的有用性”)中。对个体自身而言,这是弱小恐惧、盲目追逐和盲目屈从的原因;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这是疏离和斗争的来源。
1.2 人之存在的特征及其一体两面性
人之弱点造成了人之存在的一体两面性。一方面,人具有独特的存在特征,即自我选择下的“共在”与“(‘为其所是’意义上的)自在”的并存,也即“整体关联之在”。具体地说,人不能弃绝与他人的交往而孤立地存在,否则就不能生存;但同时,人又与其他自然物不同,他有自我意识。他的存在感、自我意识和自我同一感使其要求在思维、情感、选择和行为中确证自己,即人需要独立的存在感。因此,人既要与外界互动关联,又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即不失落自己的存在而被周围吞噬。另一方面,无论人的“共在”还是“自在”都需要克服“畏死的恐惧”。具体地说,人只有超越了将其言语和行动抛回自身的“畏死的恐惧”(即物质性或社会性的匮乏感),才能有勇气突破“严格的私人性”,从而摆脱相互言语与行动中的“对小我的有用性”的“神秘参与”而获得相互通达的能力,才可能超越封闭在“严格的私人性”中的“原子式个体”的状态而成为“超个体的个体”[2],即有勇气和能力“伸出手来拉住对方”形成真正属人的社会关系。与此同时,只有在这种属人的社会关系和其所扩展的属人的世界中,他人、关系与社会才不再成为自我实现的障碍。此时,个体的独立性、个体性和自我存在感不会被整体或类所吸收吞没,反而会在自我与外界的关联与整全中得到彰显和确证。
2 重塑扎根于生命的道德基础
2.1 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是人的本真需要
2.1.1 满足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生命实践——互慈和创
我们已知,人的本真存在方式应是“共在”与“自在”并存的“整体关联之在”,只有同时满足人的本真存在的一体两面性的行为才能成为人的本真的生命实践,笔者称之为“互慈和创”。具体地说,“慈”是生命固有的本真驱动力,此种驱动力肯定、成全与创化生命,它既指向整合,又指向创造,即在整合中创造,在创造中整合,在整全与创造中超越。“慈”以其超越性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扩展将人链接成永恒的“人类生命共同体”,也即每一个人类的个体都是潜在的永恒的“人类生命共同体”,由此也赋予了人类个体以“与永恒相关的生命意义”。
“互慈和创”是由“慈”推动的人与人之间肯定、成全与扩展双方自我,肯定、成全与扩展双方生命的,协同创造的有意识的生命实践活动。在其中,人们能以“慈”所赋予的与永恒相关的生命意义推开畏死的恐惧,从而具有真正的安全感,即获得“选择自己的自我”的勇气和能力。由此可见,“互慈和创”是人的(区别于虚幻的自由和形式的自由的)“实在的自由”的表现、确认和获得方式[3]。
2.1.2 满足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社会关系——“生-生”式的社会关系
通过“互慈和创”的本真的生命实践,人们之间达成了符合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相互承认与协同创生的“生-生”式的非对象性的属人的社会关系。在其中,双方的人格都被承认,双方的本真需要都被满足,即双方都被允许“如其说是”地存在与行动。同时,双方也都通过将对方的需要当作自己的需要而形成的“我们”而超越了“原子式个体”的“严格的私人性”,从而相互扩展和创生了双方的生命。
2.1.3 “互慈和创”是道德实践,“生-生”式的社会关系是道德关系
在这种“生-生”式的属人的社会关系中,每个人都不把对方当作观察、研究与利用的客体或对象,更不把对方视为可操纵的工具,而是在相互合作的过程中扩展、创化和实现双方的生命。因此,这种互为目的的属人的社会关系本身就是道德关系,而达成此道德关系的“互慈和创”的生命实践就是本真的道德实践。
2.1.4 道德是人的本真需要
由此可见,道德行为(本真的生命实践)就是由人的本真的生命驱动力(慈)所推动的本真的生命实践,而“生-生”式的道德关系(属人的社会关系)则是人的本真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道德(无论是道德行为,还是道德关系)是人的本真需要。由此,我们将道德扎根在了生生不息和刚劲有力的生命之中,即道德行为是出于生命的本真驱动力而指向人(自己、对方和人类生命共同体)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本真需要的本真的生命实践,它作为“自由的必然性”体现了对自己、对方和人类生命共同体的责任。
总之,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是人的本真需要,人的本真存在和实在的自由就体现在他的道德实践中。
2.2 道德权威性的根据
所谓“道德权威性的依据”是指道德依据什么而对我们具有权威性,即我们因为什么而一定要遵守道德。于古代,道德权威性是由宇宙法则,或“道”来保证的。于中世纪,道德权威性的根据来自上帝。需要说明的是,上帝于两个方面保证了道德的权威性。一方面,上帝以其绝对权威保证了来自于他的道德律令和行为规范的普遍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通过爱上帝,人类可以部分地克服将其言语和行动抛回自身的“畏死的恐惧”从而获得道德实践能力,进而使道德实践具有有效性。文艺复兴和欧洲启蒙之后,随着神的权威衰落,人类不仅失去了绝对的普遍的道德权威性的依据,致使各种道德相对主义蔓延至今,并导致了当代的道德虚无主义;同时,人们也失去了凭借上帝(这一外在的、具有永恒性的“权威大他”)超越畏死的恐惧而获得道德实践能力的可能性。绝对的道德权威性的根据的缺失是当代道德哲学所面临的根本困惑,也是人类继续同生共存所面临的根本挑战!
然而,当我们将道德扎根于生生不息和刚劲不已的生命时,也即当我们确认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是人的本真需要时,便将道德权威性的根据建立在了内在的、绝对而普遍的根据之上,即“人类生命共同体”这一“内在的永恒的大我”和人的本真存在方式(“整体关联之在”)这一属人的社会性意义上的“人的本真需要”之上,从而拯救了道德相对主义所带来的道德虚无化的危机;与此同时,道德实践和道德关系都是由“慈”这一生命的本真驱动力所驱动的,后者所具有的整全与创生基础上的超越性得以使每一个人类个体都成为潜在的“人类生命共同体”,其所蕴含的“与永恒相关的生命意义”可以推开“畏死的恐惧”,即赋予道德主体以道德实践能力,也使道德实践具有普遍的有效性。
2.3 道德实践出于“内在自由”,达于“实在的自由”
需要注意的是,道德实践既是自由之子,又是自由之父,即它出于“内在自由”,达于“实在的自由”。具体地说,一方面,道德实践是自由之子,即它出于通过(人们对自己是“潜在的人类生命共同体”的确认而被赋予的)“与永恒相关的生命意义”对“畏死恐惧”的超越而获得的内在自由;另一方面,道德实践也是自由之父,即它是“实在的自由”的实现方式。具体地说,人们通过作为本真的生命实践的道德行为,及通过此种道德实践所结成的“生-生”式的道德关系及其所拓展的道德世界实现了“共在”与“自在”并存的人的本真的存在方式,使得人的潜在的自由本性得以实现,即获得了“实在的自由”。也就是说,在道德行为中,人首先需要摆脱生存性的“恐惧感”和“匮乏感”的逼迫,才有可能在“慈”驱动的道德实践中使自由得到现实化。
3 道德主体应具备的道德实践能力
道德实践的有效性依赖于道德主体具备的道德实践能力。道德实践能力是指区别于道德认知能力和道德判断能力的,践行“互慈和创”的道德实践从而形成“生-生”式的道德关系的能力。
首先,道德实践的有效性需要主体具备“内在自由”意义上的“独立能力”,即通过超越“畏死的恐惧”而摆脱“匮乏感”逼迫下的盲目追逐而获得内在自由,进而具有“选择自己的自我”的勇气和能力,体现为既独立于“恐惧”的逼迫,又独立于“匮乏感”所指向的对象的“诱惑”。18世纪的启蒙道德思想家笃信道德动机或意向的独立性,而后者需要以康德意义上的伦理性的消极自由来保障。具体地说,康德认为以被欲求的对象为意志决定根据的行为是不自由的,是役于物的(用叔本华的理论来说,是被盲目意志摆布的)。而只有摆脱这类奴役和摆布而获得康德所谓的消极自由,才能使善良意志及其推动的道德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善良意志是建立在消极自由基础上的自由意志。我们以“畏死的恐惧”理论进行分析,发现康德所谓的消极自由,本质上是超越了生存必须性胁迫及“畏死的恐惧”的内在自由,它是自由意志或善良意志的基础。可惜无论康德还是叔本华,都没有发现造成人类“役于物”(康德语),或被“摩耶之幕”(叔本华语)下的盲目意志逼迫[4]的原因在于“畏死的恐惧”,因此,他们没有发现超越“畏死的恐惧”是获得内在自由的有效途径。
其次,道德主体需要具有通达能力,这是被伦理思想家普遍忽略的。毋庸置疑,“互慈和创”的道德实践和“生-生”式的属人的道德关系的形成都需要通达能力,即通过言语和沟通而对双方的本真需要进行相互了解和交流的能力。此通达能力的形成必须去除“生存性恐惧”的障碍。原因在于,后者会将人限制在“严格的私人性”中,即对其所遭遇的任何事情,包括他人的言语和行为,都会反射性地机械性地用“对生存性小我(即扎根于相互分离的身体及其延伸物的生存性安全感意义上的仅仅为了活着的目的下的那些需要)的有用性”来衡量,也即“生存性小我”及其(基于“对小我的有用性”的)反射性的机械性的情绪冲动成了相互通达的障碍。
最后,道德主体需要“勇气”,即无论“独立能力”还是“通达能力”的获得,都需要具有超越“畏死的恐惧”的勇气,这同样是被伦理学家普遍忽略的。具体地说,一方面,只有具有了超越“畏死的恐惧”的勇气,才可能具有内在自由,即有能力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忠实于自己,从而肯定自己的存在和肯定自己的生命,也即具有独立性。这正是古希腊将“勇气”作为成就卓越(即向世界彰显“我是谁”,而不是“我是什么”)的前提,和获得“公民”资格的“首要政治德性”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只有具有了超越“将所有的言语与行动都抛回自身的畏死的恐惧”的勇气,才能突破“严格的私人性”而获得通达能力,从而使得“相互言说”,进而使得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成为可能。
总之,勇气、内在自由意义上的独立能力和通达能力(及其基础上的相互言说)是具有道德实践能力的人的根本表征。
4 人的两重境况中的两种个体及其道德实践能力
根据“能否超越畏死的恐惧”,我们将人类的生活境况和其中的个体分为两种,即超越了“畏死的恐惧”的“超个体的个体”,和不能超越“畏死的恐惧”的“原子式个体”。前者具有道德实践能力而处于生命的本真存在境况,即生命性(或道德性)境况;后者不具备道德实践能力而失落了存在,即处于生存性境况[5]。
4.1 生存境况中的“原子式个体”
被“畏死的恐惧”摄住从而封闭在“仅仅为了活着的目的”和“严格的私人性”中的生存性境况中的“原子式个体”是“萎缩者”和“匮乏者”,他们失去了道德实践能力。原因在于:(1)“原子式个体”失去了内在自由意义上的独立能力。具体地说,失去了“共在”的“原子式个体”面临着“他人即地狱”的处境,即处于“生存性安全感意义上的匮乏,即不自足”的状态,表现为对匮乏所指向的“需要”(即匮乏对象)的盲目追逐,即被匮乏感及恐惧感支配而陷入康德所谓的“役于物”的对象性范式的欲望中,失去了意志自由,从而失去了实践“出于自由的道德”的可能性。(2)“原子式个体”失去了通达能力而无法相互言说。具体地说,这里的“无法言说”并不是指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而是指失去了表达自我的本真需要和理解他人的本真需要的能力。究其原因,首先,如前所述,原子式的个体因恐惧而被阉割了内在自由,从而失去了“选择自己的自我”的勇气和能力,也就难以表达自己的本真需要;其次,如果人们对他人的言语和行为都反射性地以“对小我的有用性”来衡量和歪曲,便无法真正“听到”对方的需要,从而失去相互言说的有效性,即失去了相互通达的能力。此时,“原子式个体”的言语和行动都被恐惧抛回自身,失去了结成“生-生”式的道德关系的可能性,即失去了实践“达于自由的道德”的可能性。(3)以上这些都是“原子式个体”不具备超越“畏死的恐惧”的“勇气”而造成的。
4.2 生命境况中的“超个体的个体”
当人们有勇气超越“畏死的恐惧”,摆脱了“匮乏感”的逼迫和对象性的生存性意欲的强制,就摆脱了叔本华所谓的盲目意志的支配而具备了内在自由,进入了生命性境况。其中的个体既是超越了“严格的私人性”从而具有通达能力的“超个体的个体”,又是超越了“畏死的恐惧”从而具备了“选择自己的自我”的勇气和能力的具有独立性的“强壮的个体”,总之,是具有道德实践能力的个体。
在生命境况中,强壮的“超个体的个体”以勇气推开了“畏死的恐惧”,使得生命固有的本真驱动力得以呈现,进而使其所推动的道德实践和道德关系成为可能,后者进一步扩展便是真正属人的世界,即道德的世界。于道德关系和道德世界中,人们达成了本真的存在方式,即“整体关联之在”,并实现、扩展和创化了自我、对方和“我们”的生命,使自由得到现实化。
综上,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是排斥恐惧的,它们只存在于超越了“畏死的恐惧”的生命境况中,并由本真的生命驱动力(“慈”)来推动。同时,道德主体只能是超越了“畏死的恐惧”而具备道德实践能力的“超个体的个体”,而不是被“畏死的恐惧”阉割了“通达性”和“独立性”的“原子式的个体”。
5 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错误及其引发的道德无力症和道德冷漠症
欧洲文艺复兴和之后的启蒙运动发现了人,发现了人的个体化的需求,却误将“原子式个体”当作人的本真存在方式,并误认“原子式个体”为道德主体。如前所述,“原子式个体”被“恐惧感”和“匮乏感”阉割了道德实践能力,是无法承担道德实践和道德关系的。正是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这个前提错误造成了道德无力症和道德冷漠症。
5.1 西方当代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错误
当代主流伦理理论主要是义务论伦理学、功利主义和美德伦理学,它们都误将“原子式个体”作为道德主体。具体地说,从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开始,西方在伦理上就陷入了范式错误,即以认知式反思的“主-客”结构套用在本是“生-生”结构的生命或道德关系中,后者将自我与周围割裂而凸显出来成为“原子式”的存在。康德继承了这种认知范式,其纯粹理性作为理念,与经验割裂。且认知性反思结构决定了道德主体只能是“原子式个体”;功利主义本身就是以“原子式个体”的生存性匮乏感的满足定义“功利”,并以生存安全感意义上的仅仅为了活着的某种目的作为目的论预设,从而偏离了自然法意义上的道德客观性;当代美德伦理学对其主体一直是语焉不详的,同时,各种美德的内涵同样语焉不详并具有相对性的特征,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当代美德伦理学的主体更多的是“原子式个体”或“原子式集体”。
5.2 道德无力症
对于义务论伦理学来讲,以“原子式个体”作为道德主体造成了“道德无力症”。简而言之,“原子式个体”是生命与存在被“恐惧之纱”遮蔽的状态,是与生命隔离的,因此,以“原子式个体”作为道德主体,就使道德失去了鲜活的生命本真驱动力的支撑,即失去了有效的道德动力。具体地说,认为人是以匮乏性的“原子式个体”的形式而存在,使得康德将所有意欲都归为盲目追逐的“役于物”意义上的他律的对象式范式而逐出道德领域,并将人类无法摆脱这种对象性的意欲作为人类的基本境况和其理论前提。由此,既无法发现(超越了“畏死的恐惧”而具有生存性安全感意义上的自足性和通达性的“超个体的个体”之间的)“生-生”式的非对象性的本真的生命意欲,又错失了将道德建立于生命本真驱动力的可能性。虽然对康德而言,其道德律令表现为“自律”,即自我立法,但它隔离于刚劲的生命内在于“原子式个体”的普遍理智之中,后者对道德律的“尊重”难以抵抗“畏死的恐惧”及反射性的机械性的情绪冲动,无法有效推动道德行为,即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对于道德实践是无力与不生产的。
5.3 道德冷漠症
以“原子式个体”作为道德主体还造成了“道德冷漠症”,即冷漠的道德。原因在于,“原子式个体”是失去了通达能力的,即其所有的言语和行为都被“畏死的恐惧”抛回自身。因而,关系双方的隔膜感,及对方心理的恐惧、疏离、冷漠和算计是可以被觉察出来的。同时,在社会对个体的美德的要求或伦理律则的要求下,“原子式个体”因恐惧而表演的“道德表象”会被他人感觉为“伪”,原因在于此种情形中的“原子式个体”的“道德行为”或“美德”仅仅是依照“剧本”的表演,其本质是将道德作为以盲目追逐的方式获得物质生存性安全感,或以盲目屈从的方式获得社会生存性安全感(即自保)的手段。这是我们无法对道德表演者感到亲切的根本原因。
义务论伦理学的“道德冷漠症”还存在另外一个原因,即康德基于与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决裂而坚持纯粹理性下的彻底的义务论立场,从而误将本真的生命驱动力的表达,作为通达性情感的“同情”与“爱”作为“偏好”驱除出道德领域。这在其“慈善家案例”中表达得相当清晰,他认为因富有同情心而行善并不具有道德价值,因为道德价值体现为“不能出自偏好,而只能是出自义务去做出这些行为”[6]。在某种机缘下,人自己的悲伤消解了其对他人的同情时,即当他变得冷漠时,他才能仅仅出于义务而行善,其行为才具备道德价值。由此可见,在义务论伦理学的视角下,后者,即冷漠的人,比温暖的充满同情的人更近于道德,这显然是违背常识的。这种现象的更深层的原因仍然在于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的前提错误,即让封闭于“严格的私人性”中的“原子式个体”承担了其根本无力承担的道德责任。具体地说,“原子式个体”因恐惧而无法超越“严格的私人性”,即将言语和行为抛回自身(对小我的有用性)。因此,其所表现出的“爱”与“同情”并不是建立在“慈”基础上的通达性的情感,而是以“对小我有用性”审慎考虑后而被评价为“有用”的手段。本质上,它们根植于“恐惧感”和“匮乏感”,并最终指向对匮乏对象的盲目追逐或私人占有。这是康德将“原子式个体”所表现的“爱”与“同情”逐出道德领域的根本原因。
6 道德无力症与道德冷漠症对医疗的影响及对“勇气”的呼唤
当前,世界范围内医患关系异常紧张,纠纷甚至暴力频发,这些都与主流伦理学的前提错误所导致的道德无力症与道德冷漠症息息相关。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医生是康德意义上的他律的,即被“匮乏感”逼迫而“役于物”,同时,又丧失了“慈”基础上的通达性,包括通达性的情感(如爱与同情)和通达性的言说能力,即成为了“原子式的个体”,则本真的医德便成为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再者,如果医生仅仅因为害怕被惩罚,或仅仅出于“不得不”的被动的义务感,或仅仅因为希望得到奖励或顺利晋升而冷冰冰地履行遵守医学伦理原则的义务,或表演其所学到的和被要求的医德,那么即使他表演得很努力,医术上也没有缺陷,病人仍不会感觉自己是被当作人来对待的,即感到羞辱、愤怒和难过。原因在于:本真的道德行为是温暖而有力的“互慈和创”,本真的道德关系是在“互慈和创”中形成的“生-生”式的相互承认与相互创生的生命本真的存在方式,本真的医患关系是“互慈和创”的“医患生命共同体”,而这些都是人之为人的本真需要,即道德与生命本是统一的,道德与幸福也是统一的。
医疗上的道德无力症与道德冷漠症呼唤医德中“勇气”的培养,即只有具备勇气,我们才能成为具有道德实践能力的“超个体的个体”。而勇气的培养关涉超越“畏死的恐惧”的重大命题,我们称之为“人类文明再启蒙”。关于勇气的培养和人类文明再启蒙我们将另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