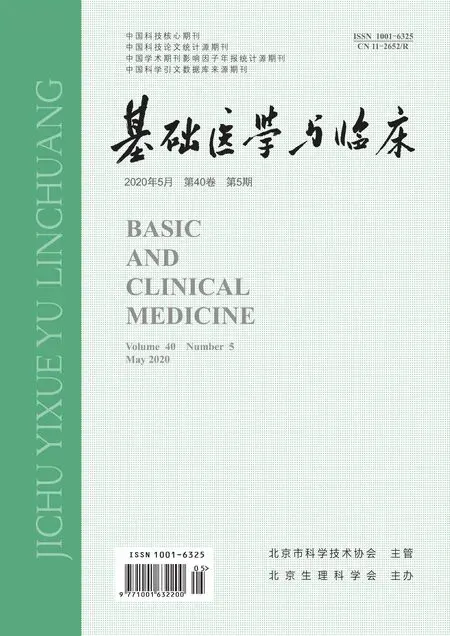黄家驷教授与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
王向华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天津 300192)
黄家驷教授是我国杰出的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胸心外科专家。他不仅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老院长、老校长,而且是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和生物医学工程研究室是在他的倡导下组建,生物医学工程第一个科研发展规划是在他的主持下审批通过。他先后担任第一任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组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主编。他通晓欧美医学科学体系,先后担任美国胸腔外科专家委员会创始委员、苏联医学科学院国外院士,并获得美国医学会世界医学教育家奖,对包括生物医学工程学在内的国际医学科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1 前瞻医学科学未来,积极倡导生物医学工程研究
黄家驷一贯关注国内外医学科学发展的动向,多次著文介绍医学及外科学在国内外的进展,展望现代化建设的趋势和方向。早在1962年,他就邀请张孝骞等教授一起商谈医学遗传学的规划。他发表在《中国科学院院刊》的《医学科学研究的某些重要进展》则深刻剖析了现代医学科学在预防医学研究、 临床医学研究、 药物抗菌素生物制品研究、中西医结合研究、基础医学研究和生物医学工程学研究等多个领域的发展趋向。概况总结了中国医学科学的成就和不足,明确指出了医学科学的发展总是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伴相随。当前不同学科之间交叉融合日趋明显,尤其是分子生物学和电子学已经成为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现代化的带头学科和有力工具,为中国医学科学研究发展指明了方向。
国际上生物医学工程学在20世纪50~60年代已进入快速发展期,人工器官和医用高分子材料应用迅速。中国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起步晚, 直到20世纪70年代,生物医学工程学才逐渐被我国医学界所关注。作为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倡导者,黄家驷以他特有的学者的敏感和远见卓识,充分意识到工程技术将对医学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认为“生物医学工程学是综合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原理和方法, 从工程学角度了解和认识人的生命过程,并以其独有的特点配合医学解决防病治病问题, 以达到维护人类健康为目的的一门应用科学[1]。”因此,即使在古稀之年,他仍以老骥伏枥的精神立即对该学科知识进行了宣传、介绍和普及,倡导与扶持这门边缘学科在中国的发展。1974年6月,他亲自出席在天津举办的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第一次全国性学术活动——医用高分子座谈会,并给予热情支持。会后,他马上向卫生部领导汇报,积极倡导在我国开展生物医学工程学研究,建立研究基地,先后在上海、广州、天津等地开展人工心脏实验研究,逐步组织起由医务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队伍。
2 借全国科学大会春风,领导建立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科
1977年12月,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召开,黄家驷有关以人工心脏来带动生物医学工程的发言引起大会重视,将生物医学工程纳入要发展的新兴学科之列。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通过《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决定在中国建立生物医学工程学科[2]。在大会发言中,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明确提出,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创立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必须在中国开展生物医学工程研究,并建立相应的研究基地。自此,生物医学工程学迎来了春天,黄家驷也以极大的热情担负起创立学科的领导工作。
2.1 主持审定中国第一部生物医学工程学的科研发展规划(1978—1985),担任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组长
1978年7月, 全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科规划会议在天津蓟县召开,黄家驷主持会议,会上审定通过我国第一部生物医学工程学的科研发展规划(1978—1985)。1978年11月, 全国第一届人工心脏学术交流会在广州召开,黄家驷主持会议,这是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界的第一次盛会,会上成立了全国人工心脏研究协作领导小组。1979年11月,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学科组在重庆宣告成立,黄家驷任组长。他领导学科组开展了大量有关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建设的相关工作,并和其他学科组成员一起,根据学科发展趋势和国家发展需求,以及学科重大改革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向国家提供咨询提出建议。
2.2 组建成立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和生物医学工程研究室
为适应医学科学研究的新形势,特别是生物医学工程学的新发展,1978年初,黄家驷率先在刚刚迁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建立了生物医学工程研究室[3]。其后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简阳分院重新组建了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将生物医学工程确定为研究所的战略科研方向和主要任务。1978年6月2日,在黄家驷的领导下,中国医学科学院向卫生部报告,将中国医学科学院简阳分院医学仪器研究所改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1978年12月,卫生部批复同意更名,至此中国第一家以生物医学工程命名的国家级研究所组建完成。期间,1978年6月3日,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召开,黄家驷在发言中明确提出狠抓生物医学工程这一薄弱环节作为发展医学科学的一个突出问题。1978年7月,黄家驷主持审定的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规划(1978—1985)讨论稿中进一步提出,三年内,首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建立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不仅如此,黄家驷还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选址做了大量工作。早在1979年11月全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成立大会上,黄家驷组长就和专家们提出,为加快发展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必须建立一个中心研究基地,具体建议就是四川简阳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并考虑将其迁至北京或天津,使之有利于与各有关单位加强协作交流。1982年底,黄家驷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受动脉硬化影响身体出现了间歇性跛行,即便如此,他仍然多次往返于京津之间,为生物医学工程所迁址天津不辞劳苦[4]。
2.3 担任第一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和《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主编
1980年11月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成立, 基于他对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贡献,黄家驷被推荐并当选第一任理事长。他为增进全国各地研究人员的团结,促进各学科之间的协作,争取经费做了大量的工作。随后,协会的各项工作在他的领导下逐步开展起来。
1982年《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创刊,由黄家驷担任主编。他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学报》的任务就是为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界的科技工作者提供一个沟通学术思想、交流学术经验的园地。
作为学会理事长,黄家驷多次莅临各省市分会,通过介绍国内外学科发展情况、宣讲学科知识、主持学术活动等方式,关心分会的建设和发展。1983年5月,他不顾年迈体弱,前往上海分会,亲自到曾为其题写过“新的学科,新的园地”创刊词的《上海生物医学工程通讯》编辑部,同编辑人员亲切交谈,对刊物今后的发展提出殷切希望。
3 加强国际交流,推动生物医学工程学向纵深发展
黄家驷非常重视国际交流,坚持走出去战略。 1980年5月,他率中国医学科学院人工心脏考察团赴日本考察, 成员包括杨子彬、罗致诚、杨成民、张化新等学者,先后访问了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大阪大学、国立循环器病研究中心、人工肾透析中心等单位,围绕人工心脏、医用材料、电子仪器等内容与渥美和彦、樱井靖久等知名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参加了在冈山召开的第十九届医用电子与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年会[5]。这是我国在确立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后,派出的第一个专项技术考察团,历时22天。这推动了中国人工心脏研究的发展,对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0年9月,他率中国生物医学工程代表团赴美国、联邦德国等地做专业考察,并出席了第33届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年会,受到以冯元桢教授为首的各界同道热诚欢迎与接待,建立了广泛的国际联系。这是中国正式派出的第一个生物医学工程综合性学术考察团体,历时48天,其中在美国30天,先后访问了NIH及其心肺血液研究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HP公司等19个单位;在西德18天,先后访问了亚琛工科大学Helmholtz生物工程研究所、波恩大学附属医院、西门子公司等11个单位[6]。通过考察,实现了了解美国和西德在生物医学工程科学管理、教育体制、培养人才以及学科最新成就和发展动向的目的,为以后两国学科联系奠定了交流基础。李宗明、乐以伦、周伯达等参访成员,后来都成长为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各二级学科的带头人。
另一方面,坚持请进来战略,通过举办国际会议,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访学,扩大中国学界的国际影响力。1983年5月他带病主持了在武汉举行的中、日、美第一届生物力学会议,和冯元桢、深田荣一一起担任大会主席,与来自中、日、美、加、法、意、荷等国家的170位生物力学科技工作者进行了大会交流[7]。随后他接受腹主动脉瘤切除和更换腹部主动脉的大手术,即使术后体质非常虚弱,黄家驷仍忘我工作。在1983年11月主持了在天津召开的血液灌流及人工器官国际学术讨论会,与加拿大人工细胞创始人张明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工心脏创始人布什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生物材料专家克林克曼等来自14个国家的141位专家进行了学术交流,报告了这一领域许多重大成果新进展,有力助推了中国血液灌流及人工器官研究深入开展[8]。
1984年5月14日,在前去主持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会的途中,黄家驷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他为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奉献和辛劳无愧于生物医学工程学奠基人的称号。
正如黄文美在《悼父亲黄家驷》中所写:“父亲属马,自幼喜欢马的形象。他的一生是在马不停蹄的开拓进取中度过的。无论是岁月坎坷之日,还是誉满功高之时,他从不畏缩停滞,更不自满苟安,总是辛勤忘我地攀登着新的高度,为后人开拓通向明天的道路[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