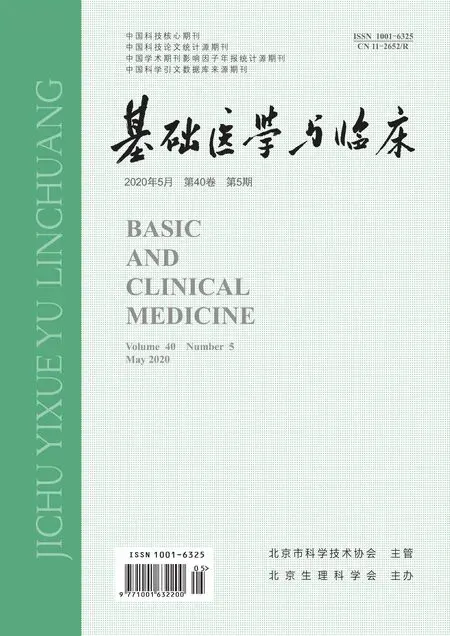50例中国男性乳腺癌临床特征和遗传学病因
秦 岭,邢泽宇,刘嘉琦,钱天一,王畅畅,王 昕,王 翔
(1.北京市朝阳区桓兴肿瘤医院 乳腺外科, 北京 100020;2.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肿瘤医院 乳腺外科,北京 100021)
男性乳腺癌(male breast cancer,MBC)是一种罕见的男性肿瘤,也是乳腺癌中的一种罕见亚型,仅占全部男性肿瘤的0.2%和全部乳腺癌的1%,其易感因素包括乳腺癌家族史、激素水平的变化、BRCA1(breast cancer 1, early onset)/2等基因突变等[1]。由于 MBC 病例数缺乏,难以开展大宗的临床试验研究,因此治疗决策大多参照女性乳腺癌 (female breast cancer,FBC)资料。基于国外报道,BRCA1/2突变见于5%~20%的男性乳腺癌的遗传学病因[2],但国内尚无大宗报道。本文回顾了2015年7月至2019年7月收治的5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和遗传学病因,探讨其临床特点、治疗和遗传学特征。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本组病例均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和北京市朝阳区桓兴肿瘤医院2015年7月至2019年7月收治的男性乳腺癌患者,患者均来自家族遗传性肿瘤综合征的遗传学研究队列(Genetic investigation of Inherited and Familial Tumor Syndrome,GIFTS研究,注册号ChiCTR1900024050)。本研究对入组患者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家族史和既往病史进行了统计。BMI分别按照24和28作为超重和肥胖的阈值。所有患者均病理证实为乳腺癌,且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本研究获得参加单位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批准(伦理审批文号:NCC2018-026)。
1.2 方法
1.2.1 临床和病理特征的检查:本研究对患者的发病年龄、肿瘤大小、淋巴结和远端转移、分子分型和分期进行统计。此外,对于患者病理类型和免疫组化特征,包括雄激素受体(androgen receptor,AR)、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进行了统计。根据美国癌联合委员会(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f Cancer,AJCC)分期对每位患者进行了分期,根据2019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CSCO)乳腺癌诊疗指南区分了分子分型。
1.2.2 遗传学检测:对入组患者中的25例男性乳腺癌患者采集外周血样本,提取基因组DNA,并进行了BRCA1、BRCA2、PALB2、CHEK2和RECQL5个基因全部外显子区域的二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测序由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参考美国医学遗传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Medical Genetics and Genomics, ACMG)和美国分子病理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AMP)指南[3]对胚系突变进行注释与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其中与遗传性肿瘤相关的罕见、高致病性突变。
1.2.3 治疗:根据患者分期和受体表达情况,参考本研究患者接受了对应的手术、化疗、放疗和内分泌治疗。对于治疗后超过1年的男性乳腺癌患者进行门诊随诊,评估其复发转移情况。
1.3 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研究共入组男性乳腺癌患者50例,均为中国汉族,其中26例患者入组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24例患者入组自北京市朝阳区桓兴肿瘤医院。患者发病年龄介于34岁到84岁,平均年龄为(58±11.5)岁。其中49例为单侧乳腺癌;1例为双侧乳腺癌,该患者43岁患右乳癌,48岁患左乳癌;1例患者为左乳癌改良根治术后2年复发。在全部男性患者中,超重患者(BMI介于24~28)占34.00%(17/50),肥胖患者(BMI>28)占26.00%(13/50)。其中72.00%患者(36/50)无肿瘤家族史,3例患者(6.00%)伴有乳腺癌家族史,而2例患者(4.00%)伴有卵巢癌家族史。全部患者均未曾患有其他肿瘤。
2.2 患者的临床和病理特征
病理组织学类型方面,39例(78.00%)为浸润癌(其中37例为乳腺癌浸润癌、2例为隐匿性乳腺癌),8例为乳头状癌,2例为黏液癌,1例为腺样囊性癌。分期方面,肿瘤最大径介于0.3 cm~6.5 cm,26例患者(52.00%)肿瘤属于T1期,13例患者(26.00%)肿瘤属于T2期,仅有2例患者(4.00%)肿瘤属于T3期,没有患者属于T4期,2例隐匿性乳腺癌患者(4.00%)未发现乳腺肿瘤,但有7例患者为外院活检术后无法评价其乳腺肿瘤大小(Tx)。腋窝淋巴结转移见于19例患者(38.00%),远处转移仅见于1例患者(2.00%)。17例患者(38.64%,17/44)属于ⅠA期,10例患者(22.72%)属于ⅡA期,2例患者(4.55%)属于ⅡB期,4例患者(9.09%)属于ⅢA期,9例患者(20.45%)属于ⅢC期,1例复发患者和1例远处转移患者为Ⅳ期。6例患者缺少原发灶大小无法分期,另有1例缺乏原发灶信息患者因N3分为ⅢC期。病理分子分型方面,在接受病理免疫组化检测的患者中,95.24%(20/21)的男性乳腺癌患者为AR阳性,89.36%(42/47)患者为ER阳性,87.23%(41/47)患者为PR阳性,仅有6.38%(3/47)患者为HER2阳性。在47例进行免疫组化检测的患者中,23例患者(48.94%)属于Luminal A 型,16例患者(34.04%)属于Luminal B型(HER-2 阴性),3例患者(6.38%)属于HER-2阳性(HR阳性),5例患者(10.64%)为三阴性乳腺癌。
2.3 患者的遗传学特征
通过对25例乳腺癌患者外周血的基因组DNA进行遗传性肿瘤相关基因检测,发现其中2例患者存在致病性胚系突变(germline mutation)。1例57岁患者存在BRCA2:c.7007G>A, p.(Arg2336His)突变,但无明确肿瘤家族史;另1例76岁患者存在BRCA1:c.5095C>T, p.(Arg1699Trp)突变,其2个女儿均患卵巢癌。以上2个突变均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主办的与疾病相关的人类基因组变异数据库ClinVar数据库(https://www.ncbi.nlm.nih.gov/clinvar/)标记为致病突变(编号分别为38077和55396),在国内尚无报道。此外,还有1例54岁患者存在CHEK2:c.444+3A>C胚系突变,注释分类为意义未明的突变(variant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VUS),无肿瘤家族史,该突变在国内外均无报道。
2.4 患者的治疗
50例患者中除了1例发生远处转移的患者均接受了手术治疗,其中31例患者直接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1例患者进行前哨淋巴结活检阳性后采取乳腺癌改良根治术;11例患者采用乳腺单纯切除术+前哨淋巴结活检术;2例患者选择乳腺癌保乳术+前哨淋巴结活检,1例患者进行了乳腺癌保乳术+腋窝淋巴结清扫术;2例患者因隐匿性乳腺癌仅进行了腋窝淋巴结清扫术;1例46岁男性患者因“左乳癌改良根治术后2年复发”行左胸壁肿物切除术。52.00%(26/50)患者在术后进行了化疗,20.00%(10/50)患者在术后进行了放疗,内分泌受体阳性患者在术后均应用他莫昔芬(tamoxifen)或托瑞米芬(toremifene)进行内分泌治疗。对这40例治疗后1年以上的患者进行随访,随访时间为(13.3~73.9)个月,平均随访时间为(32.5±12.9)个月,除1例初诊Ⅳ期的男性乳腺癌患者以外,均无复发转移。
3 讨论
男性乳腺癌是病因不明、少见且研究较少的恶性肿瘤,而目前大部分关于乳腺癌的临床试验都会在入组标准中除外男性乳腺癌[1,4]。国外报道男性乳腺癌的平均发病年龄为59~67岁[1],而在本研究中患者的平均年龄为58岁,较国外发病年龄早。本研究中,肥胖患者占26.00%,较先前报道的中国女性乳腺癌患者高(约14%)[5]。中国男性乳腺癌的遗传学病因研究较少,虽然本研究中2例患者存在BRCA1/2致病性突变,1例患者存在CHEK2意义未明的突变,但大部分患者的遗传学病因仍然未知。
根据国外报道,乳腺浸润癌是男性乳腺癌最常见的类型,导管原位癌、乳头状癌和黏液癌都相对少见[6],本研究与其一致。本研究接近半数患者存在腋窝淋巴结转移,与此前国内报道比例相似[7]。免疫组化方面,国外报道绝大多数的男性乳腺癌都是激素受体阳性和HER2阴性,而仅有不到1%的肿瘤为三阴性乳腺癌[1,8-9]。而在本研究中虽然89.36%的肿瘤为ER阳性,仍有10.64%肿瘤为三阴性乳腺癌,这一比例高于既往研究[8]。
尽管近年来,保乳术和前哨淋巴结(sentinel lymphnode, SLN)活检在女性乳腺癌外科治疗中的比例日益提高,并在男性乳腺癌中也被证明安全可靠[10-11],但乳房全切和改良根治术仍是其目前的主要外科治疗方式[8]。本研究中31例直接进行腋窝淋巴结清扫的患者中,17例患者最终腋窝淋巴结未见转移。回顾性研究证实男性乳腺癌患者能够从辅助化疗和内分泌治疗中受益[12]。但在本研究中仅有26例患者接受了术后辅助化疗,即使在13位III期患者中也仅有10例(76.92%)接受了术后化疗。同样的,虽然术后辅助放疗对于降低保乳术后或腋窝淋巴结阳性的男性乳腺癌患者复发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同样应用不足[8]。在本研究中,3例选择保乳术的患者仅有2例接受放射治疗,III期的13例患者中仅有7例(53.85%)接受了放疗。辅助治疗不足的原因可能为对于男性乳腺癌缺少成熟的多学科合作机制以及患者对辅助治疗重视不够。可见,在治疗方面,手术方式可以进一步做“减法”,内分泌治疗在术后辅助治疗中占重要地位,而术后辅助放疗和化疗则应作“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