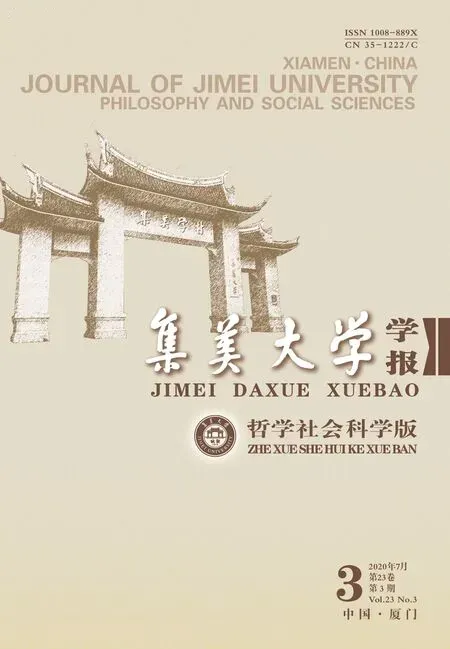《猫眼》的叙事伦理研究
王青璐
(1.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发表于1988年的小说《猫眼》是一部关注女性成长和女性艺术生涯发展的成长小说。作者阿特伍德本人也指出,《猫眼》是一部有着“阻止时光流逝或带回旧日时光的企图”[1]的作品。小说背后丰富的内涵受到了评论者的关注,如西斯摩尔认为,《猫眼》“看似是一部私人小说,但性别和殖民政治隐藏在私人故事之后”。[2]小说的艺术形式也得到了广泛关注。评论者既对小说叙述形式进行点评,又对画作在小说中的意义展开阐述。帕隆博就指出:“伊莱恩超然的、讽刺的叙述内容与她的画作构成对比,表达了伊莱恩本人无法言说的内容。”[3]
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论界“伦理转向”兴起后,西方和中国的学者先后挖掘叙事和伦理的关系。如亚当·纽顿“将叙事伦理批评确立为独立的批评视角,主张文学艺术由人类创造,反映人类的生活状态,其本身作为一种行为即具有责任与义务的伦理性”。[4]他提出叙述伦理、表征伦理与阐述伦理三个核心层面,认为“叙事伦理一般可以同时从两个方向来解释,一方面,它赋予叙事话语某种伦理地位;另一方面,它指的是伦理话语通常依赖于叙事结构的方式,这使得叙事与伦理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显得更加重要”。[5]我国学者伍茂国在总结中外学者的叙事伦理见解后,提出了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的研究框架:故事伦理是“纪实叙事(或日常叙事)与伦理”,叙述伦理则是“文学艺术叙事(或虚构叙事)与伦理”。[6]用叙事伦理的框架对《猫眼》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小说表达了两层故事伦理意义:第一层通过展现主人公伊莱恩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校园暴力,传达要用理性意志管束自由意志,避免恶行发生;第二层是通过聚焦伊莱恩的艺术生涯发展,看伊莱恩如何在绘画中完成自我的伦理身份认证。在叙述伦理意义上,小说的非线性叙述形式起到了展现人物在过去和现时之间进行努力调解、丰富人物性格层面和成长轨迹的作用。在叙事伦理框架下,小说的丰富内涵意蕴与精妙的艺术结构形式得到了一一展现,为了解阿特伍德的创作,发掘作品的文学价值提供了新途径。
一、故事伦理一:成长经历与伦理混沌
第一层故事伦理关注伊莱恩的个人成长,其中校园暴力是一个重要的伦理结。一些研究者在解读伊莱恩的童年经历时,提出她的遭遇具有普遍性,同时也挖掘了校园暴力背后深远的政治意义。如尤蕾认为游戏是“孩子们管束小伙伴的重要手段,其背后是一套严格规范的社会行为方式”[7];怀特认为“科迪莉亚和另两个女孩用来欺负伊莱恩的方法和专政政府采取的手段一致”[8];海特则提出欺负伊莱恩的其他小女孩也是受害者,她们将伊莱恩当作“替罪羊”,以发泄“自己作为父权制成员的痛苦”。[9]小说借助伊莱恩的成长困惑,反思了校园暴力与世界上围绕种族、性别、政治等问题产生的暴力行为间的关系,从个体的需求出发来探讨暴力的发生机制。伊莱恩倾尽一生在寻求答案:她要怎样化解他者的恶意,在她有一定能力后,是否要转变成对他者施加恶行的人。
而校园暴力会对伊莱恩产生影响,也与其个人伦理意识的觉醒程度有关。当时的伊莱恩尚处于伦理混沌阶段,即“人出生后至伦理选择前这个时期的伦理状态”[10]257,在没有产生恰当的伦理意识也不能做出伦理选择的时候,会为自己遭遇小伙伴的不平等对待感到苦闷。八九岁的伊莱恩显然没有成熟的自我意识,所以会任由那些女生虐待她。伊莱恩同喜欢欺负她的科迪莉亚、格雷斯和卡罗尔三人结伴上学、做游戏,将科迪莉亚三人当作成长的榜样和生活中的参照对象,以为自己样样不如人。在拜访了科迪莉亚的家后,她“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是穷人”[11]70,还跟着科迪莉亚一家去参加每周的宗教活动。可是,她的父母都是科学家,家庭环境不会弱于科迪莉亚家。伊莱恩还听信同伴的话:“我不正常,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这是科迪莉亚和我说的,不过她会帮助我。”[11]120
成为其他女孩的恶作剧对象后,伊莱恩出现了心理危机:“有好些日子我几乎都下不了床。我感到说话都困难。”[11]36负面心理现象干扰到她的日常生活。在学校,她的书写退步了,“那些字母不再像原先那样又圆又漂亮,而是像蜘蛛网似的,疯狂,奇丑”。[11]129她还会在白日里突然昏倒,“几乎是什么时候想昏倒就能昏倒”。[11]178同伴开的玩笑也逐渐升级。一次,科迪莉亚把伊莱恩的帽子扔到结冰的桥下,命令她下去捡回来。在捡帽子的过程中,她踩碎了浮冰,掉进了齐腰深的溪水中。三个同伴却在这个时候悄悄溜走,将她独自遗弃在雪天刺骨的溪水里。伊莱恩险些丧命,但三个伙伴却毫无歉意,甚至责怪伊莱恩出卖她们。这段经历让伊莱恩狠下心同三个女生绝交。放弃这段单方面的友谊是伊莱恩从伦理混沌中脱离出来的象征。
十二岁的时候,伊莱恩又同科迪莉亚重逢。两人之间角色互换,伊莱恩开始对科迪莉亚施行言语暴力,把科迪莉亚变成练习刻薄话语的靶子。伊莱恩取笑科迪莉亚喜欢的男生,说他们是“干酪一块”,“他们身上就是像乡巴佬似的满是玉米胚芽油我看你也会喜欢的”。在科迪莉亚对学校卫生措施发表意见后,伊莱恩反驳:“这是谁跟你说的?你妈咪吗?”她还会取笑科迪莉亚最喜欢的那几个歌手,说他们唱歌是呻吟。这种情况下,科迪莉亚有时能辩驳,有时“她只会说:‘太狠了!’”“将舌头伸到嘴的一边然后换个话题”“要不就点上一支烟”。[11]240理性意志又在发挥影响,让她觉得对他人行恶如同“越过那条能为社会所接受的行为规范的界限”,又如同“在薄冰上、半空中”[11]240行走。在《猫眼》中,影响伊莱恩是否要作恶的,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的动力主要来自人的不同欲望,如性欲、食欲、求知欲等”。[10]282故而,包括校园暴力在内的种种暴力源自人内心不受限制约束的种种欲求。
这些得不到满足的愿望不仅会通过主体影响他者,还会反作用于主体。如伊莱恩在报纸上读到年轻女生遭遇猥亵和凶杀的案件后,内心反而对受害者的服装细节描写更为关注,觉得“谋杀也应该有一个比较能拿得到场面上来的理由啊”。[11]247成年后,她帮陷入生命危险的情敌苏茜叫来救护车,脑海深处也传来一个小小的刻薄的、“古老而得意”的声音说:“她活该。”[11]331在她经受婚姻失败后,这个声音又出现了,指使她自杀。它说:“干吧!来啊!干吧!”[11]391“它并不险恶而是兴奋,彷佛是在建议人玩一个恶作剧、一个玩笑、一个令人开心的游戏”。[11]392
既然校园暴力与其他恶行间有着同构性,那么主人公伊莱恩面对身边暴力采取的行动也有着一定的倡导性,即是要用理性意志去约束自由意志,以减免伤害的产生。虽然在救助苏茜过程中,伊莱恩有受到自由意志的影响,责怪情敌活该,但她始终在帮助苏茜摆脱生命危险。尽管第一段婚姻经历挫败,伊莱恩甚至试图以自杀摆脱痛苦,但在被救助后,她又立刻采取积极的行动,带着女儿离开多伦多。在温哥华,她让自己沉浸于工作中,远离伤痛,并有意与传递负面情绪的人群保持距离。温哥华的女性团体在“相互传递尖刻却又合理的判断意见”,是对童年时代科迪莉亚小集体的延续,她们想要改造伊莱恩,把她“变成为她们为我设计的某种样子”“改造得更好”。[11]397面对可能发生的暴力行为,伊莱恩不再困滞于伦理混沌中,“知道什么东西对于我来说是危险的,所以努力避免事情发展到边缘状态”。[11]399她合理地利用理性意志管束自由意志,辨别是非、曲折,做出判断。
二、故事伦理二:艺术创作与伦理身份
小说第二层故事伦理意义在于伊莱恩克服创作困境,通过画作实现了自我伦理身份建构。豪威尔斯也发现,“在伊莱恩的话语性叙述尚不完整时,她的绘画提供了对扭曲、压抑的记忆进行纠正的方法”[12];画作也“讲述了另一个关于伊莱恩作为主体的故事”。[13]而在阿特伍德的小说创作中,主人公也经常通过蛋糕烘培、绘制画作、摄影等形式来抒发内心的情绪,琼斯在对比了《猫眼》与《可以吃的女人》后提出“蛋糕和绘画的创造都反映出一种用语言无法表达出来的强烈不满”。[14]
在刚踏入绘画行业时,伊莱恩遭遇了行业的性别传统压力。男性画家打压她,男友乔将伊莱恩的画贬低为“插图”,而“只要画出的东西可以被辨认,他都说成是‘插图’”。[11]338美术界存在的对女性作画潜力的否认与传统性别话语中对女性的否认同质。吕斯·伊里格瑞认为“女人这个‘性别’不是‘一个’性别。在普遍男权主义的语言——一种阳具逻各斯中心的语言——里,女人成了那不可再现的。换句话说,女人代表了一个不能够被思考的性别,是语言的不在场和晦涩难解的部分”。[15]13故而,伊莱恩的绘画事业等同于用画笔对女性的性别身份进行勾勒和描摹,是对男权主义语言下女性性别可能遭遇的“语言的不在场和晦涩难解的部分”[15]13进行的填充。最后,伊莱恩也成了一位知名的画家,而曾经打压过她的绘画事业的男性们反而都不得志。乔迫于经济压力,也改画伊莱恩画的商业性插画,最后又转行成为道具师。早年教育伊莱恩绘画,并和伊莱恩等女性有过恋人关系的老师约瑟夫也放弃了绘画事业,转而拍摄电影。
在绘画领域为女性性别身份成功正名之外,伊莱恩的画作还反应了她的伦理身份建构。伊莱恩也有将画画视为“真正的生命线”[11]283,把自己的所有精力和情感熔铸于绘画中,“我再也无法控制这些画,再也无法叫它们去表达什么意思。无论它们具有什么样的能量,这能量全都出自我身。我如今只是一个残留的躯壳”。[11]427画作也沉淀了她对过往、现时和未来的思考,融入她对现时自我和过往自我、自我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的思考与定位。当她在画展房间里漫步时,会感到“被自己描绘的时光包围着”。[11]427特别是多伦多画展中展出的最新完成的五幅画,都体现了伊莱恩个人的价值选择和伦理倾向。这些画分别是《皮秒》《三个缪斯》《一只翅膀》《猫眼》和《统一场论》。它们对伊莱恩的叙述话语进行补充,反应伊莱恩对宗教的否定与对科学的支持,对殖民教育的批判和种族平等的宣扬,以及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宽解。
《皮秒》和《一只翅膀》是为纪念父母和哥哥斯蒂温创作的,融入了伊莱恩对原生家庭的纪念之情。在《皮秒》中伊莱恩用了一种“光滑,细腻,柔和,如快照似的十分写实”[11]67的风格,还原了童年时父母带着她和哥哥在野外生活的场景。《一只翅膀》是为缓解哥哥英年早逝带来的伤痛而作的,画中在高空坠落的男子穿着二战时加拿大皇家空军的制服,显得很平静,手里握着一柄儿童的木剑。伊莱恩的父母与哥哥共享着科学家的伦理身份,他们都“不相信给儿童洗脑子有什么好处”,并且认为“宗教必须为许多战争和大屠杀负责,盲从和偏执其根源也在宗教”。[11]95然而伊莱恩在八九岁时对家人产生过质疑,“有些东西我父母一直在瞒着我,而这些东西是我所需要了解的”。[11]101可在她随史密斯一家去教堂做礼拜后发现,真实的史密斯们是与他们宣扬的宗教理念格格不入的。史密斯太太还放任其他女孩欺负她。这样的经历让伊莱恩“对上帝失去信心”[11]194,也意识到自己原先接受的家庭教育是正确的。在对亲人的悼念中,画作表露出伊莱恩对过往自我存在的肯定与对科学的肯定。
《三个缪斯》和《统一场论》反应了伊莱恩否定英国殖民统治的政治理念,显示了她在面对社会大环境时所保持的独立姿态。她在小学接受的殖民统治教育腐朽落后。学校宣扬“大英帝国太阳永不落”,传递关于殖民地的错误信息:“在非大英帝国统治的国家里,他们割儿童的舌头,尤其是男童的舌头”[11]79等。这两幅画是对传统的族裔偏见的回击。《三个缪斯》画的三个外国人源于现实,分别是犹太邻居费恩斯坦太太,学校里教画画的斯图亚特小姐和父亲带的印度留学生班纳杰先生,他们都给予伊莱恩关于国外世界的正面影响。他们让伊莱恩意识到大洋另一边生活的人民和加拿大人民都是一样平等、独立,值得尊敬。从苏格兰流亡到加拿大的斯图亚特小姐让伊莱恩脱离了虚伪的帝国殖民教育,知道了“在别的什么地方,这些别样的外国人确实存在”“他们的服装如花似锦,他们的民歌轻松欢快”。[11]166班纳杰先生漂亮的印度面孔让伊莱恩发现学校关于外国人长相的宣传是错误的。犹太人费恩斯坦太太让伊莱恩意识到“宗教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种类”,只有像希特勒那样的精神错乱的“自我扩张狂”[11]138才会否定其他宗教。而在《统一场论》中,伊莱恩颠覆传统圣母的形象,创作一个身穿黑衣,“收留一切迷途者”[11]426的圣母马利亚形象。现实中黑衣圣母存在于墨西哥,她是一切丢弃物的圣母,专门负责丢弃物的复原”。[11]201奥斯本认为伊莱恩通过黑衣圣母实现了“与少数族裔在字面上和比喻上的结盟,以克服来自加拿大白人中产阶级社会的压抑”。[16]黑衣圣母的黑衣,直面并破除了主流社会利用宗教制造出的种族歧视,也寄托了伊莱恩对加拿大社会要去除存在的族裔歧视与偏见的心愿。
而在自画像《猫眼》中,伊莱恩通过绘画直面童年记忆。画中三个脸在阴影里的小女孩穿着40年前的冬装在雪地里朝前行走。根据伊莱恩对童年生活的回顾可推测,三个女生应是科迪莉亚、格雷斯和卡罗尔,展现的即是自己被同伴丢弃在冰天雪地里的经历。马尔库塞认为记忆有治疗作用,“有一种保存希望和潜能的特殊功能”。[17]而画作题目“猫眼”来自伊莱恩小时候赢来的一颗蓝色的玻璃弹子,是她的护身符和象征,“某种未知的然而却又存在的东西的眼”。[11]61这段经历促使伊莱恩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从他人对她施行的恶中抽身而出。同时也以绘画个人早年悲惨经历的形式,进行自我警示:一定要用理性意志约束住自由意志,不能让各种欲求成为作恶的理由。在暴露自己最不堪、最难过的经历时,伊莱恩也同过往自我实现和解。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她会在回到多伦多后不停地想象自己和科迪莉亚重逢的场景,能解释为什么航班上的两个老太太能够给她感到放松,“一切责任都已从身上卸下,什么义务,宿怨,悲伤,全都已抛开”。[11]438这两个老人身上反射了她对自己同科迪莉亚关系的憧憬,而她同科迪莉亚间可能发生的和谐共处的场景,也象征着理性意志同自由意志在博弈之后最终获得的平衡。
三、叙述伦理:非线性叙述与伦理建构
在叙述伦理层面上,小说的非线性叙述形式完成了文本的伦理建构。伦理建构是“人物在文本伦理结构中给读者留下的伦理期待,是伦理矛盾与冲突形成的过程”。[10]小说开篇处,伊莱恩回到了多伦多,到处寻找“时间的碎片”。[11]403当她在街道上漫步、重返熟悉的地方,与不同人物的相遇或重逢之时,叙事的时间线也就随伊莱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转变,在正常时序内以倒叙的形式回溯了种种往事。李文良还发现《猫眼》在原文中采用现在时去呈现伊莱恩过去的经历,传达出“现在就是过去的延续,不能把过去完全和现在割裂开来”[18]的后现代时间观。非线性叙述将伊莱恩在不同阶段下的不同经历拼凑在一起,以今昔对照的方法呈现其清晰可辨的变化。
故而,非线性叙述也很好地满足成长小说的叙事需要:“以更多的讲述来深化性格,并以性格的丰富为由,要求有更复杂的次要情节”。[19]伊莱恩成年后同男友、前夫在不同时空中发生的纠葛,通过非线性叙述在小说一些章节中得到集中地展示。这些根据个人情感经历生成的不同时空实际又都是围绕着相似的伦理矛盾与冲突形成。由此,在小说的非线性叙述形式将不同时空交错、整合在一起后,人物在不同时空中面对相似的伦理困境,做出的不同伦理选择,推动了文本伦理建构的实现。而关于管束自由意志和积极承担起个人责任的伦理教诲内容在非线性叙述中得到了突出。
伊莱恩对自己求学时期往事的回顾在与前夫乔的约会中开启。离开乔以后,伊莱恩沿王后大街往东走,想起了自己多年前画过的《坠落的女人》:三个女人在往下掉,跌向男人身上。她是通过曾经的画作,对过往进行一番点评,达到叙述干预。伊莱恩解释坠落“是一种违背自己意愿但也并非他人强迫的往下坠落的行为”,而“坠落仅仅是坠落”。[11]275由此,回顾前的叙述者干预实现了对叙述者伊莱恩在现时中所处立场的交代,反应现时的伊莱恩对过往的批判,对个人要承担起责任的强调,同时也预告了自己曾由于放任自然情感而受到伤害。
在伊莱恩开始学美术到离开多伦多的这段回溯性叙述中,小说采用了可构成平行关系的双线形叙述模式。叙述者伊莱恩没有遵循传统的线性顺序先后交代自己去上美术课,再与美术老师和男友乔谈恋爱、分手等等。有关美术课的回顾性叙述活动是与追溯自己同美术老师、男友恋爱的叙述活动同时进行的。她先从自己和约瑟夫某次在法国餐厅吃蜗牛、喝白葡萄酒的场面开始,从对用餐过程中约瑟夫对伊莱恩说话腔调的点评,转回到五月最后一周的人体素描课,再展开有关自己与约瑟夫是如何在课程作业评估过程中突然地建立起恋人关系的回顾;最后叙述又回到了法国餐厅的约会,伊莱恩在饭后随约瑟夫坐车前往他的公寓。这种叙述上的平行关系指向了叙述者伊莱恩对这段恋情在伦理道德层面上有出于本能的排斥,同时也建构出一个伦理困境,即伊莱恩对于与年长自己十七八岁的老师谈恋爱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她让自己沉溺于原始的自然情感中,通过个人行动来对社会规约中的悖德行为表示赞同;但另一方面她又耻于公开他们的关系,并通过对情敌苏茜的语言性攻击来发泄自己的被动与不满。
让这段关系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她和约瑟夫两人又各有其他情人。在伊莱恩之前,约瑟夫已经与伊莱恩的同班同学苏茜公开交往。伊莱恩也瞒着约瑟夫,和同班男同学也即她的第一任丈夫乔偷偷约会,认为“拥有两个男人也就意味着我不用拿定主意跟定他们中的任何一方”。[11]325她将婚姻视为“不道德的、粗俗的交易,而不是一件自由的礼物”。[11]307年轻时的经历又被突然打断,小说叙事一下子回到了现时中。伊莱恩继续一个人在街道上散步,并走到了约瑟夫以前生活过的区域。“当几个地点按族类排列起来,就可与精神的、意识形态的和道德的对立相联系”。[20]伊莱恩又以评论性的叙述干预形式来表明自己对那段悖德恋情的批判和否定:“这些房子过去跟动物住的窝差不多。”[11]321之后,伊莱恩又开始从母亲的伦理身份出发,去思考如果她的经历发生在她的女儿身上会怎么样:“要是我的两个女儿中有一个爱上了这样一个男人,那我是要发狂的。”[11]322
在街上徜徉片刻,伊莱恩又开始回顾往事。她总结自己当时从约瑟夫那里得到的“是乐趣,是混乱”“他给予的是恶作剧般的胡闹”,[11]326承认自己年轻时是在放纵自由意志。在结束了有关与约瑟夫之间的恋情的回顾后,叙述者开始回顾自己同第一任丈夫乔之间的往事。伊莱恩在当时容忍着乔的出轨和对她的数落。接着叙述又转回到现时中,二婚的伊莱恩和同样是二婚的乔开始了新的约会。他们先在酒吧里约见,之后两人去了乔的工作室并发生肉体关系。可是伊莱恩没有为现任丈夫本感到愧疚,她认为自己“只是在忠于某种比他先到、与他无关的东西”。她很平静地看待自己与乔在此刻的关系:“过去的愤怒已经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我们曾经对对方怀有的那种夹带了紧张不安与猜忌的欲望”。[11]385
之后,小说叙述又回到了伊莱恩与乔水深火热的婚姻生活中。于是在现时与过往的叙事交织间,产生了反讽的喜剧效果。她在看到乔“耳朵后面的头发已开始发白”后,还打趣地评论:“刚才那事我们干得正及时,要不几乎就太晚了。”[11]386所以,现时中伊莱恩与乔重逢并发生出轨行为的过程可看作是她对与之平行的过往叙述线中事件的仿照与模拟。于是,一种通往未来的行动的可能性得到了生成:在现实中再次隐瞒情人与他人出轨的伊莱恩,或许将会仿照过往她与约瑟夫、乔的三角关系,在未来的行动中又会建构出一个新的三角结构。“伦理不是遵循各种规则,而是在平衡各种相互矛盾的要求后,对我们最终所作的决定负责”。[21]在现时与过往、未来的交织中,《猫眼》对伊莱恩提出了人性的疑问:伊莱恩能否在未来用理性意志约束好自由意志,避免重蹈覆辙呢?
不过,在现时与过往两条平行叙述线的对照下,伊莱恩在现时中的责任承担意识得到了凸显。小说叙事又回到了多年前伊莱恩与前夫乔之间紧张得一触即发的婚姻生活中,绝望到极限的伊莱恩采取了割脉自杀的行为,又被回到家的乔及时送到了医院。伊莱恩结束了婚姻,带着女儿萨拉离开乔和多伦多。离婚出走是伊莱恩在成长历程中实现人格独立的最后一步。在她到达温哥华以后,她有意地与女性群体保持距离。奥斯本在解读伊莱恩对女性群体的疏远时,提出伊莱恩看来“因为这些女性人物像她的第一个女性朋友一样,都像评判者”[16],疏远是出于自我保护。实际上,伊莱恩对那些女性的疏远,也是与她所承担的母亲伦理身份有关。她主动远离在那群争取女性权力同时又强调个人利益的女人,而是去结交可以相互帮忙看孩子的单身母亲。这行动本身就反应出伊莱恩对母亲伦理身份的清醒认知和承担意识。伊莱恩同女儿和家庭的伦理关系超越了其他伦理关系,母亲身份也成为她最重要的伦理身份。母亲身份和亲子伦理关系也推动她去化解同过往自我以及他者间的矛盾,让她得到实现伦理层面的成长。
四、结 语
以叙事伦理框架解读《猫眼》,可以丰富对小说艺术和伦理层面的认识。在故事伦理层面上,伊莱恩的成长个案展现了以伦理意识觉醒的方式去克服伦理混沌,走向自我独立的经历;伊莱恩的绘画作品实现了女性艺术家身份的建构,表达了她对自然同科学、种族同国家、过往同现时等关系的反思。在叙事伦理层面,小说中的非线性叙事手法有效完成了文本的伦理建构,突出了小说的主题:既要以理性意志约束自由意志,积极承担起与个人身份相关的责任意识。小说打通不同的时空,丰富了人物性格层面和成长轨迹,传达出源源不断的正面力量,鼓励其读者敢于直面现实中的性别、种族等偏见成规,突破过往的束缚,积极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