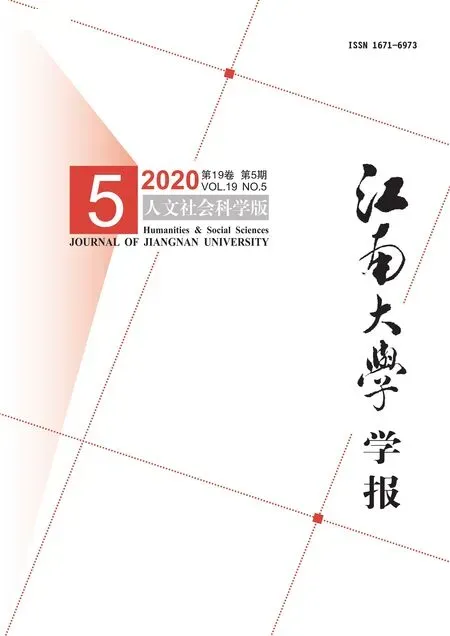往来天地间:庄子伦理政治的理据
张榕坤
(上海理工大学 沪江学院, 上海 200093)
庄子哲学并非逍遥遁世之学,相反地,庄子对复杂的人间伦理关系与政治局势有清明的洞察与反省,同时提出了极具特色的应对之道,具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庄子指出:“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子之爱亲”与“臣之事君”分别代表了伦理意义上先天所係的责任以及政治场域中后天当为的道义,是人所面对的“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存在处境。杨国荣先生说:“在叙述形式上,庄子由‘事其亲’、‘事其君’而论及‘自事其心’,但在实质的层面上,前者(履行‘事其亲’、‘事其君’的义务)则本于后者(出乎自然意义上的‘自事其心’):以安于必然与出于自然的一致为‘德之至’,便表明了这一点。‘与人为徒’(包括履行伦理、政治的义务)属人道或‘当然’,‘与天为徒’则表现为天道或‘自然’,以‘与天为徒’的原则与进路处理‘与人为徒’的伦理、政治关系,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天’(天道、‘自然’)对于‘人’(人道、‘当然’)的主导性。”[1]下面,我们亦将在“天”与“人”两大维度上,详细论析庄子对人间伦理及治国为政问题的回应。
一、“天德”的提出——“人德”的价值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在提出人间世“义”与“命”两大戒之后,尤其强调了“自事其心”的修养工夫,以涵养己“德”,以期达到“德之至”。因此,“德”之涵养是正确认识并处理伦理政治关系的基础。以下,我们将首先进行对“德”的探讨。在《大宗师》,庄子由对儒家所倡仁义道德的批判出发,暗示了人之德应当以“天道”为师:
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然而,许由却以“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回应所谓的尧舜之道。“黥”与“劓”说明,仁义与是非就像束缚人的刑罚,是对人自然本性的戕害。在此背景下,许由发出了“吾师乎!吾师乎!”的感慨。这里的“师”则指“天道”。人须师从“天道”,因为它能“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林疑独注曰:“齑碎万物而不为义,与‘亡国而不失人心’意同,谓万物皆自然,仁义之名将谁寄哉”;[2]而“泽及万世而不为仁”则类似于《老子》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道无私,不会对万物有所偏爱,故而,天道的仁义超越了一般所谓的仁与义;(1)钟泰先生解释《大宗师》中“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时说:“夫尧之仁非桀之比,人无不知也。然博施济众,不能无病。是其仁亦有尽时,不如天之无心于物,而物无不蒙德也……曰‘化其道’者,尧忘其尧,桀亦化其为桀,一纳于道之中,而誉与非更无所用之也。”参见钟泰:《庄子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也就是说,尧之仁,表现在他能博施济众,其仁德之行能见赏于人。但是,由于他“有心”为仁,其“仁”乃是有条件的仁,亦常常不能避免师心自用;不如天地无心育物,万物却能恒久蒙受其德。虽然天道自古以存,却不以之为老;虽然成就万物以不同的形状,却是浑然天成,超越人为的技巧。这几句话中的“不为”,都意在表明“天道”化育万物之自然无为。其实,这就是外杂篇所谓之“天德”:
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天地》)
故曰: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刻意》)
由此可知,庄子对客观的“自然之天”的理解,已不再停留在生养化育万物的层面上,而是抉发出天地生养万物之可能的条件,也即恬淡寂漠的“无为”之德;同时,庄子认为人之德也应当以此为法,故有“虚无恬淡,乃合天德”一语,这也是“吾师乎”的意义所在。例如,在许由回应了仁义之道将“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之后,意而子回答说:“庸讵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钟泰先生解释说:“‘造物者’,天也。惟天可息黥补劓,以喻仁义是非而能行之以天,则黥不为黥,而劓不为劓也。”[3]163这就是说,以“天道”为师,德合于天,便可以弥补仁义之伤,从而复其全德。也正因此,庄子由天地无为而生万物之德,提出人的修德之道,以及帝王的治国原则。同时,他指出,德充其中,必会符应于外,与天地万物建立和谐共荣的关系,所谓“德者,成和之修也”(《德充符》)。对此,庄子有“德不形”之说:
何谓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德充符》)
所谓“德不形”,即是冲虚之德集于怀而不荡之于外。《道德经·三十八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德之人,不以德为德,能顺任自然,无为无执;下德之人,则执着道德名相,有心为德。庄子指出,儒家的道德乃是“有形之德”,儒者既游于方内而兴礼乐之教,则不免在世间有种种“迹”。这虽体现了儒者成己成物、内圣外王的济世理想,却易造成人劳形怵心、以物为事;且不免将“成心”加诸于物,从而会限制万物按其本性自然发展。因此,“有心为德”对人自身以及万物而言,都不是至善之德。而庄子所肯认的冲虚恬淡之德,就像静止的水一般,万物自来取法而不离。庄子在《德充符》篇多次举例说明形缺而德全之人,生命自有光辉而能使众人归附,此乃“德者,成和之修也”。褚伯秀释曰:“至和内蕴,接物无间,若青阳流布,无不被生育之恩。盖以无心为心,故能无感不应。”[4]90以虚静之德应世接物,将如光之照物,无心而照,物却无不感通,这也是“天下乐推而不厌”(2)《老子·六十六章》曰:“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的道家圣人之写照。
正是在此意义上,庄子在《德充符》中提出的“天鬻”才可得到恰当的理解。他说:
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斵,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德充符》)
成玄英疏:“鬻,食也。食,秉也。天,自然也。以前四事,苍生有之,秉自天然,各率其性,圣人顺之,故无所用己也。”[5]释德清云:“谓四者淳德,乃天德也。鬻,犹售也。四德乃天售,即所谓天爵是也。”[6]
“天”不仅赋予人以形体,且赋予人以“四鬻”(“不谋”“不斵”“无丧”“不货”),也就是四种具体的天德。然而,众人却常因其情私有所谋虑而利用“知”,因失其自然之和合而强合之而利用“约”,以自外相接而非出于自然本性的态度而利用“德”,为了一己私利(“货”)而如商贩似地利用“工”;相对而言,游心于世间的圣人,不图谋虑,故不用“知”;顺任自然,故无胶约;本无所失,故不务求道德;不求私利,故不通商。庄子认为,“天”既已赋予四种具体的天德于人,人若能发用于外,以天德处世,生命自然可以蒙受补给,得于天养而所行无所不通,此乃“德充符”之本义。唐君毅先生说:
此皆不外言圣人之只游心于德之和,即足以使人亲悦之,而不待以人间之知约等为用也。此亦正所以见圣人之德之和,纯出于天,故谓之为“天鬻”“天养”“天食”而“属于天”也。[7]
唐先生所说的“只游心于德之和,即足以使人亲悦之”便是德性内充而符应于外的表现。圣人之德,纯出于天,不待人间之知约德工以为用。它无外在造作的痕迹,其发用却展现出与万物、他人共荣共长的和谐秩序。在此意义上,可说“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这也正是庄子在《天道》篇所指出的:“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若能深刻体认并秉有天地朴素无为之德,则可与天地精神往来,证成天和之境;此德发用世间,则会成就人与人之间的和乐。人之心既通和于天,又通和于人,共成天人之乐。赵虚斋更将这一天人共和之乐表述为庄子式的“内圣外王”之道(3)陈鼓应先生指出:“‘内圣外王’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作为一种理想道术的型态而提出。《天下》篇所标示的‘内圣外王’的理想,是十分独特的,它怀抱着‘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的社会意识,又具有‘配神明,醇天地’的宇宙精神。”参见陈鼓应:《道家的人文精神》,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0页。陈政扬先生亦言:“庄子的‘内圣外王’思想既不是个人遗世独立、修身自保之学,也不是探究帝王功业的政治哲学,而是以一种‘淑世’哲学的风貌呈现安立天下的整体关怀;此亦即是说,庄子的‘内圣外王’的理想实是通过无执的道心消融物我的隔阂封限,在物我共荣之中,还予天、地、人、我一片天清地宁,以圆现天地自然和谐之大美。”陈政扬:《孟子与庄子内圣外王思想之研究》,东海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109-110页。,褚伯秀又进一步做出申发:“道之在人,静则为圣,动则为王,皆以无为而尊,朴素而美。犹天地之德,何尝有为?何尝文采?而阴阳四时无不为,日月山川无非文。明乎此理,则天下之大本大宗立矣。所谓‘本’‘宗’,即内圣外王之道,与天和者也;用以均调天下,则与人和。”[4]231-232与儒家不同的是,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并不建立在所谓的道德与礼法之上,而是以无为而尊,朴素而美。如同阴阳四时、日月山川之无不为、无非文,人的无为朴素之德亦可以均调天下,与天人共和。
二、“天与人不相胜”——对伦理价值标准的基本态度
庄子的天人共和、内圣外王之道既然是在与“天德”同质的“无为之德”上立基,而在现实应用层面,是否意味着庄子对世间的是非善恶采取超越的立场?
庄子在《大宗师》描述了他所认为的理想人格:“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面对是非善恶的判分,真人一方面可以做到“与天为徒”,即“和之以天倪”;另一方面可以“与人为徒”,对于世间由成心所形成的是非善恶则以“因是已”的方式对待之。以下分别述之。
首先,庄子在《齐物论》提出“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张默生先生说:
自然间有一种天然的分际,也可说是自然间的“是”与“不是”、“然”与“不然”,无容己私意参与其间。[8]
这种说法肯定了自然间自有的、非因成心或己意而有的“是”与“不是”、“然”与“不然”。这也就是所谓的真是非、真然与真不然。[9]所谓“真是”“真然”即是万物的“自是”与“自然”。例如,庄子在《齐物论》指出,“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且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各有其“正味”。每一物的“正”即是其“自是”与“自然”(即万物的自然本真之性),因而也是“真是”与“真然”。由此,“天倪”即是指万物的“自是”与“自然”,也即因着万物的本真自然之性所形成的自然的分际。由此,庄子提出“和之以天倪”的主张,即人之认知与行为应与万物自然的分际(自是、自然)相符合、协调。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真是非”是相对于由人之成心所构建的“是非”而言的,对于天地万物本身而言,只有“自是”与“自然”,不存在由成心所建构的“非”。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说,圣人之心,可以完全与万物的“自是”与“自然”相符应。
然而,倘若执着于万物的“自是”与“自然”为一绝对的“是”,那么在面对众人因着一己“成心”而有的是非认知时,便会以他人为绝对的“非”而不能对其有同情的了解。因此,庄子提出“与人为徒”的“因是”之道:“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齐物论》)当与众人相处时,真人未有对“自是”“自然”的执心,而仍能做到随顺、因循众人由各自的判断标准所形成的是非认知。换言之,真人的认知虽然可以全然与万物的本然之性相符应(合以“天倪”),因此自身不入是非之途,但对于世人由“成心”而来的是非,真人只是顺任其差别,因物付物,尊重、肯认并因循每一个人各自的“是”(各自的认知脉络与存在意义)。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波逐流,毫无原则呢?事实上,庄子所说的“因是”是以生命主体(4)王邦雄先生说:“百骸、九窍、六藏,具备于吾身,彼此各有专司,地位等同,吾人自不能有所私亲,而使其为主;彼等亦不可能皆属臣妾的茫然无主;或递相为君臣的轮换不定;由是以证立人的生命,必有统摄官能而超越其上的真君,就是人的生命主体。”参见王邦雄:《中国哲学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4年,第79页。的确立为前提。在此,陈德和先生强调:“主体的整全开显,依儒家为例,必心量德量之无穷,在道家则是能容通万物而无私无偏、无障无隔……通过扬弃和升华的历程,超转活化了自我,使物我皆得其所。”[10]所以,庄子所说的“因是”是建立在更高生命主体(合于“天倪”)基础上的因顺,而非纯然无主的顺任物势。
庄子对“是非”如此,对“善恶”亦然。他提出:“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钟泰先生解释说:“夫尧之仁非桀之比,人无不知也。然博施济众,不能无病。是其仁亦有尽时,不如天之无心于物,而物无不蒙德也……曰‘化其道’者,尧忘其尧,桀亦化其为桀,一纳于道之中,而誉与非更无所用之也。”[3]141也就是说,通常被人所肯认赞誉之物(或人),亦不可能完全“无病”。例如有仁德的尧,由于他博施济众、有心为仁,故其仁德之行能见赏于人。但是,“其仁亦有尽时”,不如像天地一样无心育物,万物却能恒久蒙受其德,这即是所谓的“大仁不仁”。因此,从“天”的角度看,尧与桀皆非。故而,正确的对待方式,应首先浑化、忘却毁誉是非之论。然而,此处的“忘”并不意味着庄子不分是非、善恶,而是仍有是非、善恶的辨别,却不执于此,心中明了即便是“非”与“恶”,其背后亦有可以溯源的成因脉络,从而能以“无弃人”“无弃物”的若谷虚怀给予感同身受的理解与体贴。这也体现了道家式“常善救人、常善救物”(5)《道德经·二十七章》曰:“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的伦理关怀。如《道德经·四十九章》所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无私心、通人我,这是一体包容的感通之爱;圣人成己德,化万物,这是对于不善、不信者的不弃不离与同情的理解。对此,赖锡三先生评论道:“没有任何一人一物遭受遗弃,全部都能以本来身相得见真人而蒙受滋润纳容。这种‘无弃人’‘无弃物’如大海般的胸怀容纳,便是道家所渴望的冥契伦理学、原始伦理学。”[11]
三、法于“天德”的“不仁之仁”——治国者的为政之道
庄子不仅提出了“天与人不相胜”的处世原则,而且,他也依此提出了“为天下”之道:
夫圣人之治也,治外夫?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应帝王》)
这段话含义有二。首先,从正面而言,天地万物皆自知趋利避害的法则,如鸟知高飞以避弓矢,鼷鼠藏于深穴以避熏凿,天地万物自有其自全之道,不待教而然,不待为而成。因此,君王只要顺民本然之常性,不以经式仪度外加于民,则天下可以自治。正所谓“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化”(《道德经·五十七章》)。其次,从反面来说,鸟鼠本来天性自得,人若欲以机械取之,则会迫其高飞深藏而避之。百姓之自然天性,如同鸟鼠,人君愈有心治民,民愈惊而趋避。由上可知,鸟鼠作为天地万物之一,同时是万物自然状态的表征;庄子藉鸟鼠避害的例证说明了君主的治国之道,应当无为自然,顺任民之常性,则自会有无不为之功。该段文字的落脚点在于阐明万物的自生自化,以及有心有为之患。正是在此意义上,庄子在本段开头说:“夫圣人之治也,治外夫?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圣人之治并非殚精竭虑以“治外”,而应“正而后行”、无为以治。在此,庄子并未提及天地的自然无为之德,但庄子将人民与因着天地的“无为自然”而天性自得、自有其自全之道的鸟鼠作类比,天德已呼之欲出了: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故帝王圣人休焉。(《天道》)
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天地》)
君临天下,须以“天德”之无为自然为本。在此意义上,庄子反对“以天下为事”,并主张“外天下”:
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逍遥游》)
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大宗师》)
“弊弊焉以天下为事”特指将天下作为一“外物”来治理。己心不虚、物我对立,因而不能“旁礴万物以为一”,所以有“外”天下的必要。需要注意的是,“外天下”的“外”并非遗世独立,欲将“天下”排除在外;恰恰相反,所谓“外天下”,乃是“不以天下为事”,是消弭一己“成心”(无己),与天下玄同的实践工夫;其义涵类似于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四十九章》)。当治国者消解了一己成心而能以百姓心为心,“天下”将不再是被对治的身外之物,而成为治国者与之感同身受的同体存在,由此,治国者对百姓的全情体谅、尊重与顺应将最大限度地开出百姓自治的活力空间,达成无为而无不为的现实效果。与之相对地,庄子对怀有“仁德”以经世济国的儒者是持否定态度的。如下所言: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应帝王》)
其中,“非人”包含两层含义。其一,“非人”为“天”也。“未始出于非人”是说有虞氏有心为仁以得人心,则虽得人之道,却不及天之浩浩也。[3]168因此,“未始出于非人”是说有虞氏的仁德仍是有心之德,未若天地的自然无心之德,这也是我们在上文反复提及的“大仁不仁”。王煜先生说:“‘大仁’与‘不仁’前后两个仁字的对象似同而实异,不仁是对个体而言,即对万物之中每一物而言,而大仁是对万物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天地既有生生之德,使宇宙充满生意,那末天地就是至高无上的仁者了……天地是最伟大的生生者,也是最伟大的杀生者,假如天地仅生而不杀生,那末自然界的均衡便丧失了。”[12]这就是说,天地使万物生生不已的大仁是建立在“万物一体”基础上的无心之仁,是对万物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看似泛爱而一无所爱。因此,“未始出于非人”所包含的第二层含义即是有虞氏之仁,只是限于人而言,而未泽及天地万物。这也隐喻了儒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爱有差等,“爱物”的工夫次第乃是排于“亲亲”与“仁民”之后。从文中“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的“藏”字也可以看到,有虞氏所怀之“仁”是有所保留之仁,并非是以万物为一体的无心之仁;相反,天地自然无为的“生生之德”对万物的成就,则是以万物一体为基础,庄子所肯认的治国者的得人心之道,亦是万物一体基础上泛爱而无心的“大仁”。在此基础上,庄子构化了理想的社会图景: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马蹄》)
善治天下者,如“天”之自然无为,这一无心的不治之治看似不仁,实为大仁。这表现在治天下者的无心无为,给出了万物(包括人)顺其自然的发展空间与生命活力,不仅能使人人顺其真性,安其居,乐其俗,不以自我的机心巧智破坏浑然素朴、无知无欲的天德;而且能与鸟兽和谐融洽地共生共长,与天地万有达成一体的和谐。这里的“一而不党”“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强调了在治天下者的浩荡之仁中,人人都可以摒除私心,抛却智巧,成就无心之仁;在此前提下,已无所谓君子小人的分别与对立(“恶乎知君子小人哉!”),这便是庄子心中理想的“至德之世”。
四、结 语
历史上,荀子曾批判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实误解庄子之意。事实上,庄子对人间伦理及政治秩序有其深切关怀。他将自然无为之“天德”作为人修德的价值依据,旨在成就天地人我的大和谐。面对人间世的伦理价值标准,庄子提出了“天与人不相胜”的应对之道:一方面,人应“和之以天倪”,其认知与行动能与万物的本然之性相符应,因此自身不落是非之途;另一方面,人亦不曾废弃是非善恶、遗世独立,而能因物付物,与众人共饮太和。在为政治国领域,庄子主张国君应深刻体认万物本为一体的存在处境,法“天德”而行治道,实则是以不仁之大仁实现万物自治。由此可见,庄子的伦理政治主张本质上是在“天”与“人”之间寻求一种圆顿的平衡,从而集中体现出《天下》篇所彰明的庄子哲学“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圆融理境。
——亚里士多德arete概念的多重涵义及其内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