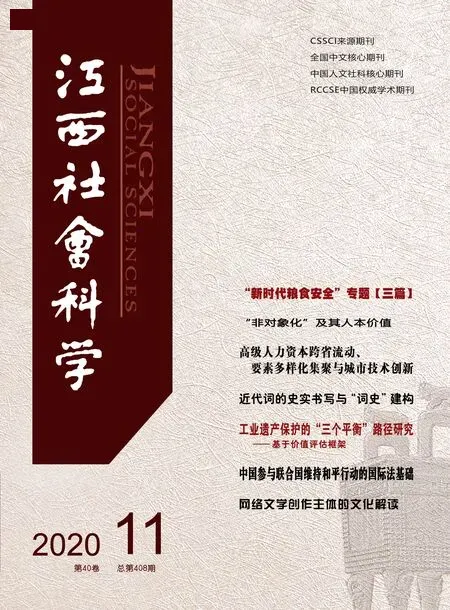工业文明裂变下的现实主义:19世纪英国小说的精神图谱
19世纪英国小说的成就举世公认,那个时期名家辈出,如司各特、狄更斯、萨克雷等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从各自角度和方向都准确地切中与呈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的现实风貌,如司各特虚构历史的民间传奇小说、狄更斯反映社会底层的社会批评小说和萨克雷讽刺上流社会的社会讽刺小说。从群像的统一性来看,这些小说所传递出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与精神取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但就各自特色而言,则又是各有千秋,相映成趣,如司各特嵌入超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狄更斯基于人道主义的现实主义和萨克雷弘扬仁爱的现实主义。
对于英国文学创作而言,19世纪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有着世界影响力的小说家,有司各特、狄更斯、萨克雷、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等。相比其他文学体裁而言,小说更能够具体且充分地描述和反映现实生活,而维多利亚时期很多小说都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如司各特的民间小说、狄更斯的社会批判小说、萨克雷的社会讽刺小说等。这些小说家们的成功主要来自于他们贴合英国民众口味的叙述风格和语言形式以及内容对民众世俗生活的现实主义关怀。相较以往的作家,他们更愿意在其创作中关心现实中的问题,如政治、经济、社会、婚姻、女性、儿童、环境等。国内对19世纪英国小说的研究初期多以翻译为主,如李未农等人合译的《英国小说发展史》(1935)、李儒勉翻译的《英国小说概论》(1947)、刘玉麟翻译的《简明剑桥英国文学史》(1987)。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研究才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硕博论文和专论,并持续保留着较高的学术热度。本文通过对司各特、狄更斯、萨克雷的群像分析,进一步分析19世纪英国小说在工业革命冲击下所表现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取向与叙事方式。
一、嵌入超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司各特的民间传奇小说
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是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一生创作11部长篇叙事诗,27部长篇小说以及数量庞大的短篇小说、散文、日记和历史传记等。[1](P93)他影响了曼佐尼、普希金、巴尔扎克、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等人的文学创作。[2](P28)司各特所有创作中,最具鲜明个性的当属民间传奇小说,内容包罗万象,想象天马行空,令读者爱不释手。他将欧洲古代社会中常见的生活图景和历史传说,如鬼魂、吸血鬼、诅咒、魔法、巫术、充满迷信色彩的乡村习俗、神秘的苏格兰乞丐以及四处讲述异象的流浪汉、富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人物等,借助文学艺术的加工合理地融入他的民间历史小说中,让这些看似曲折离奇的超自然现象真实地嵌入小说人物的日常生活中。[3](P98)
在《流浪汉威利讲的故事》《挂绣帷的房间》《两个赶牛人》《玛格丽特姑妈话镜子》等短篇小说中,作者运用了将超自然的现象和传说嵌入历史人物生活中的技法。《玛格丽特姑妈话镜子》写了许多神奇的故事,比如,福雷斯特太太为了得到一个关于自己丈夫的确切消息,便不顾一切去寻找法力高强的巫师来测算自己丈夫的命运。《流浪汉威利讲的故事》则讲述了威利的爷爷斯蒂尼·斯廷森为何以及如何去阴间找罗伯特·雷德冈特利爵士讨债的故事,其中描写了不少有关地狱和鬼魂的场景,深受苏格兰清教徒们的喜爱。
同样,司各特熟练恰当地将许多超自然主义的文化、知识与习俗融合到长篇小说创作中。在《海盗》中,他极力地描绘了绚丽多彩、波谲云诡、诡谲怪诞的极光风景,运用海上救难活动被视作灾难的民间信仰推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并在故事中掺入了大量的民间习俗和广为流传的巫术,使得超自然主义成为小说不可忽视的元素和结构。《昆廷·杜沃德》故事背景设定在路易十一致力于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的历史中,刻画了勃艮第公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权力斗争,情节主要集中于路易十一与勃艮第公爵查尔斯·博尔德之间的权力竞争。为了准确刻画路易十一的形象,司各特在小说中直接坦言:“要完整地描写这个可畏的人物,还得注意另外两个特点”,而“第一特点是路易非常迷信……路易作恶多端,引起良心的责备,但他并不放弃勾心斗角,改邪归正,反而枉费心机,用迷信的仪式”。[4](P4)由此可见,《昆廷·杜沃德》运用了许多近乎迷信的超自然素材来描画路易十一,甚至由于这些超自然元素介入反而弱化了路易十一在历史记忆中凶狠诡诈的形象。同样,在《艾凡赫》中,司各特成功地塑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如汪巴、葛尔兹、蕊贝卡、黑甲骑士艾凡赫、隐士柯普曼赫司特牧师、罗宾汉等。其中,汪巴意图探听外来的骑士们是否由仙境而来,是否带来了仙王奥布朗王的消息;隐士柯普曼赫司特牧师为了护持圣者,时常克制欲望,仅靠食豆和喝水度日,神奇地却能保持身体健硕、孔武有力;仆人奥斯瓦尔德坚信神仙能将他的少爷救走;撒克逊人相信预兆,认为黑狗挡道乃不祥之兆;当地土著相信教规上提到的,“恶魔常以妇人为饵,诱惑教徒使他背离升天的正道,因此规定不准备吸收妇人参加我们的教派”[5](P346),并从此不准对自己的母亲和姐妹行亲吻礼节。这些近乎神奇的超自然主义描写让司各特的小说奇幻异常,大大激起了读者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上述展现在司各特小说中的超自然主义手法的运用,体现了作者希望通过将虚构与真实的超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相结合,从而使人们“长出一双透过超自然的奇特非凡的事物表象洞察现实的慧眼,让人们从虚幻、缥缈、离奇的事物背后看到其所隐喻的社会现实的本质”[3](P98)。由此可见,司各特在小说中向读者传递的真实历史观便是在真实中虚构、在虚构中诠释真实。司各特所运用的民间传说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但一定是历史的真实。因此,司各特的超自然主义的虚构只服务于历史的真实,而不是真实的历史。黄永林曾指出:“(超自然主义的)神秘文化的描写不仅在小说中营造了一种奇幻的生存气氛,制造了一种浓郁的神秘气息,形成小说奇异、浪漫的色彩,而且使作品蕴含着玄奥的人生哲理,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厚重感和历史感。”[6](P136)书写在司各特小说中似真非真的历史主要是为了展现出所有人(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会、也必将会在历史生活中展现出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当然,对生活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掌握与书写主要还是来自于司各特对普通人的“生活艰难有着透彻而全面的了解”[7](P40)。
司各特文学作品中这些充满浪漫幻想的超自然主义因素,不仅在其自身成长经历中有其必然性,而且能够更加真实深刻地揭露出19世纪英国普通民众的精神风貌。司各特因幼年患病,行动不便,使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倾听祖母和姑母讲述各种各样的充满传奇色彩的苏格兰边境故事和歌谣,这些唤起了他对战争、勇士、宗教纷争、宫廷阴谋、苏格兰古老历史传说等内容的兴趣和想象。成年后,司各特在诉讼代理的过程中又接触到了大量当事人讲述离奇古怪的经历、故事以及风土人情。他还曾一度去往原始的利德斯代尔地区采风,寻获了大量的民间歌谣和乡土传奇。这些都促使他对超自然现象以及古老历史充满了探索的兴趣。司各特历史小说的主角通常都是一些平凡的普通人,“是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半历史性或者非历史性人物”[7](P114)。这就使司各特容易将充满幻想的超自然故事和传说嵌入小说,让小说中半历史性人物的生活显得真实可信又充满奇幻色彩,不仅容易引发读者的共鸣,而且还起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二、基于人道主义的现实主义:狄更斯的社会批判小说
相较于洋溢着神秘气息的超自然主义在民间传奇小说中的运用,狄更斯(1812—1870)更愿意将目光和创作的兴趣投向现实生活中社会底层民众如何以及为何遭遇不公和苦难的现象,他常常以富有人性的笔调促人深思,也试图以社会批判的方式推动中产阶级读者思索未来社会的改革之路。所以,狄更斯的小说一直以来都被视为绽放在现实主义中的人道主义鲜花,而狄更斯基于人道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837—1841年,应属狄更斯现实主义创作的早期。该时期的作品通常强调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的不公和富有阶层对贫苦民众的冷漠无情,表达出对底层人民生活困苦的同情,树立起邪不压正的道德信念,洋溢着乐观的人道主义精神,主要作品有《雾都孤儿》(1837—1839)、《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8—1839)、《巴纳比·拉奇》(1841)等。《奥利弗尔·退斯特》(1837)、《尼古拉斯·尼可贝》(1838)和《老古玩店》(1840)等作品通过对贫苦子女在工业革命浪潮中窘迫生活的描写,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冷漠与凶残,甚至连最贫弱的儿童也无法激起慈善和教育机构本该有的怜悯和帮扶,反映了社会变革中的人性堕落和道德沦丧。由于这一时期属于狄更斯小说创作的初期,此时作品重在描写伦敦城乡之间的风土人情,表达出的思想与情感都较为单薄,仅有简单的是非善恶判断和天真烂漫的情感,所以,此时的人道主义主要是基于批评现实生活之困苦和不幸的浪漫化的人道主义。
第二阶段是1842—1858年,属于狄更斯现实主义创作的成熟期,对现实生活的揭露更为深刻全面,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技法更加娴熟,表现出非凡的创造力,特别是在底层劳动者的形象塑造上尤其成功。虽然此时狄更斯依然保持着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关心,但还是反对通过暴力革命来改变社会现状,希望通过改良来缓和社会矛盾,从而使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结局都保留着其一贯的喜剧风格,体现出狄更斯在精神上抚慰底层民众陷溺于不幸现实的苦难悲情的人道主义。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董贝父子》(1846—1848)、《大卫·科波菲尔》(1849—1850)、《荒凉山庄》(1852—1853)、《艰难时世》(1854)等作品。《美国札记》(1842)以及《马丁·朱述尔维特》(1844)两部小说主要着力抨击当时的种族仇视、社会上弥漫着的贪得无厌和争逐名利的风气。《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小杜丽》《艰难时世》等作品生动再现了富裕阶层的堕落与贪婪、伪善与阴毒以及司法的腐败与行政的无能。其中,《大卫·科波菲尔》中透过大卫一生的悲欢离合,狄更斯向读者揭露出金钱至上观念对当时英国社会各层面、各角度的腐蚀与败坏,暴露了英国儿童教育和司法制度的黑暗,谴责了社会邪恶势力的阴险、狡诈、狠毒和淫乱。《小杜丽》通过对小杜丽家庭财富变迁的历史描写,揭露繁荣背后的邪恶以及英国官僚制度和文牍繁复中的麻木不仁。《艰难时世》描述了某工业市镇上的庞德贝和葛莱恩两人家庭之间的艰难生活。这些作品在揭露丑陋腐化的社会现实时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与狄更斯早期乐观浪漫的人道主义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此时的狄更斯经历了早期生活的磨砺,对现实生活的苦难和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有了更为真切深入的认识,使他从原本乐观地寄望于社会改良主义到此时寄托于宗教、道德、善良人性来改变充满苦难的社会现实。因而此时作品大都不遗余力地重复宣扬诸如反对暴力、博爱仁慈、人性的善良和甘愿牺牲等人道主义精神。
第三阶段是1859—1870年,可视为狄更斯现实主义写作的晚期。此时期的作品无论是写作技法,还是艺术特性和思想意境上,相较前期都更为成熟和多样化。但值得注意的是,狄更斯此时的作品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悲观,比如《双城记》(1859)、《远大前程》(1860—1861)、《信号员》(1866)等。作为狄更斯的代表作之一《双城记》以梅尼特医生受迫害的经历为主要线索,描绘了法国大革命前夕,封建贵族如何败坏腐朽、如何凶残暴虐、如何疯狂压迫和残害百姓,而人民心中又积压着怎样的深仇大恨,形象地指出法国大革命的必然性,警示当时英国统治者应该重视社会现实的不公,并应该努力为此寻求出路,改变现状。《远大前程》创作出了许多生动人物形象和扣人心弦的情节故事,如皮普、艾丝黛拉、郝薇香、乔、马格韦契、马修等,狄更斯借助这些人物和故事展现出恻隐之心才是促进人们生活正常情感的要素,体现了作者对人的热爱、对生活的一切丑恶的强烈憎恨,拥有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心灵。[8](P63)这一时期,狄更斯的生活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故——如离婚、婚外情等,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从而对社会黑暗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不幸和苦难的理解更加透彻,导致这一时期作品的基调略显灰暗与悲观。也就是说,此时的狄更斯在批判现实世界的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人道主义是基于同情的哀婉的人道主义。
由上述可知,狄更斯小说以高度的艺术概括、生动的细节描写,又用个性鲜明的角色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将维多利亚下层民众塑造成一个个深入人心且发人深思的形象,更加逼真地描述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社会风貌。从他的小说中,不难看到既有对丑陋腐化的社会现实的生动再现,更有基于对广大贫苦人民深切同情的人道主义关怀,从而使狄更斯的现实主义并非毫无温度的冷漠旁观,而是在贫苦中注入希望,从绝望中流露出幽默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曾有过相似评论,他认为狄更斯以“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做的还多”[9](P211),因此,狄更斯应该是“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0](P146)。因为他从来并不特别关心透过小说表达怎样的思想和观点,而更关心如何表达和呈现现实世界。
三、宣扬仁爱的现实主义:萨克雷的社会讽刺小说
作为与狄更斯齐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小说家,萨克雷(1811—1863)同样创作出享誉世界的《名利场》(又译《浮华世界》),除此之外还有《班迪尼斯》《亨利·埃斯蒙德》《弗吉尼亚人》等重要作品。他的小说从不同角度对英国中上层阶级的社会生活图景展开深入且完整的研究与描绘,创作出众多令人难忘的角色,从他们的故事中真切地体会到美德、虚荣与罪恶的结合,同时也能感受到萨克雷在风趣幽默地讽刺社会现实中透露出引领人们走向仁义与慈爱的博大情怀。
《名利场》的问世永久性地确立了萨克雷在世界文坛的名望。该小说以法国结束对欧洲统治的滑铁卢战役为写作背景,通过描写三个上流社会中彼此熟知的联姻家庭之间的故事,再现出当时欧洲社会的生活群像。全书情节围绕着丽贝卡和艾米丽两位性情迥异的年轻女人的人生际遇而展开。丽贝卡出身低微,是个穷画家的女儿,为人机灵乖巧,一心想掌控命运,摆脱困境,遂而不择手段,凭借谄媚奉承飞上高枝,后因自私自利被其丈夫所识破,而遭抛弃,致使身败名裂,最终重操旧业,招摇撞骗,再度混入上流社会。艾米丽出身富商家庭,性情单纯善良,且柔弱笨拙,一生渴望爱情,早年迷恋上曾受其父恩惠家族中的纨绔子弟乔治,从此整日忍受来自乔治姐妹的挑剔,然而,其父破产后,就立即遭受解除婚约的羞辱,但在都宾的斡旋下与乔治秘密结婚,婚后不久又备受冷落,却依旧一往情深,在得知乔治战死后,痴情不绝,将乔治视若神明,疼爱她们的儿子,直到丽贝卡恶意揭穿了乔治的不忠和虚伪,她才下定决心与真挚且富有同情心的都宾喜结连理,从此过上幸福安逸的生活。丽贝卡和艾米丽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女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丽贝卡一生孜孜以求富贵名利,常常无所不用其极以达成其心中所欲,且又欲壑难填,形成了争强斗狠、阴损无耻的性格,而其结局却是黄粱一梦;艾米丽性情寡淡、无心功利、乐善好施、坚忍克制、内心平和,对生活始终保持着乐观而谨慎的态度,虽历经欺骗,却又终获幸福。正是因为有了艾米丽的存在,才凸显出丽贝卡这一人物形象的生动性与深刻性。由此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塑造的人物都是真实的男男女女,而不是那些具有超人情感和美德,经受了难以令人置信的考验和磨难的英雄。其目的就是要创造出一种更为接近现实的小说,它不作为读者想象生活的媒介,而是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11](P66),从而使小说所“表现的逼真度和评价的公正性都显而易见”[12](P214)。整部小说宏大的叙事结构足以容纳当时的社会全景——从贵族庄园、商贾府邸到平民陋室,从宫廷到牢房,从市镇到乡村,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德国,从拿破仑战争到英国殖民,背景之广,足以称之为“全知视角凝视下的广阔全景”[13](P61),甚至“具有一种社会文献的作用,准确地表现了历史、社会和心理”[14](P312)。《名利场》深刻批判了隐藏于繁华现实背后的堕落与腐化。由于维多利亚时期公共性的写作要么卑躬屈膝,奉承权贵,要么醉心描绘豪门盛宴的精美华贵,这让萨克雷痛心疾首,于是,他把小说当成了“对当时社会的宣战书”[15](P710),“批评英国各大报纸的撰稿人出卖人格,交换文字产品,以博得金钱利益和统治阶级的认可”[11](P64)。与其他伟大的作家一样,萨克雷“具有神一般存在的特质……是一个怀着焦虑的良心的神”[12](P214)。其实,这里的“良心”并不应该是指萨克雷通过其小说揭露了社会阴暗面和现实的丑陋,也不是对此展示出来的戏谑调侃式的讽刺和批判,而是对善良的守护、对仁爱的倡导。萨克雷在《名利场》中透过艾米丽人世沉浮的经历告诉世人:先人后己、助人为乐、克制私欲、摒弃烦扰等美德才是我们应当守护和弘扬的,因为“仁爱与同情能让最微不足道的行为变得高尚”。因此,在萨克雷所有小说中,仁爱与同情始终处于引导小说情节走向的核心线索以及讽刺社会现实的价值基石。
四、结语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一直扮演着世界工业革命的领路人,无论在器物上,还是科学技术上,都曾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器物终将腐朽在历史的烟尘中,科学技术也会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地迭代。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回味和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虽然无法完全摆脱彼时的器物与科技,但更值得我们留恋和追慕的应该是那时人们所思所想的精神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小说是世界文学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诸如司各特、狄更斯、萨克雷等名家所创作出来的小说更是这部分之中的精华。阅读和研究这些名家们的小说无疑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最好途径之一。
总之,司各特嵌入超自然主义的民间传奇小说、狄更斯基于人道主义的社会批评小说与萨克雷宣扬仁爱的社会讽刺小说,这些璀璨绽放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瑰宝向世人呈现出一组连续的而又不断变化的现实主义小说群像。无论在内容架构、创作方法、主题选择、风格塑造等方面,还是思想表达、观念输出以及道德引领上,这些小说都展现出作为人类优秀文化群像的极大统一性,即关注生活本真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