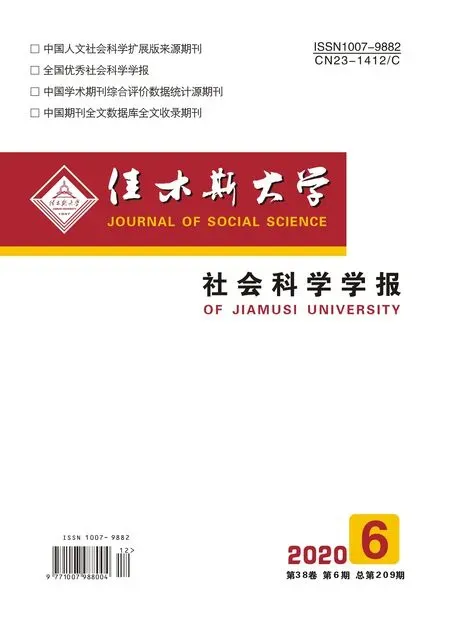普鲁士改革家提奥多·冯·舍恩不同史学思潮下的形象变迁*
闫 健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提奥多·冯·舍恩(Theodor von Schön)是19世纪上半叶普鲁士自由主义改革派中的代表性人物。作为施泰因最重要的助手,他是《十月敕令》这一对普鲁士历史影响深远的农奴解放法令的主要起草人,也是《施泰因政治遗嘱》这一重要思想著作的实际撰写人。此外,他作为封疆大吏主政东西普鲁士省长达26年,位高权重,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是唯一一位在任期间便获得国务委员头衔,在国务院享有席位和投票权的省督,卸任后更被授予黑鹰十字勋章,并加封玛利亚堡伯爵,在普鲁士政坛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研究19世纪普鲁士行政史和官僚史,舍恩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
鉴于舍恩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自19世纪至今,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专门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舍恩的政治形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然而,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我国史学界却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史学史的角度对180年来关于舍恩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剖析,寻找出其形象演变的轨迹,为本国学者研究舍恩及同期普鲁士政治史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19世纪的舍恩形象——夸张、扭曲、意识形态化
舍恩在世时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政治人物。他性格强势,意志坚定,毕生反对官僚集权统治,呼吁国家放松对社会的过度管控。支持者认为其直言敢谏,是勇于同旧势力作斗争的“斗士”,视之为自由主义的代言人。尤其是1848年革命之际,激进派甚至利用其声望为革命造势。而反对者则抨击他独断专行,将他描述为“普鲁士省的统治者”[1]42、“副国王”[2]9。这样的评价分歧鲜明地体现在后世对舍恩的研究中,并与不同时期的史学潮流紧密相关。
19世纪的德国,得益于以史料批判和如实直书为特色的兰克史学,逐渐成为西方史学研究的中心。关注精英人物、重大政治事件的叙事风格逐渐成为主流。
1842年,《普鲁士政治家系列丛书》在莱比锡出版,分别介绍了施泰因、哈登贝格、舍恩和尼布尔等政治家。第三卷介绍了舍恩从幼年直到卸任的人生经历,可以称得上是关于舍恩的第一部小型个人传记。文章尤其对舍恩草拟的《施泰因政治遗嘱》和政论文章《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进行了重点介绍,对舍恩追求民众自由、反对官僚统治、推进等级融合、构建道德国家的政治理想进行了总结,着重突出和赞美了舍恩的自由主义形象[3]。1843年,艾维琳娜出版了《省督奥尔斯瓦尔德与舍恩地位之比较》,通过详细阐述施泰因的治政理念,对《施泰因政治遗嘱》是由舍恩所草拟的说法提出质疑,批判了当时“舍恩是改革的大脑,施泰因只是执行者”[4]的说法,将舍恩解读为一个沽名钓誉、自私自利的人。可见,早在19世纪40年代,人们对舍恩的评价就已经出现了分歧。
第二帝国成立后,历来主张“历史学家可以根据现实政治需要去理解和解释历史”的普鲁士学派大放异彩。该学派利用历史为普鲁士的扩张和战争政策服务,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意志,鼓吹民族主义,宣扬强权政治。不少人甚至走向了沙文主义。该派的两位重要历史学家聚贝尔和特赖奇克,“宁愿树立英雄典范式的俾斯麦形象也不愿意承认德国精神被征服所带来的灾难”,认为“征服是统一不可避免的代价,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比宪政改革和公民自由更为重要”[5]39。
但同样是这一时期,政党政治兴起,帝国议会中的自由派已经积聚了不可低估的力量。作为对普鲁士学派思想的抵制,1875年至1883年,6卷本《国务委员及玛利亚堡伯爵提奥多·冯·舍恩选集》陆续出版,遴选了舍恩著述的日记、游记、通信和自传内容,是当时第一部正式公开发行的舍恩作品集,涉及到舍恩在处理等级议会事务、推动行政机构改革、推行教育和教会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6]。1876年至1896年,署名为“一个东普鲁士人”的编者鲁道夫·伊瓦尔德又继续出版了《在舍恩墓旁抵抗和防御——耻辱与暴动时代的图景》《国务委员及玛利亚堡伯爵提奥多·冯·舍恩文集补录——上世纪末一位青年政治家的英国考察旅行》《来自坟墓的警告——国务委员及玛利亚堡伯爵提奥多·冯·舍恩关于祭司统治的三篇备忘录》[7-9]等文献。
该文集自出版后引起了广泛批评,原因是政治意图和论战特征太明显,文献选取断章取义,甚至牵强附会。舍恩在改革时代和前三月时代提出的政治诉求,被自由派当作典范过度夸大,试图在党派政治中把舍恩打造成为自由主义的代言人,以壮大反俾斯麦阵营的声势,严重影响了学术性。例如,在1881年出版的《国务委员及玛利亚堡伯爵提奥多·冯·舍恩文集之再补录》中,几乎有半数篇幅是编者自己的话,这俨然已不是舍恩的文集选录,而是以舍恩档案为论据阐述自己观点的专著了,序言中即表明了编者借古讽今的意图:“如果今天的帝国首相(俾斯麦)总想着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避开合议制,让所有的部门主管都降格为自己个人意志的工具的话,那他就毁灭了普鲁士的建国基础。”[10]
史学家伊萨克松认为这套出版物严重侮辱了舍恩:“编者将自己的观点与舍恩的文献和引述混淆得如此厉害,以至于人们很难将二人的思想分开。”[11]11特赖奇克批评得更激烈,甚至极端:“仅用三言两语很难弄清舍恩的复杂性格。关于这个虚荣的骗子的激烈争吵给人带来的不适几乎不比那些没有思想的极端自由分子把他当成神来崇拜的行为让人舒服多少。”[12]X
同期,被伊瓦尔德视为“粗制滥造的作家以及维特根施坦派政策代言人”的马克思·雷曼编撰的《克内瑟贝克与舍恩——解放战争期间的文稿》,序言里就表明了完全有理由对这个“讲述者”(舍恩)持怀疑的态度[13]。
可以看出,在19世纪,尤其是后半叶,舍恩的形象不仅存在正反两方面的争议,而且总体上是扭曲的,其个人思想被有意地误读曲解或是过度拔高。舍恩在逝世20年后被推上神坛,被塑造成一个反专制的极端自由主义者,成为当时自由派反对俾斯麦专权的工具。在双方的相互攻讦中,舍恩的形象充满混沌。
二、20世纪上半叶的舍恩形象——理性化、客观化
进入20世纪后,传统的兰克史学虽然地位出现动摇,但鉴于德国的特殊形势,德国史学变革较之西方其它国家却很缓慢,并未大幅转向关注社会、文化、规律等内容的新历史研究模式。此期间关于舍恩的研究也依然没有脱离传统史学的范畴。不同的是,此时对舍恩的评述不再是以往那种论战模式,科学考证被重点强调,研究开始理性化、明辨化以及专题化。
1910年马加雷特·鲍曼的论文《提奥多·冯·舍恩的历史叙述方式及其可信度》以原始档案为依托,结合舍恩时代的局势及同僚的评价,详细考证了舍恩所述的1813年以前关于农业改革、《施泰因政治遗嘱》、战时议会、成立国防后备军等内容的可信度。作者一方面确证了舍恩自身的问题,例如,“对于同僚的评价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评价事物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因而从来未能完整揭示重要人物的全貌”,但也同时对上世纪关于舍恩的偏颇评价进行了驳斥,“人们对舍恩的批评是有缺陷的,即对舍恩所处的内外部条件没有给予重视,不去考察其作品的实际价值,却用一个客观史学家的标准和要求来衡量他”[14]。
这一阶段,研究成果最突出的是汉斯·罗特菲尔斯。其专著《提奥多·冯·舍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与1848年革命》堪称研究舍恩对1848年革命之态度的经典之作,对后世学者了解舍恩晚年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著作借助档案着重探讨了舍恩在1848年革命前后关于宪法问题和民族统一问题的思想及变化过程,特别是详细剖析了舍恩对革命的态度越来越保守的原因,彻底打破其19世纪被极端自由派过度美誉的自由主义者形象,为我们再现出一个游走在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将倡导个人道德自由同奉献国家紧密关联起来的舍恩。“舍恩坚持‘国家观念’,这种观念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国家服务意识相接轨,同时还包括了建立在康德思想基础之上的改革派官僚‘思想共同体’(一种看不见的议会)理念……舍恩国家观念的核心是中产阶级—国家公民理想……精神自由不是反对国家,而是源于国家,国家是文化历史的最高内容。”[15]
此外,这一时段的舍恩研究开始体现出专题化的特点。古斯塔夫·哈瑟在《提奥多·冯·舍恩与施泰因经济改革》中专题探讨了舍恩于1807年至1808年间在废除农奴制、推动地产自由、废除领主世袭裁判权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使舍恩的真实思想,尤其是改革时期对待贵族的强势态度进一步明晰:贵族是落后时代的残余,终将退出历史舞台[16]。爱德华特·迈耶尔的《提奥多·冯·舍恩参与和领导下的东西普鲁士省的复兴》是第一部专题剖析舍恩在担任省督期间政策的著作,以舍恩1817年至1835年间对国家拨发的复兴基金的经营管理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舍恩对待农民阶层的冷漠态度,从而得出舍恩可以算是自由主义者,但不是民主主义者的观点[17]。另外,他撰写的《1815年后提奥多·冯·舍恩的政治经验与思想》深度分析了舍恩的思想来源,揭示了舍恩建构在自由与道德基础之上、国家先于民族的国家观[18]。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舍恩政治形象的最大变化是趋于理性化。学者们通过史料考证,比较客观地重塑了舍恩的政治形象。其政治思想,例如对宪法和革命的态度,对国家和民族的态度,以及对贵族和农民的态度,都在这个时期走向明晰。
三、20世纪下半叶至今的舍恩形象——立体化、生活化
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传统史学的营垒开始松动,历史研究迎来两次重大变革。一是60年代以后,“社会史”逐渐成为研究的主流。以汉斯·韦勒和于尔根·科卡为代表的社会史学家呼吁研究方式从传统政治史中只关注精英人物的描述转向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分析,强调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关注经济和社会结构。二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蓬勃兴起,主张将研究视角从传统史学中的精英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以及社会史学中非人化的社会结构转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微观世界,从“政治”和“社会”转向“文化”。
这一时期的舍恩研究显然也受到了新的史学思想,尤其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的影响,体现出非政治化、生活化、研究主题多元化的特征。在继续重视史料考证的同时,尝试多元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使舍恩的形象变得更加饱满,对其评价也更加理性客观。此外,两德统一使原始档案的获取变得更加便捷,编纂方面取得了新突破。
埃里希·霍夫曼专门研究了舍恩对西普鲁士省小学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重点揭示了他试图破除宗教和民族对立的政策理念[2]。爱思特·柯尔柏探讨了舍恩在担任省督期间的学校教育政策[12]105-116。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部作品明显受到社会史观的影响,通过对西普鲁士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的描述,以及引入相关统计数据作为论述基础,进一步揭示了舍恩的人文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观。沃尔夫冈·诺伊格鲍尔在论文《1823/24年之后的普鲁士省等级议会和提奥多·冯·舍恩》中,首先重点分析了普鲁士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从宏观角度再现了一个立体的普鲁士省,再通过探讨舍恩在任省督期间与地方等级的互动关系,深入考察了他对当地自治发展的影响[12]125-140。
走出“政治”,聚焦“普通生活”的研究倾向也鲜明地显现出来。乌尔苏拉·格鲁贝特研究过舍恩的私人交际圈子和“裙带关系”,以及这种人脉资源对其推行政策的作用[19]。作者还分析了舍恩在大学时期、游历时期以及从政时期所结交的朋友圈,并分析不同时期的朋友圈对其个人思想的影响以及后来施政的支持力度[12]41-53。古斯塔瓦·克劳萨对普鲁士秘密档案馆中1813年舍恩与妻子阿玛利亚的通信档案进行了整理和编撰,出版了《我热切期盼明天的邮件——阿玛利亚与提奥多·冯·舍恩1813年解放战争期间的通信往来》,向我们展示了舍恩在政治舞台之外的温和慈祥的丈夫和父亲形象[20]。
关于舍恩的自由主义形象,此时也更加真实了。乌尔苏拉·格鲁贝特在《省督提奥多·冯·舍恩——普鲁士改革中的自由派?》中从舍恩的自我身份认同、同僚评价以及普鲁士省的具体执政实践三个层面展示了舍恩“非自由主义”的一面,“他的自我认知与实践行为不完全相符,更多体现出一种矛盾性和非连贯性。有时舍恩追求的目标并不是‘现代化的’和‘改革导向的’,而是‘传统的’和‘保守的’……‘省领导’‘全能的省统治者’的行为要比表面上勾画出的‘自由主义改革家’的形象明显得多”[1]29-58。叶尼西的论文《提奥多·冯·舍恩的历史观及其眼中的普鲁士形象》通过研究舍恩重建玛利亚堡的案例,揭示出舍恩自由主义表象背后的建立在历史基础之上的普鲁士本土主义历史观和国家观。“作为一个‘老普鲁士人’,舍恩将玛利亚堡视为普鲁士整体国家的象征,就如同西敏寺对于英格兰一样。在骑士团精神中,他发现了一种历史的宏大,而这种宏大此时只能在解放战争以及国家改革中得以重现和升华。”[21]185-186诺伊格鲍尔也认为,舍恩具有自由思想,但这种思想却有一定保守性,并未从根本上脱离东普鲁士传统自由观的范畴。
在编纂学方面,贝恩特·塞瑟曼是需要重点提及的史学家。自上世纪末开始,他主持了舍恩遗稿再版项目。从学术质量上说,此版本与一百年前的版本相比有着巨大进步。主分4个部类:自传、考察报告、旅行日记、通信。2006年和2016年先后出版了《舍恩个人文集》第一卷(个人自传)和第二卷(考察报告)。第一卷汇集了舍恩一生所有的自传文章,甚至包括各种自传性质的散记,这就很好地避免了之前版本那种为政治目的而断章取义的情况。另外,新版采用“评注版”的方式,不仅对原文中出现的文法问题,如单词拼写、语法结构、旧式文体等错误进行了修改并在脚注中一一罗列,而且对原文涉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一一进行背景注解,更为难得的是对原文中舍恩自己某些过于主观或者有争议的观点进行了考证。总览该卷,脚注部分就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参考文献有80页之多[11]。此外,前文提及的由克劳萨编撰的舍恩与妻子的通信集也是这一时期文献编纂的显著亮点。
四、结语
总体来说,在新的时代形势和史学思潮影响下,舍恩的形象基本上从以往的偏激与刻板中摆脱出来,最大程度地接近真实了。舍恩本人由于性格强势、言辞激烈,曾经引发诸多误解,甚至是恨意。然而,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揭示出:舍恩既不是一个高高在上、暴烈激进的自由先锋斗士,也不是一个忘恩负义、沽名钓誉、虚伪势利的弄权小人,而是一个对经济、政治、阶层、社会、国家都有着完整和系统理解的政治家。
作为改革家,他具有一定的自由主义思想,但并未脱离东普鲁士地区那种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传统地方自由观。他虽然追求自由,但也潜存着成为地方统治者的反现代欲求。他反对贵族特权,认为它会破坏公共精神,却又同意贵族继续存在,成为社会的道德榜样。他支持全国性的议会制度,却对宪法态度模糊,维护君主制,将君主理解为上帝的代表。他主张建立权利平等、自由法治的公民社会,但对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却非常冷漠。他呼唤国民自由与道德,但认为这只是手段,国家才是最高目标。这个国家是普鲁士,而非德意志,因此他并不支持1848年革命,也不关心德意志统一。所以,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不是民主主义者。他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但不是民族主义者。他是一个普鲁士主义者,但不是德意志主义者。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有进步,也有保守,他的行动有坚持,也有妥协。此外,他还是一个不唯活于官场,而是有着自己的家庭、朋友、情感、情绪的普通人。通过历代学者的研究积累,舍恩的形象如今更加立体和充盈,这是舍恩研究的一个巨大进步。
本文探析了180年来舍恩在研究文献中的形象变迁。可以看出,对于舍恩的研究往往与时代形势息息相关,也受到不同时代史学思潮的深刻影响。从史学史和编纂学的角度来看,对于舍恩的研究并未完结。毕竟时至今日,对于舍恩的研究基本还是限于德国,其它国家甚少。我国史学界对这样一位具有鲜明性格特色、对普鲁士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改革家也同样尚未给予太多关注。塞瑟曼主持的舍恩文集再版项目以普鲁士秘密档案馆的原始档案为依托,为学者客观准确地研究舍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项浩大的编纂工程目前还在进行中,大部分内容尚未出版。可以推断,其余卷册出版后必能带来不少新内容,届时舍恩的历史形象会更加清晰,这对于整个普鲁士政治史研究也会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