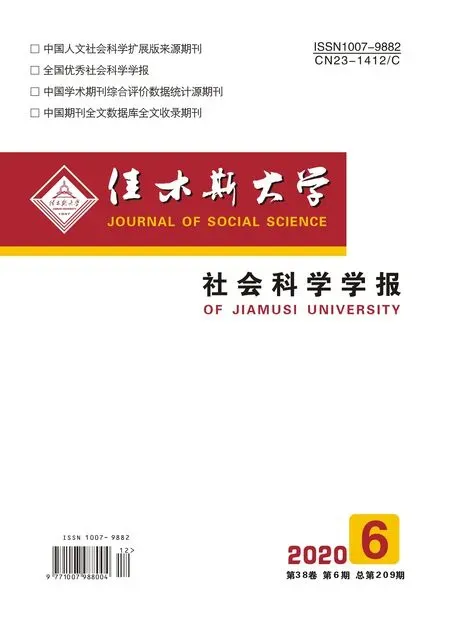自由的荒诞人*
——解析贝恩哈德作品中的主人公模板“有灵之人”
续 文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1)
一、贝恩哈德及其作品
奥地利作家托马斯·贝恩哈德(Thomas Bernhard,1931—1989)是20世纪德语文坛上一位特立独行且备受争议的人物,大众对他的接受呈现出极端的分化:他拥有大批的崇拜者、模仿者和敌人。到今天,时间作为检验作家作品优劣、去粕存精的效力也许尚未能完全发挥,但对贝恩哈德盖棺定论的客观条件业已具备。正如有研究者早在贝恩哈德逝世10周年纪念会后不久所说,无论为了文艺批评的写作、为了出版社的利益,还是为了同时代人的记忆、最主要的是为了文学研究,进一步加强对这位作家的纪念、研究和评价的理由已经足够多了。
贝恩哈德作品的情节极度简化,情节不过是为了承载其大量爆炸性思想的框架。此外,无论情节安排、环境设置、人物刻画还是语言风格,都具有极大的重复性,这使得系统地研究他在这些方面的创作特征成为可能。
他的自传体五部曲中现实与想象并行,讲述了作家贯穿整个二战时期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年幼的他是传统眼光中的“问题儿童”,多次搬家让他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无所适从;他被送入管教中心,后又在寄宿学校里受到纳粹主义和天主教传统的双重折磨,亲身经历战争的严酷;16岁的主人公在某一天上学路上临时决定逃离至今在他眼中无意义的可恨生活,走上相反的方向:在一家食品店里当商业学徒,在地下室里他与同样被社会排挤的人相识相处,加入他们混乱、迷失却又全新、自由的生活;然而严重的肺病再次把他推入深渊,亲人也相继去世,接二连三的打击促使他在医院这座“死亡之屋”里回忆、观察和思考,战胜绝望,获得新生,从此正式投身文学。
70年代是新主体主义(Neue Subjektivit t)盛行德语文坛的时期,作家通过对个人经历和感受的叙述折射社会的症结。自传中的“我”的遭遇是与他同时代的同类人的共同命运。通过多个文本的横向比较可以看出,贝恩哈德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把“我”及其同类人的某些部分加工、放大,塑造出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极端人物,“我”及其同类人就是其主人公模板的最初轮廓:
小说《石灰窑》(Das Kalkwerk)的主人公康拉德把自己和妻子封闭进一座废弃的石灰窑,为了撰写他钻研了几十年的关于听觉的论文,日复一日地在瘫痪的妻子身上进行过量的听力实验,但他永远把握不住写作的“最佳时机”。《维特根斯坦的侄子》(Wittgensteins Neffe)可以看作是作家在与保尔·维特根斯坦的深入交往中延续了他的自传,他观察着这位著名哲学家的侄子的愤怒、病痛、疯癫、贫穷、孤独和死亡。《水泥地》(Beton)的主人公鲁道夫深受结节病的折磨,十年来一心想为他最喜爱的音乐家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写篇论文,但总是在各种干扰下开不了头。《历代大师》(Alte Meister)则是借第一人称叙述者阿茨巴赫之口铺陈艺术评论家雷格尔关于历代大师、哲学、艺术、文学、国家、阶层等极其负面的种种想法。
这一类叙事作品与其称为小说,不如称为长篇散文,作为“故事的破坏者”的贝恩哈德无意构思精巧的情节,而是用人物铺天盖地的独白填满读者的头脑。伍尔芙在《论小说与小说家》一文中援引贝内特的话说:“优秀小说的基础就是人物塑造,此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风格是有价值的;情节是有价值的;观点的新颖独创是有价值的,但是,它们中间没有一项像塑造令人信服的人物那样有价值”[1]292-293。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贝恩哈德的作品不为叙事,只为塑人,并通过此人的眼与心审视世界。他笔下的主导人物有个共同的名称:“有灵之人”(Geistesmensch),德语中“Geist”一词内涵深广:既指精神、心灵,又指思想、智慧、英才;或说想象、相对于现实,或说灵魂、相对于实体;甚至含有着魔、精神错乱之义。他们身上集中且夸张地凸显了现代有思想之人所处的生存窘境。
二、存在与精神的重负
物质与精神、生存与理想的冲突是文学中的常见主题,在思想深邃的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激烈。贝恩哈德笔下的“有灵之人”就是这样一类在矛盾的漩涡中挣扎下陷的悲剧人物,他们的身份大多是艺术家或学者,暂时还能维持一种体面的生活:雷格尔每天去国宾饭店,康拉德长期让饭店送餐,鲁道夫四处旅行,保尔慷慨救助穷人。但这不过是最后的光鲜,作家不经意地、却也不会忘记在每一篇中点明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变卖祖产或亲朋的救济。金钱的匮乏直接威胁到人物的生存,是导致他们走向毁灭的外在因素。然而即便如此,在他们眼中,物质和精神必须是对立的。康拉德迫不及待地低价卖掉石灰窑中的家具,毁掉原有的装饰,似乎有形的物质是阻碍他研究的最大敌人;保尔最终把钱财抛光,财源枯竭,但他认为自己的思想财富是取之不尽的;鲁道夫与他那位不放过一丝做生意的机会的姐姐格格不入。
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2]16;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是现代人对世界产生疏离感,并进一步发展成荒诞感受的主要根源之一。早在17世纪,笛卡尔就认为,精神和物质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精神的本质在于思想,物质的本质在于广袤;物质不能思想,精神没有广袤;二者彼此完全独立,不能由一个决定或派生另一个。这种二元论的哲学观点将物质和精神绝对对立起来。到了现代社会,“广袤”表现在物质利益将一切价值和人际关系普遍客观化,金钱锻造出平均化、量化的价值取向,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2],人的异化日趋严重。
贝恩哈德毫不回避这种对立,并将之具现化:代表精神价值的“有灵之人”的身边总有那么一两个人物,将物质世界的价值观和物质与精神的不兼容、以及前者对后者各种形式的迫害表现出来。鲁道夫的身边,是姐姐为了积累金钱,不停干扰并最终毁掉他的写作,还企图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贬低和改变他;于保尔,那是利用孩子的可怜相赚钱的贪婪母亲,精神和良知被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目标的卑鄙行为欺骗;于雷格尔,那是展厅服务员伊尔西格勒,雷格尔对他的改造失败,暗示着物质最终不能被精神同一。
然而,尽管贝恩哈德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现代社会中物质的消极作用,并将“有灵之人”置于物质的对面,但是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摆脱物质的控制,尽管他们一心追求形而上的精神,一度将之奉为能让自己遗世而独立的避难所,却始终无法彻底进入精神世界,最后仍会回到世俗中来。一来,“有灵之人”虽然鄙视金钱,却都是一些(尚且)有钱之人,他们的生活标准也不仅仅满足于维持温饱,而是要达到一定的舒适程度。二来,“有灵之人”和与他们异类的人也并非不可和解。少年贝恩哈德放弃继续受纳粹主义和天主教传统的荼毒教育,走向能让他变得“有用”的食品店地下室;雷格尔与其妻在精神世界里有重大分歧,可是当妻子去世后,他认识到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艺术“最终在生存的关键时刻不再有任何意义”,“艺术总的来说也不过是活命艺术而非其他”[3]186,妻子才是他与这个荒诞尘世的唯一联系,而非艺术,将艺术称为活命艺术就将它拉下了神坛,贬低为和物质相差无几的生存手段。
“有灵之人”观察、解析、批判一切,这一切包括自己,观察变成自我观察,解析变成自我解析,批判变成自我批判。他越是鄙视世界,也就越是否定自己。物质生存已让他不堪重负,人类的精神产品带给他的也只有幻灭。因此贝恩哈德的作品并不仅仅表现了物质和精神的对立,而且进一步否定了两者,两者都是造成现代人荒诞处世感受的根源。然而同时也要看到,“有灵之人”并非全然消极地被重负压倒,少年贝恩哈德的决定和鲁道夫终于走出书斋去寻找旅途中邂逅的苦命女人,都是在将目光转向生活,寻求在尘世中生存下去的方式。
三、一切疾病都是心理疾病
疾病是贝恩哈德式荒诞的一个重要符号。“有灵之人”几乎都病魔缠身,或者将疾病安放在身边的人身上,以映射的方式表现出来。这自然与作家少年时的患病经历和在病程中的思想飞跃有关。他在很多作品中不吝笔墨描写疾病的症状、用药等信息,并明里暗里地将疾病与死亡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人类共同的遭遇、集体的命运。疾病只是死亡的缓刑期,“当人们想到死亡,一切都变得可笑”[4]3,一切行为都变得无意义和荒诞。
“有灵之人”或其身边人的疾病各式各样,有生理上的,如肺痨、瘫痪、结节病,也有精神疾病。但贝恩哈德在《寒冷》卷首援引德国浪漫文学作家诺瓦利斯的名言“每一种疾病都可被称为心理疾病”[5]312似乎将这些疾病都隐喻化了。少年贝恩哈德所患的结核性胸膜炎首先承担起隐喻的任务,结核病在19世纪所激发出来的幻象,源自它在当时的医学水平下无法被探知的神秘。结核病的许多症状都是假象:例如潮红的面色看起来是活力和健康的标志,其实来自发烧[6]24-25。这就将健康和疾病相对化了,患者似乎总在发病,不曾健康,人的一生都在以生病的方式奔向死亡。结核病是一种消耗病,患者身体内部在燃烧,逐渐消瘦,“大概存在着某种热情似火的情感,它引发了结核病的发作,又在结核病的发作中发泄自己。但这些激情必定是受挫的激情,这些希望必定是被毁的希望”[6]34。在“有灵之人”身上,这种受挫的激情化为潮水般的愤怒,他们肆无忌惮地抨击一切:国家、社会、人、文化、艺术、信仰,最终自己也被这激情吞噬。结核病的发病部位在肺部,容易激发人们关于呼吸和活力的想象;在身体的上半部,也是与头脑联系更紧密的地方。因此从隐喻的角度看,肺结核在文学中常被视为一种灵魂病,无论从发病原因还是症状上,都与精神疾病有许多共通之处。由于跟一切对着干,最终如他人所说的丧失了自我控制的能力,“我”(少年贝恩哈德)成了肺病患者,而保尔成了精神病人,“我”至少是和保尔一样疯癫[7]226。
除了隐喻精神倾向的生理疾病外,“有灵之人”或多或少地具有精神病人的情感特征,外在表现为双向障碍,躁狂和抑郁交替发作。在躁狂发作的时候,他们行动果断,思维奔逸,滔滔不绝,注意力不能持久集中,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而转移,甚至像康拉德那样出现幻听,或像鲁道夫那样突然行动力惊人,做出一些奇怪举动。在抑郁发作的时候,他们深刻地体验到孤独、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并不可避免地生出自杀的念头。
孤独是心灵的孤独,来源于他们的敏感,贝恩哈德在多部作品中异常详细地描写了他们与周围人的格格不入。除去这些表层原因,现代孤独的根源仍要归结到宇宙法则的不存在。人失去对神的信仰和可依循的规律,不知从何处来,不知向何处去,莫名其妙地被抛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上,体验到荒诞的在世孤独。
恐惧和焦虑是“有灵之人”的心理常态,萨特认为,恐惧和焦虑是有区别的,“恐惧是对世界上的存在的恐惧,而焦虑是在‘我’面前的焦虑”[8]60。“有灵之人”对来自自然、社会和他人的一切感到恐惧,决定自己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过程中则伴随着焦虑,自由是造成焦虑的根本原因,因为焦虑是面对多种可能性的反思情绪,因为不知这些可能性的未来而焦虑。所以焦虑是他们直面自由的态度,同时他们也看到了身边的人却大多采取了麻木不仁的自欺,放弃决定自己生活的自由权力,而把社会规定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于是安于小市民生活的现状,蒙蔽在由谎言构成的社会关系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待自由的态度,是正视还是回避,也是“有灵之人”和普通人的基本分歧。
在抑郁发作的时候,“有灵之人”经常会想到死亡。读寄宿学校时期的贝恩哈德在鞋屋里练琴时,总是想到自杀,在拉琴的同时完全地沉浸到自杀的想法中去[5]14,然而,尽管他尝试了多次,自杀总是会以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失败,他活了下来,并且在后来遭受严重疾病的折磨时还是坚持活了下来。在贝恩哈德的作品中,死亡和生命是辨证的一对,“‘死亡是我的主题,因为生存是我的主题’,作家以此宣告把对死亡的感知等同于对生命和存在的感知”[9]10。除了真正实施的自杀外,死亡还常以隐喻的方式出现,比如康拉德在梦中的自杀和在现实里的苟活。这说明他不是像海德格尔定义的人的存在是走向死的存在,不是“死而是自由的”,也没有像德国浪漫派的艺术家那样诗化死亡,而更多的是个“自由的必死之人”, 在死亡荒谬地到来之前采取了自由的行动。
在世俗人眼中,“有灵之人”是疯癫的,因此保尔被送进精神病院,“一再被精神病医生毁灭,然后又靠自己的能量重新站起来”[7]226,作为世俗之人的精神病医生总是采取南辕北辙的手段让病人的境况雪上加霜。事实上,“有灵之人”的疯狂源于世界的疯狂,在一切皆徒劳、人对世界无能为力的悲伤体验下,他们唯有幻想以凌驾尘世的精神性来超越荒诞,精神病的症状是他们勉强存于世间的方式,是无法医治的,不可理解的世界只有通过同样不可理喻的极端行为才变得可以忍受。
在东西方的神话中,都有神因为对人类恶行的不满而降下疾病作为惩罚的故事,统治者失道,则瘟疫横行,疾病被赋予道德上的意义。在现代医学史上,心理疾病的范畴不断扩大,心理的疾病只能控制而无法治愈,人们一贯相信的科技的力量对此无能为力。贝恩哈德将疾病普遍和抽象化:“我的故乡事实上是一个不治之症,居民在疾病中诞生,并被卷入其中,如果不能在关键的时刻逃离,就会直接或间接、或早或晚地……突然自杀或……走向毁灭”[5]11-12,这里明确指出,故乡萨尔茨堡乃至整个奥地利所患的这种病因不明的不治之症具有道德上的传染性和毁灭的力量,所谓的逃离也不过是一种幻想,每个人和整个世间都陷入了不治之症,荒诞始终存在,战胜荒诞的方式只有直视它,就如贝恩哈德和保尔所做的那样:保尔几十年来扮演着疯子的角色,从疯癫中求生;除了疯癫还有肺病的贝恩哈德则“以相同的程度利用了两者”,把它们变成自己“生存的源泉”[7]227。
保尔和贝恩哈德带着各自的疾病度日,不回避疾病,而是寻求与它的共生,试图利用它,化弊为利,是“有灵之人”积极对抗荒诞的示范性行动。因此贝恩哈德描写疾病,并非像表面所示的那样是完全消极、阴暗无望的,作者正是用令人感到恐怖的方式来让人置之死地而后生,隐藏着积极的导向,导向对生活的激情的、执拗的肯定。
四、永不可及的“统一纯粹”
“有灵之人” 最大的自由行动和自由反抗,在贝恩哈德笔下常常表现为某种学术研究,具体化为他的论文写作——一种对“统一纯粹”的“精神产物”(Geistesprodukt)的不懈追求。鲁道夫写门德尔松,康拉德写《听觉》,创作论文的意图成为整篇无情节线索的散文的红线。萨特在《局外人的诠释》中曾说“最初的荒诞首先显示一种脱节现象:人对统一性的渴望与精神和自然不可克服的两元性相脱节;人对永生的憧憬与他的生命的有限性相脱节;人的本质是‘关注’,但他的努力全属徒劳,这又是脱节”[10]57。 也就是说,对统一、纯粹、正确、完美的东西的追求总会因为必然的(如死亡)或偶然的(如具体困难)的因素而遭到失败,真理难以证明,现实无法理解,这些构成了荒诞的极端。在《石灰窑》和《水泥地》中,论文就代表了一种纯粹完整的精神性,对它的追求是主人公荒诞人生的决定性特征,而写作的失败就象征了这条裂痕永难逾越。
以《石灰窑》为例,康拉德选择听觉为论文主题并非偶然,他认为“没有什么比一个完美的或至少是接近完美的听觉能造成更大的清楚了然”[11]26,而且“毫无疑问,听觉比头脑重要”[11]64。他的研究动机说明了“听觉”的实质:它是一个非理性非逻辑又超越理性的存在(比头脑重要),能够完美清楚地解释自然和世界的本质;如果说按萨特的看法真理还有着难以证明的多元, 那么这隐喻性的“听觉”就应该是真理的真理。倘若它可以得到,它就会象过去的宗教、理性一样,将人和世界重新联结在一起,抹杀荒诞的根源。但是,宏观上人类的科学发展、社会体制等都远未做好洞穿“统一纯粹”的准备,微观上形为避世、实为在世的康拉德仅凭一己之力的抽象追求无异蚍蜉撼树。透过表象,所有的主观原因又可统归为“有灵之人”超越(于物质)到极端变成偏执(于虚无)、敏锐到极端变成自扰的精神性特点,也即是他的荒诞人格特征的决定性方面。
除了前述荒诞的论文主题本身具有的摧毁性外,这里再度凸显了精神存在(论文)的无限和个人行为的有限之间的矛盾。这里不妨借助跨文本的方法来对比说明:尽管贝恩哈德很多作品里的主人公都在写作科学论文上失败,但也有极少成功的例外,如小说《便帽》(Die Mütze)里的主人公也为了论文将自己孤立起来,失去自控陷入半疯,在街上他捡到一顶所有居民都会戴的便帽,寻找失主未果后将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忽然间就摆脱了罹病的头脑的控制,而是被这顶粗糙、肮脏、厚重的灰色便帽操纵,回家后重新有了正常的身体感觉,虽然结局未明说,但读者有理由相信他的论文已在进行中:“所有人的头上都有着这样一顶帽子,我想,所有人,我写着写着写着……”[12]34。帽子消除了他对头脑和精神的病态执着,从而重新唤醒了写作能力。这里的便帽是成百上千顶日常帽子中的一个,是身份认证的标志,象征着淹没在大众中的平凡正常,写作即意味着看到平常而有限的世界[13]71,逐步辨证地具现化头脑中无边的思想:“一切应该都可以用唯一的一句话来述说,就像一切已经用唯一的一句话说出那样,但是没有人能够仅用一句话说出一切”[12]26,主人公也一再强调了他写作的不足,每篇论文都只是一个对真理的接近,无法一下子掌握它的全部。对比起来,康拉德一方面不能融入社会,他不接受社会,反过来社会也不接受他;另一方面认为前人关于听觉的论文基本都一钱不值,正是因为看到了它们的局限性却不肯认同这是客观的、必要的过程。他想要以一个全能的自然科学家兼艺术家、预言家的复合身份写出可以成为听觉领域的研究终点的论文;他着眼于全宇宙,想将万物联系起来,就像事物之间本来就存在的普遍联系那样。他的出发点正是他绝望的根源。
对贝恩哈德笔下的学者来说,承认研究的有限即意味着对自己思想的背叛,写作只能作为对写作的限制和否定来获得被外界认可的成功。这里体现了文学中表现荒诞的一个有力的艺术手段——悖谬,它是一个自相矛盾、不合常理的逻辑公式,作为艺术特色,指作家在正反两面之间寻找的交汇点[14]37。康拉德清楚认识到了他所要研究的对象是无限、非理性的,但写作却是要将它有限和抽象化。精神工作因而只能存在于脑中而无分毫实际行动,又因为精神活动从不止息,对论文创作的追求就质变为对它的幻灭的追求[15]43。因为他越是不停实验,就越发现既得成果的不完善;越是貌似接近真理一步,就越领悟到绝对真理的不可到达。
五、结语
荒诞是现代人对人生、对世界的心理感受的综合,它是普遍存在的。在贝恩哈德的作品中,荒诞具体化为生活意义的虚无、和谐关系的丧失、人的异化等子题,这一切全都通过作家全集的人物模板“有灵之人”的眼睛来观察、分析和批判。他们是一群思想深邃、精神超越的艺术家或学者,本身是异于常人的“荒诞人”,却也同时受到来自荒诞尘世的各种重压。尽管现有的研究大多将贝恩哈德笔下的“有灵之人”描述为“在彷惶寂寞中忧伤,在无能为力中精神错乱,在绝望中走向毁灭”[16]121的精神狂人,尽管他们往往被动地遭到环境的压制和破坏,尽管他们由于自身不足、方法错误等原因最终迎来失败,本文仍认为这抑郁疯狂的背后还是隐藏着对真正自由、绝对真理的积极追求。从反抗荒诞的意义上说,与普通人面对荒诞尘世的消极接受,或用物质存在自欺、顺应习惯的力量、逐步异化的反应相比,“有灵之人”能做出像写作论文这样的各种尝试,虽然最终失败,仍是值得肯定的悲剧英雄。
另一方面,作家在创建“有灵之人”的模板时,本身即采用了表现荒诞的有力手段:悖谬。他们作为精神的代表鄙视物质,却仍然受到物质的框囿;作为“精神病人”忍受癫狂的世界,并与其他“病人”相互折磨;努力追求统一纯粹的精神性却与之越行越远。“有灵之人”在批判周遭一切的同时也批判自身,对世界的观照反射为自我观照,因此“有灵之人”本身也构成荒诞的一部分,是被置于舞台上的角色。贝恩哈德将一切荒诞化、间离化,读者或许不必对他笔下的任何人物产生好感或同情,而是通过冷静的观察和反思做出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