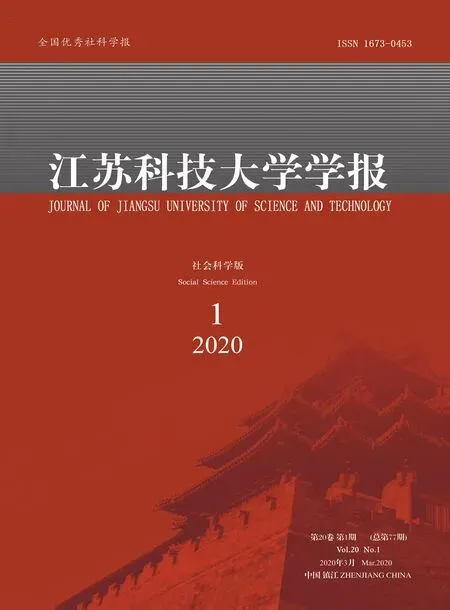启蒙运动中希伯来语与文言文的不同命运、原因及反思
李俊宇
(宁德师范学院 语言与文化学院, 福建 宁德 352100)
1925年,茅盾(沈雁冰)在《新犹太文学概观》一文中说:“不啻宣告那在实际上已是死的文字的希伯来文字已经不宜为犹太著作家发表思想宣泄情感之用了。”[1]2同样,也是在这个时期(1927年),王鲁彦(鲁彦)在《犹太小说集》的序言中说:“在19世纪初叶和那时以前希伯来并非没有文学,但那时的作家用的是希伯来文字,一种过去的,渐为他们本国人所不认识的将死的文字。”[2]与之呼应的是,“胡适期望中国文坛也能放弃使用三千年前的死字,使用20世纪的活字”[3]292。胡适在1928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中考察了汉朝的白话文发展状况后说:“这可见古文在那个时候已成了一种死文字了。”[4]9他在1929年出版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分析了曾国藩引领的古文中兴之后也说:“这一度的古文中兴,只可算是痨病将死的人的‘回光返照’,仍救不了古文的衰亡。”[5]众所周知,希伯来语后来“复活了”,而文言文却“死了”,那么,为何曾经同为“将死的”且都属于“古字”的希伯来语和文言文呈现如此迥异的命运?
一、 启蒙运动中的希伯来语
犹太人在上千年的流散过程中使用过多种不同的语言,如希伯来语、意第绪语、德语、法语以及西班牙语等,而希伯来语被认为是他们的“民族语言”“神圣的语言”。因为犹太教的典籍在很早以前都是用希伯来语书写和传承的,正统犹太教拉比在各种宗教仪式上使用的语言也是希伯来语。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希伯来语渐渐成为一种书面语言,不再在口语中使用。因此,国内许多人士将希伯来语说成“已死的文字”,希伯来语的复兴是“复活”。这种说法本身是不准确的,其实它并没有真正地“死去”,所以也就无所谓“复活”了。正如国内学者钟志清所言,“称希伯来语已经死去,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实际上指希伯来语已经不再是一门口头用语,并且逐渐失去了以希伯来语为母语的人群”[6]。
希伯来语的复兴得益于启蒙运动和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17世纪在欧洲掀起的启蒙运动于18世纪传到犹太人社区,先是在西欧,之后遍及东欧。其中,对犹太社会贡献最大的是德国犹太思想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ohn)。他发起了犹太启蒙运动,并和他那些马斯基里姆(Maskilim)弟子们不遗余力地将启蒙思想引入犹太社会。“犹太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是圣经希伯来语,并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密德拉西希伯来语和中世纪希伯来语。”[6]在他们看来,圣经希伯来语是犹太民族纯粹、神圣、正宗的语言。在欧洲乃至其他地区,启蒙运动又导致了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兴起。现代民族主义就是世俗民族主义,“它强调土地、血缘和语言对于一个民族团体的重要性”[7]342。在现代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之下,犹太民族主义意识再次复苏,并继而发展成为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而希伯来语能够得以复兴的关键就是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启蒙运动的重点在于普遍的启蒙和宣扬泛泛的自由主义,可是它却发动了一场希伯来特有的复兴运动。”[8]260
可是,随着启蒙运动扩散到东欧,意第绪语在东欧犹太群众中成为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语言。如此一来,希伯来语的地位受到极大挑战。正如王鲁彦所言,希伯来文字成了东欧犹太人“渐不认识的将死的文字”。在19世纪后半叶,当希伯来语受到意第绪语等其他语言的强烈冲击时,它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犹太著名小说家什·约·阿布拉莫维奇(S. J. Abramovitz)和诗人戈登(J. L. Gorden)在用意第绪语创作时并没有放弃使用希伯来语创作,而且他们对希伯来语进行了革新,以此推动了希伯来语的现代化,“阿布拉莫维奇率先将一种新型的希伯来语引进近代希伯来文学。该外来语由《塔木德》的词汇和从意第绪语词汇译出的希伯来语句子组成,能够与犹太大众所说的简单语言揉合在一起。这种形式也能使故事中的人物活起来,并使得人物和对话都烙上现代的印记”[9]40,而且“阿布拉莫维奇还曾埋头写作希伯来语的《自然科学史》”[9]40,这本书丰富了新型的希伯来语。阿布拉莫维奇是新犹太文学的领军人物,对后来的作家们产生了深刻影响。诗人戈登则将希伯来语与意第绪语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颖的希伯来语言风格,他尤其注意用《塔木德》及其诠释的词汇。可以说,戈登在文学创作中的语言使用上充分利用、发掘了犹太经典和犹太传统文化。在阿布拉莫维奇和戈登等文学家的不懈努力下,“希伯来文学不再是一种传播启蒙或是向那些只能用希伯来语阅读的一部分以色列人民灌输民族主义思想的权宜之计,它已成为包罗万象而富有活力的民间文学”[9]100。也就是说,希伯来语和希伯来文学主动走下“神坛”,进入普通犹太人的生活,新希伯来语和新希伯来文学也就随之出现。
另外,力图保住希伯来语的犹太文化人士对语言持一种兼容并包的开放心态,“犹太文学批评家雅考夫·拉宾诺维兹(Jacob Rabinowitz)1922年在《回声》杂志中写道:惧怕不规则、粗俗的语言是荒谬的”[10]。而最终促使希伯来语走向普罗大众的是本·耶胡达(Ben Yehuda),“1882年,本·耶胡达致力于使希伯来语重新成为一种活的语言。到当时为止,希伯来语的复活仅限于书面语。本·耶胡达通过他进行的词汇学研究,以及通过创造了数以百计的新词,为希伯来语的复兴做出了很大贡献,从而为人们树立了一个榜样,有力地促进了希伯来语的复活和民族振兴”[7]360。本·耶胡达除不遗余力地创造新词、编纂希伯来语词典外,还带头在日常生活中用希伯来语进行交流,并要求自己的家人也说希伯来语。在本·耶胡达等人的努力下,“自20世纪第一个10年以来,希伯来口语不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散居各国的许多犹太人中间开始传播开来”[9]75。威廉姆·萨福仁(William Safran)在回顾这段普及希伯来语的历程时指出,像耶胡达那样的犹太文化精英在复兴希伯来语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巴勒斯坦真正有效地传播希伯来语的是那些工人、初级学校的教师和年青人”[11]。确实如此,希伯来语能够传播开来主要靠的还是广大群众。
总之,希伯来语的及时“现代化”以及在口语中的使用是其不至消亡的重要原因,“如果希伯来语只是一门书面语,就无法长期存在下去”[6]。而在这个复活的过程中,希伯来语作家的努力功不可没。因此,吊诡的是,启蒙运动不仅没有加速希伯来语的消亡,反而激活了这种古老的语言。
二、 启蒙运动中的文言文
20世纪初,中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使用白话文、摒弃文言文。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启蒙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被引进,在民族处于由封闭走向开放之际,白话文的崛起是民族启蒙运动的需要,白话文的应用功能和启蒙功能是旧文言所无法比肩的,它大大有利于现代科学知识和思想的传播。“文言崇尚意境而白话擅长说理。”[12]而擅长说理这点恰恰是现代科学所急需的,因为现代科学中演绎思维的表达追求清晰、明了,而表达模糊、曲折的旧文言则显得不合时宜。如果用旧文言撰写现代科学书籍尤其是教材,会导致普通读者和学生在理解上相当困难、费力,就是撰写者本人也很难做到言辞达意。众所周知,在很多时候,表达之难并非因为思路不清晰、道理不明白,而往往是因为缺乏相对应的语汇。旧文言对于现代科学的普及、传播是极为不利的,而当时中华民族急需的正是科技的进步、国家的强大,所以采用白话文、废除文言文是历史的选择,而陈独秀、胡适等人只不过是顺应历史潮流罢了。因此,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对待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态度并非是由他们个人的好恶决定的,而主要是由历史趋势与时代需求所决定的。
在文言文面临衰亡之际,文言文维护者也努力改良这种语言,以达到挽救文言文不至消亡之目的。林纾大量翻译西方文学的目的并非在于推动新文化运动,而是要复兴文言文,以达到挽救古文之目的。因此,他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所采用的语言是古文而非白话文,但他所使用的语言是经过改良的文言。“事实上,文言守护者在改良文学上认为,应该以现有文言书面语为基础,吸取白话文和其他营养,来逐渐改造汉语书面语。”[12]可见,这些文言守护者是站在以文言为本的基础上进行语言改革的。“严复、林纾等人开始在翻译时加工、改造传统文言,大量新名词的创作、白话的引入、灵活语法的应用,使文言向着越来越简洁、平易的道路上迈进。”[12]可以设想,如果沿着这条轨道前行,文言文的地位也许能够保住。但是,这种“改良”的速度太慢,历史等不及,而且文言文一直停留在书面语的层次,并没有在口语中大量使用。语言的生命力更多体现在口语而不是书面语中。在历史长河中,许多语言尽管没有被书面记录,却口口相传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这就是明证。在20世纪初的启蒙运动时期,反对使用白话文的声音也是十分强劲的,提倡白话文与维护文言文形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作为在客观上起到推动新文化运动作用的翻译家林纾就极力反对使用这种语言。他说,新派文人“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3]292。
三、 两种“语言战”与两种不同的命运
20世纪初,在希伯来语和意第绪之间爆发了一场“语言战”。它是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m)与流散主义者(Diasporism)之间的文化和政治冲突,实质上“就是由那些政客们、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和者、学会组织者、理论家们以及文化掮客们挑起的斗争”[13]。而那些东欧的犹太作家们并没有真正站在哪一边。他们在创作和翻译中常常轮番使用这两种语言,因此并不参与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之间的战争。导致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发生在欧洲的启蒙运动所引起的民族主义。语言对于一个民族统一体是十分重要的,“在民族统一体的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过问的就是语言”[14]。语言更是民族主义意识中的重要部分,在流散时期,犹太民族可以使用多种语言,而“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没有双语的地位”[13]。也就是说,在一个民族内部只能使用一种官方语言,尽管以色列建国后规定使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但犹太民族内部使用的只有希伯来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提倡复兴希伯来语的犹太作家、语言学家、政治家都支持启蒙运动,“希伯来语作家不仅表示出对启蒙运动的支持,对犹太生活世俗化过程的支持,而且千万百计为新思想辩护,反对僵化、刻板的传统思想,表现出一定的激进主义”[15]。犹太启蒙运动并未排斥希伯来语,在启蒙运动中,希伯来语著作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希伯来语的保存与复活又促进了现代犹太民族主义的发展。在东欧的启蒙运动中,与启蒙运动派相对立的是哈西德派,而哈西德派信徒们广泛使用的语言是意第绪语,但这两派在语言使用上并没有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在启蒙运动中和启蒙运动后,近代犹太社会在对待犹太教与犹太传统问题上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派别,如正统派、保守派、改革派。这些派别各自在激进与保守上又细分成若干支派,所以没有真正形成完全的“保守”与“激进”两派一直对峙的局面。这种多元性是由犹太民族的流动性和散居性所决定的。在流动中,各种力量之间此消彼长、变动不居。
相较而言,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却态度鲜明地排斥文言文。新文化运动伊始,许多支持文言文的文化人士也是支持启蒙运动的,如严复、林纾等,但后来却与支持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派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僵化态势,结果导致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结局。其实,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所谓的“革新派”还是“守旧派”,都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意识,都是站在民族振兴、维护民族利益立场上的。但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他们对启蒙运动的态度却迥然有别。历史潮流需要的是启蒙运动,而不是因循守旧甚至退回到蒙昧状态。历史证明,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又出现了一股复古思潮。这充分说明了复古派对时代和历史的要求缺乏清醒认识,从反面证明了新文化运动的正确性。
就语言环境而言,犹太民族在启蒙运动时期所处环境远比中华民族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处环境复杂得多。在犹太启蒙时期,由于散居原因,犹太人使用多种语言,文化呈现多元化态势。而中华民族由于上千年的封建集权统治,文化相对而言比较单一。启蒙时期,在犹太人使用的主要语言中,真正能够与希伯来语“抗衡”的也就是意第绪语,而在许多犹太民族人士看来,意第绪语也是传承犹太传统的重要语言。因此,“他们中间有同时操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的犹太人,这两种语言都是犹太传统可贵的捍卫者”[16]。他们认为,使用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才是“语言同化”。从客观上讲,尽管意第绪语也是传承犹太传统的重要语言,但意第绪语并不适合作为犹太人的民族语言。
意第绪语是犹太民族散居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在散居中被半同化的结果,尽管它很大程度上是在自然交流基础上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常被当做一种杂交语言”[11],比较适合普通犹太群众,但如果将它作为犹太民族统一的官方语言显然不合适。因为希伯来语与以色列政治文化中心耶路撒冷紧密相依,如果采用意第绪语,则会出现“言虽顺”但“名不正”的尴尬局面。所以,复兴希伯来语是复兴犹太民族的重要部分,它被蒙上了强烈的民族、政治色彩。正如萨丕尔(Edward Sapir)所言,“特定的语言往往最适合地表达了某种自我意识中的民族/国籍”[17]。对于经历了上千年流浪生涯的犹太人来说,他们需要用一种语言来表达一种有根的、相对稳固且有传承性的民族意识,所以希伯来语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意第绪语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走向衰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发生在欧洲的犹太大屠杀,大约400万使用意第绪语的犹太人被杀害,进而导致意第绪语的社会根基基本被拔除。迁移到美国的犹太人由于受同化的影响,他们中许多人放弃了意第绪语而改学了英语。另外,在以色列,官方对意第绪语加以排斥。以上种种原因,导致说意第绪语的人越来越少。
不难发现,语言的产生、发展、演变、消亡并非如同生物进化演变那样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它往往受到民族、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正如萨丕尔所言,“这些重新恢复或半制造出来的语言,许多是伴随着政治文化敌意的抵抗而来的,如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希伯来语”[17]26。人为的干预往往会影响甚至决定语言的走向。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努力和以色列官方的干预,希伯来语的复活是不可能的。同样,中国白话文地位的确立是以胡适、茅盾、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派努力的结果,而且最终得到了官方的认可。1920年1月,北京政府正式颁布法令,将全国国民学校的国文改为语体文(即白话文),随后将“语体文”一词改为“国语”,正式确立了白话文的地位。
语言确实无所谓优劣、高低级之分,但语言确实有新旧之分。语言有不同变体,不同变体对应于不同时代,如英语有古英语和现代英语。可以说,语言是有时代性的,一种语言对应于某个时代。语言本身不是静止不变的,而且它的变化要跟得上时代的变化。固守旧语言而不作任何改变,将其封闭起来,只会导致它的消亡。文言与白话的论争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持续了多年,且隔一段时期又重新出现。其实,孰优孰劣的论争意义不大,关键是要让语言适应时代要求。文学语言与科技语言又有很大不同,适合于文学表达的语言不一定就适合于科学表达,文言文就是这样。在“赛先生”(science)进入中国并成为不可扭转的潮流时,固守旧的文言文肯定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语言的变化并不是自足的,不可能顺其自我演变而将人为作用排除在外。语言也是一种文化遗产,必须在它们原有基础上对其予以创新,吸纳整合是创新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方式。开放不是放弃自身的根本,更不是“同化”“西化”或“欧化”。对语言的改变,要在时代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加快步伐,时代的变化往往就是文化的变化,“文化的超常变化必然伴随着相应加快的语言变化速度”[17]61。
四、 反思
(一) 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犹太民族,因为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都积淀了丰富而厚重的传统文化,所以在启蒙变革时期,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对中犹两个古老民族都极其重要,“传统与现代化是许多古老民族难于解决的问题,犹太人也为此常常陷于困惑之中”[18]。但犹太人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还是比较成功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犹太人对待传统与现代的成功做法,对于我国的文化建设具有较大的意义。
首先,应借鉴犹太人善于及时反思、总结的特点。对于犹太启蒙运动的得与失,后来的犹太文化人士进行了比较深刻而全面的反思。在启蒙运动时期,绝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在欧洲,要在文化上避免“欧化”,对这个古老民族而言是一个大难题。在启蒙运动早期,“语言同化”现象出现并成为核心问题,许多犹太人选择了散居之地的语言。“语言同化” 本质上是一种民族同化思潮。被称为“德国的苏格拉底”的犹太启蒙运动领导者摩西·门德尔松是第一位用德语发表著述的犹太人。犹太文化的核心在于犹太教,而传统犹太教的存在是与希伯来语生死相依的。在犹太启蒙时期,一些新犹太文学作家如扎·什尼奥尔(Za Schnauer)大肆攻击希伯来语和犹太教,主张完全“欧化”。“德国的犹太改革家已向西方屈膝投降。他们害怕德国人说他们不忠,就从祈祷书中删掉了‘锡安’二字,废除了祈祷用的希伯来语,彻底清除了犹太礼仪和庆典中带有民族色彩的一切遗迹并且禁止犹太人纪念犹太民族的伟大人物。”[8]261这种做法显然带来了消极后果。
对此,克劳斯纳(Joseph Klausner)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这些作家本人及受他们影响的青年人根本不理解犹太教具有的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价值,也不理解恰恰是以色列人民过去的特殊生活规定了他们将来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个参与了数千年来人类所进行的一切伟大运动的民族,犹太人民在上帝的庇佑下一直与人类的总体文化之发展相分离,但它作为一个民族却始终前进在一条独特的道路上,并奉献给了人类以重要的文化价值,它应当把自己的民族文化与整个欧洲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19世纪)70—80年代的大多数犹太作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没有创造出另一种积极的犹太价值并把它补充到人类的积极的总体价值中去,这种犹太价值应该使犹太人民为本民族利益而汲取欧洲文化。”[9]62在这里,克劳斯纳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批评了东欧那些激进的犹太启蒙运动作家抛弃犹太教、一味追求欧化的态度,并指出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应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何吸纳其他文化并创造出自己新的文化。克劳斯纳的立场非常鲜明,现代化并不等于“欧化”,坚持犹太民族立场也并不等于排斥欧洲文化。他继而针对那些完全否定、放弃本民族文化的现象发出感叹,“我们难道是生活在一个本末倒置的时代”[9]104。克劳斯纳的意思是,犹太民族放着自己灿烂而丰富的民族文化不用,而去一味迎合欧洲文化,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愚蠢做法。犹太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对犹太人一味欧化的反拨。犹太历史学家阿巴·埃班(Abba Eban)在《犹太史》中也指出,“犹太人忘记了自己独特的历史,也就是放弃了唯一和独立的前途”[8]261。19世纪欧洲发生了系列反犹事件,令犹太人从美好的同化幻想中猛然醒悟,“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对犹太人濒于绝境的状况第一次做出了清醒的估计,并第一次为解决这一难题指明了道路”[8]262。
新文化运动启蒙时期,也出现过“欧化”思潮。“在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西学的同时,白话文建设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欧化’的影响。”[12]“新文化运动之初,一些有识之士掀起彻底否定传统文学、文化的狂潮。”[12]在当时的中国,一些学者甚至主张取消汉字,使用欧洲的拼音文字。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身份的标志。文言文和希伯来文都是一种“古字”,它们与民族传统的联系相较于白话文和意第绪语而言更加紧密,抑或说它们带有更强的民族性。这种差别是不可否认的。中国文化领域中的有识之士对“欧化”现象也进行了及时反思。梅光迪认为,“中国只经历了一代人,便从极端的保守变成了极端的激进。如今在中国的教育、政治和思想领域扮演着主角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已经完全西化,对自己的精神家园缺乏起码的理解和热爱”[19]。
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国学研究因此取得了很大成绩。无独有偶的是,在犹太启蒙运动时,犹太民族主义者也开始大力整理、诠释犹太旧经典。可见,在启蒙运动中,两个民族都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然而,当时中国的“整理国故”运动导致了复古风气出现,胡适等立即掉转矛头,反对整理国故,“整理国故”运动就此止步。胡适“整理国故”的目的是“再造文明”,也就是要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这本是十分正确的。坚持传统的基础地位,并不等于固守传统、一成不变,也不等于完全排斥外来文化。巴姆伯格(Bernard J. Bamberger)在评价犹太启蒙运动时也说,“要想把新潮流拒之门外是不可能的”[7]338。
(二) 如何对待外部思想、文化潮流
文言文之于希伯来语,白话文之于意第绪语,在时间上本就有距离,在空间上更是相隔遥远,但它们却在20世纪初的中国产生了交集。在当时的上海,不仅有犹太人居住、停留,而且还出现了意第绪语报纸刊物、电影话剧等,肖洛姆·阿莱汉姆(Sholem Aleichem)等人的文学作品也广为流传。白话文与意第绪语、文言文与希伯来语之间的相似性,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的关系,以及意第绪语与希伯来语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相似。这是茅盾、王鲁彦等大力译介意第绪语文学的重要原因。茅盾于1921年、1922年先后在他主持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他翻译的犹太作家裴莱兹(Isaac Loeb Peretz)的《禁食节》、阿莱汉姆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人》、宾斯奇(David Pinski)的《拉比阿契巴》。这三个短篇故事后来被收入短篇译文集《雪人》,解放后被收入《茅盾译文选集》。1926年,中国作家兼翻译家王鲁彦(笔名鲁彦)翻译了部分世界语版本的犹太作品,他们分别是阿莱汉姆、裴莱兹、宾斯琪、泰夷琪(J. Tajc)的共八个短篇故事,并集结成书《犹太小说集》。该书于该年12月在上海开明书店正式出版,隔年在开明书店再版。王鲁彦还在该书中撰写了一个向国人介绍东欧犹太文学的非常重要的序言。1925年(民国十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犹太文学一脔》一书,里面有茅盾撰写的《新犹太文学概观》、李汉俊翻译的《犹太文学与宾斯奇》《犹太文学与考白林》以及赤城翻译的《现代的希伯来诗》。这几篇译文的原作者分别是:日本的千叶龟雄、 L. Blumenfeld、Joseph T.Shipley,其中Shipley曾经编著过《世界文学词典》。茅盾在该文的结尾说明了为什么要将近代犹太文学称为“新犹太文学”。他说,“近代犹太文学与其说是‘犹太’文学,不如说是意第绪文学更切合,因为那些著作都是用Yiddish写的,我如今译为‘新犹太’就取这一点意思”[1]24。
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往往推动文学运动新潮流的延展。在新文化运动中,茅盾、王鲁彦、周作人等翻译、介绍了犹太文学作品。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发展。正如犹太汉学家伊爱莲(Irene Eber)所言,“中国作家从意第绪文学中发现了对他们自己目标的肯定。看一看他们选择翻译的作家及作品,能进一步证实这一点”[20]。茅盾他们达到了这个目的,但实际上茅盾等人误读了白话文之于文言文、意第绪语之于希伯来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像茅盾和周作人这两位关注意第绪文学的重要作家,也和其他人一样,误把意第绪语当做犹太人的白话。他们觉得,如同文言在中国终将逐渐被取代,意第绪语也正在取代希伯来语”[20]。意第绪语与希伯来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而白话文与文言文其实是同一种语言,都属于汉语,只是一新一旧而已。
另外,在20世纪20年代,希伯来文字和文学已经处于复兴阶段,茅盾和王鲁彦等人还将希伯来语称为“将死”或“已死”的文字。这显然不符合当时希伯来语的真实状况。“希伯来语的复兴有三个阶段:希伯来白话的复兴(1890-1918),希伯来语的标准化(1918-1948),希伯来语的词汇现代化(1948-)。”[21]显然,茅盾等人在断言希伯来语“将死”或“已死”的20年代,希伯来语已经进入复兴的第二个阶段。也许这是许多白话文运动者所没有注意到的,抑或是他们的有意误读。但这种滞后性误读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意第绪文学正在兴盛之时,而且正如上文所言,20世纪初在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之间还爆发了一场“语言战”。
实际上,茅盾等人正是通过这种误读达成了他们推进白话文运动的目的,可以说他们的努力是一种“歪打正着”。这个现象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对待外部思想、文化潮流不必亦步亦趋式地跟进,应根据国情进行取舍,做到“为我所用”。在当时有一个极有趣的反面例子。1919年梁启超带领一帮人参加了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同时顺带考察了欧洲战后的情况。其间,他与欧洲一些像亨利·伯格森(Henry Bergson)这类学者进行了交流,由此对现代科学产生了厌恶之情,继而“在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中,痛斥现代科学带来的恶果”[3]314。19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已经进入现代工业社会,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前工业社会,现代科学还处于起步阶段,正需要大力发展之时,梁启超就大泼冷水,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正如一个人还处在呀呀学语的孩童时代,大人就告诉他“人生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什么意义都没有”一样。梁启超等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大谈科学弊端的结果导致了保守顽固势力的猖獗,“使一批愤然于社会上居然革起孔孟之命来的守旧文人,大为兴奋”[3]315。梁启超等人此时的做法恰恰违背了中国的时代潮流。总之,一味地与西方同步往往是有违中国历史与国情的。
五、 结语
由上可见,希伯来语的复兴是人为的,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努力,使希伯来语在口语中推广使用,这是希伯来语能够复兴的主要原因。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中胡适、茅盾等人的努力则加剧了文言文的衰亡,文言文停留在书面语阶段也是其衰亡的重要原因。从两种语言“一升一降”的历程可以看出,语言的兴衰并非完全是自然演变的结果,人为的干预往往会改变其命运。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身份的重要标志。希伯来语与文言文分别是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古老语言的态度体现了其对待传统的态度。在启蒙运动中,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出现了“欧化”思潮,这是对传统的背弃,值得后来者深思与警惕。从文言文和希伯来语不同命运的原因中也可以发现,古老语言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传统是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起点,但坚持传统为立足点不是固守传统、一成不变,吸纳与创新是让传统充满活力的秘诀。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前后相继的关系,而外部思想、文化潮流与本土思想、文化的关系则是内外关系。从表面上看,前者是一种纵向关系,后者是一种横向关系。但这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变得错综复杂。可以看到,许多民族很多时候正是因为外部思潮的冲击才激发了传统的现代化。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完全独自前行,但对待外部文化思潮应该立足于国情,采取有取有舍的态度。在历史长河中,各个民族的发展阶段往往不一致,尤其表现在科技的发展上,而且各个民族有其自身特点,有其弱势也必有其优势。保守顽固、不思进取、不思改革,只会导致落后甚至挨打。但一味与西方“攀比”“同步”,甚至将西方所谓的“先进思潮”移植到本国更是滑稽可笑,因为西方那种所谓的“先进思潮”是与其经济基础相一致的,况且文化本身并无优劣之分,适合自身的才是最好的。从今天来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茅盾等人将东欧弱小民族“引为同道”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当时犹太这个弱小民族在处理传统与现代、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上也曾陷入困惑,也曾走了些许弯路。
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了近100年,回首“往事”仍有一定意义。茅盾在《新犹太文学概观》中断言,“已是死的文字的希伯来文字已经不宜为犹太著作家发表思想宣泄情感之用了”。这句话中的“死的希伯来文字”实际上指的是希伯来书面语。而语言与文学表达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正如奈达(Eugene A. Nida)所言,“所有的语言都会有非常优美的表达的可能性”[22]79。茅盾与王鲁彦用“死文字”“活文字”来分别指称希伯来语、文言文和意第绪语、白话文,这确有“语言进化论”的嫌疑,但是他们也的的确确看到了语言与时代的关系,即语言应该适应时代。因此,要保住“古语言”,就必须对它们进行革新。奈达说,“今天复兴了的希伯来语对于以色列人的科学思维并没有什么妨碍”[22]78。这里的希伯来语是现代希伯来语,即新希伯来语,它在词汇、语法尤其是修饰语上已经与圣经时代的希伯来语大不相同。威廉姆·萨福仁说,“今天,希伯来语词汇对科学、技术以及文学批评等方面的表达已经非常够用了”[11]。这句话反过来说明以前的希伯来语在词汇上是不适合现代科技的。胡适所说的曾国藩引领的“古文中兴仍救不了古文的衰亡”这句话显然过于武断。如果在曾国藩、严复、林纾等人大幅度、及时的革新之下,假以时日,还是完全有可能挽救其命运的。
如果说希伯来语是“死而复活”的话,那么文言文就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吗?其实没有,只不过在这个舞台上它不再是主要演员而已。在弘扬民族文化的今天,文言文因其形式上对仗的工整、抑扬顿挫的声韵以及凝练的表达,仍然具有强大的魅力。现今的人们正是通过文言文所记载的各种文化资料了解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因此,文言文并没有“死”去,相反,它在今天“一带一路”文化经济建设的大力推动下有着更为宽广而灿烂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