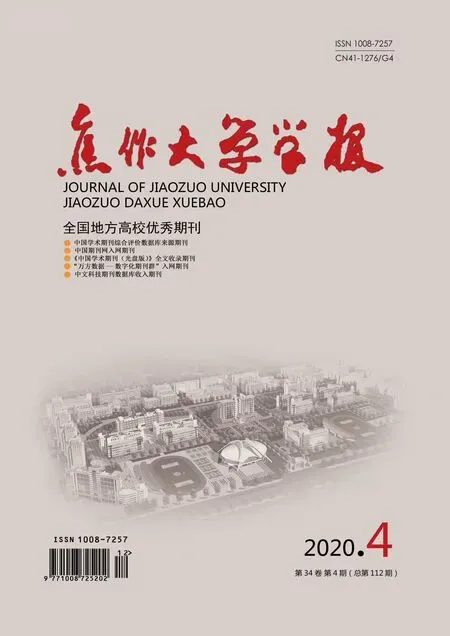理学视野下薛瑄对孟子“存心养性”的诠释
龚 瑞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存心养性”最早出现于《孟子·尽心上》,孟子提出:“存其心, 养其性, 所以事天也。”[1]在这里,他将“存心养性”视作保持赤子之心,修养善良之性,以涵养天性的修养之法。随后,明道先生继承了孟子这一思想,只不过他把“识心见性”和“存心养性”进行了区分,即一个是上学,一个是下达。其后,薛瑄吸收了孟子和二程的思想,认为存心是见天理的重要枢纽,见性是修养身心的重要法宝,最终目标是要复人的至善之性,从而对“存心养性”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
1. 存其心为天理之正性
薛瑄从理学的视角出发,主张把心安放于事物之中,用心感悟事物之中的义理,将存心释为明得义理并且无限接近义理之要;从用敬释存心,把敬作为为学、存养身心的一个条件,涵养心性之法;以存有清正的心作为见大道的基础,来说明存心的重要性,在诠释“存心”的过程中构建和完善理学体系。
1.1 心存理见
“存心”是孟子思想主张的重要范畴之一,也是其追求义理、省察自身的重要方法。他认为,学者之患在于“放其心而不知求”[1],所以他主张:“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1]即通过找回丧失的“本心”, 恢复善性, 培养善德, 使天赋的本善“良心”不被陷溺,并扩而充之,达到至善的境界,这就是学问之道,亦即“存心”。
处于理学思潮中的薛瑄继承了孟子的存心思想,他同样认为为学当以存心为本,将存心视作学者时时刻刻的切要工夫,是心趋于理的发展方向。因此,他主张为学之际应将心投入于事物之中,用心感悟事物之理,存心方可在知识层面穷究事物之理,进而在实践层面躬行实践、切己体察所得到的义理,最后明得此番义理。但这并不是将心投入于任何事情之中,在他看来,就像清澈的水中可以看见毫毛一样,存有澄澈的心方可感悟天理。如果把心存于闲事之中,便会产生烦扰,心中存养的义理反而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他指出,“存心”,即用心对待事物,就可以从事物中得到启发、感悟,进而左右逢源,触处皆得益,正所谓“心常存,则因事触发有开悟处,所谓‘左右逢原’者可见”[2]。如果“心不存”,即不用心对待事物,就会与理相背离,就算与清晰的义理无限接近,也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正所谓“与理相忘,虽至近至明之理,亦无觉无见也”[2]。
1.2 存心居敬
薛瑄把“主敬”作为存心的修养工夫,以敬言存心,以敬言涵养。“敬”作为理学所建立起的修养方法,多位理学家对其有所论述,包括程颐注重“涵养须用敬”的内在修养;朱熹提倡“持敬是穷理之本”的为学纲领;曹端“立基于敬”的为学宗旨等。待此思想发展到薛瑄这里,他在吸收“用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用敬涵养身心的主张,认为“常‘主敬’则心便存,心存则应事不错”[2]。但是, 人心“易遥而难定、易昏而难明 ”[2],惟有通过“主敬”涵养人心,才能明朗而坚定。所以, 为学还须由“用敬”入手,方能收敛身心,穷得事物之理:
“千古为学要法无过于‘敬’,敬则心有主而诸事可为”[2];
“才收敛身心便是居敬,才寻思道理便是穷理,二者交资而不可缺一也”[2];
“心才敬,则人欲消而天理明”[2]。
在薛瑄看来,只有持敬之心才能明理。若不用敬将心存养,心就会放逸,身体也会懈驰,虽然有人之形,也没了血肉之坚,和物没有区别。在论述存心须“居敬”的同时,薛瑄也阐述了不居敬的危害,他指出:
“人不持敬,则心无顿放处”[2];
“人不主敬,则嗜欲无涯,驰骛不止,真病风狂惑之人耳”[2];
“人有斯须之不敬,则怠慢之心生”[2]。
从而从反面强调了要将主敬纳为修养身心之法,加强敬的工夫,以涵养礼乐之教、安顿身心、清心寡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持敬的工夫并非是不闻不见不思的兀然端坐,而是要将敬持于心中。
1.3 心存识道
站在理学的视野下,薛瑄对“存心养性”的诠释,不论是存心见理,还是以居敬存心,其最终目的都是实现人的修养以接近大道。“道”是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薛瑄认为:“心存, 则因器以识道。”[2]即只有存心于事物之中,才能认识各种事物之理,甚至见道。若心不存,虽然也能粗略认识事物,却不能识得道了。因为,道虽然从没有远离人,但如若心不存,人就会自然而然地远离道。这就对孟子认为人都有仁义之心,之所以丧失良心,是因为不善于保养的观点有所发展。薛瑄把以理养心作为涵养的内容,将以心识道视作涵养的延伸,时时刻刻注重自我省察,不让意志有所偏颇,不妄动念想,因为“斯须心有不存,则与道相忘。要当常持此心而不失,则见道不可离矣”[2]。薛瑄强调心离不开正理,身离不开正道,因为心与理、道是紧密结合的。
理学家对于心境的持守、人心的内在体验、精神境界的追求都有自己的修养方法,而薛瑄则从孟子提倡的“存心”入手,注重存心的修养工夫,主张在日用之间皆用省察涵养身心,以存心减少物欲,摆脱私欲的侵扰,以义理、道、居敬养护身心,这与孟子所提倡的“存心养性”是一脉相承的。
2. 养其性为身心之修养
薛瑄承继孟子“尽性”思想,提倡通过内省反躬自身修养的方法达到知性、尽性甚至是养性,充分发挥心中的至善之性。他认为在日常学习及生活中“存心”可以明白事物的义理、属性,进而可以知天,以存有这种心思来侍天。他把尽心视作修养身心的一个阶段,是知性、尽性的前提,主张保留一颗良善之心以保持人性的纯粹,以侍奉“上天”的态度去完成使命。
2.1 知性尽心
薛瑄对“性”的认识大多继承于孟子,他曾在《读书录》中说道:“自孔孟后,皆不识性。”[2]“自孟子没, 道失其传, 只是性不明。”[2]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性”这一理论上对孟子的推崇。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是水总是趋向下流一样,而人性不善就像水向上倒流,是其所处的形势迫使它这样的。薛瑄也把性比作水,但是他又认为“孟子专论性,不及气耳”[2]。“程子曰:‘气清则才善, 气浊则才恶。禀得至清之气生者为圣人, 禀得至浊之气生者为愚人’”[2]。薛瑄很认同此说,但他更加注重气对性的作用。其言道:“水有清、浊者,渠使之然,而水则本清; 性有昏、明者, 气使之然, 而性则本明。”[2]他在“性本善”的基础上提出“性本明”的认识,认为性的昏浊是由其禀赋的气所决定的。
在“性本明”的理论中,薛瑄更强调“知性”是“尽心”的落脚点。他认为,“‘尽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2], 人能够“知性”“知天”就可以明得天下万事万物之理,进而做到与身心相互贯通。反之,若不能“知性”“知天”,心中有了妨碍,就不能明白此理,也就不能通晓世间无穷无尽之理了,所以,“知性”“知天”对知“尽心”是极其重要的。在这里,薛瑄承继了孟子“知其性,则知天矣”[3]的观点,认为懂得了人的本性就懂得了天命,保持本心,养护本性就是在世间的安身立命之法。他主张在“知性善”的基础上,尽心达到对事物完善的理解,“存其心, 养其性, 所以事天也”[3]。
2.2 为仁尽性
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大多和“修身”有关。孟子在孔子“仁、义、礼”的基础上延伸出“仁、义、礼、智”,并提出了“四德”及“性善论”,认为若人没有“仁义礼智”这“四端”就不能称之为人,因为这是人内在所具有的本性,也是为人处世的立身之本,更是伦理关系的道德准则。
“克己复礼为仁”[3]源自《论语·颜渊》,是孔子对颜渊提问如何达到仁的境界所做的回答,他把“克己复礼”称之为“仁”,将之视为通达仁境的修养方法。薛瑄引用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的观点来阐述“尽性”,指出“‘克己复礼为仁’,则尽性矣”[2]。薛瑄以复性为宗,认为仁、义、礼、智皆是人性的一部分,他想要求复的就是“仁义礼智之性”[2]。他认为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归于礼就可以做到仁,做到了仁就尽了仁、礼之性。另一方面,他认为“仁义礼智即是‘性’, 非四者之外别有一理为性也”[2],道、德、诚、命、忠、恕,皆是遵循性而行,性是万理的最高范畴,理虽存于万事万物之中,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名称也有所差异,但都不过是性而已。
2.3 存心养性
薛瑄认为,心大到可以包罗天下万物,小到天下万物无物不入,所以非常重视对心的养护。他主张心的存养在于不应有私欲,应当正大明白,因为心不可有丝毫偏向,有了偏向就容易被人利用,造成相反的效果。在薛瑄看来,“如自有其善,便为善所累;自有其能,便为能所累;自有其贵,便为贵所累;自有其富,便为富所累”[2],万起万灭的私欲一直扰乱主体的心,主体因得而欣喜,因失而忧愁,心就必受其所累。人无尽的放纵欲望只会让人一步一步地失去羞恶之心,只有把私欲都去除,得失的喜怒不累于外物才能心定,才能回归湛然之性。因此,人应当“荡涤私邪,存养心性,端谨容节”[2],注重涵养,淡化欲望,不被怒气所支配,心才能不为私欲所动。
对薛瑄来说,心是气的灵魂,亦是理的枢纽,心的养护是十分重要的。他把“君子修之吉”[3]与《孟子》所说的“存心养性”等同视之,认为君子要懂得修养存心养性,心静时可以做很多事情,也能明白其中无限的义理。但是,由于人每天面对不同事物,产生新气象、新发展,心也是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所以能以静言性,但是不能以静代性。他引用孟子提出的“动心忍性”来时刻反省自身,常常在心、意、言、动上下工夫,认为“心必操,意必诚,言必谨,动必慎,内外交修之法也”[2],主张读书时也应不滞于言语,而是把书中的内容与自己的身心相结合,这同样有助于存心养性。
3. 立以复本原之善
薛瑄注重人的内在体验,以存心明义理、见大道,以养性涵养身心。从理学角度来看,他认为人性本善,善是人性最初的样子,主张为学之人就是要明善,进而从善,体验人心向善的纯粹。在薛瑄看来,人性本善,因受遮蔽而变浊,所以,去除物欲、回复本善是人应该追求的,这正与他一生以“复性”为宗,躬行实践“复性”的自我修养相契合。
3.1 明善
薛瑄肯定了孟子“性本善”的理论,认为“反性为恶,而本善常在”[2]。在他看来, 人性本是同一的,若人们顺应本性而为即是善,恶则是因为违背了本性。所以,我们必须明善,时刻体察恶并将其剔除,这也是从善、甚至复性的基础。他还强调,若心中产生疑惑或者动摇,亦可从圣贤书中寻找培善资源,体悟其善德以自立。
薛瑄认为“‘明善’,即是‘知性’”[2],他把善和性相等同,主张世间只有一性,一性分散为万善,“善即性也”[2],为善也就是要尽性, 反之,为不善也就失其性。所以,他认为“《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 是因为言善时性已经在其中了,言性时善也已经在其中了,善即是性,“善、性一理也”[2]。
对于明善之后,薛瑄也有所阐述,认为要时刻省察人的万善,从细处着手,不可轻视丝毫动作、思虑。因为人有两个不正的念虑,即妄念与恶念,妄念是主体思虑后不可得的事,恶念是主体思虑违背道理的事,一经发现这两个念头就应该遏制,知行一些正的念头,如合乎仁、义、礼、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性情,那些不正的念头也会自行消散。
3.2 从善
明善的目的是要从善,世间只有一善,人本性善无恶,若不从善、为善,又怎么能称之为人。若是有善,不应沾沾自喜,应存心养性继续保持其善,若被恶的气质所拘,更应存养心性摒弃其恶。
虚中无我能从善。薛瑄言“虚中无我,惟善是从”[2],认为无论是人还是天下万物都是从阴阳造化中来,是和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切不可采取一种高高在上、不配合的态度,应以无我的视角看,把世间万物看做一个整体,做到内外合一,与天为一。真正的从善表里都应当澄澈,不应当夹杂丝毫的私欲,因为善是本分,是人本应当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若是因为受到影响才开始从善,则是因为功名之心,这是人的欲望而不是天理。
心正能从善。薛瑄认为心统领着性情,当心中不着一物时,心是正的,性也是善的;当心中有物,若心是正的,那性也是正的;若心不正,性亦不正。人心不正,为人处事时摇摆于事物之中,动摇于动静之间,做事情又怎会做的正呢。薛瑄提倡“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终不为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2],自己没有做到善,那么别人称赞你,也不足以喜,若自己做到了善,即便招到别人诋毁,也不足以怒,丈夫当以正大立心,方能心中存善,行为从善。
不偏执己私能从善。世间大多数人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谋求自己或是所在集体的利益,往往偏向于自己,这种不能克制、约束自己的功利的行为,薛瑄认为是不能从善的。在他看来,人们的私欲是无边无际的,只有减少私欲,心体才会发展,要“心役物不可役于物”[2]。这是因为“‘心生于物’,物诱也;‘心死于物’,物化也”[2],也就是说,人们复杂的心思往往是由外物影响而产生的,这是外物对人们的诱惑;人的心思是由外物干扰过度泯灭的,这是外物对人们的干扰。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要从善,首先要以正大立心,保持内心的公正,提高自身的修养。然后,树立虚中无我的态度,保持内心的清澄,与天地为一体。最后,要不偏执私欲,不要被外物支配。如此,方可复本原之善。
3.3 复性
从善的目的是要复性。薛瑄一生以躬行践性为宗旨,相信人性本善,但是由于人禀受了有杂质的气从而导致恶的产生,所以他追求恢复人善的天性,也即是复性。而要达到复性仍需进一步加强修养,以存养良善之心,摈除私欲为途径,通过用敬、为仁、明善、从善的方式,在内心形成修养的体系。
薛瑄提倡“存心养性”的目的是实现复性。他认为“为学者,只为人固有之善或蔽于气质物欲,有时有失,故须学以复之”[2], 为学的目的就是要知性、复性,千古圣贤所教给人们的也在于“复性”。在薛瑄看来,那些因为私欲、物欲或者禀受其他气而遮蔽了善的本性的人可以通过存心于事物之中,明白事物所蕴涵的理,进而明白人对待事物所具有的情来“复性”。正大的内心对理解事物之理、对待事物所具有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这就复了物之性。
薛瑄注重性本善,认为本然之性是至善无恶的,气质之性是有善有恶的,以人本就具有的至善的本然之性为根据,以复性则可以入尧舜之道作为精神目标,追求复性,以复见本原之心,这为为学之路、存心养性指明了方向。
薛瑄虽承继了孟子的“存心养性”思想,但是与孟子对“存心养性”的诠释不同。薛瑄站在理学视域下,以立心为本,更以“存心”“养性”作为修养之法和为学用力的方向,在孟子“性善说”理论中嵌入了气的元素,认为善恶之分在于每个人禀受的气不同。他更突出人的后天努力, 一方面可以涵养、保存善,另一方面可以为善去恶,通过“存心养性”使心合乎天理,实现天人合一,最终实现至善之性,以期达到一种自然而然的精神境界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