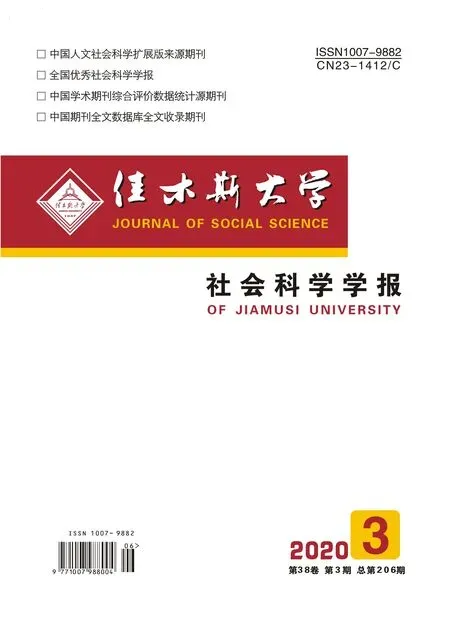家与亲情的回归:重复视域下的胡塞尼小说研究*
黄杰忠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校务处,云南 临沧677000)
一、前言
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塞尼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视角和精湛的叙述技巧,通过《追风筝的人》(下文:《追》)(2003)《灿烂千阳》(下文:《阳》)(2006)及《群山回唱》(下文:《唱》)(2013)中故事的描述,在英语语言主导的世界里唤起无数读者对阿富汗人民水深火热的生存现状的同情与关注。三部小说人物、背景、叙述视角存在较大差异,但细读却可发现小说间有许多围绕家庭、亲情的重复书写,作者借此向世界诉说着阿富汗人民的苦楚与遭遇[1],讲述散居他国的阿富汗人的突围与回归[2],阐释着生命的拯救与救赎[3]及家庭伦理[4]。
希利斯·米勒认为小说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重复现象的理解来实现的,它们可以发生在对小说的语词、事件和场景,或是动机、主题或人物等的重现,及一部作品对另一部作品的重复中[5]1-2,但重复并非一尘不变,而是一个包含着延续和变化的过程[6]24。通过对三部小说人物关系、行为及经历的重复描写进行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理解胡塞尼书写在阿富汗故事内外的深刻意义。
二、人物关系的重复
“一部小说终究处理的是人们之间的关系”[5]232。胡塞尼每一部小说都以成对的主要人物关系为线索来讲述阿富汗的故事,在三部小说间形成对家庭、亲情的重复书写,对命运相连“家人”关系的重复书写:阿米尔与哈桑是被隐藏着的同父异母的血亲关系,玛丽雅姆与莱拉是在患难中结成的“姐妹”或“母女”关系,阿卜杜拉和帕丽是因自小分离而缺失的兄妹关系。这些成对“家人”关系的重复书写让人物彼此完整,如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与阳:两两对应,构成完整的脉络,在不同故事中演绎着相同的逻辑主线——在差异中重复着相似的轨迹、在重复中获得圆满:阿富汗的苦难也无法割断爱与亲情的重复再现,千里散居亦能回归心之所属。哈桑的勇敢、忠诚与牺牲是阿米尔所缺失的,也是使阿米尔在哈桑遭遇强奸时逃离的重要原因,而他回归阿富汗拯救哈桑的儿子的行为是他寻获完整生命的重复。《阳》中私生女玛丽雅姆童年的离群、孤独及不幸让她对生活绝望与隐忍,而少年莱拉的独立、对幸福和爱情追求弥补了玛丽娅姆多年的缺失,让她最终能将铁锹全力挥向拉希德[7]374——在牺牲自己拯救莱拉一家中获得圆满。被卖掉的帕丽与阿卜杜拉兄妹亲情因分离而缺失,又因历尽千难万险不忘掉彼此在兄妹重聚时得于重续。在巴黎成长的帕丽缺少“家”的归属感,如爸爸故事中喝下“魔鬼”药水的孩子与他的父亲,忘了彼此[8]14,直到帕丽回到失去记忆的哥哥身旁,接续上他忘记了后两句的家乡童谣时,兄妹情的寻回才让缺失58年的归属感回归[8]429。
三、生育与死亡的重复
生与死的重复是自然循环,彼此既互为开始与结尾,又相伴而行。
1.母亲之死的重复。“爱欲是死亡冲动的面具,生活是通向死亡的一条迂回曲折的旅程[5]154”男女爱欲的归宿是繁殖与生育,生之旁往往盛开着死亡之花,难产而亡的母亲们便长在其中。阿米尔的母亲在生他时难产死去,他总觉得“爸爸有些恨我,毕竟我‘杀死’了他最心爱的妻子,他美丽的公主”3[6]20,这是他想通过参加风筝节的比赛赢取父亲赞许的初衷,也是他陷入人生另一罪孽的开始。同样,帕丽与阿卜杜拉的母亲重复着同样的命运,在生帕丽时难产而亡,让兄妹两人相依为命却又不得不最终分离。
自杀而死常被赋予特别的意义。“除去生活中短暂的一瞬间,交流沟通无法实现。在对过去的重复中唯一能重新拥有过去的便是自杀的行为”[5]222,对女儿玛丽雅姆的爱是母亲娜娜能独自承受生下私生女的耻辱的唯一凭借,但女儿的背叛彻底摧毁了这位坚强母亲最后的支柱,既然与女儿无法沟通交流,自杀就成了她重新拥有属于自己对女儿爱的记忆;而她的自杀也让玛丽娅姆对父亲抱有的幻想破灭,真正开始了隐忍和孤独苦难的人生。《唱》里,作者重复着自杀这一利器让另一位母亲离去,妮拉是一位推崇西方的东西混血儿、一位阿富汗先锋女诗人,然而,在阿富汗传统文化上离经叛道的母亲在自己养女抢走自己情人的不伦之爱面前,也变得彻底绝望,自杀是她能继续保持在东西文化边缘徘徊的唯一方式。而她的自杀也是作者唤醒迷失的帕丽开始去对自己“根”的追寻。
2.无法生育与无法接受的生育的重复。生育使人类得以繁衍存在,使个体记忆得于存续。人们“无法生育”有各种原因,而阿米尔的是“不明原因的不孕”[6]201,“也许是在某个地方、有某件事、某个人因我曾经所做过的事拒绝让我成为父亲”[6]204,既然科学没法找到原因,那就只能归咎为“一种惩罚”[6]204。此时,父亲好友拉辛汗告知的另一个仆人阿里“无法生育”[6]240的故事让阿米尔获知父亲生前的秘密:哈桑是父亲的私生子。玛丽雅姆的无法生育是拉希德的暴力造成七次不幸流产后的生育功能丧失,但同阿米尔一样,玛丽娅姆把自己无法生育归因为阿拉因她对母亲做过的罪过而对她的惩罚[7]99。作者以“无法生育”的方式让阿米尔与玛丽娅姆对自己(及父亲的)罪过重复认知,让他/她失去通过生育来延续自己的记忆、从而获得救赎的机会,迫使他们另寻一条“重做好人”的途径来结束罪过的循环。作者在《唱》中妮拉身上重复着“无法生育”,让它在故事中起着不显眼但无法抹去的影响。没有浓墨渲染妮拉的不孕,留给了读者更多阐释的机会:是妮拉与阿富汗传统文化背道而驰,但又被西方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矛盾的重复再现,也是对众多对旅居西方少数民族族群尝试在西方主流文化中寻求认同的失败的重复。
维柯认为人类存心满足自己的兽性淫欲而抛弃自己的子女,而他们却创造了合法的婚姻制度来繁衍家族,这一切都在人类历史中不断重复[9]121-122。“私生子”是人类既要满足自己的淫欲又没给它穿上合法外衣的产物,是无法被等级森严的阿富汗社会接受的生育。胡塞尼善用这种“无法接受的生育”,不断再现人类淫欲不受控制后的罪孽,控诉着阿富汗社会苦难的重要源头:种族不平等与父权制下的畸形家庭。拉辛汗曾给阿米尔讲述过他年轻时爱上并打算娶一个邻居家的哈扎拉仆人“美得像个仙女”的女儿时全家如临大敌的故事[6]107,作者清晰地写出了这种跨越种族、跨越社会阶层的通婚在阿富汗的不被接受。哈桑童年时受人鄙视的“哈扎拉人”身份与在塔利班为抢占他在喀布尔居住的大房子残忍杀害他时的理由:哈桑是“像所有哈扎拉人一样的骗子和小偷[6]236”都重现了对哈扎拉人的歧视,这些重复描写让阿米尔父亲与哈扎拉仆人阿里的老婆私通生下私生子更加不堪言说。对哈桑的偏爱,甚至原谅最不齿的偷盗行为[6]115,在哈桑父子执意离开时的挣扎与痛苦[6]116-117等童年时父亲种种迷惑行为,在真相面前显得如此苍白,较于此,阿米尔的谎言与罪过不过是父亲满足一时淫欲的罪过的重复,也是让他走上“再次成为一个好人”的救赎之路的原因。与哈桑被隐藏着的私生子身份不同,玛丽雅姆“harami”身份一开始就是让她与母亲离群索居的源头。作者将私生子这样的“无法接受的生育”重复再现,不仅是为玛丽雅姆的苦难隐忍生活打下伏笔,让玛丽雅姆一生带着被赋予的“harami”屈辱身份,在幸福生活的期望与绝望中循环往复,直到最终的重生,也是通过描述这一由父亲造成,却让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来承担所有罪责的原罪,对阿富汗父权家庭畸形发展的控诉。
四、离开与回归的重复
突围与回归是胡塞尼小说重要的主题[2],通过在小说间对离开与回归的重复书写,作者进一步阐述阿富汗人民历经苦难后仍心念故土、向往希望的情感。《追》对阿米尔背叛哈桑亲情的行为进行了三次重复书写:把哈桑当成获取父亲认可需要牺牲的羊羔[6]84,目睹哈桑被强奸后的逃离,以编造谎言让父亲赶走哈桑父子的方式“尽快逃离”[6]93内心的愧疚,把美国当成“埋葬自己的记忆的地方”[6]114的逃离,然而带着愧疚与罪恶的离开让阿米尔无法摆脱曾经的梦魇。“离开”在《阳》中故事叙述起着重要作用,玛丽雅姆背叛母亲,离开与母亲居住的泥土房,去寻找父亲致使母亲的自杀成了玛丽娅姆失去追寻私生女没有权力获得“家与家人接纳”[7]4的希望的开始,而她的牺牲帮助莱拉一家出逃奔向幸福又是让玛丽娅姆回归新生,在离开人世时有了苦苦追寻的“朋友、伴侣、监护人、母亲”[7]396的身份。帕丽两次被动离开——被迫于生计的父亲卖到喀布尔,被养母带到巴黎——是作者对许多被迫远离母国的阿富汗人的经历的重复书写。小说重复的方式并非一成不变的,往往需要仔细品读。小说间对人物的回归进行了重复书写:阿米尔回归战乱中的喀布尔寻找并拯救哈桑的儿子,是寻求自我心灵救赎的回归;作者让玛丽雅姆挥下铁锹,是让她重获新生的回归;莱拉带着家人重走玛丽雅姆的故乡,帕丽回到哥哥身边是她缺失身份的回归,尽管他们的方式与目的各有不同,但潜藏背后都是对家人的爱,对阿富汗美好未来的期许的重复书写。
五、小结
一部特定的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很可能不在于它直接了当表述的东西当中,而在于讲述这个故事的方式所衍生的种种意义之中[5]200。作者通过在三部小说中对主要人物关系、经历与行为的重复书写,以“家”为中心,描述了那些与阿富汗有联系的人们,无论是兄弟姐妹、父母儿女,富人、穷人,本土人、旅居欧美的阿富汗人或是前往阿富汗援助的欧美人,虽历经苦难,依然向往亲情、友情的“阳光”、渴望阿富汗“向好”的未来。这种向往与渴望跨越种族、跨越身份、跨越地域,如一圈圈无法抹去的痕迹,拓在阿富汗乃至世界千疮百孔的岁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