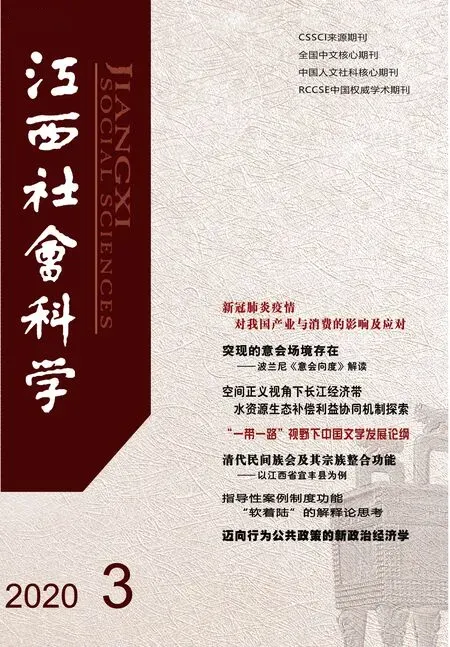清代民间族会及其宗族整合功能
——以江西省宜丰县为例
龚汝富 徐志强
清代江西宗族势力活跃得益于族会产业的兴盛,族会以敬宗收族为宗旨,以股份合作、轮值管理、账目公开为原则,倡立各种基金支撑宗族内外各项公益事业。敬宗收族、光前裕后、乐善好施的族会善举背后,融汇宗法伦理与经济理性的管理智慧,激发了族众参与宗族事务的热情和动力,并将公益事业与私人股份利益结合,做到义利合一、公私兼顾。
“敬宗收族”是在明清宗族谱牒序跋中被高频率使用的词汇,寄托了纂修者与所有宗族成员团结互助的美好愿望。然而,修族谱、建祠堂、祭先祖、济困穷、备灾荒、恤老幼等善缘张举,莫不依赖于族众的经济实力。清代光绪年间江西萍乡绅士李国琪在书写李氏清明会会约时,公开声明“无会不能收族”,因为族内“一切美举皆会内公费使用”,道出族会在宗族整合中的特殊地位。[1]晚清民初因修订民律而开展民事习惯调查,江西民间宗族共有款产“众会”备受瞩目[2](P6),“众会”作为江西民间宗族共有款产的代名词,既表明其产权属性为族众所有之“众”,也表明宗族会产存在名目众多之“众”[3](P5、P64-68)。江西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宗族势力比较活跃的地区,乾隆年间还因省会南昌的合姓联祠泛滥而遭官方厉禁。[4](卷五五《奏请禁江西祠宇流弊疏》)其后,宗族祠宇承载的敬宗收族使命转而由各种族会具体筹划,民间宗族祠会产业规模之大、功能之全,使得宗族内部整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进而为地方社会治理创造了合作基础。
笔者以宜丰县(清代称为新昌县)为例,就清代民间倡立族会情形及其功能价值做一样本分析。样本选择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宜丰县自清代乾隆年间以来人口一直徘徊在25万上下,是一个起落变化不大的中小县,既无簪缨世族和强宗豪右,也无土客族群矛盾,具有相对稳定和客观中性的样本价值;二是宜丰地方文献较少为学术界所关注,而其原始族会文献保存之多,江西几无出其右者。所以,以宜丰为清代江西族会研究个案,可以生动再现江西民间族会形成过程,以及其整合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功能价值,深化我们对传统宗族社会治理结构的认识,正视宗族会产在消弭族众贫富分化和防范社会风险中的积极价值。
一、族会样本列举:阄书、会簿与族谱
清代江西民间族会盛行,既有宗族整合的治理需要,也体现了族众股份合作的一种经济理性。什么是族会?族会就是族众为了某一公益目的而筹款成立的事业基金,如修谱要筹款则成立谱会,按人丁派款,也可以设立丁会、丁兰会等基金,在每年族内申报新生人丁时量收定额丁钱,留作修谱时开支。理论上说,宗族治理存在多少开支项目,也就有多少立会的可能和需要,只是迫于族众经济实力限制,而不可能完全覆盖。但略有经济能力的宗族成员,总是会千方百计发起成立各种族会,为宗族发展强盛未雨绸缪,这在宜丰地方文献中也得到了有力证明,笔者仅以芳塘熊氏家族一份阄书、天宝邹氏一族印发的会簿、天宝墨庄刘氏一部《墨庄阶下重修房谱》等所叙族会情形,即可概览清代江西民间族会繁荣之一斑。
光绪二十年(1894),宜丰芳塘下屋熊阿李,在丈夫熊接三去世两年后,考虑“息肩之计”,将丈夫继承所得和夫妻打拼财产进行分割继承。在29位族人和5位亲戚的见证下,三个儿子钦世、锦世、镛世以“致中和”字号抓阄,钦世得“致”字号,锦世得“中”字号,镛世得“和”字号,阄书一式三份,保留至今的是镛世的“和”字号阄书,但完整反映了家产阄分的全部财产信息。每人除了分得数额庞大的房产、店面、山场、租谷、债权外,还分得各色族会17个,共37股:贵灯会3股半、翰洲会4股、忻灯会3股半、敏丁会4股、贵丁会3股、浙灯会1股、翰灯会1股、豹觞会2股、和斋公丁会2股、萃灯会2股、天符祠社会4股、天符会1股、天符祠观音会1股、狮山庵观音会2股、三官会1股、发萃园文昌会1股、新兴花轿会1股。由此可见,这些族会集中在祭会、丁会和神会等产业。
在三兄弟阄分财产之外,熊阿李还给自己日后生活安排保留了巨额财产——“扣留口食存众业产”。在这份财产清单中,入会48个,共69股半:翰洲会1股、典翰洲会4股、忻灯会1股、典忻灯会2股、大宗义学会2股、斌灯会1股、抡才会2股、斌公渡船会1股、禁赌会1股、接戏会2股、青山会2股、敏丁会半股、贵公老丁会1股半、贵泮香会1股、贵喜香会1股、贵丁会2股、斋胜会1股、斋文会1股、斋香会2股、浙灯会1股、浙培坟会2股、忻喜觞会2股、喜丁会1股、翰灯会半股、翰丁会1股、翰香会1股、江家洲会5股、义合会1股、永兴戏会2股、培耕会1股、天符祠灯会1股、老老良会1股、新老良会2股、关帝会2股、狮山戏会1股、真君会2股、文昌阁魁光会1股、三官殿关帝会1股、兴贤堂集贤会1股、桥头太保会2股、立大同年会1股、上街头华光会1股、芭蕉桥排仔会1股、楼里太保会2股、下屋太阳会1股、贵公太阳会1股、六合会1股、喜庆会1股。熊阿李所拥有的族会,无论种类数量和股份金额均远超三子均分之会,且社会与经济功能无所不包。显然,熊阿李作为家长,仍然把参与宗族众多活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48个族会全方位展现了熊氏家族活动的具体内容和基金构成,正是因为熊接三、熊阿李夫妇经营得法且家境富有,所以对族会参与度也高,在芳塘下屋熊氏族谱记载阙如的情况下,熊阿李笔立阄书生动再现了清代江西丰富多彩的民间族会。[5]
宜丰天宝龙冈邹氏因为明代后期族人邹维琏官至闽浙总督,成为县内少有的名宦家族,所以从清初开始便注意精心打造名宦世族的形象,立义塾、修文塔、建试馆一应俱全,据宣统年间重修《崇祀录》所载繁文缛节和用度宏富的崇祀礼仪,足以说明邹氏大宗祠拥有的祭会产业极为惊人,否则难以支撑崇祀礼仪近乎奢侈的场面。[6]此外,邹氏族众特别注重维护宗族风水龙脉和改善族众生产生活,发起成立各种性质的会社。尽管由于历史原因邹氏家族除《崇祀录》外的其他历史文献散佚殆尽,但笔者从民间收集到近十种该族族会簿册,恰恰弥补了该族乃至宜丰一县族会样本的缺失,据此可以清晰展示族会发起宗旨、会员、股份及其管理规则。根据族会是否具有经济效益来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经济收益的互惠族会。如诏公松茂堂会。据《诏公松茂堂会簿》记载,诏公植下管有大片荒山,担心被他人盗垦侵占,诏公植下子孙众议,于嘉庆十二年(1807)正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荒山“栽插松树”,有力者出力,无力者补钱。三天出工193个,补工钱者18.6千文。总扣507工,就作507股,凑成一会即“松茂堂会”。由于该会经营得法,会产收入颇丰,诏公祠的许多公益活动都靠该会支持,诏公祠众前后借用该会数百千文,无力偿还,最后将诏公植下北门店房三间作价400两银子,开荒所得山场作价3000文,立契约拨给松茂堂会“另标管首”。会众每股分得800文之后,将北门店房仍返还给祠众以作清明祭会之资,而开辟荒地所形成的松林产业则归松茂堂会众所有。由于松茂堂会与诏公祠双方的抵扣划拨是在祠众内部进行的,所以,该会会股严禁在祠众之外交易,在《凡例》中特别强调“只许售到本支管业,不许外行买卖以负起会至意”[7]。又如龙岗荒田会。《龙岗荒田会崇祀录》记载,从咸丰六年(1856)开始,邹氏族众借鉴松茂堂会的成功经验,集股开荒种地,凑成一会名为荒田会,共150股,收益扣除会本后储蓄归公,作为祭祀会众先祖之需要,是一种劳动收益转化为祭祀资本的族会。[8](P3)再如文蔚堂会。《文蔚堂崇祀录》民国三年重修,邹氏温公支下子孙自光绪三十年起,参加捐纳者另外起立一会,即文蔚堂会,每人出代席钱20千文,名为专祭温祠推广孝思,实际上是捐纳者合资筹办的一个公益基金,除了每年腊月初九祭祀温公分得胙肉胙钱外,余款放租生息,但不准私下扯债。后来温祠以外的邹氏族众捐纳者也有入会的,共计100股。[9]
另外一类是没有经济收益的纯公益支出型族会,其中以祭祀会为多。如镇江会。据《镇江会录》,又名《南门镇江会录》记载,龙冈邹氏从北门水渠入口到南门水口,都要疏浚水道,捍筑堤岸,培植风水林。而邹氏一族奉祭清江神,道光二十七年(1847),族众发起成立镇江会,筹集126股,每股出钱200文。但到民国十年重修《南门镇江会录》时,仅剩20股,这个完全公益付出的族会难以为继。[10][11]又如南门社会。《邹氏南门社会本》记,道光二十年,族众就南门社祠举办祭神赛会,佥议敛钱立会以为祭赛之资本,每股捐钱百文,共285股。这种寓祭于乐的迎神赛会是民间较为盛行的娱乐性族会,与戏会一样捐钱不多,门槛不高。[12](P3)再如石神会。《岩前石神会崇祀录》和《彭家山石神会崇祀录》显示,祭祀石神是宜丰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只要有巨石、怪石的村落,就有崇祀石神的活动。同治五年(1866),邹氏族众发起成立岩前石神会,每股出钱200文,用以每年八月初八祭祀石神。[13]光绪七年,又以同样方式凑起彭家山石神会,股份钱额和祭祀日期也一样。[14]不过邹氏族会簿册显示,非收益型的族会,也可能在社会救助、保护农耕、促进教育方面做出积极贡献。例如:其一,《龙冈永龄堂会本》。道光二十九年,邹氏族众每人捐钱千文,以股份的形式建立福利基金,生息置产,滚动获利。对年满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赡养和年节肉饼福利。原定60名,后来扩大到96名,以邹氏族人为纽带,受益人却不限于邹姓,如岳父、岳母、舅舅、舅母、外公、外婆均可成为会股受益人。显然,这是借助福利基金来减轻未来赡养负担,颇富创意。[15]其二,《培耕堂会簿》。咸丰七年,邹氏族人设立一种开放性的禁会,由邹氏族众发起,也不排除田地相邻各族人等加入,目的在于严禁人畜祸害以保护农耕生产,也即保秋苗禁六畜,禁猪牛鸡鸭闯放,禁盗贼偷窃。根据田亩多寡量收薄谷以为会股,集腋成裘而立基金,用以支付看护人员工钱和奖励费用。[16]其三,《塔下文昌会本》。同治元年,邹氏族众发起成立文会以兴人才,集资114股,敛钱600千文,置买田产,收租生息,除完国课和祭费外,羡余用于奖携人才,在没有上项开支的情况下随多寡照股均分,每年二月初二到范阳书室执会本领取。[17]
天宝墨庄刘氏民国五年所修的《墨庄阶下重修房谱》,其卷九至卷十二在祭产、义产、各会庄田等章节中,对族会产业做了详尽介绍,从立会到不同时期的会本会股赢缩情况登载详细,为观察清代族会提供了一个动态模板。[18]其一,崇本会。乾隆四十八年(1783),用银圆13两价买一厅两间屋为祠。乾隆五十二年开始与胙会朋买产业,并收入一半利润。嘉庆二年,用银圆560两买产。嘉庆十五年,用70两买产。嘉庆十六年,用银60两买产。道光元年,用45两买产。道光元年,与储会、胙会、谱会、祔食会、报丁会、新祭会朋买山场田地庄屋,每年可收租9石8斗。契管本乡三十三都田产,与大宗义学会田产相连。其二,新祭会。光绪二十三年新祭会开始大量典入田产,各祠堂和族会助钱尤多,如助钱的会有同仁会3股、二灯会3股、崇先会2股、房谱会2股、莅堂公助福社会2股、朗窗公助老兴贤胙会1股、四应公助本祠同仁会2股、士尤公助本祠崇先会1股、储会助本祠同仁会2股、灯会1股、光裕堂助花庄桥会1股、戏会助二社会1股、溥亭公助耆英会1股、刘善之助本祠福主会1股、凤鸣公众助大宗中元会1股、本祠同仁会1股。新祭会买田置产主要集中在光绪二十三年,其后偶尔买入其他会产,如光绪二十四年用31.5千文买下崇文会田产,租额3石5斗;光绪二十七年用6千文买下刘洪泰老兴贤胙会1股。其三,祔食会。乾隆四十七年用银70两买产,租额15石。道光七年用钱78千文买产,租额4石5斗。道光二十二年,用钱108.8千文买产,租额7石。同治三年与胙会、同仁会、续储会、谱会、戏会用银110两买产,租额14石(本会4石)。同年,用银26两买产,租额4石。光绪二年与胙会朋买用银40两,租额8石(本会4石)。光绪八年与福主会用银40两朋买山场,租额2石5斗。光绪三十四年与储会、胙会、崇本会、谱会、报丁会、新祭会朋买产业,租额3石5斗。同年与胙会、同仁会买产,租额10石7斗(本会2石2斗)。光绪四年,用钱3.4千文买入刘曲波耆英会1股。光绪十三年,用钱4.8千文买南门安澜会一股,管有崇先会3股、南门副灯会1股、同仁会18股、二灯会31股、昭公清明会2股、元灯会2股、节公清明会4股。[18](卷九《祭产》、卷一一《义产》)
墨庄刘氏族会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是,几乎所有的会均被赋予丰富的经济内涵,即如崇本会、新祭会、祔食会等纯支出性的祭会,也通过借本生利、本利滚涨而不断买入新的产业。因而除却祭祀、酒席费用之外,仍有可观的盈利用于分配,这是该族众会财产运营的独特之处,其成功经验源于族人很多都是从事贸易的商人,精通利滚利、钱生钱的道理和方法。正是因为引入商业运作模式,该族胙会并没有独立置产,而是与其他各会朋买产业,按股收租分红,后来干脆逐步置换成各族会会股,完全退出族会产业管理环节,大大节约了管理成本,提高了资产收益率。所有族会按照投资收益考量,不可避免会遇到投资风险问题,如何避免会本亏噬,仅凭本会强化管理仍是不够的,规避投资风险的最好办法是会与会之间彼此持有股份,如上引各会成立时接受他会所“助”股份,甚至买入他会股份,就是明证。又如该族崇文会乐助名单中,文奇翁众300两、用节公50两、报丁会10两、进主会10两、清明会10两,其实就是各翁祠、会根据捐助多少已经持有崇文会相应股份,而崇文会也持有本祠牌主会半股、节公清明会3股。储会则持有鸡公岭禁山会1股、七耆英会5股。光绪八年发起成立的福主会,管有二社会1股、福社会9股、安澜会1股、同仁会2股。同治十年起立的抽头会,光绪二十年曾用银25.4两购买孝思会1股,也即孝思会一股涨到25.4两了。[18](卷一二《各会庄田》)孝思会,顾名思义,就是一个追怀先人的祭祀性族会,能够运作成如此增值的股份,确实需要经济智慧。
三类族会样本,给我们提供了观察清代江西族会的不同视角:芳塘熊阿李笔立阄书展现了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族会名色,拥有不同族会股份就意味着不同的权利和收益;天宝邹氏散存至今的族会簿册,既是族会股东的入会权证,也是族会发起与建章立制的原始凭证,是解读族会制度的核心文本;《墨庄阶下重修房谱》所列族会赢缩变化的动态过程,说明即使是纯消费性支出族会,也可借助经济投资手段使其保值、增值并积极避免入会的投资风险。
二、敬宗收族:族会兴起的伦理逻辑与经济理性
从熊阿李笔立阄书中的“扣留口食存众业产”所列48会,我们试图分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祭会和谱会。立会旨在祭祖和修谱,这是敬宗收族的根本大计。如翰洲会、翰灯会、翰丁会、翰香会、贵公老丁会、贵泮香会、贵喜香会、贵丁会、贵公太阳会、浙培坟会、浙灯会、斋胜会、斋香会、喜丁会、喜庆会、忻喜觞会、忻灯会、斌灯会、敏丁会等。二是文会。立会以作兴人才,这是宗族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如大宗义学会、斋文会、抡才会、文昌阁魁光会、兴贤堂集贤会等。三是神会。立会祭各路神仙以保平安,是民间宗教信仰的生动体现,如天符祠灯会、关帝会、三官殿关帝会、真君会等。四是戏会。立会请戏以助教化,如接戏会、永兴戏会、狮山戏会等。五是禁会。立会以助禁约,禁止赌博、盗窃、祸害青苗、砍伐山林、盗挖沙洲等丑行,如禁赌会、青山会、培耕会、江家洲会。六是养老会等。本尊老孝敬之义,立会以助养老。如老老良会、新老良会、立大同年会、桥头太保会、楼里太保会、上街头华光会、下屋太阳会等。七是合会。立会以济缓急,轮换分享会金,如义合会、六合会等。八是义渡会。立会以助涉水通行,如斌公渡船会、蕉桥排仔会等。尽管熊阿李夫妇已经拥有足够多的会产了,但在这串长长的会股名单中,仍然缺失乡村慈善救济的备荒会、救荒会,该族先人熊廷璋捐银千两立救荒会的义举曾载入同治县志[19](卷一九《义士》),熊阿李夫妇不会不知道救荒会的存在,只能揣测他们可能不是同道中人,而且他们的经济条件也无虑于荒凶之饥。
熊阿李夫妇拥有股份最多的是祭会和谱会。在以上祭会和谱会中,均以某代祖先字号立会,如上引各会中的翰、贵、浙、斋、喜、忻、斌、敏均为先祖之名,因为大宗祠有祭会和谱会,族下各支祭会和谱会则多以灯会和丁会等各色名号来立会。灯会就是祭会,在该族圣瑞翁植下便有麟灯会:“吾支联兹胜会,效金钱之欲,买光燦祖灵。”[20]丁会便是谱会,与熊氏一乡之隔的万载潘氏族谱对丁会有明确解释,“夫丁会也,因丁敛钱,积本生利,以为修谱之资者”[21](卷一○《生凤公子孙丁会记》)。县城巨族胡氏四修族谱时设立玉兰会,“族人有添丁者,于每年五月二十日投祠报明登册,每丁敛钱百文”[22](卷一《五修族谱新增凡例五条》)。当然,丁会在宗谱纂修完成之后,也可备用族中其他公益事业,如宜丰县城漆氏所立玉兰会,初生男女“出喜银一钱,立簿收存,年终诣宗祠稽考生殖,备族中义举公事”[23](卷首《凡例》)。祭会和谱会是封闭性的,即以植下子孙为限。祖先代数越多,由近及远可以举办的会也就越多,同一曾祖者立一会,同一高祖者也可立一会,入会越多,参与祭祖入席雅聚的次数也多,彼此攀亲带故的机会也越多。但祭远祖入大会与祭迩祖入小会,立会者和入会者都是有讲究的。比如,熊接三的高曾祖若是名宦,自然重视立小会,独享名宦后裔的身份光彩,但他家门户太小,要傍族中名宦的声势,便要找出自己与名宦的共同先祖,以该先祖名号立一会,并建某公或某翁祠,与名宦便接上关系了,都是某公或某翁植下子孙。
熊阿李夫妇拥有如此多的祭会和谱会股份,其考量是具有充分的伦理逻辑和经济理性的。入祭会、丁会越多,参与的宗族人际圈子也就越紧密,既享有孝子贤孙的美名,也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立会建祠祭祖雅聚,看似是纯消费性支出,但却是一种名利双收的盈利投资。因为立某翁祭会,入会者可将已逝的祖、父祔祭(又名祔食)祠中,木主分为大主、小主两种,捐银数额不同,股份多少也不同。如乾隆二十一年,星溪卢氏祳公、祯公、祥公三房子孙借屋当祠,共立祭会。祳公、祯公、祥公三个牌位是大主,大主捐银50两1股。祳公植下子孙捐银25两,仅得半股;祯公植下捐银100两,分得2股;祥公植下捐银150两,分得3股。祔食60位,即祔祭60位小主,每位小主捐银30两,共捐银1800两。经管会首将此2000多两银子全部用以购买邻村戴氏、熊氏等各种产业,放租生息,收益颇丰。所有利润按三七分成办法,大主5股半分割3成利润,用以办理各房祭祀、戏灯、花红等费用。小主60股分割7成利润,捐银买主位者既尽了子孙孝道,又年年可得稳定的股息回报。所以,嘉庆二十一年,三房子孙正式建造新祠而吸收祔食主位时,仍按每股30两的价格,加捐55位小主,计1650两。由于卢氏祭会经营得法且公私两惠,到道光六年时,星溪卢氏一族已在瑞州府专门建有安顿本族考生的南城试馆,道光二十五年,又在省会南城建有卢氏试馆。[24](《乾隆丙子各分捐银裕后》、《嘉庆乙亥各分捐银裕后》)星溪卢氏与芳塘熊氏相隔仅数里,且两族通婚颇密,捐银买主位的祭会运作方法估计大体相同。可见,熊阿李把如此多的祭会、丁会股份作为继承财产,不仅仅是参与众多宗族活动的身份荣耀,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名利双收的入股投资。
以笃敬孝诚之善念立会,谋丰盈垂久之基业,是所有族会举办者的初衷。当我们将宜丰境内各大家族族会仔细考查比对后,会发现敬宗收族的伦理逻辑与子母相权的经济理性竟然完美结合在一起。如熊阿李所在的下屋熊氏大祠早先立有赞贤会,从祠会收入中划拨一部分奖励族中子弟的学业,因为读书人多而定的“赆仪”标准过宽,后来仅凭大祠划拨难以维持,所以同治七年族绅商议暂停支付一切生童束脩盘缠,将赞贤会从大祠剥离出去,重新按照捐银入股的方式来运作。[25](《赞贤会公议条款》)同治年间,该族为在瑞州府买地建筠阳容斋试馆,除了容斋翁祠捐钱200千文立试馆会外,从一开始便吸收族众捐赠各会股,仅同治十二年宽公植下即捐有老祭会36千文、新祭会39千文、复兴会33千文、接兴会40千文、灯会9千文、家课会50千文。因经营有方,很快便显成效,光绪三年宽公植下又加大捐赠力度,续捐老祭会219千文、新祭会237千文、复兴会202千文、接兴会243千文、灯会54千文、家课会100千文、一甲会100千文。从同治十二年到光绪三年这短短四年时间,捐赠会股力度之大,除了赞贤睦族的道德高义之外,试馆会本身具有的经营盈利模式应该是最大的吸引力。[26](《筠阳试馆序》)
熊氏家族的经营模式并非独一无二,宜丰各大家族经营族会大体上都是相近的。如沙溪廖氏宗祠的清明会和冬至会,都是采取捐钱买主位的方式,醵资买产生息滚动运营。廖氏清明会原有主位519个,光绪丁未年新捐主位62个,计田租110石,大片山场林木产业;冬至会原有主位430个,光绪丁未年新捐主位53个,计田租110硕,竹林株树一大片。廖氏宗祠的春秋两祭依托清明、冬至两会,不仅办得有声有色,而且与会族众也获得入祠祭祖的心理安慰和分享胙息的经济实惠。[27](卷首《廖氏佔基》)枥溪巢氏族会有松坡公年祭会、源清公附食会等,后人捐助早晚田租给祠会,以便确立祖父母永远享受祭祀的权利,如道光二十四年季材公植下嗣孙凤传和自枥捐租5石5斗给源清公附食会,换取舆槐夫妇和珠传夫妇“永远享祭”。[28](卷首《产业》)宜丰五盐胡氏发脉自高安华林胡氏,光绪丁酉年华林胡氏宗祠落成,五盐胡氏奉进祥蔼公主位1个,捐钱20千文,每年清明派一人赴祭。在五盐胡氏族众看来,华林胡氏宗祠中的祥蔼公主位及捐入祠会的20千文,其实既是一份与祭权益,也是一份投资产业。[22](卷一《产业》)正是因为祭会会股是可预期的投资收益,而不单单是一份祭祖孝心,所以,对于会股转让借贷均有严格规定,如宜丰双峰邓氏大宗祠祭会,立有祭会简章十四条,其中第九条关于股东在祭会借谷问题便有明确要求:“各股东于借谷及还谷时,必须按股派借,不得越股强借及藉势坑骗,分拆股金破坏善会,如有此种情事发生,即以铲祖灭祭论。”[29](卷首《祭会章程》)即将会员的借贷风险,限定在其出资的股份范围内,唯此,才能避免会本被侵蚀而祸及祭祖大事。
祭会作为族会最基本、最常见的形式,虽然立会宗旨充满敬宗收族、睦族通财等伦理高标,但祭会本身具有的经济属性,决定了它的运作过程必须遵循经济规律,运用经济手段以保证祭会所支撑的宗祠祭祀聚议及其他公共事务持续有序进行。这在各祭会章程条规中,反映非常清晰。如宜丰漆氏基祖安卿公二子五孙发脉五支(五系),嘉庆乙丑年(1805)五系子孙曾发起成立奉先会,因各系财力捐助不均,而仅凭奉先热情无法支持下去,不得不分割祭产,五系各自办理祭祖事宜。道光戊戌年(1838),五系复改立崇本会,股份银两俱照奉先会章程陆续置产以作兴祭之资,但崇本会管理则完全按照股份制运行,并通过八条崇本会条规加以列明。如第一条筹款,大主5位即五系支祖,每位大主捐银64.64两,上等附食主位25位,每位捐银16.16两,次等附食主位共357位,每位捐银2.02两;第二条用处,买产置田,收租生息,除用于祭祀外,有剩余的留待来年四月备荒平粜;第三条管理,管首、总理、租首必须选任“殷实端正者”,所有进出账目祭祀后一日当众清算明白,若有挪用侵渔,“问本房赔补更换”;第四条祭祖入席,参与祭祀酒会,每年当班大主各6位,上等附食各1位,次等附食八年轮流1位,以抓阄为定;第五条祭祀时间和事务安排,每年十一月初十日办祭;第六条分配胙肉胙面规则,胙肉上等附食每位两斤,次等附食当班每位两斤,不当班者不发;第七条敬老、尊贤、大小考试盘缠及喜庆事宜贺仪酒席乐助等款,俱未详列,俟会盛大再定章程;第八条崇祀录刊集383本,各执一本,一本存箱,“以后主位不准更换”。[30](卷首《条规》)由于崇本会完全依照股份制运作,轮值管理无缝对接不留死角,而且崇本会预设功能定位就是祭祀和颁胙,其他善举留待该会盛大之后再定,体现了一种按照成本收益原则开展的权责明确、互惠渐进的经济理性。
三、光前裕后:宗族兴旺的目标与使命
任何一个家族要整合起来,固然需要为建祠修谱等敬宗收族义举提供财力支持的善士,更需要统领宗族的核心人物,其中既要有热心宗族公益事务的领头人,也要有为宗族势力扩大抛头露脸的官宦人物。如前所述,在乡村宗族社会存在层层叠叠的某公或某翁祠堂,其实都是打着祭祀某代先祖的旗号,“寒门欲矜望族”[4](卷五五《覆奏查办江西祠谱疏》),不断标榜同宗某房支的头面人物,以使自己获得与某头面人物为近亲的证据,如清代天宝邹氏无不以邹维琏后裔相标榜,使得邹氏一门不仅与天宝墨庄刘氏为门当户对的世代姻亲,而且与县城熊、胡、蔡、漆等四大家族也有联姻。所以,如何培养子弟成为光宗耀祖的人物便显得极为重要。在科举时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家族兴文会、办义学、奖励子弟科举考试才是正途,族中子弟一旦考取进士,方圆百里之内该族顿时蹿升为名门望族,不仅光宗耀祖,而且作为官宦正绅从此成为整个家族的保护伞,这是宗族兴旺发达的最强音。因此,在宜丰各宗族会产中,文会产业是祭会、谱会等祠会财产之外最普遍也是最庞大的宗族会产,肩负着宗族兴旺发达的目标和使命。各家族的文会产业,包括办族学、奖励举业、建立试馆等具体项目。
倡立文会以兴办本族私塾和书院,为宗族子弟提供义学启蒙教育。如嘉庆至道光年间,宜丰广德乡红园万氏族众输谷于祠成立义学会,“或塾或庠,量为度支,俾得专意讽颂,而郡邑岁科、乡会小大诸试,亦具赆仪以壮行李”[31](卷首《义学会引》)。天宝乡南平刘氏在道光年间倡立文会,县丞刘涛和族人刘汉琦、刘洪昱、刘炳星等捐银均在百两以上。刘理德在《文会小引》谈道:“迩来比闾族党各立文会设义学,莫不互相培养以副圣天子作人之雅。”[32](卷首《尚义录》)肯定了宜丰境内已经风行族学文会,即通过倡立文会兴办本族私塾和书院,族内子弟不论贫富均免费入学,这些私塾和书院又称为义学,而支撑义学的文会也称为义学会。在宜丰境内,各大家族基本上都是采取以会养学的形式,形成一会一学的办学模式,如丰溪李氏建立的回澜书院,该族文会捐有学租,而荷舍李氏兴文会则建有一鉴轩。胡氏兴贤会建立柏园,后来胡思敬改为冬青书院。芳溪下屋熊麟元植下的崇文会,则建有玉成书舍。同安张氏人文会建有文成书屋,桂冈张氏义学会则建有经纬阁书院。党田毛氏裕学会,建有曲江亭。上凌云漆氏义学会,建有春光别墅。棠浦高氏义学会,建有青云轩。钩下周氏义学会,建有青绿园。[19](卷五《学校·书院》)通过文会兴办族学,安顿本族子弟启蒙教育,奠定他们的举业初阶。
奖励族中子弟的举业进步,是倡立文会更具目的性的举措。兴办族学只是解决了族内子弟免费接受启蒙教育的问题,对于子弟学业好坏,则需要引入激励机制加以奖携。在宜丰境内各族文会根据其经济实力强弱,以束脩、膏火、花红、津贴等形式奖励各学业阶段成绩优异的子弟。如芳塘下屋熊氏家族,除了有家课会支撑家塾义学外,另外还有道光二年熊麟书倡立的赞贤会,给文武举人会试10千文、监生乡试1千文、童生院试200文不等的“赆仪”,鼓励族人慕贤笃学。[33](卷首《赆仪》)光绪年间熊氏族人特别倡立俸学会,顾名思义,就是进学如工作,可支取俸禄。熊氏俸学会鼓励族人积极捐赠乐输,醵金数百千文,并散发了106本捐赠义举的征信会簿,作为后代科举进身领取膏火津贴的依据。其中,对于入学散给束脩膏火标准都有明确规定,如发蒙者给束脩600文;做破题承题给束脩1000文;做起讲、提比中股者,给束脩1800文;做文章者,给束脩3000文;文生员肄业帮给4000文;文生童在凤仪书院肄业者,帮给膏火钱4000文;在豫章书院肄业者,帮给8000文。[34](卷首《议定散给束脩膏火章程》)此外,还制定了不同层次举业成功的“贺仪”标准,如文武入泮,送雀顶钱2千文;文生员补增,送1千文;文生员补廪,送10千文;恩拔岁副优贡贺仪3千文;中乡榜4千文;中会榜6千文等。[34](卷首《议行贺仪馆谷章程》)前引南平刘氏家族的文会,同治五年再次扩大规模,刘香远在《义学会记》谈到该会散给进学子弟的束脩津贴,“凡从师者给束脩有差”[32](卷首《尚义录》)。若其会簿流传下来,则具体奖励力度和标准应一目了然。
为给家族子弟科举应试提供免费食宿,经济条件宽裕的家族文会还在县城、府城甚至省城建试馆,如前引芳塘熊氏家族和宣风星溪卢氏家族均在县城和府城建有家族试馆,以便安顿本族应试举子。这种家族试馆是官府鼓励的,乾隆二十八年,江西省垣各姓大成祠奉例通禁,因废宗祠改为公馆,天宝龙岗邹氏在南昌所建宗祠便改为试馆。[6](卷末《祭产》)乾隆年间天宝栿溪吴遗宝为其家族在瑞州府建了一所试馆。[35](卷一六《人物志·善士》)道光六年朝廷钦封“义士”、天宝墨庄刘圣文倡导族众在瑞州府城和宜丰县城分别建造两所试馆,“寓合族应试者”,但也为同乡举子提供住宿便利,所以“乡党邻里深感佩焉”。[19](卷一九《人物志·义士》)宜丰县城漆德辉,在省垣“修一族试馆”[19](卷二五《漆公孝传》)。这些为宗族子弟赶考提供食宿便利的试馆,都是在宗族领袖人物感召下,以文会、祠会或试馆会筹资兴建的。如与宜丰紧邻的上高大塘况氏家族在瑞州府兴建的试馆,便是该族观文会和各房支图甲捐建的,专为士子应考而设,平常除了在瑞州凤仪书院读书子弟可以居住外,其他人一律不许在内逗留。[36](卷首《试馆议规》)芳塘熊容斋翁族众在瑞州府建的筠阳试馆,也是为了给族中子弟赴府试提供便利而建,其议规也同况氏一样,除了在府城高安的凤仪书院就学子弟可以入住外,平常不许其他族人盘桓驻足。与况氏试馆兴建资本不同的是,熊氏试馆全部是族中各会款为本钱,而况氏则偏重于按照图甲田亩量捐而来。[26](卷首《试馆条规》)宜丰全县熊氏大宗祠则在省城南昌棉花巷建有熊氏试馆,经过近百年的运转,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仍为熊氏学生旅居省城的主要居所。[37]
文会兴盛与否,是衡量一个家族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文会作兴人才,从设族塾书院等义学机构,到奖励科举功名津贴和建造家族试馆,全方位服务于科举人才打造的每个环节。正是有了文会的全力支持,族内子弟无论家境贫富,均有望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如墨庄刘拱宸祖上世代农耕,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和族中文会的奖励支持,考取进士宦囊渐丰后又反哺宗族义会,慷慨捐助巨额银两扩大文会规模和功能。[19](卷二五《柏源刘公传》)由于进士知府刘拱宸和举人知县刘如玉的大力提携,墨庄刘氏子弟备受鼓舞,人才辈出,使墨庄刘氏在晚清县域政治版图中跃升为首户,县城熊、胡、蔡、漆四大家族垄断科举宦业风光不再。
四、乐善好施:宗族整合与地方善治
族会虽然以祭会、祠会、谱会、文会居多,但族会兴盛起来后,其范围囊括族众生产生活各个方面,既有救饥、备荒、平粜等物质层面的,也有祭祖、祭神、兴学等精神层面的;既有禁赌、禁山、培耕等宗族治理,还有修桥补路和造船摆渡的公益考量。族会不仅加速了宗族整合,而且促进了地方善治,从宗族内部掀起了一股乐善好施的良好风尚,为宗族社会治理创新了管理模式。
族会的良法美意和独特功效,为族众的财产纷争提供了一个慈善归宿。在宜丰宣风刘氏族谱中,保存大量的“助约”,都是族人捐助族中祭会或文会,如乾隆十六年,刘步阳同弟媳阿胡立助约,将家产一半,早晚田种近6石捐与宗祠:“今因兄弟亲生无子,自愿同阿胡请凭族戚,将此业产内一半助与本族宗祠,致祭族祖,并作祖父维端、妣黄氏娇贞,父储兴、母吴氏茂贞,及己身步阳、妻李氏梅贞,弟嘉熬、胡氏二贞各夫妇附祭之资,任凭族众管业收租。”与此同时,刘步阳与弟媳阿胡将家产另外一半捐给文会:“将此业产内一半助与本族绅矜文武生童人等,以作兴贤、义学支给膏火盘费、捷发贺礼之资。”对于后一半财产,刘步阳服内人与宗祠发生激烈冲突,耗费大量财力,宗祠迫不得已给步阳立嗣,将剩余财产拨与后嗣管业。嘉庆四年,刘阿吴也仿照刘步阳的做法,将早晚田种2石产业之一半捐给宗祠,换取族、翁、己身三代入祠享祭的待遇。而另外一半捐与本族文会,作兴科举事业。在族中刘维英、维怡、维保、广兴、花兴、天申等共同书立的一份拨约中,交代了阿吴捐产助祭助学的原因:“缘族侄加铮与寡嫂阿吴互相构讼,二载弗休。”并交代了阿吴立继和衣食需费的数额及其具体安排,显然这种助约与拨约是抗衡族侄觊觎财产的最安全做法。
捐赠族会的善举背后,其实也有族众防范财产风险的绝妙安排。同治七年,刘明远将早晚田租20石的产业捐与祠堂,一半助祭,一半助学。值得注意的是,刘明远是有子孙的,他捐出财产时附有条件:“再批,此田祈族众发与明远子孙永远耕作交租,日后如有转承转顶情弊,任族每年实收租谷二十石正,不让升合,决无异说。”刘明远将子孙由地主变为佃户的大义之举背后,可能已预见到了败家子的未来结局。光绪三十三年,隆公裔孙刘宝才捐租20硕更富有戏剧性,由于赌博欠下巨额债务,其父生前禀明族房,与其给败家子还赌债,还不如捐族会,“缘因光绪癸巳年,被族相林、沂川等煽诱外边私赌一场,此时年幼无知,逼书手票数百余千文,厥后父知其情,随票禀族房,即将各业一应助族。后蒙族房劝解,虽有业产,焉有不愿其后。今父仙游,敢遗父命。爰是请族戚,愿将上载之业助与族内,向义会管业收租无阻,以杜后患。奈棍徒沂川等欲心未遂,隐匿所书手票数百余串,突于丙午六月间,复将此票掇出,会拐脚在家塞闹藉端滋事。蒙族属将此票作一并归转取消,如日后再有癸巳手票发现,概作废纸。倘有复行滋事,蒙族内尊斯一力承担。至所助之业,系自甘愿,并无反悔,而族绅矜亦毋得转行售卖,败此义举”[38](卷首《助约》)。
在宣风刘氏族众踊跃捐赠族会的善举中,我们看到了内在动机的多样性。深明大义且慷慨捐助者固然不少,但借捐赠避免财产继承纠纷和败家子消耗所带来的风险考量,也为数甚多。与其消耗暗亏且憋屈困窘,不如捐赠族会保有佃权而存生计。但族会吸收族众捐赠也存在一定风险,因为有些捐赠者本来就是以转移风险为目的。如嘉庆二十四年,蕉溪胡氏固公植下阿熊仝男允训将每年收益银15两的山场捐与国瑞公祠祭会,但到同治二年熊氏之孙胡上林侵害生事,族众因受讼累,将其祖母所捐祭会财产退还上林,缴回助帖。[22](卷一《产业》)
可以肯定,源源不断的族众捐赠,使得族会所积累的“众会”财产规模越来越大,成为宗族内外最大的地主,而这种公共地主又以各种性质不同的族会形式打理宗族公共事务,全方位影响族众的生产生活。族会的宗族伦理和经济理性决定了它的管理形式更具有股份合作的机制,在宗族整合方面更有优势,比家法族规的强制性更能凝聚族众的是,满满的互惠互利的利益分享和作为股份会员的参与意识。
族会的成功经验,显然也会传导地方社会的资源整合和治理改善。虽然祠会、谱会具有强烈的宗族封闭性,但文会、神会及其他公益善会其实是可以从宗族内部延伸到宗族以外的。如广贤乡柞溪黄氏倡立族内兴贤会,很早便有在府城瑞州筠阳和省城南昌设立试馆的想法,但黄氏并非势大望族,广贤乡乃偏远山区,也无甚巨族大姓,黄氏一族便将兴贤会扩充到广贤乡所在的三十七都、三十八都、三十九都、四十都等四都,并在该乡内建造兴贤祠崇祀乡贤主位,采取捐银买主位的方式筹集资金。黄氏主导的全乡兴贤会有了足够会股基金后,便在嘉庆年间兴建试馆,先由三十九都和四十都的兴贤会在瑞州府合建试馆,再由三十七都、三十八都、三十九都、四十都共建省城试馆,使广贤乡举子赴省试、府试均有栖息之所。[39](卷首《新邑广贤乡兴贤祠崇祀主位试馆志》)天宝刘氏、邹氏、吴氏等家族除了本族在县城建有试馆外,还主导兴建了全乡共有的远大图试馆,使得全乡士子有了共同切磋应考的安身之所。[40](卷首《天宝乡集义堂崇祀录序》)
族会向外延伸,可能在迎神赛会和公益路桥会等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沙溪廖氏家族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对各路神仙格外崇拜,在其族谱中记述,早在明末清初,廖氏与谈氏合建紫阳坛,祭祀周仙人显灵,成为天宝乡香火最旺的一处神祇。此外,五岳祠、三元殿、里社祠则是廖氏一族独立出资建的,这些神祠都是通过会的形式集资建成。[27](卷首《廖氏佔基》)石崖滩是宣风乡所在地,竹木夏布交易频繁,商贾辐辙却困于锦水分隔,从乾隆乙卯年开始,黎伯侯、宁仲春、卢德彰、刘辉璧等代表邻近四姓大族,量田租之多寡,鸠资成立永济会,造船摆渡以济行人。会簿分为集、腋、成、裘四本,四姓轮值管理。道光二年,除黎、宁、卢、刘四姓之外,何、叶、江等三族加入,在永济会的基础上成立继盛渡会。乾隆年间的永济会四姓会众88人,每人出资1千文,到道光年间续补会员12人,每人出资3.2千文。可见渡会便民利济的同时,余资滚动生息盈利不少,会股增值到三倍多。[41](卷首《会规》)光绪年间,兴修县城到芳溪的石路,成立路局和宏义会,在宏义会的捐助名单中,多是芳溪各族各姓的族会股份,如熊、蔡、彭、胡等大宗祠各捐助30~80千文不等,城中乐善于会20千,车上福兴桥会10千文,武曲洲竹会10千文,熊忻课会、熊氏两都保村会、哨前公禁会各4千文,培元会3千文,熊氏太保会、崇神会、淳公接风会、熊钦贤会、熊仪丁会、熊资荒会、熊定课会各捐2千文,熊欣丁会、叶文昌会各1千文。[42](卷首《乐输芳名》)举一乡之力,办一乡之事,由族会延伸而成的区域合作义会,为地方公益事业奠定垂久基础,“大江舟楫,山涧桥梁,所以便行人者,莫不有会。有会则有储积,可以垂久远也”[43](卷首《启》)。
另外,民间禁会因为需要宗族之间彼此紧密合作,往往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如禁山会对森林竹木的保护,往往是多个村落联合起来,禁止入山砍伐。如宜丰紧邻的万载黄田江禁山会便由两都百姓99人,在嘉庆十八年倡立,得到当时梅县令的赞赏,立会集资雇佣管山人和佃山人,照管竹木茶桐和山地木薯香菇等物植,到光绪二十五年禁山会运转如常,有力维护了山地民众的基本财产。[44](卷首《条规》)宜丰民间称风水林都叫禁山,所以砍伐禁山等于铲祖灭祭,家族内部的禁山会便是保护风水林的,如墨庄刘氏的鸡公岭禁山会,就是旨在保护鸡公岭风水林的。[18](卷一一《义产》)前引沙溪廖氏在村庄水口建有峦林保护风水,则通过峦林禁会来维持日常运作。[27](卷首《廖氏佔基》)而由临近各村落联合倡立的禁会,其保护的利益主要是山林植被和山地植物,如治平乡山田桥团的禁会便是如此,各姓民众鸠资立会,雇请专人巡山看管,厉禁偷砍树木、盗挖瓜薯,该会运转百年,到民国后期仍然是山田一带非常重要的公团法人。[45]天宝龙岗邹氏发起的培耕堂会,最初也是邹姓一族各房支44人发起成立,咸丰七年该会吸收外姓84人,成为天宝地方保护农业生产的重要公益会社,当时新昌邹知县特示禁令予以支持。[16](卷首《会内鸿名》)民国初年天宝墨庄刘氏留日学生返乡创办农林职业学校,取名培耕学校,其实正是源于培耕会在天宝的深刻影响。
从族众热情捐助族会,到地方民众积极鸠资参会,在乐善好施的道德光环下,会不仅在宗族整合和地方善治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融入了股份合作、轮值管理、账目公开的先进管理方法,所以许多民间族会和地方公益善会能够长久发展下来。有人认为会能垂久在于得人:“会之成败何常,惟视乎经理之人耳!经理非人,则会之已成者恒败;经理得人,则不特会之初起者必成,即会之已败者,亦不难挽其败,而复使之成。”[46](卷首《序》)其实,真正能够使经理人奉公守法的不单是人品,更重要的是会簿会册中开明宗义的详列条规,是那些先进的管理规则在约束经理人,使他们循规蹈矩,不敢逾越权限而侵渔贪渎。越来越多的民众乐意将私人财产转化为族会或地方公益善会的股份,与其说是乐善好施,毋宁说是一种理性的财产投保。拥有族会和公益善会的股份,不仅是一种道德和身份的象征,而且获得了财产保值和增值的安全保障。
五、结语:安顿族众精神家园的义产
从宜丰这一中小县份清代族会发展情形,可概见江西民间族会运行之一斑。而在土客矛盾尖锐的修水、万载等地迫切需要强化宗族内部凝聚力,倡立族会更是整合宗族的首选策略,并据此将宗族整合延伸到特定族群的联合。如万载的族董会和修水的文昌季(会)便被赋予特别鲜明的土客族群整合意义,万载族董会是民国时期万载土客各族统筹族会产业的管理机构,当然也就成为宗族管理机构,这种近似股东会管理的名称,正是万载土客各姓在清代积累大量祠会产业的现实需要。[47]而修水文昌季(会)则是修水客家怀远各姓在原有各族会基础上,以祭祀文昌帝君的名义将大家团结起来,首先为客籍子弟争取就地考试资格,其次奖励客籍子弟获得科举功名。[48]两地土客各姓都通过集腋成裘的筹资方式,将本金加成行息以保值增值,以之支撑宗族内外的各项公益善举,经理得当的众会产业一直传承到民国仍然发挥着特定的功效。毫无疑问,在清代江西,族会是安顿族众精神家园的义产,是宗族整合和地方治理的重要纽带。
江西族会的历史源头已难考究,但闻名遐迩的德安义门陈氏家族和金溪义门陆氏家族阖族共财的典范背后,肯定存在一个宗族产业日常管理的合理化问题,无论运作成败都会为后人提供借鉴。所以,敬宗收族不单是一句口号,要有稳妥的财力支撑。但过于张扬的宗族祠宇,也会引发官方的隐忧和查禁。清代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抚辅德奏称,在省会府城江西同姓共建的联祠有89个,一族独建的家祠有8994个。在这9083个各姓祠堂中,有稳定祠产支撑者6739个,其中收支略有盈余者760个。也就是说近75%的祠堂是由稳定祠产来支撑其日常运转的,其中8%的祠堂经费还有富余。[4](卷五五《覆奏查办江西祠谱疏》)但由于散立在省会府城的各姓祠堂为族人赴府与省控案提供栖身便利,“祠堂有费实为健讼之资,同姓立祠竟为聚讼之地”。所以,江西全境对各姓在省会和府城的祠宇一律查禁,要求改为平房店铺或应试举子的公寓。[4](卷五五《奏请禁江西祠宇流弊疏》)官方禁令使地方各宗族迅速调整策略,在省会府城的祠堂,“因废宗祠,改为公馆”[6](卷末《祭产》)。原来依托于宗祠举办的各项宗族善举,也开始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通过各色族会来解决具体宗族事务,避开官方对宗族祠宇的过分关注。笔者查阅江西各府县志后发现,江西民间族会多样性蓬勃发展也正是在乾隆年间以后,而仔细比对乾隆《新昌县志》和同治《新昌县志》对义士、善士、善举的具体描写,前者罕见提及会或族会,而后者则将举办族会誉为义士善举。显然,作为宗族款产——族会如此众多并被目为“众会”,实际上是规避官方查禁后的理智抉择。
族会因其支撑宗族内外各公益目的而获得族众的广泛参与,而族众在族会运作中又获得了可预期的会股收益,所以,族众对于宗族事务已不是一种单纯的道义责任,还有一份更强烈的参与感,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联性。族会运作的成功经验,不仅造福广大族众,而且惠及地方社会治理,正是有了族会这一义利兼容的合作经营方式,才为宗族势力冲突频繁的地方社会寻找到了和谐共处、同舟共济、互惠互利的现实纽带。由族而乡,由乡里而跋涉远方,会无所不在,并成为在外游子抱团取暖的精神归依。如景德镇陶瓷业的繁荣,会聚了江西各大商帮及各地能工巧匠的智慧,这些旅居景德镇的商人和工匠,平常聚居之所除了各属会馆祠社外,还有一姓一县一帮之会,诸如都昌杨姓会、陈姓会、徐姓会、黄姓会、程姓会、詹姓会、新建夏姓会、婺源汪姓会、婺源施氏会、南昌麦舟会、奉新令公会、安义清明会、安仁长城会、新建茭草会、都昌瓷行把庄会,等等。他们倡立各会在于切磋陶瓷工艺,坚守祖传秘诀,彼此周恤互助,将敬宗收族的高义复制到旅居之所。由于这些会本身具有的优势,所以直到景德镇新中国成立前夕仍然非常活跃,并承担许多公益责任。[49]
无论宗族整合和地方治理的理想具有多么崇高的道义价值,要付诸实现就必须要有经济基础做后盾。而经济基础并不仅仅意味着兴办善举的资本筹措,更在于筹措的资本能够永续利用而保值增值。清代江西族会这种融汇宗法伦理与经济理性的运营模式,有力提升了族众参与宗族事务的热情和动力,并将公益事业与私人股份利益巧妙结合起来,做到了义利合一、公私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