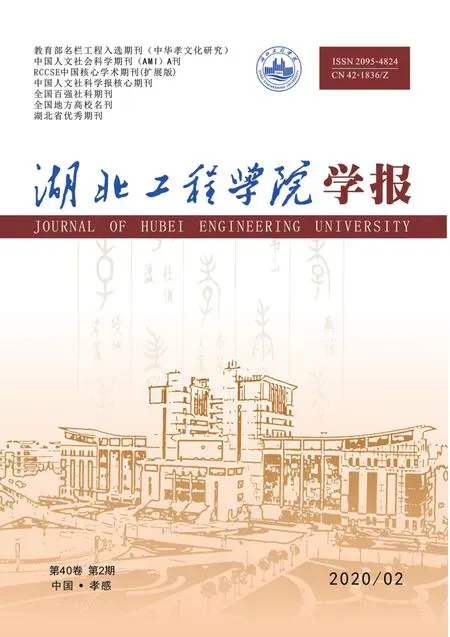论《西厢记》中莺莺张生的情之真
王 彬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9)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它和《红楼梦》一起被赵景琛誉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1]。明初贾仲明在续编《录鬼簿》时所作的追吊王实甫的《凌波仙》中赞誉《西厢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2]《西厢记》自问世以来,成为流传范围最广、版本最多的中国古典戏剧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仅明刊本就有56种,清代(1840年之前)刊本就有95种,其所受读者喜爱程度可见一斑。[3]学界把《西厢记》的不朽归结于其伟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西厢记》的主题思想表现为对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强烈反对,对封建门阀制度和礼教观念的尖锐批判和对青年男女追求纯洁美好爱情所表现出的斗争精神和坚强意志的颂扬。郭沫若在《〈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一文中指出:“人们殆不能不赞美元代作者之天才,更不能不赞美反抗精神之伟大!反抗精神,革命,无论如何,是一切艺术之母。元代文学,不仅限于剧曲,全是由这位母亲生出来的。这位母亲所产生出来的女孩儿,总要以《西厢记》为最完美,最绝世了。《西厢记》是超过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4]《西厢记》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深刻的思想体现于近乎完美的无与伦比的艺术之中。《西厢记》艺术性一方面表现为结构之严谨,情节之曲折。围绕追求自由爱情主题,作者将莺莺、张生、红娘和老妇人、郑恒之间的矛盾斗争,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误会冲突,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结构紧凑,情节精彩,引人入胜。金圣叹赞叹《西厢记》为天衣无缝、不见斧凿痕迹的“天地妙文”。李渔指出:“吾于古曲之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鲜瑕者,惟《西厢》能之。”[5]俄国柯尔施主编、瓦西里耶夫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说:“单就剧情的发展来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即使在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到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6]另一方面,《西厢记》的艺术性还表现为文字的简洁而优美。《西厢记》留下了众多传唱千古的优美句子,如描写离别之苦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等。吴梅论王实甫《西厢记》,说它“以蕴藉婉丽,易元人粗鄙之风”[7]。林黛玉认为“但觉词句警人,馀香满口”[8]。《西厢记》的经典还在于其语语学院教授。
言之简练,臧晋叔《元曲选序》说《西厢记》“不可增减一字,故为诸曲之冠”[9]。上述学者从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思想,紧凑与严谨的结构,简洁与优美的文字等角度对《西厢记》的经典性进行的解读都毫无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西厢记》中莺莺与张生之间情的真切也是其能够打动不同时代读者,成就其文学史上不朽丰碑的重要原因。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西厢记》中莺莺与张生之间的情真意切,学界尚鲜有涉及。有鉴于此,笔者拟就王实甫如何彰显莺莺与张生之间的情之真进行简要的剖析,以飨读者。
一、莺莺与张生情真意切的建构路径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庄子曾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10]《西厢记》动人之处之一就在于张生与莺莺之间的情之真。《西厢记》以情为一篇之骨:有张生对莺莺的一见钟情,有两人之间的相思之情,历尽风波的两情相悦,离别之情,直至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完美结局。《西厢记》主要通过以下路径彰显了两人之间的真挚感情。
首先,作者通过风景描写对情感的真挚进行了铺垫与强化。比如在莺莺出场时,作者以景导情,通过对暮春景色的描写(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导出了莺莺的思春和伤春之情,对莺莺与张生之情进行了铺垫。在长亭送别张生赴京取应时,作者以一幕萧瑟的晚秋之景强化了两人之间令人肝肠寸断的离别之情(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毫无疑问,作者对残春及晚秋风景的描写并非纯客观的风景描写,通过写景,作者使景的意象与主人公的情感特征实现了契合,通过情景交融强化了情这一主题,使得情显得更为真切。
其次,作者通过对莺莺貌美和张生才气的描写使张生与莺莺之间的炽热而真挚的感情显得甚为真实。唐代以来的恋爱标准是郎才女貌,李白《代别情人》曾云:“我悦子容艳,子倾我文章”。在莺莺出场部分,作者对莺莺的美貌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渲染,从而使张生的一见钟情显得顺理成章而颇为真实。对莺莺出场时具体的静态外貌描写虽着墨不多(“宫样眉儿新月偃,斜侵入鬓云边”“樱桃红绽,玉粳白露”),但首先从侧面写莺莺按照皇宫里流行的样式描眉,眉毛像一弯新月且眉长入鬓,可谓翩若惊鸿,然后描写其樱桃小口,齿白唇红。莺莺的美貌还表现在其举止上,其说话“未语人前先腼腆……半晌恰方言。恰便似呖呖莺声花外啭”,其走路“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未语先腼腆,把莺莺的大家闺秀之风和娇羞之态显露无疑,黄莺般的声音足见莺莺声音动听,“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展现了莺莺走路时的可爱(可人怜)样子。事实上,莺莺之美,可谓美名远扬,孙飞虎正是因探听得莺莺“眉黛青颦,莲脸生春,有倾国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颜”才因色起意而欲掠莺莺为妻。莺莺之美使得张生的一见钟情显得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张生见到莺莺的感受是“著人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谁想著寺里遇神仙”,“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世间有这等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乎”。莺莺的国色天香让张生失魂落魄,张生以为遇上的是观世音、神仙,表明莺莺已经美到让张生惊为天人的程度,从而使张生的一见钟情、一往情深乃至相思成疾显得顺理成章。如果说莺莺的国色天香之美使得张生的情自然而然的话,张生之才则使得莺莺的意切水到渠成。张生以“萤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满腹文章”的形象出场,及至后来,其赋诗被莺莺盛赞“好清新之诗”,危难之时,智退贼兵,一曲《凤求凰》让莺莺觉得“是弹得好也呵!其词哀,其意切,凄凄然如鹤唳天。故使妾闻之,不觉泪下”,直至后来金榜题名,都充分彰显了张生的才华横溢。如此才子,怎能不让正值思春之际的女子动情,张生之才也使得莺莺情愈真,意愈切。
再次,作者通过一些细节描写实现了对张生与莺莺之间真挚感情的生动描绘。我们以作者对张生两次等待莺莺、张生赴京取应时莺莺的临别之情及莺莺对张生欲迎还拒的细节描写为例。张生从红娘带回的莺莺回简(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中揣摩出莺莺相约花园。张生急于赴约,心中怅恨时间过得太慢:“恨杀鲁阳贪战,不教红日西沉。……安得后羿弓,射此一轮落!”张生觉得时间太慢,恨不能得后羿弓射落太阳。其急于见到莺莺的心情跃然纸上。在经历莺莺的赖简风波后,张生收到莺莺的第二次书简:“休将闲事苦萦怀,取次摧残天赋才。不意当时完妾命,岂防今日作君灾?仰图厚德难从礼,谨奉新诗可当媒。寄与高唐休咏赋,今宵端的雨云来。”张生从书简中领悟出莺莺的相约共赴巫山之意,欣然赴约。在第二次赴约时,张生等待莺莺时依然是急不可耐。“僧居禅室,鸦噪庭槐。风弄竹声、则道似金珮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意悬悬业眼,急攘攘情怀,身心一片,无处安排。……数著他脚步儿行,倚定窗棂儿待。”乌鸦的叫声很烦是以景写出了张生焦躁之情,张生听到风吹竹声,以为是莺莺走路时金珮做响,看到月光下花的影子,以为是莺莺到来,倚在窗棂边,准备数着莺莺的脚步声等莺莺的到来,此情此景足见张生用情之深,其情义之真诚可谓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在张生准备赴京取应时,老夫人安排了一次送别的宴会,作者对宴会上莺莺在张生临别之际的苦闷之情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想著俺前暮私情,昨夜成亲,今日别离。我谂知这几日相思滋味,却元来此别离情更增十倍?”“若不是酒席间子母每当回避,有心待与他举案齐眉。虽然是厮守得一时半刻,也合著俺夫妻每共桌而食。眼底空留意,寻思起就里,险化作望夫石。”“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伯劳东去燕西飞,未登程先问归期。”临别之际,莺莺感觉别离情更胜相思十倍,近在咫尺,虽有心举案齐眉,却只能“眼底空留意”“险化作望夫石”,以至于泪湿青衫,未别离先问归期,足见莺莺对张生的难舍之情。作者对莺莺哀婉凄恻的惜别之情的精彩捕捉使得莺莺情之真切可谓达到极致,其伤离别形象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莺莺对张生的情之真还体现在其传统礼教束缚下对张生之情的欲迎还拒。囿于传统礼教的束缚,莺莺尽可能把对张生的情压抑在心底,从而屡次对张生的热情表现得较为冷漠。比如在红娘第一次把张生的书简带回来时,莺莺“开拆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足见其对张生之情是心里欢喜的,但在红娘面前表现得勃然大怒:“小贱人,这东西那里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贴儿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当红娘看到她勃然大怒时,便道要去夫人那儿出首张生。莺莺却道:“我逗你耍来。……张生两日如何?”本来表现出的是勃然大怒,看到红娘欲出首张生却又道是在玩笑,并马上表达了对张生病体的关切,足见其怒非真而其情却真。就情的描述而言,作者反弹琵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鉴于莺莺相府小姐的身份和传统礼教的束缚,莺莺的欲迎还拒使得她对张生的情表现得更加真实。
最后,作者通过把张生与莺莺的情置于合理的冲突解决之中更加凸显了两人之间的情之真。冲突是戏剧生命力的源泉,没有冲突就没有成功的戏剧作品。戏剧中的冲突指的是剧中人物行为动机之间的矛盾纠葛及人物自身性格的内在矛盾。冲突能够制造悬念,吸引观众,形成强烈的戏剧效果。王实甫在《西厢记》中通过一系列矛盾冲突把张生与莺莺之间的情之真表现出来,塑造了不朽的经典爱情人物形象。一方面,两人之间的情是在与传统礼教之间的矛盾冲突解决中逐步升华的。传统礼教要求女子的婚姻应由父母做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在婚姻方面不遵从父母之命被认为是可鄙的。《孟子·滕文公下》曾云:“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11]在遇到张生之前,莺莺的父母已经安排好要把莺莺嫁给郑尚书的公子郑恒为妻,只因父亲去世,丧服未满,不曾成禾。莺莺与张生之间的情严重违背了遵从父母之命的传统礼教要求,王实甫通过情礼冲突的合理解决,谱写了一部爱情经典,彰显了张生与莺莺之间的情之真。莺莺出场时是老夫人要求红娘看看前面庭院无人时带小姐去散心的,说明莺莺一贯是秉承不出闺门之训等礼节的,她与张生的相遇是一种巧合,是不违于礼的。两人相识后虽情愫暗生,但不合于礼,于是作者安排了孙飞虎抢亲,老夫人为了不辱没家门而出于无奈允诺有能退得贼兵者便送莺莺为妻。后来张生应募且驰书破贼,使得两人之情合之于礼。老夫人赖婚后,在得知莺莺与张生成就欢爱,欲责罚红娘时,红娘也用老夫人的失信据理力争。老夫人要求张生赴京取应,张生金榜题名后,郑恒妄生诽谤而骗婚,杜将军晓之以礼,斥之为“行不仁之事”,终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两人之情本不合礼,但作者通过一系列的冲突解决,赋情于礼,使得两人之情愈显真实。上述冲突是人与人(张生、莺莺与老夫人和郑恒)之间的外在冲突,作者通过外在冲突的解决实现了不合礼的情的合礼化,使两人之情显得颇为真切。对妙龄青年而言,即使不合于礼的情也可以战胜理智,作者通过莺莺心里的内在冲突强化了情真的效果。莺莺与张生交往过程中自相矛盾的行为即彰显了其内心的矛盾冲突,如莺莺在第一次回简中邀张生“待月西厢下”,见到张生时却怒斥道:“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在红娘代为求情后又道:“先生虽有活人之恩,恩则当报。即为兄妹,何生此心?万一夫人知之,先生何以自安?今后再勿如此。若更为之,与足下决无干休!”在以兄妹之礼斥退张生后,张生相思成疾,莺莺却又写一简:“仰图厚德难从礼,谨奉新诗可当媒”,告知张生自己“难从礼”,以新诗做媒。莺莺的心口不一是她心里情与礼矛盾冲突的表现,最终情战胜了礼(难从礼)的心路历程使得莺莺之情显得更加真实。
二、结 语
王实甫通过风景描写实现了对莺莺与张生之间情感真挚的铺垫与强化,通过一些细节描写实现了对张生与莺莺之间真挚感情的生动描绘,通过对莺莺之美和张生之才的描写使两人之情合于自然人性,通过把张生与莺莺的情置于合理的冲突解决之中使两人之情从不合于礼走向合于礼。张生与莺莺之间的情真意切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西厢记》的经典,使其成为后代写情作品的典范,为后世作者广为借鉴,“到了明清,凡写男女情事的戏曲、小说,很少有不受《西厢记》影响的”[12]。《西厢记》所表达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爱情愿景甚至被写进了西湖月老祠的对联:“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其影响力之深远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