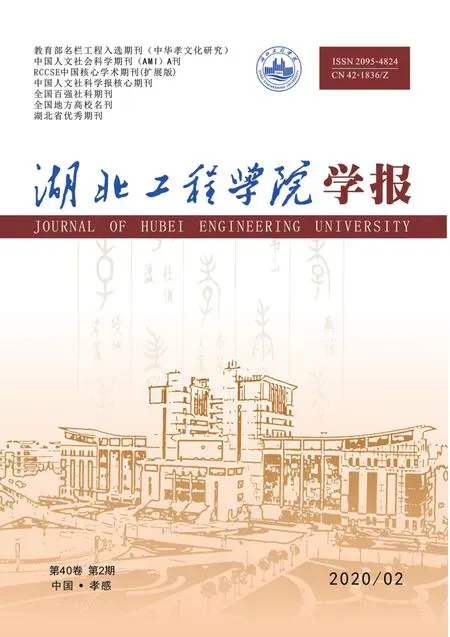明儒刘宗周对孟子思想的阐发
刘 奎,田 霞
(中国孟子研究院,山东 济宁 273500)
唐君毅先生认为周濂溪为宋明理学之开山祖,而刘宗周则为宋明儒学最后之大师。[1]牟宗三先生亦肯定刘宗周的历史地位,认为其“上接周、张、明道,以《中庸》《易传》合《孟子》《大学》”。[2]刘宗周注重借鉴先儒的观点和思想,并将其中的许多元素加以统合,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学术体系,具有“消融统合”的特点。因此造成其著作多复杂而晦涩,除其弟子黄宗羲等人之外,不为世人所重。在孟子学的发展史上,他虽没有专门研究《孟子》的著作传世,但作为朱熹、王阳明之后儒学“道统”观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中却早已打上了孟子学的烙印,其孟学思想也正是在其对学术的“消融统合”中加以呈现。其孟学思想影响了黄宗羲等众弟子,尤其是黄宗羲作《孟子师说》,就自认为是承继老师刘宗周思想而来(《孟子师说》题辞云:“先师子刘子于《大学》有《统义》,于《中庸》有《慎独义》,于《论语》有《学案》,皆其微言所寄,独《孟子》无成书。羲读《刘子遗书》,潜心有年,粗识先师宗旨所在,窃取其意,因成《孟子师说》七卷,以补所未备,或不能无所出入,以俟知先生之学者纠其谬云”)。因此可以看出,刘宗周本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在孟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亦亟需后人加以梳理。
一、刘宗周行状
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起东,号念台。明代绍兴府山阴人(今浙江绍兴人),因曾在山阴蕺山讲学,被世人尊称“蕺山先生”。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以行人司行人,累官至顺天府尹、工部侍郎。其从政时间很短,为官清廉刚直,有操守。一生多数时间从事讲学活动,其弟子中最著者有陈确、张履祥、黄宗羲等数人。因其讲学之所在蕺山,后世将他跟他的弟子称为“蕺山学派”。在其没后,相关著作亦由其弟子相继编撰整理,有《刘子全书》《刘子全书遗编》《刘子节要》《刘子粹言》等数种存世。
一方面,面对明末混乱的政治局面,刘宗周勇于上疏直言,针砭时弊,讨伐阉党,声援东林士人,对崇祯帝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称其“耳目参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凭一人之英断,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衷其是”[3]216,由此触怒天威,最终被革职为民。明亡后,清军南下,绝食而殉国,气节为时人称道。另一方面,明末阳明学耸动天下,阳明众弟子中成就最大者为王艮和王畿二人,他们最终将阳明学发扬光大,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黄宗羲认为也由于此二人,阳明学的宗旨渐失,特别指出“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之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4]。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颜山农、何心隐等,最终破除封建伦理束缚,成为儒们正宗眼中的异端。有学者认为,他们所倡导的,无论是玄虚证悟,还是天然率性,都远离了宋明理学家所理解的实践理性主义本质。[5]虽然刘宗周在学术渊源和旨趣上,与湛甘泉、王阳明的心学一脉相切近,但对阳明学却是“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辩难不遗余力”[6]464。正是在明末阳明学狂乱的境遇下,刘宗周力图对晚明的学术风气进行匡正,对宋明儒学进行了总结,牟宗三先生称许其为“宋明儒学最后之殿军”[7]。
二、刘宗周对孟子思想的阐发
面对明季思想混乱的局面,刘宗周力图正人心,挽救时局。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与孟子相合,最后若伯夷、叔齐之类,为仁义而殉道的气节,令世人敬畏。其作《五子连珠》[6]323,特别称赞宋代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传孔孟之道,与孔孟同出一源。孔孟如天上之二曜,光耀千古,而“五子”如经纬加以辅助衬托,并对孔子之后的道统追求进行总结,认为是“求仁”而已。他通过对“五子”的评价和赞许,继承了宋儒以来的道统学说,并颇有以“道统”自任的意味,体现了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承继“道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造就了其对宋明儒学整合贯通的学术成就。作为宋明儒学嫡脉,在其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想中,每每展现出《孟子》文本的征引,经常流露出对孟子思想的认可。其对孟子思想的阐发,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发展了孟子的“心性”理论,重视“理气心性”一元;二是发展了孟子“诚”的思想,强调“诚意慎独”的工夫;三是发展了孟子的“圣人”观,注重“证人”的圣人境界追求。
1.重视“理气心性”一元的本体。孟子最早提出“性善论”“养气说”等思想,并特别重视“心性”等概念。(1)孟子对理、气、心、性之论述均有涉及,诸如:“理”的命题,“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孟子·滕文公上》);“气”的命题:“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孟子·告子上》),“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等;“心”的命题:“不动心”、“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求放心”(《孟子·告子上》)等;“性”的命题:“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孟子·尽心上》)。这些思想都为后来的宋明理学家所继承,尤其是朱熹、陆九渊二人。朱熹重视《孟子》一书,最早将《孟子》辑为“四书”之一。陆九渊则明确表示,其学“因读《孟子》自得之”[8]。朱熹和陆九渊对孟子思想中的“理气心性”等概念加以继承,分别提出了“性即理”和“心即理”针锋相对的命题。刘宗周在此基础上加以融合,提出“理气心性”一元的思想。
首先,刘宗周继承了传统中的“理气之辩”,始终坚持理气一元,坚决反对理气为二。在他看来,“阴阳之气一也,而其精者则曰神与灵,其粗者则物而已”。阴阳统一于气之中,同时创生人和万物,但有粗细之别。然而,“惟人也得其气之精者为最全,故生为万物之灵,而礼乐仁义从此出焉”。只有人得天地之气最精纯,从中生育礼乐仁义等良知美德,是先天圆满的。“惟人禀阴阳之精而生,故为万物灵。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相对人来说,物仅得天地之气的一部分,是不圆满的。因此,人与物相较,多了先天的纯粹性。这种圆满纯粹性,在孟子思想中有同样的表述。孟子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刘宗周这种阴阳一气,创生万物的观点,就是承认了礼乐仁义等道德主义,先天具有纯粹性,是对孟子“天爵”思想的承继和延展。同时,刘宗周认为理气相依相生,但是“一体两分”,不离不即。因此,他反对“理在气先”和“理在气外”的观点,理只能存在于气之中,义理之性只能存在于气质之性当中,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性,其明确指出“道心”只能是指人的“本心”。故而,他说“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知此则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性”[6]410。与此同时,他试图打破理、气、心、性之间的界限,将他们合而为一,融汇贯通,体现了他浓烈的一本论倾向。因此,他承继孟子,接续明代以来关于“心性”伦理的讨论,认为性只有气质之性,义理之性才是气质之性的本质,言心的话便是言“人心”“道心”。“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气质、义理,只是一性。识得心一性一,则工夫亦一。”[3]1583他这种逻辑表达形式,与孟子言“性善”论——以善为性的表达方式具有相似性。同时,他还认为,理气心性一体,“离心无性,离气无理”,“只是心之性,决不得心与性对”。在理气心性的讨论中,性不仅是心之理和心之本源,同时能够引导气,并使之条理。但是又有所分别,“虽然气即性,性即气,犹二之也”,以“四端”为体现的“心”,属于内在,是外在气质变化的动因。虽需要依靠知觉来呈现,但并不是说在知觉之外,另有“四端”可言,而是“性一心耳,心一知耳”,在刘宗周这里,理、气、心、性等最终被打通,归为一元。
其次,刘宗周借用孟子的“四端”理论,认为“性情”一体,提出了“性情”相生相克的观点。他将伦理道德与人性情感联系并统一起来,把孟子所提倡的“四端”——仁义礼智等伦理规范及道德观念,与人性情感中的喜怒哀乐等情绪融而一体。认为,天地之间充实的只是一气,万事万物皆是其所化,气聚形成万物的实体,其中包括人。性,附着于人体器官之上,最终形成了“仁义礼智”。他直接引用孟子对“四端”的论述:“仁非他也,即恻隐之心是;义非他也,即羞恶之心是;礼非他也,即辞让之心是;智非他也,即是非之心是也。是孟子明以心言性也。”并批评后人不能将“心”“性”有机结合起来,融会贯通,而是“必曰心自心,性自性,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转和会之不得,无乃遁已乎”,结果离孟子的本旨越来越远。他用《中庸》的“中和”来统合《孟子》中的“四端”:“至《中庸》则直以喜怒哀乐,都出中和之名,言天命之性,即此而在也,此非有异指也”[6]280,得出的结论认为恻隐是喜之变,羞恶是怒之变,辞让是乐之变,是非是哀之变,把“四端”和“四情”对应起来,并把这作为子思“以心之气言性”的宗旨。为了进一步证明其“情性”一体的观念,他继续借用孟子“四端”理论加以阐述,把仁义礼智之“四端”、喜怒哀乐之“四情”、春夏秋冬之“四时”相对应,气在其间,将它们彻底贯通起来。“喜怒哀乐四者,即仁义礼智之别名。在天为春夏秋冬,在人为喜怒哀乐,分明一气这通复,无少差别。天无春夏秋冬之时,故有无无喜怒哀乐时,南面而终不得以寂然不动者为未发,以感而遂通者为已发。”[6]258在将“四端”“四情”“四时”对应以后,刘宗周进一步将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恻隐,心动貌,即性之生机,故属喜,非哀伤也。辞让,心秩貌,即性之长机,故属乐,非严肃也。羞恶,心克貌,即性之收机,故属怒,非奋发也。是非,心湛貌,即性之藏机,故属哀,非分辨也”。并最终得出结论:“四德相为表里,生中有克,克中有生,发中有藏,藏中有发”[6]421,即,情性一体一元,四德、四情、四时“相生相克”。
2.强调“诚意慎独”的工夫。“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在先秦时期,孟子较早提出了“诚”的概念,且加以论述。在这里,孟子并没有对“诚”的概念作具体的分疏。“诚”,既可能是道德本体——“天之道”,同时又可能是实现本体的工夫。“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通过“诚”这一工夫,是能够达到“仁”“乐”等理想境界的。关于“意”的论述,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的文学评论观,强调文学诠释中要实现主体自我意识与文本他者的统一。刘宗周对孟子“诚”“意”等思想加以继承,在以《中庸》《大学》统合《孟子》之后,特别强调“诚意慎独”的概念。作为刘宗周学术旨趣中的重要命题,“诚意慎独”体现了其为学之方和宗旨。在刘宗周死后,其弟子黄宗羲和其子刘汋在刘宗周一生学术的总结上产生了分歧(2)黄宗義将刘宗周一生为学的宗旨归结为“慎独”:“先生宗旨为‘慎独’。始从主敬入口,中年专用慎独工夫。慎则敬,敬则诚。晚年愈精微,愈平实,本体只是些子,工夫只是些子,仍不分此为本体,彼为工夫,亦并无这些子可指,合于无声无臭之本然。”而其子刘汋则坚持刘宗周学术宗旨“三期说”:“先君子学圣人之诚者也。始致为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独,而晩归本于诚意。”,造成了后人对刘宗周“主敬”“诚意”“慎独”等概念的重视程度有不同的认识,但是“诚意慎独”在刘宗周学术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在刘宗周“诚意慎独”理念中,其对孟子的阐发,重点在于对“意”的探讨上,最终发展成了“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3]170的“独体”思想。
首先,刘宗周发展了孟子“心之四端”、“以意逆志”的思想,在处理“心”“意”关系上,与朱熹(3)“意者,心之所发也。”(见朱熹:《大学章句》)和王阳明(4)“心之所发便是意。”(见王阳明:《传习录》)以“心”为体,以“意”为用的观念不同。刘宗周特别突出“意”,认为“意”为“心”之主宰,并且“意”为“心”之本根。结合自身所处的时代,刘宗周希冀能够对阳明心学的“心意”观有所匡正,因此晚年作《良知说》对阳明学加以臧否:“只因阳明将意字认坏,故不得退而求良于知;仍将知字认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于心。”他认为,阳明对“意”没有探求清楚,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地去探求“良知”。在这里,刘宗周凸显了“意”的地位,消解了“良知”在阳明学中的重要性。他承认孟子以来对“心”重要性的定位,认为“心”能够随处变化“能方、能园、能平、能直”,具为产生天地、四气、万类、五常的能力。[3]241然而就“心”“意”的关系上来讲,“意”在“心”之上,是“心”主宰,是天下万物的根基所在。所以他说“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6]360。为此,其对“意”添加了自己的注脚,将“意”作为“心”之主宰,进一步进行阐述。他说:“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止言心,则心只是径寸虚体耳。著个意字,方见有了定盘针,有子午可指”[6]337,“心如舟,意如舵”[6]467,有“意”为主宰的“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若单纯言心,那心便只是一堆血肉,只是径寸虚体而已。心就如同船,可以载人载物,但是若没有“意”作为指针,那么就会失去方向。“意者,心之所存,非所发也”[6]337,“心之主宰曰意,故意为心本”。同时,他反对“意”为“心”所发的观点,主张“意”为“心”之所存,“意”为“心”之本。通过上述两个对“意”的形象比喻,明确反对了前儒重心不重意的传统,阐述了“意”为主,“心”为仆的思想倾向。
其次,在“意”性质的探讨上,刘宗周将“意”等同于“至善”,完全是延续了孟子“性善论”圣学血脉,并且对“意”的阐述路数,完全是复孟子前辙。在孟子的“性善论”当中,性善有“性是善的”和“以性善为性”两种倾向。但是孟子更加肯定的是人皆有“善端”,如“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毫无外在情感干预下本心所呈现的“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扩而充之,可以为“仁政”“善政”。但是“善”在接触具体事物后会产生私欲,甚而产生“恶”,所以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孟子·告子上》)。人性会在富岁、凶岁差异这么大,在孟子看来,不是在天性本质的差别,而是因为“陷溺其心者”,即丢掉了本心。孟子在“性善论”中所认可的“善”或者“至善”,不断为后世学者所继承和演绎。在王阳明那里,变成了“良知”和“致良知”,在刘宗周那里则变成了“意”。在人何以造成“善”“恶”差别的问题上,王阳明注重“未发”和“已发”,认为“未发”的是纯为善的“良知”,“已发”是与物象接触后形成的无定向的念头,可以为善,亦可以为不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的,可以为不善的。”[9]而刘宗周则用“意”消解了“良知”,认为“意”是至善无恶的:“意者,至善之所止也”[6]390。阳明“四句教”中“有善有恶意之动”,认为“意”是造成善恶差别的源头,刘宗周对此极不认可,反对把“意”作为“心”的已发状态。在他看来,只有在善恶的观念产生之前,做好修养的工夫才有存在的价值。因此,需要把修养的工夫继续往前推进,一直到自我主体的内心最深处,在恶的念头产生之前就加以“诚”的工夫,真正落实到“意”的本体上,最终才能达到至善圆润的完美境界。只有这样,修养的工夫才有意义。
在孟子“诚”概念中,虽然“诚”具有即工夫、即本体的倾向,但是并未详细说明。刘宗周在统合《中庸》《孟子》《大学》之后,形成了“诚意慎独”的思想,把原来作为工夫和方法的,一般意义上只具有道德修养意义的“诚意慎独”进行统合,最终发展成为即本体、即工夫的“独体”学说。刘宗周之前的宋明儒者,包括朱熹和阳明,延续了《中庸》重视“慎独”的传统。在朱熹(5)“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见朱熹:《大学章句》)那里,“慎独”不再仅仅是个人独处的“独”,而是变成了人、己相对之时的“独”,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把工夫离析为两段,失之支离。[10]而王阳明(6)“只是一个功夫,无事时故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见王阳明:《传习录》)则用“良知”取代了“慎独”,并仅仅把“慎独”作为一种修养的工夫。刘宗周的“诚意慎独”思想,对朱熹和王阳明都进行了批评,尤其是对阳明学说进行了修正,他用“独”取代了“良知”。所以,他的学生陈确才会评价说:“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11]清人彭启丰则明言刘宗周与王阳明的这种差异:“阳明教人致良知,而先生教人证独体。”刘宗周说“独者,物之本”,把“独”最终上升为产生宇宙万物的本原,最后“独”由一种功夫,成为具有唯一性、至上性和绝对性的实体存有。但是这种实体存有,最终还要与“意”,也就是“至善”结合起来。所以他说:“独即意也”。刘宗周将“独”解释为“意”,以“独”来赋予“意”的形而上的含义。这也就是说,刘宗周是在贯通道德本体与宇宙本体的意义上将“意”界定为“独”[12]。在孟子“性善论”基础上,刘宗周利用“诚意慎独”的观念,贯通《大学》《中庸》,对自己同时代陷于流弊的阳明心学进行修正,特别是克服了王艮以情识为“良知”和王畿将“良知”玄虚化的弊端,最终打通了“诚意”“慎独”之间的界限,以“至善”为根基,形成了“诚意慎独”的思想体系,突出和强化了孟子以来儒家的道德主体意识。
3.注重“证人”的圣人境界追求。孟子对先秦时期的几位先贤进行了评价,认为伯夷是“圣之清者”,伊尹是“圣之任者也”,柳下惠是“圣之和者”,然而孔子最伟大,为“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孔子能够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他的人生理想便是做孔子一样的圣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成圣成贤并非高不可攀,而是“圣人与我同心”,每个人通过尽心、尽性,与外在的实践最大程度地结合,都可以实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优入圣域。故而,孟子之后千百年,追慕圣人,成为圣人,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的理想追求。朱熹从小便立志“学做圣人”,而王阳明在拜访了娄谅之后,亦认为“圣人可学而致”。因此,这种圣人观也被刘宗周所继承,其晚年作《人谱》以“证人”。证明人人只要充分认识到自身的尧舜之性,圣人人人可做,于此方能见“良知眼孔”。所以,他还说,学者应当拓开眼界和境界,眼下光景是要有“人禽之辨”的觉悟,堂堂做个“人”。每个人内在的善性和美德,天生圆满,为上天赐予,圣人与我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圣人于自身善性“完具”所以成圣,而凡人不注重修身“偶自亏欠”成为凡夫,并非是“生而非圣”。
首先,在“成圣”的道路上,刘宗周继承了孟子“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的强烈使命感,不仅自己立志要做圣人,还要帮助世人也成为圣人。所以他说“吾学亦何为也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因此,他怀抱理想,于崇祯四年(1631)在绍兴府专门创办了“证人社”,利用其“诚意慎独”的思想,用以“证人”,来做成帮助世人成圣成贤的事业。“宗周独深鉴狂禅之弊,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务以诚意为主,而归功于慎独。”[13]他希望通过教学实践与理论的双向促进,来凝聚世道人心,扭转王学未流空疏禅化的弊端。
其次,刘宗周认为,每个个体“成圣”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建立在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性善论”基础之上的。刘宗周借用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诠释,认为“盈天地间,本无所谓万物者,万物皆因我而名”。父、君这些伦理纲常,其实是与我内在的“孝父”“忠君”之心相合,是个人自我情感的真实流露。个人通过“反身而诚”的功夫,最终实现“万物非万物,我非我,浑然一体”的最高境界。同孟子一样,刘宗周认可人类自身德性的圆满无缺,得出万物与我浑然一体的论断,展示了其强烈的心学趣味。同时,他以桃李之仁化生万树为比喻,认为虽然“桃李之仁同禀一树”,能够化生千树万树,可是在具体到个体上,却显示出了差异性,有的“夭折而不成”,有的“臃肿而不秀”,“然其为天下桃李则一也。故孟子一言以断之曰性善”。虽然个人在后天发育上产生了差异,但是他们作为桃李的本质并没有差别,孟子将他们一概归为“性善”。在这里,刘宗周将孟子的“善”立为人极,作为独体和本原,即本体,即工夫,显示了其体用一源、知行合一的哲学倾向。
再次,在刘宗周看来,凡人最终没有“成圣”,完全是因为凡人没有恒心,在功夫上做得不够,最终使得“善性”被私欲蒙蔽,结果是如孟子所说“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梁惠王上》)。因此,他借用孟子的“义利之辨”“人禽之辨”加以演说,认为为学第一要事便是要明“义利之辨”,具体到个人行为,起心动念之际,具是天理呈现,学者应当“凛闲居而独处”,注意“慎独”的工夫,勘破“义利之辨”“人禽之别”,不要让积习陋俗蒙蔽了心性,失去了自我。因此,刘宗周认为修养的工夫要在生活小事上磨炼,不可有一时的松懈。“学不可不讲,尤不可一时不讲”,这些功夫要具体落实到行为践履中,外则父子、兄弟、夫妇等伦理关系中,内则“燕居独处,自心自讲”,时刻思考“如何而为食息,如何而为起居,如何而为圣、为狂、为人、为禽”等问题,不能够有一时的放空。如若不然“一时放却,便觉耳目无所施,手足无所措,大之而三纲沦,小之而九法斁”。刘宗周强调的这种自我省察与实践,通过事事物物上的不断磨炼,使个体在为圣、为狂、为人、为禽的问题上,最终成为修养工夫的自主选择。正是在这种日积月累不断的事上磨炼下,凡人亦可以臻于圣域,成为“圣人”,最终打破了凡圣之间“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的界限。在他看来,“君子存之,善莫积焉”,“人禽”之间的差异正是来自于“积善和积不善”的结果,知道“不善”加以改过,然后能够从内心的“善”端出发,最后能够达到“无不善”和“至善”,这样才能尽“人之学”,也就是所谓的“圣学”。最终在这里,借助对孟子思想的演绎,刘宗周肯定了周敦颐“主静立人极”观点,阐述了存善、积善,以别人禽,立于人极,成为圣人的圣学思想,体现了其孜孜不倦的圣人境界追求。
三、小 结
纵观刘宗周的整个学术思想脉络,其基本上是建立在孟子“性善论”的基础之上的,并且认为任何离心言性的心性主张最终都难免出离儒家性善宗旨。[14]明儒刘宗周坚持“知行合一”,不仅在思想上“继往圣,开来学”,是孟子思想的传承者,更是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一“大丈夫”理想人格的践行者。他坚持操守,崇尚气节,内外兼修。他不畏权贵,刚正不阿,明末家国破亡之际,效法伯夷、叔齐,守义而死,是孟子“仁义”思想的践行者;他笔耕不辍,讲学育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孟子“君子三乐”的拥护者,更是嶯山学派的开创者;他上承孔孟,融合诸家,系统总结和批评宋明理学思潮各家各派的思想和观点,集明代理学之大成。其既是明季王学的终结者,又是有清一代学术风气的开辟者,其学术涵养和精神面貌,时雨化之深远,甚至对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亦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