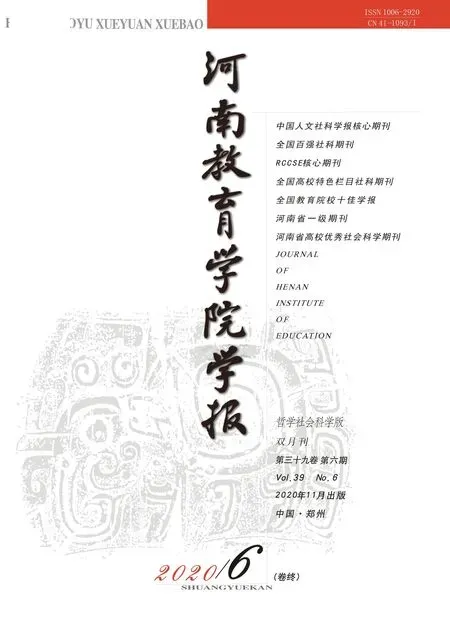“《诗经》即《乐经》”说简论
常恺蓉
《乐经》传为“六经”之一,汉代以来的古文家多将毁于秦火作为其消失的主要原因。也有学者持“《乐经》不亡”论或“散而不亡”论。“《乐经》不亡”论包括三个观点:《周礼·大司乐》即《乐经》,《乐记》即《乐经》,“六代乐舞”即《乐经》。前两个是古人观点,后一个是当代学者提出的[1]。“散而不亡”论则认为原《乐经》内容保存在《乐记》、三礼、《左传》、《国语》等书中。[2]汉代以来有些学者认为《乐经》即附着于《诗经》的一种乐谱,没有文辞。[3]3060在这些观点之外,尚有“《诗经》即《乐经》”的说法,当代学者少有提及,本文略加阐述。
一、起源于唐宋的“《诗经》即《乐经》”说
“《诗经》即《乐经》”的说法起源于唐代的孔颖达。《礼记》云:“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丧复常,读乐章。”孔颖达疏曰:“乐章,谓《乐书》之篇,章谓《诗》也。”[4]1257这种观点强调《诗经》与《乐经》关系的紧密,可以说是“《乐经》不亡”论中的《诗经》《乐经》一体论。
此后,南宋学者王应麟记载了胡寅的观点:
致堂胡氏曰:“礼、乐之书,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记》为《礼经》,指《乐记》为《乐经》。其知者曰:‘礼、乐无全书。’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诗》与乐相须,不可谓乐无书。《乐记》则子夏所述也。”[5]130
致堂胡氏即南北宋之交的胡寅,他批驳了“《乐记》为《乐经》”及“礼、乐无全书”的观点,认为《乐记》为子夏所作,显然不是《乐经》。所谓“无全书”是指《乐》没有独立的书,而是其他书的附属物,或者只是部分内容存在于在其他书中。胡寅认为《诗经》的特点是“诗与乐相须”,也就是唐孔颖达“诗是乐之心,乐为诗之声”“歌其声谓之乐,诵其言谓之诗”“有诗则有乐”[4]271的意思,即诗与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胡氏认为不能说“《乐》无书”,也不能说“《乐》无全书”。言下之意,《诗经》即《乐经》,二者浑然一体,是一本完整的书。
南宋哲学家、永嘉学派创始人薛季宣在《答何商霖书二》中说得更直接、更明白:
《诗》,古《乐经》。其文,古之乐章也。《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三百五篇,非主于声而已。[6]卷二四
薛季宣直接断定《诗经》就是《乐经》,《诗经》之诗文即乐章,这显然是承孔颖达遗义而更进一步。就是说,《诗经》以辞言之则《诗经》,以乐言之则《乐经》。依《尚书》的说法,“歌”“声”“律”都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诗》。所谓“三百五篇,非主于声而已”,指诗的主要任务是“言志”,而不是仅仅重视音乐。孔颖达则从重视音乐的角度谈这个问题,云“为诗必歌,故重其文也”[7]270,其疏“主文而谲谏”云,“‘主文’知作诗者主意,令诗文与乐之宫商相应也。……先为诗歌,乐逐诗为曲,则是宫商之辞,学诗文而为之。此言作诗之文,主应于宫商者。初作乐者,准诗而为声。声既成形,须依声而作诗。故后之作诗者,皆主应于乐文也”[7]271。孔颖达提出诗与乐相配的两种方式:一是先有诗文,后以曲相配;一是曲已确定,新作诗文以配。前者强调“乐文”配“诗文”,后者关注“诗文”配“乐文”。无论哪一种都必须重视“乐文”“诗文”的契合性。这与郑玄笺“主文”的意思一样。
二、明代刘濂、朱厚烷以来对“《诗经》即《乐经》”的认识
有学者认为:“明代《诗》学最有意义的贡献,且形成自己的特色,并不在经学的研究上,而在于这个时代的学者第一次从文学的角度审视这部圣人经典,以群体的力量改变了《诗经》原初经学研究的方向,开创了‘《诗经》学’的新航线,并将《诗经》的文学研究推向了高峰。”[8]这个分析是不错的,但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到,明代对《诗经》的研究,除了经学、文学两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恢复《诗经》诗乐舞一体的本来面目。也即,明代《诗经》研究至少有三个方面,即经学性、文学性、音乐性。
在明代,“《诗经》即《乐经》”说首先由刘濂及朱厚烷提出、分析,并且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实践。如刘濂在《乐经元义》一书中提出:“六经缺《乐经》,古今有是论矣。愚谓《乐经》不缺,三百篇者,《乐经》也,世儒未之深考耳。”[9]506他认为《诗经》在孔子那里本来就是辞、乐并重的。只是孔子去世后,后人已经不能传承这个音乐了;秦代灭学之后,即使连辞意也逐渐不能理解了。所以他说:
夫诗者,声音之道也。昔夫子删诗,取风、雅、颂,一一弦歌之,得诗、得声者三百篇,余皆放逸。可见,诗在圣门,辞与音并存矣。仲尼殁而微言绝,谈经者知有辞,不复知有音。如以辞焉,凡书皆可,何必诗也。灭学之后,此道益加沦谬。文义且不能晓解,况不可传之声音乎?无怪乎以诗为诗,不以诗为乐也,故曰:“三百篇者,《乐经》也。”[9]506
“以诗为诗,不以诗为乐”,显然是批评只把《诗经》当经或诗这两种倾向的。他认为在孔子时代辞、音并存,就是《诗经》《乐经》合一,秦之后,则知辞不知乐。
针对有人提出的“乐之用广矣,大矣,乃以三百篇当之,何局而不弘也”,他辨析说:
乐之道与他书不同:有以文义存者,器数存者,声调谱奏存者。文义存者,诗章是也;器数存者,六律八音是也;声调谱奏存者,工师以神意相授受是也。古圣人以明物之智制为黄钟之宫,自十二律出,而律吕之能事毕矣;自钟、磬、琴、瑟、笙、箫、埙、篪出,而声音之能事毕矣,则器数者,即经也。周太师制歌声……《国风》《小雅》多商音,《大雅》多宫音……至春秋,而鲁庭师摰犹能传其音。汉兴,制氏以声音之学肄业。晋杜夔尚能传《文王》《鹿鸣》《伐檀》《驺虞》四诗余响,此以音调相授受也。《南陔》《白华》《华黍》《崇丘》《由庚》《由仪》六篇,其辞已不可考,而笙、竽独能存其音节,此以谱奏相授受也,则神意者,即经也。二者其始,皆出于圣人,既寄之器数,即求之器数;寄之神意,即求之神意。遗此,而使圣人更复著经,将何著经?惟所谓《诗》者,以辞义寓乎声音,以声音附之辞义;读之则为言,歌之则为曲,被之金石弦管则为乐。三百篇,非《乐经》而何哉?[9]506-507
此段可说是诗乐的发展简史,刘濂认为音乐的传承方式有三种,即文义、器数、声调谱奏。文义方面,诗章可以保存;器数方面,六律八音可以体现;声调谱奏方面,工师都各以神意相授受。圣人把音乐的规矩、定制体现在器数和声调谱奏上,我们也可以从这两方面反求之。
文义方面的音乐传承,本来可以由任何诗章来体现;然而唯有《诗经》不是一般的配乐诗章,而是原有定制。因此,《诗经》在总体上,其“诗章”,圣人所裁,是经;其“器数”,圣人所制,是经;其“声调谱奏”,神意所授,是经。《诗经》综合了音乐传承的所有方式,而这些方式都是经典。基于此,他得出结论:《诗经》本身就应该是《乐经》。
他又进一步分析,认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9]509正是古代诗乐的完整形式,是“古乐之全”,体现了文义、器数、声调谱奏的有机统一,是《诗经》即《乐经》的又一证明。
朱载堉记载其父朱厚烷的论述:
《乐经》者何?《诗经》是也。《书》不云乎:“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此之谓也。
迄于衰周,诗乐互称,尚未歧而为二,故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又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此称诗为乐也。孟子曰“齐景公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此称乐为诗也。
秦政坑儒灭学之后,礼乐崩坏。汉初制氏,世在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齐鲁韩毛但能言其义,而不知其音,于是诗与乐始判而为二。
魏晋已降,去古弥远,遂谓《乐经》亡。殊不知《诗》存,则乐未尝亡也。惟笙诗六篇者不可得而见矣。尝效颦为之,依次第附录焉。[10]1032-1033
朱厚烷从另一个角度更加清晰地论述了“诗”与“乐”关系发展的四个阶段,即诗乐自然统一阶段、诗乐互称(称诗为乐、称乐为诗)阶段、诗与乐判而为二阶段、知诗不知乐阶段。其也持“《乐经》不亡”论,认为“《诗经》即《乐经》”“《诗》存,则乐未尝亡也”;只是认为“笙诗六篇”为遗憾,此后更补二十五章。
三、朱载堉对《乐经》及“古乐”的基本看法
朱载堉认为《周礼·大司乐》就是古《乐经》,其云“汉时窦公献古《乐经》,其文与大司乐同,然则《乐经》未尝亡也”[9]147,所以有《乐学新说》之作,即对《周礼·大司乐》以十二平均律理论重新注释;认为“后世君子欲学古乐,宜以《虞书》为法,间用《周礼》补其缺略,不必尽从旧说可也”[10]774-775。
不过,朱载堉并没有明确否定“《诗经》即《乐经》”的说法,而是认为刘濂《乐经元义》一书虽“可取者亦不多”[9]1547,但“指《诗经》即《乐经》,其论甚精”[9]526。结果就连四库馆阁臣都误认为朱载堉主张“《诗经》即《乐经》”,评论说:“《乐经》之亡已久,古有以《大司乐》章当之者,载堉谓‘诗三百篇即《乐经》’,凿矣。”[9]5244-5245
至于“古乐”失传的原因,朱载堉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俗乐兴起。朱载堉认为,即使古乐沦亡,其主要原因也不是很多学者认为的“秦火”,而是因为失去听众。他说:“古乐绝传,率归罪于秦火,殆不然也。古乐使人收敛,俗乐使人放肆,放肆人自好之,收敛人自恶之,是以听古乐惟恐卧,听俗乐不知倦,俗乐兴则古乐亡,与秦火不相干也。”[9]1761-1762这种说法有其历史依据,史载季桓子、齐宣王、晋平公、魏文侯、卫灵公、赵烈侯等都极爱“郑卫之音”,而不喜雅乐。这表明朱氏对俗乐的特征有深刻的理解。
其二,古乐亡于“先儒纪载失实,称誉过高”。其云:“古乐绝传,其故何也?窃疑古乐绝传,盖由先儒纪载失实,称誉过高。”[10]774因为称誉过高而士大夫、下民不敢学,故而失传,这是古时礼乐等级制度使然。
其三,操缦乐谱失传。其《论操缦失传遂致雅乐失传》云:“古人于乐,重在节奏。今人学歌、学琴,多无板眼。何也?板眼者,节奏之谓也。节奏者,操缦之谓也。故学记曰:‘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学琴、学歌,先学操缦为第一之要务。操缦失则雅乐失传矣。”[9]1661-1662这是说古乐演奏时的操缦乐谱失传了,那么古乐自然也失传了。这与朱载堉的另一个观点一致,即指挥演奏的乐器失传导致古乐失传。其云:“近代雅乐节奏不明,至于舂牍、搏拊、操缦,皆乐中最要者,而多不识,此绝传之由也。欲复古乐,当以节奏为先。节奏明,则古乐如指诸掌。”[9]1762-1764
其四,歌舞技巧失传。其云:“古人学歌,以‘永’之一字为众妙之门。古人学舞,以‘转’之一字为众妙之门。何也?所谓歌者,五声六律,千变万化,举要言之,不过一气永长而已。所谓舞者,三回九转,四纲八目,举要言之,不过一体转旋而已。是知‘永’‘转’二字,其众妙之门欤?今人学歌而不能‘永’,学舞又不肯‘转’,此所以失传也。”[9]2537-2540
当然,朱载堉认为这些都可以弥补。古乐亡的是“乐谱”,但可以通过研究今乐和俗乐获得乐理。“古人乐谱今虽失传,然其理则未尝亡也。学者不过穷理而已,必欲穷究古乐未亡之理,莫若先自今乐所易知者以发明之。其理既明,一通百达,举而措之,斯无难矣,乃捷要之法也。……借今乐明古乐,不亦可乎?今人所共知者不过释奠大成乐耳”,“使后世为乐律之学者观之,深信古乐现存,未尝失传也”。[9]163其不但认为今乐是古乐遗留,可以达古乐之理,而且认为今乐和民间俗乐都可上溯至古乐,这就是他说的“古乐虽亡,人之情性音调未尝亡也”[9]2753-2754,即“古之歌音虽则失传,然其遗响犹有存者,若太常中和乐谱及释奠大成乐谱最为近之。……其次则僧家宣偈、道家步虚、船家棹歌之类,尚存古法于万一焉。夫礼失求诸野言,相去不远也”[10]924。
朱载堉不明确否定“《诗经》即《乐经》”的说法,一方面是出于对父亲及前贤的尊重,另一方面是认为其中有合理的成分。那么,这些“合理成分”在哪里呢?
正如前面刘濂说的,音乐的传承方式包括文义、器数、声调谱奏三种。现在有《诗经》之文辞,宫廷雅乐有太常中和乐谱和释奠大成乐谱,民间又有流传的笙琴及口传心授之声调谱奏,朱载堉自己又创制了十二平均律,只要把这些结合起来就可以恢复《乐经》本来面目,或者说恢复“古乐”。朱载堉恢复《诗经》音乐性的主要用力之处就在诗、乐、舞三个方面,包括对《诗经》的考证、乐律的创制、乐器的考证和改造、舞谱的制作等,具体操作上与“《诗经》即《乐经》”的说法暗合。
总之,朱载堉主张《周礼·大司乐》即《乐经》,又批判继承前人“《诗经》即《乐经》”之说,并在理论与实践中作了创新性的发挥和应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古代的歌诗传统,进而拯救明代雅乐;其方法是把《诗经》之辞与当时的俗乐相结合,“今古融通”“援雅入俗”,使传统文化在当时得到有效的传承和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