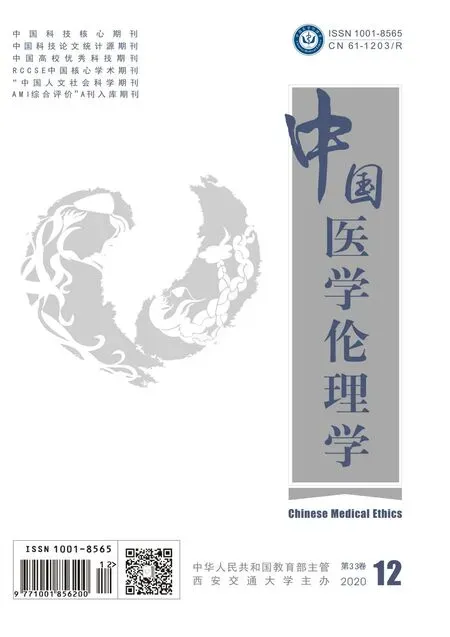整群随机试验的伦理问题分析
赵励彦
(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北京 100191,zgywyls2006@bjmu.edu.cn)
1 背景
整群随机试验(Cluster Randomized Trial,CRT)适合于在医疗实践、医院病区、学校和社区层面进行研究干预的有效性评估,这种设计可以更好地避免不同干预之间的污染[1-3]。它将受试者以群组为单位随机分配,一个群组内的受试者或者接受干预,或者成为对照。CRT不同于发生在个体水平的随机临床试验。CRT总是比个体随机试验需要更多的受试者,由于组群内个体的反应比群间个体的反应有更大的相似性,即存在群内相关,这就使研究的有效样本量减少[1]。CRT也更容易产生偏倚,包括组群之间的基线不平衡、招募偏倚、执行偏倚和退出偏倚[1]。由于CRT设计的特殊性,因此面临多方面的伦理挑战[4-9]。本文就这些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结合实例进行讨论。
2 受试者
2.1 “人体受试者”的概念
我国法规中对受试者的概念包括:《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中“受试者”是指被招募参加临床试验的个人,既可以是临床试验中接受试验用体外诊断试剂检测的人员,也可以是对照人员;《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原则》中“受试者”是指参加生物医学研究的个人,可以作为试验组,或对照组,或观察组,包括健康自愿者,或是与试验目标人群无直接相关性的自愿参加者,或是来自试验用药所针对的患病人群,均是针对临床试验中的受试者进行定义的。美国联邦受试者保护通则(Common Rule)中关于受试者的定义更加广泛,泛指所有参与人体研究的人,此定义中人体受试者指的是一个活的个体,研究者通过干预或与该个体进行互动获取、使用、研究或分析其信息或生物样本,或者获得、使用、研究、分析或是产生可识别的隐私信息或可识别的生物样本,这两种情况均属于涉及“人体受试者”[10]。笔者以前文提到的CRT例子来分析一下谁是受试者,这些受试者的概念是否适用于CRT研究来界定“人体受试者”。
2.2 界定谁是“人体受试者”
以一个示例来分析“人体受试者”的定义。一项研究为:该研究的目的评价一项尚未在临床使用的“血管功能”评价指标对降低冠心病和心肌梗死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影响。研究的干预措施为:对心内科医生进行培训,包括:对符合入组标准的患者开具“血管功能检查单”,以及学习如何解读血管功能检测结果。分配到对照组的心内科医生不接受相关培训,不给患者开“血管功能检测单”。18家医院的心内科门诊被随机分配到干预或对照组。主要分析指标:在3、6、9、12个月时检测患者的血脂、血压、血糖、体重指数、生活方式改变情况;医生开出降脂、降压和降血糖药物处方的情况。
该CRT中,人体受试者可能涉及两类人:第一类,符合该研究入选标准,到心内科就诊的患者应该作为受试者,这可能不会引起什么争议。第二类,医院的医生,如果认为其开展的是常规临床诊疗工作,那么不应该将其作为受试者,尤其是分到对照组的医生,他们没有接受任何干预,完全是常规医疗工作。
根据美国联邦受试者保护通则定义的两种情况:①研究者通过干预或与该个体进行互动获取、使用、研究或分析其信息或生物样本;②获得、使用、研究、分析或是产生可识别的隐私信息或可识别的生物样本[10]。所有参与的患者均接受了干预(对照组虽然没有接受新指标检查,但是同样要在3、6、9、12个月接受随访,并进行相关指标的检测),满足了“人类受试者”的第1条标准。此外,所有参与患者的可识别的隐私信息会被采集,满足了“人体受试者”的第2条标准。医生在研究中,干预组的医生要接受培训,对其常规诊疗工作进行干预(增开血管功能检测的单子),而且两组的医生诊疗工作的数据也会被采集用于研究。因此,同样满足两条“人类受试者”的判断标准,应该获得他们的知情同意。
在该示例中,医生不仅接受干预,而且还采集了他们的数据,有充分的理由被认为是受试者。但是,有很多CRT研究,医生仅仅是被干预的对象,不会采集医生的数据。如果仅对医生进行干预,医生应该作为受试者吗?“渥太华声明”认为除了美国联邦受试者保护通则定义的两种情况外,人体受试者在CRT中应该还包括以下两种情况:①是研究中干预或对照的接受者;②是研究操作或对照环境的直接目标[11]。根据渥太华声明,即使不会采集医生的任何数据,只要其作为研究中被干预或对照的对象,即可视为人体受试者[11]。由于不同的人群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CRT,受试者的识别是复杂的。渥太华声明指出,受试者是直接受研究行为影响的人,并将受试者定义为“其利益可能因研究干预或数据收集流程而受到影响的个人”,包括上述的四种情况[11]。例如,一项研究同伴支持计划对海洛因成瘾者进行美沙酮维持治疗保持率的影响,该研究是采用CRT设计,评估了社工支持干预与常规治疗相比,是否能够提高海洛因成瘾者在美沙酮门诊的保持率。14个美沙酮门诊按规模进行分层,并随机分配到两个研究组:常规治疗组和社工支持组。医务人员招募18岁以上,首次接受美沙酮治疗的海洛因成瘾者参加。主要评价指标是从开始接受治疗至12个月,患者在美沙酮门诊的保持率以及尿检阳性率。主要研究目的是评估社工的参与对美沙酮治疗有效率的影响。社工支持是指患者定期与“接受过研究团队培训的社工”会面,在每次会面时为患者提供一对一的支持,包括对患者进行禁毒教育;为患者提供心理咨询;督促没有按照要求来门诊服药的患者按时服药。研究者招募的社工是专业的禁毒社工,要对其进行支持计划的培训,禁毒社工所分配的患者均为其工作范围内的患者。在此示例中,依据美国联邦受试者保护通则定义的两种情况,被招募的美沙酮门诊的患者均符合,毫无疑问属于“受试者”,而此研究中的实施支持的“社工”则不属于“受试者”。但是,如果按照“渥太华声明”的另外两种情况来判断,“社工”符合其中的“是研究中干预或对照的接受者”。因为,他们同样被招募,接受研究人员的干预,为患者提供支持。而且研究目标是为了评估社工的参与对美沙酮治疗有效率的影响。因此,社工也应该属于受试者。
综上,在确定CRT中谁是受试者,可能参考“渥太华声明”的四项标准更符合伦理,即①是研究中干预或对照的接受者;②是研究操作或对照环境的直接目标[11];③研究人员为了收集数据与其进行互动;④研究者获取了他的可识别的隐私信息[11]。
3 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是尊重这一基本伦理原则的具体体现,该原则要求尊重个人的自主选择。有效知情同意必须是充分的、自愿的和经过考虑的知情[12]。CRT设计的特殊性对知情同意提出了挑战。
第一,这与CRT的方法本身有关。例如,采用CRT设计研究行为或教育干预效果,如果对受试者进行知情同意可能会导致信息污染,影响研究的科学性或是导致样本选择偏倚。Kennedy等采用CRT设计,研究一套以患者为中心的教育材料对患者了解疾病、焦虑症状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纳入的受试者来自长期随访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他们在同一个门诊就诊,经常会见面。为了避免信息污染,研究者没有采用个体水平的随机对照试验设计(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RCT),而是以组群将受试者随机在接受教育材料干预组和对照组[13]。同时,为了避免对照组会向干预组了解教育材料,研究者申请了免除知情同意[13]。当知情同意过程会引起受试者选择和结果的偏倚时,如果研究风险不大于最小风险,一般伦理委员会考虑豁免或变更知情同意[14]。
第二,有些CRT研究,可能涉及非常广泛的人群和地区,获得个体知情同意几乎是不可行的,例如,在全国范围评价一个新的卫生政策是否对降低吸烟率有效[15]。实施干预的单位是城市,即干预组城市推广该卫生政策,对照组城市不给予任何干预。这种情况,不可能获得每个受试者的知情同意。这项干预是基于城市进行的,研究者不可能尊重每位市民的意见来决定实施或不实施这项卫生政策干预;即使有人不同意,实际上还是无法不受影响,除非搬家。
第三,在一些CRT研究中,组群随机过程发生在受试者纳入之前。例如,Mullany等人将50~100个家庭作为一个组群,多个组群被随机分配到三组:用洗必泰擦洗新生儿脐部残端;用肥皂水清洗新生儿脐部残端;保持残端干燥(标准护理对照)[16]。从2002年至2005年,研究者对组群中妊娠六个月的孕妇进行招募,完成知情同意过程。由于研究开始时,大部分组群中的妇女尚未怀孕,但组群随机已完成,即随机分组发生在大多数妇女怀孕6个月之前,因此不可能事先获得随机化的知情同意[16]。
针对CRT知情同意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一些研究提出了豁免或变革知情同意的建议。
3.1 豁免或变更知情同意
McRae等报道CRT涉及以下两种情况时可以向伦理委员会申请免除或变更知情同意:第一,当CRT涉及组群级别的干预或组群规模过大,无法获得每位受试者的知情同意;第二,在知情同意过程中披露的信息可能严重影响研究结果或导致选择偏差[14]。我国对于免除知情同意在《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中提及,但仅限于既往数据和标本研究。美国联邦受试者保护通则中对豁免或变更知情同意的要求:①研究不大于最小风险;②豁免或变更知情同意不会对受试者权益和福利造成不利影响;③未经豁免或变更,研究无法实施;④在适当情况下,尽早将相关信息告知受试者[10]。可行性分析包括多种因素,例如,人群过于庞大、人群分散、研究人员不足、缺少相应的研究经费、知情同意过程复杂等,需要综合衡量是否确实不具备可行性的判断[17]。这种情况,如果伦理委员会批准免除知情同意,建议尽量向受试者提供有关研究的信息,例如,在候诊区播放相关研究的宣传片、发放传单等。当然,这种信息提供方式不能等同于知情同意的要求。还有一些研究,可能是因为告知受试者相关信息会影响研究的科学性,建议研究结束后尽快将相关信息告知受试者,如果受试者不同意使用采集到的数据,要尊重受试者的决定[15]。
3.2 知情同意在组群随机化之后的合理性
在一些CRT研究中,组群随机过程发生在受试者纳入之前,受试者在哪个组群就接受相应的干预,即组群随机化的过程发生在个体知情同意之前。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认为,研究者必须在整群随机之后尽快获得受试者的知情同意,也就是说在任何干预实施或数据收集前尽快获得受试者的同意[18]。在Mullany等人的研究中,随机化后获得知情同意符合伦理原则,因为潜在的受试者仍然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加试验[14]或研究。只要尽可能早地接触潜在的研究对象,在干预或数据收集之前获得其知情同意,是可以满足基本的伦理原则的。虽然没有获得随机化的同意,但研究对象仍有机会在暴露于风险之前,随时退出研究[14-15]。
有效的知情同意要求前瞻性研究对象获得为受试者提供充分的信息,使一个理性人能够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对于CRT,在整群随机后,向组群中的受试者征求知情同意是否可以根据组群被分配到哪个组来制定相应的知情同意书。一般告知的信息应包括研究目的和所有干预的描述,但是,当组群已经被随机分配至某种特定的干预组时,其他分配到别的组群的干预对受试者而言就不存在了。因此,有学者认为对于不同干预组群可以进行个性化的知情同意,不在本组群发生的干预可以不做介绍,这可能会减少信息污染的可能[14-15]。
4 弱势群体
《赫尔辛基宣言》中对弱势群体的定义为:一些群体和个人特别脆弱,他们更有可能被虐待或遭受额外的伤害。弱势群体包括儿童、无自主知情能力的成年人、处于从属地位的人员等。CRT如果有充分的理由纳入弱势群体,一定要对他们有足够的保护。CRT研究中的弱势群体更容易被忽视,因为这些弱势人群在组群中的存在可能被隐藏[11]。因此,研究者可能无法对其进行必要的保护。弱势人群被忽视或隐藏的原因包括:第一,弱势人群仅是很少的一部分人;第二,组群中的个体通常不被认为是脆弱的、需要额外保护的人群,例如,一些研究中的医护人员、教师或其他雇员,他们可能会感到有压力,必须要参与他们所在机构研究,不能做出自主的选择。
伦理委员会应该关注CRT研究是否可能包含弱势人群。如果涉及的话,应确保研究的获益和风险对这一人群是可接受的。例如,从属地位的人群,因为是整群随机,有些人可能无法自由拒绝研究,伦理委员会应特别注意这些人的招募、隐私和知情同意流程[14-15,19]。
5 总结
本文针对CRT可能面临的主要伦理挑战,即受试者的界定、知情同意过程和弱势群体的保护进行了分析。CRT在许多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希望能有更多的研究者参与CRT设计、审查和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伦理挑战的讨论,为研究者以及伦理委员会提供相关的参考,优化设计、规范审查、更好地实现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