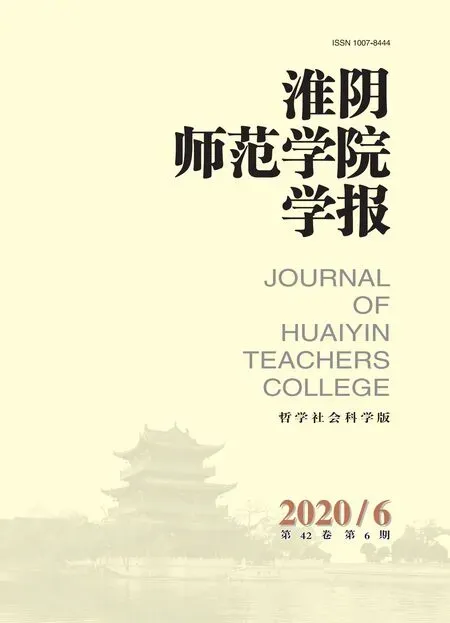吴承恩《西游记》祖本新探
郑子运
(贵州社会科学院文化所, 贵州 贵阳 550001)
一、《西游记》的祖本是鲁府本
吴承恩《西游记》(下称“吴本”)有祖本已经是共识,但祖本为何,却有很大的争议。或以为是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或以为是杨致和的《西游记传》,或以为是元代的《西游记》,但这三者应当都不是吴本的祖本。
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杨致和的《西游记传》字数都远少于吴本,事件大多相同,于是柳存仁认为吴本本于朱本,陈新认为吴本本于杨本。其实,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变》早已证明朱本、杨本删节了吴本,后来黄永年、陈洪、曹炳建无可争议地廓清了柳、陈的谬误。另外,蔡铁鹰等人指出《西游记》关于玉华州的那两回反映了吴承恩在荆王府的经历,陈澉指出唐僧师徒在地灵县蒙冤入狱影射了吴承恩在长兴县蒙冤入狱,既然朱本、杨本也粗略地记载了玉华州授徒、地灵县蒙冤,则朱本、杨本只能是吴本的删改本,不言而喻。
所谓元代的《西游记》是指《永乐大典》有一篇“梦斩泾河龙”,标明出处是《西游记》(一般认为成书于元代,下称“元本”),情节与吴本相应的部分虽然大同小异,字数却不及后者一半,而且诚如郑振铎所言,“其一枯瘠无味,其一则丰腴多趣”[1]。吴承恩将原文中的渔人对话改为渔樵攀话,便有点铁成金之妙,穿插的数首诗歌也韵味悠然。元代王振鹏(1280—1329)绘有《唐僧取经图册》,现存三十二幅,难以设想全出于画家的凭空想象,他应当是依据某部书绘制的,该书不是有南宋刊本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因为除去女儿国、火焰山等之外,内容大多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不同,如飞虎国降大班、旃檀大仙说野狐精、六通尊者降树生囊行者、悬空寺遇阿罗律师、白莲公主听唐僧说法,等等,所以他依据的只能是元本。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写南海火龙的自白是“偃甲钱塘万万春,祝融齐驾紫金轮。只因误发烧空火,险化骊山顶上尘。小圣南海火龙,为行雨差迟,玉帝要去斩龙台上,施行小圣,谁人救我咱?”[2]371南海火龙误发烧空火与泾河水龙行雨差迟是两个不同的故事,杨景贤捏合为一,前后不够融贯。既然后者据《永乐大典》出自元本,而前者对应《唐僧取经图册》“遇观音得火龙马”,自当也出自元本。据《永乐大典》《西游记》杂剧所引以及《唐僧取经图册》可以窥知元本的内容相当丰富,但与吴本整体差别很大。
朝鲜《朴通事》成书于14世纪,修订于15世纪末,不久(相当于明朝正德年间)崔世珍为之谚解、音义,后世合编为《朴通事谚解》。《朴通事》已佚,《朴通事谚解》正文提及一部《西游记》平话,并有车迟国斗圣的故事。据潘建国研究,对《朴通事》的修订基本上局限于词汇、语法层面,《朴通事谚解》的正文大体上仍然可以看作元代文本,则这篇“车迟国斗圣”出于元本,拿它与《永乐大典》所载“梦斩泾河龙”相比,两者无论是字数还是写作水平都相当接近。“车迟国斗圣”情节完整,有很多对话,语句连贯,恐非概述;涉及情节的注释只有一个(有一个先生到车迟国,吹口气,以砖瓦皆化为金,惊动国王,拜为国师,号伯眼大仙[2]481),而且这个注释与所注的句子大同小异。可以说,除去首尾两句,“车迟国斗圣”基本上就是照录原文,粗糙朴拙,而且字数不足一千一百,不及吴本相应部分的十分之一,文字差异也极大。
《朴通事谚解》标明出于“《西游记》”的注释有7个,其中第二个注释最重要,内容如下:
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蹶也。[2]479
《西游记》杂剧不言唐僧师徒初到之地是师陀国,但写到了黄风山的妖怪。该《西游记》点明初到之地的国名,加写黑熊精,并且将之后的黄风山妖怪改写成吹黄风的妖怪,演进之迹明显。《西游记》杂剧中有红孩儿、火焰山、女人国,却没有地涌夫人、蜘蛛精等妖怪,可见该《西游记》比起《西游记》杂剧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狮子怪,《唐僧取经图册》有“东同国捉狮子精”,两者当有渊源关系,但还不是吴本中到乌鸡国作怪的青毛狮子。宣德年间,朱有焞作《文殊菩萨降狮子》杂剧,写的是哪吒、文殊菩萨,与取经故事无关,后来才为取经故事吸收,与“东同国捉狮子精”合而为一。由此也可见太田辰夫、熊笃、潘建国元本与该《西游记》不是同一部书的观点是正确的。
宣德至正德之间出现的该《西游记》才是吴本的祖本。潘建国称该《西游记》为“旧本《西游记》”,并认为:“周弘祖《古今书刻》卷上著录有山东鲁府刊刻以及登州府刊刻的《西游记》,尽管这两部《西游记》是否为小说尚待考定,但从时间上来观察,它们有可能就是旧本《西游记》(或其翻刻本)。”[3]眼光敏锐,可惜停留在“尚待考定”阶段。
周弘祖与吴承恩同时,其《古今书刻》没有注明鲁府、登州府所刻《西游记》的朝代、作者和类别,或以为是元本,或以为是百回本《西游记》,或以为是《长春真人西游记》。万历中期,陈元之为金陵世德堂刊本作序称:“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而充叙于余。”(1)吴承恩:《(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明清善本小说丛刊》本。[4]由此可知,唐光禄所购的是稿本或抄本,不是刻本。若是刻本,以其内容之引人入胜,必早已风行于世,翻刻不绝,且金陵是刻书业中心,唐光禄又是书商,他必曾寓目,不必再“奇之”;实际上,百回本《西游记》是在世德堂刊刻以后才风行于世的。另一方面,若是刻本,直接翻刻就可以了,不必再“俾好事者为之订校”,除非大肆删减、改作,如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杨致和《西游记传》所为,但世德堂并没有这么做,一百回不但完好无损,而且“秩其卷目”,即在书前增添了回目,并划分了卷次。至于盛于斯《休庵影语》引周如山的话说:“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2]784,并非指周邸曾经刊刻,只是指刊刻的底本出自周邸而已。所以百回本《西游记》(吴本)最早其实由世德堂刊刻,鲁府、登州府所刻当然不是百回本《西游记》。再考虑到崔世珍为《朴通事》谚解、音义相当于明朝正德年间,其时吴本未出,他在朝鲜看到的《西游记》当是刊本,因为抄本少,不易为在华外国人购得,传至外国更不易,而且他引用的《西游记》内容与元本差异不小,所以鲁府、登州府所刻《西游记》必有一种就是宣德至正德之间出现的那部《西游记》。
鲁府指山东鲁王府。明朝尤其是永乐以后,各地的藩王不得干涉地方政事、军事,藩王、郡王养尊处优,其中有一些为遣心怡性,对戏剧、小说、诗歌很感兴趣,而登州府作为官府,一般不会刊刻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所以鲁府刊刻的是宣德至正德之间出现的那部《西游记》(下称“鲁府本”),登州府刊刻的当是简称为“西游记”的纪实之作《长春真人西游记》。世德堂本不是官板却自称“官板”,并非出王自制却宣称“或曰出王自制”(2)吴承恩:《(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明清善本小说丛刊》本.,当是因为当时鲁府本还在流布,世德堂故意混淆真假,既以招徕顾客,又留有退路,同时暗示自家所刻与鲁府本有文字渊源以及鲁府本由鲁府某王创作。乌鸡国首见于鲁府本(见下《礼节传簿》所列),鸡在十二生肖中位列第十,而首位鲁王恰为朱元璋第十子,也可见鲁府本很可能为鲁府某王创作。邹平王朱当潩有才艺,或是其人。尽管鲁府本已不存,其面目仍然可以借其他文献窥见,从而得知吴本的改进和创新之功。
二、从《礼节传簿》《销释真空宝卷》看鲁府本
抄于明代万历二年(1574)的《礼节传簿》载有大量剧目,其中有正队戏《唐僧西天取经》角色单,曹炳建、杨俊《〈礼节传簿〉所载“西游”戏曲考》一文考证《唐僧西天取经》产生于明代前期,大抵可信,下限当然是万历二年。《唐僧西天取经》内容如下:
唐僧西天取经一单 舞 唐太宗驾 唐十宰相 唐僧领孙悟恐 朱悟能 沙悟净 白马行至师陀国 黑熊精盗锦兰袈纱 八百里黄风大王 灵吉菩萨 飞龙柱杖 前到宝象国 黄袍郎君 绣花宫主 销元大仙献人参果 蜘蛛精 地勇夫人 夕用妖怪一百只眼 蓝波降金光霞佩 观音菩萨 木叉行者 孩儿妖精 到车罕国 天仙 李天王 哪吒三太子降地勇 六丁六甲 将军 到乌鸡国 文殊菩萨降狮子精 八百里小罗女铁扇子 山神 牛魔王 万岁宫主 胡王宫主 九头附马 夜叉 到女儿国 蝎子精 昴日兔下降 降观音张伏儿起僧伽帽 频波国西番大使 降龙伏虎 到西天雷音寺 文殊菩萨 阿难 伽舍 十八罗汉 四天王 护法神 揭地神 九天仙女 天仙 地仙 人仙 五岳 四渎 七星 九耀 十山真君 四海龙王 东岳帝君 四海龙王 金童玉女 十大高僧 释伽仸 上散[2]507
引文的若干讹字如误“空”为“恐”,容易辨别,不必一一指出。《朴通事谚解》还有一个注释:“释迦牟尼佛在灵山雷音寺,演说三乘教法,傍有侍奉阿难、伽舍诸菩萨、圣僧罗汉、八金刚、四揭地、十代明王、天仙、地仙。”[2]482-483由此可知,《唐僧西天取经》末尾罗列众多佛教的神、道教的仙是指唐僧师徒参见诸天神佛,不是指有一个情节复杂的故事。不仅如此,《唐僧西天取经》与《朴通事谚解》都记载唐僧初到的是狮驼国,其后的事件互有异同。可见《唐僧西天取经》虽然比《朴通事谚解》列举的事件多,实际上也出自后者所引的鲁府本。另外,《泾河龙王难神课先生》在《礼节传簿》中与《唐僧西天取经》前后相接,只是抽取单列,即鲁府本也有这个故事。
鲁府本写唐僧在师陀国遇见猛虎毒蛇,因为不是妖怪,《礼节传簿》只载国名,吴本于狮驼国改而写狮子精、白象精、大鹏鸟精,多达四回文字,差异很大。“黑熊精盗锦兰(襕)袈纱(裟)”又单列为“雄(熊)精盗宝”,该剧与南戏《白兔记》中的《咬脐打围》并列,都是在祭祀供酒盏时演唱,篇幅短小与时地正相宜。“销(镇)元大仙献人参果”,既然是“献”,恐怕不如吴本写偷人参果、打倒果树、两次逃走都遭捉回、求医树仙方来得复杂,只能是粗陈梗概。《礼节传簿》对相同的角色会注明数量,但于“蜘蛛精”下没有注明,可见鲁府本里只有一个蜘蛛精,而吴本中的蜘蛛精多达7个,还有打秋千、洗浴、干儿子上阵等情节,应是吴承恩所添。李天王、哪吒、地勇、六丁六甲出于同一个故事,误插入车罕(迟)国的大(误为“天”)仙、将军之间,元本“车迟国斗圣”中有大仙、将军,吴本没有将军,可知鲁府本基本上承袭元本。先提及小罗女,再提及山神,而且小罗女使用的是铁扇子,不是芭蕉扇,都与《西游记》杂剧相同,可见鲁府本承袭了《西游记》杂剧,即小罗女与牛魔王没有关系,其故事各自独立。牛魔王之后没有列出玉面狐狸精及诸天神,鲁府本应当没有牛魔王一妻一妾以及诸神大战牛魔王的情节。至于“昴日兔下降”,文字有误,只能是昴日鸡,或者是房日兔,都在二十八宿之中,而吴本写的是月中玉兔下降,另有寄托,情节当然差异很大。棘钩洞、薄屎洞没有列出,当是因为二洞在鲁府本中本来就没有妖怪,甚至人迹,以至于《礼节传簿》没有唐僧师徒之外的角色可排,故而略而不载,这两个故事只能是粗陈梗概,而吴本于“荆棘岭”添加了树精、于“稀柿衕”还写了蛇精。最后是“降龙伏虎”,对应的当是吴本中的黑水河鼍龙、黄风怪的虎先锋。《朴通事谚解》《礼节传簿》所列的任何唐僧取经事件都不能证明有与吴本等量齐观的详尽叙述,反而大多能证明只是粗陈梗概,或与吴本小同大异,或为吴本不取。所以,吴承恩以鲁府本为基础,重新创作,有了质的提升,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太田辰夫认为《朴通事谚解》所引《西游记》只达到比《全相三国志平话》略略进步的程度,实为卓识。
据喻松青考证,《销释真空宝卷》成书于万历年间。该书所列取经事件与《朴通事谚解》《礼节传簿》所载相比,有同有异:
正遇着,火焰山,黑松林过。见妖精,和鬼怪,魍魉成群。罗刹女,铁扇子,降下甘露。流沙河,红孩儿,地勇夫人。牛魔王,蜘蛛精,设(摄)入洞去。南海里,观世音,救出唐僧。说师父,好佛法,神通广大。谁敢去,佛国里,去取真经?灭法国,显神通,僧道斗圣。勇师力,降邪魔,披剃为僧。兜率天,弥勒佛,愿听法旨。极乐国,火龙驹,白马驮经。从东土,到西天,十万余里。戏世洞,女人国,匿了唐僧。[2]457-458
罗刹女用的是铁扇子,与鲁府本相同,与吴本不同;师力降魔为僧,也与鲁府本近似,可知引文实际上本于鲁府本。引文叙述混乱,首先列出的是火焰山,与火焰山密切相关的罗刹女却分隔在另外的句子里;《西游记》杂剧第十五出写猪八戒在黑松林现出本相,是在流沙河收沙和尚之后,吴本第二十八回、八十一回写到黑松林也在流沙河收沙和尚之后,处于两者之间的鲁府本必也如此,则流沙河不当排在黑松林之后;女人国不但在所有的灾难中殿后,甚至在取得真经之后,也极为不当。而且受其三三四的句式以及比较随意的态度所限,句中并列的事件并非严格地以类相从,如观音救出唐僧,与红孩儿有关,与地勇夫人无关,因为从《礼节传簿》所列以及吴本来看,降伏地勇夫人的是李天王、哪吒父子,该宝卷作者毕竟只是引用听众喜闻乐见且现成的取经故事,使他们乐于接受他宣传的教义,并非有意发展西游故事。依此类推,见鬼怪魍魉成群是在黑松林,不是在火焰山;将唐僧摄入洞去的是蜘蛛精,不必是牛魔王;匿了唐僧的是在女人国,不必是在戏世洞。
赵景深根据“僧道斗圣”一语以及吴本中的灭法国部分又没有僧道斗圣的情节,认为车迟国又号灭法国,所言有理,但也有可能是该宝卷作者误记。“师力”,多写作“师利”,即文殊菩萨,而《礼节传簿》列有“降观音张伏儿起僧伽帽”,当是指张伏儿误戴僧帽,被观音降伏出家为僧,此处的文殊降魔为僧只是误记或变异,当然也可能是《礼节传簿》误记。“戏世洞”明显是因为“稀屎洞”“薄屎洞”不雅而有意改变。所谓“愿听法旨”,单提弥勒佛,是鲁府本所载唐僧师徒参见如来、诸菩萨的一个简化或异化。可见《销释真空宝卷》中的取经事件确实出自鲁府本,并没有增加,只是有所变异。
王熙远30年前在广西发现的《取经道场》被看作早期的佛教宝卷,同类文本后来在贵州、湖北、甘肃、山东等地均有发现。该宝卷所载仅有魔鬼岭、山狗夫人跪拜唐僧两事不见于吴本,至于惠安索要金银,对应吴本中的二尊者索要人事,包含在唐僧师徒在西天取得真经一事之内。该宝卷既然提及黑熊精、蜘蛛精,无疑也出于鲁府本,这可以印证车锡伦该宝卷成于“明代前期(成化以后)”[4]的观点。该宝卷载有寸步难行的风野山、白猿(湖南的文本作“白龙”)撑船摆渡,分别对应鲁府本中的棘钩洞(该洞在风野山)、降龙(即吴本中的黑水河鼍龙撑船摆渡)。另外,发现于山东的宝卷《佛门取经科》抄于清末,载有同类文本所没有的猕猴妆行者,当是受吴本的影响而添加。
三、从《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看鲁府本
郑之珍《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有与《西游记》相同或相近的角色,如观音菩萨、铁扇公主、白猿精、猪百介、沙和尚;还有相似的事件,如遣将擒猿、白猿开路、过黑松林、过寒冰池、过火焰山、过烂沙河、擒沙和尚。所以两书的关系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或以为前者影响了后者,或以为后者影响了前者,而苗怀明折中两说,认为“两套西游故事各有其本事和原型,大体上是各自独立发展演进的,是一种平行的关系,但同时又彼此影响,形成一种较为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5]。但又认为“其中的白猿、猪百介、沙和尚、铁扇公主等人物形象较为粗略、模糊,很难说他们是受《西游记》的启发而产生。相反,从《劝善戏文》中西游故事粗陋、原始的形态来看,说《西游记》受其影响倒更合乎实际”。[5]未免自相矛盾。郑之珍《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成书于万历十年(1582),比吴承恩《西游记》略晚,但在后者刊刻之前,两书应当不存在相互影响。早期有关目连的著作,如宋代的《佛说目连救母经》以及元代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都没有目连西游故事,目连西游故事实际上首见于《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郑之珍创作该戏文时,借鉴还在流传的鲁府本《西游记》是很正常的,正如吴本盛行以后,《东游记》中的齐天大圣一角借用于吴本。现在主要以《观音渡厄》和《过黑松林》为例,考察《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中的西游故事受到《西游记》的祖本即鲁府本多大的影响,或者说,它多大程度上能反映鲁府本的面貌。《观音渡厄》如下:
【三棒鼓】[占]天风吹送下瑶台,救度人间苦与灾。行孝的既可怀,修善的尤可哀。观世音时闻音下界,为只为十子在途中苦难来。
家贫未是贫,路贫愁杀人。十人途路苦,口口叫观音。张佑大兄弟十人,是我在金刚山点化,他先往西天修行,日后扶助罗卜,共成大业。他等途中,将到火焰山、寒冰池、烂沙河,凡此至险,皆是天造地设,隔断红尘,不使凡人轻履佛地。不免唤过铁扇公主渡他过了火焰山、云桥道人渡他过了寒冰池、猪百介渡他过了烂沙河,早到西天,同成佛果。铁扇公主、云桥道人、猪百介早上。
【不是路】[旦]铁扇裙钗,为赴慈悲宠召来。[外]下天街,云桥直驾青天外。[净]漫诙谐,白莲会上呼百介,时人休笑为精怪。[合]奉天差,慈悲法力同天大,只得向前参拜。[见介][叙事介]
[占]铁扇公主听我分付:
【马不行】[占]铁扇风裁,制自天工体甚佳。今念十人苦楚,万里长途,几遇凶灾。好把腾腾火焰扇将开,使他堂堂大路无遮碍。[旦]自愧非才,[叠]勉成善果期无怠。
[占]云桥道人听我分付:
【前腔】人在天涯,高架云桥渡得来。今见池冰满腹,寒气侵人,冻裂肌骸。好把云桥一道跨冰崖,暖超十子过寒陌。[外][合前]
[占]猪百介听我分付:
【前腔】你猪首猪腮,中有仁心遍九垓。这便是蛇身人首、牛首人身,一样形骸。好把沙河淤塞孔将开,使他康庄直抵西番界。[净][合前]
[占]今则十人将临险地,你等可急急前去!
[占]佛化有缘人,功非可独成。
[众]三人承嘱付,各自显神灵。[6]42
引文中的“占”实为“贴”之简写。这一出中的角色,观音菩萨(占)、铁扇公主(旦)也出现于《西游记》,猪百介(净)相当于《西游记》中的猪八戒,而云桥道人(外)不见于《西游记》。铁扇公主、猪百介仅出场于这一出。诚如苗怀明所言,形象较为粗略、模糊,故事粗陋,但若说原始,则难以成立。不能因为粗陋就认为原始,《观音渡厄》粗陋是有意苟简的结果。同样是西游遇厄,《观音渡厄》粗陋,《过黑松林》却情节详尽,也可见前者是有意苟简;后者详尽,角色形象较鲜明,当是为了突出全剧的主角傅罗卜(目连)。
“天风吹送下瑶台”,若孤立地看,以为写的是道教的神仙,瑶台在高耸入云的昆仑上,李白也曾诗云“会向瑶台月下逢”,但郑之珍写的却是观音菩萨,他如此写,并不意味着这是观音菩萨最早的出处,因为从无观音菩萨居于昆仑山上的瑶台之说。郑之珍在《观音生日》一出里写观音菩萨“身居南海,迹显香山。世人有喜怒哀乐之音,我能知喜怒哀乐之意”[6]171-172,可见他知道观音菩萨的出处,此处几乎将观音菩萨写成了道教神仙,只能是他擅改,或者说有意混淆道教神仙与观音菩萨。依此类推,并不能认定此处的铁扇公主、猪百介是最早的出处,是原始面貌,是《西游记》借用了这两个角色,恰恰相反,是郑之珍将《西游记》中的铁扇公主、猪八戒借用过来,并加以改造。从猪百介自报家门以及观音菩萨对他的描述来看,他本身就是妖怪,必有故事,所谓“白莲会上呼百介”,是说他曾经皈依佛门,只是一笔带过,明明有所本。铁扇公主熄灭火焰山的火、猪百介拱出康庄大道、云桥道人架桥,单从字面上来看,也可以推知本来是各自独立的故事,篇幅不会短到如《观音渡厄》所写,只能是郑之珍将三个本来独立的故事捏合在一起,正如杨景贤将南海火龙误发烧空火与泾河水龙行雨差迟这两个不同的故事捏合为一,几句话就打发了。
“好把沙河淤塞孔将开”,意谓从淤沙中拱出一条大道,“孔”当是“拱”之误刻,从下一句的“康庄”可知猪百介开出的是大道,而不是隧道,也可见“孔”是“拱”之误。《观音渡厄》有元本没写而鲁府本所写的铁扇公主,她用的也是鲁府本所写的铁扇,不是吴本中的芭蕉扇。《观音渡厄》有鲁府本所写的拱出道路,而元本、《西游记》杂剧都没有。所以《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的西游故事其实取材于鲁府本,只是有所改造。猪八戒用长嘴拱、用钉钯筑是看家本领,如吴本写他在荆棘岭用钉钯开出道路,并拱倒树木,又写他从稀柿衕中拱出道路;郑之珍写猪百介从烂沙河的淤沙中拱出道路,并与流沙河收沙和尚的情节捏合在一起。逆推过去,鲁府本当有猪八戒拱出道路的情节,很有可能是在寸步难行的风野山。刘祯认为“白猿、沙和尚等情节正是在目连戏的不断衍变中,接受《西游记》故事影响,然后并入的”[7]。他提到的《西游记》若限定为鲁府本,则更准确。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有深沙神架桥的情节。据日本学者矶部彰研究,《唐僧取经图册》有一幅表现的是“(深沙神)在沙漠上架起金桥让一行通过”[2]537,即元本也有这个情节,继承元本的鲁府本应当也有。吴承恩对这个情节弃而不取,而郑之珍取之,把架桥者改为云桥道人,并把地点改为寒冰池。寒冰池实际上是条河流,河面冰冻,河底有乌龙精伺机吞吃冻死的行人。这个情节的远源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入九龙池处》。九龙池“千里乌江,万重黑浪”[2]80,河中有九条鼍龙,吴本中的黑水河捉鼍龙显然也脱胎于此,当然是通过鲁府本。鲁府本中的情节当是鼍龙先变为舟人,以摆渡诱惑唐僧师徒,此计不成,又使河水结冰,企图冻死唐僧师徒。郑之珍只取结冰的情节,而吴承恩既取鼍龙摆渡的情节,结撰成《西游记》第四十三回黑水河捉鼍龙的情节;又另取河水结冰的细节,融进民间鱼篮观音的传说,结撰成《西游记》第四十七回至四十九回堪称新创的通天河擒鲤鱼精的情节。
铁扇公主没有出现于《过火焰山》一出,取而代之的是赤蛇精,鉴于吴承恩《西游记》中的蛇精现出本相时也是赤蛇,不太可能是出于巧合,当是因为鲁府本中的蛇精就是条赤蛇。元本中为害的是条白蛇,并不相同。吴承恩、郑之珍都取之于鲁府本,前者以之与稀柿衕的情节捏合在一起,后者以之与过火焰山的情节捏合在一起。同样是取材于鲁府本,并加以捏合、改造,赤蛇精在《过火焰山》一出中出场时自吹自擂,实际上后来几乎毫无作为,即郑之珍写得很简略粗陋,而吴承恩写孙悟空、猪八戒斗杀蛇精,非常精彩,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过黑松林》文繁,不便全文征引,兹仅简括其内容。傅罗卜西行至黑松林,林中多虎豹,观音驱散虎豹,在林中变化出一座茅屋,并变身为妇人。妇人淫邀艳约,傅罗卜虽也敷衍应付,却不为所动,并发下誓愿。妇人调遣猛虎前来,傅罗卜拜虎,虎退去。妇人又请傅罗卜饮酒、吃肉馒头,均遭拒绝。妇人又假装腹痛,求傅罗卜用手按摩腹部。傅罗卜救人心切,将数张大纸盖在妇人腹部按摩。此时妇人、茅屋忽然都不见了。观音现身,勉励他继续西行。这就是《过黑松林》的梗概。鲁府本也有黑松林,但写的是鬼怪魍魉。鲁府本也有观音假变美女色诱唐僧师徒,但不在黑松林,吴本敷衍为“四圣试禅心”,与《过黑松林》相比,文字差异甚大。调遣猛虎前来,试探道心,早就见于唐传奇《杜子春》。至于女子假装腹痛,请求僧人按摩,则出于明代盛传的吴红莲色诱玉通和尚的故事,最早见于嘉靖年间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但郑之珍未必取材于该书,因为该故事在杭州一带早已流传,与他同时的徐渭据之写成戏文,晚于他的冯梦龙据之写成小说。可见,《过黑松林》是郑之珍挦撦诸小说、明代民间传说而成,已经是后期的过黑松林故事,甚至晚于吴本所写。
结语
不但《销释真空宝卷》所载不出《朴通事谚解》《礼节传簿》的范围,《取经道场》(包括同类文本)以及《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所载也十有八九在其内,这表明鲁府本的规模大体如《朴通事谚解》《礼节传簿》所示,约为吴本的一半。出于鲁府本之外的大抵可以认为都出于吴承恩独创,如猴王学艺、如来降猴王、三打白骨精、平顶山莲花洞、夜阻通天河、青牛精金刚琢套法宝、真假美猴王、木仙庵谈诗、假设小雷音、朱紫国行医、比丘国救婴儿、隐雾山豹子精、玉华州传艺、犀牛精偷油,等等。吴承恩《西游记》之于鲁府本的影响力,过于罗贯中《三国演义》之于《三国志平话》,其著作权不可否定。
探知鲁府本的内容,才可以看到西游故事从初次成书到吴承恩《西游记》漫长而清晰的嬗变与取代的过程:元本问世,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国内逐渐亡佚,幸而在日本有留存;鲁府本问世,元本逐渐亡佚,幸有两篇遗文保存下来;吴本问世,鲁府本逐渐亡佚,其取经事件保存在民间的戏曲和宗教文本里。是吴承恩凭借其天才使西游故事发展为文学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