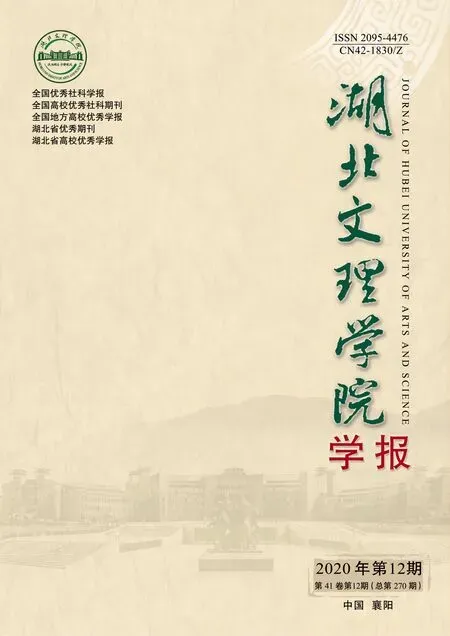国际传播视野下抗战电影的民族性表达
姜小凌,翟兰兰
(1.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2.长江日报报业集团 融媒体中心,湖北 武汉 430012)
全球化语境下,抗战影视剧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之一,不仅担负着建构抗战记忆的政治使命,也承担着参与国际软实力竞争的文化使命。虽然我国影视传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政策优势和资源优势,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欧洲、韩国等影视国际传播强国相比,我国的国际传播力建设还存在相当的差距。以2017年的新主流大片《战狼2》为例,虽然创下华语电影全球票房年度排行榜的历史记录,但海外票房却非常惨淡,仅占总票房收入的5%左右。其最大症结不是“模仿抄袭”好莱坞,而是影片中毫不掩饰的强者姿态、高调表达的国家民族优越感等,与国际电影的主流价值相去甚远,以致于在海外推广遭遇寒冰。因此,怎样在全球范围内讲述抗战故事,无疑是抗战电影走出国门前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80多年的创作实践来看,无论是抗战史诗片、喜剧片,抑或是灾难创伤片(如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都贯穿着鲜明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结。我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对这种情感的表达过于直白和“火爆”,尤其是抗战“神剧”“雷剧”中超级英雄“手撕鬼子”“枪毁飞机”的战斗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同时影片中流露出的“以牙还牙”的复仇逻辑,也明显偏离了国际“二战”电影的主流价值,致使抗战电影的国际传播效果不尽如人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尝试将抗日战争纳入到世界“二战”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谱系,推动抗战记忆由国家、民族属性向世界属性位移。“这种叙事方位上的不断调试,体现出的是‘后冷战时代’的中国试图通过建构新的媒体叙事框架,超越冷战意识形态,重新回归世界现代历史的努力”。[1]同样,在这种媒介叙事框架下,抗日战争的世界属性逐渐上升到与其民族属性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主导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问题。
面对“二战”记忆全球传播与竞争的态势,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作为中国民族精神表征与载体的抗战电影,怎样处理民族性表达与国际化传播的问题?而围绕这一中心议题,至少需厘清以下问题:全球化背景下,抗战电影是否仍需坚守民族性?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视野或立场去坚守民族性?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抗战电影怎样讲述民族抗战故事,方能融入世界“二战”电影的主流价值方阵之中,实现民族性与国际化的无缝对接?本文即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全球化语境下坚守抗战的民族属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概念开始受到关注,并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意识,一种现象、一种行动、一种变革以及一种过程”。[2]全球化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同时也在政治、法律尤其是文化上带来了许多问题。针对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文化竞争,即通过强化本民族文化内容,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学者指出,应该强化优秀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内容,不断拓展阵地,以形成广泛的文化圈。[3]二是文化融合,即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吸纳多元文化,增强本民族文化的活力,最终提升其竞争力。“文化的生命力恰恰在于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以及具有不同个体经验、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对这些开放与多元的文化形态与内容所进行的生动解读”。[4]如果无视发达国家的媒介强势,脱离实际地想象本土文化的优越性而抱残守缺,甚至用民族主义态度去消极抵抗文化的全球化,显然是很不健康的态度。无论持何种观点,都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的改造和扬弃。从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实践来看,获得国际大奖的抗战影片,如《黄土地》《红高粱》甚至《鬼子来了》等,其故事均植根于地域民俗,电影的奇观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民俗元素,正是对民俗的呈现使之在国际上得到清晰的定位和明确的命名。从这个意义上说,影片的国际传播在展现民族特性、民族精神和建构民族身份的同时,也搭建起西方世界认识东方文化的桥梁。也因此,坚守民族文化的形式与内核是包括抗战电影在内的文艺作品进行国际传播的根基,离开了这点,作品的个性和魅力将会丢失,在国际传播中也将失去“核心竞争力”。然而,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封闭固守本土文化的民族本位思想注定导致民族文化难以立足于世界,成为阻碍中国电影走出国门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和建构民族性内涵,以适应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传播语境。
二、全球化语境中重构抗战电影的民族性内涵
毋庸置疑,新时期以来中国抗战电影的变革与“走出国门”是创作者主动适应国际电影审美理念的结果,也是基于西方评价体系对民族文化进行改造的结果。虽然从传统的视角看,这种改造也许是被动的和消极的,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抗战电影的繁荣,也加快了中国抗战电影国际传播、“睁眼看世界”的步伐。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全球化语境下,包括抗战电影在内的中国文化若不超越西方主导的话语藩篱,就难以摆脱依附盲从的地位而获得与世界平等交流的话语权。因此,改造和重构抗战电影的民族性以适应新的历史语境是大势所趋。在此,笔者借鉴学者胡亚敏提出的“开放的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意义框架,来诠释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抗战电影的民族立场,并在此基础上重构电影民族性的当代内涵。
胡亚敏认为,全球化语境下,民族的概念是在与他者对比和参照过程中确立的,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理应存在于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中。她借鉴詹姆逊的观点指出,“‘民族’在今天应该用来表示一个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永远应该暗指(多于二项的)相关性”。[5]同时,“民族”这个概念又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特征,且处于不断扬弃的过程中。民族性中那些陈旧的、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将遭到淘汰,外来的那些先进因素将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中。因此民族和民族性都是一个不断扬弃与转换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守的概念。而所谓的“开放的民族主义”即坚持民族的差异性和包容性并存,“表现为‘立足本土,心怀全球’,即它一方面坚持民族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希望得到世界的认同,渴望立于世界之林”。[6]坚持民族独立性即依附民族背景,发扬民族优秀传统,珍惜民族精华。坚持民族的包容性即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能力,倾听“他者”声音,吸纳“他族”优长,最终为世界所认同。因此,全球化以承认民族个性和文化多元性为前提,民族性又以全球认同为目标,二者是相互依存的。
在当今文化交流与市场竞争的大环境中,抗战电影的文本生产必须坚持民族差异性,以凸显民族特色和民族气质。需要指出的是,坚持民族的差异性,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通过寻找传统与现实的对接点,创造出新的有生命力的民族特色。以“开放的民族主义”立场接纳“他者”优秀文化,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借鉴融合,兼收并蓄。在这点上,西方尤其是美国好莱坞经验值得借鉴。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迪士尼动画片《木兰》。《木兰》的原文化虽然在中国,但经过好莱坞改造后却是中美两种文化的杂交融合;最终能够成功地在世界传播和接受,则又变成全球文化的有机构成,它又反过来作用于原文化。如此,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7]今天的民族性是处于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性,它既是个性的、传承的和发展的,也是共性的、借鉴的和包容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构民族性不是凭空想象与发明创造,而是改造,这种“改造”更倾向于系统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与我国民族文化对接和融合,产生“1+1>2”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构”和“改造”与鲁迅笔下理性的“拿来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三、国际传播视阈下抗战电影民族性表达的实践路径
以“开放的民族主义”立场重构和改造抗战电影的民族性表达,意味着在抗战电影创作实践中,需要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去探索跨文化的影像表达,既坚持民族个性,又包容他者文化;既继承传统,又吸收创新,以建构与世界“二战”电影相契合的话语体系。基于此,本文拟从价值理念、故事建构和话语表达等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重塑抗战价值:实现由“中国价值”向人类共同价值的位移
电影的国际传播意味着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的检视。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民族、地区和集团的文化,其价值目标与价值取向也各不相同,且常以各自的文化为优越,对其他文化具有天然的警惕感和排斥性。而在传播、接触和理解的过程中,很可能产生竞争、对抗甚至企图消灭对方的心理。这种文化冲突的实质是价值观的冲突。而本土文化与本土价值,是影视文化软实力的源泉与动力。开放的民族主义立场对于抗战电影国际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在于:在保留民族文化中具有普适性价值观的基础上,尊重和主动适应目标受众的文化习惯和价值理念,尽量避免民族优越性和排他性价值观,以防止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甚至文化拒斥现象。国际化“更重要的是在价值观念、叙事主题和叙事方法上的国际化”。[8]
中国抗战电影很长时期以来过度看重宣传、教化的传播诉求,呈现在观众面前最多的是抗战英雄们慷慨激昂的战斗热情和勇于牺牲的爱国行为。这种生动华彩的影像风格和在此风格暗示下的价值体系,无益于揭露日本侵略者及其军国主义的真面目,甚至与“反战”理念相抵牾:英雄传奇和胜利叙事所营造的激动、兴奋甚至狂欢情绪与战争的残酷、反人道特征格格不入;而对敌人形象的妖魔化呈现和对抗日战争的戏谑性书写,也反映出历史观上的重大缺陷。
世界经典二战电影,如美国的《卡萨布兰卡》《辛德勒的名单》《英国病人》《拯救大兵瑞恩》以及《血战钢锯岭》,德国的《斯大林格勒战争》、意大利的《海上钢琴师》、苏联的《这里黎明静悄悄》甚至包括日本的《萤火虫之墓》等等,常常通过渲染战争的残酷无情彰显英雄主义精神和至善至美的人性,揭示战争的悲剧内涵和罪恶属性,张扬一种反对战争、尊重生命与人格尊严的价值理念。即便是幽默喜剧风格的“二战”电影,如《虎口脱险》《桂河大桥》等,以展现与反思民族尊严、军人荣誉、个人生死等价值观为主。中国抗战电影虽然也彰显了英雄主义,部分影片也对战争中的人性进行了具有国际视野的呈现与反思,但是这种呈现和反思仍然是浮光掠影的,而且浓重的政治色彩也削弱了反思的深度。“我们在以中国方式来阐释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以人类共通的方式来阐释中国价值,同时在阐释中既坚守我们的价值主体性,又能够跟全世界达成最大的公约数的问题上,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方式和手段”。[9]因此,怎样在保留民族文化内核的基础上,以开阔的国际视野,表达“反战”“和平”“人性”和“人文关怀”等人类共同价值观理应成为中国抗战电影未来的努力方向。
(二)重构抗战故事,实现由“抗战”叙事向“二战”叙事的位移
遵循以上价值观进路,中国电影需要转变思维,重构关于抗战的故事。而实现由“抗战”叙事向“二战”叙事和反法西斯战争叙事的位移是重构抗战故事的前提与基础。
从字面上看,“抗战”与“二战”区别有三:首先指涉的区域不同,前者习惯上指中国本土,后者指涉所有被卷入“二战”的国家和地区。其次战争主体不同,“抗战”作为“中国话语”,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专指中、日两个国家和民族的战争;“二战”作为“世界话语”,指同盟国与轴心国的战争,或者说是法西斯国家与反法西斯国家间的战争;再次,战争性质不同,前者体现的是民族独立之战,后者彰显的是反法西斯军国主义之战。可见,“抗战”与“二战”虽一字之差,却体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视野和维度,换言之,“抗战电影”这一称谓在自我认知上都未能主动融入世界“二战”和反法西斯战争电影之列。
从创作实践来看,中国抗战电影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从世界“二战”电影的整体图景中剥离出来,更未能凸显抗日战争作为“二战”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抗战电影无论从故事主题、故事主人公、故事时空甚至视听符号等叙事元素来看,都未能摆脱“中国式抗战”的特点,而且与世界经典“二战”电影比较,在视野的宽广度和反思的深刻性上都存在相当的距离。以同时斩获奥斯卡九项大奖的“二战”影片《英国病人》为例,影片鲜明的国际视野及“世界”意识对中国抗战电影创作具有某些启发和借鉴意义。首先是叙事空间的“国际化”或全球性,影片在全世界取景,甚至有意模糊故事发生地的国家属性或民族属性;其次是主人公的多国籍和多民族身份,影片主人公分别来自5个国家、民族和地区,虽然存在沟通障碍,但却具有普适的人性和情感;再次,在故事建构上,影片以“二战”为背景,讲述了一段凄美的跨国爱情,藉以呈现和比较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其带来的影响,探讨多元文化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最后,影片的价值观聚焦于婚姻伦理和国族身份两个方面。艾玛殊与凯瑟琳之间有失伦理的爱情“打破了国籍、战争、婚姻的枷锁,获得了精神上的富足。这样的‘破戒’旨在将人性从生命的桎梏中解脱出来”。[10]影片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方面强调文化差异导致的爱情悲剧,一方面极力渲染多民族文化的个性魅力;一方面凸显民族身份给主人公造成的致命创伤,一方面又构建了一个“无国无族”的理想境界。影片最终指向反对战争、追求自由和渴望和平的主题。但与主流的反战视角不同的是,《英国病人》并未着意凸显战争的性质是否正义,而是更强调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从这个角度上看,目前尚无一部抗战电影在故事建构和价值理念上达到这样的深度和广度。
(三)重塑话语:实现由民族话语向世界话语的位移
如果说价值理念属于电影的主题层面,故事讲述属于电影的内容层面的话,那么话语则属于电影的表达或者形式的层面。它涉及符号的选择和修辞的运用,因此更倾向于表达的艺术和技巧。学者胡智锋曾用“四不”概括了中国影视国际传播中的薄弱环节:“看不懂”“讲不清”“达不到”和“吃不透”。其中,“看不懂”和“讲不清”实际上涉及话语表达的艺术与技术问题。前者主要指不能将中国影视语言和文化符号转化成易于海外受众理解的语言符号,具体表现为字幕翻译、配音译制和文化符号表达上的问题,导致海外观众解码上的困难,更不用说接受文化符号背后的逻辑与价值;后者是指在中国故事的叙事表达上不清晰、不准确,难以很好地用影像描述和再现中国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中,普适性话语方式有助于在本土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搭建融通的桥梁,有助于外国受众“看得懂”和“听得进”。针对抗战电影的国际传播,其话语实践可从两个方面考虑:符号生产的在地化和修辞策略的国际化。
在地化(Localization)是相对于全球化的另一种趋势,最初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或商品流动必须适应目标地区的需求,才有可能加速发展。针对某种文化产品而言,在地化是指该产品能够为特定地区所接受的情况,换言之,文化产品的接受程度决定了在地化的程度。电影是依靠视听符号讲述故事、传达价值的艺术产品,符号是触及和刺激观众的首要的也是最直观、最重要的话语元素。电影是否实现在地化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目标受众对视听符号的接受程度。这里的“接受”涉及符号的技术解码和符号的情感认同,二者必须同时具备,符号的选择与建构才算成功。对此,好莱坞的电影实践可谓典范。近几年来,好莱坞进军中国文化市场、塑造文化认同的主要策略就是对中国文化符号的利用和转化,即“用中国元素讲美国式故事,传达美国价值观”。影片《功夫熊猫》是符号在地化生产的成功范本,电影从人物到道具容纳了很多中国元素,如从中国武术中选取老虎、鹤、猴子等动物元素,祥云、倒“福”字、灯笼、瓷器和竹筷、雕龙柱、太极拳、太极图等颇具民族特色的符号元素,显示其在地化实践。2015年在全球上映的科幻巨制《变形金刚4》中的中国元素包括维多利亚港夜景、广州小蛮腰、香港民居生活区和广州街道的特写等。该片在美国本土票房、口碑双失利,却在中国创下了票房历史纪录新高。除了场景符号外,好莱坞电影还常常取世界各地的故事素材为其所用,如借用中国古代花木兰故事,创作动画片《木兰》;借用埃及的古老传说创作《木乃伊》系列等。运用丰富的在地化符号和故事元素,大大增强了电影对于目标受众的接近性和亲和力。反观中国的抗战电影,虽然也邀请世界各地的明星参演,随之携带异族文化,但是在规模上难以与其他国家同类题材影片相媲美。
所谓修辞策略的国际化,是面对国际受众而采取的话语方法和技巧问题,意味着采用国际受众认可和喜欢的修辞方式。长期以来,中国电影在政治权力规训下形成了生硬说教、严肃刻板的面孔,以至于海外传播和接受捉襟见肘。“我们中国缺乏的,不能打进国际市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把寓教于乐、修辞和意识形态协调好。”[11]常常表现为以贴标签的方式去凸显爱国主义或者英雄主义,把讲述一个好看的故事变成粗糙生硬的政治说教,从而使影片呈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难以获得国际观众的认同。
全球化背景下,电影作为一种国际性语言,既是一种商业,也是一种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观。从根本上来讲,抗战电影创作尚需努力地将意识形态艺术地隐藏于电影叙事之中,不动声色地进行文化输出,传播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族文化。
若从1932年的第《共赴国难》算起,我国的抗战电影已历经88个春秋,其体量之大,作品之丰,令人欣慰。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国际反法西斯题材电影的既有成就相比,我们的抗战电影还有相当的差距。“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理想目标,应当是既体现艺术价值、又体现商业价值、并最终体现民族文化的魅力和价值。以此为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2]新时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抗战电影文本生产与消费越来越显示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一方面表现为抗战的崇高感、胜利的喜悦感和民族优越感,与此相适应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过度丑化敌人和刻意渲染仇恨,这种情绪很容易与现实社会中起伏跌宕的中日外交关系形成“互文”关系,导致非理性的社会舆论与行为。正因如此,抗战电影更应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彰显民族优秀品质的前提下,通过抗战故事引导观众的理性思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中,倡导“反战和平”这一积极的战争观。一言以蔽之,面对文化的全球竞争与传播,抗战电影应以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人类意识书写抗战历史,重构抗战记忆。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抗战电影在国际传播中实现抗战精神与价值的全球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