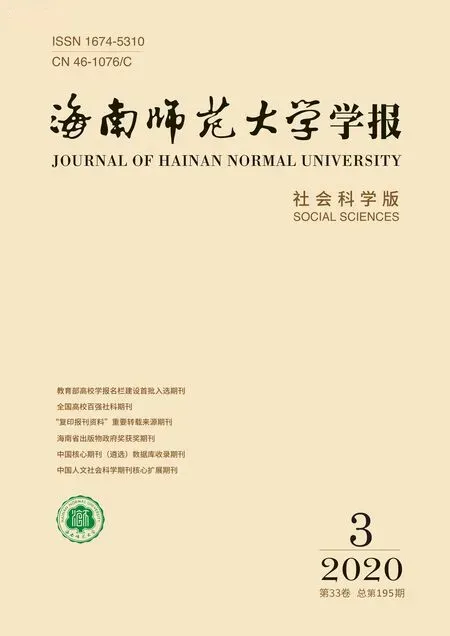论吉加·维尔托夫对中国电影理论的影响
朱言坤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中国电影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百年中国电影创作实践为基础的,同时又敞开胸怀,积极译介外国电影理论著作,从中吸纳理论创造所需要的各种思想资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电影理论不同程度上接受西方的影响,其深度和广度往往超过中国的文学理论和其它艺术理论”。(1)罗艺军:《中国电影理论研究——20世纪回眸》,《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在译介到中国的丰富多彩的西方电影理论中,吉加·维尔托夫创建的“电影眼睛”理论,对中国和“世界纪录电影以至艺术电影的影响都是巨大而久远的”(2)俞虹:《苏联蒙太奇学派》,《当代电影》1995年第1期。。
吉加·维尔托夫(Дзига Вертов,1896—1954,以下简称为维尔托夫),原名丹尼斯·阿尔卡其耶维奇·考夫曼,苏联著名电影导演、编剧、电影理论家,“电影眼睛派”的创建者与主导人物,苏联纪录电影的奠基人之一。
维尔托夫的《电影周报》与《电影真理报》成就了苏联新闻电影,他所创作的《电影眼睛》(1924)、《持摄影机的人》(又译为《带摄影机的人》1929)、《热情:顿巴斯交响曲》(1931)等纪录片,既是其理论创造的实践基础,又是实践其“电影眼睛”理论的典范。
维尔托夫在《我们:一个宣言的变体》(1922)、《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1923)、《从电影眼睛到无线电眼睛》(1929)等文章中,用散文诗般的语言反复申述,电影首先是用来观察、发现和认识真实的世界与世界的真实的,而能达此目的的只有纪录电影。因此,只有纪录电影才是真正的电影,戏剧化的剧情片都是“麻醉人民的毒药”,应该判其死刑,让纪录电影取而代之。维尔托夫强调电影的纪实性,指出应摒弃虚假,把镜头对准现实世界客观地拍摄,随机发现和捕捉真实的生活与生活的真实;反对使用剧本和演员,反对搬演,不用化妆、照明和布景等手段。维尔托夫认为电影摄影机可以承担起发现和认识世界的重任,因为电影摄影机如同人的眼睛,但又胜过人的肉眼,“把电影摄像机当成比肉眼更完美的电影眼睛来使用”,可以“探索充塞空间的那些混沌的视觉现象”(3)[苏联]吉加·维尔托夫:《从电影眼睛到无线电眼睛》,皇甫一川,李恒基译,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增订本)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第 216 页。。维尔托夫认为电影不仅要真实地纪录客观世界,而且要解释客观世界。为了能更好地解释世界,应探索实验包括蒙太奇在内的各种电影技巧。维尔托夫认为电影眼睛的基础是蒙太奇,蒙太奇是各个画面的组织,只有运用蒙太奇来重新组织那些来自生活的原始素材,电影才能很好地揭示现实,发现并解释世界的本质真实,从而获得艺术感染力。维尔托夫把自己既客观又主观的复杂理论概括为一个简单明了的理论公式:“电影眼睛=电影视觉(我通过摄影机看)+电影写作(我用摄影机在电影胶片上写)+电影组织(我剪辑)”(4)[苏联]吉加·维尔托夫:《从电影眼睛到无线电眼睛》,皇甫一川,李恒基译,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增订本)上册,第 227 页。。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不仅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而且至今依然具有难以逾越的先锋色彩。
“电影眼睛”理论,于20世纪30年代初译介到中国,对现代中国的先锋电影与左翼电影的理论与创作都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再次译介到中国,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特别是“新纪录电影”的理论与创作,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维尔托夫对中国先锋电影理论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既是中国电影的转型期,同时也是中国电影理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与变革,与有声电影的出现、电影流派和电影团体之间的理论争鸣与创作竞争、外国电影理论的译介等有关。外国电影理论的译介,为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与变革,提供可资借鉴吸纳的理论资源。中国电影人译介的外国理论,有来自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各种电影理论,如法国的印象派-先锋派电影理论等;有来自苏联的电影理论,如蒙太奇理论、“电影眼睛”理论等。其中,对“电影眼睛”理论,“新感觉派”电影人刘呐鸥、左翼电影人石凌鹤等,都进行了介绍和阐述,而以刘呐鸥最为积极,其颇具先锋色彩的电影理论与电影创作受到维尔托夫的影响也最大。
最早系统介绍和阐述维尔托夫“电影眼睛”理论的文章是刘呐鸥的《俄法的影戏理论》。在这篇文章中,刘呐鸥将“电影眼睛”译为“影戏眼”,认为“影戏眼”是“最进步的最尖端的”理论(5)刘呐鸥:《俄法的影戏理论》,《电影》1930年第1期。,并对“影戏眼”理论的基本观点、内在逻辑与外在原因等做了简明而准确的介绍与阐述。在《影片艺术论》《论取材:我们需要纯粹的电影作者》《Ecranesque》等文章中,刘呐鸥所阐述的先锋电影理论,借用并转化了很多外国电影理论,而以“电影眼睛”理论影响最大。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五点。
第一,刘呐鸥认为,电影是“机械艺术正在摇篮时代”的宠儿(6)刘呐鸥:《影戏·艺术》(原载于《无轨列车》1928 年第4期),康来新,许秦蓁合编:《刘呐鸥全集·电影集》,台南:台南县“文化局”,2001年,第247页。,多了些其他艺术形式没有的“机械的要素”(7)刘呐鸥:《影戏·艺术》(原载于《无轨列车》1928 年第4期),康来新、许秦蓁合编:《刘呐鸥全集 电影集》,第246页。,“最能够性格地描写着机械文明底社会的环境”(8)刘呐鸥:《Ecranesque》(原载于《现代电影》1933年第2期),康来新,许秦蓁合编:《刘呐鸥全集·电影集》,台南:台南县“文化局”,2001年,第282页。,因而是内容与形式都随着时代走的“艺术界的革命儿”(9)刘呐鸥:《影戏·艺术》(原载于《无轨列车》1928 年第4期),康来新,许秦蓁合编:《刘呐鸥全集·电影集》,第246页。,是最具先锋性与时代性的艺术样式。这种观点,既有法国先锋派电影理论的影响,也有来自“电影眼睛”理论的影响。如维尔托夫在发表于1922年的《我们:一个宣言的变体》中就这样说:“电影也是一门根据科学的要求在空间中创造事物运动的艺术;它体现了发明家的梦想,无论他是学者、艺术家、工程师还是木匠;它是电影化的对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梦想的实现。”(10)Edited by Annette Michelson, Translated by Kevin O’Brien ,Kino-Eye: The Writings of Dziga Vertov,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9.
第二,刘呐鸥注重电影摄影机在电影艺术中的地位与作用,宣称以开麦拉即摄影机为主导的“Cameraman System的时代”的到来(11)刘呐鸥:《中国电影描写的深度问题》(原载于《现代电影》1933年第3期),康来新,许秦蓁合编:《刘呐鸥全集·电影集》,台南:台南县“文化局”,2001年,第294页。。“开麦拉能够觉察‘言外之意’,能够把我们普通的视觉所觉查不到的状态和过程表示出来,……是一个自己的形式的创造者。”(12)刘呐鸥:《影片艺术论》(原载《电影周报》1932年第2-15期),康来新,许秦蓁合编:《刘呐鸥全集·电影集》,台南:台南县“文化局”,2001年,第259页。这种观点的形成,也主要是受“电影眼睛”理论的启发与影响。在世界电影理论史上,维尔托夫最早强调摄影机在电影艺术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他认为摄影机优于人眼,能看到人眼看不到的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并且能把看到的记录下来,让人们看到只有摄影机才能“看见的世界”(13)[苏联]吉加·维尔托夫:《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皇甫一川,李恒基译,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19页。。摄影机既然如此重要,所以要解放“处于可怜的奴隶状态”的摄影机(14)[苏联]吉加·维尔托夫:《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皇甫一川,李恒基译,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第216页。,提高摄影机的地位。刘呐鸥虽然批评“Vertov 是一个机械主义者,所以他的主张未免太倾重于机械的崇拜”(15)刘呐鸥:《影片艺术论》,康来新,许秦蓁合编:《刘呐鸥全集·电影集》,第269页。,但他自己同维尔托夫一样看重摄影机的作用,只不过他不关心摄影机对现实的发现与认识作用,而更关注摄影机在使电影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中的作用。
第三,刘呐鸥认为“影戏应该有影戏的特质”(16)刘呐鸥:《影戏漫想:影戏和演剧》(原载于《无轨列车》第5期),康来新,许秦蓁合编:《刘呐鸥全集·电影集》,台南:台南县“文化局”,2001年,第252页。,强调电影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性,获得独特性的途径是科学的机械表现手段,反对电影过分依赖字幕、文学、戏剧等非电影的艺术手段。刘呐鸥在多篇文章中反复申述:“影艺既然是新艺术,应当有独特的新锐性,有它自己的美学”(17)刘呐鸥:《论取材:我们需要纯粹的电影作者》(原载于《现代电影》第4期),康来新,许秦蓁合编:《刘呐鸥全集·电影编》,台南:台南县“文化局”,2001年,第295页。,“‘影戏的’(Cinegraphique)这语底内容包含着非文学的,非演剧的,非绘画的,这三素性。”(18)刘呐鸥:《Ecranesque》(原载于《现代电影》1933年第2期),康来新,许秦蓁合编:《刘呐鸥全集·电影集》第282页。“电影是科学(光化学,工学)和艺术的混血儿。所以它的表现上根本就有了许多遗传的机械性。只就这一点它就已经是跨过了从来诸艺术如文学,绘画,雕刻,音乐,戏剧等的领域外了。”(19)刘呐鸥:《中国电影描写的深度问题》(原载于《现代电影》1933年第3期),康来新,许秦蓁合编:《刘呐鸥全集·电影编》,第286页。也就是说,电影应该从戏剧、绘画、文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运用由科学(光化学,工学)所获得的艺术的机械表现手段,去创造具象化的、运动的时间和空间,从而成为具有独立美学品格的“新艺术”,即“‘电影的’电影”(20)刘呐鸥:《电影节奏简论》(原载于《现代电影》1933年第6期),康来新,许秦蓁合编:《刘呐鸥全集·电影编》,台南:台南县“文化局”,2001年,第311页。。电影艺术的机械表现手段,涉及运动、节奏、镜头、角度、机位、时空处理、取材、表演等问题,刘呐鸥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极为专业地深入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刘呐鸥的这些理论探索,是最贴近电影艺术本性的,也是最先进的,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对电影的认知电影观念,虽然有多样的理论来源,但与其“电影眼睛”理论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关系。维尔托夫认为用“电影眼睛”方法拍摄的非虚构电影才是具有“电影性”的电影(21)Edited by Annette Michlson,Translated by kevin O’ Brien,Kino-Eye:The writings of Dziga Vertov,p5.,反对用文学、戏剧方法拍摄的虚构叙事电影,并对此前非“电影性”的所有电影判处“死刑”(22)[苏联]吉加·维尔托夫:《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皇甫一川,李恒基译,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第216页。。维尔托夫反对剧本、演员、化妆、照明、布景等虚构叙事电影的惯用手段,但在技术上做了多方面的实验探索,拍出了《电影眼睛》《持摄影机的人》等世界电影名作。刘呐鸥所说的“‘电影的’电影”,近似于维尔托夫所说的“电影性”的电影。刘呐鸥也如上文所述主张用电影化的诸种方法创作“‘电影的’电影”,但不反对戏剧性的叙事电影。这是他既受“电影眼睛”理论影响,又与其有很大不同的地方。
第四,刘呐鸥的蒙太奇理论也受到维尔托夫蒙太奇理论的影响。刘呐鸥对普多夫金与维尔托夫蒙太奇理论的异同有准确的理解和认识。刘呐鸥将普多夫金的Montage译为“织接”,认为“织接”是“影片生成上最生命的要素”(23)刘呐鸥:《影片艺术论》(原载于《电影周报》1932年第2-15期),康来新,许秦蓁合编:《刘呐鸥全集·电影集》,第258页。,其作用在于能够把零碎的、片断的动作和影像按照统一构想组织成为一个时空连续的整体,从而创造出新的“被摄了的现实”。刘呐鸥认为维尔托夫的“影戏眼”蒙太奇比普多夫金的蒙太奇更进了一步,“能够在千千万万的主题中选出一个主题,能够在种种的观察中作一个更便当的选择而实行主题的创成。她具有感情、气力、节律和热情。”(24)刘呐鸥:《影片艺术论》(原载于《电影周报》1932年第2-15期),康来新,许秦蓁合编:《刘呐鸥全集·电影集》,第268页。刘呐鸥敏锐地注意到维尔托夫的“影戏眼”蒙太奇的“思想性”不同于普多夫金“织接”蒙太奇的“叙事性”特征。尽管刘呐鸥认为维尔托夫的“影戏眼”蒙太奇比普多夫金的“织接”蒙太奇更进了一步,也将前者的蒙太奇理论作为其认识和评价电影的理论依据之一,但他更偏爱后者的“织接”蒙太奇,这当然与刘呐鸥不反对虚构叙事电影的艺术趣味与追求有关。
第五,刘呐鸥认为电影是“温情主义的资本家所出卖的‘注册商品’”,是“逃避现实的催眠药”,这表明刘呐鸥已认识到电影作为一种工业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25)刘呐鸥:《Ecranesque》,(原载于《现代电影》1933年第2期),康来新,许秦蓁合编:《刘呐鸥全集·电影集》,第283页。。刘呐鸥的这种认识,也有来自“电影眼睛”理论的影响。维尔托夫将传统的戏剧化的剧情片视为“麻风病”,是宗教的同类——对人民的麻醉剂,是“致命的毒药”(26)Edited by Annette Michelson, Translated by Kevin O'Brien,Kino-Eye: The Writings of Dziga Vertov, p7.。他认为苏维埃电影的任务是纪录社会主义的现实。刘呐鸥受其影响,认识到电影的资产阶级文化属性,但并不像维尔托夫那样进行激烈地批判,反而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从现在的影片除掉了催眠药性的伤感主义,非理智性,时髦性,智识阶级的趣味性,浪漫和幻想等,这现代人的宠物可不是要变成了一个大戈壁吗?”(27)刘呐鸥:《Ecranesque》(原载于《现代电影》1933年第2期),康来新,许秦蓁合编:《刘呐鸥全集·电影集》,第283页。这种既否定又肯定的犹疑态度与立场,反映出刘呐欧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既批判又迷恋的矛盾心理。
刘呐鸥是“电影眼睛”理论最早的译介者,也是“电影眼睛”理论最早的接受者,从上述五个方面可以看出,“电影眼睛”理论对刘呐鸥先锋电影理论的影响之大之深。20世纪30年代,受“电影眼睛”理论影响的中国电影人除了刘呐鸥之外,还有穆时英、黄嘉谟等“新感觉派”成员,但他们在电影理论方面的建树远不如刘呐鸥,这里不再展开分析。
二、维尔托夫对左翼纪录电影理论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与电影实践的发展因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影响,总体上处于低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纪录片创作却应时而动,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拍摄手段和纪录手法上都走向成熟,出现了袁牧之导演的《延安与八路军》、郑君里导演的《民族万岁》、陈晨拍摄的《华北是我们的》等一大批纪录了战争年代珍贵历史影像的纪录片。中国电影人对纪录片的功能、形态特征、创作方法等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纪录片理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与战争时期的宣传需要、战争年代物资匮乏对电影创作的限制、战争时期中国电影人对纪录片的重视、外国纪录电影理论的影响等因素有关。
在这一时期,“电影眼睛”理论及“电影眼睛派”成员罗曼·卡尔曼的纪录片理论,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的纪录片理论,英国纪录片运动的重要人物保罗·罗沙的纪录片理论等,都是中国纪录电影理论吸纳的重要理论资源。就“电影眼睛”理论而言,本时的中国左翼电影人对其有所论述,受到的影响也大一些。以下仅就最具代表性的左翼电影导演袁牧之、郑君里与“电影眼睛”理论之间的影响关系略作分析。
袁牧之是中国左翼电影的重要导演,主要从事剧情片创作,其导演或参与表演的《桃李劫》(1934)、《都市风光》(1935)、《风云儿女》(1935)、《生死同心》(1936)、《马路天使》(1936)等,都是有影响的剧情电影。袁牧之有关电影理论的探讨也主要集中在剧情电影的表演理论等方面。袁牧之编导的纪录片,最有名的是《延安与八路军》,这是他落实“抗日计划——拍摄新闻纪录片”的未竟之果。袁牧之的纪录片理论表述,也与这部纪录片的创作有关。
1940年2月,袁牧之结束《延安与八路军》的素材拍摄,在返回延安的途中,接受了时任绥德警备区《抗战报》编辑殷参的采访。在访谈中,袁牧之“大谈”了他对纪录电影的定义、起源、功能、拍摄方法、未来发展等问题的看法,而他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看法,与维尔托夫“电影眼睛”理论有比较显著的关系。具体而言,主要有五点。其一,袁牧之认为,纪录片“创始在苏联十月革命时代”,革命后的苏联红军“夺得照像机,大量的摄取新兴力量的新闻片。浮笃夫(Vertov)在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显明的主题之下,整理和剪接许多新闻片,创造了‘纪录片’。”(28)殷参:《袁牧之带着摄影机从敌人后方来 大谈纪录电影与边区剧运》,《中国电影》1941年第2期。袁牧之所说的“浮笃夫”即维尔托夫,其对苏联纪录片的发生学描述是很准确的。其二,袁牧之认为,“纪录片不是故事片,也不是新闻片”,纪录片的“特殊任务是报导系真实现实”,“可以有完整的主题”,但其一切材料、背景都应该是真实的现实,即维尔托夫所说的“电影眼睛=事实的电影记录”(29)[苏联]吉加·维尔托夫:《从电影眼睛到无线电眼睛》,皇甫一川,李恒基译,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第227页。,其“表现或强调的方法不是想象”(30)殷参:《袁牧之带着摄影机从敌人后方来 大谈纪录电影与边区剧运》,《中国电影》1941年第2期。,即不能虚构。其三,纪录片因其“真实”而具有强烈的政治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开麦拉对正现实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种会暴露了社会的黑暗,给统治者增加困难。”(31)殷参:《袁牧之带着摄影机从敌人后方来 大谈纪录电影与边区剧运》,《中国电影》1941年第2期。在苏联,维尔托夫的纪录片“与革命同步”,不仅要展示苏联的“革命的生活方式”,而且“由电影眼睛开始,创造红色苏联电影。”(32)Edited by Annette Michelson, Translated by Kevin O’Brien ,Kino-Eye:The Writings of Dziga Vertov, p71.在抗战时期的中国,不仅需要纪录片“从抗战的各方面反映这苦难中的伟大的中华民族”,而且“也正是新的电影的准备时期,打下创造伟大的电影作品的基础。”(33)殷参:《袁牧之带着摄影机从敌人后方来 大谈纪录电影与边区剧运》,《中国电影》1941年第2期。袁牧之表达的革命诉求,与维尔托夫拍摄纪录片的革命诉求,虽然具体内涵有别,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其四,袁牧之认为,纪录片创作“如果能够事前有周密具体的计划,或者事后从丰富的材料里集中一个主题剪接,在中国的电影界将是一个创造。”(34)殷参:《袁牧之带着摄影机从敌人后方来 大谈纪录电影与边区剧运》,《中国电影》1941年第2期。这两种创作方法,前一种与维尔托夫的主张不尽一致,后一种则与维尔托夫的理论相同。如维尔托夫说:“电影眼睛是:蒙太奇,当我选择一个主题时(从成千个可能的主题中选一个)。”(35)[苏联]吉加·维尔托夫:《从电影眼睛到无线电眼睛》,皇甫一川,李恒基译,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第229页。袁牧之对纪录片创作中“事后的蒙太奇”在主题提炼与思想表达方面的作用,与维尔托夫有相同的认识。其五,袁牧之认为,纪录片的“艺术性比较差,正和通讯带有文艺性而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一样。”(36)殷参:《袁牧之带着摄影机从敌人后方来 大谈纪录电影与边区剧运》,《中国电影》1941年第2期。这种观点与维尔托夫的观点是相悖的,维尔托夫否定戏剧化的电影,只认可“电影眼睛”的纪录电影才是电影。袁牧之主要是剧情片导演,在他心目中,“比较高级的艺术”还是“故事片”,譬如,他认为苏联“故事片《夏伯阳》就是茁长在新的基础上光辉的艺术成果”(37)殷参:《袁牧之带着摄影机从敌人后方来 大谈纪录电影与边区剧运》,《中国电影》1941年第2期。,使欧美人改变了对苏联电影都是“红色宣传”的看法。概言之,袁牧之的纪录片理论既受到了“电影眼睛”理论的启发与深刻影响,也在一些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同为左翼电影人的郑君里,参演或编导了《新女性》(1935)、《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乌鸦与麻雀》(1949)等颇具影响力的剧情片,其有关电影理论的探讨,也主要集中在剧情电影方面,如《角色的诞生》《画外音》等。郑君里编导的纪录片,最有名的是《民族万岁》(1940)。郑君里在完成这部纪录片后,写了《关于纪录电影的特征》《我们怎么制作〈民族万岁〉》等文章,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表述了对纪录片的认识和看法。
郑君里自述,他的纪录片理论知识来自英国纪录片导演保罗·罗沙(郑君里译为保罗·罗扎)的纪录电影理论与苏联“电影眼睛派”成员罗曼·卡尔曼的纪录电影理论。郑君里认为,“到当时为止,我们的纪录电影仍停留在纪实的新闻片的格局上。同时在欧美苏联,纪录电影正展开一个‘纪实的’或‘戏剧化’的理论上的争辩。”(38)郑君里:《我们怎么制作〈民族万岁〉》,《民族万岁:郑君里日记1939—1940》,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354页。而“纪实的”与“戏剧化”有很大的区别。所谓纪录电影的“戏剧化”,就是“对实事加以创造的处理”,如保罗·罗沙所说:“纪录电影的方法上的精髓就在于对实事的材料加以戏剧化。……戏剧化才是纪录电影的特性。因此,在纪录电影中,甚至事实的平铺直述也需要戏剧性地传译,从此事实才能‘活生生地搬上’银幕之上。”(39)郑君里:《我们怎么制作〈民族万岁〉》,《民族万岁:郑君里日记1939—1940》,第355页。所谓“纪实的”,就是“以为纪录片的任务在于保存被摄的对象的真实性”,如罗曼·卡尔曼所说:“在事实的报道里,走戏剧化的路,这是取巧的邪路。谁都知道用纪录法拍摄事件的片段,即使它拍摄得不充分,没有中心,但比起改动失真的照相来,观众可相信得更深些。”(40)郑君里:《我们怎么制作〈民族万岁〉》,《民族万岁:郑君里日记1939—1940》,第355页。郑君里认为,“纪实方法的优点在于能保存被摄对象的真实的神韵,这种神韵绝不能受我们工作者自由支配的。”因此,“乐于这样做”(41)郑君里:《我们怎么制作〈民族万岁〉》,《民族万岁:郑君里日记1939—1940》,第356页。。但在《民族万岁》的拍摄中,“十分之九”采用的是“戏剧化的方法”,其原因,一是他熟悉故事片的拍摄方法,二是战时胶片短缺,三是有预设主题的约束。郑君里转述并认可的罗曼·卡尔曼的“纪实的”纪录片理论与“电影眼睛”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可以说,郑君里的纪录片理论与创作受到了“电影眼睛”理论的间接影响。
如上所述,“电影眼睛”理论对袁牧之、郑君里等左翼电影人的纪录片理论及创作产生了直接的或间接的有益影响。可惜的是,这种影响到了20世纪50年代没能延续下去。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和模仿苏联电影体制,致力于把新闻纪录电影拍成“电影人民日报”,但采用的创作方法并不是维尔托夫式的,而是苏联导演格拉西莫夫与瓦尔拉莫夫分别在中苏合拍片《解放了的中国》《中国人民的胜利》中采用的戏剧化方法,而这种方法正是维尔托夫所反对的。1955年,《世界电影》第7期译介了苏联大百科全书里的“Д·维尔托夫”词条,该词条认为维尔托夫的理论是“错误的理论”,将“电影眼睛派”贬为形式主义。此后的30年间,维尔托夫淡出了中国电影人的视野。
三、维尔托夫对“新纪录电影”理论的影响
维尔托夫重新走进中国电影人的视野,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先是中国电影学界对“电影眼睛”理论及其影响下的“电影眼睛派”进行了学术研究与评介。1983年,郑雪来在论述西方“生活流”电影时,对当年正热的“真实电影”“直接电影”与“电影眼睛派”做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分析。郑雪来认为,“‘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的实践家和理论家们在解释维尔托夫的创作原则时,却忽视了这些原则的主要意义。维尔托夫作为苏联早期纪录电影大师、‘电影眼睛派’的创始人,决不是主张无所用心地照录事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要求‘对现实进行共产主义的阐释’的,他搞的‘电影真理报’与‘真实电影’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此。”(42)郑雪来:《漫谈西方“生活流”电影》,《电影新作》1983年第1期。20世纪80年代末,姚晓蒙对维尔托夫的蒙太奇理论做了研究和评介,认为“维尔托夫的特点是在保持镜头内容真实的条件下,强调摄影师运用镜头之间的剪辑去发挥电影分析、综合现实的功能,也就是说,蒙太奇在纪录片中不再只是为连接镜头的技术手段,而是分析概括生活的意识形态工具”。纪录片既要富于“政治的激情”,又要有“真实的诗意”(43)姚晓蒙:《保卫蒙太奇》,《电影艺术》1989年第7期。。
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学人皇甫一川、李恒基翻译了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带摄影机的人》《从电影眼睛到无线电眼睛》等三篇文章,这是目前国内能见到的最早的译文。这三篇译文包含了“电影眼睛”理论的主要思想,对“电影眼睛”理论的传播意义重大。专门的研究文章也多了起来,如皇甫一川的《世界电影流派一览:电影眼睛派》对“电影眼睛派”做了专文介绍(44)皇甫一川:《世界电影流派一览:电影眼睛派》,《电影评介》1991年第9期。,翻译家俞虹的《苏联蒙太奇学派》对维尔托夫的电影理论做了系统的评介(45)俞虹:《苏联蒙太奇学派》,《当代电影》1995年第1期。。进入21世纪后,中国研究维尔托夫的文章日益增多。
“电影眼睛”理论经过中国电影学界的译介与研究,得到广泛的传播,不仅已成为中国电影人必备的“电影知识”,而且已浸润到中国电影人的电影观念与电影创作中,对中国电影理论与电影创作,产生了积极有益的影响,而受其影响最为显著的就是“新纪录电影”等。
中国当代“新纪录电影”,学界有“新纪录片”“独立纪录片”“边缘纪录片”“地下纪录片”等不同的指称,虽然用语不同,但所指的对象与范围大致相同,为便于论述,本文使用“新纪录电影”概念。“新纪录电影”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兴盛于90年代,至今还在发展过程中。可列入“新纪录电影”创作者的人很多,如张元、吴文光、段锦川、蒋樾、温普林、时间、郝智强、李小山、康健宁、林鑫、丛峰、王兵、宁瀛、李红、杨荔纳、雎安奇、王兵等,这份名单其实还可以列得更长。这些“新纪录电影”的创作者,受到影响外来电影理论的影响是多样的,有来自“电影眼睛”理论的影响,有来自法国“真理电影”、美国“直接电影”的影响,也有来自日本电影人小川绅介的影响。这些不同的纪录电影流派、理论、方法之间,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甚至会有矛盾冲突,但其最初的理论思想之源都是“电影眼睛”理论。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新纪录电影”导演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维尔托夫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纪录片导演丛峰。
丛峰做过气象工作,当过教师、编辑,成为独立电影人后,陆续拍摄了《信仰》(2006)、《持遥控器的人》(2007)、《马大夫的诊所》(2007)、《未完成的生活史》(2010)等纪录片。在拍摄纪录片的同时,丛峰陆续撰写并发表《丛峰:纪录日常真实》(访谈)、《百叶窗——电影/影像随想》《贫乏电影的任务》《献给维尔托夫》等文章,表述自己的纪录片理论。
丛峰在《献给维尔托夫》等文章中,将自己的纪录片理论命名为“新电影眼——社会复眼”。其理论内涵与“电影眼睛”理论之间有直接的影响关系。具体而言,主要有六点。第一,同维尔托夫一样,强调摄影机在发现世界真相、认识现实中的工具作用。丛峰认为:“摄像机是生产工具,是现实的切割机,是挖掘机的抓斗。”(46)丛峰:《百叶窗——电影/影像随想》,《艺术广角》2014年第2期。新世纪的“拍摄者”即纪录电影创作者有“以摄像机——影像手段为工具,对抗时代中的毁灭力量的职责。”(47)丛峰:《献给维尔托夫》,《艺术广角》2019年第1期。第二,同维尔托夫一样,看重纪录电影流派的作用。维尔托夫的“三人委员会”(或曰“电影小组”)是以维尔托夫为主的电影组织,发展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电影眼睛派”。丛峰提出,新世纪的纪录电影创作者不应再是单个“持摄像机的人”,他们应该成为复数,共同组合为“新的电影眼”。丛峰文中的“成为复数”的“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只是有共同追求的一群纪录电影创作者,每个人都可独立发现社会现实的真相,合起来就成为电影的“社会复眼”。第三,同维尔托夫一样,要求用“新电影眼”观察社会,对现实“再发现”,展示社会的真相与真实。反对用电影制造奇观,认为制造奇观的电影是对“平庸腐朽的表象的被动堆积与展示”(48)丛峰:《献给维尔托夫》,《艺术广角》2019年第1期。。第四,同维尔托夫一样,强调运用剪辑去分析、综合现实,即蒙太奇不只是连接镜头的技术手段,还是分析概括生活的意识形态工具。“纪录电影本身的真实性不因其方式(‘纪实’)本身而得到保证,其真实性只能来自于对现实材料的使用方式”,“通过对拥有的现实片段进行处理,生成了另一种现实——第二种现实是通过梦的透镜产生的第一种现实的投射。”(49)丛峰:《百叶窗——电影/影像随想》,《艺术广角》2014年第2期。第五,强调“新电影眼——社会复眼”应成为“社会内视”,即“一种文化——社会的内在批判视野”,而不是简单的“电影视觉”,即不是“视觉的、光学的、影像的观看”(50)丛峰:《献给维尔托夫》,《艺术广角》2019年第1期。。维尔托夫在苏联革命的早期,强调对资产阶级等的批判。丛峰也强调批判性,但其所指已与维尔托夫有了很大的不同。第六,“新电影眼——社会复眼”应该“用于制作教育——启蒙电影:自我教育与社会教育,自我启蒙与社会启蒙。”(51)丛峰:《献给维尔托夫》,《艺术广角》2019年第1期。丛峰与维尔托夫都强调纪录电影的启蒙教育作用,但就内涵而言,前者与后者又有所不同。概言之,丛峰的“新电影眼——社会复眼”理论受到“电影眼睛”理论的直接影响,又与之有所不同。在“新纪录电影”创作者中,丛峰的“新电影眼——社会复眼”理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中国“新纪录电影”的创作者,如胡文光、段锦川、林鑫等,虽然没有专门的电影理论文章,但在访谈、演讲、微博等话语形式中表述的对纪录电影的认识和观念,都或隐或显地受到了来自维尔托夫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电影眼睛”理论对新世纪中国电影人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深刻。
四、结语
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于20世纪30年代初由中国“新感觉派”电影人刘呐鸥与左翼电影人石凌鹤等译介到中国,对刘呐鸥等人的先锋电影理论、袁牧之和郑君里等人的左翼纪录电影理论,都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翻译家俞虹、皇甫一川、李恒基等再次将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译介到中国,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特别是以丛峰等人为代表的“新纪录电影”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维尔托夫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电影流派和电影人的影响,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不论是显在的还是隐性的,不论是正解还是误读,总体上看,都是积极有益的,打开了中国电影人的理论视野,促进了中国现代电影理论特别是纪录电影理论的发展。
维尔托夫的电影理论著述很多,辑录比较齐全的有苏联学者C.德罗巴申科搜集整理出版的维尔托夫文集俄文版《文章·日记·构思》(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66年版),有美国学者阿奈特·麦克尔逊主编的英文版《电影眼睛:吉加·维尔托夫文集》(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等。目前,中文译文仅有《我们:一个宣言的变体》《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带摄影机的人》《从电影眼睛到无线电眼睛》等几篇,国人难窥全貌。维尔托夫的电影作品,国内可以看到《持摄影机的人》《电影眼睛》《关于列宁的三支歌》《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热情:顿巴斯交响曲》等几部。如果能将维尔托夫的电影理论著作及电影作品完整译介,对中国电影理论与电影创作的影响,将有更加积极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