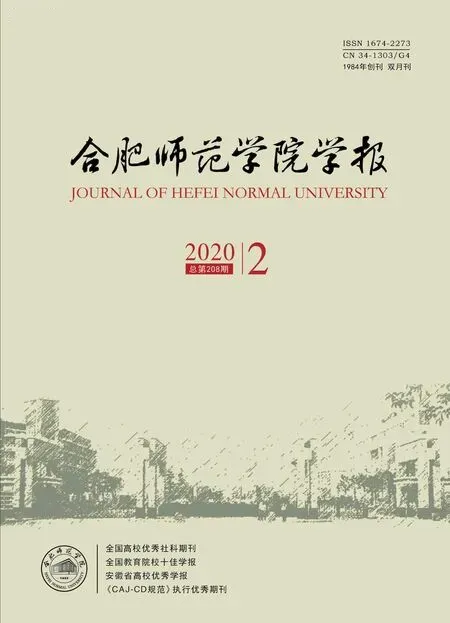晚清桐城派“中兴”的出版因素
——以曾国藩、萧穆交游为中心
束 莉
(安徽大学 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安徽 合肥 230039)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终于迎来了与太平军鏖战九年之后的第一个“拐点”:是年九月,湘军克复军事重镇安庆。此后四年,直至同治三年(1864)攻陷天京(江宁),曾国藩驻辕安庆,筹划并推进了一系列安邦求治之策,其要旨即在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早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任职于翰林院的曾国藩即协同倭仁前去拜会理学名臣唐鉴,从此服膺程朱之学,并很快成为理学经世派的领袖。对于践行程朱理学的桐城派,曾国藩也颇为推崇,于咸丰八年(1858)、咸丰九年(1859)分别作《欧阳生文集序》与《圣哲画像记》两文,表达自己“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1]第14册,第247页的学术取向。驻防安庆期间,经过深入探访,曾国藩认识到了桐城派所深陷的危机与复兴的潜力:乾嘉以来,汉学昌明、骈文流行,坚守程朱理学的桐城派已处于“文敝道丧”的穷途;然而世变时移,随着道光、咸丰年间中外局势的颓败,桐城派文以载道的文化理想、雅洁实用的文风,却又恰好能够吻合丧乱过后,人们厌弃繁琐考证、穿凿华靡,讲求实学的需要。多年奔波作战,饱尝“客寄孤悬”之苦的曾国藩,决定“加盟”并改造桐城派,以理学为召唤,以古文为器用,维系人心,涵纳新学。为此,他探访耆老、提携后学、收辑典籍、振衰除弊,培养出了以“曾门四弟子”为中心的一批古文大家,直接促成了桐城派在同治、光绪年间的“中兴”。此一文坛盛事及其深远影响,学界已有精辟论述。(1)参关爱和:《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吴汝纶的学术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曾光光:《曾国藩与“桐城中兴”》(《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范丹凝《“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的产生与接受》(《烟台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等文。然而,回到中国古代的文化情境,文学书写的活跃与文献编纂的繁盛通常是一体两面、相互促进的。同治、光绪年间,曾国藩及其弟子不仅以丰富的撰述对桐城义法进行了发扬光大,也在桐城派经典著述的辑存和出版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资料显示,与曾国藩关系密切的桐城后生、被誉为桐城派“后起之英”的萧穆(1834—1904,字敬孚,亦作“敬甫”“敬父”)[2]1,即为兹事的主要受托者与执行者。
一、萧穆与晚清桐城派经典文献的辑存、出版
据《清史稿·文苑传》,萧穆“遇孤本多方劝刻,所校印凡百余种”[3]第33册,第12445页,视野颇为广阔,而细察相关资料可知,桐城派经典文献的搜辑与刊刻,实为其古籍整理事业中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以下结合时间及内容,对相关典籍作一介绍:
1.光绪八年(1882),助王先谦编选《续古文辞类纂》。
2.光绪十五年(1889),为黎庶昌编纂、校勘《续古文辞类纂》。
3.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吴汝纶共同出资刊刻刘大櫆《历朝诗约选》。[2]42-43
4.约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前后,撰成并刊刻《国朝桐城文征约选》。
5.光绪二十七年(1901), 校勘姚鼐《古文辞类纂序》毕。正月元日,代出资者、滁州富商李承渊作《校刊古文辞类纂序》。
*以上为桐城派重要选集。
6.同治七年(1866),为安徽巡抚英翰校勘《刘海峰集》。
7.同治十一年(1872),编定姚鼐《惜抱轩尺牍》。[2]196
8.光绪二年(1876),代冯焌光校勘方苞《朱子诗义补正》。[2]95
9.光绪四年(1878),为曾国藩弟子吴桐云校勘其《小酉腴山馆诗集》。[4]序言页
10.光绪九年(1883),助马其昶编订《重编左忠毅公文集并年谱定本》。[2]35-37
11.光绪十八年(1892),撰写并刊刻《戴忧庵先生事略》一卷。
12.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后,校刻《张文端公全书》。[2]93
13.咸丰四年(1854),抄录《刘海峰先生唐宋八家文选》。[2]39
14.咸丰七年(1857),抄录《孙麻山先生遗集》。[2]37
15.光绪十五年(1889)抄录钱澄之《田间尺牍》。[2]171
16.抄录《跋方望溪先生所传录归震川史记标录》。[2]105
*从此本开始,成稿时间不详。
17.抄录方世举《方息翁汉书辩注》。[2]107
18.抄录方世举《方息翁手评贾阆仙诗》。[2]151
19.抄录方世举《春及草堂笔记》。[2]317
*以上为桐城派名家著述。
20.同治九年至十年(1870—1871),与马起升共修《桐城志稿》。[2]310
21.编撰《桐城耆旧传状碑志汇钞》,时间不详。[5]397
*以上为有关桐城的地方志著作。
综上可知,萧穆所纂辑的多种桐城派相关著作,可分为三个类别:诗文选本、名家撰述、地方志著作。它们在各自的类别中,多具有经典价值。如诗文选本类的《古文辞类纂》系列,它们在晚清民初的桐城派古文选本中,是最为核心的。其面貌的最终定型,萧穆功不可没。同时,桐城派的名家别集及地方志,亦经由萧穆,完成了重要版本的编辑,基本确定了其传世面目。对于暂时无力刊刻的珍贵稿本,萧穆也以钞本的形式,完成了初步的编纂工作,避免散佚,促进传播,并为刊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从古文研习者到古籍编纂出版名家
在萧穆问学的初期,他和无数桐城学子一样,服膺乡贤的古文成就,并以文章作者自期。他以朱道文、苏求敬、刘宅俊、文汉光、汪正堃诸位先生为师,以左庄、马木庵、马慎庵等为友,其古文获得了“气力醇厚,颇近先秦、两汉”(《刘悌堂先生墓志铭》并序)[2]203的评议。然而,正如《年谱》所云,萧穆在读书撰文的同时,也出现了另一动向:“时已留心朝章国故,注意网罗文献,开始收书、抄书。” 这样“分心”的表现,实与当时桐城特殊的文献环境有关。
首先,桐城历经咸丰兵燹后,文献的收辑、保存实为燃眉之急。
据《年谱》,咸丰三年(1853)起,“太平军占领安庆及桐城。桐城城内读书老辈多移居乡间,其大家藏书亦多散出。萧穆因之得亲师友,以广见闻,并收得某些图籍”。据萧穆自述,此一阶段他收获颇丰:“时邑中穷年为贼所距,世家大族所藏之书,兵火之余,贫民拾得一二,出售于外。余族人某有获书数千卷,乃午夜翻阅,取数十种。”(《孙麻山先生遗集后序》)[2]27因战火而导致的文献纷披,却给萧穆这样的寒门少年提供了饱览与收藏图籍的机会,实为意外之幸。
其次,桐城派发展到道、咸之际,著述丰硕,但大量前辈名家的成果,此时尚未得到及时整理。在已编校的著述中,精善之本也并不多见。有些总集收之过滥,未惬人心。如咸丰七年(1857)春,萧穆得徐璈《桐旧集》读之,并作《书桐旧集后》,“既欣慕乡先辈功力之勤、搜览之博,使一邑之文献可考,而又惜其拾之太滥、择之不精也。夫前人流传之集,原为后人之所取法;而总集尤宜加谨严,不第为后人取法其词章之工,且以一邑之人品、学术,为后学之金鉴也”[2]78-79。
最后,道咸之后,禁书渐出,激发起学者们的探究兴趣。(2)参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第十二章《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清史稿·文苑传》评价萧穆:“博综群籍,喜谈掌故,于顾炎武、全祖望诸家之书尤熟。”[3]第33册,第12445页参之萧穆文集,可知其对清代前期因触犯忌讳而殒身的乡贤,实有表彰之热忱。咸丰十一年(1861),27岁的萧穆即为因“《南山集》案”获罪的戴名世作传,题为《戴忧庵先生事略》。[2]275另外,与戴名世关系密切的宿松人朱书(字杜溪),其文章对桐城派的形成亦有着导源之功。戴名世罹难后,“朱公后人悉取原版及印本,拉杂焚之。至嘉庆以后,其原刊全本,宿松旧家已不可得”[2]174。萧穆对此深感痛惜,对朱书遗文详加考述,并撰《跋杜溪文集》,期待其早日获得整理、刊布。
如果说桐城当时的文献环境使得萧穆的学术兴趣发生了某种倾斜,那么,曾国藩的指点与提携,实为其改变学术志愿更为关键的原因。
据萧穆《敬孚日记》,他拜谒曾国藩,乃在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其引荐者为曾国藩的弟子、桐城友人姚慕庭、徐宗亮。这次拜谒乃为其业师、桐城文士朱鲁岑求助营葬之资。此次相见,曾国藩不仅慨然应允资助,且“下问久之”,礼遇周备。(3)其事见《敬孚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29册,第288页。萧穆《朱鲁岑先生墓志铭》:“两江制府曾相国闻先生学行,慨然助白金若干,属邑人甘君绍盘为买山资,以同治元年夏□月□日,葬先生于龙眠山都家窊之原。……相国大书刻碑,题曰‘大清文学朱君鲁岑之墓’。”《敬孚类稿》卷十一,第301页。
作为年轻士子,萧穆在拜谒曾国藩之时,依然系心科举。他于同治二年(1863)考中秀才,以第二名入桐城县学;后于同治三年(1864)、同治六年(1867)赴江宁参加乡试,惜未能中举。而据姚永朴《萧敬孚先生传》,萧穆“少谒曾文正公于安庆。文正语人曰:‘异日缵其邑先正遗绪者,必此人也。’”[2]559也就是说,曾国藩对于萧穆的期许,并非科举入仕,而是乡贤文献的整理。萧穆从同治十一年(1872,时38岁)开始,任上海广方言馆翻译馆编纂(文字润色)一职近三十年。此事有多种文献记载,均以曾国藩为荐举者。然据萧穆《敬孚日记》,此事实由曾国藩弟子吴桐云、沈秉成促成,事在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6]第30册,第661页二人为萧穆安排此事,意在为其提供一个“安研之所”,使其“快意读书,得以讲论”[6]第30册,第661页。“自此以后,三十余年,萧穆只身在沪,住一小楼。母、妻均在故乡,每年两次回桐省视。又常因校书、刻书往来于江宁、苏州等地。……时南北文人学者,经过上海,必访萧穆,互观所藏书籍,商量学术,交换见闻。”(《年谱》)光绪二十七年(1899),67岁的萧穆,在《与溥玉岑大司空书》中,仍再三致意:“下走寓海上二、三十年来,耳目闻见,自度精力已衰,不能附和维新诸人,仍确守曾文正公遗训,时时仍以朝章国故为念。”[2]93
“确守曾文正公遗训”,为何对萧穆如此重要呢?结合其出身和经历,其中缘由或可推断。据萧穆在《先宅记》[2]426-428、《先考溪源君序略》[2]428-431中的自述,萧氏先世姓陈,徽州婺源人。明初,因赘于萧氏,遂改姓;经过历代迁居,最终定居于桐城汤家沟东十五里钱氏小墩。其祖萧永兴、父萧锡光,相继为里中富室刘氏司事,故萧穆幼年时,家境才稍有起色。太平天国期间,江淮之间多为兵锋所扰,萧氏因居所僻远,得以幸免于难。然而,功名的缺失、地缘的偏僻,再加上清代桐城众多文化家族的辉映,萧氏此一枝系可谓黯淡。青年萧穆凭借自身的勤勉,获得了一定的称誉,结交了一批乡邑先辈与同辈才俊,眼界却难称宽广。曾国藩驻守安庆,延揽名士,其中不乏海内知名的耆旧宿儒,如汪士铎、钱泰吉、莫友芝等多人,安庆俨然成为长江要冲上的才士荟萃之所。萧穆先后在曾国藩及安徽巡抚英翰等处任幕僚,侍从请益,学问、襟怀皆为之拓展。而后,他又在曾门弟子的安排下,来到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任职,迈出了从乡邑贤士成为海内名家的关键一步。其问学志趣的转向与文化处境的提振,皆得益于曾国藩及其弟子群。萧穆一生服膺曾文正公之学行,孜孜以其遗训为念,便不难理解了。
三、守正与开新:萧穆与清末桐城派的学术进境
萧穆的学问根柢于桐城,然而,作为“后起之英”,他的文献采编范围,已远远超越前贤的视野。
(一) 破除汉宋畛域的学术取向
从乾嘉时期起,汉学与宋学的纷争就俨然成为桐城派与考据学派、经世学派的聚讼所在。从学术角度来说,萧穆也认为汉学不无可商榷之处,但对其文献的辑存,却同样重视。例如,对于汉学中坚惠栋,萧穆即指出其“好为大言,好为僻论”的缺点,但却肯定其《左传杜氏补注》《汉书补注》等著作具有“拾遗补阙之功,洵有裨于后学”(《记惠半农松厓两先生阅明北监本汉书》)[2]217-218。光绪二十五年(1899),刘世珩刊《惠松崖先生文集》,其底本即为萧穆于同治十二年(1873)过录赵元益所藏旧抄本,及其所搜辑的书序、碑志等,共40篇,与清代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所记载篇目相符,对其著作面貌的还原可谓贴近历史真实,其功甚伟。[2]50
(二)不拘骈散的文章观念
清代乾嘉以来,桐城派以唐宋八大家为宗,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典范,将汉唐以来的辞赋、骈文均排除在文学殿堂之外,表现鲜明的“辨体意识”。画地为牢的师法范围、机械套用的撰述规则,也逐渐窒息了自家文派的活泼生机。至道光、咸丰年间,有识之士开始倡导“不拘骈散”的文风,为文坛带来了新鲜气息。萧穆以自身的编校实践,对这种新动向给予了呼应与支持。他曾校勘骈文选本《六朝文絜》(光绪三年,1887),并作《重刊六朝文絜后序》,认为该书“考订入微,同异不苟,可备学者之新闻”[2]51。在与黎庶昌共同编订的《续古文辞类纂》中,亦设“箴铭”“颂赞”“辞赋”等的骈文类目,以供学者研习。
(三)保存清代皇室档案的呼吁
光绪二十七年(1901),萧穆作长函《与溥玉岑大司空书》,委托其代为查看“京师大内及各重地所藏列朝实录及国史各类,并保和殿东、西廡所藏世宗硃批有无残缺”[2]93。萧穆以一布衣,急切呼吁大内档案的保存,实基于国家危亡之际的特殊形势。就在作此书札的前一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萧穆作《跋临川桂氏摹刻唐拓孔子庙堂碑拓本》,慨叹“惟今京师拳匪横行,继以各西人联兵纷扰,大内所藏古今珍物,一旦空诸所有,此两墨宝已不可问矣。北望神京,万感交集,此尤其小焉者也”[2]183。民国时期,这批档案的价值被罗振玉、傅增湘等学者发现,经过数次波折,入藏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建国后统一交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为与殷墟甲骨、敦煌藏经并列的二十世纪中国重大文化发现之一。回溯历史,萧穆的先见之明令人敬仰。
(四)促进域外汉籍的回流
光绪八年至十年(1882—1884),黎庶昌、杨守敬等在日本刻成《古逸丛书》,海外古籍珍品首次集中亮相,士林为之耸动。作为黎庶昌的多年知交,萧穆在黎庶昌的接应下,于光绪十四年(1888)冬,自筹旅资,前往日本访书。此行收获颇丰,而归国之后,他感念域外汉籍的珍贵,多次催促黎庶昌在《古逸丛书》之后,再精择汉籍付刻,然黎忙于政务,无暇顾及。光绪十三年至十五年(1887-1889),黎庶昌第二次出任驻日大臣期间,萧穆致函,云:
年来风闻中外士大夫皆以执事此次出使毫无建白,与前判若两人。愚以执事前此出使之功,不过为精刊《古逸丛书》,究竟此书不过刊工精致,多为小品,紧要者不过三五种,若宋刊《史记》、两《汉》,洋洋大观,目下虽无经费办此,而传校一部回中华,鼓励他人刊版,以广流传,其功仍在执事,惠而不费,弭谤之方,莫妙于此。今执事以无暇及此,请托他人为之云云,似以为鄙人之私事。今合两事观之,执事之神志荒惑,日暮途远,已见于此,鄙人惟有为之长太息而已矣。[7]157
言辞可谓激切,然萧穆保存典籍之急切,亦豁然可见。
(五)重史地边疆之学
在萧穆校刻的书籍中,地方志及史地著作所占比重相当大。他亲自纂修的地方志有《桐城县志》(同治九年至十年,1870—1871)、《续修句容县志》(光绪二十七年,1901);抄录辑存者有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华度《亳州志》等。史地著作,刊刻者有西清《黑龙江外纪》及萨英额《吉林外纪》等,抄录辑存者有《孙渊如先生水经注手校本》等。《年谱》认为,无论是亲自纂修,还是刊刻、钞录,“萧穆之校刊古书与其关心朝章国故,皆有经世致用之意,于此可见”。而萧穆自己亦有剖白,呼吁“讲求舆地之学,有备经世实用者,(于地理书)不能不深有所取焉”(《跋吉林外记》)[2]119。
以上所列数点,常有交叉之处,兹不赘述。更值得陈述的是,萧穆对于文献的关注与否,并非仅关乎个人喜好,而是与曾国藩影响之下,晚清桐城派共同的学术取向密切相关。
首先,清代中期开始,地方督抚权责并重,他们对于统辖地区的文化往往有着显著的化导效用。姚鼐的学生、昆明人钱沣于乾隆末期任职湖南学政,他奉行程朱理学,“视学湖南,以正谊笃行风楚之人,所取率多端士”(《葛寅轩先生家传》)[1]第14册,第280页。钱沣弟子葛寅轩,即为曾国藩父亲曾麟书的老师。因此,曾国藩日后为官,所到之处,对于文化尤为关注。他希望萧穆致力于董理乡邑文献,并非偶然,而是基于重塑桐城派这一文化构想的郑重嘱托。也正因为此,萧穆所担当的古籍整理一事,就远远不是穷经皓首的机械劳作,而是具有经世价值的文化创举。
其次,曾国藩及其麾下士人,于国家动荡之际,戎马倥偬,弦歌不缀。特殊的政治时势和问学环境,足以展拓其胸襟,对安徽、江浙、湘乡等多个文化区域给予平等观照,促使它们从汉宋、骈散之争等“零和博弈”中解脱出来,在整合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开眼开世界,接纳新鲜事物,稳步走向近代转型。因此,萧穆以乡邑文献为经,以多种类型文献为纬,错杂而有序,恰好为桐城派的视野拓展,提供了多维度的文本支撑。
四、余论
客观审视曾国藩与萧穆的交游,二人其实难称亲近:萧穆虽然短暂充任过曾府幕僚,却并未求取格外的恩宠;曾门弟子众多,萧穆亦未侪身其中。他密切交往的,其实是与其有着共同爱好的曾门士子,如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等。某种程度来说,他类似于一个曾门的“编外人员”。可贵的是,萧穆以过人的热忱与定力,竭尽才力,终生践行曾国藩的嘱托,成为当之无愧的古籍校勘、出版名家。吴孟复在《文献学家萧穆年谱》中评价道:“有清一代,吾皖经学、文章,焜耀海内。惟目录、版本、與地之学,逊于江浙。萧穆以穷乡之寒士,终成为清末之文献名家。”[2]567也就是说,萧穆在文献整理、出版方面的成就,实际上代表着桐城派在目录、版本、舆地等领域,对于原有疆域的拓展。清末、民国的桐城派后学,往往从他那里获得问学的津梁。姚永朴作《萧敬孚先生传》,称:“在上海凡数十年,四方贤公卿,下逮游客,语及见闻洽熟,必曰‘萧君’。”[2]559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中,称其生前“相识遍天下”,“没后,藏书散轶,人争传宝,书贾至盗其收藏印记,价辄倍蓰。”[5]397始为桐城寒族,终成名家师长,萧穆以自身的文献编纂事业,助力桐城派“中兴”这一文派消长大势,堪称真谛所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萧穆去世的半年前,他曾前往湖南长沙,拜访时任湖南布政使的张筱传,即桐城名臣张英六世孙,“将以《续修桐城县志》及刊布先辈经世实用诸书商之”[8]4026。然而,张筱传虽然厚加款待,并浏览了他所开列的乡贤应刊书名录,却未作回应,萧穆失望而回。在离开长沙之前,萧穆特意探访了该地的曾国藩祠,并在祠中的思贤书局购得《曾太傅读书记》一书。“于湘江归舟中逐卷阅之。乃深服公生平阅书处处入细,一字不肯放过,考订之精,识议之博,益人心思,实非浅鲜。归里后,发春之暇,将用硃笔标录一过,传示子孙。”[2]79在这寂寞的归舟中,阅读着曾太傅遗文的萧穆,心中所系念的,依然是当年的恩情与嘱托。而他难以解悟的是,桐城子孙对于乡邑文化遗产不再关心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晚清的落幕,桐城派短暂的“中兴”也将徐徐拉上帷幕。同样,“缵其邑先正遗绪”这一文化使命,也从富有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变成被遗忘的话题。萧穆就像一个刻舟求剑的愚者,停留在同、光年间的文化经纬上,依依不忍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