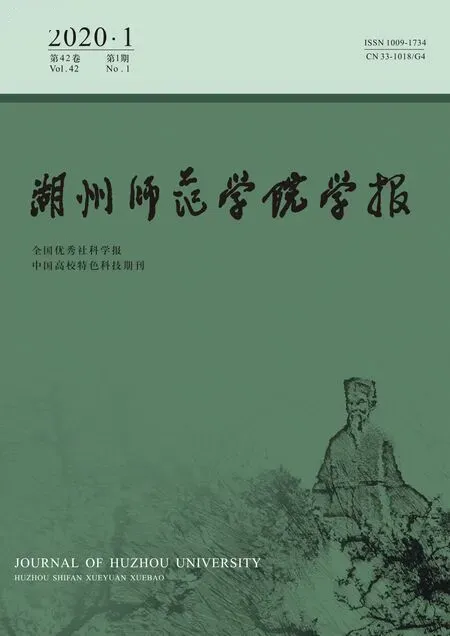道家文化对林语堂创作思想的影响*
阮慧玲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林语堂所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坛,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多元存在,启蒙与救亡成为华文创作的主旋律,左翼作家们表现出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和深刻批判,这样的文学创作主流是值得肯定的,民族大义与国家重责应摆在一切问题的前面,只是过分为政治主导的文学也必然存在失之偏颇的地方,比如文学的智性与审美性被遮蔽,比如柔性文学对战争创伤的治愈力量,比如接纳万物的包容之心。
林语堂因其所倡导的“幽默性灵”文学被视为文化转型期的一支清流,从而形成标颖独到的人格符号。而对一位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必须有一个历时性统观的视角。林语堂先生文学创作之路的选择与美学思想的最终确定,经历了一个摸索前行与受挫思变的过程。林语堂先生于20世纪初在文坛崭露头角之时,文风“浮躁凌厉”,大有要与旧文化彻底决裂的凛然姿态。直至1927年始在政治高压下经历了亲侄遭枪决、同盟社杨杏佛被暗杀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林语堂先生孤独彷徨,开始“大荒中寂寞的孤游”,他无奈地意识到“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1]20卷,47,在文化思想上他更近老庄一步,在文学创作中他奉公安三袁为不祧之祖。
一、身于尘世,不脱缰现实的“有所隐”
林语堂在20世纪初淡出主流文坛的隐逸,并非彻隐,而是身于尘世、不脱缰现实的“有所隐”。隐逸之举是被“迫成隐士”的无奈之举,是明老庄之哲的保身之举,亦是回归田园初心的道家诗学之举,是用道家文化解释世界、疗愈战乱疮痍的聊慰之举。
(一)回归田园初心的城市生活
中国有历史悠久的隐逸文化渊源,居高岸深谷的巢父、许由,委运任化的陶渊明等等,亘古不乏高士、文人的怀古与归隐,但隐逸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对现实的逃避和消极对抗,它是平衡外在压力与内心冲突的一种处世态度,在个体生命价值的体认方面表现出一种诗意的崇高,它源于道家生存的智慧,是在“道不济”“道不盈”状态下的自我实现。林语堂欣赏道家放低姿态、隐匿锋芒的做法,视《老子》为“世界文学中最辉煌、最顽皮的自我保护哲学著述”[1]20卷,99。但我们看到林语堂在短暂出仕后的隐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彻底地归隐,而是有选择的“有所隐”。他依然选择城市生活,只是在城市生活中注入了田园的元素,他以城市文化心理来审美观照田园,再以田园淳朴气息向往城市文明,因为城市生活的便利与田园初心的回归,二者都不可或缺。在他眼中,“城中的隐士”优于山林的隐士,中庸之道的中产阶级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群,因为“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名字半隐半显,经济适度宽裕,生活逍遥自在,而不完全无忧无虑的那个时候,人类的精神才是最为快乐的,才是最成功的”[2]117。
林语堂是被“迫成隐士”的,但远离权力中心和主流话语,也恰好给予他一种边缘关照社会与现实的淡泊心态和客观视角,给予他所谓的“超政治、近人生”的文学观。很多左翼作家作品,因为与政治粘得太近,充满一种“凡事必与救国相连”的“方巾气”和“猪肉味”[2]367,且不说是不是政治图解式或意识号令式,放之今日看他们的作品缺乏隽永流传的活力,而远离政治话语中心的少数作家的作品却因为保留了文学本质的审美品格而获得被一代代解读与阐释的生命力。“隐逸”之逸,本身就含旷达和逸放的意味,表现于文学创作的题材中便擅写田园山水、虫鱼花鸟等一切生活自然事,表现于文学创作的风格中便显出冲淡、平和与闲适的况味。林语堂的文学创作也不外乎此,在旅美后的第一部书稿《生活的艺术》中,我们看到他谈“茶和交友”“论花和折枝花”等等出自生活逸趣的作品,现相无相,立说无说,哲思蕴藏,理趣浑然。林语堂说“趣”,认为“人生快事莫如趣,而且凡在学问上有成就的,都由趣字来”[3]215。隐逸之藉,让隐逸者从外部世界退回主体世界,自由抒写本真的自我,而非社会关系中的自我,以一种审美的精致的眼光领悟自然和生命的整体意义。
(二)以逸放外的道家智慧注目时局
看似逍遥自牧外于政事的林语堂,依然选择关注时局,甚至未停止思考整个人类命运走向与发展的问题。在避免政治危势的锋芒下,他以更加自由的身心投入到文化的介绍、传承和创作中。“中国人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迁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2]114,中国人浓郁的生命意识和现世的态度,决定他们的思维向度,不求渡彼岸世界,不逃离文明,或选择脚踏实地的儒家精进精神,或是选择通过韬晦和隐忍来消解内外矛盾的道家智慧。正如林语堂所说:“吾们倾向于放弃不可捉摸的未来而同时把握住少数确定的事物,吾们所知道可以给予幸福于吾们者,吾们常常返求之于自然,以自然为真善美永久幸福的源泉。”[1]20卷,314
左翼文化主流对林语堂多有批判,认为倡幽默性灵之论不合于当时世,既非关乎经国之伟业的载道文学,又非唤醒民众之觉醒的启蒙文学。这样的观点是偏颇的,“幽默”之于文艺观、之于生存环境,绝不是左翼所说的缺乏灵魂实质的或是麻醉人民的“笑笑而已”,幽默本身代表的是一种温厚而宽容的包容立场。林语堂并不赞同文艺界知识分子奔走呼号大揽社会责任的方式,他纵横历史,思接千载,指出所谓魏晋名士清谈误国实则是种错误归因,他理解并认可魏晋名士的隐逸姿态,指出“晋之亡不在阮籍猖狂,而在昏君暴主杀人如麻使阮籍不得不猖狂之环境”[1]14卷,179。当然,比起魏晋隐逸文人的狷介狂放,林语堂的在野显得更加理性和自律。实际上林语堂之隐是有所隐而非彻隐,他选择用道家文化解释世界并试图化解社会危机,用道家的价值符号在现实的土壤里进行新的建构,以期达到一种疗愈社会与人心的效果,“老庄文章气魄,足使其效力历世不能磨灭”[3]148。他肯定道家的柔、弱、俭、让的智慧,对于以强权政治妄图建立属于他们的世界统治秩序的西方国家,他规劝他们在内政外交方面学习道家“内不弊外不挫”的方略,懂得“不争而善胜”的政治智慧[1]23卷,137。而对于民族危亡的时局,他首先有一个日本必败的清晰判断,因“日本军力万不足以征服中国,财力万不足以长期作战,政治手段又不足以收服民心”[4]35,西安事变不是政治绑架,而是全民族团结抗战抵御外侮的始端。正如老子所说“夫慈以战则战,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子·第六十七章》)。他并不信奉蛮力解决问题的方式,“坚则毁矣,锐则挫矣”[3]145,道家贵柔守雌的处世方式同样适用于国际争端问题的解决,道的世界讲求齐物与平等,世界不应该是对抗性的,不同质的文化形态可以圆融共存。林语堂还推崇道家的“无为”,他的书房取名“有不为斋”,在作品《奇岛》中他描绘了一个乌托邦的社会,推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的治世理想。对于被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所异化的西方人的精神世界,林语堂也给予了深切的悲悯同情,他认为心为物役、身为形役是因为数理逻辑的哲学思潮排斥了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探索,只讲求效率、准时、成功的“美国三大恶习”[1]21卷,154便是最悲哀的人之异化的表现。道家的哲学能够实现对人之异化的矫正和救赎,“见素抱朴”的安俭生活与“法天贵真”的超然自适,能帮助人摆脱膨胀的物欲和冰冷的理性,从而多了自由与温情的生命情怀。
二、性灵、浪漫、富于想象力的道家美学
在浩瀚无垠的中国文学史历程中,道家一派长于譬喻与警寓之文,富于性灵与浪漫之篇,如玄映空月,峡云层起,乃千秋文脉。郭沫若说:“中国文学史大半是在《庄子》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林语堂所倡性灵一派文学根邸在于道家美学,表现出独抒自我、不役文法、贵真尚质、浪漫奇崛的美学品格。
(一)庄子美学为性灵文论的衍出之源
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林语堂极为推崇公安三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艺观,在《论文》《狂论》《说浪漫》《说潇洒》等诸多文章中都提及公安三袁。他给“性灵”下了“性灵就是自我”[1]14卷,147之定义,又说“性灵赖素时之培养”[1]18卷,236,“由于性灵之培养,乃有豪放之议论,独特之见解,流利之文笔,绮丽之文思”[5]77,强调“性灵之启发,乃文人根器所在,关系至巨”[1]14卷,152,哀乎“性灵之摧残致文学之干枯”[1]14卷,152。林语堂对“性灵”文艺观的推崇和发扬,直接导源于公安三袁,间接导源于庄子。庄子美学是公安三袁文论思想的主要衍出之源。
袁宗道言己“《道德》、《南华》,以及竺典,亦多涉猎(《送夹山母舅之任太原序》)”。他反对明前后七子“篇篇模拟”之袭古,不仅被格套束缚,而且缺乏真情真意,“今之圆领方袍,所以学古人之缀叶蔽皮也;今之无味煎熬,所以学古人之茹毛饮血也”[6]65。文章的语言也不必蹈袭前人,“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1]14卷,148,语言是自然创现的,“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1]14卷,147。袁宗道的这些文论思想皆来源于庄子的“法天贵真”,“真者,所以受于天地,自然不可易也”(《庄子·渔夫》),“真”从来就是生发共情的内在力量,“真”由道家的哲学概念逐渐演变为审美概念。是谓性灵,必是真性真情,“大喜者必绝倒,大哀者必号痛,大怒者必吼叫动地,发上指冠”[1]14卷,147,这是不加矫饰的真性情,无切身之感而勉强发文则若“戏场中人”,“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6]68,这是文章因陈蹈袭缺乏性灵之秀的症结所在。林语堂也说:“性灵派文学主真,发抒性灵,斯得其真,得其真,斯如源泉滚滚,不舍昼夜,莫能遏之。”[1]14卷,154袁中道曾作《导庄》,认为日常生活中“道书除却眼难开”“左置庄周右离骚”,思而总结半生境遇再回读庄子,便发出“近日颇精《人间世》,全生大抵要无才(《春日》)”的感悟,其文学创作也深受庄子影响。对于公安派“不拘格套”的文论观,林语堂认为“意之所之,自成佳境,决不为格套定律所拘束”[3]114,并进一步阐释“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1]14卷,151的文体解放论。
作为公安性灵派的核心人物,袁宏道是林语堂提及最多次、赞誉最高的一位,遇到与自己文学气质相近的人,无异于“灵魂之转世”,甚觉是“智力进展里边一件最重要的事情”[1]21卷,353。袁宏道曾做《广庄》(共七篇)阐释庄子思想,其文“纵横跌宕,出入玄墨,可与郭象抗衡”[7]5卷,208。虽然他对《庄子》一书的阐释存在有与庄子原旨不相一致的地方,但诚如清人尹廷铎所言,“注《南华》者,自向秀、郭象以来,无虑数十家,率皆支离蒙混,大都依稀仿佛间,而《南华》之旨率未大白也”[8]162。袁宏道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发展也是自然不过的,但其受庄子影响至深,在其文论思想中皆有体现。他所标举的性灵,除了出自庄子“法天贵真”的主张外,还与庄子重视人本之“性”有关,《庄子·骈拇》中载“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庄子言辞素被视为长满“诋訾”孔门的棱角,在庄子看来,就是仁义礼仪的灌注使人伪装了起来,不以性之本然的面貌示人。林语堂进一步阐释,不止仁义礼仪伤天性,智慧亦伤天性,“不要运用智慧去发展人性,应该顺乎自然去发展天性;因为迎合天性的合于道德,运用智慧就会伤害天性”[9]14。道家向来是厌智甚至是弃智的,提倡应“绝圣弃智”,因为看到了智识发展的负面,就是对性灵的伪饰甚至扭曲。袁宏道深受庄子思想影响,他认为文贵出性之本然、情之真诚,就不用有自菲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不必初、盛也”[7]5卷,208,“古之不能为今者也,势也;今之不必搴古者也,亦势也。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7]5卷,759,即文章因世势、时势、情势而变,不信古不厚今,自然而然,又说“文章新奇,无定格,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7]5卷,763。袁宏道的创作践行了其文论主张,性灵标颖,也常将庄子书中题材放置到自己作品中,如“兴来学作春山画,病起重笺《秋水》篇”[7]8卷,329,“十分学得漆园五,逍遥犹可物难齐”[7]8卷,330。林语堂言:“人生在世,无一事非情,无一事非欲。要在诚之一字而已。诚便是真。去伪崇真,做文做人,都是一样的。”[10]24人如其文,在作文之外言及做人之真,便是不压抑真实性情,不扭曲真实人格。对于在仕的体验,庄子以神龟做喻,“宁其死为留骨而贵,宁其生而曳尾涂中乎”,坦然选择后者;袁宏道苦叹在仕“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林语堂也数次入仕受挫,他说“也许在本性上,如果不是在确信上,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他们对仕途的淡泊,除了“全生葆真”的宗旨外,亦有庄子所谓的避“金斧夭害”之意。公安派的文章曾被批评为“轻率浅露”,缺乏蕴藉,除了“宁今宁俗”的俚俗语入章,“不复计较字句之文野”[3]312外,部分也与公安派尚质求淡的文论主张有关,他们反对藻饰之文,主张化绮为质,从枯见腴。袁宏道言“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7]35卷,203,林语堂也说“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11]61,又说“不知写作润饰为何物,只如春水奔江,滔滔而下;如老吏断狱,出口成章;如盲女唱曲,字字如珠”,质与性灵、淡与贵真,自然联系在一起,从这里亦可见庄子美学品格的蔚然濡染。林语堂从袁宏道淡朴自然的尺牍中获得确立其语录体小品文文体的启发,他认为小品文应“笔调极轻快的,以自然清新为主”,从而使得“中国文体必比今日通行文较近谈话意味了”[12]118。
(二)浪漫情怀与奇崛想象力的道家美学
林语堂认为深受道家思想浸染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宗教的作用一语,足以说明道家美学的渗透力和信仰力。“自是道家思想遂成为中国之浪漫思想,若放逸、若清高、若遁世、若欣赏自然,皆浪漫主义之特色”[13]360,这与道家倡导的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的超然人生观相得益彰。林语堂赞誉老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警句制作者之一,《老子》一书以格言警句式进行书写,它简约不多言,达理不炫智。但在文学创作领域,相比于老子的俏皮圆滑式的冷淡,庄子显得更深邃而迷人,在他洋洋十万言的无端崖之辞内,充满浪漫的情怀与人文色彩的思考。林语堂所处的时代与庄子生活的“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庄子·则阳》)”的战国时代极为相似,人的生存的相似境遇和共同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使二者在不同的时空产生共鸣。战争灾难的背后引发人对终极生存意义形而上的思考,更加向往一个有道的真理的世界。庄子所谓的“道”,并不是指自然本体,而是人的本体,他把人作为本体提到道的宇宙的高度来说明[14]172—175。庄子行文,汪洋恣肆,行所欲行,止所欲止,但浪漫不只是主体强烈的抒情和高度的自我表现,它更是对现实苦难的艺术性超越,亦是对道之真理的叩问与追寻,即“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林语堂认为庄子是中国所曾产生的最伟大及最有深度的哲学家,因为他觉察到且能表现出人生难以忍受的内在的不安,他超越生与死的意义,他关注灵性的宇宙问题,“把万物自性的追求看作世界的最高真理”[2]246。庄子是中国的帕斯卡,“没有人比他更感到为一切变迁所摆布的人生之可悲”[15]139,但这种可悲却是以真挚的美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3]148。
在汪洋辟阖、仪态万方的《庄子》中,“藉外论之”的寓言充满奇崛而瑰丽的想象,如“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逍遥游》),极言鲲鹏之大与奋飞,实现一种天地广阔乘物以游心的逍遥理想,将抽象的哲理借想象的神来之笔具象化。清胡文英评《逍遥游》:“前段如烟雨迷离,龙变虎跃;后段如清风月朗,梧竹潇疏。善读者要拨开枝叶,方见本根,千古奇文,原只是家常茶饭也。”王国维认为《庄子》一书可当为散文诗来读,因其想象力之伟大之丰富,“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这种想象力独于屈原、庄子等南人身上见着,而“决不能于北方之文学中发见之”,故这种想象力特喻名为“南人精神”(《屈子文学之精神》)。道家文学这种气势恢宏的想象力,林语堂极为钦赞,“想象力被用来给平凡、枯燥的世界罩上一层美丽的面纱,使这个世界的脉搏和我们的美感一起跳动”[1]20卷,91,并且叹止庄子的异禀才情,“庄子的风格是属于一个才智的巨人,再加上玩世的机智,经常准备好的天赋想象力,及一个作者熟练的表现力。”[15]134道家的天真浪漫与想象力、艺术化的情境、直觉体验的方式,亦是观照世界和审视人生的态度,林语堂认为“就其本质来看,正是一种审美的态度”。他还发现中西方艺术可以打通,他所肯定并借鉴于创作的克罗齐和斯宾加恩的表现论与庄子美学有相通的地方,“庄子为求得精神上之自由解放,自然而然地达到了近代之所谓艺术精神的境域”[16]60,它们都属于纯艺术论,都主张体悟的直觉性,重视想象等一切感性经验,都反对艺术的功利性考量和逻辑性分析推断,推崇“坚强深厚和一致性的主体情致”[17]28的艺术天才。朱光潜也常用庄子“鱼相忘乎江湖”来阐释克罗齐,即所谓的“形象直觉论”。而正是这种“为艺术而艺术”[16]27的艺术精神,将审美提到无上高度,真正保护了文学自性和作家自性。
林语堂对道家美学的肯定与发扬,集中表现在20世纪30年代对小品文写作的倡导,他所明确提出的闲适、性灵、幽默文艺观,“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学——可称它为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理的态度。”[2]133此外,他更在其直接的创作中体现道家哲学、美学的精神。如为之立传并向西方介绍的深得道家隐逸文化精髓的陶渊明、一蓑烟雨任平生飘逸洒脱的苏东坡等历史人物形象,以及创作的“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中自由逍遥的姚思安、中法自然的姚木兰、写《科学与道教思想》并研究“人性的害虫”的孔立夫等一系列小说人物形象,可以说这些人物的再现与塑造加入了林语堂自身的理性思考与秉性投注,既有旅美生活中所接受的西方科学、民主、自由的元素,又有传承道家文化的性灵、浪漫、幽默的特点,这些综合的文化特质在林语堂笔下绽放出异彩。“以道家思想为基本立场、以科学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价值观,这种新价值观在道家思想与西方科学精神之间建立起融通的途径,从而使古老的道家思想获得了返本开新的可能性”[18]53,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林语堂被很多学者称之为“新道家”。
20世纪初的文学创作是多向度且驳杂的。载道文学当然是需要的,但文学创作需要更丰富的表现形态与话语空间,异质而多元才更贴近这个世界的真实。诚如王兆胜先生所言:“林语堂较少关注人的阶级性、社会性、时代性和思想性等重大命题,而是倾心于对人生尤其是人生本相的观察、思考和感知。”[19]78当然,从林语堂自身的经历和创作表现来看,他并不能称之为纯粹的“道家老庄之门徒”,他只是接收了道家超脱飘逸的文化精义,同时摒弃了其中虚无消极的成分。严格上说,是更赞成“把道家的现实主义和儒家的积极观念配合起来的中庸的哲学”[2]90。但正是这种隐藏的却确证存在的“内心的浮浪和爱好浮浪生活的癖性”[20]107,却是“生活于孔子礼教之下”感情上的救济,同时在艺术创作上是“过于崇尚显示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成分”的孔教的补充,这部分道家文化深刻影响着林语堂的生存选择与美学品格。他甘做“城中隐士”,用逸放外的道家智慧注目时局。他奉公安三袁为其文学创作的不祧之祖,而道家美学是为三袁性灵文论的衍出之源,道家浪漫的情怀和奇崛的想象力,这些都影响着林语堂创作之路的选择与美学思想的最终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