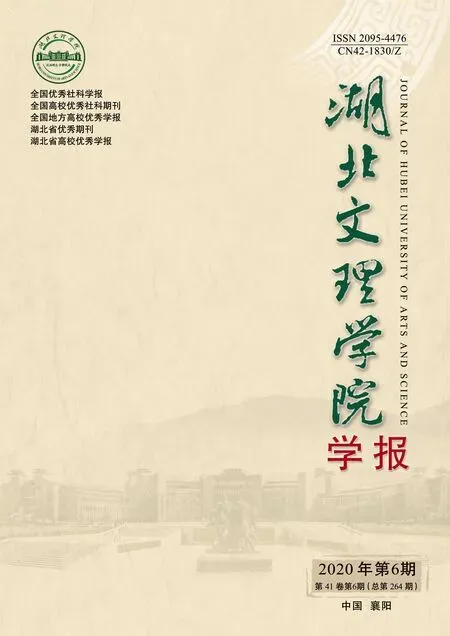西方文艺新动态:文学动物学批评
高家鹏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一、理论的创建
文学动物学正式形成于21世纪初,但该理论在西方文化史上,很早就有了雏形。玛丽·桑德斯(Mary Sanders)指出,文学动物学的产生与西方精神“逻各斯主义”密切相关,源于一种阐释(explain)和解构的冲动。西方人在考量动物的时候,通常以己度人,将“敢于牺牲”这一特性无限放大到所有他们能接触到的动物。[1]桑德斯认为,这种行为实际上是西方人在拷问自己,是“逻各斯”公式的扩大化运用。比如,西方人认为马是优雅并且遵守纪律(disciplined)的,但实际上,马的表现只是该物种对于系统人类驯化的回应。西方人喜欢用狗和忠犬一类的词汇赞扬忠诚和热情的人类,但是事实上,狗的行为也只是天性中受猎物的刺激而成,它们的忠诚是建立在狩猎竞争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文学动物学也是一种反叛,其目的是要颠覆人类长久以来对动物的错误理解,研究文学作品中动物本该拥有的形象,从某种意义来说,文学动物学就是运用科学的动物学(zoology)理论,探讨当代文学作品中对于动物的“误读”。可见,文学动物学的成立并不是简单的归纳总结,并不只是将文学作品里的动物抽象论述。而是延续了20世纪后期西方的解构主义热潮,是对后现代谱系的生动呼应。
并且,文学动物学还有鲜明的“反人文”以及“人之死”的倾向,是驳斥所谓“大写的人”的后现代哲学在文学批评上的技术承接。这种驳斥在文学动物学的观念上最早起源于对莎士比亚的批判,在英国人文主义运动发展的时期,莎士比亚高举大旗,在他的喜剧中赞扬“人”的伟大,高度宣扬人的主观能动性。如《哈姆雷特》(Hamlet)中,莎士比亚就赞美人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作品!”人的行为“像天使一般”,人的外表“像上帝那样”。西方的这种人文主义思维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一直到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创作,都没有摆脱这种纯粹的人类崇拜观念。文学动物学将上述的作品定义为“作家努力地想要将人类和未知的野外区分开来,不惜敌对(oppose)自然”。虽然同样是反叛和革新,但文学动物学不同于后现代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技术批判(如福柯的规训理论),而是将革新焦点聚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上,透过关系在目标文本中的矛盾,抽离、解析出被驳斥的其余物种(other species)的价值。
文学动物学批评并不局限于文学动物形象研究,其理论拥戴者希冀利用该理论研究“人类的思想”。加拿大学者凯里·威尔(Kari Weil)认为,动物是未经检验的基础,人文学科的建立就是基于该基础之上的。[2]于是小说中的动物形象也能够解释了,即动物在小说之中充当着沉默的见证者或者与人类呼应的比较对象。文学动物学还归纳出动物在小说中的表现形式,有的表现出对共同生存的渴望,比如儿童文学就是如此,但另一批小说却表现出人类控制失效的不可知(unknowable)现象,凯里认为,美国七十年代流行的动物恐怖说(animal horror)是文艺创作上对后一批小说的印证。动物,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集体的身份,都是人类衡量自身的标准。
文学动物学也不仅仅是生态批评的延续,而是观照人类的窥视镜。文学动物学试图从生态中人类和非人类的对立与融合关系中切入,进而探究人类的心理。文学动物学的文本批评重点理所应当地落在了动物小说中表现不可知论的那一批作品。作家迪尔德雷·马登(Deirdre Madden)的代表作《茉莉·福克斯的生日》(MollyFox’sBirthday)就是一部完美的解析样本,小说的中心人物,双胞胎乔治亚和贝西,就被引入了一个接近魔幻现实主义的场景,这个场景模糊了人类和非人类生活之间的界限。就在他们出生之前,这对双胞胎被描述成一种仓鼠,在灌木丛中奔跑,直到意外被车撞到。在几天后,主人公以人类的身份出生,但他们依旧存在着无法解决的身份困惑。小说表明,身体体验从根本上来说是暴力的,并且抗拒明确的分类。评论家使用文学动物学理论解构《茉莉·福克斯的生日》,不只是探讨人类与作为大自然的代表的非人类动物之间的关系,不拘泥于生态关系探讨,而是发展到身体、身份、语言这样的词汇解构游戏。
可见,文学动物学对语言有很高的解构执着,这种理论“执念”是完全可以溯源的。文学动物学首先发掘的就是语言中动物失位的状态。人类对人性与语言的关系之间的讨论自古希腊伊始,能够溯源到亚里士多德,然后可以一直持续到20世纪理论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研究。二位理论家都提倡语言是必要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基础,阿伦特继亚里士多德之后,认为人类与自己或他人言说并且理解言说的行为才让人类得以体验意义。而海德格尔则认为,语言是世界塑造人类的表现。海德格尔的观念并没有改观西方对于人类与自然关系本质的理解,海德格尔并没有建立一个清晰的二元对立概念,也不试图去定义动物与人类:他反对物种的概念层次结构,并警告说,剥夺动物的年代并不等同于没有世界,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3]相反,海德格尔认为,在维持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时,只有人类才能作为存在并接触到其他存在。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动物因为缺失语言,所以它们被剥离出世界体验的范围。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同样参加了语言学学者对非人类的动物的“围攻”,他认为语言是只属于人类的唯一特性,自然世界中找不到任何拥有该特性的其余物种。[4]虽然语言学学者承认动物拥有交流和传感系统,但是他们一再否认动物与人类交流系统存在着重叠。幸运的是,这种偏见在近年来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观,凯莉·奥利弗(Kelly Oliver)发展了赫尔德的语言理论,赫尔德举例论证了英语中“绵羊”的发音就是起源于绵羊的叫声。赫尔德据此认为,人类的语言起源于非人类动物的交流系统,并且也因此区分开来。奥利弗总结了赫尔德的理论,认为这种语言起源于非人类动物是“动物教学法”(animal pedagogy)的最好例证。动物教导人类的方法,正是通过将他们自身排除于人类的分类之外的。奥利弗的研究佐证了非人类动物对人类语言系统形成的重大作用。奥利弗的理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在她之后,西方学者的态度就更加激进了,语言学学科内出现了一批尝试突围“围攻”的先锋学者。英国学者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就宣称人类的语言体系是“动物游戏的产物”“完全是动物模式的”。[5]法国学者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进一步说明,人类所谓的人类语言相较于动物的优势区分,总是以人类自身为权衡标准的,很少考虑动物本身的机能和习性。这些学者进而指责一些所谓的针对动物的语言实验(1)二战后,美国动物科学家展开许多测试动物语言的实验,其中著名的有美国比较心理学者凯洛格夫妇和海斯夫妇的教大猩猩说话实验。本质上是人为的,而且将一切负面的责任推卸给非人类动物。
从以上的分析可得知,文学动物学利用分类学提炼文学作品中的动物形象,以其形象为研究对象,探讨人与非人类动物及自然的生态关系的同时,发掘出文学作品及其语言中的动物失位状态。批驳人类中心理论成了该学说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批驳之后,文学动物学又灵巧地回归人类的本位思考,透过动物映射出的人类行为去解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类心理学机制。所以文学动物学是一个新兴的、后现代的、并且较为全面、较为科学的文学批评理论。
二、理论的范式
文学动物学的研究范式在轨迹上摆脱了“定义”与“概念”式的经验主义研究,将理论范式提升至“后现代”模式,提倡研究物种间的“关系”。该理论想要介入人类与非人类动物之间的博弈,以相对客观中立的立场进行挖掘、整合有动物形象和动物寓言的文学作品。
文学动物学通过分析动物的痛苦来切入这种“关系”研究的书写,类似的研究最先出现在与文本关联不大的动物权利学者的论文中。“痛苦”(suffering)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的一种语言建构。在文学动物学的领域,痛苦被定义成人类和非人类动物所共有的特性。最开始,这种痛苦只局限于身体和肉体方面,但目前许多动物权利学者将“哀悼”“缅怀”“悲伤”等情绪和精神的痛苦纳入到研究体系中。皮特·辛格(Peter Singer)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动物比人类经历更少的痛苦或快乐”[6],他提倡“人类应该尽自己可能地去减少动物感到的痛苦”。他的理论显然引导了20世纪末欧洲社会中牲畜屠宰业的人道主义“改造”,屠宰动物的手段更为快速、人道,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动物的痛苦。但同时,又有一部分学者提出了更为深入的结论,动物的权益看似得到了保障,但这种“保障”实际上是人类心理的弥补,仍然是人类观照主导的行为变迁。这些学者将人类与非人类动物之间的关系探讨重新放在了语言层面之上。美国学者卡里·沃尔夫(Cary Wolfe)直接说到,“以痛苦为基础来考虑动物的权利证明了言论本身与立场问题是完全不相干的”[7],他认为,一旦语言的使用不再被视为人类的核心组成部分,权利的问题就会以指数的方式扩大,对物种的等级理解就会开始瓦解。以沃尔夫为代表的新兴学者对“动物保护协会”“环保主义者”等机构、群体的动物理解发出质疑,学者们认为,所谓的动物保护只是语言衰败、人类语言失位的一种表现,而并不是精神层面的人道主义进步。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就曾直言:“如果狮子会说话,我们也不会理解其含义”[8]。在维特根斯坦这句话的语境下,狮子成了这种语言困境的绝佳反例,也许人类可以通过外在行为来推理出人类内在的心理和状态,但由于非人类动物与人类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即使非人类动物能够清晰地表达出他们的痛苦,那种痛苦也将是极其隐秘而且难以阅读的。
正当学者们感叹人类处于语言危机的世代,又崛起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声音。德里达等解构主义者,将“语言”关系问题升华至“权力”的关系探讨之上,将研究重点放在现象之上,如果将沃尔夫等人的观点总结成“人类心理学-动物权益”的范式,那么德里达、福柯等学者的态度就是“社会学-现象学”的二元结构。德里达从根本上否认人类的“语言”心理优势,“问题不在于人类或者非人类动物拥有、能做什么事,而是他们不能做什么”。德里达将动物的语言能力缺失和弱势地位定义为“脆弱”(vulnerability),他认为人类中心主义者对于人类语言特性的坚持是一种对世界权力关系的错误理解。这个世界的权力不在于人类个人的主张,也不在于一个物种对另一个物种的统治与征服,而是在于存在于一种关系之中,德里达赋予意义的脆弱就涵盖了人类与非人类动物关系问题。德斯普瑞(Vinciane Despret)继续了德里达的讨论,提议反思“哀悼”的意义,提议反思诸如黑猩猩实验这样人类主导的探究,他将自己的观点比作“翻译”,人类的这些实验必须得到另一种领域的“审视”。德斯普瑞直接否定了人类能够与动物“同情”,他认为人类和大猩猩的“哀悼”可能是意义完全相反的两种事物。
从目前学术的研究来看,如何审视动物的情感仍然处在争论之中,但研究的方向已经在不同派别、地区的学者的博弈中统一起来: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物种差异,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引发了对身体、经验和语言的彻底反思,即研究中立、客观、科学的立场与偏见影响下的立场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差异。所以文学动物学范式也就是研究人类与动物的这种“差异”。
文学动物学的文本批评范例和运用,主要集中在驳斥拟人化,重塑(rebuild)非人类动物观念之上。而且文本批评的范例几乎都集中于欧美新兴的“学者作家”(scholar writer)的作品,并且相当一部分作家拥有“文学-创作-环保”三重叠加身份,这些作家不仅是文学研究者,而且关注环境问题。美国学者作家韦林·克林肯堡(Verlyn Klinkenborg)是其中的典型,韦林不仅仅是一名文学研究者,持有普林斯顿大学英语博士学位,而且他持续关注全球环境问题,出版数本环境问题专著。他的《蒂莫西或者可怜虫的笔记》(Timothy;or,NotesofanAbjectReptile)讲述18世纪科学家吉尔伯特·惠特(Gilbert White)和他的乌龟蒂莫西相遇的故事。这部小说同样将故事推进的重点落在了语言上,表达出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由于语言产生的沟通困难和隔阂。普林斯人借惠特之口,说出了“野兽创造的语言根本不是语言,真正的语言是人类的,其余的是无法表达的隐喻”[9]这样的感慨。惠特与蒂莫西的紧张关系实际上反映出非人类动物与人类之间那看似平静的友谊,实则是非人类动物的“沉默”所致,物种间的友谊是非人类动物的牺牲和妥协的产物。对拟人化的批判正是来源于上述认识,动物本就是禁止言说的,赋予他们在文学文本上“言说”的也正是人类,文学动物学认为将动物拟人化的表述方式只是人类单边言说,是完全错误的文本产出方式,拟人化消除了至关重要的物种差异,这样的行为在评论家看来是十分危险的。在欧美文艺学领域,上述观点引起了评论家、作家的强力反弹和回击。因为对拟人化的全盘否定使得文学动物学将先前几乎所有的儿童文学、动物寓言视作本体理论的敌人,甚至连安徒生都被纳入文学动物学的批判范围。
文学动物学的批评范式还有这科学研究与实验难以触及的优势性。文学动物学的批评范式是一种“自我批判”,是一种重新审视和反思,然而自我批判往往不被科学研究重视采纳。科学研究的倾向是“线性”的,通常采用昂扬进发的研究方法,很少反思审视前人的思索,所以科学实验对于动物的观念上就产生不少误差,走了很多弯路。而文学动物学的研究方法是“循环式”的,在推进研究的同时,又注意到审视的必要性,才得以产出相对正确的结论。所以文学动物学批评范式还有“审视”与反思的优点。
综上所述,文学动物学的范式,是一种基于环保主义、人类学、文艺理论的泛哲学式批评。文学批评学通过对拟人化的攻伐和动物本位主义的坚守,在认可“物种差异”的观念之下,展开讨论批评文本中隐藏动物语言,分析文本中人与动物在“沟通”“从属”“权力”等诸多方面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该理论具有对动物研究科学的文本互补意义,能够指导动物实验的研究方向,纠正科学家的一些观念错误。
三、文学动物学的理论互动:以女性主义为例
文学动物学与女性主义有不可分割的理论渊源。
文学动物学是一种全新的批评方法,这还体现在它的批评对象之上:文学动物学尤其钟爱后结构小说(post-structuralist)。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garet Atwood)的早期作品中的动物元素就成为文学动物学批评家的关注重点。《可以吃的女人》(TheEdibleWoman)以及《神谕女士》(LadyOracle)两部小说多次出现受宰的肉牛和猎杀兔子这样的画面叙述。她在著名的批评论文《生存》(Survival)说到“不要期待熊会跳舞”,可见玛格丽特对于动物叙事有着执着,而且经常将女性问题与动物问题放置在作品中进行结合讨论。最近,学术对于玛格丽特的动物元素研究主要是讨论玛格丽特的动物政治观。美国学者芭芭拉·希尔(Barbara Hill)就发现了阿特伍德的作为创作者和她的作品的一个矛盾,芭芭拉总结了阿特伍德笔下的人物,发现他们“很少有肉食者,几乎以蔬菜为生”[10],然而阿特伍德自己却宣称“当别人问我是否是个素食主义者时,我回答我是吃肉的,这通常让他们很震惊”。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恰恰是阿特伍德动物政治观的体现——她将动物的处境与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交叉论述,将受压迫的动物与女性现状的一些特点进行类比研究,也就是说,阿特伍德已经将动物问题纳入了自己女性主义的理论范围之内,而女性“身体”问题则能解释阿特伍德的矛盾举措。在她的女性主义观点中,女性的身体是二元的。美国学者亚当斯和多诺万就曾指出,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女性的身体就被认为是有害于塑造她们自身的理性的,所以女性在之后的十几个世纪笼罩在男权观念的“理性霸权”之下。阿特伍德这看似矛盾的行为很有可能是一种“示威”,为了宣泄对于女性理性与身体脱钩的误解的不满。
亚当斯甚至认为“讨论动物的处境是女性主义的必经道路”,美国70、8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和研究就讨论了启蒙运动中的大男子主义(masculinism)和身体恐惧论,这样的观点与动物研究的讨论不谋而合。亚当斯总结了美国流行的色情刊物中的情色图片,认为“女性的身体等同于动物的身体”,她们几乎全裸,像动物一样暴露在男性的视野之中。该学者将动物的虐待与女性所遭受的虐待进行比较讨论,认为不仅仅人类自身之间存在着身体恐惧现象,而且这种恐惧现象同样适用于物种间的紧张关系。所以,亚当斯提出的理论应该是一种动物身体政治论。亚当斯提出,这一时代的身体观是不完整的。可能对于初民而言,他们有着相对完整的身体观念,但很快男性中心主义冲击了这种完整的身体观念,不仅剥夺了女性的身体,也戎害了动物的身体。她在她的代表作《既非野兽,亦非男人》(NeitherManNorBeast)中抛出了下述论断:
我们拒绝某些身体的文化建构,因为它们完全是物质的,以至于它们的身体变得无关紧要。动物的身体是及其重要的,因为我们认为我们与动物共享同一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人类与动物是主体的共同体,而不是客体的集合,即使对于主体的观念是如此的破碎。只有肯定上述前提,我们才能建立起完整的、令人尊敬的身体。
因此,亚当斯从物种学家的观点中恢复了动物身体的完整性。从理论上讲,她的论点呼应了女性身体的再生,通过性别和性别的划分,促进了第二波女权、性主义对传统构想的女性特质的批判。亚当斯还援引了身体本质主义,在过去的十年里,性别和性别的划分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审视。亚当斯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女性主义代表作《至关重要的身体》(WithBodiesThatMatter:OntheDiscursiveLimitsof“Sex”)的写作。巴特勒讨论了亚当斯的动物身体政治学,提出了自己的论断,认为“身体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构造的”[11]5。巴特勒引人注目的论点使目前为止讨论的问题中的社会建构理论变得尤其激进。在对物种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直接批判和与之相伴的对动物身体完整性的支持,甚至对于动物的呼吁都打上了一个问号。她的论文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种意识形态批判的不足。
巴特勒的论断主要集中在性别观念上,巴特勒吸收了生物学的性别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成为人”的性别观点。她认为人并非一开始就是“完备”的人,为了成为人类,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适应性别机制的环节,才能够正确地认知自己的性种。她认为,性别的建构是通过排他性的方式进行的,这样一来,人类的创造不仅是反对非人类的结果,而且是人类自己拒绝了另一种文化表达的“可能性”的结果,巴特勒认为,人类在成为人类的过程之中,由于他们自己被迫进行“唯一”选择,使得很多可能性丧失掉了。因此,声称人类主体是被构造出来的是不够的,因为人类的构造是一种不同的操作,它不仅产生“人类”,也生产出不可想象非人类的机制。这些被排除在外的机制束缚了“人”的外在部分。
巴特勒的“构造性别论”启发了文学动物学的理论架构,文学动物学使用构造的观点去讨论了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关系,将人类的整体进化和个体出生的过程看作是一种选择的过程,绝大多数非人类的机制被抛弃掉了,但肯定留下了一些能够佐证兽性的机制,这也充实了类似“人类就是动物”论断的证明方法。
这同时也是社会学观念的“共同体”的“生态”回炉重塑,巴特勒在“共同体”的观念上表达了她对女性现状的强烈不满。她认为,不是所有的人类都能进入“主体群落”,人类主体的社会使建立在“排斥”(exclude)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的建立不仅仅排斥了极端弱势的非人类动物,而且极度抗拒着流动和变化。巴特勒列举了阶级、性别、种族和性征以及反理性的儿童罪犯和精神病患者这些事例来佐证她的论断。巴特勒的理论可以看作是对于社会不公的有意识反叛,更可以看作是对于前沿动物学家的一种社会性观点补充。亚当斯就认为,人类和动物“都应该进入这一共同体”之中。每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国家、性群还是种族都有他的社会属性,巴特勒的理论叩问了8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是否有重新考量包容的可能性”[11]193。巴特勒还认为,在没有排斥主义的石器时代,动物肯定是被纳入进社会形态之内的。物种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通过拟人化的反面写作手法,混淆了动物世界的现实与人类所编织出的想象动物世界。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所有的这些理论都是基于语言的辨析之上的,也就是说,文学动物学的理论根基还是后现代的,是一门继承了自索绪尔以来的语言分析以及语言解构的批评方法。语言是最适合各类学派进行分析的“完美中介”,对于文学动物学而言,作家主动的无意识语言表述与构造提供给文学动物学无穷尽的物质中介。并且最为重要的是,动物和语言在特性上有着不能忽视的共同点,语言从所指导向能指的过程揭露出文字、语言的象征意义。而根据巴特勒的观点,动物完完全全是一种象征,“拟人化”就是塑造象征的重要手段,尽管产出的象征并不是合理的。
文学动物学是一门与女性主义高度结合的批评理论,在“消灭中心”的运动中,文学动物学以其合理的科学性与女性主义形成了互补,同时,女性主义中的“身体”与“性别构造”的观点也丰富了文学动物学理论。文学动物学在与女性主义的互相阐释之中,完成了从语言向身体,再从身体走向社会共同体的理论“三级跳”,呼应了后现代学科建设中的有机规律。
文学动物学也有其理论的缺陷。其一,纯粹的语言、语义分析和科学研究相去甚远。正如黑格尔所言,“形式被错误地宣布等于本质”。文学动物学所采取的语言分析方法只是一种途径,或者说,一种中介,并不是理论应该达到的终点。过度强调语言语义分析容易让学者忽视同样至关重要的社会、经济乃至文化的影响因素。“话语之外别无其他”,文学动物学掉入了这种后现代研究方式的研究陷阱中。其二,就是哲学意义上的不可证困境。文学动物学吸收了巴特勒的性别抉择理论,提出了人类区别于动物的过程是排除兽性的历史。然而文学动物学将科学意义上的问题强行并入自己体系的话语与身份研究,这使得文学动物学理论的这块内容无法通过人类普遍的科学研究方法去证明。提倡话语研究的文学动物学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很强的生命力,但该理论确实很难在自然科学家的支持下推进研究。无论如何,这些缺陷都不能否认文学动物学在社会科学子学科中的地位。
然而文学动物学作为21世纪的新兴文学批评,不仅仅承接了欧美一连贯的后现代“关系史”探讨,该理论更是对于整个西方社会科学大学科的“他者言说”。而且它在与女性主义、动物科学学科的互动与联动阐释的过程中,显现出高度跨学科性的批评活力。综上所述,文学动物学具有很强的理论潜力,是新世纪文学批评中的突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