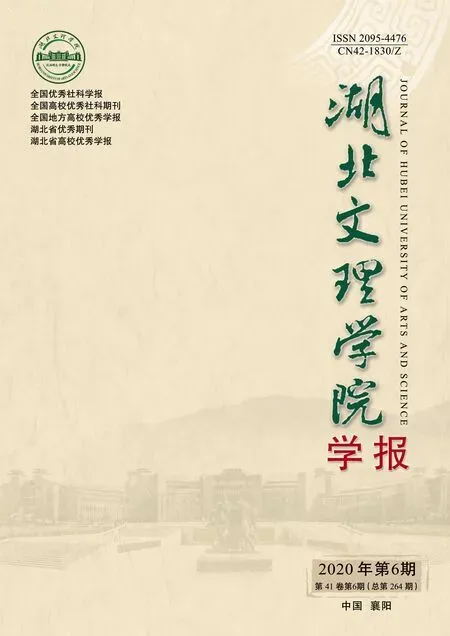论徐訏赴港后戏剧中的荒诞色彩
方桂林,程一冰
(1.中国艺术研究院 戏剧戏曲学系,北京 100029;2.杭州师范大学 艺术教育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36)
徐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鬼才”,以小说《鬼恋》《风萧萧》闻名于世。与此同时,他也是一名剧作家,创作了近四十个剧本,还发表了大量戏剧评论及剧场理论。但作为剧作家的徐訏,在戏剧史的书写中却一直被冷落,其剧作的相关研究也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其剧作的质量良莠不齐,另一方面则是20世纪50年代后徐訏客居香港而逐渐在内陆文学界失语。近年来,随着《徐訏文集》等相关书籍的出版,研究者逐渐得以窥见徐訏作品的全貌,对徐訏的戏剧创作也有了新的认识。笔者也从中发现,徐訏赴港后的戏剧创作与内陆时期相比,有着较为明显的风格转变,尤其是剧作中呈现出一种“荒诞”色彩。这种“荒诞”既是传统概念又有现代意识,本文便是利用多维度的比较方法,来具体阐释徐訏赴港后剧作的“荒诞”意味。
一、基于荒唐与怪诞的本义解读
(一)佯装与谬论
荒诞一词在中国古典语义中常与荒唐、无稽相勾连。在《辞海·词语分册》中,“荒诞:不真实,不近情理;虚妄不可信。如荒诞不经。李白《大猎赋》:‘穆王之荒诞,歌白于西母’”[1]。清纪昀有言:“虽语颇荒诞,似出寓言;然神道设教,使人知畏,亦警世之苦心,未可绳之以妄语戒也”[2]。在西语中,荒诞原指音乐中的不协调,逐渐引申成不合理或者不恰当的意思。
从这个角度看,中西传统的荒诞定义是接近的。在传统戏剧中的表现常常是人物语言的夸张,逻辑推理的跳跃,情节设置的奇异。非正面人物占据正面人物位置,极尽摆弄,在反理性的逻辑引领下,创造难以预料的情节。在徐訏赴港后的喜剧中常常使用这样的方法,其剧作《红楼今梦》讲述的是一位研究《红楼梦》的赵博士来到裴正大律师的事务所,请裴律师保护他的研究成果,以防其它研究者偷窃。他的研究成果包括《红楼梦》讲的是共产党在中国的政治运动,贾宝玉是共产党,大观园象征着东交民巷,十二金钗是各国大使,《红楼梦》的作者正是他本人。最后曹雪芹到访,赵博士仓促逃跑。
剧中的赵博士在论述自己论文观点的时候极其自信,他认为共产党的旗帜是红色的,贾宝玉住在怡红院,又号“怡红公子”,爱吃红胭脂,断定贾宝玉是共产党,最后贾宝玉穿着大红猩猩毡的斗篷跟一僧一道走了,认为猩猩毡是俄国料子,这一僧一道想必就是苏联人,贾宝玉作为共产党去了苏联。故此,剧作荒诞感的来源正是赵博士这样一个非正面人物顶着博士头衔在不合理的推论中走上神坛。
张健在其论文中借用“佯谬”(1)“佯谬”一词原为物理学概念,即paradox,指的是从某种前提出发推理出违背常识或一般观念的结论。张健在此处仅是挪用概念,与原义不同。来定义这种现象,“作家因此才会以一种见怪不怪的态度将这些承载着负面价值的人物安排到原来是由正面角色占据的位置上,处之泰然地让他们去哄骗,巧辩,去施展诡智,尽兴表演”[3]。徐訏在其喜剧中抹去个人价值偏向,使“佯谬”贯穿全剧。《红楼今梦》中的赵博士对于自我有着强烈的认同,对其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超博士论文的评述存在着有违常情的推理,剧中人裴律师也并不拆穿,身份的佯装与逻辑的愚谬正制造了荒诞。再如剧作《白手兴学》,讲述陈博存租房办研究所的故事,他看到了学术的商业价值,准备办各类各样的研究所,拉房东做股东,借名教授的光,挣政府和学生的钱,空手套白狼,把学术当成买卖,计划还没开展,就已经有客户上门了。所谓的“佯”,一方面是角色本身的不自知,另一方面是剧作者对这一形象的有意创造。其“谬”一方面是角色的愚谬,一方面是剧作者主动创造的悖论。说得简单点,就是从头到尾说反话,不戳穿,来考验观众的接受与审美。
(二)虚妄与怪诞
徐訏赴港后的戏剧除了符合“佯谬”原则之外,还夹杂着虚妄的想象。故事内核虽然有着现实的基础,但也有着极大的夸张与改造,传统的戏剧性消隐,充斥着剧作家任性的创作冲动,剧作完全不考虑其合理性,其它人物并非为情节服务,而是为主角服务,或者说是剧作家借角色表达社会意见而即兴的产物。如《白手兴学》更像陈博存一个人的独角戏,憧憬未来大业,房东许禄光像是相声艺术的捧哏,配合陈博存对于研究所的各种想象,如何申请资金,如何聘请教授,如何运营,如何招生。而赞比亚的政府人员撒真达和浸会学院的毕业生李志仪就像是陈博存或者说就是剧作家本人的提线木偶,时机到了,虚拟出来。故此该剧作荒诞之处除了“佯谬”,还有一种类似相声式的虚妄想象。也就是说这种荒诞的来源不是完全出自于剧本的内涵,还包括戏剧创作的方式,不依赖于情节的点线串连,而是在一个静止的情境中依赖角色的胡言乱说,虚妄假想让戏剧变得荒诞可笑。
这或许是徐訏从传统相声艺术中得到的灵感,他曾经谈到:“中国的相声也可以说是非理性对白的一个支流”[4],非理性使相声在空荡的舞台上仅凭口技就可获得极大的创作空间,可以指天说地,架空臆想。如上文提及的赵博士对于《红楼梦》的新颖见解,《看戏》中夫妻二人通过“意识流”对台下观众身份和遭遇的猜想,都受益于这种非理性的虚妄想象。
荒诞在中国文学艺术范畴中,并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美学范畴和哲学思维,它始终在其原始义上逡巡。常常以令人称奇的情节和反常酷烈的造型示人,与“怪诞”有着相似的意义。中国志怪文学中存在着诸多例证,《搜神记·河间郡男女》中就写过这样一个故事,男人从战场回来,到女人墓前表达哀思,其诚意感天动地,使女子死而复生,喜结连理。戏曲如《牡丹亭》中杜丽娘为情而死,而又为情而生,生生死死,神出鬼没。《邯郸记》里卢生一场黄粱大梦,历经人生繁华。都是通过想象制造奇异景观,以奇引人。
徐訏赴港后创作也有这种创作倾向,如戏剧《客从他乡来》讲的是史家岚过世已久的父亲史祖常托梦让他召集家人,他要回来见大家。果真史祖常的鬼魂回到家中,和大家攀谈,描述鬼魂的美好世界。当然也不单单戏剧中有这样的现象,其小说《时间的变形》《园内》中也有这种鬼魅的情节。
除了引入鬼魂的想象,他的《日月昙花开的时候》《鸡蛋与鸡》中也有超越现实的奇思,《日月昙花开的时候》讲赵家有一株六十年才开一次的日月昙即将开花,各色人物聚集在家中等待花开。传奇之处在于赵明已经逝去的父亲在临终前就预言这朵花将在今天开放,而最终守在花前的一群人未如愿看到花开,倒是已经入睡的老人和小孩见到了赵父所说的“满屋生香,光照四壁,音乐齐鸣”[5]502的景象。而《鸡蛋与鸡》中众人排起长队只为看鸡蛋与鸡,他们为是看到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争执不休,竟为此反复排队,看了十几遍,仍然莫衷一是。
但总的来说,从传统语义的视角看待徐訏赴港后戏剧中的荒诞,仍然是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起点,荒诞只是创作技法上的偏离和跃进,是通过“佯谬”的人物设置、非理性的虚妄想象、奇异的情节景观最终实现剧作家的讽刺效果或美好希冀。
二、对西方荒诞派戏剧的深度摹写
值得注意的是,徐訏赴港后戏剧的创作时间(20世纪70—80年代)正是荒诞派戏剧开始被总结回顾的时期。而徐訏本人的学术经历又是研究哲学与心理学,又曾于1936年赴法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对于彼时西方的社会气候应有一定了解,如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另外徐訏于1976年在香港《七艺》月刊上发表《荒谬剧的对白与废话的情趣》,对“荒谬剧”做了详细缜密的分析,其观点与马丁·艾斯林在《荒诞派戏剧》中“荒诞派的传统”章节的观点高度重合,从这一点上能充分证明,徐訏对于“荒诞派戏剧”是有相当深入的理论研究的,在此预设前提下,徐訏赴港后戏剧与荒诞派戏剧的相似研究就有了一定依据。
(一)身份重置与模糊
笔者以为,徐訏赴港后戏剧与荒诞派戏剧第一个相似点就在于身份的重置与模糊。在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当中,观众在正观式的审美视角下演员与角色是捆绑的,身份是固定的,演员化入角色,在情境中行动,使观众移情于中。而在荒诞派戏剧中角色扮演常常带有一种杂耍意味,身份具有不确定性。
如热奈的作品《女仆》,一对女仆趁女主人不在家,玩起了扮演主仆的游戏,游戏的内容就是颐指气使的女主人与唯唯诺诺的仆人之间的相互挖苦。现实中他们对年轻貌美的女主人感情复杂,曾害得女主人的情人锒铛入狱,为了不让事情暴露,她们决定谋杀女主人,然而并未成功,女主人离开以后,在新的主仆游戏中,扮演女主人的女仆以女主人的身份喝了有毒的椴花茶成功死去。在这个戏中,主仆身份的移位,让他们在仪式中获得一种报复的快感,他们出于对高潮的渴望,用死亡换取身份重置后的胜利。此在的真实变得廉价,虚幻的镜像身份却成为角逐的关键,游戏精神与崇高的原始献祭交映成趣,身份重置的荒诞感凸现。
徐訏的《看戏》也有类似技法,首先是戏的场景布置,“其它演员插在观众空间……舞台灯光集中中间,前后两排木椅,后排稍高,前排有四个座位,后排有六个座位”[5]467。在这里剧场空间被重置,观演关系移位。紧接着表演者夫妇二人进入剧场,走上舞台,与他们身后坐着的五位木偶演员变成观众,他们与真正的观众对峙,互为镜像。而真正的观众席中又安插着真正的演员,他们以观众的身份作为舞台上的伪观众的评议对象,必要的时候还从观众席走出,配合台上“观众”的意识流。而身后的木偶又作为观众把夫妇二人当成演员。演员与观众的身份相互置换,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与《女仆》相比,《看戏》的身份重置更像是从寓言的角度出发,层层递进的身份变化让人陷入沉思。
身份模糊亦是一种常见现象,即人物的群体化图标和符号化倾向。荒诞派戏剧试图消除能指与所指的符号关系,通过舞台形象来直接阐释“荒诞”。如尤涅斯库的《椅子》中,老夫妇热情招待的客人是挤满整个房间的一排排椅子;《犀牛》中整个街道都是横冲直撞的犀牛;他们用直喻的方式揭示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陌生感,群体的静默或骚动,使个体失去了评判的标尺,而渐渐物化。在徐訏的晚期戏剧中,“直喻式”的表达并不多见,但可以明显看到人物的符号化倾向。譬如《鸡蛋与鸡》中,人物名称都是有姓无名,性格色彩也被弱化,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处在同一个阵营,就是看“鸡与蛋”的热闹,为此争论不休,而构建了一道“对毫无意义的事情过分关心”的人物群像;在《看戏》中,演员化统一的妆容扮演木偶坐在夫妇后面,集体肃穆。在剧中唯一的行动是结尾“(夫站起,追向后台,消失)(舞台上只剩木偶们坐着)(木偶们鼓掌)幕徐下”[5]474,木偶的集体行动似乎在表达,自以为是隔岸观火的看客其实也成为别人眼里的戏子。
(二)生存本体论与偶然性的思索
徐訏作为一位哲学系出身的戏剧家,对于西方近代哲学有着天然的敏感,敏锐地捕捉到了存在主义哲学中的虚空感与无根性,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生存困境亦有着不凡的见解。他的小说《时与光》中的郑乃顿,《江湖行》中的野壮子等人物形象都在践行着人生的偶然性。徐訏认为:“时间只是人间的幻觉,如果把入世的历史看作天国的地图,那么必然和偶然不都是一样吗?”[6]郭盈在其论文中对此的评价是:“徐訏将个体存在的流浪状态与家园缺失本质构塑成了生存的基本特征,旅行结束了但是家园从来就没有存在过。”[7]这种人生偶然论与时间的陌生感和荒诞派戏剧对于人的本体论思索相当一致,在虚无的客体间,作为个体的我以何种身份存在。
这种困惑与期待也反映在徐訏的赴港后戏剧中,在《客从他乡来》(也作“客从阴间来”)中,活人世界中的史家子女忙碌在世界各地,被父亲史家岚以生了重病为由骗回来,个个都心有埋怨,惦记着手头的工作、实验,心疼来回折腾的机票钱。这与以鬼魂身份出现的祖父史祖常形成鲜明对比,他神采奕奕,风度潇洒,向众人描述灵的世界的美好,自由自在,没有争执,没有欺诈,只有爱与和谐。灵的世界是空虚的,人的外形不过是身外之物。“灵的世界是无限大,而个别的灵的存在只在活动时候才能感觉到,不活动就等于不存在。事实上它存在于一个整体之中。”[5]516徐訏对于“灵世界”的美好想象便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困境,人总是为着“物”和“欲”在相互倾轧。
戏剧的结尾,“灵世界”的祖父史祖常潇洒轻捷地离开之后,活人世界的外祖父丁德存突然昏厥,断了气。这戏剧性的一幕更是加深了徐訏对于自由虚空的“灵世界”的向往,然而徐訏曾说,“感到社会之到了绝境,尽量享受一时之快乐,极力探求鬼神之显灵。冤屈的求报应,惨毙的求超度,活人们要降福,这些都是社会问题的虚悬,人民的力量无发挥的地方,把一切依靠于渺茫的神鬼去了”[8]。作为一个无神论者的徐訏,却用鬼魂入戏,对灵的希望也正是对于当下的失望,人在现实生活中对于自我与客观世界的质疑。
事实上这种质疑也源自于徐訏的个人经历,他晚年时这样评价自己的创作,“我离开大陆很久了,对那里的状况不了解,因此不能写大陆;台湾的情况我也不了解,又不能和香港社会沟通。我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写实的东西离我越来越远,所以我开始记录自己对哲学与人生的看法,试验多种不同的表现方法。”[9]自50年代孤身来港,与妻女多年没有联系,对故乡大陆无从了解,客居香港难以合流,确是一个“自他乡来”的“客人”,故徐訏现实中对个体存在与身份认同的困惑也就自然地反映在其戏剧当中。
三、徐訏戏剧的“荒诞”辨析
(一)与赴港前剧作的比较
从喜剧创作来看,将赴港后作品填充进他的喜剧拼图中,显然能看出一副清晰的发展脉络。徐訏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创作戏剧时,涉世不深,其作品洋溢着一种对于生活的乐观态度,如《青春》《忐忑》《公寓风光》《心底的一星》等作品,即使讽刺也是温和善意的。而在他40年代的作品中,风格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走出校门,看到社会中种种乱象,众生皆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野蛮心态,让他心生鄙夷,另一方面赴法归来,其眼界和创作技法都日渐提升,这一时期的创作如《男婚女嫁》《租押典卖》,其风格不再是丁西林式的生活情趣,更有一种陈白尘式的辛辣讽刺。
赴港后的创作,如《白手兴学》《红楼今梦》《蛋与鸡》,这些作品和上一时期相比,疏离了现实主义的典型性手法,从日常生活中选择一个话题进行调侃,这种调侃没有像《男婚女嫁》一样制造曲折复杂的情节,而是就事论事,渲染夸张,发散思维。如《白手兴学》就是针对当前的不正学术之风进行虚妄想象,内容上有一定依据,但能明显看出是在用“佯谬”的方式揶揄调侃。所以从喜剧发展的线索来看,徐訏喜剧发展是从幽默到讽刺再到荒诞,是从浅到深,从实到虚的发展趋势。
再从“拟未来派戏剧”这个角度来看,徐訏在马里内蒂“未来派戏剧”的影响下仿写了四个“拟未来派”作品,《荒场》《人类史》《女性史》《鬼戏》,但这四个作品又并非与未来主义戏剧完全相似,另掺杂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方法,使其在神秘感之外还深含哲理。如《荒场》将两个人搁置在荒场之中,每一幕都是不同年纪的相遇,直至死亡在荒场立下新冢,他们的子孙又重复他们当初的相遇,循环往复。
徐訏赴港后的戏剧正是吸收了“拟未来派戏剧”中的非理性元素和哲理意蕴,制造荒诞又寓有深意的情境,如《看戏》演员成了观众,观众成了演员,木偶变成最后的看客;《客从故乡来》鬼魂入戏,畅谈灵界美好,反衬人间之凶险罪恶。然而他们亦有诸多相异之处,篇幅上,“拟未来派戏剧”篇幅短小,换景快速;题材选择上,“拟未来派戏剧”常常采取神话,寓言的方式,重象征;最后“拟未来派戏剧”的主旨更倾向于表达抽象的哲理。
总之,徐訏赴港后戏剧荒诞意味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是在延续前期的创作脉络,发扬喜剧性精神,深入非理性效果。
(二)与“荒诞派戏剧”的比较
上文提及徐訏对于“荒诞派戏剧”有着相当深入的理论研究,他曾于1976年在《七艺》月刊第三期发表《荒谬剧的对白与废话的情趣》一文深入探讨荒诞派戏剧的源起,并陆续发表了《看戏》(1976)、《红楼今梦》(1976)、《白手兴学》(1977)、《鸡蛋与鸡》(1977)、《日月昙开花的时候》(1977)、《客自他乡来》(1977)等作品。
在他研究“荒谬剧“的文章当中,其观点与马丁·艾斯林在《荒诞派戏剧》一书中的观点极为相似,甚至可以说某些观点和例证就是源自于后者。首先是他们对于荒诞派戏剧特点的总结——非理性与幻想,徐訏认为:“荒谬剧所走的正是要从理性的语言走到非理性的语言,从论理的语言转到心理的语言……用这种歪曲的形式表现作者心理的幻象与幻觉”[4]410;其次他们都认为荒诞剧的发展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戏剧,如杂耍、魔术。尤其是滑稽剧中的丑角逗笑方式对于日后的影响,徐訏的例证甚至直接援引艾斯林,如有人要买房子,问他房子什么样,掏出一块砖,就长这样;再如阐释荒诞剧的废话情趣,都引用了弗洛伊德的论述;最后他们都认为荒诞派戏剧的舞台观与禅家悟道有相通之处,都是向传统语言对抗。
然而,其后续作品的风格并没有完全与其理论同步,只能说有相似之处,如身份的重置与模糊的技法,对于自我身份的体认,但整体上看,没有反逻辑,只是在变换逻辑,以至于叙事看起来荒腔走板;也不见呓语与废话,相反语言仍较为干练精辟,故只能算是传统喜剧的一次跃进。徐訏的赴港后戏剧是以荒诞的外在形式包裹着一个合理的内核,其表达的主题仍然是确定的、理性的,如《白手兴学》《红楼今梦》是对于学术不端的讽刺;《看戏》是对观演关系的思考;《日月昙开花的时候》是对生活的体悟;《客从他乡来》是对桃花源式的生活向往。
荒诞派戏剧在香港的发展并非始于徐訏,早在20世纪60年代,岛内就出现了受荒诞派戏剧影响的实验戏剧,如《等待》《五十万年》《夜别》等作品,但此时的戏剧创作者主要是在校学生,其作品也只能算是校园戏剧,同时这些戏也“是从荒诞派戏剧中接受了存在主义的哲学和理念,而以传统的理性写作方式将其表现出来。”[10]在专业领域的香港本土剧作家,有20世纪60年代译介西方作品的钟景辉、80年代发表《废墟中环》的潘惠森、创作《无人地带》的邓树荣与詹瑞文,而像徐訏这样的客居香港、业已成名的大陆老作家,仍然不囿窠臼,敢于创新,实属难得;从同时期的大陆戏剧家对比来看,由于十年浩劫刚刚结束,各种被中断或未翻译的西方理论和剧目纷至沓来,面对各式各样的流派理论,大陆创作者还在努力消化之中,我们现在所认为受到荒诞派戏剧影响的内陆作品的集中出现,也是80年代以后的事了。
在传统与现代、前期与后期、内陆与香港的多维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徐訏赴港后戏剧确有其独到韵味和研究价值,从荒诞色彩的视角切入看徐訏的赴港后剧作,不论是对于构建徐訏喜剧的整体谱系还是重新确立徐訏的戏剧史地位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