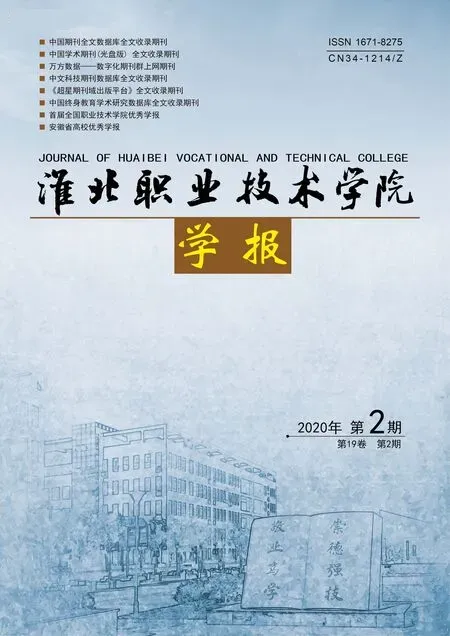《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中上海的延续与转型
楚浩然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不同于“摩登年代”的光怪陆离,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是否意味着上海“繁华”的消逝与“单调”上海的出现?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给出了“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旧在场”[1]17的答案。随着新史学的推陈出新与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于新革命史之下重写革命的态势成为革命史研究的一大趋向。翻越传统革命史的藩篱,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在中国共产党“运动群众”到“群众运动”的政治统合之下,传统制度的逐渐消逝但依旧尚存与新意识形态的逐步渗入交织于上海城,政治整合与个人命运在新的统治体制下亦有着方向的急转。
本文力求再现书中相关内容,对里弄的基层政治空间,影院、报社的社会文化空间与大变局下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的沉浮进行界定与思考,借以探讨20世纪50年代以延续与转型为主题的都市革命中上海国家权力与社会重构之间复杂交织的错综关系。
一、贯穿里弄:都市革命与基层管控
保甲制度作为控制基层社会的有效方式,于战时重新嵌入上海的都市社会,成为“国家与社会共同的政治空间”。[2]此时的保甲组织面临着群众上层接纳、下层脱离的两种倾向,加之上海所具的大都市特性——人口密聚且流动频繁、邻里关系错综复杂、非单位人群与劳动人民同居共处。因此,如何有效管控基层社会,保证基层控制的稳定性,进而有效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动员,成为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初期的现实问题。
中国共产党掌权后的政策既灵活又谨慎,“没有采取与过去一刀两断的策略,没有出现血流成河的局面,上海在逐渐的变化”。[3]这种“逐渐的变化”正是中国共产党基层控制的灵活选择与成功所在,是延续与转型的突出表现,也是接管大城市经验不足的中国共产党难能可贵之处:
其一,延续与革新。罗马非一天建成,20世纪50年代的里弄政治空间并不是与过去的一刀两断。对于现存的保甲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发挥其“余热”的同时,“革旧”与“图新”双管齐下,利用丰富的政治动员经验,以“冬防”为契机,通过大规模组织和发动里弄居民,最终实现了居委会的“软着陆”。[1]43
其二,背离与调适。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阶级理论与现实的悖论:“理论上的依靠者,即里弄中的非单位人靠不住,而最终要被消灭者却从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与统战中得到优待,仍居于社会上层。”[1]79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首先根据基层群众激情盲从易感染的特点,以利益为导向,结合劳动就业进行阶级清理。当然仅一次的阶级净化定不能使执政者满意,“镇反”主题的里弄整顿随之即来,同时通过与社会生活计划化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既加强了对里弄空间的政治控制,也建立了这种控制的体制机制。[1]72
其三,动员与改造。面对人民当家作主的承诺,如何动员群众参与民主生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又一难题。在中国共产党的掌控下,群众在革命、国家与社会三者交织的舞台中进行了一场既激动人心又小心翼翼的集体性演出。舞台之上,资格审查、典型塑造、代表当选等不同剧情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以阶级分层和政治动员为主题的基层政治革命。
新政权的改造贯穿于上海都市革命中的基层管控。这种对基层政治空间的控制不是对传统制度的完全颠覆,而是在充分发挥其效用的同时,借助自身所具有的社会改造与政治动员经验,通过“利益满足与农民主体性发掘”“政治鼓动与革命主体塑造”[4]两大环节,最终实现了国家基层政治空间的延续与转型。
二、记忆隔绝:都市怀旧与文化革新
摩登时代的上海走在时尚前沿,百乐门的灯红酒绿、大光明影院的欧美电影、霞飞路的时尚万千和十里洋场的笙歌燕舞,孕育了老上海的都市风情。中国共产党在接管上海之初,将国家权力下移至公共文化空间,用“红色话语”改造“小资产阶级文化”,力图使其告别晚清以降的大众文化消费市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新运动却始终存在着国家控制与群众意识之间的张力,但“在革命炫目的张力后面,也必有自己的限界”。[5]在与国家话语的角力后,五彩斑斓的都市文化烟消云散,最终被纳入社会主义控制轨道。
“笔杆子”向来是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武器,因此,中国共产党对社会舆论的严密掌控成为建国初上海社会文化改造的重要环节。新政权的报业改造紧抓三大要素:“自上而下的党管报纸的机构和制度的建立,党报及其权威地位的确立,民营报业的控制与改造,以此推动报业国营化,报纸政治化的进程。”[1]138
私营报业的改造依然“缓进”。新民主主义的统战政策对私营报业的改造并非疾风骤雨,而是先使其复刊与受助,但亦使其掣肘。这种限制为私营报业的改制提供了契机,在“改人”完成以后,“改制”随之而来。“改制”同样注重“延续”:“在公私合营后,政府也没有立即在文汇报实行国家工资制度,也没有套上相应的行政级别……直至1956年下半年,文汇报才进行工资改革,确定相应的级别,实行国家工资。”[1]184社会主义改造后,私营报业最后完成转型,获得了国家政治待遇,以往的“掣肘”消失殆尽,成为国家舆论体制下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影院作为群众的日常娱乐空间,同样接受着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洗礼。国家意志主导下的电影行业改造使“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迅速沉寂,但群众的文化生活并未完全断裂,而是缓慢转型直至被吞噬。在抗美援朝时期禁绝好莱坞电影之后,部分香港与欧洲影片依然可以作为“进步”电影在影院中播放,“小市民”依旧可以通过它们重温上海旧梦。相比于这些影片的火爆,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国产与苏联影片则受到冷落。在此情形下,政府的指令性控制不断加强,直至1963年香港故事片完全消失于上海文化领域。
报业与影业的改造既体现了建国初上海文化事业的非“割裂”性,也为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提供了1949年前的社会文化记忆,突出了历史的延续与转型。同样不可否置,经历了“蜜月期”与小市民的软性抗衡,国家权力彻底将社会文化事业从“摩登”之中抽离,纳入了全能主义政治的社会文化发展轨道。
三、谁主沉浮:都市变局与个人命运
从1951年的镇反运动到1952年的“三反五反”,至1957年的“反右”,加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国共产党长期积累的阶级斗争经验在建国初期的阶级净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政治运动的风波使20世纪50年代的个人命运走向殊途,且有不同程度的潮涨潮落。
典型塑造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中重要一环,底层小人物在经历国家所需的形象塑造后,不仅走向典型引领的正面,个人命运也随之发生改变。1953年的第一次普选运动中,李杏生、李小妹等小人物通过“主人翁”形象的建构,于普选中脱颖而出,成功翻身,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107反之,阶级成分模糊的居民在选民资格审查中就已栽了跟头。“由于革命被构建为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正当性,再没有人敢于公开表示反对革命。当革命被神圣化的同时,反革命也被建构成为一种最大的罪恶行为。”[6]站在革命与反革命的红线左右,维权还是保命成为个人在政治运动中的重要议题,无法取得主人翁身份则意味着成为反革命分子,生死攸关。[1]93
避让折中与放言敏行两种迥然不同的政治态度,往往决定了个人命运的浮沉。徐寿成与严宝礼紧跟思想改造的步伐,努力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在政治压力与自我反省的双重作用下,从消极到积极,从困惑到紧跟,不仅完成了思想的“升华”,且有着从民间报人到国家干部的“意外收获”。[1]184
同样,黄氏兄弟在大变局中的不同命运亦体现出个人态度在都市变局中的重要作用。嘉德站在红线之外,谨言慎行,听话跟走,躲过了历次政治劫难,得以善终;而嘉音则越界进入了无知也无力把握的政治空间,最终不知所终。[1]258
中国共产党20世纪50年代的阶级净化机制不同于文革时期,依然是平稳过渡。遵从与坚守成为环环相扣的政治轨迹下多数人的人生态度,这种“与世无争”使他们得以延续与转型,成为“人民国家的新主人”。但 “入世”之人的命运却截然相反,最终湮没在政治运动的山呼海啸之中。
四、余论
罗兹·墨菲认为,上海是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集中体现了西方现代性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回应。[7]20世纪50年代上海的都市革命扮演着重要角色,里弄政治空间的重组、报业的改人与改制、新环境中的电影事业与大变局下的个人命运,不仅体现了建国初上海社会的“缓进”,也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社会重构在全国范围内的缩影。伴随着延续与转型的主旋律,中国共产党最终建成了强大的政治体系来控制社会、改造社会,实现了根本性的制度突破。
虽然“东方巴黎”的图景在“全民革命”的浪潮里星落云散,但新政权政策的灵活性与政治运动客体的软性抗衡并未使现代上海的历史断裂。国家与革命的“入场”没有迅速消解并重构城市原有的社会秩序,而是与之展开了艰难的博弈和斗争。历经改造的新上海于革命、国家与社会三个逻辑之间,充满活力的同时也包含了诸多的不稳定性。
“摩登依旧在场”实际上指的是社会及文化范畴内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权力的缓性改造与市民的软性抗衡保留了上海的传统色彩,而非现代上海与老上海之间的一脉相承。因此,未能界定“依旧在场”的范畴不得不说是本文的一大遗憾。但借助扎实的史料功底,通过“集权主义论”、现代化论及新革命史观的有效观察与解释路径,张济顺笔下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的延续与转型依然有重要意义:新政权的强力改造,使上海这座浮华的消费型城市近乎消逝,各阶层逐步成为了高度受改造、高度统一的“有用”公民;而在国家权力强力推进的背后,上海本身所多年持有的韧性,被称作“摩登”的性格,却依然顽强的存在,依然按照自己旧的轨迹发展……
——上海里弄居住功能更新方式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