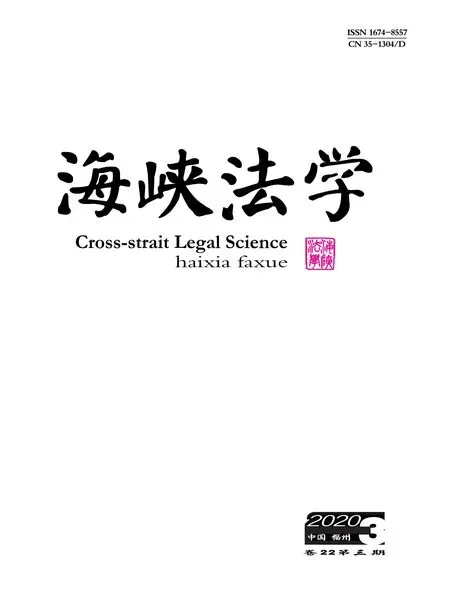中国的准宪法解释机制:原理与实践
尹好鹏 ,林自立
引言
学界对于宪法解释的讨论很多,多数研究以宪法教义学为视角,试图界定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为《宪法》)上宪法解释的概念,并讨论宪法解释权的归属。尽管众多学者对于宪法解释的概念界定并未达成共识,但是几乎都依据现行《宪法》第67条第1款所规定的宪法解释主体和解释对象,将宪法解释等同于有权解释或正式的宪法解释。①许崇德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胡锦光、韩大元著:《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163页;苗连营:《宪法解释的功能、原则及其中国图景》,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6期,第40页等。基于此种定义,学者们很容易引申出中国不存在宪法解释,或者说至少不存在正式的宪法解释的结论,并以此敦促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但此类定义和推论在宪法理论层面存在可商榷的空间,亦难以回应中国的宪法实践。
因此,近年来,一些学者已在研究范式和理论视野上有所扩展,试图从宪法实施的角度观察和理解宪法解释。陈鹏教授指出,一国的立法机关是否是宪法审查机关,是否得到宪法的明文授权,其职权行使都具备宪法解释的功能。②陈鹏:《立法机关的宪法解释功能比较研究》,清华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页。而黄明涛教授则提出,在现行宪法的体制下,存在两种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分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所进行的抽象解释和在司法过程中进行的不具有一般性的宪法解释。③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第297页。林彦教授研究了全国人大如何通过立法解释宪法,实现重新分配政府权力、重塑公民基本权利的功能,并将之视为一种隐性的宪法实施。①Yan Lin; Tom Ginsburg,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n Lawmaking: China’s Invisible Constitutional Enforcement Mechanism,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Vol.63, 2015,pp.468-470.黄卉教授基于教义学的解释方法和实践需求,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应被理解为最终的、最高的宪法解释权,而非唯一的、垄断的宪法解释权,②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第298页。法院行使其审判权则必然涉及对宪法的理解,从功能适当的角度来看,法院亦应当被赋予解释宪法的权力。③同上,第300页。
上述研究虽已开始关注宪法实践中的宪法解释,但大部分仍旧围绕作为宪定宪法解释主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展开,尽管有向其他宪法主体赋权的呼吁,却鲜少观察到其他国家机关已经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解释着宪法。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宪法文本自身的特殊性。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第1款直接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的宪法解释权,在规范层面上,该条款对于宪法解释权的列举似乎排除了其他国家机关解释宪法的权力。但是,跳出第67条来看,《宪法》序言即指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在国家机构章节亦为各国家机关列举了各自的宪法职权,为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各国家机关需要在履行各自宪法职权过程中服从宪法规范的约束。这就要求各国家机关要对相关宪法条款作出理解和解释,解释是实施的前提,适用宪法的各国家机关享有解释宪法的当然权力。④朱新力:《论宪法解释》,载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2页。
本文并非否认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解释主导机关的地位,也并非质疑具有终局性的宪法解释权的归属。但是,正式宪法解释的“终局性”(Finality)和“权威性”(Authority)并不必然意味着“排他性”(Exclusivity)。而“立法至上”(Legislative Supremacy)或“立法主导”(Legislative Dominance)更多指向“终局性”和“权威性”,而非“排他性”。而即使认为《宪法》第67条第1款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垄断了正式的宪法解释权,也并不排斥各国家机关在实施各自宪法职权、实现自身宪法职能的过程中对宪法进行理解和解释。相反,作为宪法实施的主要主体,各国家机关在宪法上皆具备遵守和实施宪法的义务,而作为宪法实施的必要步骤,各国家机关在实施宪法的过程中进行事实层面的宪法解释是无法避免的。而且,这种解释并非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解释,而是能够透过相关规范性文件进入到我国的制度体系之中,并进一步影响新的宪法规范之生成和发展。就此意义而言,各国家机关通过在实施宪法的过程中积极解释宪法,使得宪法的原则和规范得以制度化,更容易实现宪法规范的析出和形塑。相较于正式的宪法解释,可将此类宪法解释称作准宪法解释(Quasi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或实质宪法解释(De Facto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⑤该概念名称之确定受启发于程洁:《中国的准违宪审查制度初探》,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3期,第3~13页,在此说明。了解准宪法解释的存在有助于理解宪法解释的性质和功能,亦为正式宪法解释的出台以及宪法实施体系的建构提供实践基础。
本文将重点研究宪法所列举的正式宪法解释的规范意涵,提炼共存于宪法规范框架内的准宪法解释概念,论证其在国家权力配置语境下的合理性,最后观察其在宪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一、正式宪法解释的规范分析
宪法解释作为宪法学的基础概念之一,在既有的学术语境下,经常与宪法实施、违宪审查、宪法监督等概念交替使用,但诸概念之间的关系尚未厘清,宪法解释概念本身的范畴和分类也一直存在争议。这一方面是因为学者们在定义宪法解释时借鉴了不同的宪法基础理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学者们试图从多个维度找寻能够沟通中国宪法的规范与实践、最具解释力的概念建构之路。
本文并不打算再定义宪法解释的概念,仅作必要说明。就学理而言,宪法解释是指从宪法文本中提取其一般规范内涵和特定含义的活动,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解释。①Rytter, J,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Between Legalism and Law-Making,Scandinavian Studies in Law, Vol.52,2007,pp.256.而根据我国的主流学说,宪法解释被定义为有权解释机关根据宪法的精神和原则对宪法条文规定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说明,其具有与宪法层面的效力。②《宪法学》编写组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7页。该定义强调了宪法解释的宪定有权主体和宪法解释的效力层级,对学理上的宪法解释进行了限缩。根据该定义,我们很难观察到相应的解释行为。据此,相关研究通常认为我国不存在正式的宪法解释。而宪法解释又被认为宪法实施的首要途径,③刘国:《宪法解释之于宪法实施的作用及其发挥——兼论我国释宪机制的完善》,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1期,第45页。这是否意味着现行宪法没有得到解释也没有得到实施呢?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我国现行宪法正不断从语义宪法走向规范宪法,这已逐渐成为学界共识。那么,这是否又意味着规范与实践之间出现了落差?是故,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宪法条文,去捕捉宪法条文背后的真实意味。
基于宪法学研究的立场和方法,对于宪法解释的研究应从实定宪法的相关条款出发和展开,尤其在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第1款已明确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职权的情况下。那么,以该条款为起点,我们是否能够尝试回答宪法解释主体的问题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再次申明,宪法解释的“终局性”和“排他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种机关提供最终或权威的宪法解释是一个问题,而解释是否可以或应该由不止一个解释机关做出则是另一个问题。明确上述的基本区分有助于让我们认清所回答问题的本质。根据上述区分,能够对该条款文意之可能作出如下列举:1.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终局的”“排他的”宪法解释权;2.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终局的”“非排他的”宪法解释权;3.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非终局的”“非排他的”宪法解释权。那么,何者为对该条款较合适的理解呢?我们有必要结合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比较法上的参考来进行分析。
1.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终局的”“排他的”宪法解释权。该理解为我国学界所约定俗成的理解。大多数持该观点的学者都通过下述论据来支撑其论点:首先,现行《宪法》中有且只有第67条第1款写明“解释宪法”,因此,仅有全国人大常委会为有权解释主体,现行《宪法》所设定的宪法解释权具有专属性和排他性;④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第111页。其次,相关研究多以“我国采取立法机关解释宪法的制度”⑤蔡定剑著:《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是宪法解释的主导机关”⑥姚岳绒:《宪法解释权归属的文本分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11页。之类的论断来作为立法者原意的还原;再次,其他国家机关仅有适用宪法的权力而无解释宪法的权力。
2.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终局的”“非排他的”宪法解释权。近年来,基于宪法学理论的推演以及对我国宪法实践的观察,该种理解逐渐被更多学者所采纳。持该观点的学者们认为,首先,现行《宪法》对于宪法解释权的列举并不必然意味着其他国家机关无权解释宪法,在逻辑上,无法直接通过前者得出后者;⑦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第296页。其次,在采纳“立法机关解释制”的国家中,并非仅有立法机关拥有解释权,例如英国即存在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共享解释权的情况。⑧Michael J.Perry,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n a Democracy: What Role for the Courts,Wake Forest Law Review,Vol.38 ,2003,pp.670-673.同时,在采用司法机关解释制或是遵循“司法至上”的国家,并非仅有司法机关能够对宪法作出解释,也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主导”或“至上”更多代表的是宪法冲突下的“最高性”和“权威性”。①Gant, S.E,Judicial supremacy and non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Hastings Constitutional Law Quarterly, Vol.24 ,19 97,pp.364-365.再次,基于遵守和实施宪法的义务,各国家机关当然享有解释宪法的权力,宪法解释是宪法实施的前提条件。
3.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非终局的”“非排他的”宪法解释权。持该种观点的学者多认为,最高的、最终的宪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虽然现行《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拥有正式的宪法解释权,但是基于全国人大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以及其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决定的撤销权,应当推定全国人大亦具有宪法解释权。②翟小波著:《论我国宪法的实施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胡锦光、王丛虎:《论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第4页。那么,即使不承认各国家机关都具有宪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亦非最终的;而若承认其他国家机关的宪法解释权,那么各国家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就能够共同构成多层次的宪法解释体系。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几种理解之间的紧张关系呢?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关于“终局性”的讨论并非我国宪法解释权争论的重点。在比较法视域下,各国对于宪法解释权争论的重点在于讨论何者应该或者能够作出“终局性”的宪法解释。例如,在美国,目前对于宪法解释权的讨论多是在对抗式三权分立的宪制结构下,围绕“司法至上”(Judicial Supremacy)与“部门主义”(Departmentalism)展开,希望明确宪法冲突中的权威解释主体。③Erwin Chemerinsky,Interpreting Constitution,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87,pp.82;Johnsen, D.E,Functional departmentalism an d nonjudicial interpretation: Who determines constitutional meaning,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67,2004,pp.105;Tyler,D.W, Clarifying departmentalism: How the framers' vision of judicial and presidential review makes the case for deductive judici al supremacy”, 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Vol.50,2009,pp.2217-2264;李晓波:《宪法解释权分配的理论模型分析——以“本位主义”为中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3期,第102~117页,该文较系统地将该讨论引入了中文语境。在国家权力配置的语境下,我国“终局性”的宪法解释权归属于立法机关是没有争议的。同时,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④韩大元:《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宪法地位》,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6期,第4页。但是,有必要明确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并不来自其国家立法机关之身份,而是来自于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之身份。在稳定的宪制秩序之下,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视为最高的、终局的宪法解释权是可欲且可行的,但不应排除全国人大行使具有兜底性质的宪法解释权。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拥有“排他性”的宪法解释权则是争议的焦点。现行《宪法》第67条第1项对宪法解释权的规定意味着正式的宪法解释仅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职权能够排除其他国家机关在行使各自宪法职权的过程中进行附随性的宪法解释,发挥宪法解释的功能。尽管我国在国家权力配置上并不存在对抗式的权力分立,全国人大作为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现行《宪法》亦为各国家机关分别授予了各自的职权。贯彻和落实宪法,推动宪法实施并非仅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责任,各国家机关亦需要遵守宪法、实施宪法、对宪法负责。基于宪法文本本身可能存在的语义空间,实施宪法必然涉及对于相关宪法条款的理解和解释,这些理解和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析出宪法规范、促进宪法规范继续形成的功能。就该层面而言,我国宪法权力的配置结构决定了各国家机关理解和解释宪法的界限。
据此,我们能够发现,我国现行《宪法》中实际上藏有两个维度的宪法解释概念:一者为《宪法》第67条所明确列举的,仅能由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正式的宪法解释;二者则是由各国家机关的宪法职权引申而出的,体现在各国家机关实施宪法过程中的准宪法解释。从现行《宪法》第67条仅能推导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终局的”“正式的”宪法解释权,但该职权并不能排除各国家机关在行使自身宪法职权的过程中发挥解释宪法的功能。
然而,在我国关于宪法解释的讨论中,两个概念时常被混淆。很大原因在于《宪法》或相关法律皆未对正式宪法解释之形式和程序作出规定,且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从未正式宣称过自己行使了宪法解释权。因此,学者们难以从形式和程序上区分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在行使正式的宪法解释权,亦或是在实施宪法的过程中行使理解和解释宪法的当然权力。
二、准宪法解释概念的界定
为了容纳上述各国家机关在实施宪法的过程中形成的宪法解释,并将之与宪法所列举的正式宪法解释区分开来,我们尝试提出“准宪法解释”的概念。准宪法解释概念存在功能主义导向,但并非不受宪法规范的约束。相较于宪法所列举的有权解释而言,其在解释主体和效力层级上有所扩张,但又不至于完全回归学理层面的宪法解释,因此具有以下特点:1.准宪法解释的主体并不局限于宪法明确列举的宪法解释权主体;2.准宪法解释不具有特定的宪法解释程序或形式;3.准宪法解释并非最高的、终局的,不具备宪法层面的效力;4.准宪法解释需能够实现宪法规范的析出与再生成。同时,尽管准宪法解释是在宪法实施的语境下形成的,具备一定的功能导向,但其依然需要回应宪法理论和宪法条文。因此,具体而言,准宪法解释概念的界定需要满足以下命题,才能同时具备规范与实践上的意义。
首先,准宪法解释既不同于无权解释,也不同于狭义的有权解释。根据解释宪法的主体是否有宪法解释权,可将宪法解释分为有权解释和无权解释。而有权解释又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解释的宪法依据是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第1款,该条款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因此主流观点认为仅有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所列举之宪法解释权进行的宪法解释才为有权解释。然而,从宪法实施的角度去展开思考,宪法解释不仅是宪法实施的一种特殊形式,亦是各宪法实施行为的必要步骤。理解是实施的前提,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并非宪法实施的唯一主体,现行《宪法》为各国家机关分别授予了相应的宪法职权,并对所有的国家机关提出了遵守宪法、实施宪法的要求。因此,各国家机关在各自的宪法职权范围内,理应享有理解和解释宪法的权力和义务。那么,在实施《宪法》的过程中对《宪法》进行的解释,应为广义上的有权解释。准宪法解释即属于广义的有权解释。
其次,准宪法解释应具备解释宪法的功能,但其与正式宪法解释存在不同的目的导向。宪法条文的原则性、模糊性使得大部分宪法条文需要通过解释得到具体化和补充。尽管诸学者对于宪法的功能存在不同的表述,但是他们的表述在实质层面并无太大差异,例如,林来梵教授列举了宪法解释的五个主要功能,该列举基本含纳了宪法解释的形式和实质功能。①林来梵著:《宪法学讲义(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2页。从形式上看,宪法解释使宪法条文得到明确化和补充;从实质上看,宪法解释析出宪法规范,使得宪法能够在特定背景下被适用,并且促进宪法规范的继续形成。通过宪法解释,规范与现实方可得到平衡。正式宪法解释和准宪法解释皆能够实现解释宪法的功能,实现规范的析出和再生成,但是两者的目的并不相同——准宪法解释着眼于实施宪法,而正式宪法解释则意在对宪法的实施进行合宪性控制。
再次,准宪法解释应具有普遍的法效力。根据我国既有研究的主流观点,宪法解释的效力相当于宪法,或者至少处于高于普通法律的特殊位阶。②韩大元:《试论宪法解释的效力》,载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准宪法解释行为不具备宪法效力,但是必须具备普遍的法效力。如上文所述,相较于全国人大常会的正式宪法解释,准宪法解释是由各国家机关在行使自身职权、实施宪法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随附性。其效力亦自然依附于各国家机关实施宪法职权的行为。准宪法解释不具有最高性和终局性,但是具备相应位阶的法效力,这是将之与一般意义上的无权解释区分开来的标准之一,同时,其随附性和效力层级亦说明了准宪法解释仅能作为一种机制存在。
最后,准宪法解释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形成,但不等同于宪法实施。相较之下,正式宪法解释本身即是一项宪法监督制度,一种特殊形式的宪法实施。而准宪法解释并不作为一种独立的宪法实施形式而存在,其依附于各国家机关各种形式的宪法实施行为而存在。尽管准宪法解释的概念与宪法实施有着众多的交叉或重叠,但是不能将两者简单等同。的确,没有各国家机关的宪法实施行为,就无法形成准宪法解释,而准宪法解释亦要为实施宪法服务。但是并非所有的宪法实施都是在进行准宪法解释。
尽管对于准宪法解释概念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语境下关于“非司法解释”(Nonjudicial Interpretation)或称“司法外宪法解释”(Extrajudicial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概念存在相似,但是我们亦有必要认识两者的不同。“非司法解释”含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美国各州等政府分支对于宪法的解释。其关注于讨论在三权分立与联邦制的框架下,法院是否应当排他性地成为宪法的最终解释者,若答案并非肯定,那么,政府各分支各自在何种范围内拥有最终的宪法解释权。①Dawn E.Johnsen, Functional Departmentalism and Nonjudicial Interpretation: Who Determines Constitutional Meaning,Law and C ontemporary Problems, Vol.67,2004,pp.105-147.而提出准宪法解释则意在发掘各国家机关在宪法实践中如何发挥解释宪法的功能,准宪法解释并不存在宪法层面的效力,亦不与正式宪法解释权存在冲突。相反,依据准宪法解释概念,我们能够观察立法机关如何在不进行正式宪法解释的情况下,对宪法进行解释,使宪法得到实施。
基于上述论述,我们基本能够明晰准宪法解释概念的规范样貌,其代表着一类由各国家机关进行的,在形式外观上与正式的宪法解释存在差别,但是在实质上同样发挥了宪法解释的功能与作用的行为。现行《宪法》的架构为两种形式的宪法解释的共存留下了空间,但是其是否符合我国《宪法》自身的规范预设呢?我们有必要再从宪法理论出发,论证准宪法解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三、准宪法解释的理论基础
在外观上,准宪法解释与正式宪法解释的同时存在似乎亦与通识的宪法理论存在背离。那么,准宪法解释的存在是否具备宪法理论层面的支撑?我们认为,关于宪法解释权配置的问题需要置于国家权力配置理论的语境下进行思考,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以西方分权理论作为参照,方能理解为何我国形成了既有的看似特别的准宪法解释机制。
在美国的分权理论语境下,在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上强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对抗式分立,所有赋予政府的权力都被分入政府的三个分支,仅就理论上而言,政府的各个分支之间相互分离,向宪法负责,政府的各个分支在行使其宪法权力时有义务解释和适用宪法。②Gary Lawson; Christopher D.Moore, The Executive Power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owa Law Review,Vol.81,1996,pp.1268-1272.也正因为如此,分权体制即会面临如何解决宪法冲突的问题,即何者的解释为最高的、终局的。马歇尔大法官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奠定了“司法至上”的原则,但是马歇尔对于司法至上的态度并非想象中那么强硬。一方面,马歇尔认为确定法律的含义是司法机关的职责所在;③Marbury v.Madison, 5 U.S.(1 Cranch) 137,177 (1803).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其他政治机构也在积极解释宪法,这些解释被广泛接受为权威性的解释,制宪者们制定宪法时并非仅将其作为法院治理的一项规则,其同样适用于立法机关。④Keith E.Whittington, Extrajudicial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Three objections and responses,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Vol.80,2002,pp.775.而在论证司法机关为何适合且应当成为宪法的最终解释机关时,法官和学者们通常认为,相较于政治机关,作为法律机关的法院更能够做出独立、明智的决断;法院是代表人民执行他们为一个有限政府的各个机构所规定的规则,不具备直接民主合法性来源的法院以一种看似反民主的方式维系着民主政体的运转。然而,对于批评者而言,司法机关解释宪法的合法性是自我证明的,①[美]亚历山大·M.比尔克著:《最小危险部门——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5页。由于缺乏足够的合法性论证和明确的宪法依据,司法机关的权威解释权亦时常被认为仅仅是实践的产物,政府的其他分支亦存在推翻法院判决的能力。因此,基于分权理论的特性,政府各分支能够在自身宪法权力范围内解释宪法是肯定的,而争议点则在于政府各分支在多大范围内享有最终的宪法解释权。
在我国民主集中制理论的背景下,现行《宪法》明确了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正式宪法解释权主体,各国家机关需要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受其监督。这也就决定了对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必然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部分研究认为将宪法解释权授予立法机关而缓和了立法与司法的关系可能并不严谨。根据宪法条文,宪法上的各国家机关需向“权力机关”而非“立法机关”负责。②林彦:《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结构》,载《法学家》2018年第5期,第38页。全国人大在我国宪法中同时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但其之所以应当享有正式宪法解释权是因为其为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其由人民产生,对人民负责,因此,才具备解释宪法的合法性。我国《宪法》之所以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是因为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的实施应当受到人民的监督。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身份监督宪法的实施时,其方能被看作在行使正式的宪法解释权。
另一方面,尽管我国不存在分权,但亦重视各国家机关间的“合理分工”③钱坤、张翔:《从议行合一到合理分工: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历史解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45页。,各国家机关在自身宪法职权内存在一定的自主地位,且需对其宪法职权负责。各国家机关凭借宪法授予的权力和地位,从而拥有与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内的其他宪法主体相对抗的自主空间。④陈明辉:《论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工:概念、方式及结构》,载《法商研究》2020年第2期,第103页。在各自的自主空间内,各国家机关为实施宪法享有当然的解释宪法的权力。宪法上的国家机关作为制宪权的产物享有的是宪定权力,并不能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所享有的同样为宪定权力的立法权所任意支配。⑤陈明辉:《依宪行政:理论、规范与实践》,载《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3期,第93~95页。因此,当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机关的身份为实施宪法而通过立法具体化宪法内容时,其仅能被视为在进行准宪法解释。
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权力配置原则,我国宪法上的各国家机关一方面需要向自身的宪法职权负责,另一方面需要向代表人民的权力机关负责。前者决定了各国家机关进行准宪法解释的必要性;后者则指向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正式宪法解释权的最高性。应该说,正式宪法解释与准宪法解释并存的宪法解释格局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必然产物。
而从宪法发展的角度来看,若想使大多原则且模糊的宪法条文能够面向实践,实现语义宪法向规范宪法的跃升,就必然需要对宪法条文在不同评价背景下进行解释。在人大优位的五元结构之下,⑥林彦:《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结构》,载《法学家》2018年第5期,第31页。各国家机关为了更好地实施自身宪法职权而阐发和理解宪法,既是当然的权力,也是必然的义务。由多元主体参与宪法规范的塑造,有助于各主体形成共同合力,是保持宪法鲜活生命力的重要途径,也符合宪法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客观性要求。⑦祝捷:《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宪法解释方法论的反思》,载《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194页。
四、准宪法解释的主要存在形式
据此,下文意在对中国的准宪法解释实践进行观察,展现目前我国各国家机关在宪法实施中进行理解和阐释宪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文章中对这些实践的发掘和描述并不意味着对这些准宪法解释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合宪性判断。但认识到这些形式的准宪法解释的存在对于观察中国的宪法实践、理解宪法解释的性质和功能是有意义的。
基于上述对准宪法解释概念的定义,我们能够观察到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行政机关的国务院以及作为司法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各自的宪法职权范围内皆对《宪法》进行了较为活跃的准宪法解释行为。我们能够透过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窥探到宪法解释的端倪。
(一)立法机关的准宪法解释
在我国的宪法制度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既是国家的权力机关,也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又是宪法上的狭义有权解释机关,在实定宪法意义上被认为是宪法实施的“第一责任者”。尽管其被认为从未正式行使过宪法解释的职权,但是学界一直关注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在实施其他宪法职权的过程中解释宪法。①Yan Lin; Tom Ginsburg,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n Lawmaking: China’s Invisible Constitutional Enforcement Mechanis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Vol.63,2015,pp.470-490;周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解释案例研究》,载《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62~65页;胡锦光、王丛虎:《论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第4~7页等。然而,有必要知晓的是,该种类型的解释宪法行为仅能算作准宪法解释,而非宪法上所列举的正式宪法解释:一方面,其不具有正式的宪法解释外观;另一方面,其亦不具备超越法律层级的效力,不具备最高的、终局性的宪法效力。
具体而言,立法机关进行准宪法解释主要依托于以下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立法具体化宪法;二是以决议或决定的形式解释宪法。那么这两种形式是否存在宪法上的依据呢?从宪法层面来看,作为宪定权力的立法权自然需要受到宪法规范的约束。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为《立法法》)第3条和第87条分别对立法提出了“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和“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制定法律必然涉及对宪法的理解。但是,有必要提及的是,正如姚岳绒教授所言,直接将立法理解为宪法解释的一种,显得过于宽泛,并且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区别。②姚岳绒:《宪法解释权归属的文本分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14页。立法行为自然不应完全被视作宪法解释,例如,尽管目前大部分法律都在序言处说明自身的宪法依据,③根据威科法规数据库,大部分法律在序言处皆说明本法是依据宪法制定的,但是在具体表述上不尽相同。其中75部法律有“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类似的表述,也有少部分法律写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特制定本法”。较为特殊的为《中国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其序言表述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五条‘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和其他有关条款的规定,制定本法。”直接说明了其所依据的具体宪法条款。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法律即为准宪法解释,大部分的法律条文与宪法并不存在直接的解释与被解释的关系,而部分条款中对于宪法条文的简单重复亦不能认为是宪法解释。仅当某些法律条文确实对于某些原则性的或者具有争议的宪法概念或条文进行了阐述和说明,使得宪法规范被析出,方能被认为具有宪法解释的功能,而被认为是准宪法解释的一种。同理,全国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在行使自身宪法职权的过程所形成的决议和决定中,时常涉及对于宪法的理解,但不必然为准宪法解释,应根据其内容和功能确认其是否为准宪法解释又或仅仅是在行使宪法业已明确规定的其他宪法职权。
从既有的研究与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中,我们能够对我国立法机关如何进行准宪法解释有所了解。一方面,绝大部分的法律都涉及对于宪法条文的具体化,但如果仅是单纯的具体化,那么我们很难将其视为一种准宪法解释;另一方面,亦有部分法律条文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个别决议或决定存在宪法上的隐含甚至是建构而符合准宪法解释的要素。
在宪法概念的解释方面,根据《宪法》第9条规定,水流为国家所有。“水流”本身作为描述性构成要件,表明“实在的事实”,其语义范围大体上是清楚的,但是亦存在语义上的判断余地。①[奥]恩斯特·A.克莱默著:《法律方法论》,周万里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6~32页。对于空中水和地下水是否为水流存在争议。而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资源保护法》(以下简称为《水资源保护法》)并未使用《宪法》第9条所列“水流”一词,而采用了“水资源”的概念。《水资源保护法》第3条表明“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与《宪法》第9条在内容和表述上形成了对应关系。而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外的相关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此一用语是有意而为之,并被其视为自身解释宪法的一次实践。②陈斯喜:“改革开放以来人大制度的选举与组织的发展”讲座,2019年10月18日于中国人民大学。通过“水资源”的概念强调了水的资源属性,并明确指出“本法所称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从而避免了宪法上模糊不清的“水流”概念所造成的适用困境。同理,“公共利益”作为《宪法》中极其重要的价值概念,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在不同评价背景下明确其涵射范围。③[奥]恩斯特·A.克莱默著:《法律方法论》,周万里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33~38页。而在2019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第45条列举了为了公共利益能够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六种具体情形,实质上是对于《宪法》第13条中的“公共利益”概念在集体土地征收的评价背景中进行了解释。
在调整国家机关职权方面,大量立法和决定皆会涉及各国家机关职权的边界调整和具体行权方式。大部分立法或决定并不会明显突破宪法条文的核心语义空间,但是亦有个别案例存在宪法上的争议。例如,我国现行《宪法》第62条第11款将“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的职权授予全国人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20条则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中央决算”。在此即涉及对《宪法》的理解和说明,如果推定全国人大充分考虑了相关问题的合宪性,那么,该条款的制定至少表明他们认为,首先,批准中央决算的权力是能够授予的,而且,将批准中央决算的权力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合宪的、功能适当的。
在形塑基本权利方面,大量立法本身即存在对于《宪法》所列举的基本权利保护的具体化,亦有少数立法实现了对《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护。尽管我国《宪法》未明确列举隐私权与生命权等基本权利,但是这些权利为我国公民所享之基本权利已成共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积极形塑和保护了这些宪法未列举的基本权利。例如,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通过规制讯问、搜查、扣押、人身检查、技术侦查等强制措施而实现了对于刑事被追诉人隐私权的保护,其《宪法》依据即是我国《宪法》所未明确列举的公民隐私权。④赵秉志、孟军:《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隐私权保护——以刑事被追诉人为视角》,载《法治研究》2017年第2期,第85页。而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5条第1款、第246条第1款以及第252条可以被视作在刑事实体领域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具体规定。除此之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都存在相关的隐私保护条款。
相对于讨论较多的隐私权,居住权的建构尚未在学界达成共识。然而,居住权(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正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所广泛认同的基本权利。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居住权主要是调整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住房财产关系,以保护公民的居住权利,防止遭受公权和他人的侵害。⑤李永然:《人民居住权的法律保障:中国台湾与大陆的比较》,载《人权》2015年第2期,第79页。我国现行《宪法》并未明确列举居住权,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保障法》也暂未颁布,但是通过我国的相关法律文件仍能够窥探到对于公民居住权的保护。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指出,“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42条亦规定“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除却金钱补偿,相关条款对被征收人居住权的保障亦提出了要求。通过上述条款,立法机关完成了对于居住权在征收语境下的保护。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能够看到,立法机关在行使自身宪法职权的过程中,在调整国家机关职权、形塑基本权利、解释宪法概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其并不具有超越法律层级的效力,但是在实质上完成了宪法内容上的建构,促进了宪法规范的析出和再形成。
(二)行政机关的准宪法解释
关于行政机关如何解释宪法的问题在学界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也并非无人涉猎。部分学者亦指出,国务院作为宪法适用主体享有解释宪法的当然权力。①朱新力:《论宪法解释》,载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屠振宇:《论我国宪法解释的主体》,载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现行《宪法》第89条列举了国务院的职权,而第1项直接指明,国务院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这意味着,进行相关的行政行为需以理解和阐释相关宪法条文及其背后的宪法规范为前提。其中存在争议的地方在于,行政法规是否能够直接解释宪法,还是必须通过解释法律来执行宪法。对此,现行《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为行政法规直接解释宪法留下了空间。其第9条与第65条列举了能够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除却“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外,行政法规还能够规定“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授权决定先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相关条款表明,国务院依据自身宪法职权或立法授权,在制定行政法规的过程中,存在直接解释宪法的权力。这种权力一方面是宪法授予的,另一方面,也是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所认可的。
行政机关的主要内容集中于建构其行政管理职权行使的具体形式,而出于行政权自身的特殊性质,行政法规的制定亦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与保护。从2009年来,国务院已经公布并实施了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其中明确表达了行政机关依据《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以及为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而制定的任务和目标。而相关人权保障任务的落实即是通过行政法规和相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实现的,也就是说,可以推定,在制定相关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行政机关对于如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有所思考的。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大部分行政法规都是在其上位法律的框架内,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或保护。这种模式难以区分是在解释宪法还是在解释法律。然而,也存在少数行政法规在未存在上位法律的情况下即对《宪法》列举的基本权利进行了限制。例如,《出版管理条例》的序言说明了其依据《宪法》而没有列举其上位法律的依据,并且直接对《宪法》所列举的出版自由进行了限制和保护。对于该条例的制定,可以推定行政机关至少存在以下理解:首先,对出版的管理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是《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因此,无需列举其上位的法律;其次,《宪法》第35条所规定的出版自由受宪法、法律和法规的限制,而非绝对法律保留事项;最后,条例所列举之对出版自由的限制符合《宪法》保护出版自由的要求。又如,2004年颁布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同样在序言中说明了依据《宪法》,但是亦未说明自身所依据的法律。但是,其亦成为了我国宗教自由保护的主要依据,并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有所体现。基于上述例子,能够观察到,在行政管理的背景下,行政法规能够直接保护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在具体建构相关的制度和形式的过程中,基本权利的范围和边界也得到了形塑。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法规对《宪法》的准宪法解释在经历实践检验之后,存在效力层级上升的空间。《立法法》第65条即指出,“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先制定的行政法规,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国务院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此外,并非仅有授权立法的行政法规具有效力层级上升的可能。例如,2019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5条,其基础即为国务院201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8条,二者对于“公共利益”的列举大体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运行良好之后,其适用范围能够得到扩张,也能够得到立法机关的认可而成为法律。另一方面,我国的立法机关又为我国《宪法》所明确列举的宪法解释主体,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亦能够推定这些准宪法解释的合宪性受到了认可。
(三)司法机关的准宪法解释
法院系统一直承载着我国公法学者的诸多期望,研究者们都希望法院能够在既有的宪制格局下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采用类似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方法来确立自身的宪法地位已被证明并不妥当。与美国宪法不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终局性的宪法解释权的归属,因此,“宪法司法化”极易导致宪法结构上的矛盾。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法院系统即完全无法发挥解释宪法的功能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是也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主要通过制定司法解释以及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准宪法解释。
现行《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其中的“法律”概念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依照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审判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我们很难通过对该条款中的“法律”作狭义理解,而将宪法完全排除出审判权之外。但是,如果直接允许法院直接适用宪法进行审判,基于司法自身的终局性特征,极易与享有终局性宪法解释权的立法机关形成对抗。而我国《宪法》133条又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因此,司法机关并不具备与立法机关对抗的可能和能力,其势必导致宪法无法作为个案审判的直接依据。正如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的《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其中列举了可直接引用的规范性文件,而在其扩大列举的范围中仍然没有宪法。同时,该规定第7条又规定,“需引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存在冲突,根据立法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无法选择适用的,应当依法提请有决定权的机关作出裁决”,实际上避免了法院对下位法与宪法之间的冲突作出独立判断。①林来梵著:《宪法学讲义(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6页。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该规定实际上体现了其对于正式宪法解释权的理解和尊重,并为自身在行使审判权过程中适用宪法的范围和方式作了限制,本身即是一种准宪法解释。此外,最高人民法院1986年《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1988年《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2001年《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及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皆涉及对宪法司法适用性的理解而应被视为一种准宪法解释。
而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中,唯一明确“根据我国宪法”的,为1999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尽管该规定的具体条文与宪法条文之间并未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但是其具体条款对法院如何行使《宪法》授予的审判权有所续造。现行司法解释中最明显发挥宪法解释功能的司法解释为2018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其第2条即对行政诉讼法第13条第1项所规定的“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的涵射范围进行了列举,规定国家行为为“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行为,以及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宣布紧急状态等行为”。尽管在形式上属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但是不可否认,其在内容上存在对于宪法相关条款的解释,涉及对《宪法》第67条、第80条、第89条等条款的理解。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仅局限于自身宪法职权行使的具体化和自我设限,亦对公民权利的重塑和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观察到,许多未为《宪法》或法律所列举的权利皆是通过司法解释而被析出和建构的。例如,尽管“隐私”一词在法律文件中的使用最初可见于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5条第2款、第53条、第58条、第103条第1款。该法第1条亦存在“以宪法为根据”的表述。但学界所广泛接纳的“隐私权”概念却源于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该解释把侵害个人隐私的情况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②王晨光:《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的程序思考》,载《法学》2000年第4期,第11页。当然,此时的隐私权是作为一种民事权利而存在,而其后,“隐私权”的概念在法律文件中被广泛使用,亦被用于调整宪法关系,成为了被广泛认可的宪法上未列举的基本权利。相较于未列举民事权利的建构,最高法院在建构未列举宪法权利方面保持着较强的克制,但是,我们依然能够观察到,通过立法,相关民事权利保护亦可能沁入宪法领域,而逐渐成为公认的宪法权利。
如上文所述,《宪法》中各国家机关的职权条款以及《立法法》的相关条款皆为各国家机关进行宪法解释留下了规范空间。而根据观察,各国家机关在实施宪法的过程中,皆有可能发挥宪法解释的功能。在此仅列举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准宪法解释的形式与案例,并非意味着其他国家机关不具备进行准宪法解释的能力和实践。中央军委、国家监察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人大等国家机关亦有能力在行使自身宪法职权的过程中进行准宪法解释。
总结
本文试图在我国宪法规范的框架之内,从我国宪法实施的具体实践入手,尝试提炼准宪法解释的概念,其代表着一类非宪法列举但具有宪法解释性质和功能的广义的有权宪法解释。这些实践隐藏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及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等宪法实施行为过程之中。这些实践以各国家机关的宪法职权为基础,以实施宪法为目标,实现了宪法规范的析出,并促进了宪法秩序的形成,因此具有准宪法解释的性质。尽管对于我国准宪法解释形式的描述在外观上似乎与现行《宪法》对宪法解释权的规定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背离,但是需要明晰的是,何者解释宪法是一个兼具规范性和描述性的问题。该问题存在两个面向:(1)谁应该解释宪法。(2)谁解释了宪法。本文的第一部分试图回答在我国的宪法规范中,谁应该解释宪法;第二部分试图界定正式宪法解释以外的有权宪法解释;第三部分试图理论层面论证准宪法解释存在的合理性;第四部分试图探索在我国的宪法实践过程中,国家机关如何解释宪法。那么,既有的宪法规范和宪法实践之间是否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呢?我们认为并非如此。本文对于准宪法解释概念的定义及其具体形式的列举,并非试图质疑或冲击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终局性的宪法解释权。相反,在理论层面,明晰两种意义上的有权宪法解释有助于弥合既有宪法解释概念与宪法实践之间的落差;在实践层面,通过多元的、多层次的准宪法解释体系,宪法即能够得以制度化地实施。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意识到,在正式宪法解释从未进行过的情况下,各国家机关的准宪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即成为了最高的、最终的,在一定程度上,《宪法》明确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正式的宪法解释权似乎被虚化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更倾向于通过事前的协调和事后的认可,保持对各国家机关准宪法解释行为的合宪性控制。当然,从更广袤的视野来看,无论是美国联邦法院或是日本的最高裁判所,都对于作出最终的宪法判断持有相当程度的消极立场。③Diarmuid F O'Scannlain, Lawmaking and Interpretation: The Role of a Federal Judge in Our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Marquette Law Review,Vol.91,2008,pp.896-897;张允起:《日本宪法诉讼的理论、技术及其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5期,第9~11页。通过协调和控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无需急于行使自身的最终解释权,而各国家机关的准宪法解释也必然在推进宪法的制度化实施过程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