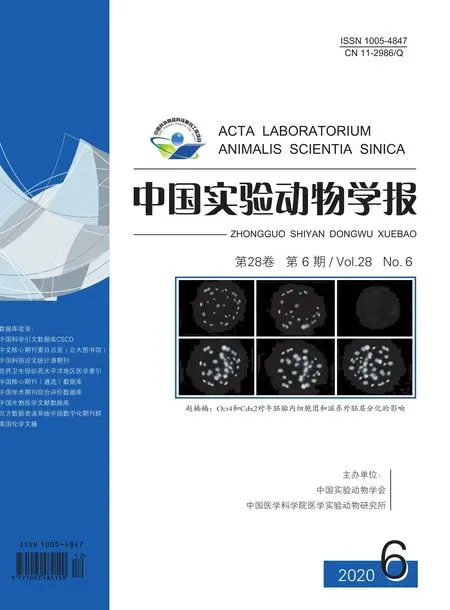脂多糖诱导肺炎动物模型的研究进展
唐思璇,肖芳
(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学系,长沙 410078)
肺炎(pneumonia)是指终末气道、肺泡和肺间质的炎症,可由病原微生物、免疫损伤、理化因素、过敏及药物等因素所致,主要临床症状为发热、咳嗽、咳痰,部分可发展为重型肺炎出现循环、呼吸衰竭而危及生命。细菌性肺炎是最常见的肺炎,也是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在抗菌药物应用之前,肺炎对健康的危害极大,抗菌药物的普遍应用后肺炎的病死率一度呈下降趋势。但近年来,尽管强力抗菌药物不断被研发并应用于临床,肺炎的病死率非但无明显下降反而有所上升,目前其发病率、病死率及疾病负担仍保持在较高水平[1]。目前在老龄、幼龄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中肺炎仍有很高的发病率和病死率,给社会及家庭带来沉重的疾病负担[2]。因此肺炎的发病机制、影响因素、预防措施及治疗方案一直是医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为了更好的了解肺炎发病机制、全面了解疾病全过程、考察药物的预防和治疗效果,在实验研究过程中建立稳定、便捷、重复性强、接近人类临床感染情况的肺炎动物模型则至关重要。
肺炎动物模型根据肺炎病原学可分为细菌性、真菌性、病毒性、衣原体支原体性、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诱导性、化学诱导性等多种类型,其中使用细菌建模的方法较常用。通常将细菌悬液使用不同的途径感染肺部,其与细菌感染所致肺炎相似,但操作较复杂,配置悬液时易引入杂菌影响实验结果。LPS是革兰氏阴性(G-)细菌细胞壁中的一种成分,是G-细菌的主要致病因子之一,由Q-抗原、核心多糖、类脂A构成,其中类脂A是LPS主要的毒性中心和生物活性部分,高度保守且无种属特异性,故不同菌种感染后产生的LPS毒性作用大致相同[3]。LPS在机体内可诱发炎症细胞浸润、炎症因子释放[4],引起的炎症损伤与G-菌真实感染相似,最初用于构建急性肺损伤的动物模型[5],后逐渐用于建立肺炎动物模型。然而,在建立肺炎模型过程中,LPS的诱导剂量和给药途径通常差异较大。故本文作者从CNKI、Web of Science及PubMed检索近年来利用LPS诱导肺炎模型的相关文献,从动物品种选择、造模方法及剂量、评价指标等多种角度进行比较,以期找到稳定、高效、易操作的脂多糖肺炎模型,为肺炎发病机制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实验依据和理论参考。
1 动物品系及性别选择
LPS诱导的肺炎模型常选用啮齿动物,其中大鼠常用的品系有Sprague Dawley和Wistar,小鼠常用的品系有C57BL/6和BALB/c。需要注意的是,人与大鼠、小鼠的巨噬细胞的分布有所不同,大鼠、小鼠缺少肺泡巨噬细胞,其巨噬细胞主要存在于肝和脾,故全身给药后,血液中的LPS多在肝、脾中沉积[6];而有肺泡巨噬细胞的物种(如人),较少量LPS即可引起明显的肺部炎症反应和肺损伤[7]。除此之外,选择动物时还应考虑其体型的大小,小鼠体型过小,测量一些生理参数(如动脉分压)受到限制,采集到的标本量也远不及大鼠,可能无法满足较多的研究指标检测。在性别选择方面大多数研究选择雄性动物作为实验对象,分析其原因可能为雄性动物较雌性动物体内激素水平更为稳定,对实验干扰更小。袁伟锋等[8]在研究中使用了雌雄各半的BALB/c小鼠,但结果中未比较雌雄动物间的炎症反应是否存在差异。有研究指出,同物种不同品系间的动物对于LPS的敏感性也有差异,BALB/c小鼠对LPS较C57BL/6小鼠更敏感[6],但目前尚无LPS所致肺炎模型在不同品系或不同性别动物间的比较研究,故何种动物最适合用于构建LPS所致的肺炎模型还需要进一步证实。
2 造模方法的选择
使用LPS建立肺炎动物模型,常见的给药途径有:全身给药法[9-11]、气管内给药法[11-14]、吸入法[15-19]以及雾化法[20-22]等。
2.1 全身给药法
全身给药法包括腹腔注射法和尾静脉注射法。腹腔注射法[8,10-11]是将LPS溶液注射进腹膜内;尾静脉注射法[9]是将LPS溶液注射进尾静脉,尾静脉注射建模多使用大鼠。两种方法均是通过LPS作用于免疫系统引起全身免疫反应,而肺易受炎症损伤从而达到建模的目的。全身给药法在早期的肺炎建模中常用,但由于其诱发全身免疫反应较重,现也常用于建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及脓毒症模型。
2.2 气管内给药法
气管内给药法又分为颈部皮肤切开后气管注射法和经口气管内给药法。Conti等[13]用异氟醚麻醉小鼠后固定,颈部备皮后切开皮肤暴露气管,使用1 mL注射器向管腔内注射LPS溶液,术后消毒并缝合伤口。Brown等[12]使用经口可视化气管滴注法,将小鼠用氯胺酮麻醉后,用线将门齿固定在一倾斜60°的木板上,打开口腔并拉出舌头,将LPS溶液通过插管滴入气道。大鼠经口气管滴注较好操作,小鼠较难操作,操作不当易导致实验失败,在Su等[23]的文章中使用一种透射冷光源照射声门后直视气管的灌注方法,并研究了插管深度与溶液进入肺部部位的关系,导管插入深度为12~14 mm液体分布至双肺,插入深度为15~17 mm时,则多数分布在单肺;杨彪等[24]将此方法进行了优化,并在文章中对操作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
2.3 吸入法
吸入法主要包括口咽吸入法和经鼻吸入法(滴鼻法)。口咽吸入法[15-16]是将动物麻醉后置于倾斜的平板上打开口腔并牵拉舌,将LPS溶液滴于咽后壁并马上捏住鼻子,待动物将药物吸入肺部后松开鼻子。滴鼻法[17-19]是将动物麻醉后,吸取LPS溶液滴入2个鼻腔中,并迅速捏住鼻孔,维持20~30 s,待液体全部吸入鼻腔即可。
2.4 雾化法
雾化法需使用专用的暴露塔给药,动物不需进行麻醉,直接放入暴露塔中在清醒平静状态下吸入含有LPS的空气[20-22]。不同于其他方法,雾化法通常需要多次给药。由于需要专用的设备,使用该方法的研究较少。
2.5 不同方法间的优缺点比较
袁伟锋等[8]研究发现,气管滴入LPS后以肺组织破坏为主,表现为病理损伤显著而肿水肿相对较轻;腹腔注射LPS引起肺局部组织破坏较轻,肿水肿程度则比较显著。有研究认为腹腔注射法和尾静脉注射法不能很好的模拟肺炎发病过程,与肺部局部用药相比同样剂量下引起的肺部炎症反应较轻[11],且容易引起全身炎症反应,若剂量过大易发生实验动物的死亡,因此研究人员多选择肺部局部给予LPS建立模型。张亚平等[20]在研究中比较发现滴鼻法大鼠肺组织炎症较轻,肺部病理变化组内差异较大,气管滴入法和口咽吸入法肺组织炎症较重;雾化吸入法大鼠炎症表现为中度,组内各实验动物肺部炎症损伤程度一致,病理变化表现稳定,组内差异小。在Su等[23]研究中发现,比起气管内滴注,滴鼻法进入肺部的溶液明显较少,溶液同样分布在鼻、气管、食管和胃中,分析可能与动物的吞咽反射有关。
因此,以上几种给药方式各有优缺点:全身给药方式早期应用较多,操作方法较为简单,但相同剂量下引起的肺部炎症反应较轻,由于引起全身炎症反应易出现中毒性休克,且血中炎症细胞及炎症因子不能很好地反映肺部受损的严重程度;颈部皮肤切开气管内注射法可精确的控制给药剂量,但其切口可能会被微生物感染而出现炎症,影响实验结果;经口气管内给药法无伤口,但对操作要求较高,需准确找到声门,否则易将LPS灌入食管,使造模失败,同时可能药物会仅作用在某一叶肺叶,不能造成全肺感染[25];口咽吸入法和滴鼻法操作较简单,但进入下呼吸道的LPS溶液量不可控,可能使实验结果产生较大变异[23],同时由于药物可能在上呼吸道截留,达到相同的肺部炎症反应需要较多药物;雾化吸入法是通过自主呼吸给药,最接近肺炎发病的过程,但其对实验室设备要求较高,同时吸入动物肺部的药物量无法估算,也可能会因为不同个体的呼吸深度不同而产生个体差异。
3 药物诱导剂量的选择
LPS一般以动物体重给药,常见剂量为1~10 mg/kg,需用生理盐水或PBS配成适宜的浓度,同时肺部局部给药的溶液不宜过多,如滴鼻法一般为5~50 μL[25],过多可能引起动物窒息。 张亚平等[20]以1 mg/kg的剂量处理大鼠后可观察到口咽吸入法和滴鼻法引起的肺部炎症与气管滴入法相比明显较轻;Chen等[26]也提出,腹腔给药或静脉给药相同量的LPS溶液在肺部造成的组织损伤远不及经气管或气管内给药,故若选择以上两种方法应适当加大剂量,以确保建模的成功。LPS 5 mg/kg是相关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剂量,观察这些文献中肺组织病理切片可以发现,其肺部炎症反应严重,出现弥漫性的炎症细胞浸润,肺泡壁明显增厚,几乎无可辨认的肺泡结构,说明该剂量已导致重症肺炎,甚至可能已经出现了急性呼吸窘迫。D′Almeida等[19]使用的剂量为每只25 μg,换算成单位体重剂量仅约为1.25~1.38 mg/kg,肺部切片也观察到了较明显的炎症反应。杨东等[16]使用口咽吸入法诱导小鼠急性肺炎模型时,使用剂量为每只10 μg,按照小鼠体重换算后仅约为0.5 mg/kg,已可以观察到明显的肺部炎症反应;焦光宇等[27]使用气管滴注法建立轻型肺炎模型时,使用的剂量仅为0.1 mg/kg,处理后4 h可观察到肺组织有较多炎性细胞浸润,肺间隙水肿,但肺泡结构仍完好,结合血象结果后分析此剂量已成功建立肺炎模型。故在建立模型时,应充分考虑到动物体重、给药方式、研究目的,综合考虑后选择合适的诱导剂量。
4 评价指标
人类肺炎的诊断多依赖体查和X光检查,辅以血细胞计数、动脉血氧分数等实验室检查结果,但对于实验动物而言,界定其肺炎尚无统一的标准,虽然动脉血氧、影像检查等可在部分实验动物身上进行,但对实验室条件要求较高,大多数实验室并不具备完成此种检查的设备条件,故这些诊断标准并不能直接类推至实验动物。LPS诱导的肺部炎症反应的特征为肺水肿、肺泡-毛细血管屏障的完整性的破坏以及广泛的中性粒细胞浸润和炎症介质的释放[28],血浆蛋白和中性粒细胞渗漏到肺泡腔,并伴有细胞因子的升高,故相关评价指标主要有以下几类。
4.1 肺组织病理学检查
病理学的变化是急性肺炎模型最直观的指标之一,可直接反映肺组织炎症反应的程度。正常肺组织的特征是肺泡壁薄,偶见肺泡内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也较少;当肺组织受外源性LPS刺激出现急性炎症反应时,病理学表现为肺泡腔变小、肺泡壁充血水肿、炎性细胞尤其是中性粒细胞的浸润,严重时几乎无法辨认肺泡结构。病理学形态学检查的结果可以通过肺组织病理学半定量评分进行量化比较。Mikawa等[29]经典的肺组织病理半定量评分方法评分标准:对肺泡充血、出血、肺泡腔或血管壁中性粒细胞浸润或聚集、肺泡壁增厚和(或)透明膜形成等4项指标,分别依病变轻重评为0~4分(0分指无病变或非常轻微病变;1分为轻度病变;2分为中度病变;3分为重度病变;4分为极重度病变),总分16分,4项评定分数总和为肺损伤的总评分。
4.2 肺泡-毛细血管屏障的改变
肺泡-毛细血管屏障的完整性的破坏,表现为血液中的蛋白质及体液渗漏至肺泡腔,出现肺水肿,常通过肺组织湿/干重比值(W/D)、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liquid,BALF)中蛋白总量进行衡量。相比对照组,LPS处理组肺组织湿/干重比值明显升高,说明出现了肺水肿;肺泡灌洗液中蛋白含量明显升高,说明屏障受损后,血浆蛋白向肺泡腔漏出。
4.3 炎症反应的测量
与肺部炎症反应程度相关度最高的有三个指标:BALF中中性粒细胞数量、BALF中促炎细胞因子的浓度、肺组织中过氧化物酶的活性或浓度,其中前两者是研究LPS所致肺炎中较为多见的检测指标[30]。
在LPS诱导的肺部炎症反应中,中性粒细胞是诱导免疫反应的最重要的细胞之一,在炎症早期即可观察到其显著的升高。故炎症反应的程度可以通过血液中或BALF中中性粒细胞的数量进行评价,但测量血液指标时多代表全身炎症反应的严重程度,尤其是建模方式为腹腔注射或尾静脉注射时,血液中中性粒细胞的数量可能不能完全代表局部炎症反应的严重程度。
在LPS诱导的肺部炎症反应中,白介素-1β(IL-1β)是最早释放的主要前炎性细胞因子之一,与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协同促进炎症反应的发生,白介素-6(IL-6)也在LPS诱导的肺部炎症反应中起重要作用[31]。故在使用LPS建模的肺炎相关研究中,这三种炎症因子是测量频率最高的炎症因子。值得一提的是,焦光宇等[27]研究中虽然观察到了经气管注射LPS后,肺组织炎症反应较经腹腔注射法更为严重,但血清和BALF中的TNF-α水平在两种方法间却无明显差异,表明肺部炎症反应与细胞因子水平可能不是平行关系。
4.4 指标测量时间
指标测量时间也是实验成功的关键,过早或过晚都可能得不到较好的实验结果。美国胸科协会认为观察肺部急性炎症损伤应在给予刺激后24 h内进行,以区别肺部慢性及亚慢性损伤[30]。杨东等[18]在经口咽吸入 LPS 后的 3、6、12、24、48 h 分别处死小鼠,比较其病理学改变,发现3 h时仅出现轻微炎症细胞浸润,6 h时炎性细胞浸润明显,12 h时已无正常的肺泡壁结构,24 h时已出现明显肺实变;宣国平等[32]在比较尾静脉给予 LPS后1、3、6、12 h大鼠肺部组织切片、W/D值、肺组织炎症因子水平后,认为处理后6 h炎症反应达峰值,为观察到的最佳测量时间,处理后12 h肺组织炎症反应已较前减轻;分析两个研究在12 h炎症反应程度出现差异可能由于药物给予方式不同。有研究指出,BALF中炎性因子在4 h时已有明显升高,但24 h时已经开始下降[11];在焦光宇等[27]研究中也观察到了相同的趋势,说明若是将24 h作为测量点,可能观察时间已经较晚。
5 小结
早期肺炎研究中,常使用菌悬液建模,但研究发现此种方法建模稳定性不强,重复性不高,影响因素较多;后期作为G-菌主要毒力成分的LPS逐渐用于建立肺炎模型、研究肺炎发病机制及预防治疗药物的研发;但由于LPS仅为G-菌主要致病成分,与G+菌所致肺炎的机制有所不同,而肺炎致病菌中G+菌也不容忽视,故LPS用于构建细菌性肺炎模型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LPS用于建立肺炎模型时,给药途径较多,各方法有各自的优缺点,应根据研究的特点和实验室的条件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给药剂量方面目前尚无研究比较不同诱导剂量所致的炎症反应的强弱,且受给药方式影响较大,而不同研究间由于操作过程、实验研究条件等因素的不同,无法进行横向比较,故仍需进一步的探索。动物实验中建立肺炎模型,通常由于给药剂量较大,引起肺部较重的炎症反应,但实际上人群中轻型肺炎发生率较高,多少剂量可以达到模拟轻型肺炎的发生,以及动物的轻型肺炎与重型肺炎如何界定,仍需进行更多的研究。只有动物模型更加地接近临床疾病发生发展情况,才能为药物研发、疾病预防、临床指导用药等方面提供更多的证据支持。